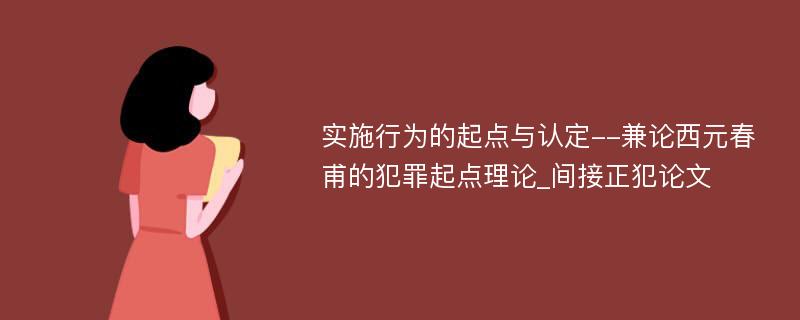
实行行为的着手及其认定——兼论西原春夫的犯罪着手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兼论西原春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08)04-0060-07
由于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已经着手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但对“着手”的含义没有作出界定,因而,导致在理论界众说纷纭。日本著名刑法学家西原春夫先生对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及特殊犯罪的着手认定均有着深刻的研究。对于我国学界进一步探讨该理论问题有着很高的启迪价值。本文系笔者学习西原春夫先生的《犯罪实行行为论》的点滴体会和肤浅见解,期待同仁们指正。
一、实行行为及其着手的理论争议
在研究实行行为着手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弄清实行行为的含义及内容。我国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实行行为,即实施符合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行为”[1]179;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直接威胁或侵害某种具体社会关系而为完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行为”。[2]这些观点都只是界定了:“实行行为是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由于不同的犯罪其客观方面的行为内容不同,所以对该概念的界定不免有些模糊不清。西原春夫先生认为,“实行行为原本是作为构成要件之核心的行为,它必须具备每个构成要件中所描述的各构成要件要素。”“每个实行行为必须包含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内容。虽然杀人的实行行为并不包含人的死亡这一结果,但是,它必须包含足以引起这种结果的危险性,而且只要这种危险性就足够了”。谈到实行行为的实质,西原先生指出:“当构成要件的形式以禁令为内容之时,实行行为的实质基本上是作为。但是,由于不作为也可以侵入禁令之中,在这种场合,实行行为的实质就是不作为。……当构成要件的形式以命令为内容时,实行行为的实质则仅限于不作为”[3]13-14我们认为,西原先生的观点,较好地界定了实行行为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内容,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但其“实行行为必须包含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内容”,我们不敢苟同,原因是犯罪的预备行为,特别是接近实行行为的预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危险,如果笼统地把“包含法益侵害之危险”作为衡量实行行为的标志,就可能使实行行为侵犯预备行为,不适当地扩大了实行行为的范围。笔者认为,犯罪的实行行为,应当表述为,它是指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害刑法保护法益,造成危害结果或造成危害结果危险性的犯罪构成必须的客观方面的行为。
在弄清实行行为的概念后,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实行行为的着手,否则,则可能致使实行行为的前移或者拖后,导致犯罪预备形态与未遂形态定性错误。由于各国刑法都没有规定着手的含义,这就为理论界探讨着手的概念留下极大的空间。关于犯罪的着手,理论界概括为三种:
(一)客观说
即以客观行为为标准,主张从客观事实出发来确定着手的含义,认为衡量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不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应以行为本身的客观性质为依据。该说基本上立足于客观未遂理论,认为未遂犯之可罚性基础或刑罚理由,在于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在客观上有可能导致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或者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侵害之危险。其中有形式的客观说和实质的客观说。(1)形式的客观说。即从形式上观察,指开始实施相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为实行的着手。如日本的团藤重光认为,“所谓实行,应当是符合基本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开始,就是实行的着手”。[4]在日本,坚持该观点的还有小野清一郎、大塚仁等。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观点使处罚过于狭窄,因而在内容上应加以修正,主张不仅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实行的着手,而且实施与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有密接关系的行为”或者着手于犯罪构成要件定型的行为之一部分者。例如,植松正指出:“关于着手的意义,从客观的方面下定义者,认为实现构成要件的全部或部分或者与此密接的事实是着手”。[5]529(2)实质的客观说。即从实质上观察,指为完成犯罪所必要的行为,或者指使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发生现实危险性的行为。该说以未遂犯的可罚性之实质的根据为判定着手时间的标准,又有现实危险说与具体危险说。如日本的大谷实主张现实危险性说,“实行的着手,应当认为指含有至于发生构成要件的结果之现实的危险性行为的开始”。[5]531具体危险性说认为“未遂犯不是抽象的危险犯,而是具体的危险犯”,“结果发生的具体危险”发生了时,是实行的着手(迫切性说)。[5]532
(二)主观说
该说认为,判断实行的着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为标准,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性格,所以实行行为着手的判断,不能脱离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只要行为能够表现出行为人的危险性格,或具有完成犯罪的犯意表动时,犯罪即已着手。如日本的宫本英修说:“犯罪实行的着手是有完成力的犯意的表动,又这种犯意的表动解释为犯意的飞跃表动,详言之,即实施了一段飞跃的紧张的犯意的表动。”[5]533
(三)折衷说
即主张“从行为人的整个计划来看,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是否已经迫切”为标准,认定犯罪的着手。它从行为人的整个犯罪计划,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加以个别评价。如日本的木村龟二主张:“以行为者‘整体的计划’为基础,在对该构成要件的保护客体,至于直接危险化的行为中,犯罪的意思被明确地表现时,认为有实行的着手。”[5]534德国学者威尔泽尔认为:“实行的开始的评价,立于个别的行为者的计划这样基础之上进行,不是从假定不知犯罪的计划的观察者的立场进行。……实行的开始,常常依存于个别的行为者的计划。”[5]535受上述学说的影响,1975年施行的西德刑法第22条规定,当“根据行为人关于行为的认识,直接开始了构成要件的实现”时,未遂犯成立。这就较明显地体现了折衷说的思想。
客观说以行为本身的客观性质来确定着手的含义,标准较明确,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对目前研究实行行为的着手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该说在强调客观行为的同时,否认了主观犯意是犯罪构成的重要条件,容易导致客观归罪的错误。例如,行为人在他人面前挥刀舞剑,能否就这一行为认定为着手呢?实际生活中,在他人面前挥刀舞剑,教给他人学武术的情况是有的,着手实施杀人、伤害他人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撇开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单就客观行为的性质是难以认定犯罪的着手的。再说,以“部分说”、“密接说”、“危险说”作为认定着手的标准,仍有模棱两可之嫌,没有界定清楚什么是部分行为、密接行为、危险行为。正像大塚仁所说,“扩张着手的范围到实施与实行行为密接的行为时,很容易使概念不适当地变得暧昧,恐怕要招来预备、阴谋与未遂区别的困难吧!因为毕竟要进一步明确到何处才是与实行行为密接的行为。这样就应该彻底根据实行行为的开始是否存在来决定着手的有无。”[5]529因此,这种客观说不但忽视了主观方面在认定犯罪着手上的作用,而且也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客观标准,不容易划清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界限。
主观说坚持以确认犯罪意思的行为或有犯意表动的行为,为实行犯罪的着手,纠正了客观说否认犯罪意思是确认犯罪着手的重要因素的错误,有其合理性,但单纯以主观犯意或犯意表动为标准,谈论犯罪的着手,不免陷入错误的极端。倘若按此观点推论,那么,犯意表示和犯罪预备行为,都可以说是犯意的表动,难道能认定为犯罪的着手吗?显然不能。因此,主观说实质上没有明确认定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往往把仅有犯意表动的犯意表示错定为犯罪未遂,导致主观归罪,也容易把犯意表动的——犯罪预备行为误定为犯罪未遂,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且不利于行为人在预备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与客观说相比,有着更多的缺点和弊端。
折衷说能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认定着手的起点,克服了客观说与主观说各自的片面性,有一定的综合性和进步性,战前、战后得到德国刑法的认可,在日本学界也成为主流观点。但是,该说仍存在着模糊性和将犯罪着手的前移性。正如西原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在这种学说的内部,不是将应当考虑的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仅仅限定在‘故意’上,而是扩大到‘整个计划’,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自不待言,这个‘计划’之中除了包含行使的目的、营利的目的等所谓主观违法性要素外,还包括着‘故意’。但是,为了确定实行着手的有无,仅仅以故意的有无来判断,会出现不充分的场合。即使同样是小偷怀着盗窃的故意而从外侧触摸衣服口袋这样的行为,在确定被害者之后,意图确认钱包的位置而实施这种行为的场合,与在物色被害者的过程中实施这种行为(踩点行为)的场合,应当认为两者的结论是不同的:前者是未遂,后者是不可罚的预备,因此,有必要将实行计划的内容涵盖到故意的内部之中。”[1]11-12即是说,折衷说将“着手”的主观方面界定为“整个犯罪计划”、“故意”,是不确切的,因为犯罪预备行为是其犯罪计划的内容之一,预备故意也属于“故意”的范围。因而该说仍有将实行行为的着手提前的嫌疑。
笔者认为,界定犯罪的着手,应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持犯罪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相统一。即犯罪的着手,是指行为人认识到犯罪预备行为已就绪,实施实行行为的条件已成熟,主观上具有了实行故意,客观上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危害结果或危害结果危险性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它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行为人具有开始实施实行行为的故意;二是具有实施某种犯罪构成客观行为的起点。由此可见,犯罪的着手绝不是犯罪预备行为的终点,而是实行行为的起点。它标志着预备行为已经终了,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开始实行,犯罪已由预备阶段转入实行阶段。因此说,犯罪着手不是界于犯罪预备阶段与实行阶段之间的一个独立阶段,而是实行阶段的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
二、一般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
由于犯罪复杂多样,各式各样的犯罪就有着各式各样不同的着手,这就决定了理论上不可能找出一个公式作为认定着手的标准,必须结合具体犯罪,从犯罪构成上具体分析。
张明楷教授主张“应根据不同犯罪、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要考察行为是否已经接触或者接近犯罪对象;行为人是否已经开始使用犯罪工具;行为人是否开始利用了所制造的条件;所实施的行为是否需要其进一步的行为就可以造成犯罪结果,如此等等”。[6]对于上述观点中列举的几个方面应进行综合分析,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认定。如,有的行为虽然已经直接接触到犯罪对象(如强奸行为人面对被害妇女先进行调戏)但不能认定为着手;相反,有的行为虽然未直接接触到犯罪对象(如远距离向被害人射击)却可能是着手;有些情况下,行为人使用了工具(如撬门别锁的盗窃),标志着犯罪已着手。有些情况下使用了工具(如带着运输工具,走向作案场所),未必就是着手。还有些情况下,利用了制造的条件,也未必就是着手,如掐断电源,准备盗窃,其掐断电源的行为,只能说是预备行为。所以,张明楷教授主张对具体案件应综合分析,采用不同的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实行行为的概念、“着手”的含义及特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犯罪的着手:
(一)根据实行行为的不同,区分不同犯罪的实行行为的着手
我国刑法对犯罪构成实行行为的规定可分为四种情况:单一的实行行为、复合的实行行为、择一的实行行为和并列的实行行为。
1.单一实行行为的着手。单一的实行行为是指某些犯罪构成客观要件只要求行为人实施一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即可完成的犯罪。如杀人罪、盗窃罪等。对该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应以故意开始实施单一的实行行为为着手。如以刀、枪为凶器的故意杀人罪,行为人面对被害人拔刀、举刀或举枪、抠动扳机的动作就是杀人实行行为的着手。但应当指出,单一的实行行为不是指单一的动作,而往往是一系列密切相连的动作组合而成的(一个持刀杀人行为,是由拔刀、举刀、刀砍下组合而成),其中最初的动作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
2.复合实行行为的着手。复合的实行行为是指某些犯罪构成客观上所要求的外部表现为前后衔接、内部表现为手段和目的相联系的两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所合成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如抢劫罪、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分别是由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行为、拐骗行为与抢夺财产行为、奸淫行为、贩卖行为结合起来的复合行为。对于复合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是依哪个行为的开始为着手呢?一般认为,应以方法行为的开始为实行的起点。如强奸罪,只要行为人开始对被害妇女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行为,就应认定为强奸罪的着手,不应以开始奸淫时为着手。
3.择一的实行行为的着手。择一的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某些罪的实行行为列举了几种行为,不论行为人实施其中的一种行为或多种行为的,仍然成立一罪的实行行为(即属于选择罪名的犯罪)。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罪,只要行为人开始实施其中之一行为的,如开始非法制造枪支、弹药的,就是本罪实行的着手,并不要求每一行为都要开始实施。
4.并列的实行行为的着手。并列的实行行为是指两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同时实施才能构成的一个实行行为。它的着手,必须两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都开始实施,才能认定为犯罪的着手。如,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只有“冒充”和“招摇撞骗”都开始实施时,才认定为着手,只“冒充”不“撞骗”或者“未冒充”只“撞骗”,均不能认定为本罪的着手。
(二)把握预备行为的外延,认定犯罪的着手
认定实行行为的着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效的方法,就是借助犯罪预备行为,从犯罪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区别来正确认定着手实行犯罪与否。”[7]通常情况下,对准备犯罪工具、拟定犯罪计划、了解被害人的住址、行踪、生活规律、物色共同犯罪人及分工、搞犯罪实验、排除犯罪障碍等,均能认定为预备行为,没有什么争议,但对行为人“携带作案工具进入作案现场”、“尾随被害人行为”、“守候被害人行为”、“几乎接触到被害人的行为”、“寻找被害人行为”等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上述各行为已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等造成威胁、存在较大程度的危险性,应认定为着手;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尾随行为”、“守候行为”、“寻找行为”等都是为实行行为选择适宜的时间、地点,寻找犯罪对象的预备行为。尽管上述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或财产具有较大的危险性,但由于该行为不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所要求的行为,故不能认为是实行行为的着手。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只有当行为人认为作案时机已到,面对被害人或财物,开始“动手”的时候,才可认定为实行行为的着手。否则,就会重蹈前面提到的“密接说”、“危险说”、“紧迫说”的覆辙,缩小了了预备行为的外延,提前了着手的时间,扩大了实行行为的范围。
(三)以作案的时间、地点、案件性质,作为判断某些犯罪着手的标准
对于同一种犯罪,由于作案的时间、地点不同,判断犯罪着手的标准也不同。如同样是盗窃商店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在商店营业时间步入商店,寻找时机行窃,属于盗窃的预备行为。只有行为人开始实施破坏货柜或者把手伸向货柜,才能认为是盗窃的着手。如果行为人在晚上商店停止营业后行窃,则只要作出破坏商店门窗或撬门别锁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盗窃的着手。原因在于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对财物的控制力度不同,所以着手的起始时间不同。
对于同一种行为,即使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同,因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导致行为性质不同,因此认定是否着手必须借助于行为的性质来衡量。如非法入室行为,对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来讲,一入室就是既遂,不存在预备与未遂问题;对盗窃罪来讲,非法入室就是着手行为;如果入室是为了诈骗、强奸、杀人、伤害等,这种入室行为,就是实施这些犯罪的预备行为。
三、几种特殊形式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认定
(一)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
关于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是一个理论上争议较大、实践中做法不一的难题。对此复杂问题,西原先生曾作了全面、深度的研究。他在《犯罪实行行为论》中,介绍了日本学界相互对立的观点及其本人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应当在利用者的利用行为中认定实行的着手。例如,牧野英一主张:“依据实行的观念,实施意味着正犯的行为阶段的行为之时,就应当就利用者对被利用者的利用来论述实行的着手。”宫本教授也认为“利用者着手利用被利用者,亦即着手犯罪的实行”。[3]198
第二种观点认为,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在于被利用者的行为开始之时。例如,弗兰克认为,“间接正犯是通过中介者实行犯罪的形态,因此其实行的着手不能早于中介者的着手。”该说认为,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的实质在于现实地引起结果的被利用者的行为。该说得到了日本的判例、少数学者以及德国通说的赞同。其理由是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的实质在于现实地引起结果的被利用者的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将间接正犯区分为利用有故意的工具与利用其他的工具。就前者而言,认为被用者开始行为之时是实行的着手;就后者而言,认为实行着手在于利用者的行为开始之时。[1]209这一观点得到德国威尔泽尔等权威学者的认同,西原先生也赞成,主张:“间接正犯的实行着手并不总是在利用行为开始之时;在某些场合,在被利用行为开始之时也可以承认实行的着手”,并认为“在单纯举动犯的场合,利用者的利用行为通常是预备行为;在结果犯的场合,则根据被利用者实施预定行为的盖然性的高低,要么认为被利用者开始实施行为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要么认为这并非实行行为的着手而只是预备行为。而且,在后者的场合,我认为在幕后利用和支配被利用者之行动的利用者的行为是间接正犯的实行行为。当然,被利用者实施预定行动的盖然性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不同的个案,例如,在利用有故意的工具的场合,盖然性就很低,也可以通过某种程度上类型化的方法来考虑问题。”[1]220-22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实行行为的实质和特征,把“利用行为”牵强附会地解释为实行行为,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利用行为”本身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危害结果或结果的危险性,造成危害的恰恰是“被利用行为”。因此,这种观点即使在间接正犯发祥地——德国,至今仍没有达到上升为通说的地步。第三种观点结合具体间接正犯的不同情形,提出了折衷式的观点,即对一部分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利用行为的开始实施为标志,另一部分的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以被利用行为的开始实施为标志。这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对该问题的研究更具有深度,更启发学界的反思,尤其是认识到部分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以被利用者的行为实施为标志,具有科学性。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把一部分间接正犯的着手界定为利用行为的开始实施,仍然背离了实行行为的本质特征,况且,以“被利用者实施预定行动的盖然性的高低”区分不同的着手,仍有模棱两可之嫌,把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给司法实践造成困惑。因此我们也不赞同第三种观点。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不论利用哪种“工具”的间接正犯,其实行行为的着手均应以被利用行为开始实施为标志。理由是:间接正犯是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无罪过的人、合法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本人不直接实施实行行为,严格说来,它不是正犯。之所以称之为“间接正犯”,是因为被利用者不具备犯罪主体资格或不发生共犯关系,利用者相当于正犯,可以说是法学上拟制的正犯。被利用者的行为,应当视为(或者拟制为)利用者的行为。倘若以利用者的行为作为实行行为的着手,利用行为本身不会造成危害结果或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不具有实行行为的本质属性。再说,真正的正犯,利用工具实施犯罪都是以工具的开始使用作为实行行为的着手。间接正犯也是利用工具(不过是活体工具),只有当活体工具运作时,才能认定为着手,因此说,间接正犯实行行为的着手,应以被利用者的行为开始实施为标志。
(二)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
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因设定行为→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实施结果行为→危害结果。这个链条说明原因自由行为构成的犯罪,其行为是由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组成的,那么,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是以原因设定行为的开始为认定的标准呢,还是以结果行为的开始实施为标准?这是理论界争论较大而且至今未达成共识的棘手问题。对该问题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有两种:
一是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应当“在原因(设定)行为中寻求实行的着手时间”。[1]305主张这一观点的显然是固守了“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的原则,认为实施结果行为时,行为人丧失了责任能力,但在原因行为的设定时,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所以,应在原因行为中寻求着手的时间。例如,在日本“许多教科书中都引用了企图利用自己的酒癖,在醉酒之后杀人,因而故意饮酒而杀人的案件,在这种案件的场合,就不得不说饮酒行为就是杀人的实行行为。”[1]132
二是以西原先生为代表的折衷说。“认为根据行为人的整个计划,法益侵害的危险具有必然性或者具有与此相近的盖然性之时,就是实行的着手。如果根据这样的标准,那么原因自由行为实行着手的时间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在有的场合,实行着手的时间在于原因设定行为之时;在有的场合,实行着手的时间在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中直接引起结果的行为之时。”并且举例说,在故意作为犯的场合,正好与通常的犯罪的场合一样,正如为了杀人而准备刀、为了盗窃而接近财物那样,开始直接的引起结果的行为之时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之时;在不作为犯的场合,开始原因设定行为之时就是实行的着手之时。”[1]141
第一种观点,为了遵循“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的原则,把原因自由行为实行的着手,提前到原因设定阶段。但从情理上分析,假若行为人在招致责任能力丧失之前存有某种犯罪的故意或过失,但行为人在醉酒或药物麻醉后无责任能力的状态下,没有实施结果行为,或者因醉酒或药物麻醉而昏睡不醒,那么,对其原因设定行为,就认定为着手,显然不符合情理,世人难以置信。例如,司机认为自己饮酒后不影响驾驶,当其醉酒后,认为控制能力大大减弱而自动放弃驾驶或者他人阻止其驾驶,那么,醉酒仅仅是一种状态,不会导致交通事故,司法实践中,哪一位法官也不会以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认定醉酒司机为交通肇事罪的未遂。再说,也不符合实行行为本质的要求,而原因自由行为的原因设定行为(如醉酒行为)不会产生危害结果或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倘若坚持这一立场,势必导致未遂犯范围的扩大,甚至把本来不构成犯罪(如醉酒后的昏睡行为)误定为犯罪未遂。因而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
第二种观点,把原因自由行为构成的故意作为犯的着手,以结果行为的开始实施为标志,完全符合实行行为的特征,并且认为在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不同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只要在“行为”之时存在就够了。笔者赞成西原先生这一部分观点。但对其原因自由行为中的不作为犯,以原因行为设定时为实行的着手,本人认为不妥。原因自由行为中的不作为犯也是由原因设定行为+不作为行为(结果行为)构成的。如果行为人单纯地设定了原因行为,尚未到履行作为义务的时刻,则不能认为犯罪已经着手。如铁路上的扳道工,喝醉酒昏睡不醒,但距其扳道叉的时间还有较大的间隔,到了该扳道叉的时刻,他已醒悟,履行了扳道叉的义务,难道能以其原因设定时为犯罪的着手吗?显然不能。
综上,笔者既不赞成第一种观点,也不完全同意第二种观点,原因自由行为实行行为的着手,应当一律以结果行为的开始实施为标志。理由之一是,只有结果行为才是危害结果发生或者威胁着刑法法益的直接原因,才符合犯罪构成的实行行为的特征,坚持此点,才能认真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否则,就会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未遂犯的范围。理由之二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是认定一般犯罪应遵循的原则,在原因自由行为中,结果行为未必与责任能力同在。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之所以确立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但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设立原则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因此我认为与其对实行行为做牵强的扩大解释,不如径行承认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8]西原先生与左伯教授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责任能力在‘实行行为’之时不存在也可以,只要在‘行为’之时存在就足够了。”“应当意识到实行行为是以有责任能力状态下伴随着故意、过失的意思决定为基础的。换言之,无责任能力的人的手脚运动并不是行为,而是应当将包括这些运动背后的责任能力者自己有意的主体态度在内全体行为视为行为。本来,所谓行为并不仅仅是指自己身体的运动或静止,而是指超越这种运动或静止,被赋予了社会意义的存在。”[1]130-141既然刑法中的行为是规范评价上的行为,赋予社会意义,因而就不能单纯地以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概念去把握。只要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就可以认定原因自由行为人对其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三)不作为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
不作为犯是指通过不作为来实现犯罪的场合,其内容是违反作为义务。为确定违反作为义务,首先行为人必须具有应当保证使结果不发生的地位(保证者的地位),具有保证义务。这就涉及到作为义务何时产生,何时不履行义务才是不作为犯罪的着手问题。
对作为义务产生的时间,由于不作为犯的种类不同,其产生的时间不同。对于真正不作为犯应当认为在有作为要求之时就会产生作为义务或者认为作为义务产生于行为人具有保证人地位之时。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如果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引起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作为义务随之产生;如果没有行为人的作为就会产生法益侵害危险的场合,作为义务也会产生。
作为义务产生之时能否认定为不作为犯实行行为的着手?换句话说,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着手如何认定呢?对此,学界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表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就是不作为犯的着手”(《法学杂志》,1983年第3期)。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从形式上来说,只有在这种作为义务违反的结果——法益侵害的危险迫切的阶段才能认定不作为犯的实行着手时间,如果母亲怀有杀意而不给孩子喂奶,那么,即使一、两次不喂奶,也可以认定违反了作为义务,但是,据此并不能立刻说是实行的着手。如果母亲继续不喂奶,那么,即使孩子没有立刻死亡,只要到了出现生命危险的阶段,就可以认定为实行的着手”。[1]19
对第一种观点,笔者持反对态度。因为行为人“表示不履行”并非真正不履行或者说未到该履行的时候而表示不履行。例如负有扶养义务的行为人,开始表示拒不扶养,但被扶养人暂时不需要其扶养(如子女口头上说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但父母有工资收入、生活能够自理时),就不能认定为不作为犯的实行着手。对第二种观点笔者持赞成态度,即行为人作为义务产生后,开始不履行并不意味着实行的着手,只有到不履行义务将要产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严重危害或严重威胁时,才能认为是不作为犯实行行为的着手。如前述母亲杀婴案。所以,对不作为犯的实行着手的认定可否概括为:(1)从时间上,行为人到了应该开始履行义务的时候,即客观上不履行义务将使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而行为人仍不履行;(2)主观上具有不履行义务的故意或者过失。只有坚持该履行义务的时间条件和主观方面,才能准确地把握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的着手。
收稿日期:2008-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