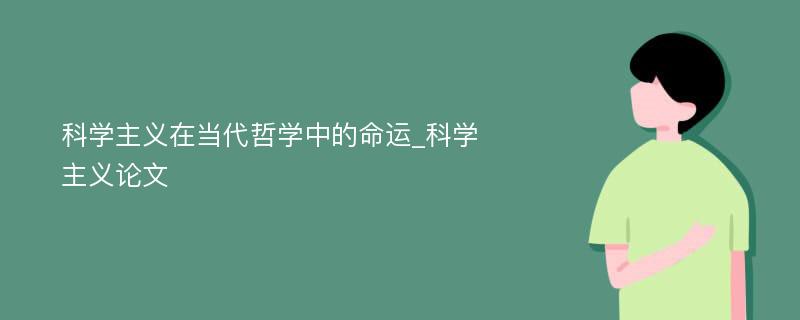
科学主义思潮在当代哲学中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804(2006)03-0014-04
一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在人类文化的影响
科学主义与科学是两个紧密相关的概念。科学主义思潮是与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在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是合而为一的,科学已经有了萌芽。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5、16世纪。科学本身亦构成了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方面。启蒙运动以民主、平等、自由、科学、进步等为基本的理念,其中蕴含着普遍的价值取向:它在某种意义上以民主、自由等价值原则否定了权威主义、神学独断等前近代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本质上旨在实现价值观念的转换。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科学也相应地被赋予某种价值的规定。科学的这种价值内蕴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理论前提之一,并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展开而逐渐突出与强化。科学主义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形上的信念和原则。在这一维度上,科学主义的特点在于将科学泛化为一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并相应地将科学引申为构造的原理。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世界似乎可以被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规定,而这种规定同时又成为以科学构造世界的前提。胡塞尔曾对此做出过批评,认为“伽利略把世界数学化了”。[1] 自然科学的方法往往被理解为科学的核心,实证的观念、数学化的追求则常常被普遍地引向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有关人生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例如,奥斯特瓦尔德就认为,快乐的程度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数学公式,即“G=(E+W)×(E-W)”[2],其中G表示快乐的程度,E是自愿消耗的能量总数,W是被迫耗费的总能量,快乐及其程度属人生哲学的问题,在此,物理学和数学便被引入了人生领域,并成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成为了文化之王,成为评判一切文化形态的标准。科学主义以科学化为知识领域的理想目标,并多少表现出以科学知识消解叙事知识与人文知识的趋向,与之相联系的是以科学为解决世间一切问题的万能力量。科学主义把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认为“人的行为依赖于知识,而自然秩序和有关的知识则不依赖人的活动”,[3] 科学的方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方法。刘明根据韦氏英语大词典进行了考证,认为“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和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果地被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4] 对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绝对信任与崇拜,激发了西方世界认识自然、探求规律的热情,大大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领先包括中国在内的文明古国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科学主义的形式下,科学成为了一种信仰的对象,一种神。科学的公式代替了诗意的光辉,机械的操作扼杀了生命的涌动,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密德格雷(Midgley)曾认为,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中,科学有时充满了以往由宗教来满足的需要。科学常常被规定为真理的化身,并异化为独断的权威。科学的异化这一现象之后所隐含的是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技术与生活等多重紧张关系,导致了二重知识、二重文化、二重领域的疏离和对峙,它不仅导致了文化的冲突,而且也引发了存在的分裂。这给人类文化的多样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 科学主义思潮在当代的遭遇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化过程的逐渐完成,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的角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大多数的思想家对科学主义有了更多微辞,对科学的过速膨胀发展的后果表示忧心。他们主张在发展科学的同时,重建人文精神,重提人文关怀。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等批判哲学家不无忧心地指出,技术理性“对自然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5] 爱因斯坦也对科学主义思潮的膨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6]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原子弹的爆炸、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出现的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和疾病使得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究竟是在给人类造福还是在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是人性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剥夺?自然界的一切除人之外的事物是否也有其生存的发展的权利?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是否真的可广泛适用于人类文化的其他领域?科学似乎由原来的神变成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科学主义遭到了来自其内部和人本主义者的广泛批判。
一方面,科学主义思潮内部逐渐对其自身原来的某些原则进行了淡化,不断地吸收人本主义的某些思想,以应对当前的困境。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库恩在其不朽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范式这一概念及其在科学史上的更替规律来对科学理论的进步进行了解释,用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来体现新旧科学理论之间的差别。科学哲学家们不再主要关注科学理论的语言和其静态的、凝固的结构,相反,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家共同体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因素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地肯定。另一位科学哲学家费伊阿本德则淡化甚至取消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认为任何用固定的观念和法则来定义科学都是行不通的。“它否定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性,它使科学更少适应性而有更多的教条,”[7] 任何非科学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值得科学汲取的思想观念。科学本身并不完美,在许多方面同宗教、神话等非科学形态一样带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因此“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7] 总之,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对于人自身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共同体意识等因素有了更多的关注,形而上学问题又悄悄地回到了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中,甚至在瓦托夫斯基那里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形而上学蓝图论,科学主义中的人文因素日益得到彰显,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趋势也更明显,而且愈来愈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的各流派为了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压制而奋起对科学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批判。针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作用和地位的彰显和对人的本质的忽视和压制,人本主义哲学家极力弘扬人的本质、人的生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合法地位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它们拒绝承认科学主义的凌驾一切的霸权话语,主张消解一切具有特权的传统观念,要求把科学从人类文化的神坛拉下来。
新康德主义的哲学从方法论上对科学主义模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挑战。针对科学主义所提出的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适性的观点和“统一科学”的计划,也即认为自然科学的说明或解释的方法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去的观点,文德尔班把康德在“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之间所做出的区分发展为在“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所做出的区分,“事实世界”就是表象(现象)世界或经验世界,“价值世界”则是人的主观意识世界。在“事实世界”中有许多表象依据“因果性”、“必然性”等先验的范畴而相互联系,彼此依属,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事实命题或知识命题,关于它们的判断都是逻辑判断。在“价值世界”中表象依据“价值规范”与认识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发生关系。知识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与价值有关的问题,也受价值观念的支配或影响。李凯尔特追随文德尔班,坚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对立,强调“价值”是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范畴。他断言“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着,而只能说它们有意义或没有意义。”[8] 他们通过证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来反对科学主义的“统一科学论”,为人文科学争取地盘。早期的解释学思潮中,德罗伊森(J.G.Droysen)把自然科学的目的归结为“说明”(explanation),而把历史学的目的归结为“理解”(understanding)。狄尔泰则把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真正目标,指出人文科学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对象是既存的,人文科学的对象是构成的;自然科学的说明或解释遵循因果决定论原则,人文社会科学则到处渗透着人的自觉意识的影响,人文科学和方法只能是“移情式的理解”,而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他们从方法论上对科学主义的“统一方法”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另外,存在主义哲学从社会的层面对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存在主义的哲学流派标榜关切人的善,尊重人的价值,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主张非理性的临界体验,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造就,对科学技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严厉斥责现代社会的科学文明放弃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追求,忽视了人的真正的内在生活世界,放弃了人类情感、价值、意念等重要方面,只为人类留下一个冷冰冰的“科学世界”,把欧洲文明送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他们认为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在对宗教神学的颠覆和对人的力量的肯定的同时,也蕴含了某种人文的关切。但随着科学向生活世界和人生领域的无孔不入的渗透,它似乎又趋向于将人非人化。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9] 因此,海德格尔主张,通过弘扬艺术、诗歌来消除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神化。
科学主义思潮在后现代思潮的猛烈批判下,已经产生了一些极端的后果,例如极端的反科学思潮,也即把由于对科学的滥用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归结为科学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特征,从而从根本上拒斥科学、反对科学。这样一种思潮同科学主义思潮一样是片面的、不符合人类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需求的。
三 后现代科学的状况及前景
实际上,后现代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科学,把科学视为是一无是处、只会带来灾难的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大多数人认为,后现代科学不应像现代科学那样将物质与意识,事实、意义与价值,以及科学、道德和真理割裂开来。现实世界遭遇到的种种危机,部分就是由这种割裂造成的。割裂的根源主要在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片面性。后现代科学的发展必须克服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片面性。因此,后现代科学不是还原论的、反理性的或绝对主义的,而是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综合性的和协同学的。尽管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相对主义的,但也同时带有辩证法倾向。这是他们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向前现代时期的回复。正因为如此,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并不主张完全否定现代科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坚持认为后现代绝不是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时代。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只是它主张迄今为止人类所接受的东西都必须被怀疑,即便它只有一天的历史。“后现代主义的‘后’字只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10] 因此现代科学不论有多少副作用,人类都将永远需要它。不管今天的科学悲观主义如何激烈地主张驱逐科学回到水磨和油灯的时代,人类都会一如既往地发展科学。只是在利用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及时去除科学异化中的负面效应,以便更有效地迎接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到来,让科学重新拥有更多的人性。换言之,后现代科学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防止或杜绝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变成电脑控制的全自动化工厂的看管者;在个人命运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支配,拥有更多空间自主权的同时,防止信息通讯专政、文化专政和电脑对于官僚体制与军事帝国主义起到的强化作用;在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需求的同时,要预防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以及失业状况的恶化;在进行遗传工程的同时,要严防毁灭性病毒、退化变异的产生和人体的退化;在消灭饥饿、灾荒和减少疾病的同时,要防止贫穷国家的人口爆炸和有限资源的无节制滥用。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繁荣服务,同时又坚持一种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决不纵容作恶,竭力推动人类进步。他们并不一味地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而是对科学持一种肯定的理性态度。他们认为,科学只是对有限对象的有限认识,还有许多科学没有认识到的或不能很好认识的对象,但是,科学是对某些对象的正确认识;虽然科学方法并不能保证我们所获得的科学认识是绝对正确的、确定的,但是,它能够保证科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具有相对真理性的知识体系;科学方法虽然并不是普遍有效的,但是,它可以视具体情况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中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科学持批判的态度,坚决杜绝对科学的盲目崇拜,认为人类的能力再大,科学的力量再强,也不能迫使自然做它不能做的事情,如制造永动机等。“事物只做它们被允许做的事,从不会做它们不能做的事。”[11] 不仅如此,对于科学,还存在数学上的不可能性、物理上的不可能性、材料上的不可能性等;对于技术,它的单纯利用不能超越增长的极限。总起来说,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否认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推动作用,只是从科学、技术的伦理价值负效应出发,对科学技术进行人文主义批判,指出科学、技术发展并不必然将人类导向幸福的彼岸,科学、技术进步自身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进步安全、生存,相反,有时还有损于这些保证人类幸福要素的实现。可以说,西方绝大多数对科学、技术进行人文主义批判的思想家就持有这种态度。如,海德格尔主张用弘扬艺术的方法来消除对科学、技术的神化;弗洛姆主张用人道化技术替代异化的技术,马尔库塞主张用历史的合理性改造工具的合理性等,均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进一步反思启蒙运动和现代性,以及科学主义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科学主义成了人们反思的对象。国内学界也曾兴起了一阵反思科学、批判科学的热潮。一时间,科学由人执著追求的对象变成了人人深恶痛绝的唾弃物。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科学主义在当前还是具有其他任何思潮所不具有的强大的渗透力,而且它已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中。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也应用于由千夫共指的局面转向更多的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们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来进行,要谨慎从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可以说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还是非常迫切的。从整体上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素质不高,还有数亿文盲。在这样一种国情下,我们大张旗鼓地对科学主义进行批评确实是有些过分夸张了,虽然在五四时期我国曾有过对赛先生的宣传与推崇,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在这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而且在历史上我国的科学主义思潮似乎还从未在国民的思想形态中占过上风,对科学的推崇乃至崇拜就更说不上了,可以说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和艰难。因此,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人的后面叫喊着要反对或对付科学主义,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科学主义思潮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我们也不能不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一方面要强调科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把科学看成是万能的,以至于把科学视为替代上帝的另一种崇拜物,或者说推行自然科学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话语霸权。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自身并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进步、生存,相反,有时由于人类对科学的滥用而有损于这些保证人类幸福要素的实现。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深化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念,清除唯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认清和避免科学技术的负效应,明了科学技术进步对于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意义,消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弘扬科学文化、人文精神,让它们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种建设性地对待科学主义思潮的态度,这种态度和观点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一致的,应该大力提倡。
总之,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生存方式,科学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彰显,但人的存在除了像科学那样以概念符号等形式描述、解释世界之外,还必须以反思、理解等形式展开价值追问和人文观照。这样一种人文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只有“科学和艺术携起手来,人类活动的最高动机便达到了,人类行为的真正源泉便唤醒了,人类天性的最高功能便有保证了。”[12]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对任何一方的过分彰显或过分抑制都有害于人类人文的丰富性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今天我们谋求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二者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文化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