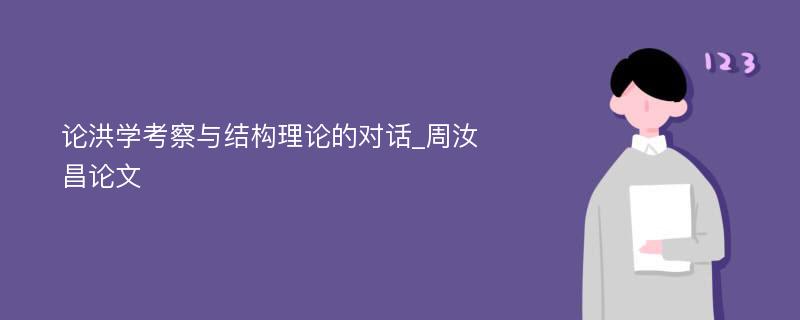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结构论文,探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拙文《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在《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刊出后, 被人大报刊复印中心转载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6期),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 陈维昭先生的鸿文《“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即是直接来回应的。陈先生将他这篇大稿寄给我,并在信中如是说:“我……总以为,真正的学术品格是目前红学所最需要的。问题的提出、讨论的方式、对话的姿态等都要求具有一种真正的红学品格。我曾以呼吁‘学院派’的出现去表达这个意思。21世纪的红学应是‘学院派’的红学。”并说:“又考虑到您那篇大作是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现斗胆请您推荐给该学报……”自拙著《石头记探佚》出版以来,愿意就“红学探佚学”作专门的、较深层次的对话讨论,这是第一篇。此前虽然也有某些文章涉及红学探佚,但多属“表态性话语”而不肯深入,更缺少“学院派”的文风学风。因此,陈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格外值得重视。因为陈先生的文章中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我就将他的大稿寄给周汝昌先生,希望周先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很快来信,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并寄来了《探佚与结构两学科》的对话文章。
陈先生的文章较长,周先生的文章较短,但他们的观点都很明确,而态度都是“学院派”。这一点也许比观点本身的是非更有意义吧。
陈文对“红学探佚学”作了全面的评析,第一部分针对拙著《石头记探佚》,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先生的“大对称”概念,第三部分针对美国的浦安迪教授,第四部分针对王国华先生的《太极红楼梦》。他的中心论点是认为“大对称”并非曹雪芹原著《石头记》的真实,而是探佚研究者为了使“探佚在操作上达到理想化状态”而主观臆定的,因而“与索隐红学殊途同归”,“探佚善破不善立,由于其结论的或然性,它所谓还本来面目便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这个批评事实上是极严厉的。
陈文对拙著的评析是很客气的。陈文在引姚奠中先生《〈石头记探佚〉前言》中的话之后,作结论说:“上述两种材料(指脂批和伏笔)决定,《红楼梦》探佚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而实际上,梁著在总体上正是明智地止步于这一限制之上。……”同时,陈文又肯定“仅此而论,《红楼梦》探佚研究已显示出其重要意义来。……这使我们对前八十回和高续后四十回的悲剧性质、价值观念乃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上的优劣异同有了清醒的认识,使我们对曹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意义的理解的视界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显然,陈文对探佚并不完全否定,只是关心探佚的限度问题。但陈文又这样说:“探佚可能如何呢?对《红楼梦》的探佚研究最终可以达到何种境界呢?周先生认为可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话说得比较模糊,如果说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那就比较明确。如果是要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则它的结果将涉及一些‘遗形取神’、‘得鱼忘筌’的、包括理解、解释内涵的探佚,这样的探佚就很难有具体的限制。”我以为陈文的这种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如果仅仅止步于“形”和“筌”而不“取神”和“得鱼”,那探佚倒会真正堕落到“索隐”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许多具体的探佚问题上,各位研究者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林黛玉是死于春末还是中秋?是投水还是病死?贾府是否真地遭了火灾?等等。我以为这些争论应该允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关键的问题是探佚研究对高续后四十回的“证伪”,是它显示出的曹雪芹原著的“精神面貌”。难道在具体探佚问题上存在争论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吗?这正是关捩点所在。首先,正是在一些涉及全书“本质”的大问题上,探佚显示了震撼性的魅力,使读者耳目一新并达到了共识。如尽管对林黛玉之死的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推考,但大家却都认同原著“眼泪还债”的悲剧与高续“钗黛争婚”的悲剧有质的不同,前者以“爱心”为指归,后者则以“仇恨”作导向。尽管对贾府是否“遭火”有争议,但正是探佚使大家认识到原著的“抄家”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同于高续的“沐皇恩、延世泽”。也就是说,尽管探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具有“结论的或然性”,但探佚的精髓却正在于“遗形取神”。其次,应该说已经取得的探佚成果已不仅仅是“某些片断的探索”,如果真的如此,探佚绝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反对探佚、认同高续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痛心疾首了。各种“片断的探索”早已产生了“集体效应”——整体效应了。各种具体问题上的争议并没有妨碍探佚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天换地”。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十几年来,已经有上千的学生听我讲过探佚,可以说绝大多数听者都接受探佚的思路。此外还经常有未曾谋面的读者来访来信来电话,表示对探佚的认同。我想这并非我的讲解有多么高明,而是探佚本身的真理性和魅力所致。在这一点上,常常让人感叹“民间”与“红学界”的水平之差异,事实上,探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高续而对许多读者发生影响。当然,由于高续是附骥于前八十回的小说,有其历史惯性,而探佚是研究,其文本流传量不成比例,许多读者根本接触不到探佚的著作,而一些以探佚思路再创作的作品艺术功力太差,也不可能取代高续。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高续与探佚将仍然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但这并不能“反证”探佚不如高续,遗憾的是一些人常常执持这种简单化的逻辑。最近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探佚已经很深入了,现在的问题是普及,面向青年和群众的普及,让大家都知道探佚。这种来自“民间”的声音是意味深长的。
我的认识是:探佚的精髓和本质正在于“遗形取神”和“得鱼忘筌”。
二
关于“大对称”,陈文的驳议方法是采取形式逻辑的推导。这是陈文的力量所在,但也是其弱点所在。
周汝昌先生得出《红楼梦》原著具有“大对称”结构,首先是从对前八十回文本及脂批的感觉和研究中得到实证和灵感的,至于对中华传统审美观念的“转述”和“类比”,那是深一层的“追根溯源”。因此,陈文用“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驳议“大对称”其实并不符合周先生的思路顺序,没有“得其环中”。我读陈维昭先生的几篇论文感觉,陈先生的气质偏向于“理性”和“客观”。而探佚研究是需要感性和智性共同运作的。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艺术的感觉或艺术的悟性和感受力,是与曹雪芹的灵感思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契合交通。俞平伯、周汝昌以及不少红学家赞同第五十四、五十五回之际为原著全书的“中点”,也许不可能举出许多“硬证”(但并非完全没有),主要是来自于一种艺术的感悟。
陈先生似乎太看重形式逻辑了,太看重概念的精确性了,他因此把“对称”和“对比”严加区别,从对周汝昌文章的逻辑驳议层层推进,却忽略了对周氏研究历程的“文心”与“悟性”的深微体察。这样做的结果,也许能显得“论证严密”,却无助于问题的切实解决。如认为“周先生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使探佚在操作上达到理想化状态。只有‘对称’才能成为量化的基础。”似乎“对称”是为“理想化状态”和“量化”而生造出来的,而不是从对《红楼梦》文本的阅读中感悟出来的。揆之于周汝昌研究的实际,这未免是倒果为因。
对周汝昌先生“大对称”的一些具体结论,如后28回具体回目的分布等,我并非完全认同,也没有必要完全认同。这正像浦安迪先生对《红楼梦》的情节结构的重点的理解不尽同于周汝昌。陈先生因此得出结论说:“这种以主体价值诠释去完成逻辑命题的做法,是探佚学实现体系化、整体化的必经之路,但也是探佚学无法自我实现的明证。梁归智先生称‘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其奥秘就在这里。周认为《红楼梦》情节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在第五十四回和第五十五回之际,浦认为在第四十九回、第五十回之际。究竟谁的理解更合理呢?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局的。因为它不能由逻辑实证去证明。”
陈先生的这一段话倒让我联想起西方二十世纪后期逻辑实证主义和消解(解构)主义之间的分歧。显然,陈先生仍然站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论”立场上,要求一个“体系”和“中心”,一种“逻辑实证”的确定无疑的“证明”,要求依据第一义、无懈可击的原理建立具有永恒性的思想体系。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却都要颠覆永恒的中心的形而上学的传统,德里达的后现代消解主义更强调游戏和隐喻。话扯得远了,但要深入下去,“探佚的本质是美学”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深入到这种哲学层次中去,那将是饶有兴味的。探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游戏和隐喻,但这并不减少它的科学性,而是增加了它的魅力,更接近了艺术的创造性本质。我曾反复强调过,探佚是科学与艺术、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的交汇。因此,仅立足于形式逻辑的“实证”立场来批评探佚往往是相当隔膜的。
退一步说,探佚学还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还在讨论,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局的”。从后现代思维来说,“结局”本身就是需要置疑、加括号的。广义来说,任何学术讨论都是“没有结局的”。今天占世界人口相当比例的基督教徒仍然不认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宏观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微观的波粒二象性,都是“没有结局”的。在人文学科领域中就更是如此,荷马、屈原、莎士比亚的存在与否也有人怀疑,《金瓶梅》的作者候选人有几十位,《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水浒传》的作者是不是施耐庵,全都“没有结局”。脂批本已经发现快一百年了,不是还有人对其“真伪”质疑吗?曹雪芹的生卒年,曹雪芹的家世……又有哪一个问题是已经百分之百的“一致”“统一”了呢?周汝昌曾凭悟性臆断曹家家谱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人,后来被新发现的康熙时的《曹玺传》所证实。但如果《曹玺传》从来不曾出现呢?是不是曹宣就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呢?所以从另一方面说,争论又是“有结局”的,那就是看“历史”和“人民”(具体到红学,当然只是那些热爱《红楼梦》的“人民”——那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红迷”)更倾向于接受哪一种说法。对于探佚学这样一种更需要灵魂介入和悟性参与的学问,当然更要求“知音的耳朵”了。
至于王国华先生的《太极红楼梦》,我坦白的看法是王先生对《红楼梦》原著的“大对称”结构有一种会心和直感,但其学力不足以使其思考和论述臻于深入完善,因而有许多可落话柄的缺失和偏漏。我们既不必因为其学力的不足就完全否定他的某些合理见解,也不必把其缺失和偏漏与探佚学拉扯到一起,更不必把王国华与周汝昌划等号。
由此引申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逻辑”与“悟性”、“科学理性”与“艺术感觉”在红学研究中的张力的问题。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中我已经提出,红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进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堂奥,不能与曹雪芹的心灵作深层的对谈,也就是不“解其中味”。因此尽管考证成绩硕果累累,“意义”研究却滞后不前。这一点在探佚研究中尤为突出。这是由探佚研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探佚研究要求深入曹雪芹的创造思维,考证与推测只是手段。也就是说,重要的是“遗形取神”和“得鱼忘筌”,是“张力”的微妙合度,而其契合性,是在“方寸”之间的。
陈先生在文章结尾否认《红楼梦》结构的“有机”和“完美”,认为《红楼梦》“常山之蛇”的前后伏笔照应不可靠,这就涉及到探佚的存在合法性问题了。提醒探佚时应把握适度是一回事,对处处皆在的“草蛇灰线”是否承认则是另一回事。而所谓《红楼梦》的“未完善之处”是否危及到探佚本身的合理性更是需要作全面论证才能作为前提的。陈先生以“旧稿新裁说”和“二书合成说”作为立论的当然依据,这是不够慎重的。在我看来,所谓“旧稿新裁说”和“二书合成说”所“揭示”的“不完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一种误读的产物,其实并没有揭示多少真理。所谓前八十回的“未完善之处”其大多数是因为研究者没有理解曹雪芹的天才匠意文心和陌生化效果而产生的错觉。这样说又涉及到艺术感悟的问题了。
探佚学与高续,尊曹与尊高,两种学派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各有各的信从者。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正迎来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时代,更尊重个人选择的时代,探佚并不强迫尊高派改变信仰,它只是要求尊高派有同样宽容的胸襟,也不要强迫尊曹派改变立场。探佚学不追求“舆论—律”和“定于—尊”,只追求在宽松的学术争鸣环境中自由地竞争读者,竞争未来,看看谁更有前途,更有蓬勃的生命力。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