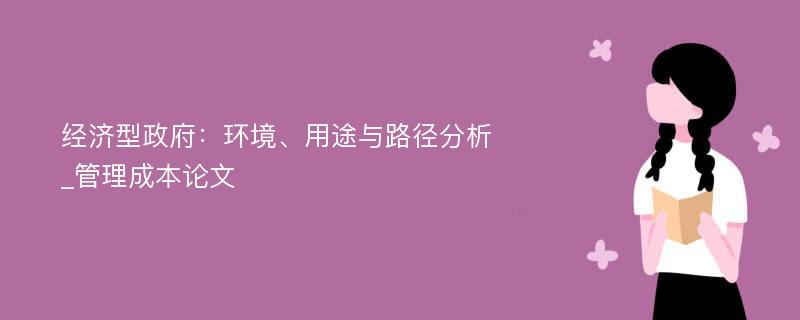
节约型政府:境遇、用度与路径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度论文,境遇论文,节约型论文,路径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 (2006)04—0083—06
在“后现代社会”宏大的历史语境下,一种理解政府组织与能源、资源关系,以及政府组织与社会成本支付之间关系的新的政府范式——“节约型政府”呼之欲出。“节约型政府”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的话语重塑与严谨的理论建构,其目的是提高“节约型政府”的话语效力。
一、“节约型政府”凸现的三重历史境遇
1.“后现代社会”——政府范式选择面对的宏大历史境遇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此时,社会治理的现代性遗产与后现代世界之间的冲突在不断加剧。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当现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毁誉、自我拆除的阶段时,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性”就意味着掌握与转移。[1] 可以说,后现代的社会历史境遇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间,因为,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和努力去解决的问题,不但包括过去已经完全治疗好而现在又以新形式出现的旧问题,也包括过去人们不知道或没有引起注意的新问题。因此,人类社会治理的革命性变革需要以一种新颖的方式被理解与处理,其中,对政府范式的选择尤其重要。因此,基于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理论运思就应运而生。“我们的目的是想依据后现代的状况改变思考公共政策与行政的方向。我们坚持认为,这一状况在治理领域可以通过一系列近似真实的话语来加以改良。这不仅仅是扩展性的调整,它需要我们大胆地偏离已经过时的轨道,许多为人所珍爱的前提性假设将被揭穿。”[2]
那么,如何理解当今政府范式的选择与变革呢?“后现代”作为这一选择的支援性历史背景,它在“质疑”与“拆除”现代性遗产的基础上,给我们带来了哪些观念的转变呢?
第一,反物质主义的消费观。现代社会物欲的泛滥培育出了一种物质主义的消费文化,它引导人们追逐流行的消费时尚,并通过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于是,对物的索取与资源的占有常常被看作人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后现代性在反思中表现出对这种物质主义消费观的蔑视与批判。美国学者艾伦·杜宁认为:“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是惟一的选择。”[3]
第二,简约主义的生活态度。现代性社会在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与推崇下导致了社会消费的畸形化,也导致了生活本真意义的丧失。在后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反思中,我国先秦道家“自然无为”的生活方式被重新“激活”,一种简约主义的生活态度体现出巨大的价值。美国哲学家亨利·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人应当过一种素食、简朴的生活,“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生活的舒服,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大有妨碍。”[4]
第三,泛道德主义的生态观。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拆除中,一个颇有生命力的理论命题就是伦理关系的扩展,即把原初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绿色和平组织在1979年的年鉴中提出:“必须要用那种把所有植物和动物都纳入法律、道德和伦理关怀中来的超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来代替人本主义的价值观。”[5] 因此,在后现代视野中,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环境的干预不仅仅只具有经济学上的效率意义,而且还应该接受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检视。
2.“自然资源困境”——改变政府治道理念的现实境遇
20世纪以来,人口的迅速增加,经济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正在超过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自然资源迅速耗减甚至枯竭,人类所面临的已是一个满目疮痍、不堪重负的地球。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自然资源困境日益突出。如果仅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堪称是“资源大国”,因为中国主要自然资源的总丰度与世界各国相比,仅次于俄罗斯与美国,位居全球第三位。但是,如果将我国人口因素以及资源的质量、分布等因素考虑在内,我国又是一个资源小国。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将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加之人口的持续增长,可预见的未来,人均占有资源还将继续降低,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中国面临的资源困境将很大。这一点,从我国的国家资源安全系数上也可以看出。参见下表。
资源环境安全系列国家分类[6]
分类及安全系数指标 数量国家(安全系数值)
一、高安全度国家(>5) 3俄罗斯(23.98)、美国
(13.97)、巴西(11.38)
二、低安全度国家(<5) 7
1.一般低安全度国家(5—3) 2孟加拉(3.78)、尼日利亚
(3.19)
2.次低安全度国家(3—1) 4印度尼西亚(2.17)、巴基
斯坦(1.78)、印度
(1.74)、中国(1.73)
3.完全低安全度国家(<1)1日本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属于次低安全度国家,且处于该类国家中的最后一位,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状况极为不佳。因此,对资源利用的节约意识至关重要,它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3.“节约型社会”——促发“节约型政府”话语的社会语境
2003年以来,电荒、油荒、煤荒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以及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能源饥荒逼近中国。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当代中国人身上。因此,2005年的上半年,“节约型社会”成为一个常见而重要的语汇。
首先,2005年6月12日,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中央机关全面启动了以“建设节约型政府,做资源节约表率”为主题的“节能宣传周”活动,由此拉开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活动的帷幕。6月25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建设节约型社会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召开。一些中国政府高官、国内外著名学者与企业领袖等200多人参加了研讨。《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7月号,以《节约!节约!!节约!!!》的醒目主标题,对这次会议进行了综述与报道。可以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动了“节约型社会”话语的传播与普及。
其次,6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中, 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为题作了重要讲话。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电视电话会议上,以《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为题,对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抓好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并强调:“政府带头节约资源,既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任务,又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加大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工作力度。”因此,在这两次重要政治活动的“话语重塑”后,“节约型社会”的话语效力获得空前强化。
最后,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社论,从舆论宣传上强化了“节约型社会”的主题;同一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从工作部署上来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工作。至此,“节约型社会”已成为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一种主流社会话语,而且它正在经受学术界与新闻界双重的话语重塑——理论论证与媒体宣传。尤其是在“节约型社会”的语境下,“节约型政府”的话语被强烈地凸现出来了。
二、“节约型政府”关涉的四维政府用度
当“节约型政府”的话语凸现时,它意味着什么?当代法国的语言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指出:“合法的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言语,它使其所要说的东西得以成立。……语言生产着存在,从这种力量中,语言获得了无限的生成性的同时也是创造性的——康德派意义上的——潜能。”[7] 那么,“节约型政府”这一话语的“生成性建构”或“创新性建构”何以进行与展开?《南方周末》2005年6月16日刊载了题为《从人道情怀看中国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文章。文章指出,建设节约型政府,由此构成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节约的内涵不单是节能,而应该是节制一切可以节制的政府用度。必须认识到,政府用度消耗的不单是经济成本,实质上是生命成本,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节制政府能耗,就不只是为了节约几个钱,更是为了体恤民力,尤其是体恤人的生命和健康。笔者认为,这是对“节约型政府”一种高层次的理论建构。很显然,在这一建构中,不是简单地把“节约型政府”理解为“政府节能”。
托马斯·库恩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的转换就是科学的革命,即由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换。因此,在各种历史境遇下凸现出来的“节约型政府”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政府组织与能源、资源关系,以及政府组织与社会成本之间关系的全新范式。“节约型政府”作为一种新范式,它可以统摄我们以前提出的诸多政府理念,这些政府理念包括:“廉洁政府”、“适度政府”、“廉价政府”与“高效政府”等。对于两者的关系,如果我们把“节约型政府”比作一座“四方大厦”的话,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四根立柱”就是以上的四种政府理念。也就是说,要想建好“节约型政府”的宏伟大厦,就必须首先把这“四根支柱”建好。可以说,任何一根支柱的瘫软,对于节约型政府大厦的建构都是致命的。这是我们理解“节约型政府”应该具有的学术高度,依此,笔者拟从四维“政府用度”的视角,来解读“节约型政府”的新范式。
1.遏制政府的“腐败用度”,打造“廉洁政府”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第一大支柱。
笔者认为,在“节约型政府”的四大支柱中,打造“廉洁政府”是一道底线。道理很简单,一个腐败的政府必然要消耗掉很多本可以免除的政府用度。当今,腐败用度已是政府用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国际反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说:“无论仁慈还是专制的国家,都牢牢把握着重要资源的分配,同时也能让人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收益和成本的分配都为那些拥有自由决定权的政府官员所控制。而且,想获得政府优待的个人及私营企业可能会乐于为此花钱。如果付给政府机构一笔钱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好处或规避惩罚,那么,这笔钱就具有了腐败的性质。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8]
在我国现实的政府行政过程中,由于腐败与经济增长乃至经济活力相伴生的假象,掩盖了由于腐败而产生的额外成本与资源消耗,并且扭曲了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实际价值。因为,腐败的政府官员总是支持上马过多的毫无实效的公共投资项目,同时却又无法维持已有的较为合理的投资项目。腐败一方面降低了国家的总体投资水平,另一方面还助长了基本建设投资的泛滥。在腐败市场中,政府消耗掉的各种公共资源,不是指向社会公共福祉,政府的服务只提供给了行贿者,贿赂增加的收益变成了政府公务人员的“黑色收入”,而不是流入国库。更为严重的是,对某些公共生活领域内腐败现象的容忍将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染指腐败交易,从而造成政府“腐败用度”的增加。
2.削减政府的“超载用度”,维持“适度政府”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第二大支柱。
“适度政府”是指政府规模的适度性,它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社会系统维持并供养一个适度规模的政府是社会管理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从理论上看,政府规模过小,政府力量难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管理的需要,社会有可能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而政府规模过大,政府过剩的力量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危害公众权益的力量;而且,超出社会需要的政府组成就构成了“政府对于社会的超载”,而这一超载所消耗掉的政府用度即“超载用度”,对于社会而言就是不必要的能量耗费。
衡量政府的规模可以依据不同的指标,一般有三个客观的数据可以判定,即政府机构的数量、政府官员的人数与政府支出。从世界各国政府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规模总是呈现出不断膨胀的态势,这一情况在我国尤其突出。这表现在:(1)就政府机构而言,其膨胀的势头虽然得到了抑制,但并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公务员数量急剧上升。1999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政府人员增长了1.36倍, 平均每年增长4.2%,而同期社会劳动力的数量仅扩大了0.76倍,平均每年扩大2.7%。(3)政府支出上升迅速。1978年中国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费为49.09亿元,1999年增加到1525.68亿元,21年间增加了30倍,平均每年增长17.8%。[9] 可以说,政府的“超载用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用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量度,因此,维持“适度政府”就是削减政府的“超载用度”,它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3.节制政府的“成本用度”,锻造“廉价政府”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第三大支柱。
政府在产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同时,必然涉及到许多社会资源的投入,忽略成本的政府不符合现代政府的设计原则与评价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公众越来越要求“廉价政府”的出现,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时,所消耗掉的社会资源过大,这显然不符合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原则,也违背了“节约型政府”的理念。对于政府的“成本用度”,我们可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看。广义的政府成本用度是指,社会为获取政府特有的功能而付出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资源的总和;而狭义的政府用度是指,政府公务员工资与政府机关办公费两项耗费之和。
在我国,政府成本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许多政府官员恐怕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决策还隐含着成本投入,他们已习惯于不计成本地讲业绩。据2003年6月10日《新快报》A2版报道称,“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学者杨永华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我国政府狭义成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1978—2002年,无论是中国政府成本,还是省级地方政府成本,都显示出上升的趋势,而且政府成本增长比较快。[10] 综观理论界的研究,我国政府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政府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口多、工资成本高;(2)政府行为失当,政府决策失误、政府管理效率低下等不合理政府行为;(3)缺乏健全的财政预算体制。当今,不论是从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角度,我国政府成本用度节制的空间还很大。
4.节约政府的“时间用度”,培植“高效政府”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第四大支柱。
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已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时间作为资源,它具有“供给无弹性”、“无法蓄积”、“不能取代”和“不可再生”等特性。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杜拉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中也提出,时间是最稀有、最短缺的资源,因此,有效的管理者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能管理时间。鉴于时间的资源特性及其与效率的密切联系,现代组织都把时间纳入管理的内容即“时间管理”,并提出了“时间成本”的概念。时间管理强调要通过制定计划合理地使用时间,节约时间,避免时间资源的浪费。政府管理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展开的,因此,在政府管理的各种成本消耗中就必然包括时间用度。时间用度既是衡量政府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测定政府成本的重要指标。
由于长期受封建小农经济的影响,国人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习惯,时间观念与效率观念十分淡薄,人们把对时间的浪费更是排除在道德谴责与经济考量之外。在行政实践中,缺乏现代时间观念的各种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会议冗长、会而不议、议而不决等。针对我国政府管理中时间浪费的严重性,从思想意识深处培育珍惜时间、节约时间成本的行政组织氛围,应该被纳入到节约型社会、节约型政府的范式建构中。况且,现代社会已进入高效率的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必然要求人们养成珍惜时间的习惯与品质。
总而言之,打造“廉洁政府”以遏制政府的“腐败用度”,维持“适度政府”以削减政府的“超载用度”,这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两大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节制政府的“成本用度”与“时间用度”这两个指标,建设节约型政府“大厦”的目标就能实现。
三、“节约型政府”范式的两个实现路径
1.培养既节制“有形资源”又节制“无形资源”的节用意识。
在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中,一贯倡行“节俭”,这一行为是对先秦墨家“节用观”的践行。墨子作为社会中下层劳动人员的理论代言人,在国家经济政策上,他从实用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节用”与“节葬”的主张,“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子认为,节用可以使一个国家成倍地增长财富,“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解读墨子的节用主张,它向我们传达了三层相互递进的内涵:第一,节用表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就是简约主义的生活态度。“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第二,把国家节用与体恤民情、不劳民力联系起来,“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第三,把国家节用提高到统治合法性的高度,认为节用是圣王“所以王天下”的根本措施。“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11] 笔者认为,墨家的“节用”主张,在当前的社会境遇下体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与生命力,而且这一思想对于建设“节约型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张力。
政府节用,就是节制政府的一切用度,从资源的角度看,既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在节约型社会、节约型政府的提议中,只讲节制有形资源,而不讲节制无形资源肯定是片面的。由于受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们对资源的理解与认识往往存在偏差,一般把资源仅看作是有形实物,像矿产资源、水力资源与森林资源等。这种对资源的理解是基于主要依赖于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工业经济时代的,当历史进入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已有了新的认识。当今,资源已不仅仅限于有形的自然资源,也涵盖了社会的、无形的其他资源。笔者认为,在我国政府的实际用度中,不仅有形资源的损耗令人吃惊,而且无形资源的损耗也是惊人的。
政府应节制的“有形资源”,主要是指政府在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五个方面节制政府的一切有形用度,并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中做出表率。然而,笔者认为,政府节制有形资源只是政府节用的基础工作,还应该强调政府对无形资源的节用。当前,我国政府应节用的无形资源主要指“时间”与“人力”这两种无形用度。因为仅从感性的角度看,我国政府管理中对时间与人力等资源的损耗是巨大的。其原因概括起来有:(1)如上文所言, 东方传统的历史与文化没有形成“时间是资源”的社会共识,因此,浪费时间在社会管理与政府管理过程中司空见惯。(2)由于我国传统社会没有严格的“公域”与“私域”的界分, 人际关系与权力关系纠结与交叉所带来的关系复杂性,常常是耗费政府公务人员时间、精神与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3)我国社会风尚中重人情往来的习俗而导致的“请客送礼”风气,也消耗了大量公务人员的精力、时间与体力。因此,在“节约型社会”与“节约型政府”的视野下,应从观念上实现四个方面的转变:第一,在整个社会“时间就是金钱”的话语背景下,培养公务人员珍惜时间、讲究效率的行政习惯;第二,在社会活动中严格界定“公域”与“私域”的范围,在社会关系中严格界分权力关系与私人关系的作用空间,使社会人际关系趋于理性与简单化;第三,削减各种形式主义的应酬,公务人员不合理的应酬活动既是无形资源的浪费,也是有形资源的浪费。第四,政府及其各部门之间实行“阳光合作”,因为在我国政府管理中已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现象,即不仅“私事”要私办,即便是“公事”也要私办,政府间的“公务合作”也常常是在暗箱操作中完成的。暗箱操作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有形用度,也消耗了大量的无形用度。
2.建构节制政府用度的“软约束”与“硬约束”制度与机制。
第一,树立政府的“公共支持”意识,构筑节制“公共税收”的软约束机制。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得不到公共社会的支持,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君权神授论遮蔽住了。在东方,人们崇尚的是“天之立君”的信条,在西方则形成了“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信念。君权神授论的权力原则遮掩了国家与政府必须接受“公共支持”的事实。正是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契约论和新经济理论揭示了国家与政府存在的世俗基础,这个世俗的基础就是“权源”和“物源”。[12] 所谓“权源”是指公众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政府只是国家权力的受托者;所谓“物源”是指政府的开支与费用来源于税收与政府收费,纳税人是政府财力的来源。政府的“两源”基础决定了政府的“公共支持”属性。
在现实中,认识到政府的公共支持属性,其重要性在于要把原有的“税款交纳者”观念,转变成“纳税人”观念。因为,税款交纳者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消极服从者而存在的,它只有纳税的义务却没有相应的权利;而纳税人则是负有纳税义务也享有纳税权利的税赋承担者。在现代社会中,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应包括:赞同纳税权、选举代表权、要求政府服务权与要求税款节约权。[13] 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只有承认并尊重“纳税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并切实体会到:是纳税人在养活政府,而不是相反。政府消耗的各种用度实际上是纳税人的生命成本而非国家的钱财时,一种珍惜纳税人“公共税收”的“节约型政府”才可能变成现实。
第二,建立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构筑节制“公共支付”的硬约束制度。要使节约型政府变成现实,还必须构筑政府“公共财政”的制度体系与一系列实现机制。因为,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差别只在于制度是表层的行为法则,而观念则是深层次的行为信念。在大多数情况下,观念与制度之间起到的是相互支援的作用,即观念规范着制度的基本取向,而制度的正常运转则强化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换言之,任何一项制度体系都是某种意识与观念的体现,反过来讲,任何一种观念的实现都必须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规则。
“制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其含义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都将制度理解为“规则及其组合”,即它是在特定范围内由一个集体或组织制定的、对其成员的个体行为起引导和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的总和。缪尔达尔将欠发达国家由于制度短缺而造成的一系列病症称为“软政权化”。[14] 制度短缺导致了我国政府财政支付中的不规范行为与随意性程度都很大。因此,建立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构筑节制政府“公共支付”的一整套规则机制,并用这些制度体系与规则机制来规范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行为,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随意性与任意性是刻不容缓的事。节约型政府的实现,迫切需要具有普适性与刚性的“硬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