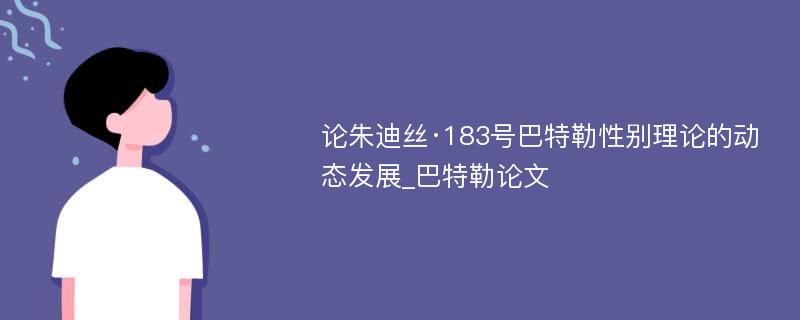
论朱迪斯#183;巴特勒性别理论的动态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理论论文,巴特勒论文,动态论文,朱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5-0065-09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马克欣·爱丽亚特(Maxine Elliott)讲座教授,是当代美国享负盛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其学术思想融合了哲学、女性主义理论、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精神分析等众多领域,对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电影研究、文学研究等多种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在早期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以下简称《性别麻烦》)中提出性别操演理论以来,她的性别理论已引起学术界各个领域相关学者的广泛讨论,其中不乏锐利的批评,这使朱迪斯·巴特勒在回应这些批评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并在后续著作中继续对性、性别和主体构成等问题进行思考,形成她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鉴于朱迪斯·巴特勒在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勾勒20年来朱迪斯·巴特勒思想的发展轨迹,以便从中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范式上的转换,即从以启蒙现代性为基础的传统女性主义走向关注差异、解构固化身份的后女性主义。
一、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
作为女性生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思想的核心是对主体构成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因为女性主义理论说到底是要重建女性的主体性。而朱迪斯·巴特勒对主体构成的哲思,始于“性别操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概念的提出。性别操演性是朱迪斯·巴特勒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对改变人们关于性别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什么是性别操演呢?我们通常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它等待着我们去揭示其意义,但是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性别本体和本质,它只是我们的一种期待,正是这种期待的结果产生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sex),我们认为我们自身有某种“本质”的性别特质,这其实是社会规范不断作用于我们身体的结果。因此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生理性别并不是先于社会话语存在的事实,它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我们再也无法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出区分,而只能说性别形成于某些持续的行为生产中,这些行为的产生受制于话语规则和实践,正是这些持续的话语规范对身体进行性别的风格化而使性别得到暂时的稳固。性别的“内在本质”其实是服从于性别规范的一系列行为的重复,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的本体身份,性别身份形成于持续的操演行为中,先有操演行为,后有性别身份,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
1990年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建构性别操演理论,其根本目的在于批判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解构性别的本体概念,同时将性别建构为流动性的、过程性的身份。为了做到这一点,朱迪斯·巴特勒首先质疑了“妇女”这一具有本体色彩的范畴。作为卓有建树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身份政治在实践上排挤有色人种妇女或性少数群体,其症结在于这种身份政治仍然认同一种“实在”的主体认识论,没有脱离性别本体论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她首先对女性主义第一、第二次浪潮把具有总体特征的“妇女”范畴作为斗争的基础提出质疑。传统女性主义把“受压迫的妇女”作为一个普遍的基础,暗示父权制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结构,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但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压迫存在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历史语境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连贯和一致,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态交相作用。因此,“性别”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汇中分离出来,而只能在这些交汇中被生产并得以维系。朱迪斯·巴特勒指出,“妇女”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即使是在复数的情况下,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焦虑的起因”,[1](P6)因为这个词不能尽揽一切,包含所有的多重意指。由于“妇女”这个范畴不能包含所有的含义,当女性主义宣称它代表“妇女”(实际上是某些妇女)并为其争取权益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被排除在外的妇女的反对,这也正是身份政治的局限性。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为了符合再现政治上女性主义必须表达一个稳定的主体的要求,女性主义又必须以某个共同的身份为基础,因此遭到了错误再现的指责。身处这种两难之境,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试图将可变的、流动的身份作为一个方法上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女性主义理论从单一的基础中挣脱出来,避免遭到被它排除在外的那些身份位置的挑战。这就是朱迪斯·巴特勒思考流动的、可变的(性别)身份的根本原因。
接着,朱迪斯·巴特勒使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谱学方法,通过重新阐释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西蒙德·弗洛伊德(Sigrmund Freud)、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露丝·伊利格雷(Luce Irigaray)、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等人的观点,对性别本体概念形成的历史条件做深入剖析,指出它在文化中运作的主要方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异性恋规范。朱迪斯·巴特勒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社会中的异性恋规范如何作为一种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规定某些形式的社会性别表达是正确的,而另一些却是错误的?朱迪斯·巴特勒发现,社会性别的层级结构以统合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的一致性为基础而得以建立。为了建立性别的统一性,首先需要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一个人如果在生理上是女性,那么她就应该展现她的“女性特质”,并在异性恋为规范的模式下渴望男人的爱。也就是说,以异性恋模式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只允许男性与女性两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存在,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决定其社会性别和欲望取向。这种性别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其实是社会管制的结果。生理性别的单义性、社会性别内在的一致性以及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框架,都是管制性实践虚构出来的,它们起到巩固和自然化异性恋主义权力体制的作用。稳定的社会性别因而服务于异性恋规范,排斥任何非规范的性实践。朱迪斯·巴特勒作为性少数群体成员之一,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性别生活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被异性恋假设给扼杀了,她才在《性别麻烦》中思考非规范的性实践如何冲击异性恋预设这种暴力的假定。可以说,通过建构性别的操演理论,朱迪斯·巴特勒希望能够根除一般以及学术话语所充斥的理当如是的异性恋假设,对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中所行使的暴力给予批判。
最后,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朱迪斯·巴特勒对扮装(drag)做了讨论,提出女性主义政治应从以性别本体为基础的身份政治转向一种戏仿的政治策略。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所谓“真品”和“仿品”的区别并不存在,因为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在社会性别表达方式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正是这些表达方式被称作社会性别的结果,操演性地组成身份。”[1](P33)如果社会性别的内在真实是一种假象,是文化在身体表面铭刻的一种幻想,那么就没有所谓真的或假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本身是一种模仿性结构,它所模仿的就是“真品”这个概念本身,因为性别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原件的仿品。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扮装的意义在于它有力地嘲弄了“真实”的性别身份。扮装体现了扮装者解剖学上的身体与被操演的性别之间的差别,说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偶然性的。扮装是一种性别戏仿,它所产生的增衍效应使霸权文化无法再主张自然化或本质主义的性别身份。在扮装这样的戏仿实践中,身体不是一种存有,而是一个可变的疆界。朱迪斯·巴特勒以扮装为例,说明越界的颠覆性和走向戏仿政治策略的可能性。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促使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传统女性主义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为了驳斥性别歧视者所持的“生理即命运”的观点。为了反对女性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说法,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无论女性的生理性别是多么的不可撼动,她的社会角色是文化建构的,因而对社会性别的塑造是可以改变的。这种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使女性能够暂时从“天定”的命运中解脱出来,但是朱迪斯·巴特勒诘问的是:关于“生理性别”的阐述是一种事实,还是服务于某种利益的科学话语?“生理性别”被认为是自然的、前话语的,好像它是先于文化的,在那里等待文化在身体上有所作为,这种“生理性别”在本质上被建构为非建构的特点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却正是为了稳固生理性别内在的稳定性与二元的框架,从而服务于异性恋的规范。通过操演理论,朱迪斯·巴特勒揭示了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将生理性别从自然化的表象中解放出来,为寻求颠覆和置换那些支持男性霸权的自然化的性别概念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彻底推翻了异性恋霸权主义对性别的认同模式,即我们生而为男为女,生来具有男性或女性的生物性特征,通过压抑对母亲的欲望逐渐在文化秩序中获得男人或女人的社会性别身份。由于获得社会性别身份的过程就是对欲望压抑封杀的过程,从进入文化象征秩序的那一刻起,欲望始终被套上文化规范和乱伦禁忌的枷锁。朱迪斯·巴特勒在深刻地指出权力话语对欲望的压制和生成的同时,认为:性别和欲望灵活多变,性别是欲望的化妆表演。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体属性,而是文化规范对我们身体的物质化过程中的表征。
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挑战了传统女性主义以身份政治为基础,以实际的妇女群体和经验为基础进行政治建构的尝试和努力。她对语言和话语的关注使女性主义反对男性霸权主义的阵地从实施物质压迫的社会体制转向意识形态批判和话语实践领域。只有在文化结构最深入的语言层面颠覆菲勒斯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导话语,女性主义才有可能动摇父权制这个坚固的堡垒。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中提出的操演理论及其在后续著作对操演理论的丰富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二、批评、误读与回应
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自问世以来,学术界反应褒贬不一:有狂热的推崇、恶意的攻击,同时也有犀利的批评和中肯的评价。例如,朱迪斯·巴特勒的学术观点在她的学生中间大受欢迎,学生们甚至在网络上成立名为“朱迪”(Judy)的电子杂志,宣扬朱迪斯·巴特勒的思想。与此相对照的是,由于朱迪斯·巴特勒文风艰涩,1998年《哲学与文学》杂志评选“最糟糕文风奖”,朱迪斯·巴特勒高居榜首。一些学者随之对其进行攻击,以1999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玛莎·纽斯堡(Martha Nussbaum)在《新共和国》刊载的文章“戏仿教授”为最甚,该文从两个层面抨击朱迪斯·巴特勒:玛莎·纽斯堡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制造新词,讨论前人已经谈到的话题;她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脱离实际经验和非学术界。笔者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确实是旁征博引,借鉴和重读了像西蒙·德·波伏娃、米歇尔·福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西蒙德·弗洛伊德、雅克·拉康、瑞威尔、露丝·伊利格雷、莫尼克·维蒂格等人的观点,但是朱迪斯·巴特勒在重新阐释上述理论家的观点时提出了自己创新性的观点,如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使异性恋成为规范的同性情欲禁忌以及性别的戏仿政治策略等。[2](P91)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本体的系谱学追问正是以重新阐释为主要手段,从中找出激进和变革的可能性。其次,玛莎·纽斯堡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脱离实际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这种观点恰恰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发生范式上的根本转变。1999年女性主义杂志《希帕蒂亚》(Hypatia)刊载了韦斯特林的文章,题为“朱迪斯·巴特勒的复杂建构论:一种批判性的评价”(“Butler’s Sophisticated Constructivism:A Critical Assessment”),对朱迪斯·巴特勒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该文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女性主义理论出现了新范式,即激进的建构论,而与此范式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新范式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女性主义内部怀疑的声音。
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面临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对广泛吸收后结构主义及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朱迪斯·巴特勒而言,其学术观点处于女性主义内部论争的焦点是可想而知的。朱迪斯·巴特勒使用操演性这一概念来说明并不存在一个预设的主体,主体是一系列操演行为产生的结果。这一观点质疑了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谈论“妇女”这一范畴时预设一个固定的女性主体的假想。传统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如果脱离具有可靠先验感觉的统一主体,就没有女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义政治也不可能存在。在女性的概念上没有了基础,女性主义似乎会陷入相对主义,这是不利于女性主义政治的。而且妇女之间的多元化一旦被承认,并被认为比妇女的群体更重要,任何以妇女为类别和以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为目标的集体行动就会受到质疑。针对女性主义理论出现的困惑,朱迪斯·巴特勒撰文“不确定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Contingent Foundations: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Postmodernism’”)来说明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援助政治理论是可行的。问题不在于维护还是放弃基础,因为所有的理论和政治主张都对社会现实和知识的本质作出假设。关键是我们看待基础的方式,因此她并不主张放弃女性这一范畴,而应该把女性这一范畴看成长期可质疑的假设,并用语用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使之赋有多元的意义,这样我们既可以在女性争取权力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又可以聆听来自不同位置的妇女的多种声音。
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一直强调社会性别是操演性的,不存在一个先在的身份作为属性的衡量依据。它不是固定、稳定的身份,而是依赖于时间、地点的流动性的、暂时的操演。这种将性别和身份理解为话语的建构在女性主义批评家中间引走了质疑,因为如果身份是话语建构的,我们就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身份和人的主体性。这在一些女性主义活动家看来是行不通的。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因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95年收录在论文集《女性主义争论》(Feminist Contentions)中女性主义学者希拉·本哈比博(Seyla Benhabib)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她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将主体贬为语言的效果,从而化解了意向性责任性、自我反思和自主等多个概念,而在女性主义争取法律、道德和政治领域中的权利时,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等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女性主义政治需要将主体理解为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决定的能动者。[3](P20)对希拉·本哈比博来说,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排除了这种理解,因而将削弱女性主义政治。针对希拉·本哈比博的质疑,朱迪斯·巴特勒首先诘问的是女性主义政治是否一定要明确表达一个“稳定的”主体。她认为,“当主体具有稳定性或统一性的前提受到质疑时,政治的特定形式就会以不确定的形式出现。”[4](P7)一旦像“妇女”这样的身份范畴不再被理解为代表统一稳定的身份,那么以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朱迪斯·巴特勒质疑的是政治领域将稳定的主体设为必需的根本目的。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事件之后一定有一个行为者”这样的设想是为了让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是为了道德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虚构。对她而言,“行为者”构成于“行为”之中,而“主体的这种构成性特征恰恰是能动性的先决条件”。[5](P46)如果主体的构成性特征意味着它永远是一种非固定的过程,那么就可能有重新意指和改变的可能性,抵抗就不是不可能之事。能动性就在于主体的非稳定之中,因此操演性的主体性具有一种解放力量。
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自提出以来,随即引起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也不乏对操演理论的误读。有些学者从朱迪斯·巴特勒对扮装的戏剧性表演的赞赏中得出结论,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是一种戏剧舞台意义上的表演,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改变。在一次访谈中,朱迪斯·巴特勒谈到了这种误读:“有一种对《性别麻烦》的糟糕阅读,即:我早上起来以后打开衣柜,开始决定今天我将扮演哪一种性别。很不幸的是,这种糟糕的阅读却成了流行的解读”。[6](P659)针对这种误读,在“批判性地怪异”(“Critically Queer”)一文中,朱迪斯·巴特勒对操演性(performativity)和操演(performanance)做出了区分。她说:“操演性重述人们赖以形成的规范:它不是社会性别化的自我的一个激进组装,它是规范的强制性重复,我们无法自由地摆脱这些先于我们的规范,它们建构、激活和控制性别化的主体……而操演则意味着先行存在一个表演者。”[7](P21)操演以一个事先存在的主体为前提,总是预设一个行动者的主体,而操演性则没有预设主体。在操演性的概念里,操演先于操演者,操演者只是操演产生的效果。朱迪斯·巴特勒对这种唯意志论的看法作出了更正,指出并不存在先于操演行为的本体论的身份,正是一系列的操演行为形成了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本质和身份。对性别操演的唯意志论解读从根本上误读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观点,应予以纠正。
对《性别麻烦》的另一个误读是人们对扮装的理解。在最后一章“从戏仿到政治”中,为了揭露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朱迪斯·巴特勒使用扮装这个例子来对抗性别规范所实行的暴力,认为扮装是对社会性别的戏仿,它揭示了异性恋规范的不稳定性,同时打开了重新意指的空间。但有人认为朱迪斯·巴特勒低估了政治,将其贬为戏仿;也有人将扮装表演看作是抵抗或政治参与的榜样。针对于此,1999年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的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扮装并非是颠覆的一个范例。把它当作颠覆行动的范式,甚至是政治能动性的一个模范,将会是一个错误”。[1](Pxxiii)迪斯·巴特勒并不认为戏仿的颠覆性可以作为女性主义反对父权制的政治策略,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戏仿都具有颠覆性。朱迪斯·巴特勒的目的在于使用扮装的例子揭示性别的内在真实是一种假象,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具有颠覆性的范式。朱迪斯·巴特勒讨论扮装,并不是要颂扬扮装,把它当作一种模范的性别表达,而在于说明自然化的性别认识对真实构成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朱迪斯·巴特勒使用扮装的例子恰恰是要说明性别的“真实”并不像我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在后续著作《消解性别》里,朱迪斯·巴特勒又进一步解释了扮装表演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扮装说明身体处于过程(becoming)的模式中,身体在遵循规范时也在抵抗规范。“遵循和抵抗与规范形成一种复杂的悖论关系,这是一种苦难形式,也是政治化的一个潜在场所。”[8](P217)通过扮装这个例子,朱迪斯·巴特勒让我们看到:扮装不仅制造了一种颠覆性场景,同时揭示了现实被复制以及在复制过程中被改变所依据的机制。
三、性别理论在后续著作中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并没有圆满解决如何进行意指和重新意指的问题,当一切都成为话语建构的产物时,应如何看待身体的物质性呢?针对有学者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忽略身体的物质性这一点,1993年朱迪斯·巴特勒推出《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以下简称《至关重要的身体》)一书。该书诘问的核心问题是:身体是否具有纯粹的物质性?朱迪斯·巴特勒继续对意识哲学的主体假设进行批判,并将身体推到主体构成的前台。她认为身体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单位,更是权力、知识和话语的汇聚点。这就是说,身体的物质性不是纯粹的,它受到话语的控制。作为主体性基础的身体也可具有文化性,因为“身体总是和语言有关”,[9](P68)语言的意指实践具有构成力量,在语言的范围之外我们永远接触不到现实,因为事实的真相总是由语言来表述的。这一点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文本之外别无它物”的思想吻合,一切都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各种制度、规范与习俗的形成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各种制度的、道德的、法律的和社会的规范存在于语言中并以语言作为其存在载体,用语言来界定、来表述,而且它们必定在人们的言语活动中生成、存在、演化和变迁。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习俗和规范必定要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来完成,并以语言的形式来实现。谁掌握了语言文字的主导权,谁就能制定规范我们行为的制度,谁就会创造“我们”。朱迪斯·巴特勒显然深刻意识到了权力、话语和知识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朱迪斯·巴特勒在此书及后来的著作中如此关注语言问题的原因。
由于语言问题具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性,而我们只能从语言中理解身体的物质性,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朱迪斯·巴特勒借鉴英国著名语言分析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操演理论。约翰·奥斯汀1961年在其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认为证实性言语(constative utterance)和述行性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是两类最基本的言语行为。证实性语言可以对既成事实作出正误判断,如《皇帝的新装》中小男孩儿诚实的叫喊“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是正确的;撒谎的少年说“狼来了”这句话是错误的。述行性言语则不涉及对错之分,但它“言出什么也就做了什么”,具有“以言施事”的力量(illocutionary force)。这种施事话语要有以言取效的结果,发话人必须有适当的身份、地位和权力,而且他的话语要符合一定的惯例。例如,当牧师在教堂主持新人婚礼时,当说到“我宣布你们为夫妻!”的那一刻起,这对新人就成了夫妻。朱迪斯·巴特勒正是借鉴了约翰·奥斯汀关于述行性言语的生成力量而宣布性别的操演行为生成性别身份,并不存在独立于这些操演行为之外的“本体论的”身份;人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先在的,而是流动性的、过程性的。㈣(P138)
为了进一步说明性别的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它通过身体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得它的结果,朱迪斯·巴特勒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借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雅克·德里达的理论提出社会性别不仅是操演性的,而且是引用性的。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身份是对性进行界定的话语产物,我们根据已经被书写为我们社会文化传统的那个剧本底稿来表演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同性恋与异性恋。按照这一观点,身份是文化的建构而不是预设的。社会性别是一种总在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行为。它的产生是由于异性恋模式中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习惯性的、日积月累的不断重复。在路易·阿尔都塞的“询唤”(interpellation)理论的影响下,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引用理论”(citationality)。通过引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询唤”概念,朱迪斯·巴特勒提出,话语对性别的建构是通过“询唤”达成的。她写道:“考虑一下医学询唤的情况,这种询唤把一个婴儿从‘它’转变为‘她’或‘他’。在此命名中,通过对性别的询唤,女孩被‘女孩化’(girled),被带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这种对女孩的‘女孩化’却不会就此完结;相反,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线,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9](P232)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就像牧师主持婚礼时宣布“我现在宣布你们为合法夫妻”时一样,当医生宣布刚出生的婴儿为男孩儿或女孩儿的那一刻起,对性别的询唤就发生了。婴儿成了一个性别化的主体。他/她就处于该文化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界定之中。女孩儿被抚养成女孩的样子:穿粉红色的衣服,玩洋娃娃,长大后化妆、刮腋毛,学做家务,为进入成年妇女侍候丈夫和孩子的角色做准备。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不断地“引用”社会性别规范。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建构是在不断地被个人引用的过程中维持和进行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朱迪斯·巴特勒的引用概念不是机械、被动、原封不动地重复文化习俗和规范,而是借用雅克·德里达“引用性”的概念,扩展了操演性的语意张力,因为在雅克·德里达那里,引用性瓦解一切权威的起源;引用性总是处于一条引用链中,没有起源,没有终结。它既重复引用既有的规范,又不断延缓、阻碍和消解形成既有规范的权力话语。引用性蕴含了对规范的顺势引用和对规范的不断修正这样的双向过程。[11]通过引用性这一概念,朱迪斯·巴特勒有力地说明了动态的操演行为裂变性别身份的可能性。
就像朱迪斯·巴特勒自己在《性别麻烦》再版序言中所说,她有时把操演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朱迪斯·巴特勒现在认为这两者互相关联,而且彼此错落出现。如果将言语行为看作是权力的例示,我们就会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1997年出版的《可激动的语言:操演的政治》(Excitable Speech: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中,朱迪斯·巴特勒进一步将言语行为理论与路易·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相结合,关注仇恨语言、反淫秽语言和同性恋论争等文化事件中的言语行为,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与语言的惯例隐含的关系,促成一套结果的产生。
朱迪斯·巴特勒的主体观沿袭尼采对“实在形而上学”的批判,认为实体的“我”是一种幻灭,它不是语言再现的一个统一、稳定的存有,而是语言语法结构的产物,即主体是一个语言范畴和一个形成中的结构。[12](P18)也即,身份范畴是语言和意指的操演效果,它不是基于身体物质性的个人特性。为了论证这一点,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有必要对主体的形成做深入分析,因此在《权力的心理生活:服从的理论》(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Theories in Subjection,1997年)中,朱迪斯·巴特勒尝试将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体如何通过语言的手段生产出来。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不仅压迫主体,它也构成主体;权力不单单是我们所对抗的东西,还是我们所是的存在所依靠、隐匿和保有的东西。主体的形成以对权力的屈服(submission)为开端,这一观点已经体现在路易·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或福柯的话语生产理论中。路易·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认为,主体的屈从是通过语言,作为召唤个体的权威的声音的结果而发生的。当一名警察召唤街道上的一个行人,而这个行人转身并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被询唤的人时,行人这个社会主体就在询唤的话语生产下诞生了。但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路易·阿尔都塞并没有解释那个人为什么会转过身来,认同并接受警察的召唤。同样,朱迪斯·巴特勒认为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生产理论也没有详细阐述在屈服中主体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屈服是服从的一个条件,那么权力如何让个体屈从,是什么样的心理形式让个体得以屈从呢?这个问题驱使朱迪斯·巴特勒将权力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讨论规范话语如何在心理层面上实现对个体的管制。可见朱迪斯·巴特勒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从更深刻的层次上说明身份范畴是语言和意指的操演效果,而不是基于身体物质性的个人特性。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论述奴隶获得自由的途径和他陷人的“苦恼的意识”时早已谈到主体如何在屈从中形成的问题。黑格尔认为,摆脱外在权威获得解脱的奴隶并不足以将自己引入自由,因为当他摆脱明显外在的“主人”时,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必须服从各种规范的伦理世界,陷入了受道德律令困扰的“苦恼的意识”中。朱迪斯·巴特勒认为,黑格尔在“苦恼的意识”里关于服从中身体的依恋和对身体依恋的不可避免的观点,在米歇尔·福柯的理论框架中被重申。[13](P34)借鉴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生产理论,朱迪斯·巴特勒将主体化看作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过程:一方面,外在的权力对我们的心理施加影响,促使主体在屈从中诞生。“我宁愿在屈从中存在,也不愿不存在”的困境说明主体为了延续自己的存在,必须接受权力的管制、禁止和抑制。在服从的范围内,存在的代价就是屈从,正是在不可能作出选择的时候,主体把屈从当作存在的承诺加以追求。而另一方面,主体又成为权力的代言人和自我心灵的监视者,在心理空间中对自我进行监控和管制。朱迪斯·巴特勒在此著作中侧重批判的是权力的循环性及其循环重复过程中主体的认同困境。由于主体与权力之间存在复杂的依赖和共生关系,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以主体为中心的身份政治已经难以为继。朱迪斯·巴特勒从规范权力主宰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运作过程敏锐地指出了后革命时代身份政治的艰难困境。而在朱迪斯·巴特勒与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及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合著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Contingency,Hegemony,Universality)中,朱迪斯·巴特勒更正早期著作中对“普遍性”持完全否定和排除性的观点,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化翻译工作”,重点讨论霸权理论及它对理论上的行动主义左派所具有的含义。可见,朱迪斯·巴特勒的后续著作一直在思考她所建构的主体形成理论与政治抵抗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
2008年英国女性主义学者莱恩·西格尔(Lynne Segal)在《主体性》(Subjectivity)杂志中发表了题为“朱迪斯·巴特勒之后:身份,谁需要它们?”(“After Judith Butler:Identities,Who Needs Them?”)的论文。该文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在回应其他学者的评价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五种发展轨迹:从符号学分析到强调社会文化时刻的重要性;从政治抽象到伦理推理;从对性别号性的集中关注到对“他者”地位的普遍关注;从对外部性和操演性的米歇尔·福柯式介入到对内部心里能动的关注;从对身份认同的拒绝到拥护一定形式的身份政治。[14](P384)莱恩·西格尔的总结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朱迪斯·巴特勒的学术发展轨迹。近年来,朱迪斯·巴特勒已从早期对性别身份的哲学探问转向关注更为宽泛的“他者”所处的政治困境,她将犹太人、怪异人、艾滋病人乃至当今世界一些民族国家中受战争折磨的普通百姓称作“危险的生命”(precarious life),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他们被认为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从而被暴力地剥夺了哀悼等权利的原因。可以说,朱迪斯·巴特勒的一系列著作始终在思考一个黑格尔式的命题,即主体的构成如何必须关涉他者性。为了建立“适宜”的主体性,社会要求驱逐不适宜、不清洁和无秩序的成分。为了建立异性恋规范,非规范的性实践被视为社会禁忌和污染源,成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说的贱斥物,被直截了当地打入“他者”之列。纵观历史,文化规范在社会主体的认同中不断地设定犹太人、同性恋、艾滋病等边缘性社会的存在,幻想出可怕的社会死亡对象,并将其赶入道德和律法合围而成的领地进行压制。从《性别麻烦》到《安提戈涅的声明:生与死之间的亲属关系》,朱迪斯·巴特勒非常关注被规范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如果说《性别麻烦》揭示的是异性恋规范如何以排除像同性恋、双性恋、易性等异己为代价,用一种虚幻的稳定感掩盖性欲的多元性与不连贯性,从而将其控制在以生殖为中心的异性恋的强制性框架内,那么,朱迪斯·巴特勒对古希腊悲剧人物安提戈涅的重读则从哲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人类学的亲属观,剖析了异性恋霸权如何排除他者并否定他者拥有爱和哀悼的权力。可以说,近年来朱迪斯·巴特勒的著作已从集中讨论性别身份转向关注普遍的“他者”地位。在2004年出版的《危险的生命:哀悼和暴力的力量》(Precarious Life: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一书中,朱迪斯·巴特勒还将思想的触角扩展到全球政治所关注的问题当中,她敏锐地剖析了当代政治中霸权对引发战争的主导作用,尤其对由动荡的政治因素而引发普通民众处于暴力甚至死亡的危险境遇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通过不同的理论著述,朱迪斯·巴特勒在回应种种批评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强化了性别操演理论的颠覆力。她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不但解构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解构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女人等范畴本身。朱迪斯·巴特勒对操演性身份的理论建构已成为理解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她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已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目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