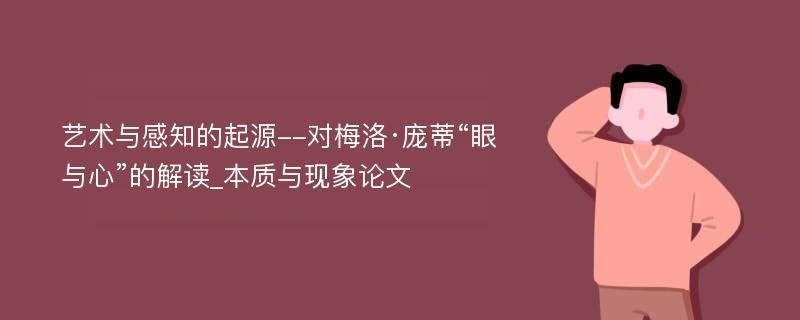
艺术与知觉的本源——梅洛-庞蒂的《眼与心》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源论文,知觉论文,艺术论文,梅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哲学家们常常会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委实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仔细想来,这大约是因为绘画建立在视觉活动的基础上,而视觉从古希腊开始就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视觉“最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揭示各种各样的区别。”[1](P27>这就是说,视觉在各种感觉器官中具有最强的认识功能,因而绘画艺术中或许就潜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秘密吧!
把上述思路反转过来,就意味着绘画的真理性根本上取决于视觉活动的认识功能,因而一旦哲学家们对视觉采取否定的态度,那么绘画的真理性自然也就受到了质疑。不难发现,这正是柏拉图哲学所采取的立场。在他看来,画家和诗人一样,对于自己所描画的事物并无真正的知识,因为知识只能来自于理性,而绘画却依赖于视觉,“视觉器官是肉体中最敏锐的感官,为身体导向,但我们却看不见智慧”。[2](P165>视觉之所以看不见智慧,是因为智慧来自于真正的存在。视觉只能把握事物的颜色和形状,而“真正的存在没有颜色和形状”,它居于“诸天之外”,只有在灵魂与肉体结合之前,通过理智才能直观得到。这样一来,视觉就无法为我们提供真正的知识,而绘画自然也就不可能包含真理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否定感觉以及绘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感性与理性、身体与心灵、现象与本体(真正的存在,即相)截然对立起来,因此彻底否定了身体及其感觉活动的认识功能。要改变这一主张,就必须首先克服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观照梅洛-庞蒂的《眼与心》一文,我们感兴趣的乃是他如何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系统地颠覆了柏拉图的认识论以及本体论学说,从而对于绘画艺术的真理性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当然,梅洛-庞蒂所攻击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柏拉图,而是近代科学以及笛卡尔的视觉理论,但我以为这种批评对于柏拉图也是同样适用的,因为近代科学对视觉同样抱着一种贬斥和否定的态度。梅洛-庞蒂认为,近代科学的内在机制正如康德所说,是一种操作主义或人工主义的模式,它不像古典科学那样把世界本身作为自己探究的对象和目标,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一个理想的人工模型,然后通过在自然状态中的反复调试,使实际的偏差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从而使该模型获得实际的应用前景。[3](P30~31>在这种模型之下,自然本身并未获得真正的把握,因为人们期待自然给出的答案实际上是在该模型中预先设置的。因此,我们的身体及其感知活动,乃至整个的生活世界就都被排除在外了,视觉的作用根本无从谈起。这种对视觉的贬低在笛卡尔那里同样存在。他首先设置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把身体看作外在世界的组成部分,认为身体只是心灵及其意识活动的工具。这样一来,视觉的主体就不再是身体而成了心灵,视觉就蜕变成了思想活动,真正的视知觉显然并没有得到把握。
由此可以看出,要想揭开视觉以及绘画活动之谜,就必须深入探究身体在视觉活动中的作用。为此,又必须首先探明身体本身的存在方式。梅洛-庞蒂指出,身体的特异之处就在于,它“同时是能看的和可见的”。[3](P36>作为“能看者”,身体是视觉活动的主体;作为“可见者”,身体又是视觉活动的对象。身体之所以会成为视觉活动的对象,是因为构成身体的材料与万物相同,因此身体就成了外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另一方面,身体又具有看视的能力,这就使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其他事物作为一种附属品环绕在它的周围。梅洛-庞蒂把这种现象称作“身体的灵化”。不难看出,他对身体的看法与柏拉图和笛卡尔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后两者都把身体归结为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梅洛-庞蒂尽管同样肯定身体的物质属性,但同时却强调这是一种灵化的物质,也就是说他赋予了身体一种两重性或“悖谬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身体就是看与被看、触摸与被触摸之间的相互交织:“当一种交织在看与可见之间、在触摸和被触摸之间、在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之间、在手与手之间形成时,当感觉者-可感者的火花擦亮时,当这一不会停止燃烧的火着起来,直至身体的如此偶然瓦解了任何偶然都不足以瓦解的东西时,人的身体就出现在那里了……”[3](P38>既然如此,只要深入分析身体的这种内在机制,视觉、触觉等知觉活动的秘密也就有望被解开了。
那么,身体究竟是如何形成对于其他事物的视觉的呢?梅洛-庞蒂认为,这是由于身体与其他事物是由相同的材料组成的,因此事物就能够与我们的身体发生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和交流,从而在我们的身体之中形成一种内部等价物。这种等价物具有一种十分独特的存在方式:它与事物本身十分相似,但又不仅仅是原物的某种复制品或派生物,而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举例来说,原始人把动物的影像描绘在岩壁上,这影像尽管依附于岩壁,但却与岩壁本身的存在截然不同。传统理论把这种影像归结为一种想像物,梅洛-庞蒂对此也很认同,但他认为影像并不仅仅是心理活动的产物,而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的视看能力,因为影像与原物的相似性是以我们的身体与原物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然而世间万物是千差万别的,身体何以对每个事物都能产生相似的影像呢?这是因为身体具有某种类似于镜子的功能。镜子的特征在于能够使万物在自身内部原封不动地映现出来,而我们的身体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梅洛-庞蒂指出:“镜中幽灵在我的肉外面延展,与此同时,我身体的整个不可见部分可以覆盖我所看见的其他身体。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可以包含某些取自于他人身体的部分,就像我的物质进入到他们身体中一样,人是人的镜子。至于镜子,它是具有普遍魔力的工具,它把事物变成景象,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3](P48>这就是说,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互相映现的镜子关系。正是由于身体具有这种映现功能,因此人们才能形成对于其他事物的视觉。
把身体比作一面镜子,这看起来并不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因为我们一贯把眼睛看作专门的视觉器官,而近代物理学早就发现了眼睛反射光线与镜子的共同之处。在人们看来,这一发现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开了视觉活动之谜,比如笛卡尔就把视觉归结为一种机械作用,即外部的光线作用于我们的眼睛,从而在视网膜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像。按照这种理论,视觉活动显然并无任何神秘之处,身体在其中只是充当传递信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形成的影像也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只是事物的复制品而已。而梅洛-庞蒂则不同,在他看来,镜子乃是一个“幽灵”,而视觉活动则包含着一种“被动性的神秘”。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视觉活动并不仅仅是通过眼睛这一孤立器官来进行的,而是我们整个身体的映现活动。准确地说,真正的视觉器官并不是眼睛,而是我们的“肉”,或者说是我们作为肉身主体的存在。视觉的产生并不是通过光线与镜子之间的机械作用,而是我们的肉与他人以及其他事物的肉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作为机械装置的镜子其实只是这种相互作用的抽象模型而已。因此,视觉活动的真正秘密并不在眼睛,而是隐藏在我们的身体之中。
二
怎样才能解开视觉活动之谜呢?梅洛-庞蒂求助于画家及其绘画艺术。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画家的视觉活动是别具一格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画家才会“看”事物,或者说画家的“看”才是本源性的视觉活动,而普通人则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
画家的视觉和普通人究竟有何区别呢?事实上普通人最初当然都拥有一种本源性的视觉能力,即都是通过自己的整个身体与事物之间的交流来形成视觉,然而在长大成人之后,人们却接受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视觉活动简单地看成眼睛对光线的反射作用;同时,大多数人都陷入了一种功利性的生活态度之中,对于事物只是关注其最基本、最抽象的外形特征,从而逐渐丧失了与事物进行全方位交流的能力。而画家则不同,他们拒不接受关于视觉的科学以及功利性态度,而是始终立足于和事物之间的肉身性交流。因此对他们来说,视觉活动并无固定的模式可寻,每一次的视觉活动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和体验。在画家的眼中,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像近代思想所宣扬的那样只是一种无生命的机械之物。因此,视觉对于画家来说并不是按照事物的概念去分辨或者捕捉事物,而是让事物的影像或相似物自发地在自己的身体之中萌生出来。正因为这样,画家才感到视觉活动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即画家和景物在相互观察和交流。马尔尚曾经说过:“在一片森林中,我有好多次都觉得不是我在注视着森林。有些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注视着我,在对我说话……而我,我在那里倾听着……我认为,画家应该被宇宙所穿透,而不能指望穿透宇宙……我期待着从内部被淹没、被掩埋。我或许是为了涌现出来才画画的。”[3](P46>这就是说,事物的影像并不是由画家主动构想出来的,而是事物自发地涌现出来的,因此梅洛-庞蒂认为视觉具有一种“被动性的神秘”。既然影像的形成取决于事物自身而不是画家,那么每一次的视觉活动就都是全新的,因为事物是各不相同的,自然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涌现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萌发和涌现正是人的诞生和文化的起源,因为这意味着由此建立了一种人与物之间的交流关系。因此梅洛-庞蒂宣称:“当母体内的一个仅仅潜在的可见者让自己变成既能够为我们也能够为他自己所见时,我们就说一个人在这一时刻诞生了。”[3](P46~47>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诞生乃是一次性或偶发性的,因为他们随后就把这种萌发程式化了。而画家却能够把每一次萌发都变成诞生,因此“画家的视觉乃是一种持续的诞生”。
既然画家的每一次视觉活动都是原发性的,绘画艺术自然也就是非程式化的,因为画家不可能按照同样的模式来描绘不同的事物。然而绘画史上却不断产生某种程式化的表现技法,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透视法”就对此后的绘画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对此应该作何解释呢?梅洛一庞蒂认为,透视法本身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包含线性透视、高空投影、圆形投影、斜投影等多种方式,这表明画家最终仍是按照事物本身显现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表达方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透视法与其说是为画家提供了一种模式,还不如说是为画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刺激,让画家从旧的表现模式中解脱出来,从而与事物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因此,绘画技法和风格的嬗变恰好证明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绘画方法,或者说绘画艺术根本上并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艺术家与事物之间无休止地交流的问题,每当新的交流方式被建立起来,旧的方式便随之失去了生命力。因此梅洛-庞蒂认为,“画家们本身都根据经验知道,任何一种透视技巧都不是一种精确的解决方案,不存在着任何方面都尊重现存世界的、值得成为绘画的基本法则的针对现存世界的投影”,“真实的情况是,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表达方式能够解决绘画的问题,能够把绘画转变为技巧,因为没有哪种象征方式会永远作为刺激物起作用”。[3](P61>
从这种立场出发,梅洛-庞蒂对绘画艺术的各个元素与身体及其知觉活动的关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借此来揭开绘画以及整个视觉活动的秘密。绘画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艺术,自然必须准确地展示事物所处的空间维度。按照笛卡尔的二元论立场,客观事物与自我意识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其具有广延性,这样一来,空间性就成了外部事物的客观属性,与人及其意识活动无关。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笛卡尔把素描看作绘画艺术的典型,原因是素描仅仅以线条来描绘事物,不涉及事物的颜色,而在他看来,只有线条才客观地表达了事物的广延特征,至于颜色则属于事物的第二性质。由此出发,事物的高度和宽度便成了绘画艺术的两个主要维度,而深度则成了派生性的第三维度,因为画面是一种平面的东西,事物的深度其实是无法表现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深度其实是指某种事物被其他事物所遮蔽了,这种深度如果从侧面观察的话马上就转变成了宽度,也就是说深度恰恰是无法直观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笛卡尔式的空间其实是一种无深度的空间。然而现实的视觉经验告诉我们,事物的深度或者厚度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也应该是事物空间性的一个真实维度。梅洛-庞蒂指出:“当我透过水的厚度看游泳池底的瓷砖时,我并不是撇开水和那些倒影看到了它,正是透过水和倒影,正是通过它们,我才看到了它。如果没有这些失真,这些光斑,如果我看到的是瓷砖的几何图形而没有看到其肉,那么我就不再把它看作为它之所是,不再在它所在的地方看到它。”[3](P75>这就是说,当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通过一定的深度或者厚度才把握到它的,如果没有这种厚度,那么事物就不再是其所是。现在的问题是,笛卡尔何以无法解释事物的深度特征?这是因为他把事物的空间特征看作与人无关的纯客观特征,“他的错误在于把空间升格为摆脱了一切视点、一切潜在、一切深度的,没有任何真正厚度的一种完全肯定的存在”。因此,梅洛-庞蒂主张,空间并不仅仅是事物自身的特征,而是与人的身体有着内在的关联,或者说事物的空间特征乃是以身体空间为基础的,这种身体空间同时也是思想的居所:“身体空间并不如同那些事物一样是随便一种样式,广延的一个样本,它乃是被思想称之为‘它的’身体之处所,是思想寓居的一个处所”,“身体对心灵而言是其诞生的空间,是所有其他现存空间的基质”。[3](P62>从这里可以看出,身体实际上成了联结心灵与世界的桥梁,笛卡尔的二元论因此就站不住脚了。
从这种身体空间的观念出发,深度就不再仅仅是事物的“第三维度”,而恰恰成了第一维度,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而恰恰是其他维度的基础:“我之所以看到事物各居其位,恰恰因为它们彼此遮蔽对方,它们之所以在我的目光面前成为对手,恰恰因为它们各处其位。我们从它们的相互包裹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外在性,在它们的自主中认识到的是它们的相互依赖。对于如此理解的深度,我们不再会说它是‘第三维度’。”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认为各种事物都处于一定的空间位置,乃是因为它们彼此相互遮掩,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深度,换句话说,深度乃是事物空间性的基础。而这样的深度显然并不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而恰恰是由事物与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正是由于事物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看不见的,因此它才是有深度的。也正是由于深度乃是事物各种空间维度的基础,因此寻找深度便成了画家的第一要务。贾珂梅迪说,“我本人认为塞尚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深度”;罗伯特·德洛奈也宣称,“深度乃是新的灵感”。在画家的眼中,深度乃是存在的“爆炸”,是事物的“不发声的叫喊”,也就是说当事物的深度对画家显现出来的时候,画家也就把握住了事物的存在及其影像。塞尚以及立体主义者宣称要打碎事物的外壳或者外形,原因就是这种外形只关乎事物的各个空间维度,只有打破外形,寻找到事物的深度,才能弄清这些孤立的维度相互结合并构成事物外形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绘画之所以决然抛弃文艺复兴以来的透视法,转而进行各种奇特的形式试验,其目的就在于把近代绘画中事物那完美的外形拆解开来,从而弄清事物的深度之谜。当然,现代画家并没有也不可能揭晓这一谜底,因为对深度的寻求乃是一项永无休止的事业,而绘画艺术的生命也正维系于此。
对深度的重视必然带来对于绘画艺术版图的全方位重组。首先,对于色彩的贬低态度应该予以抛弃。笛卡尔之所以轻视色彩,是因为在他看来事物的空间性是纯客观的,而色彩则具有某种主观性。但从梅洛-庞蒂的立场上看来,事物的空间性是以身体空间为基础的,因此色彩恰恰集中地反映了事物与人之间的关联。画家的话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颜色是“我们的大脑与宇宙交汇之处”。在他们看来,通过颜色就能够更好地接近“事物的心脏”。正因如此,现代绘画对于颜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印象派绘画甚至为此不惜牺牲事物的轮廓和线条。当然,这并不是说颜色反过来成了营造深度最重要的途径,而是说颜色不再是绘画艺术中可有可无的元素了。其次,线条的优越地位遭到了颠覆。当然,线条仍旧是空间性的重要构成元素,但却不再是唯一的元素,因为人们发现线条也并非事物的自在特征,而是与画家的身体及其视点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存在着自在地可见的线条。不管是苹果的轮廓还是田地与牧场的界线都不是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它们始终都要么不及要么超出于人们注视的视点,始终都在人们所固定的东西之间或后面,它们被事物所致使、所暗示,甚至被事物专横地要求,但它们不属于事物本身。”[3](P78>线条之所以是非自在的,是因为线条并非来自于画家对事物的模仿,而是事物发生和显现的样式:“线条不再模仿可见者,它‘导致可见’,它是事物的发生之图样。”这就是说,线条并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或者轮廓,而是使事物对人来说变得可见的动态标志。正是因为线条具有动态的特征,因此它才总是处在人们的视点之外。也正是由于绘画中的线条具有这种不平衡的特征,因此它才能打破摄影图片那种僵死和凝固的特征,真正刻画出事物的运动和生命特征。进一步说,绘画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仅刻画出了事物的空间特征,同时也刻画出了时间特征。绘画中的线条之所以是不稳定的,就是因为这线条刻画的乃是事物在时间进程之中的空间位置,而且画家为了表现事物的运动和生命特征,还有意使事物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产生错位现象:“提供运动的乃是一种形象,胳膊、小腿、躯干、头在这一形象中各自都是在另一瞬间被捕捉到的,因此形象把身体具象在身体任何时刻都未曾拥有过的一种姿态中,并且在它的各个部分之间施加了一种虚构的连接,仿佛这些不可共同可能者之间的对抗能够并且单独能够让过渡和绵延出现在青铜里、出现在画布上。”[3](P82>表面上来看,画家似乎是在撒谎,照片才真实地刻画了事物的客观形态,然而惟其通过这种谎言,画家才真正表现了事物的内在真实或者存在——事物的生命,而照片却只能使事物静止下来,因此罗丹认为:“是艺术家在说真话,是照片在撒谎,因为在现实中,时间不会停止。”
三
梅洛-庞蒂探讨绘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揭开视觉活动的秘密,而分析视觉活动又是为了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因而《眼与心》的真正旨趣显然是在形而上学方面。不过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却并不是这一点,而是梅氏的绘画理论在艺术以及美学方面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文的最大建树显然在于颠覆了柏拉图对于绘画以及艺术的真理性的看法。柏拉图断言艺术家只是说谎者,因为艺术与真理隔了三层,而梅洛-庞蒂却认为在绘画艺术中,“沉默的存在最终显示出它自己的意义”。那么,梅洛-庞蒂为绘画艺术所作的这一辩护能否成立呢?这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分析。柏拉图之所以否定艺术的真理性,是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一种感性活动,因而只能模仿具体事物而不能模仿相本身,而具体事物在他看来则只是现象或者非存在。与之相比,梅洛-庞蒂至少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差异:首先,他否定了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存在(on)区分为10个范畴,并且主张只有本体(ousia)才是存在的首要含义或者本质,而其他9个范畴如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则都只是属性范畴。[4](P5~6>而梅洛-庞蒂却认为,“深度、颜色、形状、线条、运动、轮廓、面貌就是存在的枝条”,而且“其中之一就会把我们引回到整束枝条”,这显然是在否认各种属性的背后还存在所谓本体或者载体。而绘画艺术之所以对梅洛-庞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就是因为在他看来,“通过展现它关于沉默意义的肉身本质的、效果相似的梦幻般宇宙,绘画把我们所有的范畴,诸如本质与实存、想象与实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都混淆起来了”。从这段话来看,他实际上认为本质与实存等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为宇宙万物都具有一种肉身本质,也就是介乎于物质与精神、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暧昧性存在。而画家从自己的艺术直觉出发,始终致力于与世界建立起一种肉身性的交流,因而对形而上学的诸种概念和教条有着天然的免疫力,因此他们恰恰能够揭示出世界的这种真相。其次,他同样否定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在现代思想当中,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无疑是胡塞尔,他的本质直观学说就是强调直观活动不仅能够把握现象,同时还能够把握本质:“不仅个别性,而且一般性、一般对象和一般事态都能够达到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5](P6>梅洛-庞蒂尽管并未直接援引胡塞尔的这一思想,但他对于形而上学所设置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分法显然也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这一点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有明显的表现。在那里,他旗帜鲜明地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看作知觉问题上的两种错误主张,认为知觉活动既不是像经验主义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刺激-反应行为,也不是像理性主义所说的那种纯粹的思想活动,而是身体-主体的一种意向性活动,而身体本身则是一种暧昧性的存在。不难看出,这一主张同样贯穿在了《眼与心》一文中,正是因此,他才反复强调视觉乃是身体与世界之间肉身性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正是由于梅洛-庞蒂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彻底颠覆了传统思想的二元论主张,因此才为绘画艺术的真理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既然世界本身就不存在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视觉乃至整个知觉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感性活动,因此强调绘画或艺术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就站不住脚了。值得指出的是,梅洛-庞蒂为绘画艺术所作的这种辩护在现代思想中并不是孤立的,他的现象学前辈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也曾宣称,艺术的本质乃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6](P20>不难看出,这与梅洛-庞蒂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存在的意义在艺术作品中能够自行显现出来。而从整个思想史上来看,为艺术辩护者显然还大有人在:英国诗人锡德尼和雪莱都曾以《诗辩》为题撰写过论文。不过在我看来,这一领域卓有成效的思路无非有两条:一是采取辩证思维的方法,其特点是把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视为客观的现实,而后再试图使对立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获得统一,这显然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向。二是现象学的方法,其特点是回溯到这些二元对立尚未发生的本源性状态,从而寻找到一种特定的认识路径,这种路径能够在感性活动中以直观的方式来把握本质或真正的存在,我以为这正是现象学运动的思路——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海德格尔所谓前存在论的理解和领会活动、萨特所说的“前反思的我思”等等,所指向的都是这种本源性的状态,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显然也活动在这一路径之上。仅就艺术问题而论,我以为现象学的思路是更加有效的,因为辩证法尽管持一种对立统一的思想,但仍旧坚持把理性、本质置于感性、现象之上,因此归根到底仍然把艺术置于科学以及哲学之下。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黑格尔尽管把艺术、宗教、哲学看作绝对理念自身显现的三种途径,但却主张艺术乃是其中最低的一种,并且由此得出了艺术消亡的结论。而现象学则不同,由于它主张回溯到非二元性的本源状态,因此艺术恰恰成了显现真理的基本途径。海德格尔就明确把艺术的真理性置于科学之上,认为艺术、牺牲、思想等乃是真理的原始发生方式,而科学则只是一种衍生形态。[6](P45~46>梅洛-庞蒂甚至认为,艺术因此而反过来成了哲学的拯救之途:“哲学的这种衰落是非本质的,是从事哲学的某种方式(根据实体、主-客体、因果性)的衰落。哲学将在诗歌、艺术等等之中,在一种与它们的更为紧密的关系中找到帮助,它将重新诞生并因此重新解释它自己的形而上学过去。”[7](P124>在我们看来,这一事实至少说明梅洛-庞蒂的观点属于当代思想的主流。
收稿日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