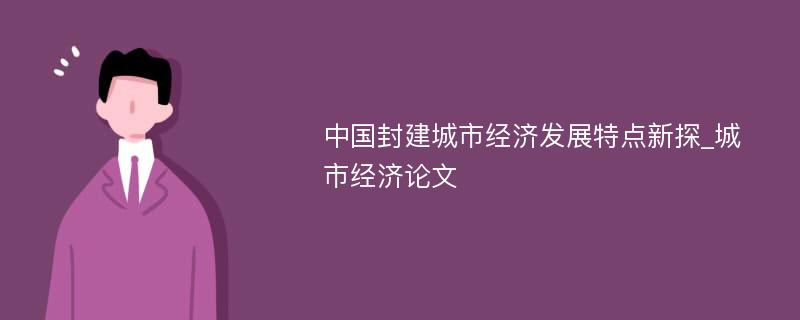
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封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2-0103-07
一、小农经济结构与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
就中国封建经济的整体结构分析,它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而这些差异本身,必然会影响于彼此的城市经济发展,并使之形成各自相异的城市经济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元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其规模相对狭小,生产关系上的各个环节,从生产到流通、分配和消费不可能在一个家庭中完全实现,因而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与市场发生依赖关系,自给程度有限;相比之下,西欧封建社会的庄园制经济的自给程度显然更高。由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所决定,中国封建城市中的商品经济自古以来即非常发达,而西欧封建城市中商品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
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郡县制城市体系至少在隋唐以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但并不能由此否认仍有大量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存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以“亦一都会”来称呼这些城市。邓福秋认为,司马迁在此用“亦一都会”,是指上述的几个经济都会城市同时也是郡国的政治中心,“其所以交代它同时也是郡国的政治中心,是因为它的主要社会作用,对于商业经济来说,不在于它是政治中心,而在于它是一个商业区的经济中心。这就是说,‘亦一都会’的社会价值,经济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政治是第二位的,次要的”[1]。由此反观西欧封建城市,其政治职能及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得更加充分,以至于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认为,如果以城市为工商业中心,则加洛林王朝时代可谓无城市;如果以城市为行政中心、军事堡垒,则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城市可谓和以前一样多。[2]皮朗的这种提法尽管被一些学者认为过于绝对化,但以此来说明封建社会早期欧洲城市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当是没有问题的。
大约从10世纪前后开始,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几乎同时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化,其结果一方面使封建城市由单一的政治、军事功能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功能转化;另一方面则在一部分新兴城市中,由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巨大发展,其经济机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西欧封建城市在9-11世纪所出现的历史性转变众所周知,这里勿需多言。容易为人忽视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封建城市同样发生了与其相类的历史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为封建政治中心城市的经济机能不断强化,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在城市发展中开始居于重要地位,而这正是以“破墙开店”为表征的、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宋代城市革命”。在中唐以前的城市中,作为居住区的“坊”与作为贸易区的“市”是明确分开的,店肆集中于市内,且交易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中唐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渐告废弛,入宋以后即彻底崩溃。城内店铺林立,“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3]。与城市商业发展相联系,其宵禁制度也逐渐废除,“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之处,通晓不绝”[4]。坊市制度的破坏,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对城市居住和商业限制的解除,城市所能容纳的市场空间可以扩大至市区的各个角落乃至溢出城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这一明显特点从欧洲人的描述中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布罗代尔在考察了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城市后转述曾到过中国的马加良恩斯神甫的话说:“18世纪中国城市中沿街都是店铺,招牌高竖,布幌招展,‘这一习俗给公众带来方便,因为在我们欧洲的城市中,大部分沿街房屋都是大人物的府第,人们为了置备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走远路到广场上或码头上去购买。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则不然,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一切日常用品,甚至能找到取乐的场所,因为这些房子不是商店就是酒馆、小铺子’。”[5]马加良恩斯神甫的描述表明,直到18世纪,中国城市中的市场分布比欧洲城市要广泛得多,其繁荣程度比西欧城市也要高得多。
二、人口流动与城市规模的扩大化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相异于西欧的另一特点表现在农民具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可以自主择业,流动性较强;而西欧封建庄园制度下的农奴没有人身自由,是“土地上的奴隶”。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一基本特点与小农经济自给程度有限的特点相联系,使中国封建城市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有可能聚集起比西欧封建城市更多的人口,进而造就封建时代城市人口的最大规模。
众所周知,在直到18世纪以前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城市无论就其人口规模还是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而言都是雄居世界首位的。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1350个有行政官署的城市中约有150座的人口超过万人,全国城市人口比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6]美国华裔学者赵冈则认为这一比率可高达约20%,而北宋首都开封的总人口应在140万以上。[7]与中国封建城市相比,西欧封建城市的人口规模要小得多。一直到14-15世纪,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整个西欧地区只有巴黎、科隆、伦敦三座人口超过5万人的大城市。那些后来著名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如布鲁塞尔、纽伦堡、卢贝克、斯特拉斯堡等,当时都只不过二三万人。西欧封建社会中更多的是人口数量在2000至5000之间、甚至于只有几百人的小城市。[8]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首位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封建时代小农经济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市场交换这一经济基础,同时也在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并未从制度上对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加以严格限制。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土重迁”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体制。自春秋战国以降,国鄙的划分消失,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一直是相对自由的,农民每逢荒歉之年往往离乡到城市谋生,其规模动辄百万。而且即使是在正常的年份,小农户若男丁较多,也往往让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个出外经商,而由其他居家者照料农田。这在中国古代是极其常见的,史书中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即使是从城市本身的记载分析,中国古代城市人口的流动性也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寓居城市经营工商业者众多。与此同时,中国封建城市对外乡之人的到来并不持排斥态度,如苏州梳妆业公所章程规定:“一议,外方之人来苏开店,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二十两;一议,外方之人来苏开作,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十两;一议,本地之人开店,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二十两;一议,本地之人开作,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十两。”[9]由此可见,外地人与本地人开张营业所纳费用完全相同,表明外地人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并未受到歧视。毋宁说,正是中国封建城市所具有的较强的容纳能力才使得农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成为可能,同时,城市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踵接而辐辏”的商贾才维持了其长久的繁荣,并使中国古代城市人口数量长期雄居世界首位。
附带说明的是,西欧封建城市之所以规模小、人口少,其原因首先固然在于西欧封建庄园制经济的自给程度较高,从而限制了城市经济的扩张,但更重要的则一方面在于中世纪欧洲庄园制度下的农奴没有迁徙自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之成为“土地上的奴隶”(servi terrae);另一方面封建城市又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按照英国伦敦13世纪的情况,城市市民资格可由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项取得:(1)合法出生于本城市;(2)经过学徒成为某行会的会员;(3)交纳一笔钱买得。[10]意大利威尼斯市政会议明确规定了两种公民权:完全公民权和部分公民权。其中在该城居住满15年才有资格申请部分公民权,满20年方可申请完全公民权。[11]西欧封建城市中的行会一向被公认为是封闭性的组织,其吸纳新成员的条件在一些城市中规定得极其苛刻。就其一般而论,一是财产资格限制;二是合法出生的自由人;三是具有市民资格或由两个以上具有公民权资格的人做出担保。[12]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居住者,如果既无市民资格以及与之相应的公民权,又不被垄断城市工商业的封建行会所接纳,那么城市所留给新来者的生活空间何在呢?布罗代尔对此直言:“被叫做苦力的都是外乡人;……乡村的弃物变成城市的渣滓”,而在灾荒之年,城市则紧闭城门,拒绝接受任何的新来者,如法国第戎市政当局就曾严令禁止公民为行善而收留贫民。[13]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所具有的相对的人身自由为城市规模的极度扩张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西欧封建农奴缺乏自由及城市的排他性、封闭性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城市规模小、人口少的基本状况。
三、社会竞争与城市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前两个特点所导致的是中国封建城市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及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那么以地主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地主经济本身则使整个社会经济相对于西欧封建经济呈现出竞争激烈的根本特点。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领主制经济下,封建领主不仅可以世代相承地、稳定地占有领地,而且能够占有劳动者农权本身;他们不仅具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从经济结构看,这无疑是一种相对于中国更具自然经济色彩的体制,封建庄园以其较多的劳动力进行着内部的简单分工,使之不仅能够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必需的手工业制造品;从社会结构看,这更是一种僵化得近乎凝固的制度,领主与农奴的身份明确,地位固定,而且这一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因封建农奴缺乏相对的人身自由及通婚自由而几乎没有改变的任何可能性,农奴既不能奢望经济地位的上升,更不能奢望政治地位的改变。这对城市工商业者亦然,“城市手工业者则把他的手工业和他的行会特权,世袭地、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还会把他的顾客、他的销售市场以及他自幼在祖传职业方面学到的技术继承下来”[14]。这种世代相承相袭的生产方式,与西欧封建自然经济下市场狭小的特点相联系,使城市工商业者“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宗法式的乐园,他们这种因循苟安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惊扰的”[15]。西欧封建行会正体现了这一追求平等、反对竞争的社会特色,它们“限定价格、维持工资水平,以防止降低产品成本,保持传统的一致性,扼杀竞争,……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被拒之千里”[16]。
相对而言,中国封建时代以地主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地主经济,使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既充满了以争夺土地为直接目标的竞争,又充满了以增殖财货为目标的工商业竞争,还有着以提高社会地位为目标的“权”、“钱”之争。其结果一方面使城市经济因竞争的广泛存在而更趋繁荣;另一方面则又因这一竞争本身往往偏离商品经济的轨道而给城市经济的顺利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仅就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部分而论,主要表现在:
(1)城乡之间的经济竞争。城市工商业相对于乡村农业而言,具有利润丰厚且获利较快等优势,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之说。正是基于工商业获利较丰的吸引,中国历代皆有众多的农民或兼营工商业,或弃农从商。进入宋朝以后,乡村居民参与工商业活动者日趋普遍。明清时期,乡村农民外出经商更趋普遍,尤其是在经济相对繁荣及人口密集地区,农民外出经营工商业者已过其半数,所谓“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17]。在外经营的乡民,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经营农业,而将工商业所得补贴家用,或购置田产,或供子弟读书求学,其与商争利的目的极其明显。然而,农民相对于工商业也存在其固有的优势,即土地收入尽管有限,但风险小,相对稳定,且农民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中有较高的地位,并可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商业者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而,在农民向城市工商业争利的同时,城市工商业者也试图通过“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向乡民争利,其前提则是“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18],即土地可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这一相异于西欧的特点,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城乡经济间的互融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商业原始资本的形成,进而对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2)城市工商业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对自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的许多大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个人发家史进行了历历如绘的描述。他不仅叙述了这些人如何地惟利是图,而且还着重指出了其赖以成功的共同特点:有一种在经营上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竞争环境。这使之能够各自竭尽其聪明才智,“设机巧,仰机利”,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这一点又与西欧封建城市工商业发展中行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西欧行会的主要作用正是表现为使每个成员都能获得营业上和生活上的均等机会,使成员之间彼此要“余力而让财”,而其主旨则在于消除城市工商业者内部及外来的任何竞争。或许正是基于两者之间的这一差别的存在,才为中国封建城市中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比西欧中世纪城市更为合适的环境,并使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展现出较西欧中世纪城市远为繁荣的景象,以至于自马可·波罗以后直到明清时期到达中国的诸多外国人都对当时中国城市工商业的盛况表示了极大的惊诧和赞佩。
(3)官僚贵族与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中国官僚体制区别于西欧封建“分封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尽管整个封建社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社稷无常侍,君臣无常位”[19],王朝更迭频繁,政治权力不断进行着再分配,“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屡见不鲜。这一帝王将相不断改姓换人的现实,为城市工商业者参与竞争提供了可能性。凭实而论,无论是官僚贵族还是富商巨贾,都有其各自的遗憾,因为他们都还算不上集富贵于一身。前者可谓“贵”,有的是“权”,但缺的是“钱”;后者可谓“富”,有的是“钱”,缺的是“权”,两者共同的愿望则是既贵且富。但在封建制度下,“士大夫不亲于工商,工商之子不当仕”[20],他们要各自达成既富且贵的愿望,势必要经过一番竞争。尤其是进入宋朝以后,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城市工商业者的地位有所上升,两者之间的竞争开始趋于激烈。这一方面表现为官僚经商、与工商业者争利已呈普遍化趋势,其目的则在于由贵而富,所谓“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也”;“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21]。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城市工商业者拚命跻身仕途,力争由富而贵。其方式则可谓花样百端,合法非法并用,目的无非是干进求仕,既可保护已有财富,更可集富贵于一身,光耀门楣。与此同时,由于科举制度下,要获取功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非兄老先营事业于前,子弟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城市工商业者所拥有的财富优势由此得以显现,其结果恰如沈尧所论:“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22]较为客观地讲,官僚贵族与城市工商业者之间的这种“权”与“钱”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得城市工商业经营更呈普遍化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工商业者政治地位的相对提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官吏的敲榨勒索,从而有助于城市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政府调控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迟滞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既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已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及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水平来看也远非西欧中世纪城市所能企及,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何以在西欧封建城市中得以孕育并顺利成长呢?对这一问题的索解,需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调节机制入手。
前已言之,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由于社会有机体的细胞相对狭小,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从生产到流通、分配和消费,便不可能在一个家族范围内完全实现,而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与整个社会有机体发生依赖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依赖关系,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获得了较之西欧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空间。但就其根本而言,一个个小农的基本倾向是自给自足的,整个封建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倾向也是自给自足的,因而这种依赖关系的极度发展势必会形成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的经济职能进而把整个社会有机体演变为庞大的自然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与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僵化结构有所不同,不仅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及高度的应变弹性,而且有着相当完善的调节机制。它既可以在强化自然经济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倾向之间来回摆动得很远,又可以适时地阻断农、工、商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渠道,以免商品货币经济溢出封建自然经济所能容许的限度。而其中的关键环节,或者说封建国家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的有力杠杆就是“重农抑商”政策。
对于“重农抑商”政策,不能单纯地、或者片面地理解为“让农民不离开土地”,它作为一种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的经济政策,实可看作封建国家既要以农为本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即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23]之时,国家应劝民农耕;当“举世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游食者众”[24]之时,国家应抑制工商业的过度发展。可见,所谓重农抑商政策的着眼点,是封建国家基于小农经济既在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的存在,而维护小农经济本身又不可使其过度发展这一客观现实,努力寻求农本经济与工商业发展之间的平衡。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货币资本的积累、社会财富的集中何以在动乱之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并长期雄居世界前列,才能理解依附于封建生产关系并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小生产者不断转化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也惟其如此才能理解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每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横遭扼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屡仆屡继,蹒跚难行。
从另一角度看,正是由于“重农抑商”的政策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才使得封建国家政权有可能建立起日趋完善的调控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等各方面的力量,强力抑制工商业的过度发展,并使得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地被打乱或阻断,既不可能使手工业作坊持续长久地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使商业资本大量地顺利转化为产业资本,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瓦解封建的自然经济体系。由此,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工商业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到相当繁荣的程度,甚至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却始终无法超脱出封建经济的窠臼。
勿庸置疑,西欧封建经济结构中也有相应的调节机制,并具有与中国相异的特征。单就以城市工商业为中心的部分言之,其经济调节的着眼点在于避免乃至消除竞争,以保证有限的市场,即通过市民资格的授予及行会本身的排外性尽可能排斥外来者,以消除潜在的竞争威胁;通过限定价格、维持工资水平、限制产品种类及其产量等方法尽可能排斥城市工商业行会成员之间内在的竞争;通过限制外来商品在本地出售和阻止外来工匠在本地开业,尽可能排斥外来的竞争。这种调节机制是僵硬的、脆弱的,而且由于其力倡者及执行者不是封建国家而在于城市工商业者本身,一旦遇有外来的强有力冲击,这种调节便会在顷刻间冰消瓦解。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由资本主义萌芽到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一个缓慢而又艰难的过程,即便是在除英国外的西欧国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经受过夭折或挫折的历史。中国封建的小农经济可以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基础,小农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的人身自由也可以为城市人口的集聚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小农作为小私有者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以求得生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这又使之具有发展生产的极大积极性,并以此带动社会各阶层的激烈竞争。从根本上说,社会各阶层广泛竞争的存在才是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本质特征,因为前两者只是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条件,竞争才使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并使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发展中领尽风骚近千年。相比之下,西欧封建社会既不存在社会竞争的基本前提,而封建城市本身又视竞争如洪水猛兽,竭力避免竞争的发生,从而窒息了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中世纪的“黑暗”。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正是基于竞争的广泛性,才使中国封建政权得以凝聚起以“重农抑商”为杠杆的相对完善的经济调节机制。它可以允许竞争的适度发展,同时也为之划出了难以逾越的界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界限的极点处徘徊了几个世纪却始终无力将之冲破。
〔收稿日期〕2001-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