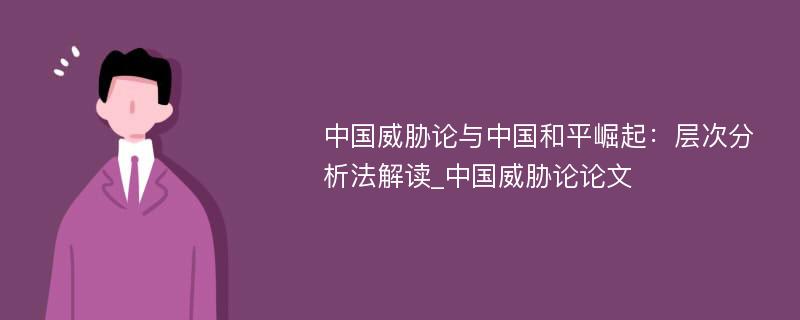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种“层次分析”法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威胁论论文,层次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几经变迁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之一。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即使到了本世纪初也尚未偃旗息鼓。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2004年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命题,从大战略的层面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就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而言,“中国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相反的图景。因此,了解中国崛起在国际上所产生的“意象”( image) ,探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并揭示其逻辑盲点,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空间,探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
一、“中国威胁论”的缘起
“中国威胁论”一般是指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的观点、理论和思潮。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并且成为某些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时尚。宣扬、赞同与附和“中国威胁论”的人可谓形形色色,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既有声东击西、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也有不知内情、人云亦云的普通民众;既有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的新闻记者,也有标新立异、各执己见的专家学者。
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 (P1),但该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1992年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甚至某些政界领导人开始对中国国力的上升表示担忧,并从各种角度、在各种场合提出并宣扬“中国威胁论”。英国《经济学家》1992年出版的专刊《当中国醒来时》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刊登的文章《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可谓开“中国威胁论”先河之“大作”。自此,“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舆论中开始赢得市场。1997年,罗斯·芒罗 ( Ross H.Munro) 与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在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宣称:中国在下世纪成为世界主导力量后,肯定是美国的长期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2]。《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可算是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巅峰之作。
这些西方媒体的思想很快在亚洲引起了回应。1992年8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断言:“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均势的不稳定因素。”[3] (P24)1993年5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时则表示中国经济一经发展,就可能在军事上抱有野心。而东南亚国家由于在历史、领土及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存在着利益冲突,因而“中国威胁论”一度在东南亚也颇具市场。1995年10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演说时宣称:“中国是东亚地区头号威胁。”[4] (P2) 菲律宾军事领导人甚至还宣称:“中国像是南沙群岛的传染病,我们必须发展足够的抗体以预防它的传染。”[5] (P158)印度等国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对“中国威胁论”在亚洲地区的扩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中国威胁论”的表现形式与主要论据
“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军事威胁论”;二是“中国经济威胁论”;三是“中国生态威胁论”;四是“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五是“中国文明威胁论”。
(一)“中国军事威胁论”
1.中国军费的高速增长。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夸大中国军费的规模和水平,声称中国正在用一种危险的方式使用财富,这就是将其用于大规模的军事集结[1] (P2)。例如,罗斯·芒罗为了证明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竟宣称“对中国实际军费的保守估计将为官方宣布的10倍。换言之,中国的实际年度军事预算至少相当于870亿美元,约为美国预算的1/3,日本的75%。”[6] (P25)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军费增长速度太快,而军费增加意味着中国可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还有人提出,中国军费增加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7] (P24-28)。
2.中国的军事力量“填补真空”,给亚太地区的均势带来威胁。“填补真空”论是指中国正在趁苏联解体和美国军事力量收缩的时机增强军事力量,以填补亚太地区的“真空”。1993年载于美国《外交》冬季号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将填补前苏联及美国退出太平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进而扩张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8]。这种“真空”将诱使中国以武力来解决其与周边国家间的边界分歧。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强大后可能会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从而引起新的边界冲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由于中国将南中国海视为其合法的国家世袭遗产,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为占有潜在的宝贵的海床能源资源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存在争议,而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9] (P205-206)
3.核能力和导弹技术发展。1994年,美国军事专家进行了5次以中国为假想敌、发生在台湾海峡的模拟战争,结果都是中国利用先进的导弹技术将美国航空母舰击沉,并取得了胜利[5] (P65)。1999年初的“李文和”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美国对中国核能力发展的疑惧。1999年5月25日,美国国会炮制的《考克斯报告》出笼。这份报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这种窃来的美国特定技术用于下述目的: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能力、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美国、美国的朋友和盟国或者美国的部队直接构成威胁。”[10] (P13)2002年7月12日,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评估报告》中宣称,中国在华南部署的数百枚短程导弹不仅威胁到台湾,也威胁到驻琉球的美军,以及美国的盟邦日本和菲律宾[11]。美国还担心中国向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扩散导弹有关技术。
(二)“中国经济威胁论”
1.对中国经济现实的估算。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 Irving Kravis) 首先提出以购买力平价( PPP) 方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12] (P60-78)。90年代以后购买力平价方法逐渐被一些国际组织采纳用以估算中国的经济实力。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的56%。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应为1.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的 23%。无论如何,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一下子将中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2倍以上[13] (P20)。
2.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测。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美国“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发表的《明显的威慑因素》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居世界第二位[14] (P231)。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认为,到2020年中国可能超过日本和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威廉·奥弗霍尔特认为:“如果按照萨默斯的计算方法,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将在11年内超过美国。如果与泰国的类比准确的话,那么它将花一代人的时间超过美国。”[13] (P21-22)
3.“中华经济圈”的形成与扩张。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将会导致“华人经济圈”或“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就提出:“中国能从日本手中夺得经济领导权力的潜力不仅在本土,更在于广大的海外华人集团,它造就了中国与华人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这种华人经济圈……已经渗透于整个亚洲,并向全球蔓延。”[15] (P10-11)
4.亚洲国家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金的争夺加剧。由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雷同,中国在西方不断扩大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占领了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外国投资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所以中国的崛起将影响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
5.贸易威胁。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以其低廉的劳动成本优势向美国国内市场倾销产品,同时却阻止美国产品和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从而造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将不断加剧。在他们看来,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加大,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断扩大,西方的工业将会大规模地转向中国,从而造成西方国家失去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的工会中较为流行。例如,有48万会员的美国国际机械和航空航天工业工人协会就反对波音公司向中国提供制造技术,并要求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惩罚
(三)“中国生态威胁论”
1.空气污染。在西方国家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过程将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量将迅速增加,这种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16] (P142)。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万吨煤尘进入天空[17] (P28)。亚洲释放的硫氧化物中也大部分源于中国[18] (P4)。这种环境问题将超越国界,对全球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将首当其冲,遭受池鱼之殃。
2.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位于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据估计,到2020年前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由于中国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发达国家普遍关注中国的温室气体增长,认为如不对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中国快速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全部或部分抵消发达国家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努力,使国际社会为保护气候的努力付诸东流。有学者认为,中国燃煤所排出的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反常、甚至引起孟加拉国和世界其他沿海地区发生洪涝的关键[8]。
3.粮食威胁论。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发表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布朗认为当今世界已由粮食过剩时代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综合各种因素,今后世界粮食供求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根据许多国家的教训,工业化进展越快,耕地减少速度也就越快,到2030年,中国预计将新增加4.9亿人口,而今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将减少1/5,未来中国必将大量进口粮食,这时世界粮食的供给能力萎缩与中国的需求膨胀必将发生激烈矛盾,进而导致世界市场粮食价格的攀升[19] (P29-32)。
4.能源短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还将导致中国的能源危机,从而形成对全球能源的“潜在威胁”,1996年美国《世界政策杂志》春季号刊登题为《中国迈进资源缺乏时代》的文章,认为在1994年中国成为能源纯进口国后,这种影响正在全球体系中扩大,1994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约5桶石油,保持这样的水平到2005年,中国将每年多进口60亿桶。如果没有其他石油资源被发现,中国迟早不得不到其他方面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他的选择代价可能更大,它不仅表现在财富上,也表现在流血战争方面[19] (P424-428)。2004年,英国石油公司( BPPLC) 首席经济学家皮特·戴维斯表示:“中国现在对能源流动有着难以置信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不仅是在亚洲,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界能源市场的整个重心正在转变。”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石油进口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得以在当年很多时间中将油价保持在每桶30美元或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20]。
(四)“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到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严重挫折,认为推行西方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大好时机来临,于是加紧在世界上推行西方的民主观念。一些学者和媒体认为,由于中国是冷战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但中国仍然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以中国崛起后仍有可能成为非西方意识形态国家的领袖。这必然对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构成挑战。罗斯·芒罗和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序言中强调:“中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价值观上与美国相敌对。”英国《旁观者》杂志发表《充满东方威胁》的文章中说:“军事冲突总是因意识形态或经济冲突引发的,在我们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这两种冲突都有。……中国也许已决定了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导亚洲的计划,这种威胁已经足够了。”[21] (P10-12)因此,中国是“非民主”国家本身就已经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必然逻辑[22] (P40-44)。
(五)“中国文明威胁论”
西方国家将西方文明看作“普世文明”,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原则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因而把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华文明”看成是世界稳定的威胁和世界冲突的根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预言:“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冲突的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也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文化方面的。”1993年夏,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篇论文。在他看来,“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成为未来国家间战争的根源,中国将与伊斯兰国家联合起来,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形成挑战。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发生”[23] (P7)。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左右世界政治,西方面对的主要敌对文明是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扩张。
三、从“层次分析”看“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层次分析”( Level-of-Analysis) 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 ( Kenneth Waltz) 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了“三个意象”:第一意象即通过考察人性和人的行为来解释战争的原因;第二意象即通过考察国内结构来解释战争的原因;第三意象即通过考察国际无政府状态来解释战争的原因[24]。1960年,戴维·辛格( David Singer) 在对《人、国家与战争》的书评中,首次提出了“层次分析”的概念。1961年,辛格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正式提出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概念,由此奠定了“层次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中的基础性地位[25]。肯尼思·沃尔兹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中,通过对结构的三方面定义进一步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明确区别开来,由此确立了结构作为体系层次主变量的地位。由于国际政治体系在排列原则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王国”,并由重复彼此活动的同类单元所构成,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实际上只能由结构的第三个方面——“能力的分配”来定义。用沃尔兹的话说:“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由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更简单地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而造成的。未来的结果的变动范围是依照假定的单位动机以及单位在其中活动的体系的结构而定的。”[26] (P3)
根据沃尔兹和辛格的“层次分析”法,我们可以检视“中国威胁论”上述5个方面的论据是在哪个层次上产生“中国威胁”之“意象”的。从“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生态威胁论”的基本论证逻辑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军力增长和资源消耗大都归位于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由此引起的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因此,前3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基本是在“体系层次”上提出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而“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和“中国文明威胁论”则聚焦于中国与西方的异质性,即认为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单元属性,从而会威胁和挑战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因此,后两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实质是在“单元层次”上提出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威胁”。
这样,无论是从“体系层次”还是“单元层次”上来看,都可能根据其主变量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系推导出“中国威胁论”。如果说“单元属性”与国家对外扩张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待于理论上的进一步提炼和经验上的进一步检验(注:着眼于单元属性的“民主和平论”与“文明冲突论”即使在美国也争议颇多。“文明冲突论”只是亨廷顿的一家之言,“民主和平论”关于“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的机理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那么“体系层次”上新兴大国挑战国际秩序的命题似乎得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更多支持,例如奥根斯基( A.P.K.Organski) 的“权力转移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 的“霸权周期理论”等,从而使这一层次上关于“中国威胁”的推论似乎具有更大的逻辑力量。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前3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会在西方知识精英中间具有那么大的市场了。然而,“中国威胁论”在逻辑上所具有的最大盲点正在这一“体系层次”上。
作为“层次分析”方法的主要奠基人,沃尔兹将体系层次上用以解释国家行为的主变量化约为大国间的实力对比,这种做法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就认为,沃尔兹的体系概念过于简明,解释不了多少东西。这里的争论并不在于是“体系层次”更重要还是“单位层次”更重要,而是如何进行“体系层次”的分析,即:“体系分析到底是简明一点好,还是复杂一些好呢?”对此,约瑟夫·奈( Joseph Nye) 认为:“我们如果分清体系的两个方面,即结构和过程,就可以理解这种争论。体系结构指权力分布,体系过程则指体系单元之间互动的模式与类型。显然,结构和过程相互影响,而且它们都可能发生变化。”[27] (P55)在约瑟夫·奈看来,如果我们既关注体系的结构,又关注体系的过程,即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那么我们将学到更多的东西。
反观“中国威胁论”的上述论据,大都聚焦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单元的属性,而忽略了国际体系进程的变化,即国家间互动模式的变化。因此,仅仅依据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单元的属性来推断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对外行为方式,在分析逻辑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实际上,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盲点。他们认为,中国究竟是否会威胁和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并非像“中国威胁论”者所认为的那么确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互动,特别是中国对由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机制的态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一书中就认为,中国必须对国际规则作出战略抉择:是基本维持国际体系现状、参与和支持现有的国际规则、当一个“建设性的伙伴”,还是调动现实的和潜在的一切力量和资源,运用各种方式和策略去改造或推翻这些国际规则[28] (P100-102)?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也认为中国未来与国际机制的关系有3种选择:第一,当中国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是自信的,但同时中国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时,中国会有意识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国际机制现状的联盟相对抗。第二,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地区扩大影响,设法确立自己远东主要大国的地位并对区域性稳定提出严重挑战。第三,中国融入现有国际机制中,决定成为现行全球社会体制的一部分[29] (P211-213)。无论根据傅高义列出的两个选项还是根据布热津斯基列出的三个选项,如果中国在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决定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和遵守国际规则,中国的崛起就不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实际上,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已经为中国在上述选项中如何作出“战略抉择”提供了初步的答案。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中国就开始淡化了国际秩序“挑战者”的色彩。这个从“挑战者”向“建设性的伙伴”转变的过程集中体现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如果说1971—1978年是“消极参与”, 1979—1991年是“部分参与”的话,那么1992年以后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战略就是“全面参与”[30] (P251-261)。在基本认可现存国际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参加了军备控制、人权、贸易和投资、金融、信息、能源、环境保护等多个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并根据自身的实际能力和利益需求而在其中一些机制中发挥着建设性乃至主导性的作用。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在多边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处理全球和地区公共问题的新理念,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中国外交新思维”[31] (P13)。仅就最近几年的外交实践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朝核六方会谈的开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中国对《京都议定书》的批准等,无不折射出中国对参与国际制度的积极态度,展现了一个“和平的、合作的和负责任的大国”( peaceful,cooperative and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国逐步参与国际制度并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有所作为的进程。两个进程的共时性使中国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崛起。正是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使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特点。正如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Michel Oksenberg) 和伊丽莎白·埃克诺米( Elizabeth Economy) 所指出的:“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为进一步推动它们在国际机制中的合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国广泛地参与了国际事务。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领导人改组了政府机构,还允许外国大规模地参与中国的发展。事实表明,到目前为止,同先前的新兴大国崛起的同期相比,中国有着天壤之别。”[32] (P21)通过积极参与现有国际制度,中国可以在崛起的过程中有效疏解它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压力,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空间也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新兴大国都要宽广、夯实。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无疑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