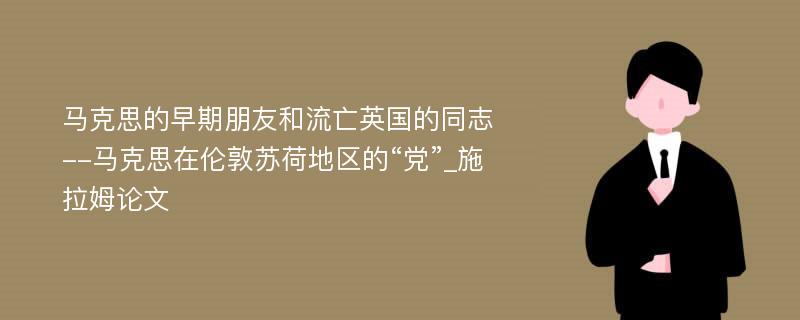
马克思英国早期流亡生活中的朋友和同志——马克思在伦敦索荷区的“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英国论文,同志论文,朋友论文,生活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以后的几年间,英国曾是大批流亡者躲避当局镇压、逮捕以及监禁的主要避难地。在1849~1850年间,从巴黎到莫斯科,从布鲁塞尔到罗马,一群几乎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流亡者,乘货轮经泰晤士河,来到了雾气弥漫中的伦敦城,他们成份混杂、民族各异,有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法国人,其中最大的一帮是德国人。虽然这中间有些人继而又到美国谋求新的生活去了,但大多数人还是定居在英国。在那里,他们觉得可以较为自由地举行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集会,在他们自家办的报纸(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一个小印刷所的话)上发表自己急进的主张。在莱斯特广场或朗爱克广场附近的小旅店的楼上,少数几个坚定分子甚至聚集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重新策划着一场欧洲革命。1851年4月,英国大文学家查理·狄更斯在其主编的杂志--《家常话》中,曾对这种流亡活动的习尚作了颇为形象的描述:“在莱斯特广场坎泰洛先生鸡肉店后面的几条后街里,在那里的几间幽僻的小客厅里,人们正在策划着各色综合全面的密谋;在索荷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人们正在编织着旨在破坏奥地利帝国统一的秘密计划--这一消息,我们是从一位尊贵的贵族老爷那里听来的;在草市,一家廉价餐馆的顶楼上,普鲁士正遭受着24个波兰人和洪维人的威胁;在各色雪茄馆内的小会客室里,人们正在抽签,以此来决定刺杀路易·拿破仑的人选……”
然而,这种异乎寻常的“自由”却受到了种种阻碍,首要的和最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活动经费,急需寻找有收益的工作来维持。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在伦敦他们已没有资金出版《新莱因报》这份曾经使他们在1849年从科伦被驱逐出境的报纸了。于是,恩格斯便赶赴曼彻斯特,在父亲开的纺织厂里工作了二十年,多少能养活自己和在伦敦的马克思一家。
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富裕的。1850年侨居伦敦的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奥斯卡·冯·赖辛巴赫伯爵雇用了他的几个流亡伙伴做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以此来资助他们。玛丽·冯布鲁宁克男爵夫人也雇了几个德国流亡者做家庭教师。她还常常在家里款待奥古斯特·维利希中尉领导的那个流亡者小组,这些人不屑于寻找有收益的工作,宁愿躲在男爵夫人的客厅里,或者在朗爱克广场谢特纳的德国小酒馆的休息室里,策划推翻普鲁士的军事行动。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约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发动起一场“新的革命”。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到达伦敦的时候,大都是一贫如洗,因此很自然地是渴望尽快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以寻求帮助。
于是,一些地区便常常成为一群群流亡者的活动中心。索荷区--特别是那里的莱斯特广场--就是其中之一。莱斯特广场有着便宜的住房,有“新型的分间出租的住宅”,还安装有供穷人使用的少得可怜的卫生设备。马克思就住在第恩街的一幢拥挤不堪的房子里,而他的几个朋友--“我的党”,马克思常常这样谐谑地称呼他们--至少在他们到达英国后的头几个月里是在一幢分间出租的住宅里度过的。圣·约翰林地,比起鏖糟的索荷,空气要好些,亦不甚拥挤,那里是经济状况略微好些的流亡者的活动中心。在伦敦的较富有的德国人,象巴林家庭,戈德斯米德家族以及罗思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在伦敦业已经营了大约三十多年的银行家和商人则占据了伦敦最受人宠爱的地方;尤其是海克纳和坎布维尔两地倍受青睐,因为那里空气新鲜,而且有着宽敞、舒适的住宅。许多政治流亡者常常跑到坎布维尔,在虽不是政治伙伴但却是他们的同胞的人们的家里授课,藉此可以弄到几英镑钱花。
当时,流亡者们的活动所受到的第二个方面的阻碍就是偏见--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以及政治上的。这些偏见就是在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为自由的”(或者象恩格斯所写道的那样:“无不自由的”)国度里也是同样存在的。由于英国本地人的竞争和猜忌,找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在避难者中,大凡学校教师,多是“自由思想者”,他们所遭遇到的常常是宗教上的偏见;而那些女家庭教师和私塾先生们则常常被他们的雇主当作社会上的低能儿。当时,“无不自由的”英国曾收留了许多流亡的画家和音乐家,而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流亡者却被看成是对辛苦操劳却仍濒临饥饿的英国工人的工作的一种威胁。
第三个方面的困难,主要是流亡者们自己酿造的,这就是相对峙的政治派别间的争吵与内耗。这一点在德国流亡者中间显现得尤为突出。他们都曾遭到德国政府的镇压,而且许多人曾因从事反政府活动而遭监禁。哥特弗里特·金克尔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判处在施潘道要塞服终身监禁,1850年他又从那里奇迹般地越狱逃跑了。所有的人都是因其各自的政治观点而被迫流亡的;然而这些观点却是大相径庭: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卡尔·布林德的国际共和主义,阿尔诺德·卢格的“黑格尔社会主义”,还有金克尔的断断续续坚持的“立宪主义”。因此,当时的德国流亡者,就像俄国的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经说过的那样:“四十次分裂就有四十个宗派”。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于伦敦设立的对手俱乐部里,在他们于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上彼此进行个人攻讦。然而,马克思对流亡者们的这种虽是戮力泛舟,然却各驶其道、殊途异路的蠢举却是洞若观火,讥讽地称其为“蛙鼠之战”。
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对避难者中的那些非共产主义者的抨击,同时也批评那些目标和策略都十分幼稚的共产主义者。从他1848年8月到达伦敦时起,他的主要活动就是:试图教育和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支部中的德国工人;努力扩大在卡尔·沙佩尔和奥古斯特·维利希的同盟工人教育协会中的影响。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比,他们的共产主义则要幼稚得多,“原始”得多,而且是很不科学的。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彻底分裂以后,马克思在写给当时在曼底斯特的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与其同这些反对他的“傻瓜们”结伴同行,不如和他们分道扬镳。
不过,马克思仍旧是一批成份各异的避难者和工人们的最高灵魂,这些人仰赖“马克思老爹”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和道义上的支持。自1850年9月同沙佩尔、维利希分裂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大多数盟员都站到了马克思一边,而一些新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的人,即那些原先在科伦曾与《新莱因报》共过命运的人(象威廉·沃尔弗和恩斯特·德朗克)来英国后对马克思也依然是忠心耿耿。马克思曾依靠他们的帮助收集证据,以援救1852年在德国遭受审讯的那些科伦共产党人,然而,他的“党”的质量问题,使他很快便警醒起来。1853年3月,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对他们做了如下批判性的评论:“这些家伙真是懦夫。他们懒惰,一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就无力抵抗,支持不住,指靠他们是毫无希望的。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皮佩尔如果幼稚的虚荣心少些,坚持不渝的精神多些,那他不会没有用处。伊曼特和李卜克内西顽强,他们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鲁普斯(威廉·沃尔弗,下同--笔者)一天天老了,而且越来越古怪。德朗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浪荡汉’。”①几个月以后,他又批评沃尔弗、德朗克以及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无聊的闲谈中浪费时光,而把全部工作都扔给了他。1852年,马克思在组织他们所有的人为他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杂志《革命》撰稿的时候,还曾表示他要“手持鞭子站在每个人后面”②,直到他们交出必要的文章时为止。
然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都未能坚持马克思“荷求”的标准。他们都没有钱--威廉·沃尔弗有一次竟差点饿死,当时他们最为迫切的需要,是要寻找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这种贫困的处境,加之人们的懒散和缺乏承诺,使得党比较缺乏内聚力,因而无法完成预期的宣传任务。而小组成员又经常分散异地--如一个人在曼彻斯特找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个在布雷福德,第三个在丹迪--这就使这种贫困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然而,今天我们追溯他们一生的经历,从而绘制出一幅符合历史真实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避难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家的生活画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生活,懒惰者与勤奋者的生活,意志坚定者与意志薄弱者的生活--依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1、名誉上的英国人
在马克思于伦敦生活的初期,他的朋友们中有两位不久就背弃了他。其中之一,就是以“鲁福斯”著称的斐迪南·沃尔弗。1848年,他曾在科伦帮助马克思编辑过《新莱因报》。
《新莱因报》停刊以后,1849年6月沃尔弗随马克思到达了巴黎。10月,恩斯特·德朗克从巴黎写来报道说他“就像个幽灵一样”四处游荡,而且是一贫如洗。不久,沃尔弗就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一幢分间出租的住宅里租了一间屋子),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他即站到了马克思一边。然而后来他却一意孤行,成了一个“名誉上的英国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再没有见到他。1851年7月,恩格斯曾写道:“红色沃尔弗经过了亲爱尔兰、资产阶级的……,精神失常和其他有趣状态等各种不同阶段,他完全不喝烧酒而喝二合酒了。”③显然,斐迪南·沃尔弗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10月,沃尔弗又出现在了马克思的家里,此前,他不知何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这时,他已“同一位英国女才子结了婚。”到1853年4月,他便做了“丈夫和父亲”,“成天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少在他的流亡伙伴们中露面④。后来他又躲到英格兰北部教书去了,年薪为60英镑。人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1877年,当时德朗克告诉恩格斯说:沃尔弗现在在布莱克本有了他自己的寄宿学校,为了这个学校,他又是登广告,又是招揽学生,而且还备有从牧师们那里弄来的一些必要的参考书。斐迪南·沃尔弗这时已经完全浸泡在英国式的生活之中了。
2、党的泼息·霍士泼⑤
1849年9月,马克思到达伦敦几天以后,康拉德·施拉姆也来到了伦敦。他,一位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指控,于同年5月被捕,被判处两年监禁。越狱成功后便直接来到了伦敦。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项计划:派遣施拉姆到美国为在伦敦继续出版《新莱因报》筹集资金。然而,这项计划却因没能筹集到施拉姆的旅费而不得不告吹了。
后来,马克思把施拉姆描述为他的“党”的“泼息·霍士泼”⑥;这是因为:正值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为两派之际,正是施拉姆代表马克思派与同样生性好斗的维利希进行实际决斗的(由于决斗在英国是非法的,所以他们渡海来到了比利时)。担任维利希监场人的法国流亡者埃马纽埃尔·巴特米尔,1853年在英国进行了一场决斗,为此他受到了两个月监禁,据马克思说:巴特米尔因谋杀了一位伦敦警察于1855年被处以绞型;而施拉姆的监场人,波兰军官米斯拉夫斯基,1854年烧死在自己木制营房的一场火灾之中。
康拉德·施拉姆没能达到目的。1851年9月他在巴黎被捕后险些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到损害,所以马克思又把他称之为“无赖汉”和“浪子”⑦。同维利希一样,施拉姆也是粗心大意、草率行事的人之一,正是他们的粗心大意和草率行事使得普鲁士当局做出了不利于科伦共产党人的判决。1852年5月,施拉姆移居到了美国,这一方面是为了去那里谋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作:充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在美国的魏德迈之间的联系人,以便于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在美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1857年,已是处于肺结核晚期的施拉姆又回了到英国,在泽稷岛结束了他的一生。1858年,就在他逝世前,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还曾去那里探望过他。
3、“一钱不值的小丑”
在马克思的流浪汉肖像栏里的那些流浪汉中的头面人物就是德国流亡者中的浪子:威廉·皮佩尔。1851年,他先是通过在阿尔诺德·卢格的鼓动社的会议上充当“侦探”来帮助马克思的。在1851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他和施拉姆的“侦察”活动被发现后,险些遭到毒打。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宪章派领袖,被恩格斯称呼为“我们亲爱的”朱利安·哈尼也和维利希以及各色民主主义者纠合到了一起。在科伦审判案期间,皮佩尔是马克思的秘书,1852年他又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18日》一书译成了英文。这篇“错误和遗漏百出的”译文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评,说皮佩尔是“极其明显地粗枝大叶”,“伦敦小市民式的小资产阶级的咬文嚼字的美文学”。⑧这篇译文本来是为魏德迈的《革命》和危内斯特·琼斯的宪章派杂志《寄语人民》而写的,然而,在1851~1852年间,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852年,恩格斯每月给皮佩尔寄两英蒡。而在其他时候,皮佩尔则不得不以教书维持生计,起先是在侨居英国的德国贵族路特希尔德家里做家庭教师,后来则在肯特和苏塞克斯两地的几所寄宿学校里任教。
在他与路特希尔德一家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是孩子们的长期家庭教师。他给孩子们辅导所有的课程,也包括外语,1851年10月他还同这一家人到法兰克福和布鲁塞尔旅行过,12月,他和孩子们的母亲,与他一直有着暧昧关系的巴罗内丝·路特希尔德发生口角后,被辞去了长期家庭教师的职位。当时,皮佩尔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玩世不恭而又有些市侩气,所以马克思送了他一个“塔普曼”的绰号,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自命不凡、好讨好人而又缺乏责任心的人物:“这个愚顽可笑的小伙子总是把丧失原则错当成显露天才的高尚精神”。然而,皮佩尔,这位马克思的孩子们所熟悉的“令人着迷的王子”(马克思的女儿们有时这样称呼他),当他从布鲁塞尔写信给马克思谈及他与路特希尔德太太的争吵的时候,他那迷人的脸蛋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着迷了,在信中他还以“弗里多林”⑨自诩,他写道:“弗里多林已不再为节省一个便士而苦恼了,在偿清债务后,他就会像他们所有的朋友一样,完全一贫如洗了,如果他在最后清帐时弄不到点儿结余的话,特别是,如果他不能把他的‘剧本’弄到手的话……弗里多林的故事结束了,就像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故事一样,平庸而恬静。他现在需要的是大批的推荐信和一笔钱,而不是‘舞台’……下星期四我要去伦敦看你。”
在回到伦敦的一段时间里,皮佩尔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1853年,恩格斯设法在曼彻斯特给他谋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他有还过一段短期的“商人”生活--在西蒂区的一家法国商店里经销各种太阳能加热器,1854年3月,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又为他找到了一个给一位墨西哥商人做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有15先令的收入。皮佩尔还有一个逛妓院的毛病(当时他想同马克思一家住在一起,马克思开玩笑地说他“现在两个口袋全空了”)。这使他染上了梅毒。马克思曾送他到圣·巴基洛缪医院做出免费治疗,后来皮佩尔便成了多尔斯顿德国医院的常驻客。在他几次发病住院(1853、1858、1859)期间,马克思都曾去那里探视过他。1859年2月,当马克思听说皮佩尔被送进了医院的时候写道:“他活该”。当时,梅毒在那些德国医院接受治疗的避难者中间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而且这些患者大多是居住在伦敦东区的穷苦工人;为了给那些“更需要慈善捐款资助的”病人腾出床位,1856年该医院委员会决定限制梅毒患者的接收名额,并且每周加收六便士的医药费。⑩
1854年10月,皮佩尔被任命为肯特郡埃耳森一家学校的住校教员。马克思当时写道,他的职务就是“负担各路活计的佣人”,马克思这样说,一方面是对皮佩尔失去了一份秘书工作表示遗憾,同时也是为住校教员这份工作去掉了皮佩尔不负责任的生活作风,去掉了他那自命不凡的心态而感到宽慰。(11)当时皮佩尔与马克思依旧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使马克思了解到在英国还有着学校教学工资奴隶:“皮佩尔在他的学校里要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九点,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要祈祷二十来次,这对他起着‘良好的’作用。不抽烟也不喝酒。领着学生上教堂,如此等等……”(12)
在伦敦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之后,皮佩尔又在博格诺接受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时他正为马克思看房子(其时是1856年6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而他的家属在德国探亲),他还写下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他仿照马克思那具有文学魅力的文笔,对自己单枪匹马地为改善许多倍受奴役的教师的待遇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描述。不仅马克思被皮佩尔很不恰当地看成是“亲爱的匹克威克”,就是在看待他在那所学校里邂逅的人的时候,也总是带着狄更斯的有色眼镜。那家学校校长的妻子--里士满夫人,皮佩尔用英语做了如下描写:“一位多丽特(13)式的小女子,她那超乎常人的对爱的追求,她那令全人类爱怜的模样,分明是在劝诫我不要去理睬她的女佣们--在对那三位倒霉的老处女进行观察之后,我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皮佩尔在信中还透露说,他已经打嬴了一场惊人的战役,其结果是被允许每天喝上一杯免费啤酒,这件事给“一个可怜的傻瓜门房”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每天打十二次钟--他总以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皮佩尔意欲为之战斗的下一次战役是:“争取自己能每两个星期过一个星期日。”
然而,不久皮佩尔便放弃了这份挣不到钱的工作。当时,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筹措一小笔资本,那怕是通过一次投机婚姻。1856年4月,马克思向恩格斯叙说了这一企图的令人乏味的内情:“皮佩尔凭着自己的天才从1月份又过起海盗式生活了,虽然从我这里得到相当资助,但每天都有被房东太太撵出的危险。他突然想到,他缺少当大人物的一小笔资本。载勒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1849年与马克思同时到达伦敦,后为躲避在伦敦所欠下的债务跑到了美国--笔者)的小姨子,蔬菜商的女儿,戴绿眼镜的蜡烛老早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位皮佩尔……皮佩尔说她很丑,但毕竟发现她并非没有头脑;她认为我们草原上的汉诺威羊是狡猾的德国拜伦,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她是有头脑的。于是,皮佩尔(这个女人不仅象牛蒡,而且象水蛭一样,粘在他身上)前天决定向载勒尔的岳父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不愿意在‘心上人’面前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一定要吻她,而这对一个还不习惯靠蜡烛为生的西方人来说,的确是件难事。但是,作为真正的皮佩尔,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要知道,他必需有一笔不大的资金,譬如说,二十至四十英镑,好给自己造成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作为未婚妻的‘心上人’有机会享受寡居的一切乐趣,并且为了怜悯起见永远不娶她……”(14)马克思用他自己家属的评论结束了这个故事:“小燕妮说他是‘斐尼狄克--结过婚过人’,但小劳拉说:“斐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15)
到1859年5月的时候,皮佩尔就已经离开了英国,在不来梅教书。此后马克思就很少再听到他的消息了,只是在1864年曾收到过一张宣布皮佩尔已经与一位不来梅教授的女儿订婚的明信片。几年以后,恩格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1867年在汉诺威,他曾在街上碰到过皮佩尔,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傲慢的市侩”了,当时正是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送交出版社的时候。大概在这以前他就早已脱离政治流亡生活了。
4、忠实而乖戾的老单身汉
与威廉·皮佩尔截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钟爱的“信徒”威廉·沃尔弗,是一个脾气倔强古怪的单身汉。这个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出生于1809年,他历尽困苦总算上了大学,在大学里,他是被查禁的大学生团体--大学生协会的领导人,1834年,他因投身于被官方禁止的活动而遭到4年监禁。长期的牢狱生活,加之1848年后在布鲁塞尔、巴黎以及苏黎世的几年间都是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度过的,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于1864年4月在曼彻斯特逝世。
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竭力劝说沃尔弗与他们在英国聚会。然而,在沃尔弗曾为之献身的《新莱因报》被查封以后,他却去了苏黎世,在那里讲授古典文学和现代语,但却没有多少学生,于是他打算移居美国。1851年4月,恩格斯写信劝他说:不妨先到英国来。既然会讲英语,又能有几份必要的资格证明--由苏黎世大学的四位教授写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找一些教书的活计是不成问题的;也不必相信欧洲大陆报刊的报道:在博览会(16)期间,英国政府将“不再让流亡者到这里来了。”“你知道在这里边境上谁也不会受到阻拦,尽管有反动报刊的这套胡言乱语,我期望在博览会期间能在伦敦见到你”(17)。恩格斯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当时在英国国会里和报刊中有少数人喊叫说:在博览会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可能发生革命密谋活动。
威廉·沃尔弗是1851年6月抵达伦敦的。八个星期以后他才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并非所有的德国流亡者都能那么幸运地找到教书的工作;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是一位音乐教师,她于3月间写道:民主共和主义者古斯塔夫·施特鲁韦由于没能在伦敦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去了美国;九月间,她又向在德国的一位朋友描述说:流亡者们就象是“一支到处寻找学生的教师移民团”。同其他的流亡者(诸如:金克尔的传记作者阿道夫·施特罗特曼及其女友马尔维妲·封·迈森博格)一样,沃尔弗也是靠给富裕的外国移民的孩子们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的。施特罗特曼教贵族布吕宁克男爵夫人的孩子,而且就住在这位夫人在圣·约翰林地的家里;马尔维妲则当上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而沃尔弗则从1850年既已侨居伦敦的西里西亚地主奥斯卡尔·封·赖辛巴赫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这可以说是沃尔弗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当赖辛巴赫因1852年12月路易·拿破伦称帝而痛苦,绝望,因而于翌年春天离开欧洲与奥古斯特·维利希一道去美国谋求新的生活之后,沃尔弗便陷入了几乎挨饿的境地。同维利希一样,封·赖辛巴赫也曾寄希望于军事行动。当时认识封·赖辛巴赫的珍妮·卡莱尔于1853年9月在写给她小叔的信中说赖辛巴赫“在弗拉德尔斐亚购置了一个方圆十五英里的大农场,然而我想:他私下里却由衷地盼望着有一场他可以参加的,并且会使自己慷慨就义的战争,而不是要去排干美国农田里的水。(18)
威廉·沃尔弗当时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然而他并没有去寻求马克思的帮助,这显然是出于他那过分强烈的自尊心。他此前曾与马克思发生过争吵,原由是:在沃尔弗和其他人已经怀疑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上校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之后,马克思还依然相信了他很久。1853年5月,马克思向恩格斯诉苦说:沃尔弗“还是老埋怨”。(19)沃尔弗在他6月21日(这天正是他44岁生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不得不在极度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20)8月,他即写信给恩斯特·德朗克寻求帮助了。当时在布雷福德当店员的德朗克随即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恩格斯,于是恩斯便劝说沃尔弗到曼彻斯特来。在那里,恩格斯委托他的朋友、德国流亡医生路易·博尔夏特寻找教书的工作。博尔夏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他曾因从事1848-1849年的革命活动而在狱中度过了三年,获释后即被禁止在普鲁士行医,遂于1852年移居曼彻斯特,而且生意兴隆,求诊者甚多,所以他是能够把沃尔弗介绍给需要家庭教师的英国或德国人家庭的。1853年9月6日,沃尔弗又与马克思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起因是:马克思借去了沃尔弗的一本弗兰塞宗著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却把它搞丢了。为此,沃尔弗当着马克思家人的面辱骂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甚至对沃尔弗这位“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的行为也表示了强烈的愤满(21)。所以,恩格斯不得不出面来消释马克思和沃尔弗两人胸中的嫌隙。
当时,马克思不满意沃尔弗,在某种程度上亦与沃尔弗对“党”的工作缺乏积极性有关。1852年马克思组织他的“党”的所有成员给约瑟夫·魏德迈的《革命》撰稿的时候,沃尔弗却什么东西都没写。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只是“党”的一个名义上的成员,而且在曼彻斯特定居之后,他也就渐渐地习惯于他周围的那种整天为身体忧心忡忡的有产者的生活方式了。不过,除了酒后与人偶有争执外,其品行还是完全值得尊敬的。马克思实际上以为,他在1856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摘选的那段描述确是符合沃尔弗这个老单身汉的生活的:“一个确确实实的老光棍的标志:一个人不带伞便不能出门,--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认为一切人都在欺骗他--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不论买什么都自己去……(22)”恩格斯也曾写到沃尔弗常与他的房东太太,他的拉小提琴的邻居吵嘴,而且有着在他经常光顾的恰思沃斯酒馆喝过几杯归来后即与人呈“势不两立”状的癖性。(23)在恩格斯的笔下,沃尔弗是一个介于堂·吉诃德和特里斯特拉姆·香迪(24)的性情暴躁的父亲之间的人物。恩格斯写道:“鲁普斯又经历了一次冒险,一个教师拿错了他的手提箱。但是由于在留下的手提箱里放着这个牧师第二天要喃喃诵念的第一次讲道稿,这件事情的惊人的严重性才得以缓和。这种事情具有了某些幽默的味道。否则,鲁普斯又要高叫:‘这个国家骗子这么多,但不是出在工人阶级,而是出在中产阶级。’”(25)然而沃尔弗和恩格斯依旧是好朋友、好酒伴,尽管马克思对他们两人的友谊和欢乐似乎颇有些妒忌。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写信给恩格斯解释说:“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我的一些妒忌,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26)
1859年,即在纪念德国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席勒协会在曼彻斯特一成立,沃尔弗即是协会的知名会员了,而于几年后成为该协会理事会理事的恩格斯却因协会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而对这次百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冷淡,并且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将这些活动报告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卡尔·布林德和金克尔一伙在伦敦水晶宫搞的庸俗的纪念活动,同样给予了辛辣的嘲讽。然而,大概是出于交际上的考虑,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并未提及沃尔弗也卷入了这些活动。沃尔弗逝世前夕,还留下遗愿,将一百英镑赠送给了席勒协会。而这时的席勒协会已是经过恩格斯改造的,由恩格斯任主席的席勒协会了。
1864年5月,就在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三个月,威廉·沃尔弗因过度劳累死于脑溢血。他终身未婚,一直过着单身汉的流亡生活。在生活中,沃尔弗还常常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例如:1855年3月间,他曾兴致昂然地要拉着弗莱里格拉特(德国流亡者,诗人,马克思家中的常客)到热带地区做一次旅行,打算在那里建一个种植园。这一计划提出后,弗莱里格拉特在3月30日给沃尔弗的复信中答复说:他不可能带着“五个弱小的孩子”一起去,婉言谢绝了他。(27)尽管沃尔弗有着这样一些古怪的念头,然而他还是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爱戴(28)。沃尔弗逝世后,马克思出席了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葬礼,当时他还记下了出席葬礼的人数:“参加葬礼的有博尔夏特、龚佩尔特、恩格斯、德朗克、施泰因塔耳、马罗茨基(光明之友的新教牧师,鲁普斯在他家教过书,他是作为生前好友而来的)、贝内克(这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施瓦伯(同上),还有三个商人。几个少年以及大约十五到二十个所谓“下层阶级”的人--鲁普斯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29)
使马克思又是惊奇又是感激的是:他发现虽然沃尔弗生活一直不很宽裕,然而却积攒下了一千英镑,而且还把其中的绝大部分都留给了他一家。沃尔弗不仅对马克思的女儿们的在校成绩总是很关心,而且还打算用自己的遗产来资助马克思实现对资本主义的伟大批判事业--《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是为了缅怀这位德国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了沃尔弗。
在曼彻斯特,沃尔弗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人物,英国人和德国人,有产者和工人都喜欢他,甚至连在家里同房东、在酒吧与邂逅而遇的酒伴们吵架也是出了名的。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会保存的他的文件档案中--除了他的几份来自苏黎世的推荐信、他的护照、他在曼彻斯特银行的存折,以及他的遗嘱都保存完好外--还有一张标有“1861年”字样的未署名的圣马伦丁节贺卡。(30)
尽管在这一时期,威廉·沃尔弗作为马克思的“党”的一名成员,没有起过多大的实际作用,尽管在生活困苦的时候也发些脾气,但是,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对朋友,对同志确是很忠诚的。
5、忠实的新兵
彼得·伊曼特,1848年革命以前是克雷费尔德的一位教员,去英国之前曾流亡瑞士。他与马克思的“党”的其他成员不同,起初,他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拥护者,只是到1852年夏天才在伦敦被争取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的。在瑞士的时候,他是金克尔美国贷款的担保人;(31)但到了1852年的8月,他就在贷款董事会的会议上为马克思做“侦察”工作了,在会上,民主主义流亡者们就如何使用金克尔筹集到的少得令人沮丧的资金展开了争论。亚历山大·赫尔岑不无偏见地在其自传中写道:这些德国流亡者把这笔钱存入了一家伦敦银行,“而且还把金克尔、卢格和奥斯卡·赖辛巴赫伯爵这三个互不两立的死对头选为董事,……他们中间只有一两个人签发了支票,而第三者却拒绝这样做。当时不论这个德国移民的团体做什么,都总是少一个人的签名”。(32)
彼得·伊曼特虽然投奔了马克思的队伍,但当他向丹迪的一所学校申请法文和德文教师的职位时,在证明人一栏中还是写上了金克尔的名字;他的另一位证明人是丹迪知名的“大诗人”费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从1852到1855年,伊曼特住在坎布威尔,当时他是在一大批富庶的德国商人家里教授语文,这些德国商人中还包括所谓的“民主主义商人”,普鲁士的密探“查理·弗略里”,马克思正是依靠伊曼特的帮助,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戳穿了他的伪装。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在这一时期,伊曼特也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写过任何东西,但是他的确帮助马克思摆脱过债务上的窘境。1855年7月,马克思全家躲在坎布威尔区伊曼特的家里,这既是为了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也是为了摆脱几个月前失去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的痛苦。然而,更主要地是为了躲避那些向马克思讨债的人,其中包括经常给马克思一家看病的医生赫尔岑·弗罗恩德。
马克思一家在坎布威尔的时候,彼得·伊曼特正在苏格兰拜访德国民主主义者亨利希·海泽(马克思的朋友之一)。1855年8月,伊曼特对马克思说他要去阿布罗斯,9月1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布罗斯找到工作。”(33)伊曼特在到达丹迪之前就已经接手了一个煤炭商的生意了,另外他还找到了五个学生,这又给他增加了四又四分之一英镑的收入。1856年2月,伊曼特告知马克思说,他向往伦敦。其实这是因为雇用他做家庭教师的那些苏格兰人过分吝啬,使他们工作很不好做。(34)]然而,他并没有去伦敦,还是留在了丹迪。1857年他又求得了一份教书的活计。1859年,他便和他的女房东的女儿结了婚。当时,他的侄子卡尔·伊曼特也和他住在一起。1858年卡尔曾从丹迪给“马克思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他正在苏格兰的一所学校读书。他在信中说:“英国的学校要比德国的好得多,它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学生不必被关晚学,每天也不必写家庭作业。”卡尔还希望马克思一家第二年春天到丹迪来玩儿,而且希望“红头发”(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和“黑头发的燕妮”也去。(35)
尽管伊曼特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并不是很经常,但彼得·伊曼特确是马克思少数几个较坚定的朋友之一。1867年,马克思寄赠给他一本《资本论》第一卷。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伊曼特却过了很久才复信,他在1870年2月的这封复信中向马克思表示:对自己长久的沉默而深感内疚。他还说,他觉得《资本论》一书,就是拼命研读也很难懂,而且第一章就是对他这样一个曾研习过黑格尔的人也的确是‘一个非常硬的坚果”。
6、忠实的信徒
在这一时期,威廉·李卜克内西要算是马克思的小组中最忠实、最积极的分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甚至1862年李卜克内西返回德国,把一生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闻编辑工作之后,也经常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然而,正是赖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的严格教诲,他才渐渐从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阅历、渴求知识的年轻人有缘认识马克思并承受他的影响和教诲,这样的好运是我万分庆幸的。”(36)然而,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并不很高,而且李卜克内西总是欣赏那种米考伯(37)气质,这也使他们感到有些头痛。李卜克内西在他的《一个士兵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我甚至比狄更斯的米考伯先生(虽然他在当时尚未问世)更为迫切地渴望着周围能‘出现一点什么事情’……”(38)这种米考伯气质在他的流亡生活中也时有流露:当时,尽管他毫无财务偿还能力,但他还总是要“借贷”,而且总是相信好运气就会到来。1865年,他在柏林的时候,手头十分拮据,思忖再三还是打算重返英国,试图在曼彻斯特谋个教书的职位。他写信向恩格斯询问说:“在曼彻斯特我能搞到一座年租金20-30英镑的带花园的房子吗?”,恩格斯旋即写信给马克思说:“李卜克内西对曼彻斯特的想法真怪!连饭都吃不上,还要向我打听这里一座‘带花园,的房子要多少钱!这家伙简直是完全糊涂了。”(39)尽管李卜克内西有其天生的弱点,然而他在19世纪70-80年代的确是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死对头。
李卜克内西在苏黎世的卡尔·弗吕贝尔实验中学教了一段书之后,便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一起参加了1848年9月的巴登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去日内瓦寻找起义领导者司徒卢威等人的途中被捕,囚禁在弗赖堡监狱,直到1849年的夏天。1850年2月,他又因参加日内瓦几家激进俱乐部的活动而被捕,遂被驱逐到法国,5月,又被逐出法国。于是,他便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见到了马克思,不久便申请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进行了一场极严格的“考试”,十分仔细地盘问了他。当时,两位导师之所以要盘问李卜克内西,是怀疑他同司徒卢威有什么瓜葛。后来,李卜克内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两位主考人怀疑我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情绪和‘德国南方人的温情’”。(40)然而,李卜克内西通过了这场考试,而且心甘情愿地做马克思的学生,钻研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很快,他就在他的教育协会的演讲中把这些理论传播给了德国工人。
李卜克内西当时是饱偿了马克思的“苦头”的,尤其是在他返归德国之后,他不仅被马克思“差来遣去”,而且常挨批评,因此,他对马克思既倍感钦佩,有时又抱怨马克思对他的态度。然而,他对马克思的态度毕竟还是钦佩胜于抱怨。他曾经这样写道:“对外界的打击、中伤,蚊子臭虫的叮蛰,谁也不能毫无反应,可是马克思就常常这样,他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受到各方面的打击,他要为生计而忧虑;在寂静的深夜里他为劳动大众的解放而锻铸武器却不为他们所理解,有时群众甚至跟着那些空谈家、虚伪的叛徒、甚至公开的敌人跑,轻蔑地谴责他。有时,他独自一人在他那清贫的真正无产阶级的书斋里常常用这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话来激励自己,并从中吸取新的力量。”(41)
毫无疑问,李卜克内西对马克思的事业,对马克思本人都有着十分强烈的忠诚感,而且当时他也十分理解马克思对奥古斯特·维利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受到一些工人们的拥戴这一事实所抱的态度。他写道:当维利希及其同伙“策划着如何推翻世界而日日夜夜‘以明天就开始’这副麻醉剂来麻痹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些‘硫磺帮’、‘暴徒’、‘土匪’和‘人类的渣滓’却坐在英国博物馆里,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并为将来的战斗准备武器和弹药。”(42)
威廉·李卜克内西除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支持马克思以外,他还是约翰·格奥尔格·科塔(43)创办的两家德文报纸驻伦敦的通讯员(当时李卜克内西以“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然而,他觉得薪水少,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他便打算找一些教书的活计。1853年1月,为了能够比较体面地去见一位德国商人(赫尔·舒特,为奥彭海姆公司银行做事),他向恩格斯借了一英镑,从当铺老板那里赎回了他的大衣。1854年6月,李卜克内西大概就已经失去通讯员这个工作了,其时正是他与其在弗赖堡监狱结识的一位典狱长的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马克思曾向恩格斯谈起过这一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李卜克内西曾非常忧郁,他在一个英国女人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举棋不定,英国女人希望嫁给他,而他却想娶住在德国的那个德国女人;最后,这个德国女人突然光临,于是他同她举行了宗教和世俗的婚礼。看来,两个人都很痛苦。他无处可去,因为人都走了。他的蜜月是在教堂街147号那所房子里度过的,他在那里负债累累,因此很是扫兴。但是,有谁迫使这个了解一切情况的蠢驴去结婚呢……?”(4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一时期,李卜克内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还是天真、幼稚的。也正是这种天真和幼稚,使他不得不回到了德国。这种天真和幼稚就是在他的著作中也时有流露。例如:他在论1851年2月博览会的那篇短文中写道:“事实是,这次博览会并非滥觞于什么世界主义的热潮,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沿波讨源,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蕴含着极镇密的筹算和极露骨的动机。我们认为:英国的工业在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进程中业已走到了如此地步,如果它找不到新路,亦不能拓宽老路,那就必然会在其自身的生产过剩中窒息而亡。走新路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把这整个社会结构彻底摧毁,那么就只有扩大那些原有的旧市场,使之能够包容更大量的英国商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章写到这里还算顺当,然而,他接着又写道:“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博览会不过是一种鼓吹自由贸易的宣传手段而已。然而,尽管如此,发起这一活动的想法本身,以及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的方式都是值得我们称道的。这次博览会已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赞誉,这就足以表明其他国家业已领悟了它的重大意义……至于隐藏于其后的动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里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富于博爱、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倒不如说是向人们自我炫耀,尽管不是有意炫耀。”(45)写到这里,李卜克内西便不能自己,信笔挥洒起来。在这里,他把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同自己欲加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加批判的赞美掺和到了一起。这对马克思来说的确是件很恼火的事。就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尽管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理论上仍有错误发生。1883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工联》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声称:英国工联一定会取得成功(英国工联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工联主义口号),并根据黑格尔派的观点(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各自代表着一定权利的两派之间的全部斗争,总是要达到某种均势的观点--来论证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反对以损害工人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资本主义的英国工联,是工人权利的代表,它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战斗中,它运用它的权利来扫除一切要阻碍工业发展的东西。他写道:“一句话,英国工联已经使英国工人成为有一切权利的公民。”(46)当时,李卜克内西还是柏林帝国国会中第一批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1882年,在帝国国会的一次演说中,他讲述了自己对资本主义英国的印象,并对资本主义的英国加以赞赏,他认为:俾斯麦与“他的保守的英国同行”迪斯累里恰恰相反,他还引述了迪斯累里1844年发表的小说《科宁斯比》中的主人公科宁斯比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大意是说,一届高明政府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法律来实现:弊政下的国民,在被拒绝给予生活诸方面的合法改善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那些目标。李卜克内西的上述观点,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862年,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后,曾一度推行自己那一套无原则的路线,这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和尚未成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间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他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然而,使马克思与德国工人运动保持经常联系的要首推李卜克内西。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是依靠李卜克内西来贯彻第一国际的原则的。
以上就是马克思英国早期流亡生活中的朋友和同志。难怪马克思在1853年说他们所有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党了。(47)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大家都是拼死拼活方能勉强糊口,因而很少有这份精力、这份能力投身于实际的工人运动中去。马克思本人的活动也仅仅囿于德国流亡者的狭小范围,因而与英国当地的工人运动亦并无多少联系,甚至连英国工联领袖人物的名字也不知道。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在于为工人阶级锻造“批判的武器”,而不是进行“武器的批判”。当时,同其他人一样,马克思的生活也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
尽管他们生活穷困潦倒,作为一股蕴藏着巨大潜力的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尚无所建树,但“马克思老爹”的生活群体当时却过得很愉快,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现在让我们用李卜克内西下面这段回忆来结束这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他的“党”的故事罢:
同当时的许多伦敦家庭一样,去汉普斯泰特荒阜过礼拜天,也是马克思一家及其朋友们的习惯。大家总是带上一只盛满烤牛肉、薰鸡和水果的篮子,从第恩街步行到荒阜,临时在沿途和荒阜的一些小摊上买些面包、奶酪、牛奶、小虾、小芹、啤酒、茶叶和滨螺,又是唱歌、讲故事,又是在草地上做体操,又是摘野花、赛跑、还有骑驴。不管日后财务支付能力的前景多么消极暗淡,亦不管日后人们对自己所选择的研究道路会持怎样的否定态度,大凡礼拜天,马克思便不再去考虑家庭的痛苦,亦不再去考虑他在大英博物馆里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李卜克内西写道:“在汉普斯泰特荒阜欢度一个星期日是我们最大的乐事。”(48)
马克思的景况毕竟还是好转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接受了亲友的遗产馈赠,他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而且由于他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资本论》终于在英国受到人们的关注,他的影响才超出了索荷区以及索荷区那成份混杂的德国流亡者小组的狭小范围。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9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卷,第586页。
④参见《马恩全集》第28卷,第583页。
⑤泼息·霍士泼(Percy Hotspur),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中的英雄人物。霍士泼(hotspur)--英文的意思是:热情鲁莽的人,烈性的汉子。
⑥参见《马恩全集》第14卷,第472页。
⑦参见《马恩全集》第27卷,第358页。
⑧恩格斯主张把“brgerliche GeseLLschaft”译为“bourgeois society(资产阶级社会)”。他认为,这一译法比译为“middle-class society(中等阶级社会)”更符合“有教养的英国人”的习惯。对德文“Sturm und Drand(疾风暴雨)”的译法也存有异议。反对使用“old societg”一语;范围不应该是“In-creased(增大)”而是“enlarged(扩大)”;还有,应译为“bourgeois(资产阶级的)”而不是“constitutional society(立宪社会)”不是“for ever and the duration(永久和长时期)”,而应使用惯用语“for ever and a day(永远永远)”等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37~142页)。
⑨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善良而谦逊的多情少年的典型。
⑩皮佩尔曾于1853年9月、1858年10月和1859年2月住进德国医院,每次都是因患梅毒。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39卷,第368页。第40卷,第350、384页。马克思1853年9月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医院给皮佩尔的颈部做了烧灼术。他的床前挂着一块牌子,写着不详的字句:‘威廉·皮佩尔--第二期梅毒’。要他严守纪律,不过这对他很有好处。”(《马恩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94页)
(11)参见马克思1854年10月17日、25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第28卷,第400页。
(12)见马克思1854年11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恩全集》第28卷,第407页。
(13)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
(14)(15)《马恩全集》第29卷,第39-40页。
(16)指1851年5月10日于英国伦敦召开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
(17)《马恩全集》第27卷,第573页。
(18)珍妮·卡莱尔1853年9月致约翰·卡莱尔的信(亚历山大·卡莱尔编《新发现的珍妮·韦尔什·卡莱尔通信及记事集》,伦敦1903年英文版,第二卷,第61页)。
(19)《马恩全集》第28卷,第246页。
(20)参见《马恩全集》第19卷,第104页。
(21)参见《马恩全集》第28卷,第288-289页。
(22)(23)《马恩全集》第28卷,第131页。
(24)特里斯特拉姆·香迪:18世纪英国伤感主义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特里斯特拉姆·香迪先生的生平与见解》中的主人公,其父性情暴躁,动辄发火。
(25)《马恩全集》第29卷,第452页。
(26)《马恩全集》第28卷,第314页。
(27)见: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会藏《沃尔弗档案》第5本。
(28)参见: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马恩全集》第19卷,第106页)。
(29)1864年5月13日,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马恩全集》第30卷,第656页)。
(30)圣马伦丁节,即情人节(2月14日)。圣马伦丁节贺卡,是在2月14日这一天匿名寄给异性熟人的表示爱情的祝语或贺词。收到收贺卡的人,往往知道是谁寄的。
(31)1851年,金克尔曾派卡尔·舒尔茨到瑞士寻找担保人。参见赫尔曼·勒施--宗德尔曼:《作为美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 als Asthetiker,Politiker und Dichter》),柏林,1982年版,第306页。
(32)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回忆》第三卷,第1145页。
(33)《马恩全集》第28卷,第454页。
(34)《马恩全集》第29卷,第16页。
(35)1858年3月1日卡尔·伊曼特致马克思(参见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会藏通信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卷D2042宗)。
(36)《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6页。
(37)英国文学家查理·狄更斯1849~1851年发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个不筹措未来、老是幻想突然走运的乐天派。
(38)《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41页。
(39)《马恩全集》第31卷,第98页。
(40)《我景仰的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41)(42)《我景仰的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页。“伟大的佛罗伦萨人”,即指但丁,他的诗句“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马克思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写到了《资本论》的序言中。
(43)德国出版商,1832-1863年是一家大出版公司的老板。
(44)《马恩全集》第28卷,第394-395页。
(45)威廉·李卜克内西:《工业博览会》(《DieIndustrieaussteLLung》),原文载〈德〉1851年3月3日,5日《有教养者晨报》,转引自〈英〉《文汇》1986年2月号,第39页。
(46)威廉·李卜克内西《工联》(《Die Trade Unions》),原文载〈德〉《新时代》1883,转引自〈英〉《文汇》1986年2月号,第39页。
(47)参见《马恩全集》第28卷,第227页。
(48)《我景仰的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