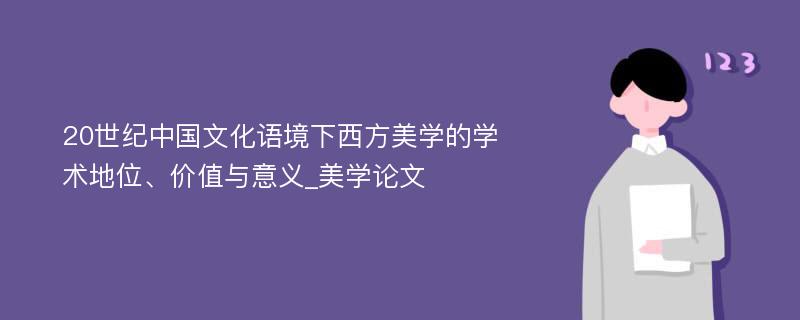
论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文化论文,美学论文,地位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已近尾声,对于当代学界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本世纪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美学界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那么,20世纪中国美学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是什么?问题固然很多,但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疑是该追问和重估一下,在本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蜂拥而入的西方美学的学术地位、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弄清这一点,对下个世纪中国美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一)
这里所谓西方美学,主要包括四大部分,一是西方古典美学;二是西方现代美学;三是19世纪俄国和前苏联美学;四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四大部分对本世纪中国美学的影响虽因历史的不同需求而各有侧重,但相对于中国本土美学而言,它们共同呈现为西方美学的整体概念和形象。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西方美学在20世纪中国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一个很通行的说法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是中、西方两大美学体系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这一说法听来似有道理,但仔细分辨就觉得不甚确切,因为这种历史态势的形成必须以对立双方力量的均等平衡为前提。然而事实上,中、西方两大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地位一直不是势均力敌、平分秋色的,其间强弱分明、主次判然的格局十分明了。既然如此,那么所谓二者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大融合的流行说法就值得怀疑。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中国美学并非西方美学话语的一统天下。中国本土美学也是有发展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已呈现出全面崛兴之势;同时本土美学面对西方美学的大举“入侵”也并未放弃抵抗。它虽然没有采取直接的、激烈的对抗方式,但却在文化根柢处对中国美学民族特性进行了潜隐的、默默的顽强坚守。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这种民族审美文化的默然坚守依然没有彻底离场。对此,我们是绝对无权忽略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无遗憾地承认,在20世纪中国审美文化语境中,西方美学的“霸权”地位和超强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是客观上无可争议的“征服”者和主导者。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一般美学理论的建设上,无论是思维形式、研究方法的选择,还是具体概念、范畴、观点、体系的确定,都无一不以西方美学为圭臬。这是每一个搞美学的人都清楚的,不用多说。二是即使是研究中国本土美学,也基本凭恃的是西方美学的话语体系。在中国本土上,中国(传统)美学成为西方美学重新阐释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无奈而客观的实情。从早期的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直到今天的传统美学研究,基本都是走的这条路子。这也是了解美学史研究的人都知道的事。如果把这条路子看作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西方化的过程,即使不完全正确,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三是在整个文化背景上,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体用之辩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西体中用”说却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这一点在“五四”前后和新时期尤为显著,而在其他时期也不曾有根本的改变(如以美学为例,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主要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即为我国美学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亦即美学之“本”)。对最后一点,我们不妨进一步设问一下,包括美学在内的整个文化上的“西体中用”,这只是个别理论家、政治家的想法,还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内在必然的需求?
对此,人们已经谈了很多,笔者只想简要指出,撇开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西方文化所谓的“全球战略”不谈,即从一种纯学术的眼光看,西方美学涌入中国语境实在是历史的自觉选择,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使然。这个内在要求就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所一直鼓胀着的走出古典、超越传统、赶超世界、进入现代这一巨大的历史渴求与文化想象。很明显,这一历史渴求与文化想象的实质也就是向西方看齐,因为在近、现代中国人的主流观念中,西方代表的就是新文明、就是现代化。正如胡适在1935年仍然在说的:“现在有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当然只能是西方文明。他还用“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不妨拼命走极端”这样的话来强调他关于学习西方的明确态度(注:《编辑后记》, 载《独立评论》142号,1935年3月17日出版。)。胡适这一不乏过激的“西化”观点,应当说是有较大代表性的。它虽指的是一般的中国现实变革和文化前途问题,不专指美学,但无疑包括着美学,反映着中国近、现代美学的主流意识。事实上,同其他领域相比,美学的“西化”欲求尤其强烈,因为它作为一门学科,本身就是西方近代的产物。所以,中国美学要满足走出传统、跃入现代的历史欲求,只有以西方美学为本体、为准的,把它视为可资凭恃的基本的理论范型和学术典式。这是本世纪中国美学别无选择的自觉选择。
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即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总体上是以西方美学为推力、为圭臬、为主导、为中心的历史。
(二)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美学而言,西方美学值得“全盘接受”的内在学术价值具体有哪些呢?我们觉得,大致地讲起码有以下五个方面。
1.“现代化”的学术承诺。
同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一样,“现代化”也是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中心焦虑”和巨大渴求。那么,谁能保证这一“中心焦虑”的释解和巨大渴求的实现?显然,本土传统美学无力承担这一使命,因为它已被人们普遍视为“非理论”的、不“科学”的,所以不可能成为“现代”的。于是,西方美学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首选对象;它被认为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提供一种学术可能和承诺。实际上,“现代化”作为一种似乎不证自明的普遍绝对的价值信念和标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已差不多就等同于“西方化”,美学的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今天仍常常听到的一些美学上的“大话语”(Big Words), 如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美学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体系,等等,无一不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美学的最高学术旨归。然而很明显,这个“现代”一词的本义,主要指的是以西方(现代)水平为标准,或至少有“赶上西方”、“能与西方并肩”诸层意思在内的。一句话,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以西方美学为基本准的、尺度和目标。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学术“约定”:要想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就要学习和掌握西方美学;而要学习、掌握西方美学,首先要学习西语,精熟西学。这是美学的基本功、基础课,无此“学历”就不配搞美学。但似乎没有人强调搞美学的人必须精通古代汉语,深解传统文化。因为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已形成的确定无疑的观念是,古代汉语之类代表的是僵死陈腐古旧过时,是与“现代”不沾边的东西;而唯有掌握了西语,才会打开西方美学的大门,也才会真正找到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金钥匙”,赢得“现代化”的学术承诺。应当说,这是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得以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领域之“霸主”的首要原因。
2.理性化的认知规范
这里所谓理性,主要不是道德理性、实用理性,也不是人文理性、生命理性,而是一种思维理性、知识理性、分析理性、科学理性,是一种唯真理是求的主体意识和认知方式。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偏重的是道德理性,当然也不缺人文理性,而较为匮乏的正是这种唯“真”是求的思维理性、科学理性;而后者恰恰是西方文化、西方美学的突出特长。所以,当20世纪中国美学渴望走出传统、进入“现代”时,西方美学的这种思维理性、科学理性便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认知规范。王国维在世纪之初就指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注:《论新学语之输入》,作于1905年,收于《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他还说:“中国一切学问中,实以伦理学为最重,而其伦理学又倾于实践,故理论之一面不免索莫”。(注:《孔子之学说·叙论》(1907年),收于《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为了改变此种状况,他专门翻译了英人杰文斯(Jevons.W.S)旨在研究“人类思想之普遍形式”的逻辑学著作《辨学》,在推动20世纪中国思维理性、科学理性的发展方面建立了筚路蓝缕之功。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赛先生”的倡扬,更标志着追求科学理性、思维理性已达到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自觉。新时期以来李泽厚等学者对“理性”、“科学”的频频倡导,更是人所共知的。反映在美学上,强调逻辑性、理论性、科学性一直是该学科建设的一大目标,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的“美学热”等,除了深入探讨了各种美学问题外,也十分自觉、成效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建设目标的实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性认知体例与规范。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这种自觉追求理性化的认知规范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西方美学那种精于思辩、长于科学的理性精神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绝对主宰和深刻塑造。
3.体系化的知识形态
同理性化的认知规范密切相关的,便是西方美学那种体系化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美学摹习西方美学、追求“现代”品格的最显明的标志。在人们心目中,美学的“现代化”几等于“理性化”,而“理性化”又几等于“体系化”,即现代美学应该是一种理性化、体系化的知识形态。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多出于散乱无序的语录、谈话、对答、注疏、寓言、随笔、感悟、心得等等形式,缺乏严密性、完整性和系统性;而西方哲学、美学则讲究概念思维的逻辑性、严整性,强调美学理论始终一贯、前后有序的系统性。这一点在近代以来尤其显著。所以,美学研究要讲究体系性,就只能以西方美学为标本。王国维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注:《哲学辫惑》刊于1903年7月《教育世界》55号。 )由此他很肯定地认为:“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注:《东洋史要·序》,《王国维文集》第四卷。)这里明确把有无“系统”、是否“严整”,视为判断哲学、美学优劣与否、科学与否的基本标准,其观点在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界、美学界都是极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此后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大都以这种体系化、系统化为最高学术追求。从20年代开始,以《美学概论》、《艺术概论》等为题的美学、文艺学著作即在不断出现,而在50~60年代之交的美学大讨论以及80年代以来的当代美学研究中,这种体系化、系统化的学术意识更趋自觉和成熟。这意味着,西方美学那种体系化的知识形态,已成为20世纪中国美学孜孜以求的一种学术总目标和总范式。
4.普遍化的阐释准则
西方美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美学来说,还有一个重要“身份”,那就是被视为一种具有合法性和普适性的学术阐释准则。也就是说,对于美学问题,包括中国本土美学问题的解读和阐释,需要有一种基本的、合法的、普遍有效的学术准则,或者说一种权威化、标准化的学术参照系。在本世纪中国人看来,本土美学是无力提供这种东西的。那么很自然,同“现代化”、“理性化”、“体系化”的选择一样,西方美学也无可争议地成为这样一种合法化、普遍化的学术阐释准则。于是,人们被告知,要想搞好美学,特别要想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就必须深通西方哲学、西方美学。王国维早在世纪初就宣布:“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注:《哲学辫惑》刊于1903年7 月《教育世界》55号。)王国维虽是说哲学,但也涵盖美学,因为在他那里,美学“俨然为哲学中”一大部分。实际上,他的美学研究也确是如此。他运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阐发“《红楼梦》之精神”;运用康德美学思想写成《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等等,即为将西方美学话语作为普遍化、合法化的阐释准则来解读中国本土美学的最早范例。其后,30~4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伍蠡甫等将西方美学理论近乎出神入化地运用于中西方诗学和绘画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李泽厚就说过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完全是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讲的。建国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获得较大发展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其学术路径,也大体还是用西方美学的理论概念、范畴、学说、命题等来解释中国美学的诸种问题,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优美、崇高、典型、形象等等见诸中国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许多基本术语,无一不是来自于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话语体系。对中国本土美学的研究尚且如此,而在一般美学理论的研究中,这种将西方美学话语作为普遍化阐释准则的情形就更司空见惯,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了。李泽厚在回答“如何学习美学、研究美学”的问题时就说,首先要多学点西方哲学,不学好西方哲学就读不懂好些美学书,就难以真正研究美学。(注:《走我自己的路》(增定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3页。)应当承认,这个看法其实正反映了20世纪中国美学界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境况。
5.科学化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主要是考据之法,其不适应现代形态的美学研究是明显的,故20世纪中国美学在方法上主要以西方为圭臬也在情理之中。从最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到一般的自然科学方法(自然辩证法),再到特殊的模式化方法(如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等等),最后是个别的、专门化方法(如统计法、定量法、考据法、考古法等等),这多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差不多都来自于西方。它们广泛地、深入地渗透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方法论热”,更把引进、摹习、运用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世纪情结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对于来自西方的各种研究方法,中国美学界持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就是这些方法都是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都是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都是事物的本质性联系和规律性运动的思维反映形式,因而掌握了它们,就能够揭露本体,发现真理,掌握规律。总之,方法论与本体论、认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是真确的、科学的。实事求是地讲,这种“方法\科学”的信念也许带有某种乌托邦色彩,但它在开阔中国人的视野,训练规范化的思维,提高整个美学界的认识能力和学术水平方面,究竟是功德无量,意义深远的。
(三)
20世纪中国美学界所认定的西方美学上述学术价值都按期如约地实现了吗?这又是一个问题。换言之,要描述西方美学对20世纪中国美学的巨大推动和强力塑造是容易的,但要指出它对中国美学这种推动和塑造的“文化限度”究竟何在,指出它究竟在何种层面和程度上不仅无法穿透、撼动、置换中国本土美学传统,而且还为后者所悄然吸纳和同化等等,这又是很难的。
但是,站在世纪之交的美学必须解答这些问题。因为,西方美学与中国语境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和解的,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种深刻的、咫尺千里的“文化缝隙”,同样是一个坚硬的事实。
王国维曾用自己的表述方式最早触及了这一“文化缝隙”的事实。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也。”(注:《〈自序〉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王国维的这段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所说的内在的“烦闷”,在20世纪中国哲学、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突出的象征意味。
实际上,他指出了西方美学在中国语境中“水土不服”的一个重大“症候”,揭露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深不可测的“文化缝隙”。
单从美学的视域看,他所谓“纯粹之美学”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的区别,基本可看作西方古典形而上美学和现代经验论美学之分野。在其义理内涵上,古典形而上美学偏于人文、理想、思辩、超越,现代经验论美学则偏于科学、现实、实证、存在。从其学术功能讲,前者固然让人喜欢,令人神往,但离现实太远,无法直接呈现于当下的审美和艺术活动,难以证明其真确与否,所以是“可爱而不可信”;后者固然可证可验,令人信服,但距理想太远,无法满足人的形上追求和超越情怀,难以安慰人的内心,所以是“可信而不可爱”。
古典与现代美学之间的矛盾反映到中国语境中,则进一步显露出了文化上的不适症状。西方古典美学过于理性化、思辩化、抽象化,终究不合讲究“实事”、“效验”,注重“经世致用”的中华学术传统,也无法直接“有用”于审美和艺术的具体实践,因而难以引起中国人持久的研习热情,最后不免要从“热”转向“冷”,从“可爱”转向“不可信”,出现理论价值上的危机。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美学本体论研究渐趋冷寂的现象,与这一危机可以说不无关系;另一方面,西方现代美学则过于模式化、工具化、技术化,终究不合缺乏科学传统的中国人的学术口味。特别是其冰冷枯燥的语言分析方法,尤其不合素以内省、体味、直觉、感悟为主流,而以语言辨析为末道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所以虽一时热闹,但反应寂寂,外“热”内“冷”,终究难成气候。这也是80年代中期以来偏重语言分析的种种美学新潮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深在原因。
从更广远一点的时空跨度看,兴于世纪初、盛于建国后的西方美学术语的大量引进和广泛使用,至今也渐呈消退之势。如用“典型”、“形象”等范畴解读中国古典诗歌,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描述中国古典文艺独特历程等等“常规”,已经开始为人们所悄然疏弃。这意味着世纪之末的中国美学已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疲于西方美学”的潜在趋向。这一点,值得我们倍加关注。
王国维由对西方哲学和美学产生“可信而不可爱”、“可爱而不可信”的“最大之烦闷”,而最终将兴趣移于文学和国故,这一学术转向引人深思。在某种意义上,哲学、美学所代表的是西学体制,而文学、国故所代表的则是本土文化。王国维最终从哲学转向诗歌与国故,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的精神从西方体制向本土文化的转移。这一转移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而言,也是具有前瞻性、预示性、象征性的。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所出现的一些新动态、新征象,似乎已在历史地呼应和展开着这样一种王国维式的学术转向,其主要表现大致有二:
1.在美学理论的建构中,建立鲜明的“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呼声和努力渐呈强势。不少学者指出,在经历了世纪初的西方美学大引进、建国后苏联美学、西方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全面渗透之后,现在该是谈论建立真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的时候了。这一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既不是以西方美学为标准和中心,也不是完全的本土传统美学的复兴,而是这双重思想资源在充分关注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基础上所达到的内在融汇和统一。显然,这一“中国特色”的理论构想,更加自觉地突出了美学的民族性、兼容性和现实性,预示了中国美学在下个世纪的新趋势。
2.在美学史的研究中,最堪称道的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蔚然大观。该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美学已从“阅读西方”转向了“重读传统”,从西方式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转向了对本土美学的发掘和深解。虽然这一转向总体上还是用西方美学的观念和方法来阐读本土美学,但这一转向本身是有深远意义的。近几年,又有一种深入研读本土审美文化史的学术动向正在形成,它比之中国美学史研究,则更关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存在”本身,因而其民族化、本土化色彩亦将愈加浓郁,愈加深沉。
总而言之,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展离不开西方美学巨大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但西方美学在中国语境中所日益暴露出来的文化阈限,以及近十几年来中国美学所发生的“本土化”转向也表明,关于西方美学的神话正在悄然崩解。因此,在这世纪之交重新评估西方美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学术意义,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