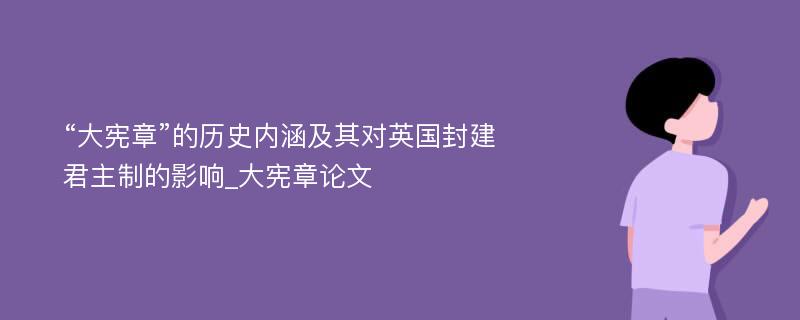
《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对英国封建君主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章论文,英国论文,君主论文,底蕴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6)02-0043-13 1215年6月,英格兰一批反叛王权的封建贵族,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英王约翰签订了载有其多项要求的著名文件《大宪章》①。在《大宪章》诞生800周年之际,如何研判它的精神价值与历史地位,再次成为中外学术界所聚焦的热点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受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之“宪政主义”历史诠释模式的影响,西方史学界乃至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常常漠视《大宪章》在其中世纪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中显示的封建性属性,倾向于用历史“穿越”的方式将《大宪章》与近代政治变动与社会诉求机械搭配起来,致力于发掘这一历史文献的“现代性”,即发掘其中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诸如“自由”“权利”“民主”“法治”之类的现代思想内涵。尽管这一学术取向不断遭到质疑和针砭,但它的“流风余韵”仍旧在学术界绵延不断,而且对社会大众深有影响。例如,1988年6月,一批英、美史学家聚集在英国的温莎城堡,举行会议纪念《大宪章》签定773周年,其主旨就是要对当代西方世界的“自由之根”(Roots of liberty)再来一次深入的揭示②。而2015年英国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大宪章》问世800年的活动,也是以《大宪章》为“自由的基石(Foundation of Liberty)”作为纪念的基调③。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反思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传统、憧憬现代民主政治建构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对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学术史的的全面追踪与梳理,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人的这一学术倾向的影响。在一些论著中,不仅将《大宪章》翻译为“自由大宪章”,而且对其“宪政主义”的历史诠释模式加以无保留的接受与认同。基于这一状况,本文拟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来考量,来揭示《大宪章》的真实的历史底蕴及其对中世纪英国政治史的实际影响。 诸多史实表明,任何一种政治文献的缘起与内涵都必然要反映与之密切关联的特定历史时代的主要矛盾冲突与主要阶级的社会诉求。因此,只有结合相关的社会背景来对某一政治文献进行文本解读,才能洞察它的特定的历史底蕴,阐明它对当时政治发展趋向的特定影响,对《大宪章》的认知也概莫能外。 征诸史实便不难发现,《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社会盛期统治阶级内部权益的矛盾与纷争的产物,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封建贵族尤其是世俗大贵族阶层限制王权以恢复和整固封建特权的渴望与呼声。 诺曼征服后,英国建立起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封建王权,国王获得一国之君和封建宗主之双重身份与地位。一方面,君主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公权遗产,如王位由王族世袭、教会的“王权神授”传统、地方分郡制乃至丹麦金的税收等。另一方面,国王与贵族缔结起私家的封君封臣等级制度,同时借助于“索尔兹伯尼誓约”和土地赋役调查,打破了大陆封建制的那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居间权力”的限制,成为可以制约各级封臣的最高宗主。同时,英王还将教会纳入封建制的网络中加以控制。然而,国王要将公权、私权整合一体进行集权,尚存在着诸多困难。其中主要的障碍乃是作为王权政治基础的封建贵族。按照界定双方关系的封建习惯,国王不仅应该让贵族作为朝臣议政参政,吸纳他们的“谏议”,而且对贵族封建骑士役征调、对封建协助金与封地继承金的上缴、对贵族婚姻和司法审判的干预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界限。而贵族在这些领域中的封建特权,正是他们效忠国王的前提。此外,由于罗马教廷的神权正处上升势头,英国教会恢复“自主”特权的呼声也不时出现;而城市也不时要求享有“自主”、“自治”的特权。 与上述特定社会背景相一致,当时的英国流行着“王在法下”或“法大于王”的观念传统,则构成了对封建君主集权的某些限制。这一传统主要由三种融合而成。其一是从早先日尔曼部落遗存下来的含蕴着原始民主观念残余的“法律”支配一切的观念。这种“法律”是通过记忆而世代传承的长期流行的部落习俗,因而“法律是被发现的、公布的,‘找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④。国王在制定“新法”时,也要派人去各地搜集已有“法律”,在贵族会议上加以讨论、整理与增减,然后颁布。由于国王不能单独立法,“法律”是“找到”的与共同议定的,那么也就必定是“法大于王”,国王理应遵守“法律”。其二则是“封建法”的观念,随着封君封臣制的建立,有关占有、继承,支助、服军役、监护、婚姻的一整套封建习惯也逐渐约定成俗,被视为古已有之的与永恒的习惯,并与日耳曼的“法律”统治观念融合在一起。“封建法”是建立在封君与封臣之间个人“约定”之基础上的,双方都应按照“约定”的规则来行事,否则“约定”就会自动解除。由于仍属于未成文的习惯,在表述与解释上,“封建法都显得模棱两可与不精确,由此而导致大量的讼争、违抗、求诉与战争”⑤。所有这些特性,都使“封建法”也被看作是被“找到的”古已有之的“良法”,也使它被贵族视为“王在法下”的原则,用作抵制国王“暴政”的依据。再就是基督教的“神法”观念。基督教将国家看作是神的机构,鼓吹“王权神授”;同时也依据“灵魂得救”高于“肉体生活”的信条,主张教权高于俗权。在教会看来,上帝神命的国王当然须服从“神法”来实行公正、仁慈的统治,否则就是违背神意的”不合法“的专制暴君。当时的神学家约翰在《政府原理》形象比喻说,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犹如一个人,国王是头,而教士则是灵魂,“头由灵魂刺激和支配”,国王必须遵守“神法”,尊重教会自主的特权。⑥这类“王在神下”的主张,也被看作“王在法下”的注脚。在当时的英国,这三种观念逐渐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朦胧的“法治传统”,为贵族、教会的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 然而,在《大宪章》产生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上述所谓的“法治“传统并未有效地限制王权。由于英国的封建习惯是基于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口头契约”(oral contract)而非“文本契约”(paper contract),其在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划分并没有一条明确精准的界限,如何遵守完全取决于双方实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史家就指出,这样的“契约”的确存在,并体现在国王的加冕誓词和特权赐予状中,若国王违背其中的约定(法),就会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受到教、俗贵族的抵抗。但“这些约束的功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王的性格”,个性强而有活力的国王常独裁政务”⑦。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英王不断政治集权,突破封建习惯的限制,对贵族阶层已享有的封建特权乃至教会教务“自主”与城市的特权构成严重威胁。国王和贵族、教会之间的冲突连绵不断。在这一过程中,也曾有国王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而对贵族作出承诺。亨利一世即位时,为笼络贵族,在其《加冕誓词》中,宣称要革除威廉二世之弊政,“废除所有一直不公正地压迫英王国的邪恶习惯”,恢复爱德华王和威廉一世的祖宗良法,并对封建习惯再次作了界定,对贵族作出承诺:封臣的继承人只须交“公正与合法”数额的继承金即可继承其封建地产;封臣之女只要不与国王之敌结婚,国王不予干预,其女如作为继承人,婚姻则根据贵族给王的建议来安排。封臣遗孀若无子嗣,可享有其携来的嫁妆与部分亡夫的遗产再嫁;除反叛者外,封臣被罚没土地时不必上交全部动产等等⑧。同时,亨利一世对教会的教务“自主”要求,也给与了一些让步。1107年他与教会达成协议,规定:国王不再以封建宗主权干预教务,主教由本教区的教士团体牧师会(Chapter)选举,国王放弃对新主教的指环和权杖的授予权。尽管要求选举但选举须由由国王监督,主教在就圣职礼前仍须向国王行封建效忠礼,但毕竟给予了教会有限度的特权⑨。此外,从1126年始,亨利一世还让坎特伯雷大主教兼为教皇在英的常驻使节,作为教廷的代表负责在英教务。对于当时开始萌发的城市“自主”特权的要求,亨利一世也从维护统治的角度予以考虑。如他曾颁令免除了伦敦市民的丹麦金、司法罚金以及大陆通行税,同时让其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使他们可以将固定为300磅的承包税直接交给财政署,并有权选举自己的城守,建立城市法庭等等。 亨利一世通过承诺而厘清的这些封建特权边界,不仅在其后期的统治中被他本人扭曲,而且在斯蒂芬王时期特遭到封建特权阶层的践踏。乘国王与“安茹派”内战之机,不少大贵族扩展地盘,不纳王命,甚至反叛;教会则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自行选举并实施独立的宗教审判权,伦敦等城市一度效忠于“安茹派”与王权对抗。因此,亨利二世上台后立即采取诸多强有力措施进行政治集权,打破、超越封建“习惯”对贵族严加控制和攫取,并在《克拉伦敦敕令》中将教会“自主”特权尽行剥夺,把教务纳入王权的直接支配之下,由此而导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激烈反抗并以身殉教。对于城市,亨利二世倒是颁发不少令状赐予特权,扩大王室财源。与此同时,罗马法的“君权至上”原理也开始渗透进来,索尔兹伯尼的约翰在《政府原理》一著中虽强调“法律”对王权的限制,但也引用罗马法强调,“国王的意志将具有一种决断力量,最恰当的是,在他满意的地方就拥有法律的力量”⑩。法学家格兰维尔在《英王国的法律及习惯》一书中,尽管将“法律”与“习惯”相提并论,并强调英国的“集体立法”传统,但也试图将之与罗马法的“君权至上”原则结合起来。故他指出,“英国的法律虽然未写下来,但无疑应该被称之为法律(因为君主所喜好者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本身就是法律)”,“法律是君主和贵族共同讨论决定然后公布的”(11)。正因为如此,史家将亨利二世的王权称为“君主独裁制度”(Despotism)或“君主专制制度”(Absolutism)(12)。 如果说,由于王权的强固与战争形势的稳定,亨利二世的独裁对所谓“法律”的超越还处在一个封建特权阶级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那么到了约翰王在1199上台后,这个限度就完全崩溃了。约翰王统治时期不断与法兰西王权争夺大陆领地,“几乎是一个不断战争的时代”(13)。此时正当法国著名君主腓力二世在位,约翰王多次派军在诺曼底、波亚图等地与法军争战,并曾征讨不愿臣服的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对法战争的惨败不仅损害了他的政治形象,而且造成巨额军费开支。另一方面,此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羊毛、粮食等商品出口的激增和白银的大量输入,英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出现。与12世纪60年代相比,在13世纪的最初10年中,牛的价格上涨了118%,羊的价格上涨了132%,小麦的价格则上涨了264%(14)。在此情况下,国王宫廷的花费急剧增加,这和军费一起导致了王室的严重财政困境。为了应对这一形势,约翰王肆无忌惮地超越封建“习惯”的特权边界,对贵族、教会以及市民进行超常规的攫取。他先后滥征骑士役、盾牌钱和动产税,新征所有进出口货物之商税。同时,滥用封君权力超常规地征取封地继承金,通过干预贵族的婚姻榨取钱财,甚至将贵族遗孀赐给自己的雇佣军首领(15)。对于抗拒者,约翰王则实施流放、监禁、没收封地与城堡等处罚,甚至将其“饿毙”(16)。此外,约翰王还变相兜售郡守职位,用“宫市”的手段低价强购宫廷用品。在国王的繁重征调和榨取下,贵族负债成为这一时期明显的社会现象。不少贵族为还王债,只得借高利贷而债台高筑,有的则倾家荡产,甚至将债务传及后代。教会更是深受其害。约翰王不仅对教士也征税,而且还仿效前朝君主利用封建宗主权任意延长因病故、出逃所造成的高级教职空缺期,将其所辖之教区、修道院的财产及土地收入攫为己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干预高级教职的选举与任免,致使教廷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在大陆滞留6年而不能赴英就职。约翰王的这些举措,导致了王权与封建特权阶级的矛盾急剧激化。罗马教廷施行的“禁教令”、“绝罚”及其英国教会的抵制使约翰王最终屈服,而贵族乘机发起并得到伦敦市民支持的武装反叛,则导致了英国封建王权的严重统治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贵族、教会的封建特权阶级诉求,乃是要扭转国王专横独断的局面,返回“先王之法”、“祖宗旧制”的轨道,恢复进而巩固原来享有的封建特权。1213年8月,为了消除一触即发的封建内战,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召集一批贵族和高级教士开会,向他们宣读并解释所谓的《佚名英国特权恩赐状》,要他们以争取此状中的“特权”为抗争目标。这份文件系兰顿匆匆草拟,仿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词》写成,其中有12项条款在1215年的贵族请愿书和《大宪章》中得以体现和扩展,它被认为是《大宪章》的一个“粗略的蓝本”(17)。1215年6月,当贵族武装与国王军队在伦敦对峙时,在兰顿的调解下,著名政治文件《大宪章》就随之诞生。自诺曼征服以来尤其是约翰王在位期间的封建时代的矛盾冲突,赋予了这一文件浓厚的封建性的历史底蕴。 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诉求主旨,《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封建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其主旨乃是要通过约定恢复“祖宗旧制”、“先王良法”,重构一个“仁君”、“明君”治理下的、确保贵族、教会特权的“合法”的封建统治秩序。正因为如此,《大宪章》的引言仍旧肯定了封建王权的合法地位,将国王视为上帝“授权”的尊严的“神命之君”和“承蒙上帝恩典”来统治的国王,视为“忠顺臣民谏议”的吸纳者、贵族、教会封建特权的恩赐者与庇护者。在此前提下,《大宪章》的六十三条条款中,对国王的有关承诺作了具体的规定(18)。 有关教会事务,《大宪章》第一条规定:英国教会应当享有“特权”,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和侵犯,尤其是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享有特权”的选举。这项承诺既是对以往屡次被国王剥夺的选举“自主”权的肯定,也是对国王通过教职空缺而危害到的教会经济权益的重申。 在贵族封建特权与义务上,《大宪章》则作了不少明确界定。有关封地继承金方面,第二条规定,一律按照旧制缴纳封地继承金。伯爵和男爵之继承人缴纳一百镑,骑士继承人最多缴纳一百先令,缴纳之后即可继承封地,“应少交者须少交”。有关贵族未成年继承人的权益方面,第三、四、五、三十七条规定,受监护的继承人只需在成年后缴纳继承封地金,其他费用一概免去;国王和其他监护人只能按照习惯征取受监护者封地上赋税与力役,不得使其土地财产遭受浪费与损毁,否则将处以罚金或自动丧失监护权,改由“合法与端正之人士”监护。有关封建支助金方面,《大宪章》第十二、十五条也重申旧制,在国王的长子晋封为骑士、长女出嫁和国王被俘时,贵族需向国王这个封君交纳适当的费用。除此之外,如无“王国共同协商”,将不征收任何盾牌钱与支助费。有关贵族婚姻方面,《大宪章》第六、七、八条规定,继承人得在不贬抑其身份之条件下结婚;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不得被强迫改嫁,但如果寡妇占有国王或其他封君之封地,应征得其同意才行。在贵族债务方面,第九、二十六条规定,凡债务人之动产足以抵偿其债务时,均不得强取其收入以抵偿债务;国王的封臣死亡而又欠债,则按照“公正人士”的意见,按照债务数额登记与扣押其动产,待其偿清后即交由死者之遗嘱执行人处理。在骑士军役上,《大宪章》第十六、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强迫骑士“服额外之役”;骑士因正当理由委托合适之人代役,不得对之勒索财物。有关对贵族的惩罚方面,《大宪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判定外,不得科以罚金。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王国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五十二条规定,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国王及其官员夺去其土地、城堡、特权或权利者,须立即归还之。第三十四条规定,国王不再颁布将由领主自己法庭审判的案件转移至国王法庭审讯之令状,以免自由人丧失其自己的法庭。 在《大宪章》中,还有一些条款并未明确为何种对象所设,而是涵盖所有“自由人”,不过其中的意旨,则是以贵族权益为轴心的。如在“特权”上,第一条承诺,国王及其后代,将宪章中各项“特权”给予王国内的一切自由人。第四十条规定,为了消除苛政,只任免那些懂得王国法律并能很好遵守之的人为法官、镇守、郡守和百户长。第二十五条规定,所有郡、百户区、村,除了国王的领地庄园之外,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第二十八、三十、三十一条规定,在王家购买货物上,国王官员不得以拖欠钱款的方式在民间强取谷物、车辆、马匹、木材等为其所用等等。第二十三条承诺,除了原先负有法律义务者之外,不得强迫任何村庄与个人修造渡河桥梁。第十七、十八、十九条则规定了一般诉讼由地方法庭审理,涉及到土地、遗产等大案的审理,由国王派出的法官在郡法庭用陪审制方式“合宜”裁决。第三十六、三十八、四十条承诺,王国法官不得借司法审判敲诈地方,不得私自实施非理性的神裁判法等等。 对于当时开始勃兴的城市,《大宪章》也给予了一些承诺。例如,在谈到封建支助金时,《大宪章》第十二条也申明,关于伦敦城之贡金,按与封建支助金的同样规定办理。第十三条规定,无论水上或陆上,伦敦城都应享有其旧有之“特权”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市镇、港口,国王也承认或赐予它们享有所有“特权”与自由习惯。谈到商品流通时,《大宪章》第三十三条规定,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之河流上所设的阻碍船舶通行的拦河坝一概拆除。而第三十五条规定,在酒类、谷物、布类的交易上,实施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第四十一条对国际贸易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作了规定:除战争时期敌对国之人外,所有他国遵守王国习惯的商人,皆可来英经商,并免除苛捐杂税;同时,在战时为了保护本国商人在敌国的人身财产安全,先行扣留敌国商人作为威慑。 粗略统计可见,在《大宪章》的六十三条条款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有明确要求保障贵族(包括威尔士边区英国贵族)及教会权益的条文约有二十六条,占全部条款的41%以上,其内容涉及保证贵族财产、司法和政治各至关重要领域的特权与教会自主选举高级教职与处理教务的特权。针对所有“自由人”但却隐含贵族权益的条款有十三条,占总条款的20%以上,这还不包括反映了贵族需求的有关森林的条款。而涉及到城市市民权益的为五条,约占全部条款的8%。 如果进一步对《大宪章》中核心术语作进一步解析,则其历史底蕴的彰显则更为清晰。首先来看libertas(liberty)。在以往的阐释中,libertas几乎都被解读为“自由”,由此而断定《大宪章》包含着自由、权利、民主的现代性。事实上,《大宪章》中的liberty、right、concession等,其本意大体上指封建的特权(privilege)或特许权(franchise),它们中既有传统的习惯,也有国王的令状所承诺、规定下来权利。有史家认为,《大宪章》中的liberty是指国王赐予的特权(privilege),与一块豁免于行政司法管辖之外的区域,如私有百户区,除此两项,别无它义(19)。事实上,多年来将《大宪章》中的liberty解读为“自由”、“权利”的那些些条款,有着三层含义。首先是土地占有、分授基础上的“封建法”或封建习惯所“约定”特权,即作为最高封君或封建宗主的国王授予贵族所享有的特权或豁免于某项义务的特权。其次,是国王依据“神法”的要求承认教会多年来所争取的高级教职选举与教务“自主”的特权。再就是国王授予城市某种“自主”或“自治”的特权(20)。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王作出所有这些特权承诺时,也将以往的“日耳曼法”、“神法”贯穿于其中,不仅冠之以“先王旧制”、“祖宗良法”、“上帝意旨”的政治标签,而且也申明涵盖王国内的所有“自由人”。因此,《大宪章》并非是什么《自由大宪章》,而应被称之为《特权大宪章》。 那么,《大宪章》中的“自由人”究竟是指哪个阶层呢?《大宪章》中一些条款都谈到了所谓“自由人”(liber homo/free man)的特权、权利,而这正是认定《大宪章》包含“民主”、“人权”之现代性的又一重要依据。如果作一仔细辨析即可发现,在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律用语中,这一所谓的“自由人”,实际上主要是指享有封建特权的贵族阶层。尽管相关的条款对谁是“自由人”并无刻意说明,为后人的解释留下来想象空间,但其中的话语则对判断这些“自由人”的身份作了不少提示。如第十五条申明“自由人”有缴纳封建支助金的义务,这正是封臣的身份标志之一;第三十四条谈及避免“自由人”因王家司法令状而“丧失法庭”,这是特指拥有私家封建法庭的贵族;第二十七、三十条则表明自由人拥有地产、财产,其意不喻自明。虽然有关“自由人”的个别条款中指称宽泛,也包括当时出现的城市市民阶层,甚至也应包括当时与领主没有严格人身依附关系的少数农民,然而相关的大多数条款表明,文中的“自由人”主要还是指当时占有地产的各级封建贵族。有史家就对此诠释说,在《大宪章》中,“自由人”(freemen)实际上是“世袭地产保有人”(freeholder)的同义词,而“这仅仅是一个被限定的阶级,作为被授予人或这类人的后裔,他们能够通过一个法律诉求成功地分享其所给予的特权”。《大宪章》在“谈到自由人时,从未意味着这包括普通的农民或村民”,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后,它才渐渐被解读为越来越小的限定意义,直到它涵盖所有的英国人”(21)。 总之,《大宪章》的主基调浸润着英国封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所赋予的历史属性,那就是由土地封授、占有基础之上的自上而下的层层统属与自下而上的层层依附的封建性。它的主旨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在传统的封君封臣制度的框架下确认国王作为最高宗主的权限与贵族作为封臣的封建特权与义务。正因为如此,有史家指出,“宪章中特权概念的表达依靠的是传统的封建特权……特权是高高在上者的赐予,他们同样可以通过正当的理由将之取走。”(22)如果忽略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冲突与历史语境的意涵,去主观想象或望文生义地阐释其所谓的“自由”“民主”“权利”的现代性,无疑是一厢情愿的误读与误判。 揭示《大宪章》的封建性,并非要否定它的重要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宪章》的问世,标志着中世纪英国封建秩序从无序化、随意性走向法理化、制度化的开端。诺曼征服后,盎格鲁撒克逊原始民主传统仍然残存,融入了大陆引进的“封建契约”之中。但由于“舶来”的封建制是随着征服战争由国王通过显赫的军事声威自上而下同步推进的,国王在与贵族之间的封君封臣私家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双方的权利义务只有“口头约定”而无“文本契约”。因此,同时具有“一国之君”政治身份的国王为了拓展公共权威,必定在实施宗主权力时常常轻易突破“约定”的封建习惯的边界,打压、缩小贵族阶层的特权空间。从这个角度讲,《大宪章》是中世纪英国第一份文本化的“封建契约”,且是国王与整个封建贵族阶层签订的。这一文本明确规定了国王与贵族之间权益的边界,对于实现封建秩序的法理化与制度化十分重要。同时,由于不是与单个贵族而是与整个阶层的“约定”且在名义上扩大到整个“自由人”群体的范畴,大宪章也就有了整个王国“宪法”的韵味。随着日后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农奴解放进程的开启,《大宪章》之“特权”所涵盖的人群数量在理论上也必定随之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宪章》中的相关条文约定,将“同意”和“代表”意涵贯穿其中,构成了日后英国议会君主制建构的政治原则。如第十四条规定,国王征收协助金与盾牌钱,需在至少四十天前,将有关令状送达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王国的共同意见”;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同侪合法裁判或王国法律判决,不得逮捕、监禁“自由人”;第五十五条规定,国王实施的一切不正当与不合法之罚金与处罚,也可以经过参与订约的二十五位贵族之意见,或其中大多数贵族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等协商处理;第六十一条规定,由贵族推选出25人组成委员会,代表王国“共同体”监督《大宪章》的实施,并拥有使用武力迫使国王改正错误的权利。如其中有人亡故,则应再推选人补充,而人数过半做出的决定,将视为合法且具有约束力。这些诉求和规制虽然带有自发的、朴素的色彩,但也显示,《大宪章》的产生意味着封建君权的运作开始步入制度化亦即“宪政”(本意是“制度”)的轨道,“王在法下”传统的建构开始有了明确的法理依据。同时,这些原则也与其他条款一道,为后世新兴政治力量的斗争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与宽泛的拓展空间。 《大宪章》的主旨乃是重构被君主独裁打乱了的封建政治秩序,在“法律”框架内厘定国王与贵族、教会之间封建权益的边界。这就决定了它并非是要否定王权,而是要限制王权,将国王的权威纳入到“正常”的制度化的运作轨道。然而,它不可能为国王与封建特权阶层的矛盾、冲突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是因为君主制的本质决定了国王不仅总是要独断专行,而且也不会完全信守在特殊时期做出的任何政治承诺。作为文本化的“王国法律”,《大宪章》能否限制王权,既取决于国王与贵族之间政治势力的实际对比,也取决于国王是否考虑培固其政治基础而做出某种让步。因此,在此后三个多世纪中,英国封建君主政治史的历史“漩涡”中,《大宪章》经历了屡起屡仆的“命运沉浮”。 《大宪章》签订后不久,亨利三世上台,为了巩固王位,辅佐国王的重臣确认《大宪章》。然而,《大宪章》中的一些承诺并未兑现。例如,《大宪章》规定贵族男爵领的封地继承金的缴纳为一百镑,但其颁布后这一承诺并没有被国王恪守。《国库卷档》有关这一类记载,1220年,理查德·得·哈科尔特交纳了500磅。1224年,尼吉尔·得·莫布雷交纳了500镑,约翰·得·比尔金支付了300马克;1227年,罗伯特·菲兹·莫尔得雷德支付了200马克;1234年,约翰·菲兹·阿兰交纳了1000磅;1247年,罗吉尔·得·莫尔蒂梅尔交纳了2000马克;约翰·得·维尔登交纳了300马克(23)。亨利三世亲政后,虽曾于1253年为获得贵族的财政支持再度确认《大宪章》,但实际上却独断专横,重用外国人,甘愿受教皇敲诈,并发动远征西西里的战争,不顾荒年要求贵族缴纳其三分之一的收入以充军费,引起了贵族的反叛,1258年开始的贵族改革运动中,《大宪章》多次被贵族作为与国王博弈的筹码。1258年贵族制定的《牛津条例》中就规定:国王不能任意没收地产、分配土地与监护土地,也不得擅自决定对外战争。1264年8月,亨利三世与反叛贵族达成协议,承诺永远遵守之前由国王赐予臣民的《大宪章》(24)。1265年3月,亨利三世进行和平宣誓,承诺如果违背《大宪章》,将被处以绝罚(25),但他背后却让王子备战,几个月后,王室的军队在埃夫舍之战中将反叛贵族镇压。大约在此时问世的体现了贵族诉求《刘易斯之歌》,从一个角度揭示了《大宪章》或“法律”难以限制国王的尴尬状态。该作品抱怨亨利三世独裁暴政,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志来为政,延揽和重用来自外国的人为廷臣,贬黜忠耿的贵族,并将之作为“叛国者”加以惩罚,“英国人被当做狗那样藐视”(26)。因此,在上帝的支持下,西蒙伯爵高举“复仇”义旗,率众为民众的权利而战,最终在刘易斯一战中击败国王及其追随者。作者感叹道,“通常说,‘当国王乐意时,法律也就趋之’。但真理却是,只是在国王屈服时,法律才挺立起来”(27)。 《大宪章》的限制与国王独裁交替的情况,在此后的三个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也不时出现。1297年,爱德华一世在全国征召军役跨海支持弗兰德尔伯爵对抗法国国王,当即遭到贵族抵制,认为王国此时受到苏格兰、威尔士的威胁,进军弗兰德尔既无价值也有风险。诺福克伯爵罗吉尔·毕哥德、赫里福德伯爵亨弗雷夫·德·波亨等为代表的大贵族,向国王递交了《进谏书》(The Remonstrances),其中悲叹,“整个王国的共同体深感悲伤,因为他们并未受到与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一致的对待、没有受到与他们的前辈常常受到的一致的对待,他们也没有享受到他们未享受的特权,这些特权被武断地搁置在一边”(28)。《进谏书》除了为此抱怨国王外,还反对国王为此军事行动任意征税,违反了《大宪章》,声称他们前辈没有到弗兰德尔去服军役的义务,此时被征调重税,让其更不堪负重(29)。在贵族强大压力下,爱德华一世颁布《宪章确认书》(Confirmatio Cartarum),其中宣称:国王亨利三世时期“被整个王国一致同意而草拟的章程”需要得到遵守,任何与之相悖逆的评判“将是无价值的和无效的”。为了王国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征调税收,应该“得到整个王国的一致同意,为了这一王国的共同利益”(30)。尽管如此,爱德华一世并不愿意受到限制。到了1300年,他在一令状中却将国王权威宣示出来:“在制定这份敕令时,国王和他的御前会议成员都在场,希望和打算国王权威的权利和特权在所有事务中被保存下来”(31)。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贵族集团要求监督王家政府,议会制进一步发展,使得《大宪章》的历史影响一度升温。国王即位后不久,贵族集团立即与以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为首的“王党”激烈冲突,并试图控制王国政府的核心——国王的“内府”。贵族代表在谏议文中提出《大宪章》展示的“王在法下”的精神,并将国王个人权力与“君权”(Crown)区别开来,声称效忠“君权”比效忠国王本人更重要,要求国王清除奸邪之人,遵守王国法律。1311年,在御前大会议上,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为首的“贵族立法团”(Lords Ordainers)拟定了浸润着《大宪章》精神的《约克法令》(The Ordinances of York),其中要求:国王需每年召开议会,需“征得他的贵族的建议和同意”来任命朝廷和内府的重臣,驱除加维斯通等奸臣,废除爱德华一世以来“违背了《大宪章》”的苛重税收。(32)次年,贵族集团逮捕并处死了国王宠臣加维斯通,但国王并未甘愿受限。不久,国王宠信德斯朋塞父子(The Despensers),继续培固势力,唆使“王党”与贵族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1318年达成休战协议,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重新颁布《大宪章》。1322年国王在博罗桥(Borough bridge)一役中彻底击败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而控制了政局,处死25名大贵族,旋即召开约克议会,制定《约克法规》(The Statute of York),废除1311年的《约克法令》,国王权力再次膨胀,直到其被王后宫廷政变废黜。 爱德华三世即位后,基于其父的“前车之鉴”,为了稳定统治形势,在第一届议会召开时就确认了《大宪章》。当其臣下建议他派军剪灭前朝反叛的贵族时,坎特伯雷大主教用《大宪章》提醒这位年轻的新王,要遵守“已经成为王国法律”并在其加冕誓词中体现的《大宪章》,不要随意去攻击王国中的任何人(33)。爱德华三世亲政后,百年战争爆发,贵族阶层全力支持国王在大陆与法国进行领土战争,因此,几乎没有发生援引《大宪章》来与王权冲突的现象,只有一次是例外,即1340至1341年间随国王在大陆作战的王家“内府”与留在英国摄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的冲突。其时,国王在首次远征回国后,将战争失败归结为大主教及其所统官员在后勤供应上的失职,逮捕了其中几人,并拒绝他们以教士身份提出的对世俗审判豁免权的要求,由此而导致国王与大主教之间的争吵。大主教遂在1341年1月给国王写信以《大宪章》精神相威胁,其中警告国王,不要像其父那样违背《大宪章》、重蹈其父被废黜的命运,指出国王听从邪恶朝臣的谗言逮捕臣吏、贵族是“违背了王国的法律和《大宪章》”,践踏了其加冕上对之遵守的承诺(34)。在随后召开的议会中,该大主教和上议院还数次坚持国王必须恪守《大宪章》的二十九、三十九条规定,不得妄为。上议院中的教会贵族,还不时提出对贵族的惩罚“须经过同级贵族审判”。此外,议会也针对爱德华二世的倒台和王后阴谋集团的独裁,不时拿《大宪章》说事。1331年的议会法令规定,自此之后任何人都不得被违背《大宪章》的指控而让国王没收其土地财产。而1354年的议会法令更外延了《大宪章》第二十九、三十九条所保护的“自由人”的含义,规定“任何人,无论其财产或处境如何”,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被剥夺财产、监禁与处死(35)。尽管如此,《大宪章》仍难以限制王权。由于此时不断展开对外战争,战争费用负担十分沉重,国王对民间的钱物的随意征调不时出现。正因为因此,出现了《爱德华三世镜鉴》(mirror of king Edward Ⅲ)这一作品,作者署名为帕古拉的威廉(William of Pagula)。该著的主基调是,寓国王的权威与尊严于道德和宗教的理论框架中:君主应当崇奉上帝的正义与公正,君主的职位和权威源于他根据上帝的意志来公正行事。他应当受法律限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公正意愿。当君主显得错误时,一定是错误的建议使然,这样的建议应当在国王那里被废除。文中对国王的征调更是十分不满,极力揭露国王朝廷的吏员、法官压价强制购买民间货物的行径。作者甚至愤怒而大胆地指出,“我的国王陛下,在某些行为上,你与强盗头子一样”,对民间肆意劫掠。而“根据普通法,任何人都不应当攫取他人财产,如果所有者不愿意和没有正当理由的话”(36)。作为一个国王,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以压价购买货物的方式来掠夺民众。文中进而强调,“虽然应当说在一些地方君王并不被法律支配,然而,根据法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适用的”,这是因为“君主的权威依赖于法律的权威”,因此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37)。这样的指责,在当时并非是无病呻吟,从一个侧面显示,要用《大宪章》这样的约定来严格限制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显然是不现实的。 理查德二世时期,随着国王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权益之争再度趋于紧张,《大宪章》再度显示出其限制王权的政治效应。在该国王冲龄即位加冕后,下议院旋即在议会中以宣读《大宪章》的形式作了请愿,提醒其“像他在加冕典礼中被要求的那样维持和遵守《大宪章》”(38)。1380年在北安普顿议会期间,《大宪章》又被向早到的代表宣读。同时,贵族集团在议会中与“王党”的权力较量也随之更为激烈。不过到1389年亲政后,国王随即违背承诺,实行独裁统治,不仅控制议会,任命宠臣主政,而且处死、监禁与流放一批教俗贵族,并剥夺其财产。国王甚至公开宣称,法律在自己的口中和胸中,惟有自己“才能够制定和改变王国的法律”(39)。由于失去贵族支持,理查德二世在1399年被其堂兄兰开斯特的亨利武装推翻。为了证明自己阴谋篡权的合法性,亨利在是年9月底召开的议会上,发布指控国王的三十三条罪状,谴责国王违背加冕誓词中的承诺,专制独裁,重用奸臣,侵夺臣民土地、财产,不经法律审判处死臣民等等。其中的二十六条虽然没有提到《大宪章》,但却贯穿了其精神,指责国王违反“王国的法律和习惯”,任意剥夺“自由人”的财产。第二十七条则公开讨伐国王“违背了1215年《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对指控的臣民实施残酷的“决斗法”来进行审判。第二十八条也申诉国王“违背大宪章”而遏制教会的司法权(40)。 如果说,《大宪章》在14世纪因王权与贵族的数次剧烈冲突而显示出特有的政治效应,那么到了15世纪,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样的效应呈现出日益淡化的趋势。用武力篡位创建兰开斯特王朝的亨利四世,为了获得贵族、教会的支持,给自己的权威披上合法外衣,在位十五年先后六次确认《大宪章》。在国王莅临的第一次宗教会议上,有人乘机提出了教会特权“尤其是《大宪章》中包含的那些特权”的享有要求。在1404年议会上,对王家“内府”多有抱怨,但追随国王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上议院演说时极力为之澄清说,国王的政府从未像当下这样受到有效监督,国王会按照《大宪章》的原则为政,遵守法律,实施公正(41)。亨利五世在位九年中,一批有关所谓不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剥夺土地财产的申诉曾接踵出现,被说成是违背了《大宪章》之精神,但都并没有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国王此时正率领贵族专注于大陆战争,权威凸显,《大宪章》的政治效应难以显现。到了亨利六世统治时期国王患有癫痫病、王权孱弱,贵族集团中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并演变成“玫瑰战争”,《大宪章》的影响也就随之日益淡出。到了15世纪后期,尽管“王在法下”的呼声仍旧连绵不绝,但诚如史家所言,在此时的英国,“《大宪章》不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究其原因,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德三世的统治显示出比较专制的“新君主制”的倾向,又因饱受战祸,“英国民众既不反对王家主权的彰显,也的确没有围绕着《大宪章》来捍卫他们的特权”(42)。这一时期的政治与法律思想,其实也折射出这一状况。著名法学家、法官托马斯·利特尔顿(T·Littleton)在爱德华四世时曾关注《大宪章》并提出一个设想,即在上议院议员被指控犯有叛逆重罪时,必须依据反映了《大宪章》原理的法令,让他由议会中“同僚”来审判。此外,利特尔顿还把《大宪章》中的“王国法律“说成是这意味着“普通法的程序”。不过,在他的享有声誉的代表作《占有权》一著中,却几乎没有提及《大宪章》。同时代的影响更大的福特斯鸠爵士(Sir John Fortescue),似未受《大宪章》的影响。他在《英国法律颂》等著作中反对罗马法中“凡君主喜好者即有法律效力”的信条和“王大于法”的君主独裁,反对国王不经民众同意而征调税物,要求国王恪守法律,“不能够任意改变他的王国的法律(43)。尽管如此,福氏在阐发这一“有限君权”思想时,从未提及到《大宪章》。 自颁布后近三个世纪的时期中,《大宪章》的确不时被贵族、教会政治势力用作抗争王权、维护权益的精神武器。但这一现象到了16世纪则成为“明日黄花”。在都铎王朝比较专制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的威权氛围中,《大宪章》则日益沉潜与退隐而被“束之高阁”。都铎君主鼓吹“君权神授”,采取诸多严厉集权措施,“践踏其王国中所有其他权威机构的传统特权,这包括贵族的、代表会议的、市镇会议的、商业公会的和教会的特权”。亨利八世的独裁尤以为甚,在其三十七年统治中只召开过9次议会,并将议会变成其集权的御用工具,以至于有史家认为,英国议会从未像此时那样“去竭力运作或拓展国王的权威”(44)。另一方面,玫瑰战争的惨烈、民族国家兴起的趋势与宗教改革引发的冲突,也使得人们更多地思考王国的稳定而非臣民的“权利”。有史家就指出,“在经历自1399年以来一系列的孱弱国王的统治后,英国人意识到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许多人发现,某些特权的牺牲是维护王国良好秩序所需付出的一种很小的代价”(45)。社会政治精英对此更是将之升华到对君主权威的赞美上。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议会议员、法学家、加尔文著作的翻译者托马斯·诺顿,曾在对1569年反叛者的一份宣传文件中说:“共同体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大船,如果它整个毁灭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安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上帝、然后感激王国和君权,感激法律和政府……所有这些我们都拥有”(46)。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都铎王朝的法学虽然盛行,但法律思想中的“真经”并非是“古代宪政”。在1523年神学博士圣日耳曼(St.German)出版的《博士与学生》一著中,学生们询问他什么是英国法律的基础,圣日耳曼回答有六方面:神法、自然法、王国多样的一般习惯、普通法的格言、多样化的特定习惯和议会法令。在讨论的过程中,该博士还指出,习惯法为基础的法律虽然是最可靠的法律,但如果习惯违背了自然法或神法,就不应该允许其显示其权威(47)。其时,法学家在关注涉及到臣民的特权时,时常考虑的是秩序、政治义务、服从等基本问题。而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法律统治的必要性时常是和要求服从已经建立的权威连接在一起的”(48)。也正因为如此,虽说随着印刷术的应用和“尚古”之风的牵引使得《大宪章》的部分条文曾数次被印刷,其完整版本在1576年被刊印,但它是被作为“古代令状”的一部分而非“宪政文献”刊布的。伊丽莎白一世的普通法法学家普劳顿在其法律案列的著作《评论与报告》中,曾在5个案列中引用《大宪章》,但其引用标明,“他只是将《大宪章》看作主要是与私法相关联的一份令状”(49)。在民族国家兴起的都铎时代,“新君主制”的建构和发展需要的是挺立王权而非限制王权,需要的是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而非各种传统特权的确认与兑现,《大宪章》被“休克”自然是难免的。即便在宗教改革发生后间或有个别教会人士引用它来反对君主对教会权利的剥夺、伸张教会的权利和自由,但它并未引起巨大的“宪政”思潮。基于这种状况,有学者强调:“至少在16世纪90年代,无论是古代宪政还是大宪章都没有成为法律思想的十分重要的阐发对象”(50)。 《大宪章》固有的原初性的封建性,既是由其文本中的条款显现的,也是由酝酿它的封建时代的背景决定的。在唯物史观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任何观念、意识只能是这一过程的“折射”与“回声”(51)。正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冲突,决定了《大宪章》的主旨乃是要厘清封建特权阶层与王权之间的权益边界,恢复或重构被王权独裁所践踏的传统封建秩序。这样的历史底蕴,使《大宪章》在促使封建统治秩序“制度化”与“法理化”中的确发挥了特有的思想效应。然而,《大宪章》在中世纪不断被确认而又不断被践踏直至隐退的史实表明,“文本”的约束力量最终取决于王权与贵族之间政治实力的对决。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崛起及其与专制王权斗争的展开,《大宪章》才再度“重现天日”。正是这一新的政治现实变动,促使柯克爵士等法学家及其后的辉格党对《大宪章》重新诠释,并为之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渲染其作为“政治自由的象征与标志”(52),为反对君主专制、建构资产阶级宪政体制披上“古色古香”的合法外衣。到了19世纪末,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沿袭辉格党的理路来诠释、阐发《大宪章》“宪政”意蕴,更使得这一文献的“现代性”在“层累的历史”中日益积淀和凸显,而其本身原初性的封建历史底色进一步被湮没。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西方学者也不时通过文本语境和内涵的解读,对“大宪章神话”进行“破译”与质疑(53),力图复原《大宪章》固有的封建性底蕴。在理论、方法上,西方学者对那种刻意以现实作为参照坐标去裁量历史、重构历史的“辉格模式”也多有批判。早在上个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史家巴特菲尔德就对之深有针砭。他指出,“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谬误在于走上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由于“为了当下而研究过去”,他们在考察英国政治史时,漠视曲折变动的历史,强调过去出现诸如《大宪章》中的“某些进步原则”来编撰“确认现实甚至是美化现实的故事”。由此,“历史的复杂纠葛在辉格派版本中被大大简单化……历史故事被改写了”(54)。由是观之,如何从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去揭示《大宪章》真实的历史底蕴与影响及其在17世纪的“翻新”,进而深化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史的研究,应该引起中国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注释: ①《大宪章》在1215年签订时其实叫“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而《大宪章》(全称magna cart libertatum或The greatcharter of liberties,简称Magna Carta或Great Charter)这个名称是1217年以后才正式确立的。在内容上,1217年版的《大宪章》把关于森林的一部分独立出来,也叫《森林宪章》。后代君主不断确认的其实是1225年亨利三世成年后重新发布的《大宪章》。实际上,“大宪章”这个译名也是值得推敲的,将之译成“特权大令状”或“大令状”则更为妥帖。基于学术界对这一译名已经约定俗成多年,本文暂且以之来论述。 ②Bllis Sandoz,The Roots of Liberty:Magna Carta,Ancient Constitution,and 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Rule of Law,Columbia,1993,p.2. ③http://magnacarta800th.com/ ④N.Zacour,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London,1978,p.123. ⑤N.Zacour,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p.129. ⑥J.Dickinson,ed.& trans.,The Statesman's Book of John of Salisbury,New York,1927,p.65. ⑦A.L.Poole,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Oxford,1955,pp.5-7,10-11. ⑧D.C.Douglas & G.W.Greenaway,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London,1955,V.2,p.401. ⑨J.C.Dickinson,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des,London,V.2,p.137. ⑩The Statesman's Book of John of Salisbury,ed.& translated by J.Dickinson,New York,1927,p.3. (11)Glanville,translated by J.Beames,Colorado,1980,p.27. (12)J.C.Dickinson,An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79,v.2,p.226. (13)C.W.S.Barrow,Feudal Britain,London,1983,p.99. (14)E.Miller & J.Hatcher,Medieval England: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s,London,1980,p.66. (15)J.C.Holt,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London,1985,p.136; J.A.P.Jones,King John and Magna Carta,London,1971,pp.71-72. (16)J.A.P.Jones,King John and Magna Carta,pp.25-27. (17)Ch.Petit-Dutaillis,Feudal Monarchy of England and France,London,1936,p.130. (18)D.C.Douglas,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London,1975,V.3,pp.316-324. (19)David Carpenter,Magna Carta,London:Penguin books,2015,p.467. (20)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可参考蔺志强教授的论文《中古英国政府对地方特权的政策初探》,《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1)W.S.Mckechnie,Magna Carta: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Glasgow,1914,p.115. (22)Ralph V.Turner,John King England's Evil King? Stroud,2009,p.187. (23)S.Painter,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Barony,New York,1980,p.61. (24)I.J.Sanders,ed.,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7,Oxford,p.298. (25)I.J.Sanders,ed.,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 1258-1267,p.312. (26)T.Wright,ed & trans,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From the Reign of John to that of Edward Ⅱ,Cambridge,1996,p.72. (27)T.Wright,ed & trans,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From the Reign of John to that of Edward Ⅱ,p.116. (28)B.Wilkinson,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216-1399,With Select Documents,London,1952,V.1,p.228. (29)B.Wilkinson,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216-1399,With Select Documents,V.1,pp.220-221. (30)B.Wilkinson,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216-1399,V.1,pp.226-228. (31)D.W.Hanson,From Kingdom to Commonwealth,Cambridge,1970,p.157. (32)C.Stephenson & F.G.Marcham edited & translated,Source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A.D.600 to the Present,New York,1937.pp.193-198. (33)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London,2003,p.121. (34)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22. (35)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22. (36)C.J.Nederman,ed.,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2002,p.84. (37)C.J.Nederman,ed.,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and,p.96. (38)G.Hindley,The book of Magna Carta,London,1990,p.181. (39)A.Tuck,Crown and Nobility 1272-1461,London,1985,p.220. (40)A.R.Myers 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ume Ⅳ,1327-1485,London,1969,pp.407-414. (41)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30. (42)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32. (43)Sir John Fortescue,De Laudibus Legum Anglie,ed.& translated by H.D.Hazeltine,Cambridge,1942,General Preface,p.81; Sir John Fortescue,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ed.by S.Lockwood,Cambridge,1997,p.90. (44)G.Richardson,Renaissance Monarchy,London:Oxford,2002,Introduction,pp.2,118,196. (45)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35. (46)Bllis Sandoz,The Roots of Liberty,Introduction,p.89. (47)Bllis Sandoz,The Roots of Liberty,Introduction,p.6. (48)Bllis Sandoz,The Roots of Liberty,Introduction,p.89. (49)R.V.Turner,Magna Carta:Through the Ages,p.141. (50)Bllis Sandoz,The Roots of Liberty,Introduction,p.77.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页。 (52)Maurice Ashley,Magna Cart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Virginia,1965,p.4. (53)Edward Jenks,The Myth of Magna Carta,Independent Review,No.4(1904),pp.260-268; Max Radin,The Myth of Magna Carta,Harvard Law Review,Vol.60,No.7(Sep.,1947),pp.1060-1063. (54)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版,第16、17页、序言、第97、18页。标签:大宪章论文; 法律论文; 自由人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约翰王论文; 王权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