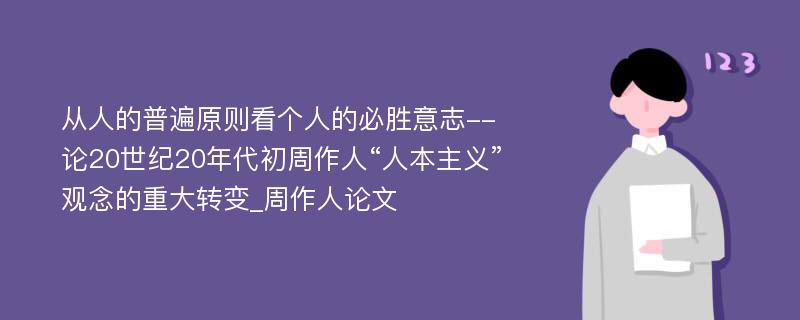
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论20年代前期周作人“人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人学论文,意志论文,求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落潮后不久,周作人思想转变就已开始,到了1924年他基本形成了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而周作人1927年以后的思想变动只不过是把20年代前期就已形成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进一步明朗化和扩大化了。关于周作人在20年代前期的思想转变,本文选择了其中一条线索——“从普遍的人道理想到个人的求胜意志”——加以分析。
1918年12月7日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他试图提出一套较有系统的“人学”观,这种观念实际上包含着两部分:其一是有严格实证科学基础的自然人性论,它以灵肉一元观为核心;其二是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它来源复杂,是经过整合后形成的。这两部分并未完全统一起来。
自然人性论是以进化论影响下的生物学与人类学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灵肉一元观:首先承认人是动物性存在,从而承认人的自然本能、自然欲求以及现世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求生意志。其次,但特别重要的是强调人这种动物又有其他动物所缺乏的“内面生活”(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精神生活。人的精神禀赋使他在进化途中“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并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按照进化的原则,每一自然的事物都有理想的发展,而人类正是一种出于自然而又能超越自然的存在。
周作人论述灵肉问题最后总是落在道德问题范围内,实际上在《人的文学》中他是把他所定的人的精神生活规范的原则限定在道德问题上的,其他方面问题未涉及。所以可以认为关于灵肉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就是周作人的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道德观——自然主义道德观的核心思想。但周作人只是用消极的排除法来划定正面的道德的界限,并没有系统地建立这种道德观的各种细则。由于这种道德观贯穿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推理方法,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道德观称作“科学的”道德观,它是现时可行的,也是普遍适用的。
可以说自然人性论是周作人全部“人学”观的基础,由此出发,他试图建立一种能够调节人类关系的社会—道德理想,这种理想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可称之为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这是一种兼容利己和利他的人道主义,周作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与自然人性论相比,这种社会—道德理想虽显得更为美好,但却缺乏科学根据。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周作人试图把它和以灵肉一元观为中心思想的自然人性论联系起来,仿佛二者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其实,一个是对人性之“自然”的肯定和认同,一者是超越自然的“理想”,从“自然”到“理想”之间不仅存在着巨大差距而且横亘着逻辑上的鸿沟,因而周作人将它们嫁接在一起,显得非常勉强。即使撇开逻辑上的困难不谈,单就实践而言,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也远比自然人性论困难得多。这里不妨看看日本新村运动的情形。众所周知,周作人曾一度对新村主义非常热心。这是因为新村运动恰恰正是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的一次社会实验,其主要目标就是要用这种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个社会运动是相当理想化的,它讲求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都要统一于理想的准则上,并且社会改造的基础落实在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上,这使它具有了巨大的道德感召力量。但运动的领袖们恰恰忽视了任何具有道德价值的宗教或社会理想的成功,必须借助世俗权力(包括组织形式及其运作),否则为追求道德、理想的完善与纯洁性而否定在实践过程中及所采取的手段中会出现的暴力流血、非人道的行为,结果必定会失败,新村运动便是如此。
从1918到1920年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及其实践——新村运动是为周作人所信仰的,宣传它们是他这两年的主要活动。他对这种精神的信仰是在1919年7月访问日本新村期间达到高峰的。在此以前,他对这种理想虽然是信服的,也给以积极提倡,但他对国人能力及自己宣传是否有效又不无怀疑,这些疑虑使当时的周作人对这种理想能否实现还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只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注: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载1918.5.15《新青年》第4卷5号。)。直到1919年7月周作人访问日本新村时,他受到日本知识分子热情的感染,转而确信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在实践上是“可为”的。从《访日本新村记》(1919.7.29)可看出周作人感到一种宗教体验式的“狂喜”,正是这种“狂喜”使他忽略掉现时的条件而确信无疑。这是由情感/直觉在“狂喜”的体验中直接上升为信仰。信仰是排除理性—怀疑的再考问的,是不能被分析的,所以周作人先前的疑虑实际上是被跨越了过去,搁置在一旁的。
从其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中周作人又进而生发出“人道主义为本”(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的“人的文学”(注:周作人:《人的文学》,载1918.12.15《新青年》第5卷6号。)的理想:首先承认个人与人类、利己与利人原是一体,因此表达个人的感情欲求与表达人类的意志是统一的,于是个人的自我表现同时也就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与共同的理想的表达,所以文学是能够沟通人们的心灵情感的;而人道主义文学的任务便是以富于人道主义理想的文学来感染人,并影响于个人的思想情感,使人道主义理想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根基,以期达到人们共同改造生活与社会的目的。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1921年周作人却出现了信仰危机,他宣称自己是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至于危机的原因,周作人语焉不详,但危机的迹象相当明显,如从本年起,他对新村运动几乎只字不提,对他前两年信仰的人道主义社会—道德理想也不再热心宣传。
从《山中杂信》(1921.6.7~9.6)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思想在1921年前后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科学的怀疑精神与理性分析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强化了,这使他的“狂喜”的宗教式的体验很快便消失了,被跨越的现实条件又重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周作人开始意识到他原先所笃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新村主义)是有矛盾的。新村主义原本就不是一个纯粹单一的思想系统,它有多重的思想来源,而各种思想因素之间也不无矛盾,新村主义的结论不过是个折衷调和的结果。在1921年以前周作人赞同这种调和,而现在矛盾突出出来,不复调和,诚如他自己所说,这些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一》,载1921.6.7《晨报副刊》。)他虽然也在疑虑:“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一》,载1921.6.7《晨报副刊》。),但还是希望能把这些思想统一起来。可到了1921年9月6日在《山中杂信·六》中,他表示放弃统一的努力,对各种矛盾的“主义”,他“现在决心放任”,就让它们矛盾并存(注:仲密(周作人):《山中杂信·六》,载1921.9.6《晨报副刊》。)。这样作实际是把信仰问题暂且搁置起来,不再热心于“主义”的“布道”了。
“布道”暂告停歇,还有一层原因。此时周作人面对艰难时世,痛感自己力量太小,心理承受能力太弱。因此他说自己既不能跟着耶稣以身殉道;也不能去跟着摩西作以血与剑判决的士师。这表明他的信仰不能持久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没有实践的能力,缺乏直面现实、以身殉道的信念及勇气;同时社会群体的利益和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他觉得前者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个体生命的价值。看来周作人是想要放下改造社会、造福于人的担子。但他必须要有一个极圆通的理由给自己及给别人。
1921年7月30日周作人终于找到了理由,他在《胜业》中写道:“偶看《菩萨戒本经》,见他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都犯染污起”(注:子严(周作人):《胜业》,载1921.7.30《晨报·副刊》。),这正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者所必须做出的彻底而且决绝的承诺,即他们必须遵循严格的道德律令的要求,稍有所迟疑退缩便违犯了应遵信的信条。当然周作人虽然放下了社会改造的担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放弃了启蒙的思想,也不愿别人这样看。因为就像《菩萨戒本经》所说的那样,“自修胜业、不欲暂废”(注:子严(周作人):《胜业》,载1921.7.30《晨报·副刊》。)也属于正当的修行,他只是从渡人改为渡己。从佛教思想来看,自我拯救也是一个信徒的胜业,而且也是有功德的事。这样一来,周作人既找到了不再从事实际的宣传和社会改造活动的借口,又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据,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从此周作人停止了高谈阔论的宣传,放弃了对社会改造的承诺,只“自修胜业”。换言之,他先前所信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理想已被搁置起来,只剩下了个人主义。
“自修胜业”观念的提出为周作人改变处境打开了一个缺口,到1922年初他进一步作出了“切合自己实际”的明确抉择:1月22日他在《自己的园地》中表示不再相信什么乐天主义和理想主义了,只想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种自己的园地。对周作人来说,这个“自己的园地”就是文艺。“自己的园地”的口号的提出,意味着周作人文艺观的重大修正。前几年周作人坚信人道主义文艺观,而现在他认为无论是文学表现的内容还是文学活动的目的,都是以个人趣味、个性为中心的:从文学表现的内容上看,文学只要表现个人自身的情思,尊重个性,满足个人趣味就行了。虽然周作人还认为表现个人即表现人类,但后者在这里已被抽空了;从文学活动的目的来看,他既已放弃了社会改造的宣传与实践,那么文艺的目的也不再是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人生了。从这两点可以看出来周作人已由为社会、为他人而写作变为为自我而写作了。不仅如此,周作人还表达出对社会的强烈厌憎,并表示要在这极不完美的社会中,建立象牙之塔,追求个人的个性完善。
可以说“自己的园地”的提出既是一个艺术选择,也是一个人生选择,因为只种“自己的园地”就是“自修胜业”的具体化。换言之,周作人是把“自己的园地”作为自己整个人生态度与生活抉择的象征和隐喻的。
《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转变方向的一个信号,只是该文暗示的成分居多。而在《诗人席烈的百年忌》(1921.7.12)中周作人的态度就明显多了。他介绍了席烈(通译雪莱——论者注)的社会思想——“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其要旨是“主张性善,又信托理性与劝喻的力,所以竭力反对暴力,以无抵抗的感化为实现的手段。(注:仲密(周作人):《诗人席烈的百年忌》,载1922.7.18《晨报副镌》。)”周作人对此颇为重视,因为这种思想与新村主义是颇为相近的,两种“主义”都要求社会改造过程及其采取的手段完全道德化、理想化,共同基础是人的理性与人本性的良善。而在此文中周作人最终强调的是席烈“并不直接去作政治的运动,却把他的精力都注在文艺上面”(注:仲密(周作人):《诗人席烈的百年忌》,载1922.7.18《晨报副镌》。)。席烈说他自己的诗并不是作直接鼓吹改革之用,这与此时的周作人心有戚戚焉。为了说明席烈这种选择的原因,周作人专门翻译了席烈的《〈解放的普洛美透思〉序》的一节。席烈很清楚自己提倡的理想现在难以实现,因为现在条件不够,所以席烈说自己现在的工作“目的只在使……读者的精炼的想象略与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相接”(注:仲密(周作人):《诗人席烈的百年忌》,载1922.7.18《晨报副镌》。),即他强调这些美的理想在现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仅仅具有“道德的价值”。周作人在这一点上与席烈的认识相同,在同年7月17日所写的《送爱罗先珂君》中他表达了这种认识,这就是周作人对他所信仰过的人道主义理想及其实践反省的结论。
经过这样的反省,周作人为他搁置其先前的信仰找到了根据——虽然那些信仰是“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但由于它们缺乏现实的可行性,因而周作人遂把它们束之高阁,并拒绝在“自己的园地”中给它们保留特殊的位置。
在搁置了人道主义的社会—道德理想之后,周作人的“人学”观中也就只剩下基于自然本性的求生意志和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的求胜意志了。这二者大体相当于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说的人的灵肉两面,但事实上他已赋予灵肉一元观以新的内容。如果说以前的灵肉一元观是对基本人性的肯定,因而对于人类的所有个体都一视同仁,那么现在的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则是对少数优秀的个人的说法。周作人认为当时的国人既缺乏求生意志,更不具备求胜意志,而只有少数精神生活上优胜的“精神的贵族”(注:仲密(周作人):《文学的讨论》,载1922.2.8《晨报副镌》。)才具备求生意志与求胜意志。1922年2月19日周作人发表《贵族的与平民的》,明确提出基于自然人性的求生意志,而且特别地强调特出者的求胜意志,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他剧新灵肉一元观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进而为他从整体上修正自己的“人学”观提出基本范畴。
在周作人修正过的“人学”观中,自然人性论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周作人用求生意志这一概念涵盖了人的动物性存在方面的全部内容,又把属于自然人性论的自然主义道德观、文明观完全建立在求生意志之上。这实际上就是蔼理斯的“生活的艺术”观念的基本观点。蔼理斯在《性心理学》中把求生意志说成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核心事实,它是人类所有生命活动与生活的基础,而人类生命活动与生活的最终目的是使求生意志得到完全的实现,并且蔼理斯为人与动物共有的求生意志提供了生理学的基础。进一步他以生理学为基础,说明求生意志是由一组相对待的因素——抑制与发扬(或称作禁欲与纵欲)组成的,这两方面因素都是有机体生命中自然存在的成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求生意志最大程度的实现。而这种求生意志的实现靠的是抑制与发扬这两方面因素的调和与平衡。对于自然界的生命体来说,求生意志可以经由本能自然地达成,这些因素会自然地得到调和,可是对于人来说,他的求生意志的实现,必须经由他自觉、主动地采取各种手段,以自身的活动能力加诸生活、生命活动本身,调和各种因素使求生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蔼理斯看来,人的这种主动的调和行为是一种艺术行为,因为艺术是指人类所有积极能力的总和(这是古希腊的广义的艺术定义)。蔼理斯认为,人类道德活动的起源就是人对抑制与发扬两种因素主动的调和的艺术行为,他并把这种道德建立方式称作道德发生发展的正当之路,即“由本能造就的传统道路”(注:[英]霭理斯:《生命之舞》,第六章《道德的艺术》,徐钟钰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P.222页。),它是生活的艺术的结果,蔼理斯面对着现代社会压制求生意志的僵化的道德规范,希望重新恢复这种道德发生发展的道路,把道德彻底还原为艺术。对于蔼理斯的这种“生活的艺术”的观念,周作人在《读〈纺轮的故事〉》(1923.11.5)、《生活之艺术》(1924.2.14)、《蔼理斯的话》(1924.2)诸文中表示服膺。在蔼理斯的观念中,人类的各种活动本质上都是艺术行为,进一步说,作为人类各种活动集合的文明或文化也应该具有艺术的本质。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由蔼理斯建立,为周作人所服膺的道德观、文明观、文化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道德观、文明观、文化观。应该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自然人性论的具体内容都能被这种新的系统的自然人性论所统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作人重新修正过的自然人性论的中心目的是使求生意志得到完满,但同时周作人又认为仅仅满足人的求生意志是远远不够的,人除了需要满足有限平凡的存在之外,必须发展超越现代的精神——谋求无限超越的发展。对于周作人来说,发展超越性的精神,就是确立并发展基于个人主义立场上的求胜意志。周作人以前信仰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是超越性的精神,不过它是与自然人性论脱节的。周作人在此时已把“人间本位主义”排斥出自己精神世界之外,这样超越性的精神只剩下个人主义了。在这以前周作人信仰“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坚持兼顾利己与利人,个人与人类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对其中个人的精神世界发展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而现在既然社会改造的理想已不复存在,于是周作人就顺理成章地把目光转向个人主义的求胜意志,而其强调的重点则是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精神能力的发展。很长时间以来,周作人忽略了这一方面,而此时他始痛感自己精神世界的沙漠化,这使他对于发展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能力产生了强烈要求,从而提出了“仙人掌似的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路”(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的命题。“外粗厉”就是个人对于外部世界以及自己的外部生活不加以改造,容忍它们中有不合理成分的存在,因为周作人已经放弃了社会改造的实践,而且把社会改造的理想也排斥出了精神世界“自己的园地”,对于他来说,社会改造不复可能;“内腴润”则是指个人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充分发展自己的精神自由与能力。周作人认为这种生活是现在的中国应有的生活形态。这表明他对外部世界以及个人精神生活以外的外部生活并不抱完全的否定态度,承认它们在自己生活中占有一定位置,所以周作人说,自己虽然因为不改造现实而单纯发展个人精神世界,让人看起来“近于现在为世诟病的隐逸”(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但实际上自己并不是隐逸。而个人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是要有条件的,至少需要个人有时间来专务于此,但中国的现状正如周作人在《绿洲·小引》(1923.1.25)中所说的那样——个人所有的时间都已被外部生活所占据,因此个人要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就必须在外部生活占用的时间之外给予它独立的时间,使这段时间成为个人全部生活时间的一段,在这段时间内个人专门发展自己的精神自由与能力。这样做,个人全部生活时间就被划分为两段;一段是没有个人精神世界的外部生活占用的时间;另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完全是个人的精神世界,在这段时间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些都是在活动中得以实现的,所以可以说个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全部活动都贯彻着自由的精神,即个人是用自由的精神生活着的,这就使个人在这段时间内实际上构造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这样对于周作人来说,整个生活就被彻底分裂为两种生活:没有个人精神世界的外部生活与只有个人精神世界的发展纯粹的精神的生活。
周作人所要发展的纯粹的精神生活由自由的活动与审美的活动组成。自由的活动是与周作人在《绿洲·小引》中提到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承担的公共事务——劳动相对立的。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分析了作为自由活动的艺术与作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承担的公共事务——劳动的手工艺的本质区别:
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做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地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注:[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版,P.149页。)
这就是说,艺术是没有确定功利目的,不为外在确定目的服务的,它是本身就产生愉悦的自由活动,它能够达到所谓“合目的性而无目的”,所以说美感是自由活动必然的结果。近代西方许多思想家认为,在“古典时代”自由活动与劳动是达到过理想化的统一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康德、席勒与歌德比较早地提出过这一观念,而他们之所以对“古典时代”有这样高度理想化的描述,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感到物质文明以及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将会导致自由活动与劳动的严重对立,从而造成完整人性的分裂。可以说自由活动与劳动的对立成为近代西方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周作人是接受自由活动与劳动分裂的这种社会既定事实的,那么对于他来说,发展自由的活动,只能在彻底理想化的纯粹精神生活中进行了,实际情况确是如此。1923年1月25日周作人在《绿洲·小引》中讲到了自由活动,不过此处论述尚嫌简略,直到1925年6月22日他在《〈陀螺〉序》中对自由活动作了充分论述,从中可看出周作人对“日常的苦工”(注:周作人:《〈陀螺〉序》,载1925.6.22《语丝》第32期。)与真的工作之间区别的分析同康德对劳动——手工艺与自由活动——艺术之间区别的分析在内容上别无二致,所以可以说周作人所说的与苦工相对的真的工作确实就是自由活动。周作人在《〈陀螺〉序》中描述了自己的自由活动,又以儿童的游戏活动为例,具体展示了自由活动的情形,他并且表示在生活中追求玩——自由活动是自己生活唯一的道了。周作人又高度估价了自由活动能够使人达到的极高的精神境界,并把自由活动与精神层次较低的风雅划分开来,明确表示自己这些活动是自由活动。周作人在文中还说:“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此外还有日常的苦工”(注:周作人:《〈陀螺〉序》,载1925.6.22《语丝》第32期。),看来周作人在个人精神领域所做的种种积极的工作都属于自由的活动。在《〈陀螺〉序》中周作人用儿戏(Paidia)涵盖自由活动,进而把游戏与自由活动、艺术等同起来,这正是康德最早提出的一个命题。现代美学思想一般认为:自由是艺术的精髓,而游戏在客观形态与主观体验上,都与美和艺术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发生是与劳动及其他所有实际活动不同的,其特点即在于它是有自我目的的自由活动,在内心纯粹与快感相结合。在康德,席勒的认识中,游戏是与自由活动同义而与“强迫”对立的,至少在“自由”这一点上,游戏与艺术是相通的。周作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游戏”的。
周作人所要发展的纯粹精神生活还包括审美的生活,其中他主要强调了高级精神领域的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审美活动。什么是审美的生活呢?周作人首先在《玩具》(1923.3.29)中提出所谓“赏鉴家的态度”的命题,他表示要在发展纯粹的精神的生活中采取这种态度,其实周作人是把它作为使内面世界的生活变为审美的生活的关键。这种“赏鉴家的态度”是周作人在谈到他所说的“骨董家”时提到的,它就是赏鉴者通过审美观照寻求审美享乐,也就是审美的态度。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描绘了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首先是赏鉴者对待审美对象采取静观的态度,周作人说骨董家对待骨董的态度是“超越功利问题”、“爱那骨董本身,那不值钱,没有用,极平凡的东西”(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这就是审美静观所说的——自我完全超越对现实生活的一切关心和欲求,纯粹地归依和专心致志于对象。通过审美静观,然后赏鉴者经由审美判断,即“趣味的判断”(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最后获得审美的享乐,审美享乐是以“无关心性”为决定性因素的,周作人所描绘的审美活动的过程符合这一要求。“赏鉴家的态度”是适用于周作人在高级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两个领域的审美活动的,不过在《玩具》中周作人谈到的是前一个领域,而他在《玩具》中提到的“好事家”也是针对这一领域的,周作人说他所说的那种骨董家,“其所以与艺术家不同者,只在没有那样深厚的知识罢了”(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周作人举出一个日文词“好事家”来给这种骨董家归类,他用英语Dilettante来限定“好事家”的内涵,也就是没有多少专门知识的普通艺术爱好者,周作人说这么称呼并非不尊重,实际上他认为他所说的普通的“好事家”与真正的艺术家、审美家是一样的;周作人引述了法朗士的说话:“两者的原理正是一样的”(注:作人(周作人):《玩具》,载1923.3.29《晨报副镌》。),即使“好事家”与审美家、艺术家相同的,关键在于他们都具有审美的态度,而且“好事家”的审美的态度是完整的,与审美家、艺术家的别无二致。对于周作人来说,审美的态度才是核心的决定性的因素,他是用人们是否有这种态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而人们是否有深厚的知识则无关宏旨。进而言之,周作人提出“赏鉴家的态度”的命题,最终目的是要提倡人们在生活中普遍地采取这种态度,他之所以如此推重“好事家”,是因为普通人大多只能成为没有专门性知识的“好事家”(周作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而从他的立论上说,只要有了审美的态度,“好事家”就与艺术家、审美家一样了,而被人们用审美的态度来对待的那部分生活也就被提升到了艺术审美的高度,变成了审美的生活。
审美的生活还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审美活动,这种活动周作人在1924年3月18日发表的《北京的茶食》中首次谈到,在此文与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喝茶》中他对这种审美活动作了极为清晰的表述,连篇累牌地谈的只不过是审美的态度——通过审美观照寻求审美享乐。周作人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审美的态度。而这种审美活动针对的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界的内容(如夕阳、秋河、花、雨等等)和生活的内容(如香、酒、点心、茶等等),审美的对象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形式以及个人对这些内容产生的官感。
周作人认为个人在通过审美观照寻求审美享乐的同时,也要在审美活动中不断培养、发展自身的审美感受能力,使之趋向丰富精微,这是个人精神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而个人发展此能力,在日常生活领域,提供审美对象的物——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界的内容和生活的内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北京的茶食》中周作人说这些物“愈精炼愈好”(注:陶然(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载1924.3.18《晨报副镌》。),这里的精炼是一个衡量标准,用来衡量这些物提供的形式的精微与复杂的程度,以及这些物能够提供给审美主体的官感的丰富与细腻的程度,周作人所向往的“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注:陶然(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载1924.3.18《晨报副镌》。)正代表了这些物在形式与给人的官感两方面达到的极高精炼的程度。而要发展出这样精炼的审美对象必须要有历史与传统的积累:首先这些审美对象的发展要有历史的传统,周作人说过“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注:陶然(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载1924.3.18《晨报副镌》。),这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这些审美对象必须曾经充分与细致地发展过,周作人专门提到日本江户时代二百五十年的繁华,因为在长时期的繁华中,这些审美对象必定是会得到充分的发展的,并且会被逐步地精致化;尤其是在颓废时期,能够提供享乐的物在形式上与所能提供的官感上的精微程度是会被发展得淋漓尽致的,达到极端的精炼。而我们说发展出这样精炼的审美对象,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过程,周作人在《苦雨》(1924.7.17)中所说的某些自然界的事物“久成诗料”就是针对这一方面而言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发展纯粹精神的生活中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划分出了自己精神生活急待发展的不同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中规定了基本的范畴与自己急待发展的内容的基本范围。可以说在周作人新的“人学”观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的求胜意志中,个人内面生活单纯发展这部分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已得到完整提出。从这部分求胜意志的内容来看,他的纯粹的个人精神自由与能力的发展确实能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因为他发展它们是基于他个人精神世界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而且自由的与审美的活动都是灵肉一致的人在各方面活动的理想发展的结果。而与此同时,周作人在其精神世界中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抉择,他把一些有益于普遍的社会人生的观念排斥出了他的精神世界“自己的园地”。
1922年前后,在周作人把他的社会改造理想排斥出自己精神世界后,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不少有益于普遍的社会人生的成分,它们也是他的基于个人主义立场的求胜意志的一部分。其中一种观念认为文学具有独特的功用:文学具有独立的美,是人类精神的载体;而文学能够使人得到感染,可以沟通人与人的心灵;通过这一中介,文学可以达到它的目的——“发皇”国民的精神。另一种观念是确信启蒙者可以利用科学对群众进行思想上、道德上的启蒙。可是从1923年下半年始到1924年,周作人突然完全否定了这两种观念,原因是他的现实际遇使他不再相信支持这两种观念的前提——人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以及“教训有用论”。而这些信念是周作人在1922年初确立的精神世界“自己的园地”中包含的有益于普遍社会人生观念的主要成分。周作人明确表示“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自序》,载1923.8.1《晨报副镌》。),他把这些信念同他以前信仰的人道主义理想都归为“蔷薇色的梦”,认为它们全是理想主义的东西,他称它们为“单纯的信仰”(注:荆生(周作人):《一年的长进》,载1924.2.13《晨报副镌》。)或“固执的偏见”(注:荆生(周作人):《一年的长进》,载1924.2.13《晨报副镌》。)。既然这两种信念是虚幻的,那么周作人不但不能再继续信服它们,而且要把它们排斥出“自己的园地”。不但如此,进一步他要从根本上排除自己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信念,并且他要保证自己能够不再接受其他“单纯的信仰”,保证自己不再重犯某些不应犯的错误——他曾经确信过那种文学功用论与启蒙信念。在周作人看来,那些信念明显与“自己的园地”的抉择原则相悖,而自己之所以曾经确信它们,他认为症结在于他自己的思想有问题,所以进而他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原因。周作人的反省是从他对那些信念与以前的信仰的接受方式上开始的,他这样描述了他接受的过程:“在古今的贤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注:荆生(周作人):《一年的长进》,载1924.2.13《晨报副镌》。),很明显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对这些观念缺乏充分怀疑的审视,他认为这种无怀疑的接受显然是不可靠的,自己之所以犯盲目信仰的错误,其原因就在于自己还缺乏彻底的科学的态度。周作人认为必须提倡彻底的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园地”的纯粹。如果我们要解释周作人所说的科学的态度的含义,那么必须先说明他提出此命题的思想根据,周作人在《一年的长进》(1924.2.13)中说明了此问题:他说他每日看报,“总是心里胡里胡涂的,对于政治外交上种种的争执往往不能了解谁是谁非,因此觉得两边的话都是难怪,却又都有点靠不住”(注:荆生(周作人):《一年的长进》,载1924.2.13《晨报副镌》。)这种说法与早期怀疑派的基本原则——“任何一项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反命题与之对立,……根据这条原则,我们就能够避免独断”——(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毕洛主义概略》,转引自《古希腊哲学》,第四编《晚期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P.657页。)。是一致的。怀疑派反对独断论者的观点——武断他相信自己对于事物的认识以及自己的观念是唯一真实的,而别人的则是虚假的,针对这种观点,怀疑派提出:任一命题都有反命题与之对立,而正反命题都分别有自己说得通的道理,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独断地作出判断,而且对于相对立的正反两命题,我们实际上应该做到在这两者之间不置可否。周作人借用的正是这一原则。但是周作人并未接受怀疑主义的所有结论,他既没有否定人的理性与感觉的可靠,也没有像古代怀疑派那样对一切问题不作判断。周作人的怀疑观念至多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者认为我们无法认识现象的本质,但能够认识现象,而且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因而科学知识也是确实可信的。因此周作人借用此怀疑主义原则目的仅仅是用它来反对现在的“独断论”与“独断论者”。周作人认为,确信自己意见是绝对而且唯一正确的独断态度靠不住,因为每种意见都有相反见解,这说明正反命题都有可以信任和值得怀疑之处。因此周作人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人们要宽容地承认各种不同意见都有存在的必要,并在此前提下对各种意见都同样加以怀疑的分析审视,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排除虚假认识,获取真知;而与科学的态度相反,人们如果不顾任一命题都有相反命题这一客观事实而偏信正反命题中的任何一方,那么这就是“狂任者的态度”(注:启明(周作人):《济南道中之三》,载1924.6.20《晨报副镌》。),而攻击异端正是狂信的另一面,周作人认为二者都绝不可取。周作人以为一旦确立了科学的态度,就保证了其思想不会再掺入不切实的成分。周作人提倡的这种态度是以怀疑的精神分析审视各种观念,不过这种怀疑是有原则——客观的评判标准的,这就是科学的常识,即他在《瓜豆集·题记》(1936.12.10)中所说的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的常识——帮助人对自己有所了解的常识,他坦承这是他唯一的知识。很显然,它们都是他的自然人性论的实证科学的基础,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周作人对各种观念的评判过程,我们还会发现他评判的标准还包括:他的灵肉一元观,自然主义的道德观、文明观、文化观……因此可以说周作人是以他的整个的自然人性论作为他的科学的态度对各种观念评判的标准。所以周作人在确立他的科学的态度之后,他自己再确立的或接受的任何观念都一定要建立在他的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之上,而他在1922年确立的“自己的园地”中所包含的有益于普遍社会人生的观念是没有自然人性论的基础的,因此它们要被排斥出他的精神世界,而且遵循这种科学的态度,凡是缺乏自然人性论基础的理想主义的观念在周作人的精神世界中也都不再占有位置。这样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求胜意志中基本上只剩下单纯发展个人的精神自由与能力这部分了,它完全建立于他的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截止1924年,周作人新的“人学”观的理论建设已经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他从1921年开始的思想人生的重大转折大体完成,他的思想也从此基本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