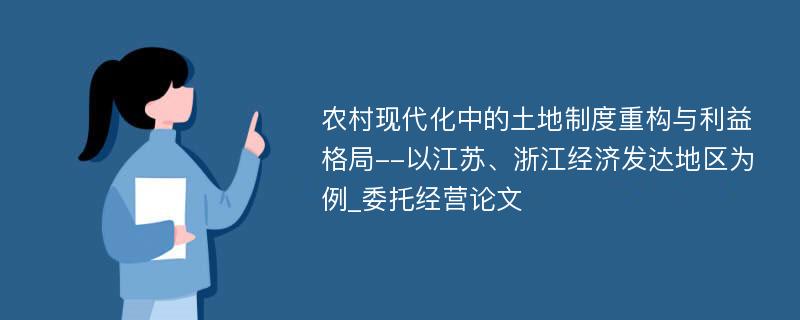
乡村现代化中土地制度及利益格局重构——对江苏、浙江发达地区的调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浙江论文,发达地区论文,乡村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两个率先”的催动下,苏、浙乡村工业化、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在加速推进,诱致农村土地制度再一次变革,农民土地利益格局也将面临新的调整。
一、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三大背景
1.苏、浙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迅猛发展,促成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加速转型,是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总根源。首先苏、浙在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成熟时期。两省人均国民生产值分别达到1.44和1.66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4.8%和78.8%;两省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降至10.5%和8.8%,工业产值份额分别为52.1%和51.2%,第三产业都达到40%左右;农村非农产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也都超过90%。其次大量农村劳动力拥挤在狭小的土地上搞饭吃的局面已打破,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准备了条件。到2002年底,苏、浙两省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45%和5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7%)12和22个百分点。以地市为单位:苏州市70%的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到非农领域;无锡市148万个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占70%;绍兴县64%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张家港市超过80%的农户和劳动力离开了土地。第三在苏南、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带等发达县域,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目标,“全面小康”的社会景象初露端倪。乡村工业已成为苏、浙农村经济的主体。两省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44.7%和42%。2002年,浙江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02亿元,年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农村工业企业共实现总产值5665.5亿元(注: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农调队农经处许勇军《浙江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规模企业产值是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1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占全部纯收入的71.2%。2002年:无锡市农民人均纯收入5850元,其中来自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收入占71%。张家港市农业产值份额降到4.2%,城镇人口(包含外来暂住城镇人口)接近70%(注:张家港全市城市常住人口37万人,外来暂住人口约95万人基本上被城镇和工业园区吸纳(比如唐桥镇,镇区常住人口8000人,而外来暂住人口却有40000人,整个镇区接近5万人的规模),这样计算城市化率为69.47%。),人均财政收入4421元,村均可支配收入84.85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700多元;义乌市三次产业比重为4.9∶51.1∶44,城市化率55%,人均国民生产值23181.55元,城乡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2741、5688元;绍兴县三次产业比重5.8∶64.5∶29.7,人均国民生产值32253元(3900美元),一些村庄的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居住条件、生活环境优于城市,成为市民向往的地方。这样的村在苏、浙发达县域已普遍的存在,华西村的星星之火,已成今日的燎原之势。
2.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迅速扩张,离农离土人口激增,引发了农地大规模的流转,为基层行政和自治组织重新配置土地资源提供了“历史契机”。首先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流转规模越大。到2002年末,江苏全省土地流转面积占农户承包面积12.5%。分地区看:盐城市土地流转面积53.49万亩,占农户承包面积的6.6%;南通市流转40.8万亩,占6.8%;苏州市土地流转面积95.2万亩,占30%;无锡市流转面积17.5万亩,占10.7%(注:数据分别来源于:作者实地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调查样本地区政府或主管部门关于土地流转的专题总结等。)。浙江省土地流转起步早,到2001年底,土地流转326万亩,占农户承包土地面积13.5%(注:新华网:《浙江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和思考》。)。2002年末,绍兴县土地流转17万亩,占农户承包面积的44.3%;义乌市土地流占承包面积31.8%。其次土地流转规模、农民土地权益实现程度与行政作为有密切关系。调查发现:经济发展和行政干预是土地流转的两大动力:前者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因此能够建立在农民自愿基础上;后者是地方政府在“两个率先”压力下急于求成的反映,是长期被压抑的土地资源配置权在新的机遇下空前释放。事实上,一些地方通过下指标、压任务强迫农民流转土地;一些地方派出“征地工作组”进村入户征用土地;一些地方冲破现行法律和政策限制,越过国家土地用途管制,使土地规模集中和大量流向非农用途,使农村土地纠纷和利益冲突凸现。
3.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政策导向,与为满足不断增长的非农用地需要而周期性调整农村土地关系之间的博弈,规定着未来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基本方向。我国自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一直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断给农民吃“定心丸”,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配置土地资源的欲望被长期压抑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农地大量转变为非农用途不可避免,调整土地关系确有需求。当长期被压抑的土地资源配置欲望可能被空前诱发后,必然受到坚持家庭经营制度和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制约。这种“调整”与“稳定”的博弈,使东部农村产生了大量“擦边球”土地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并不完全符合《土地承包法》,但却有它生存的社会条件。
二、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新趋势
1.土地流转趋向——形成在农内向种、养大户和“新三资”企业集中,在农外向“国家建设”、“工业园区和商业性开发”转移和被“乡村集体非农化利用”的三分天下。首先土地在农业内部流向三种主体: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非农村住户和股份合作社。江苏省流转土地中的58.8%进入本地种、养大户,11.5%由非农村住户经营(注:非农村住户经营的土地,包括工商资本、外来民间资本、外商资本(江苏称“新三资”)和城镇居民等经营的土地。),1%左右进入农业股份合作社,28.7%以其它形式流转、或转为非农用地,或作为建设储备地。浙江省有超过7%的土地进入工商企业,F县流转土地的67.2%由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受让和经营,剩余32.8%全部由非农村住户经营。其次农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建设、工业园区和商业性开发、乡(镇)村非农化利用。在转变用途农地总量中,政府征用(包括公益性、商业性、经济开发区用地)约占50%,乡(镇)村集体非农建设占30%,用于其它目的占15%,流转中“阴消”的土地约占5%(注:“阴消”是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土地丈量、台账、或者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的误差而减少的面积,意味着农民要承受“技术原因”导致的土地损益。)。发达地区村集体非农化用地占耕地减少总数的比例较大,Z县30%,D县33.9%。减少的农地按照用途划分,工业用地约占80%,公益性用地(如公路、学校等)占10%,其余为商业性(如商业住宅)用地。
2.土地流转形式多样,最终是由土地收益分配形式决定的;土地流转动机各异,行政推动大多是打着“规模经营”的旗号而达到重新配置土地资源之目的。土地流转形式有委托经营、转包、转让、互换、租赁、入股,其中委托经营、转包、转让的约占73%,土地入股方式最少,在发达地区也只1.2%左右。土地流转形式最终是由土地收益分配形式决定的。起初,在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土地流转到种粮大户大多都是“免费”的,有的还享受村里和地方政府的补贴。随着土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价值猛增、以及效益农业的发展,土地流转已从无偿向有偿转变,并且流转价格有快速增长的趋势。一般而言,委托经营价格每年约100元/亩,农户间转让、转包每年约50元/亩,入股土地收益最高,每年大约400元/亩,其它流转形式每年约60元/亩。我们发现,委托经营中村集体可以截留土地收益,其它流转形式不需要村集体作为中介;同时,股份合作制度机制极大限制了村集体在利益分配中的参与,这可能是“委托经营”大行其道而“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缓慢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土地流转的动因,主要不是通过市场调节解决人地矛盾。鼓励土地流转,实际上是鼓励用市场化手段配置土地资源,取代农民承包土地周期性行政调整,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动机各异,尤其是行政推动土地流转,其动机大多是打着发展“规模经营”的旗号而达到重新配置土地资源的目的。
3.“两田制”残留与“委托经营”变异。首先苏、浙的“两田制”缘起于计划体制下的粮食征购政策。苏、浙农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在“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下,每年都要化很大气力才能完成粮食定购任务。为减少征购粮食的行政成本,苏、浙普遍推行了“两田制”。农户只种“口粮田”,将“责任田”相对集中,由种粮大户生产和完成定购粮任务。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反对“两田制”,“种粮大户”的土地在账面上被均分给集体成员,而经营权却仍然留在种粮大户。2000年,苏、浙先后实行了粮食种植计划、定购任务、价格“三放开”,但“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土地的格局却保留下来。其次,委托经营及其变异“反租倒包”。承包农户将不愿意或无条件继续利用的土地委托给个人或者集体经济组织代耕代种,称“委托经营”。但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委托经营并不是代耕代种,而是在乡、村组织的干预下,农户将土地经营权委托给发包方,发包方给农户一定的经济补偿,然后将土地经营权保留在原“种田大户”或重新发包给“集体农场”、“龙头企业”。委托经营变异为现行法律、政策制止的“反租倒包”,或者说“两田制”以异化的形式存留下来。第三承包权股份化或“股田制”。承包权在账面上均分到户,经营权留给种田大户,土地流转收益按承包面积折算的股份分配,由此形成了承包权股份化的格局,有的叫“股田制”,也有的称之为“股票田”。“股田制”或“股票田”现象在苏、浙许多地区存在着,但它并没有演化发展为土地股份制,只是“不稼不穑”而凭借土地承包权参与土地收益分配的一种形式。
4.土地流转推动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东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致有3种类型:即满足建设用地和农业规模经营需求而发展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满足运营和管理村集体巨额资本需求而发展的社区股份合作社;满足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发展的行业协会或专业合作社。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特点:(1)农民自愿,有入社和退社自由;(2)入社动力不再是“政治倾向或意识形态”起作用,而主要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的经济利益;(3)产权清晰,不“归大堆”,承认并且保护个人产权及其收益;(4)股权结构、利益分配、决策和监管等方面逐渐恢复国际通行的合作社运作机制;(5)经济民主。应该指出,现实中有相当比例的土地或社区股份合作社,并不是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的只运营集体土地资本,有的只运营集体固定资产和货币资本……一句话,这些股份合作社不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只是将集体土地或其它资产的“成员权”股份化,作为收益分配的凭据,绝没有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合作。
5.集体成员无差别占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乃至文化传统正在悄悄发生改变。苏、浙已有大量农民开始“放弃”土地承包权,或者保留承包权的名义而将经营权以低价格、长期限转让,成为除宅基地以外,再也没有土地、也不再依靠土地获取收益和保障的农民。Z市5315个村民小组中,已有247个村民小组(占4.65%)35872人整体脱离了土地,连口粮田也没有留下。Z市D镇12个行政村,7500农户,1.8万农民。目前,全镇的9500亩耕地,由134个承包大户经营5000亩,7376个农户(占71.68%)只有4500亩“口粮田”,另外2000户(占26.7%)“两田”均无。C镇C村275户农民,其中45户(占16.4%)不要一分地。S县Q镇2.9万亩耕地,全镇14335个农户分配“口粮田”17000亩,剩余由130个种田大户(其中70%是外县农民)经营,说明该镇至少有1.4万个农户(占97.6%)没有“责任田”。苏、浙农村集体成员无差别地占有土地的制度和文化变迁,是以我国土地所有权法律体系和政府强有力的资源动员能力为背景的。它将直接影响中国农村未来土地制度变迁,区别于日本等国农民不愿放弃土地而制约规模经营的发展轨迹。
6.土地储备、信托、流转中心应运而生。苏、浙发达地区在乡镇和村一级普遍建立了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或者土地托管中心。苏州市已有40%的乡镇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并建立了流转土地储备库;绍兴、奉化等地成立了土地信托服务中心或土地流转中心。这类服务中心的主要作用是接受农户委托,将外出经商、打工或办企业的农户不愿耕种和无力耕种土地经营权集中,统一对外租赁或招商引资发展效益农业。这类机构,起到了“土地储备库”和“农民代理人”的作用。但这类组织大多为政府启动和主导,主要设置在乡镇农经站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因此带有明显的政府行政色彩,许多职能的履行必须依赖行政权力支撑。
三、乡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影响
如何评价东部农村社会转型诱致的土地制度及利益格局重构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影响?这是一个仍需要继续观察和研究的重大课题。有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必然大量改变农地利用方式和性质,由此而生的“稳定”和“调整”之间的激烈冲突,是人为的还是规律的反映?其二,农业社会转型,是否一定要改变家庭经营制度,牺牲农民土地权益;反过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否必然付出迟滞地方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两个问题还没有结论之前,要对现实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作准确的评价是困难的。
1.国家征用和乡村集体圈占是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两大主渠道。因为经济基础不同,目前,我国西部农村的土地纠纷,主要是“国家征地”引发的矛盾;而在东部农村,除国家征用外,乡(镇)村集体大量圈占土地亦成为侵占农民权益的“大户”。在农民看来:一是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搭上“便车”的商业性用地,只要是政府出面,集体产权和农户的使用物权不仅都无法屏蔽侵权,而且都没有谈判权。无论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还是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和规章、用地指标、批地权限等都不能阻挡农地大量被改变用途。原因在于“违法本是执法人”。在土地管理机构的参与下,土地规划可以“调整”,年度(建设)用地指标亦可购买,“土地整理”、“占补平衡”措施皆可“唯我所用”,凡政府动议征地无有不成。二是越到基层土地征用中的违规或违法行为越严重。我们看到:有的地方越过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利用“土地流转”或“股份经营”等外壳掩盖,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有的地方招商引资不惜牺牲农民承包土地权利;有的假借土地流转名义,乘机廉价“兼并”土地和“囤积”土地(注:调查显示:某市60%的村集体预留了“机动地”,其中10%左右的村集体预留“机动地”超过总耕地面积5%的规定;某县纳入村级土地储备库的土地4245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0.95%;某镇规定,中心村要预留停车场、餐饮、旅店、休闲等三产业发展和公共场所用地100亩;某村借“农田标准化”的机会,预留100亩作为集体发展用地。)。三是土地价值变化无常、不同的土地价格,搅动了农民“不患贫、而患不均”文化意识、心理失衡而造成纠纷。造成土地价格和土地市场混乱的因素有4个方面:根据土地产出确定补偿标准,因此,不同村社的土地价格有差异;各类经济成分的经济实力、土地供给稀缺程度都能影响土地价格;不同时间的征地价格不同;用地对象和出让方式不同土地价格有更大差异。大致上,商业性开发价格较高,国家公益性建设征地价格次之,乡村集体用地费用最少或者干脆没有补偿(注:Y县W村收回全村农户600亩承包地进行“农田标准化”建设,不论土地上是粮食作物还是果树,动员党员带头,一律不要青苗补偿。)。四是土地资源转移增值收益巨大,各家分食“唐僧肉”,独农民不能分享。如果以征地每亩3万元左右、出让每亩50万元—100万元计算,土地总价值的94%~97%不归农民所得。调查证实:无论土地以多高的价格出售,征地补偿4项(包括土地、劳动力、青苗、附着物)合计,一般在2.5万元左右,低的只1.2万元,最高约3.75万元;而征地报批手续费多达8项约4.5万元—5万元/亩;更多的土地增值作为“经营城市”收益当然用于城市发展。
2.“土地换社保”与“征地年薪制”同时实施,方能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土地换社保,主要是从土地出让的增殖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乡(镇)财政按比例配套一部分,共同作为社保基金;村集体补贴一部分资金和农民投保认购的部分进入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当失地农民分别达到55或60岁后,每月可以享受12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征地年薪制”是江苏昆山市的创造。2001年,该市出台了《关于调整征(使)用土地补偿办法的意见》,开始实行“征地年薪制”,即征(使)用集体土地,每年每亩按“责任田”300元、“自留地”600元、“口粮田”900元的基数发放到户,并且根据物价上涨指数每3年上调一次。按此标准,目前,全市兑现土地补偿金95.58亿元。该市还为农民办理了基本养老保险金。农民个人出资40%(低保对象出资10%),其余由市、镇两级财政用土地出让金补贴(注:按昆山市的规定,开发区和各镇工业用地出让金提取20%,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用地出让金提取30%,土地权属管理费提取90%。参见江苏《新华日报》2003年7月7日A版。),全部进入专户,用于农民养老金保险。男女村民年满60或55岁时,每月可以领取100元基本养老金,70岁以后可以领取130元/月。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要依靠它获得经济收益;土地还是农民抗御风险和养老的最后保障。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必须体现农民承包土地的双重功能。应该承认,苏、浙农村开始建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土地权益纠纷。但应该看到,土地换社保仅仅体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只有像昆山市那样,两项制度同时实施才能真正保障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
3.乡(镇)、村集体土地超过征用环节直接转为非农用途,使农地增殖收益留在了集体内部,农民承包土地有机会分享工业化的成果。有的地方不通过征地、也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由地方政府规划工业园区,出资进行水、电、路、电信、网络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集体出让农地使用权,然后招商引资、鼓励新老企业入园。企业租赁工业园区的土地,使用期限30或50年,按照每亩6—8万元的价格,缴给县或乡(镇)政府,再由县或乡(镇)财政按每年800元/亩的标准,支付给承包农户,农民获得了持续分享土地收益的权利。村集体参与土地开发有两种方式,比如苏南某村(开发了之00亩土地):其一,村集体平整好土地,完成基础建设,引企业来租赁土地、建厂房、安家落户,土地价格每年5000元/亩;其二,村集体在开发区内建设好标准厂房,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厂房一并租赁给企业,土地价格每年3000元/亩,厂房每年40—60元/平方米。目前村域内共有12家企业,1050多工人,2003年1—6月企业利润650万元,村域内的所有企业,要向村集体交销售收入3‰的管理费。该村集体土地、厂房租赁和企业管理费等收入每年可达200多万元。把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殖收益留在乡、村集体内部的做法,确实保障了农民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权益。但它绕开国家征用环节,使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了一级市场,与土地征用、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等现行法律和政策不协调。应该加快试点和法律修改工作,使农民集体土地进入一级市场合法化、规范化。
4.不间断地调整承包土地,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农地大量流转或被征用,激活了农村长期被压抑的调整承包土地的欲望,土地调整不可避免:其一,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地方第一轮土地承包并没有遵循集体成员公平占有集体土地的原则,第二轮承包又大多采取顺延承包方式,土地分配起点并不公平,为土地不断调整埋下了伏笔;其二,被“征用”或者大量转向非农和建设用地后,在现实利益面前,相当多的农民选择平均分配征地补偿、宁愿土地调整;其三,农田标准化建设或土地整理可能改变地貌而打破承包土地的边界;其四,在利益驱动下,乡村干部乘机调整土地或重新配置土地资源,从中谋取私利。可以认为,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农民土地权利并非“长期而稳定”,总是处在“短期而不稳定”状态。
5.旧村改造、乡村城镇化的过程,涉及农民宅基地和房产权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使用权人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它附着物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也是农民唯一的比城市居民优越的一项福利。按法律和现实农村的实际做法概括,农民宅基地权益如下:拥有户籍的农民有权以户单位、按一户一宅原则申请宅基地;除手续费外,农民宅基地免费;宅基地使用无期限,可以继承;农民对宅基地只享有使用权,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不能单独抵押,但宅基地使用权人可以单独就宅基地上的建筑物设定抵押;在实现抵押权而导致建筑物所有权发生转移时,抵押权人一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一些地方(如义乌市)农村宅基地可以置换城镇建房用地。
标签:委托经营论文; 土地流转论文; 农民论文;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论文; 农用地论文; 农村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用地面积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集体土地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