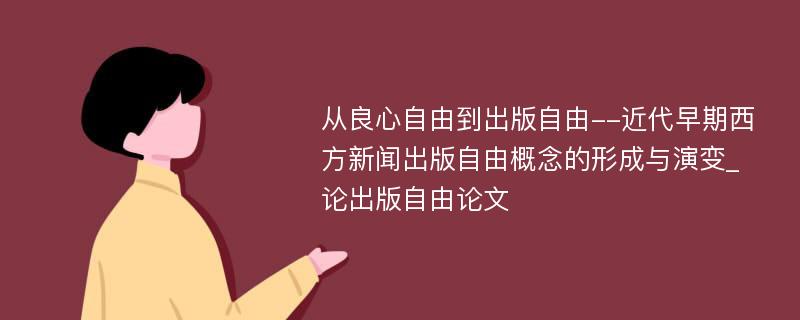
从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西方近代早期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形成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新闻出版论文,近代论文,良心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获得国会批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到:“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法案将信教自由置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前并非偶然,它不仅表明美国宪法起草先贤对前辈不朽功业的追慕(最早从英国进入北美大陆的都是反抗英国国教的清教徒),而且预示着,在他们的心目中,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乃是首要的,它们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奠基石。英国新闻出版自由观念的发展历史,也确实经历了一个从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的演变过程。
一、自由与秩序:新闻出版自由问题的由来
恰如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所言,对出版自由的控制由来已久。在古希腊,有关渎神、无神和诽谤的文字都曾遭到查禁或焚烧,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在一次演讲中因怀疑神的存在,其所著之书即遭遇焚烧。①公元325年,伟大的宗教异端者、希腊著名神学家阿里乌斯(Arius)的著作被尼西亚政务会判决焚毁。而早在公元494年,罗马教会就制定了一份禁书目录,13世纪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就曾被列入这份目录。②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出版权被教会牢牢控制,国家与社会对出版活动严厉的外在控制确实不多见,更没有成文的法律法令对此加以限制。例如,有研究者指出,“从大约公元6世纪,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本取代手抄本,书籍都是由抄写员依据一系列常规来复制的。这些抄写员身为修道士,在被称为抄写室(scriptoria)的修道院工场里工作”。③在这种情况下,敢于突破教会限制的手抄书极为少见。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1450年前后,德国美因茨的工匠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依照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wisohn Eisenstein)的说法,这不仅仅是一场“印刷革命”,它更是一场“传播革命”。④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沙泰尔(André Chastel)则将印刷术看作与照相术、磁盘存贮技术同样重要的信息技术革命。⑤伴随着这场传播革命而至的,是整个欧洲知识版图的巨大变化和社会秩序的重构。据迈克尔·克拉波姆(Michael Clapham)的研究,一位15世纪的意大利书商韦斯巴西亚诺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出版生涯时说,自印刷术出现后的50年中,“一共印行了800万册书,也许比君士坦丁皇帝于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全体欧洲抄书人完成的手抄书的总和还要多”。⑥而在法国书籍史专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眼中,1450-1500年间,印刷术的普及则更为广泛,印刷书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克拉波姆的估计。
事实是,截至1480年,西欧各地拥有印刷机的城镇超过110个,其中意大利大约占了50个,德国约30个,瑞士约5个,波西米亚2个,法国9个,荷兰8个,比利时5个,西班牙30个,波兰1个,英格兰4个。在15世纪结束之际,即印刷业肇始之后50年,欧洲人至少已完成35000个版本的印刷书,如将册数加总,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500万到2000万本;印刷铺的分布,全欧洲各地皆有。⑦
更令人瞩目的不仅仅是书籍的数量,当人们看到印刷书是一个很好的牟利途径时,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涉足于此。为了谋求更多的利润,小册子以及以往在抄写室中不可能出现的书籍,也络绎不绝地从印刷商的作坊中流向全国甚至欧洲各地。在1517-1520年短短三年间,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撰写的小册子就在科隆、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印刷中心印制了30万册。⑧在法国,人文学者、印刷业者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因撰写推崇无神论的拉丁文著作《拉丁语诠释》和印刷宣扬加尔文(Johannes Calvin)教义,于1546年被处以火刑。⑨一系列的印刷出版物引发教会和各国政府对印刷术的极大恐惧和仇视。
在教会及欧洲各国政府的统治阶层看来,印刷术的普及和印刷书的大量面世,对其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出版控制成为当务之急。1485年,德国美因茨的大主教发布命令,要求德国境内的所有通俗语译作必须获得特许方能出版;⑩恶名昭著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在去世前两年的1501年,颁布教皇诏书,确立了在美因茨、科隆、特雷沃和马格德堡等地的总主教府的“预防性审查方针”;1515年,继任的教皇利奥十世(Papa Leo Ⅹ)颁布了更为严格的教皇诏书,确立了所有图书在出版前必须经过教会当局的事前审查:“……在罗马或所有其他城市……如果未经事先检查,人们禁止出版或令他人出版书籍,无论是什么书……”(11)对书籍的宗教审查仅仅是一个开端,不久世俗政府也将此纳入管控范围。1528-1538年间,英王亨利八世(HenryⅧ)先后颁布多项措施,对印刷与出版给予限制,并最终设立特许制度,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经过事先特许方能出版。(12)现代意义上的禁书目录则是在教皇保罗四世(Paul Ⅳ)于1557年颁布的。在这份长长的书单上,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吉本(Edward Gibbon)、培根(Francis Bacon)、弥尔顿(Milton)、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科学史、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学人的著作均在禁止之列。(13)此后,一系列的出版控制措施在欧洲各国陆续推出。由此,围绕“控制还是自由”,欧洲各国教会、政府与思想先进的精英人物展开了激烈斗争,“出版自由”问题由此浮出水面。
二、出版自由的奠基:良心自由及其发端
在英国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Laski)看来,“清教主义的兴起有助于自由主义哲学的成长”,“宗教改革以间接的方式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支持”。(14)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也认为,良心自由乃是“所有自由中的首要先锋,因为它是人们得以避免邪恶的自由”。(15)拉斯基所谈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对后世自由主义的发展有奠基之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其首要的促进作用应该还是体现为其对阿克顿勋爵所谓之良心自由的激发上。
良心自由的出现,首先与宗教改革有关。在5-16世纪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教会与世俗王权紧密联合在一起,凭借对世俗政权的渗透,宗教权力获得极大扩张。14世纪初,罗马教廷在欧洲各地大量贩卖“赎罪券”,借此集聚了大量财富,而教会的种种腐败与丑闻也频频发生。在漫长的中世纪黑暗统治过程中,欧洲各国陆续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兴起了持续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前期的宗教改革家,如胡斯(Jan Hus)等人,多遭遇失败,个人也身遭不测。但是16世纪的两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恰如圭多·德·拉吉罗所指出的:“从起源上看,良心自由纯粹是新教的要求,它暗示着否认任何教士的权威高于个人的良心。”(16)正是针对教廷的赎罪券,路德于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其中提到:“教宗除赦宥凭自己的权力或根据教规所加之于人的刑罚以外,他无意也无权免除其他任何刑罚。”(17)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教廷发售“赎罪券”的合法性。与认为教宗根本没有权力给信徒刑罚相关。路德认为,信徒能否获得救赎,与教廷无关,并借此大力鼓吹信仰自由。在他看来,“信仰是一种没有限制的自由;任何力量也不能够强令人去信仰”,(18)当然包括教宗本人也不得强迫他人去信仰,而自由信仰的依据就是个人的良心。与路德相似,加尔文也认为,教会的真正首领应该是基督本人,而非教宗,在基督面前,教宗是和普通信众一样的信徒。信仰所依据的是基督的义旨和《圣经》,并不包括教宗在内的教士阶层阐发的教义。虽然路德和加尔文二人所阐述的个人平等与良心自由实际上仅仅是对教廷的斗争策略,不过是将教会的权威代之以圣书的权威,而这个圣书却又是根据“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的。(19)但二人思想中内含的个人自由、平等的观念,早已伴随宗教改革的开展而深入人心。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新教本身算不上非常宽容的宗教,但是新教运动的巨大意义在于信仰个人主义,并提出思想宽容这一论题,“为自由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余地”。(20)
良心自由的发展,与欧洲当时的世俗王权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15世纪时,教宗基雷西斯致信当时的拜占庭皇帝,指出统治世界的权力有两种,其一为教会的神圣权力,其二为世俗王权,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教会权力却高于世俗权力,这成为教会与国家不断冲突的根源。(21)而这一现象在16世纪以来的英格兰尤为突出。1527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因与西班牙籍的妻子离婚受到罗马教宗的反对,而筹划英国的宗教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英国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往来,确立了英国国教,国王本人成为英国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双重领袖。在对抗罗马教廷方面,英国政府与新教改革者的目标是一致的,由此也开启了英国容忍宗教自由的传统,特别是之后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女王(1558-1603年在位),更以开明的宗教态度著称。这就使得英国清教徒争取良心自由获得了保障。在良心自由的问题上,当时的清教徒组织剑桥弟兄会的思想有重要地位。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是剑桥弟兄会的一名清教徒,在他的眼中,“是上帝,而不是王室或者政府,赋予良心以自由”,“教会、政府和个人都有其自身的责任和权力范围,但任何一方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于其他任何一方,事实上,他们的权力都首先来自上帝……人是全然自由的,只有出于《圣经》的命令,才会服从它们……人的良心是全然自由的,不受国家管辖”。(22)帕金斯的良心自由观与路德和加尔文存在明显差异,后者在新教改革的过程中,或许是出于改革顺利推进的目的,或许他们本人思想中确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二人在倡导个人良心自由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言明教徒对世俗政府的服从,帕金斯则在论著中提出个人的良心自由也不应该受世俗政府的限制。
概言之,对个人而言,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虽然彼时看重的主要是良心自由,但是“良心自由被认为对人性至关重要,这暗示着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又加入所有涉及与其他个人关系的内容:表达与交流思想的自由,免除所有压迫的人身安全……”(23)二是提出了朴素的平等观念,当然这个平等主要限于宗教领域,对于世俗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平等尚未涉及。如果说都铎王朝的几位统治者,尤其是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出于各种原因,对宗教信仰采取了容忍政策,那么此后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对这样的政策则未能延续。而正是宽容政策的收紧,更进一步激化了新教信徒尤其是清教徒与政府的矛盾,进而加剧了反抗的力度,良心自由亦逐渐突破自身诉求范畴,向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迈进。约翰·弥尔顿正是这样一位从良心自由向出版自由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
三、神学视野中的出版自由观:约翰·弥尔顿及其《论出版自由》
约翰·弥尔顿出身清教家庭,但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清教徒。一般而言,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虽然反对教会对个人信仰的干涉,却依然服从于政府的管制。相比一般清教徒,弥尔顿的思想更显激进。当政府出于种种目的对个人的言论出版自由进行审查与控制的时候(1643年,议会颁布《出版管制法》,同年弥尔顿出版了论离婚的小册子,事前未经审查;第二年年初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第二次印刷,后遭投诉),弥尔顿奋起而争,于1644年发表《论出版自由》小册子,对书籍出版需经事前审查的制度给予猛烈抨击。
弥尔顿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论证大致如下:首先,对出版审查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弥尔顿认为,对一般书籍的事前审查没有先例,古代雅典,遭遇审查的文字只有两种类型,一为与渎神和无神论相关的文字,二为诽谤中伤的文字。除此之外,从未对其他类型文字进行审查。其次,出版审查的法案根本没有办法实施。即使严格执行审查制度,也不能起到效果,因为“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有办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24)而事实上,理性的智者是有判断能力的,邪恶的书籍恰恰更能够使他们明辨是非,帮助他们“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教会史上就曾经存在“以精通异端的书籍来反对异端”的先例。再次,严格的许可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学术自由和真理的实现。如果严格执行审查制度,就必须组建一个有效的审查机关,从事审查工作的检查员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学养。况且,很多书籍既包含了“有毒有害”的成分,同时还具有“有用而且绝妙”的内容,这就更需要更多的检查员给予删改。但是有学养的聪明之士是不屑于从事此项工作的。这就使得少数判断力和见识远不如作者的人充当审查者,这对于作者、书籍和学术的“尊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侮辱”,许可证的实施,“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们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它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25)因此,为了学术的发展、真理的实现,必须给予出版以自由。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具有浓重的神学色彩。在约翰·基恩看来,神学的出版自由观“以上帝赋予每个人理性为由,批评国家审查”,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与同时期亨利·伯顿(Henry Burton)的《独立教会之辩》、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的《自由良知》、威廉·沃尔温(William Walwyn)的《具有同情心的撒玛利亚人》都是出版自由神学论的代表论著。(26)上帝赋予每个人以理性,个体的人因此具有了认识事物、发现真理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言论的自由辩论,就能够催生真理。在《论出版自由》中,“真理”(truth)出现46次,上帝(God)出现34次,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出版(publish、published,7次)、印刷(6次,printing)和自由(liberty,7次;freedom,6次)。由此足以看出,弥尔顿所谓的真理虽然表面上看来自于理性的个体,而其本源则是上帝。在弥尔顿的眼中,“真理曾经随着圣主一度降临世界,其形态十分完美而灿烂夺目。”(27)恰如学者马凌所指出的,解读弥尔顿,不应将其与“自然神论者和理性教信奉者混为一谈,甚至不应将他的宗教观与略晚的约翰·洛克的宗教观相提并论——因为弥尔顿的激进的清教观念没有那种世俗的宽容色彩……应该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言论自由思想”。(28)
正是因为持有这种神学真理观,所以,出版自由在弥尔顿的整体思想观念中颇多矛盾之处。在《论出版自由》中,他一方面提出要放弃许可制和查禁制,让真理和谬误在战场上直接交手,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那些反对信仰和破坏风俗习惯的、不虔敬的和罪恶的事情”绝不能宽容,对于含有毒素和进行诽谤的书籍,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予查禁或者焚烧。换言之,弥尔顿的宗教宽容是有限度的,只有那些“教义或教派形式上的一些谐和的差异”,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差异”才在宽容之列,因为它们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却不妨碍“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其实,早在19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弥尔顿所谓“可以容忍的差异”建立之基础是弥尔顿的上帝(God)观念、人类天性及英格兰现状,而远远不是现代人所认可的自由价值。(29)与之相关,在宗教信仰上,触犯了禁忌的书籍和言论自然不在宽容之列。此外,弥尔顿一方面呼吁废止《出版管制法》,将出版(言论)的自由从被“少数人操纵”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极力声辩好书乃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心灵智慧,许多人的生命仅仅是土地的负担。这也再次表明他的出版(言论)自由依然是少数人的自由,而且是少数秉持上帝意志之人的自由。在论述自由如何获取时,弥尔顿提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30)这句话对于理解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非常重要,其关键之处在于他强调了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根本的自由,而言论自由的基础却是“良心自由”,有极强的宗教意味。因此,约翰·尼罗将《论出版自由》称作一部“唯信论作品”。(31)基于以上分析,当弗雷德里克·西伯特称赞《论出版自由》为“自由至上主义传统写下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庄严一笔”的时候,(32)其实是一个误会。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杰出思想家一样,弥尔顿的思想广而驳杂。除了在《论出版自由》中展示了其思想的复杂矛盾之外,像他的前辈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其所著《乌托邦》中倡导自由与宽容,担任大法官后却极力压制宗教信仰自由)一样,在担任克伦威尔政府拉丁秘书时执掌书刊检查,其行状与其早年的出版自由思想背道而驰。但是无论如何,通过《论出版自由》,弥尔顿表达了出版、言论自由的重要价值和检查制度的荒谬,虽然此书在当时未曾引起什么反响,却为一个世纪后新闻自由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之基。
四、出版(言论)自由的世俗化:霍布斯、洛克与斯宾诺莎
如果说,约翰·弥尔顿以神学为核心,论证了出版自由的合理性,那么与其大致同时代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开启了自由世俗化的先河,从而也为洛克和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言论自由观念提供了养料。
(一)霍布斯:社会契约、主权者与自由
一般而言,霍布斯往往被看做绝对主义思想家,在思想史上常常被看成专制主义的维护者。因此,在西伯特的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谱系中,根本没有霍布斯的踪影。中国学者在阐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时,将其看作从集权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虽然也看到了霍布斯思想的矛盾性,但依然侧重于分析体现其绝对主义思想的“主权决定论”。(33)其实,对于霍布斯而言,在其广泛而深邃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乃是其“社会契约”观念。藉由社会契约,霍布斯批判了宗教专制和君权神授,而论证过程中也体现了鲜明的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之中的人是自由而平等的,同时又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和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人们总是处于相互战争的状态。为了结束这种无序状态,使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就必须出让一部分个人权利,这种“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当人们把这种自我管理的权利授予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的时候,“伟大的利维坦”——国家诞生了。(34)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每一个人都有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外部障碍不存在的状态”。与自然权利相对应的是两条自然法则:第一条是通过寻求和平、信守和平保卫自己;第二条法则是人们之间自由权利的自愿的、对等的放弃。(3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霍布斯具有鲜明的无神论观念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论述臣民的自由时,提到外部障碍不仅适用于理性的造物(人类),也适用于无理性和无生命的造物,用以说明此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乃是一种“天赋的自由”,而作为享有此项自由的人类而言,这就是作为人类而自然拥有的天赋权利。
(二)洛克:社会契约、个体权利与自由
与霍布斯一样,洛克也是一位社会契约论者,但是其理论基础和最终目标却与霍布斯截然不同。与霍布斯相似,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中,“没有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享有管辖权,所以任何人在执行自然法的时候所能做的事情,人人都必须有权去做”,而且这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及处置其财产和人身,“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在遵循自然法的具有理性的人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36)但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有很大差异,前者是“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而后者是“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37)后者恰是霍布斯的观点。但是这种和平状态是不稳定的,为了维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个人需要放弃自然法的执行权,形成一种公民社会,进而组建议会制政府。这种类型的政府是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契约基础上成立的,契约的参与者既包括普通人,也包含国王、大臣。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财产、人身及其自由。与霍布斯的主权者不能反抗更不能推翻不同,洛克的政府论中,如果执政者实施暴政,侵害了个人的自然权利,那么,先前建立的契约则归于无效,人们有权推翻暴政。
如果说洛克在《政府论》(1689年出版)中的以上论述阐明了国家起源中的公民自由权利的话,那么在其次年出版的《人类理解论》中则探究了“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其中对于人类思想(言论)自由从认识论的角度给予了有力论证。洛克认为,人心初始如白纸一张,没有任何观念,也没有任何标记,人的“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也就是从经验中得来。在此基础上,洛克首先界定了思想的自由状态。他认为,自由的观念可谓分为思想和运动两种,“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能力,可以按照自己心理的选择和指导,来思想或不思想,来运动或不运动,则他可以说是自由的”,“离了思想、离了意欲、离了意志,就无所谓自由”。(38)其次,自由的人,总是依据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来决定自身的行动,只有思想自由的人,才称得上是自由的。“由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并不是对自由加了限制——这种情形不但不限制自由,减少自由,反而促进了它、加强了它,那不但缩小自由,而且自由底目的和功用还正在于此。”(39)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判断能力受到别人的支配,那就是不自由的。再次,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一种自然权利,不容侵犯。在洛克看来,“任何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这种权利就是“任意使各个字眼表示自己心中的观念”,(40)不能强迫别人表达与自己相同的观念。复次,思想自由的状态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洛克认为:“思想如不能传达,则社会便不能给人以安慰和利益,因此,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含有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他人。”(41)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在此提出了思想传播对于社会利益的促进。其实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多次论证知识、思想对于“幸福”、“善”、“至善”的价值和功效,这与其在《政府论》中言及政治权力的最终目标是“公众福利”的论点颇有相合之处。
(三)斯宾诺莎:“人人自由思想言说”
与洛克同年出生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是另一位“倡导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张人民应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42)的思想家。其思想与洛克多有契合之处,所著《神学政治论》早于洛克《人类理解论》(匿名出版于1670年)20年出版,而且斯宾诺莎将“人人自由思想言说”作为此书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详加阐述。可以说,相比洛克,在斯宾诺莎的分析中,有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论证更为突出、有力和清晰,但是可惜的是,中外主要论著在谈及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却鲜有提及他的,已有论著大概纷纷将英美思想家作为考察的重点,忽略了这位倡导言论、思想自由的荷兰思想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43)
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开篇即表明:“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容纳自由,不但于社会的治安没有妨害,而且,若无此自由,则敬神之心无由而兴,社会治安也不巩固”。他认为,人们尤其是统治阶层往往将神学和普通知识混为一谈,其结果是信仰“变为轻信和偏见的混合”。其巨大危害就是,“把人从有理性之物降为畜生的偏见,完全把判断真伪的能力闷死”,“处心积虑养成这种偏见是为扑灭理智的最后的一个火花”。(44)鉴于此,斯宾诺莎强烈建议将“神的启示”和“普通知识”完全分开,“二者各有其领域,哪个也不能说是哪个的附庸”,这样(信仰)自由即是一种个人的天赋之权利,“任何人不应别人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是他自己的自由权的监护人”。(45)在此基础上,斯宾诺莎推论出,自由思考判断的权利也是天赋的,是不能够转让给他人的,即使自愿,也是不能割弃的——“每个人的理解力是他自己的,脑子之不同有如上颚(思想之不同有如嗜好)。”(46)因此,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思想的主人”,即使是权力再大的君主和政府,也不能够限制个人判断和思考的自由:
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我们深信,最好的政府会容许哲理思辨的自由,正不亚于容许宗教信仰的自由。(47)
相反,如果一个政权违逆自由,严厉控制思想自由,这也是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与约翰·弥尔顿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强制言论一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越是设法削减言论的自由,人越是顽强地抵抗它们”。“即令自由可以禁绝,把人压制得除非有统治者的命令他们都不敢低声说一句话;这仍不能做到当局怎么想,人民也怎么想的地步”。(48)其实,斯宾诺莎心目中的言论自由是附有条件的,在其眼中,言论自由虽然不能不给予人民,但是却也不能无限地给予。享有这种自由的人应该是那些拥有理性的少数智者,而且即便是这些人,也应该将言论思想的自由与行动的自由严格区分开,如果藉由言论自由而诉诸行动反抗政府,这是绝不允许的。从斯宾诺莎这样的分析中,我们似乎能够隐约看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限定。
相比弥尔顿浓郁的神学观念,洛克的言论自由思想具有了世俗化的成分。但是恰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自然法原则并非洛克哲学-神学思想的最根本原则,在洛克思想中,依然有一个上帝存在。但是洛克的进步之处在于,他认为,虽然“自然法是上帝之法”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却“能够通过使用我们(人类)自然的理性力量而被我们所认识”。(49)而弥尔顿虽然也认为人类是有理性的,能够通过自由思想认识真理,但是他隐含的意思是:无论人类理性,还是所谓真理,追根溯源都是因为上帝的指引。以上不同恰恰是洛克比弥尔顿进步的地方,也是其自由思想能够为美、法诸国宪法制定者广泛认可的原因所在。相比而言,斯宾诺莎的言论自由思想更加彻底,也更具无神论色彩,虽然他的这一思想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五、结语
与贡斯当强调古代人的自由不同于现代人的自由不同,哈耶克(Hayek)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尤其是在雅典人那里,个体自由的观念已经存在。这些雅典思想家的自由理想通过罗马作家的作品传至近代,可以说为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50)其实在自由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于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言说者目的的殊异,对自由的理解可谓言人人殊。自由主义绝非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一家,除此之外尚有古典保守主义、现代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进步自由主义)等不同流派。(51)这种自由观念的歧异性与多变性对新闻自由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后者也呈现出复杂的意义。
在约翰·弥尔顿之前,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开启了异教徒争取信仰和思想自由的大门,虽然两次宗教改革因不够宽容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少。在此基础上,帕金斯等清教徒秉持更加宽容的思想,展开了向教廷和世俗王权争取良心自由的不懈努力。弥尔顿争取的仅仅是免于事前审查的自由,这项自由后来经英国大法官布莱克斯通的阐扬而被广泛认可。此外,弥尔顿的自由思想弥漫着浓烈的宗教神学色彩,他反王权而不反议会,强调真理甚于对自由的重视,同时他也缺乏对异教徒的足够宽容。此后,在霍布斯社会契约、自然权利思想的启发下,约翰·洛克、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等人对作为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的言论思想自由,作了深入分析,经历了从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的漫长思想演变过程,西方近代早期的新闻出版自由理念最终得以形成,并对后世的新闻出版自由观念及新闻出版实践活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注释:
①[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页。
②Jos.R.Long,“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Virginia Law Review,Vol.5,No.4,1918,pp.225-246.
③[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8页。
④[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⑤[法]让-皮埃尔·里马、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傅绍梅、钱林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⑥[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⑦[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178页。
⑧[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4页。
⑨[法]让-皮埃尔·里马、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傅绍梅、钱林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⑩[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
(11)[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
(12)方兰生:《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台湾: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6页。
(13)Jos.R.Long,“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Virginia Law Review,Vol.5,No.4,1918,pp.225-246.
(14)[英]哈罗德·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林冈、郑忠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3页。
(15)[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25页。
(16)[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7)[德]马丁·路德:《路德文集》(第1卷),雷雨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6页。
(18)[俄]梅列日可夫斯基:《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杨德友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53-254页。
(19)[英]J.B.伯里:《自由思想史》,宋桂煌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20)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2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65-466页。
(22)[美]约翰·范泰尔:《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张大军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5页。
(23)[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24)[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9页。
(25)[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8、38页。
(26)[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郤继红、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11页。
(27)[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38页。
(28)马凌:《阐释与语境:弥尔顿影响》,《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第35-42页。
(29)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Howe,1920, pp.28-30.
(30)[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5页。
(31)[美]约翰·尼罗、威廉·E.贝里、桑德拉·布拉曼:《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32)弗雷德里克·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33)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66-168页。
(34)[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0、132页。
(35)[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7-98页。
(36)[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5页。
(37)[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页。
(38)[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8页。
(39)[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8、233页。
(40)[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8、389页。
(41)[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8、386页。
(42)《神学政治论》出版说明,[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iv页。
(43)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斯宾诺莎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上的独特贡献,并对其思想作了简要评述。参见许正林:《西方表达自由观念的演变及其界碑》,载詹姆斯·密尔:《论出版自由》,吴小坤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此文为该书中文版代序。另见柯泽:《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新闻自由——从17世纪以来西方政治传播学历史文献的角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22-130页。
(44)[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2-13页。
(45)[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16页。
(46)[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0页。
(47)[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2、274页。
(48)[荷兰]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5页。
(49)[美]约翰·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杨通进、李丽丽、林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50)[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主义》,冯克利译,王焱等编:《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11-113页。
(51)毛寿龙:《自由高于一切——自由至上论述评》,王焱等编:《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2-54页。此外,展江在《传媒的四种理论》的导言中对此亦有细致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