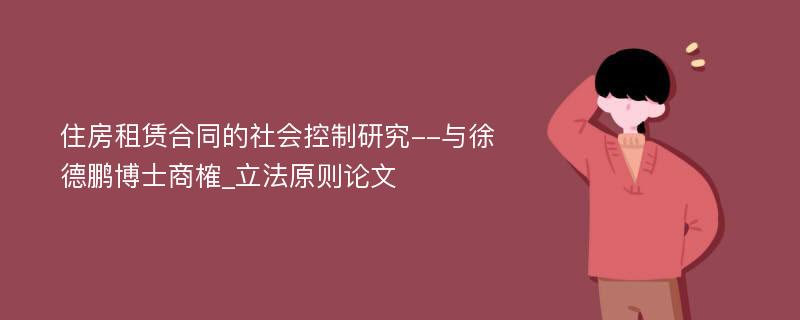
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研究——兼与许德风博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赁合同论文,住房论文,博士论文,社会论文,许德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第165页
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促进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第354页
许德风《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以下简称《控制》)一文提出:“住房是一项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为对私人之间住房交易进行规制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能性。就租赁合同社会控制的具体形式,该文首倡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同时认为对以租金管制为中心,配套以解除权限制、强制维修、防规避等规则,也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他还并进一步指出,就当下中国而言,适当进行一些“市场化”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即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是必要且可行的,未来若一些城市中的承租人比例急剧上升,适当进行租金管制亦是可选之项。①该文以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社会经济效果为立论基点,通过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比较考查和对中国住房租赁控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得出我国住房租赁控制必要和可行的结论,进而归纳了我国住房租赁控制制度五项要点和全文结论。该文是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住房租赁的原则规定和各地对住房租赁立法调整的情况下,为此项立法作出的基础性的理论解释,也是这方面极其稀少的文献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填补空白的文献。该文取成本收益分析这一法学文献少见的进路,广泛征引相关文献和调查结论,论证有力,资料充分且翔实。《控制》一文敏锐地捕捉到了住房租赁立法这一问题,认为合同法对此问题所坚持的合同自由原则立场,“在当前住房日益成为国计民生中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殊值探讨”。②
但笔者以为,对住房租赁合同进行控制的立场却是“殊值探讨”。
其一,“住房是必需品”,“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其他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是近乎永久存续的耐用品”,③“日益成为国计民生中重大问题”,也并不足以得出对住房租赁予以控制的结论,④因为有增加房屋供给、建设经适房和廉租房等措施可以保障基本人权(居住)——虽然《控制》一文也认为这不是租金管制的理由。⑤由此可以认为,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和特定情况下实施租金管制的住房租赁控制制度是预设可以“增进社会福利”的,⑥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租赁控制制度被广泛地采用”的问题。⑦而且租赁管制并不必然实现“基本人权”和解决这一“重大问题”,因为“从理论上看,在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情况下,长期限制租金水平会导致供给不足(出租房短缺)是非常确定的”,⑧“租金管制至多能限制租金,并不能提升住宅总量”,⑨显然善的初衷得到了恶的结果。
其二,《控制》一文在回答“为什么租赁控制制度被广泛地采用”的问题时,采取的是“从社会经济效果分析的角度”,使用的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论述租金管制上,就成本而言,该文针对反租金管制的文献进行了反驳,但假设的悖理性,致使结论难以成立。另外,租金管制“社会收益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租人的数量”的结论殊值商榷。⑩因为前文引用已说明,租金管制“不能提升住宅总量”确定会造成“出租房短缺”,那么就会造成越管制潜在租房人数量越大,有更多想租房的人租不到房子的悖论。在论述出租人解除权限制上,《控制》一文提出为节约交易成本,着重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有必要通过适当的规制结构加以辅助”,即法律“强行要求当事人签订长期租约”,这样“解约限制除了有保护专用性资产的效果外,还有稳定租赁关系的效果”,“最终节约缔约与解约成本,因而长期来看是有效率的”。(11)但《控制》也强调“住房租赁合同的交易成本很高”,原因之一就是“住房租赁合同是长期合同,而合同持续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大”,(12)于是出现了法律强行要求当事人签订交易成本很高的长期租约之悖论。另外,更重要的是,威廉姆森强调的是合同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而非规制(Regulation),认为新古典合同作为第三方治理的形式主要依赖于仲裁(Arbitration,不仅限于仲裁法上的仲裁,包含广泛的利益不相关第三方协助调解纠纷的方式)而不是诉讼,而且威廉姆森所关注并提倡的主要是双方治理结构和统一的结构(纵向一体化),而不是法律对合同的规制。(13)所以,《控制》一文利用威廉姆森的理论证成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正当性难言成立。
总之,《控制》一文以不适当的论证结构和论证方法得出了殊值探讨的结论,而且即便仅就结论本身而言,也是“殊值探讨”的。
本文采与《控制》一文完全相反的立场,认为若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住房租赁合同自由不可侵犯,任何方式的住房租赁合同控制都会与上述目标背道而驰。本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对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制度之租金管制进行针对性的评论;第二部分对住房租赁合同控制制度之解约限制进行针对性的评论;最后为本文结论。现今而言,《控制》一文已是一篇旧文,此时的评论已属滞后,但民法典及住房保障法的制定在即,所以住房租赁合同的理论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
一、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租金管制论
(一)纽约的租金管制
《控制》一文介绍了纽约的租金管制,但忽略了纽约租金管制立法背景、目的及相关规定。本文以为这些方面恰能反映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所以本文拟就纽约租金管制立法的背景等方面分析,证明纽约租金管制立法是因地、因时制宜的权宜之策,并不构成我们可资借鉴的范例。
“在美国,租金管制并不是普遍现象,纽约市是个例外。”(14)的确如此,租金管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全面价格管制的一部分,之后虽然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之一。即便如此,纽约的租金管制也是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选择。纽约1969年的《租金稳定法》(Rent Stabilization Law 1969)和1974年的《承租人紧急保护法》(Emergency Tenant Protection Act 1974)都是针对住房紧急情况制定的,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列有立法调查(Findings and Declaration of Emergency or Legislative Finding)章节,指出立法机关认为纽约持续存在大量人口的住房问题,住宅严重短缺,已构成严重的公共事件,这种情况使得政府干预租金防止投机性非正常的租金上涨成为必要,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规制将会威胁到公共健康、安全和总体福利,尤其是承租人紧急保护法明确规定了紧急情况是因战争、战争影响与敌对状态而生。但立法者并没有忘记为这一做法进行辩解,声称由规制向房东与房客自由协商正常市场的转变一直是政府和城市政策的目标,之所以规制只是应对紧急情况的不得已。
另外,“租金管制也不是永久性的”。(15)《租金稳定法》规定有效期到1991年4月1日,《承租人紧急保护法》的有效期到1997年6月15日。纽约市2003年6月19日通过了针对各种租赁法的修正案,(16)其三个改变包括:(1)限制政府在租金管制方面的立法权。(2)在法定租金超过2000美元时,准许放松对空置住宅的管制。(3)允许房屋所有人重建并把固定房客的租金提高到法定租金的最高水平。该修正案还规定了有效期至2011年6月15日。也许也不是因为租金管制的宪法争议,“为了谨慎起见,多数立法者还是选择了更稳妥的制度安排”。(17)
既然,“在美国,租金管制并不是普遍现象,纽约市是个例外”,“租金管制也不是永久性的”,而且“对于大部分受租金管制的房屋,租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8)那么,《控制》一文以这样例外、多变、临时生的案例来说明问题就显得牵强。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一文完全忽略了纽约租金控制的前提条件,对制度的介绍显得无所依凭。
(二)租金管制的社会经济效果
首先是“租金管制的可行性”。(19)
其一是张五常的表述为“(市场)出清:需求的数量等于供给的数量”,包括“以前发生在自由市场上的交易现在不再发生”和“合约各方再也找不到有价值的物品交易”,(20)而不是“即使在租金管制的情况下,房屋仍会和在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下一样得到有效配置”。(21)张五常一再强调的是价格管制造成的“租金耗散”——福利损失,包括“额外的小费”(22)和“排队”(23)带来的租金耗散。额外的小费可以为“钥匙费、押金或建筑费”,(24)或者为“鞋费”,确定存在且已引起立法部门的注意并在法律中进行了规定,(25)但“如果想租房的房客自愿花1000元从房主那里买一把破椅子,法庭也无能为力”。(26)这样,当然不仅这些因素,无效率自会出现。而《控制》一文认为“只要分配程序周全”加上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通常就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住租金而不导致张五常所描述的无效率后果”。(27)但法律是内在不完备的,其规定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而其会影响执法的有效性。(28)纵然法律很规定完备,《控制》一文认为成立的“租金管制的执行成本”(29)也会影响执法的有效性。
另外,《控制》一文“因此租金管制是可行的”论证曲解了所引文献的原意。(30)《控制》一文所引文献说的是:标准的租金控制图形分析表明其福利损失仅限于当且仅当对出租屋估价最高的人租到了受租金控制房屋的情形,其假设是通过排队、贿赂等非正式方式配置房屋建立了伪价格体系(Pseudo-price System),这种伪价格要承受它们带来的诸如搜寻成本(Search Costs)等无谓损失。但是在许多案例中,价格管制下的产品不是这么配置,而是在想得到它们的人之间有点或完全随机配置的。另外,价格管制吸引了那些不想以市场价格租房的新的房客。即租金控制意味着对房屋估价更高的房客被排除在外,而在市场价格之下租不到房子的租客却得到了出租屋。于是就产生了错误配置所致的损失。(31)所以《控制》一文所引文献指出,如果前一种损失是租金控制所致短缺带来的,那么后一种损失则可以认为是错误配置带来的,并且后者要大于前者。(32)
既然不能制定详细的低执行成本的房租管制法律,并且房租管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无谓损失,那么就难言“租金管制的可行性”,尽管这并不是租金管制不可行的全部的证据。
其次,供给不足与无谓损失。
《控制》一文认为非常确定的长期租金管制所致出租房供给不足“比较容易避免”。(33)理由之一是住房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不动产”,国家很容易通过不动产税等形式增加所有权人空置房屋的成本,促使其将房屋投放到租赁市场。《控制》一文在这里似乎混淆了概念。长期租金管制所致出租房短缺并非是有房不租,而是无房可租。长期情况下,房屋租赁市场的供需双方都是较为富有弹性的,“在供给一方,房东对低租金的反应是不建公寓,也不维修现有的公寓。在需求一方,低租金鼓励人们去找自己的公寓(而不是与父母同住,或与室友同住),而且也会导致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34)另外,征收不动产税并不必然提高出租屋供给,因为赋税最终要有人承担,所以相反会减少房屋供给从而提高房屋价格。而且“税收的安排是一个普遍性的转分配制度,法律无法确保将房屋所有人的利益直接转分配到特定地区有特定需求的承租人身上”,(35)所以房客除了无房可租外得不到什么好处。
事实正是如此。……纽约市的住房短缺非常严重,同时却有30万套以上的出租单元房长期闲置。几乎没有新的出租公寓正在建设中。……当大家正在为占据余下的几套空房而激烈竞争时,穷人一般早早出局,最后只好栖身于地下铁道或街道上。(36)
难怪张五常在文章的题头写道:“一项法律原本想要让长期租客有房可住,可结果却使一些租客露宿街头。”(37)
至于无谓损失,《控制》一文称“在不存在管制、租金过高的情况下,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得住房,国家需要以更大的成本来建设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这也是通过国家干涉补贴弱者,也会导致无谓损失”,(38)言外之意是租金控制的无谓损失要小于等于政府建设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的无谓损失,否则就应该实行租金控制。此处笔者不予论证,似乎也无须论证。因为当下政府正在积极建设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而并没有实施房租管制,出于经济学的考虑或其他什么考虑则在所不问。笔者认为,在不存在管制、租金过高的情况下,市场自会作出反应,因为供需法则客观地存在着并在长期发挥作用。所以“尝试提供中低价格的房屋是一个良好的公共目标。……即便目标是良好的,供求法则仍然不可忽视。”(39)
所以,房租控制下的房屋短缺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得到了证明,它的无谓损失也不可避免。
再次,租金管制与不当配置。
《控制》一文认为租金管制所致房屋不当配置的程度并不高,而且会降低部分群体的租金负担。(40)《控制》此处主要针对的是“结论也颇为可信”但“仍需谨慎对待”的一篇文献。
其一是文献的假设。文献以需求收入关系为基本考察点,(41)并认为在纽约住房与收入的相关度很高,(42)通过数据分析和推导得出纽约的房屋不当配置结论。与需求价格弹性一样,需求收入关系(弹性)也是经济学分析买方行为的基本工具。住房是正常物品,其需求量与收入同方向变动,利用需求收入关系研究住房配置自无不可。而且,就我国实证数据的分析也表明,个人或家庭是否有能力购买更大、质量更好的住房,与个人或家庭成员的收入正相关。(43)至于公平因素,法经济学以为,如果以公平观念为基础的评价并非单一地取决于法律规则对个人福利的影响,那么达到公平观念的要求会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糟,即社会福利减少,(44)这证明坚持任何公平观念,有时却意味着支持一种使每个人都变得更糟的体制,而且不管怎么对公平观念予以修正,这个问题也不可避免。(45)还有这也不是一种安排,而是经验分析。
其二是不动产市场中租金管制的效率问题。自由市场的假设并不回避现实存在的各种制度,正如经济学分析的局部均衡方法,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分析某个或某些变量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租金管制在各种市场规制制度中的作用直观且明显的,选取这一变量自有道理。对于房屋异质化程度高的问题,所引文献已经指出:“若出租屋是同质的,因为不想租的人租到了,那么配置不当的程度会很高,而当住房是异质的时,不当配置的程度会更高。如果人有很多类型且住房也有很多类型,租金控制就会扰乱不同住房的相对价格。”(46)
至于《控制》一文认为租金控制所致不当配置程度不高不足以重视的观点,因为不知道应引起重视的临界点,笔者暂且不置可否,在此将斯蒂格利茨所引的房租管制案例抄录如下:“在这种措施之下,自己或其家人久居当地者可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租到房子,而一个新来者如果想在曼哈顿租用一套带有一个卧室的公寓,月租金可能高达1500美元,而且未必找得到。……举例而言,该州参议院少数党的一个头头每月只要花费1800美元,就可以租用一套带有10个卧室、俯瞰著名的中央公园的公寓。一个负责审理房租管制案件的法官为带有两个卧室的公寓付出93美元的月租金,而在同一座大楼里,不带卧室的公寓的月租金已达到1200美元。前市长埃德·科赫居住的公寓位于格林尼治村,月租金350美元,而据塔克估计,如果没有房租管制,月租金至少需要1500美元。”(47)无论此处是否有腐败还是有别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房租管制导致了配置的明显不当。
最后,租金管制与劳动力市场效率。
此处,《控制》一文还是针对一篇文献进行的反驳。其所引文献认为,(因为租金低)老房客不愿意搬离租金管制下的公寓,所以他们很少接受其它城市的高薪职位,那么租金控制可能会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48)该文献同时引用5篇经验研究文献来论证租金控制使房客的租期较长并降低了房客的流动性。而且有学者利用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在丹麦,因为租金控制的存在,租期的灵活性明显降低,租赁控制对家庭迁移产生了非常不幸的影响并严重妨碍了住房市场的效率。(49)租赁控制和失业期间的经验研究还证明:租用租控住房越多的人越不愿意接受本地劳动市场外的工作,但更愿意接受本地劳动市场的职位,即愿意做不变更居住地的工作。(50)另外,《控制》一文假设“一国每个地方都存在租金管制,并且能保证租金水平相对于住房质量而言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和“租金因为没有控制而过高或租赁条件因为缺乏控制而很差或不稳定”,(51)就本文前部分的批评来看难言成立:因为租金管制是特定地区或特定时期的特别措施;面对异质性极强的住房市场决不会计划出合适租金水平;没有了租金控制,长期住房的供需较有弹性,自会到达均衡。那么,由假设推出的结论就殊值探讨了。
《控制》一文在“作为价格管制的租赁控制”标题下共列举了7项内容,认为成立的两项包括“租金管制的执行成本”和“不当分配所产生的不恰当激励”(但后者与其前文论述稍有出入),(52)第6、7项涉及“租金管制与税收补贴”和“住房租金管制的社会收益”,笔者于此略过,但并不说明笔者同意《控制》一文该部分的全部观点。
综上,已经表明,租金控制的必要性是不成立的,而且没有可行性。
(三)中国住房租赁控制的制度
1.历史与现状
《控制》一文在此部分论述了中国住房租赁控制制度的历史与现状,与其在“住房租赁制度的比较”部分一样,并未涉及特定时期施行住房租赁控制的特定背景,而且这部分的论述并不能为该文的结论提供支持。
关于中国住房租赁控制制度的历史,笔者遵循《控制》一文的断代,并以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53)(以下简称《考略》)一文为主要参考。《考略》首先提出了“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的背景”,(54)包括国际因素和直接诱因。前者为“为应对当时普遍出现的房荒,许多参战国家”“一战后的房租管制潮流与趋势”,后者为“主要城市的房荒问题”,可以看到立法背景都是“房荒”。《考略》接下来讨论了“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的历史嬗变”。(55)其一是“以解决房荒为目的房屋救济立法时期(1929-1936)”,立法例是1930年土地法,“但与当时西方的立法比较,土地法对房屋租赁问题的干预明显是有所保留的,一是没有授权政府在发生屋荒的时候采用强制空屋出租、防止住宅减少等比较极端的限制私权的措施;二是标准租金仅限于房荒时期适用”。《考略》总结道:“1929-1936年的房屋立法,主要是针对大城市出现的房荒问题而出台的,具有明显的临时性和过渡性的色彩。”
其二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全面房租管制时期(1937-1943)”。(56)“当时日寇的轰炸毁坏了大量的房屋,房屋数量大为减少。而大批难民由战区及战区附近移向后方,亟待收容。”“这迫使政府改变了对干预住宅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将解决房荒问题的重点转向了全面的房租管制。”立法例是1940年《非常时期重庆市房屋租赁暂行办法》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的1943年《战时房屋租赁条例》,前者只适用于重庆,后者“适用于全国,但限于战争期间,战事结束后6个月即失效”。可见,此时的房屋租赁控制法案也是应对房荒而制定的地方性或全国性和临时性的非常之举。
因为立法背景及立法意的相似性,其后的第三、第四时期略过,仅引述《考略》“民国时期房屋管制立法的成就与特点”节之部分评论来支持笔者的立场。(57)民国时期的法律对租金和房东终止契约权的限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对租金的控制限于房荒时期,而且有明确的标准。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对租金的干预限于必要的原则始终保持一贯,没有改变。”“所规定的房租管制措施均属于临时的救济措施,其适用的地域范围和时间都有限制。而且,在立法上对于战时立法与和平立法区分得相当清楚和严格。民法是永恒的,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均有效力。”“因为房屋租赁在本质上还是属于私权的范围,只有在出现必要的情况下,如前述的抗战爆发或住宅极度紧张(准备房租不足),公权力才可以且有责任干预(对私权加以限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房租管制从来不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手段,房租管制也不是住宅立法的全部内容。通过各种手段积极增加住宅供应始终被视为更为有效的治本之策。”“在民国时期有关住宅救济的立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积极增加住宅供应为内容的”。尽管笔者并不同意《考略》以住宅权的名义下房屋租赁合同控制的正当性主张,但前述的归纳和阐述足以廓清一些迷惑。
至于住房租赁控制的现状,《控制》一文其实已自我否定了:“当前对私有住房租赁合同不多的限制主要集中在治安、税收管理上。……实践中,对于治安和税收登记,无论出租人还是承租人都没有充分的动力,因此两项制度都很难执行。”(58)而且新中国成立后房租管制的立法效果也是事与愿违,“到1956年,租赁关系依旧混乱,二房东还普遍存在,一些大房主得过且过不修缮房屋,并且低价出卖房屋等。”(59)
2.中国住房租赁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控制》认为租金管制“社会收益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租人的数量”,(60)其“是否必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保护承租人的数量。只有在承租人的数量足够大时,对所有权施加限制才有充分的正当性。在这里,‘多数’还是‘少数’不再仅仅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的不同。”(61)《控制》并未界定“量”或“质”的边界或核心内容,也没有具体论证为什么“在承租人的数量足够大时,对所有权施加限制才有充分的正当性”,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在规模较大的城市,私有住房租赁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过度的租赁控制(租金管制)难言正当。”(62)另外,“住房问题的解决除租金管制以外还有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方式。……在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城市中居住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的住宅总量无法满足源源不断涌入城市的新增人口的居住需求。……因此,在商品住宅建设之外兴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也很必要,租金管制至多能限制租金,并不能提升住宅总量。”(63)另外,租金管制的有效运作的三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所以租金管制也没有可行性。(64)既无必要性,也无可行性,那么“未来若一些城市中的承租人比例急剧上升,适当进行租金管制亦是可选之项”(65)的结论是否可行呢?
《控制》一文中“住房租赁控制制度要点”部分大体略过,仅就“租金可负担”部分稍作论述。《控制》一文指出:租金“限制的具体值可以参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如将租金额控制在每户家庭总收入的30%左右。这一安排除了可确保租金可负担外,也可以‘过滤’富有的承租人,让真正需要租赁控制保护的人获得相应的福利。”(66)笔者的问题是:(1)30%的估算何来;(2)既然对租金设置了低于市场价格的上限,那么租金对任何人都是便宜的,怎么“过滤”富有的承租人;(3)若如前文所引理论预测和观察到的那样,富人租了便宜的房子,那么怎样让真正需要租赁控制保护的人获得相应的福利呢。
综上,转引曼昆引用的一位经济学家的话作为结束语:租金控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67)
二、住房租赁合同控制的解约限制论
(一)对《控制》中解约限制制度的针对性批评
《控制》一文认为限制出租人的解除权是“一种有效率的安排”,并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论证,(68)但笔者以为该论证“殊值探讨”。
其一是资产专用性问题。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中,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发生的频率是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而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69)威氏称:“交易之所以称为交易,最关键的条件就在于资产具有专用性。只有在支撑交换的双方各自投入的干系重大的专用资产的条件下,交换双方才能有效地进行互利的贸易。正是为了提高交易双方的相互适应能力,促进持久的合作,才使得对双方利益交叉问题所进行的协调工作成为经济价值的真正源泉。”(70)当事人签订效率式合同的目的就是节约交易成本,(71)而长期合同正是当事人在资产专用性条件下节省交易成本的合作与协调措施。(72)可见这与《控制》一文的阐述似有不同。
其二是“敲竹杠”问题。这其实是不完全合同问题,因为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洽约成本、合同环境的复杂性、不对称信息或证实成本等因素,合同总是不完全的。(73)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致使当事人担心被对方敲竹杠(Hold Up)而投资不足,(74)而不仅是“另一方可随时解除合同,这些投资便将失去保护”。
其三是住房租赁合同的交易成本问题。交易成本指达成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的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的监督等活动所需的成本。这一概念由科斯首先提出,他认为,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还包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以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75)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归结为事前与事后两大类。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签约、谈判、保障履约等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不适应成本、讨价还价成本、建构及运转成本和保证成本。(76)可见这与《控制》一文的阐述也似有不同。
至此,笔者以为,以解约限制来达到降低房屋租赁合同交易成本的思路偏离了要害,并不能实现其目的。不但如此,对房屋租赁合同进行解约限制也不会增进福利和改善承租人的境况。
(二)解约限制的经济效果
《控制》一文对房屋租赁合同控制的分析遵循保护承租人,当然也考虑了出租人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增进。但租金控制不能实现该文的目标,前文也已就解约限制进行了一点论述,表明《控制》一文在论证上或有瑕疵。在这部分,将讨论对住房租赁合同予以解约限制是否能实现保护承租人和增进福利的目标。
此处分析基于合同当事人签订了嵌入解除权的合同,或者是选择权合同(Option Contract)。(77)所谓选择权合同,“系指一种附属的有特权买卖某一标的物行为之约定,即在某一约定期间内,按某一价格,某人有专属权以买卖某物品”。(78)在这里,假设当事人并没有明确约定选择权,但我们仍可以构建一个嵌入选择权的合同,使得合同价格包含了选择权,即买方支付选择权价格(Option Price,用d表示)获得了以执行价格(Exercise Price,用x表示)购买合同标的物的选择权(Call Option),选择权价格与执行价格之和为合同价格P,则P=d+x。如果买方可以支付d而解除合同,那么d就是违约赔偿或终止权价格,那么合同价格里就嵌入了合同解除权价格。同时选择权价格d与执行价格x是逆相关的,d随x的上升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没有x上升的快,即x上涨1元d减少不足1元,反之则x随d的下降而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d下降的快,即d减少1元x上涨多于1元。(79)终止权价格体现了当事人对风险的分配。假设买方同意以18元购买卖方的东西,没有终止权约定,买方违约将赔偿18元。若卖方给出了解约权并要求执行价格为17元,而买方有可能对东西的估价少于17元,那么买方就会支付多于1元的价格购买解约权,这样解约的风险减少为1元。虽然价格将高于18元,也许是买方向卖方购买了保险。再假设卖方提供了免费的解除权,执行价格仍为18元。如果卖方同意执行价格降低到17元,那么买方同意以低于1元的价格购买解约权,则合同价格将低于18元。此时买方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了东西,而且若卖方再降低执行价格,买方会便宜更多。也即,无论买方对东西的估价如何,如果可以购买解约权,他或可规避风险或可获得低价格,某种情况下卖方也会转移部分风险。同理,如果卖方没有解约选择权就会提高价格自我保险。
住房租赁合同中的当事人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因为合同一旦签订将不可解约,当事人对租金波动的风险无法应对。如果当事人事前认为租金会上涨\下降,交易会以高于\低于市场价成交,那么高价伤害买方,低价伤害卖方;如果卖方预期租金上涨,买方预期租金下降,则无交易。只有卖方预期租金下降买方预期租金上涨时才会发生有效率的交易。而如果没有解约权限制,当事人会利用选择权价格来规避或分配风险,进而实现效率交易,所以解约权限制阻碍了效率交易的发生。
其实,解约限制,即使仅是出租人的解约限制,其效果与租金管制类似。因为不可解约,市场租金上涨时,老租客不搬出,新的出价高的租客被排除在外,此为资源配置不当,同时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要规避这样的风险,出租人会提高房价,租客会多付房租,同时不能支付高房租的人会被排除在外,“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政策初衷还是会导致有人露宿街头。因为出租房屋的预期收益面临不可预期的风险,潜在房屋租赁者将失去建房和修房的积极性,出租屋的供给会越发减少。因为不经出租人同意即可转租,房主将在次合同以及之后的合同中没有任何权利,所有权人的权利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方面的影响可想而知。
所以,按《控制》的立法建议,“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签订有期限的住房租赁合同”,“将不定期租约视为长期租约,除非具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除”等等,(80)将严重干扰当事人的租金预期,影响当事人的合同安排,阻滞出租屋资源的效率流转,加上“具体建立指导租金体系”——形成价格——的高昂成本,其福利损失不可低估。
综上,无论从保护承租人的角度,还是增进社会福利的角度,解约权限制都是不可取的。
契约自由,抑或契约自治,是与人身安全和财产保障相提并论的社会原则,是私法自治的基础。弗里德在《契约即允诺》中提到,休谟的人身安全、财产保障和契约责任作为文明社会的基石,是其所处时代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反映,已成为近代宪法和政治实践的前提,尤其是在私法的各个制度中得以展开并获得实质性的内容:财产法确定了合法财产的边界,侵权法保护我们免于受到越过边界的侵害,契约法认可并保证我们越过边界进行合作,那么“作为一种尊重个人安排的体制,契约法的自然结论就是自由主义的预设:个人拥有权利”。(81]哈耶克也有同样的观点,并提出对所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防止强制的基本条件,“而其他人的财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契约的可实行性或可执行性,由契约创建的整个权利网络,乃是我们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构想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基础,所以其重要性一如我们自己的财产”。(82)谢哲胜指出:“契约法用来规范各种自愿的交易,因为自愿的交易会产生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二者相加即是此次交易对社会产生的福祉,交易会产生福祉,因此鼓励交易,而在法制上以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手段,所以契约自由成为私法上一项重大原则。”(83)归结起来就是,“自治是以理想经济人假设出发,相信每个人会作出最有利于己的决定,而经由自由交易,有限资源可在最低成本下生产最大效益,整体的公共福祉也自然达成。国家扮演的角色,不是公共利益的界定者,也不是市场参与者,而只是单纯财产的界定者及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包括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争议,作出裁决。”(84)
私法自治虽自始至终是支撑现代民法的基础,但国家在私法关系的形成到消灭过程中,从来就不是旁观者,国家强制处处可见。(85)合同管制乃私法领域国家管制的表现之一,弃私法自治而施行国家管制,或从国家界定公共利益角度考虑,或从市场失灵考虑,其形式为国家参与市场而且干预人们的市场行为,(86)但合同自由与管制的争论从未停止,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合同管制逐渐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重视。正如有学者言,自由与管制处于交锋理论的两端,若将合同法不同的学说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其一端是契约自由,另一端则是社会干预,后者包括强制合同和格式合同,虽然社会干预日益强大,但私法自治的观念仍在大部分领域保留影响。(87)所以,尽管合同法社会化趋势不断加强,对合同的管制还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于此,谢哲胜提出,契约自治与管制应取得平衡,将契约自治仍作为契约法原则,管制则以必要为限,限于管制所促成的利益多于管制成本的情形。而且,他对“必要”反复予以解释和限定,称只有在契约自治的不完美处,即契约自治无法达到福祉最大,才有思考管制与否的空间。在契约自治的不完美处,不当然有必要管制,也不当然推论即等于有管制的必要,只有认定管制所带来的福祉高于管制的成本,才有管制的必要。(88)
对于房屋租赁合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足值肯定。任何形式的租赁控制都会减少出租屋的供给,产生不当配置,提高房客的负担,结果是市场上无房可租,低收入者欲租不能而街头露宿。对财产权的限制,并非不能,而是要在法律的基本原则下行事,出于价值可取技术可行而为之,应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经缜密的调查研究,采科学之方法。房屋租赁合同实与其他合同无异,以合同自由为原则,限制的必要在于非常情况,而不是动辄施行的办法。即使施行,也要遵循非常严苛的约束条件,(89)非常情况不再,即必取消。
合同法所追求的是促进合作与福利的秩序,合同自由是其中应有之义。正是利用合同,人类获得了自由,合同是最好的维护秩序的准则,也是自由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方式,而且,由于合同是部分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结果,融合了他们利己和利他的倾向,所以合同维护着社会自身的稳定,合同是社会和平的工具。(90)惟其如此,自由于合同而言,意味着秩序。
注释:
①许德风:《住房租赁合同的社会控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②③前引①,许德风文。
④《控制》按照这种逻辑得到了结论,但论证基础却是两种控制制度的成本收益比较。
⑤⑥⑦⑧⑨⑩(11)(12)前引①,许德风文。
(13)Oliver E.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2,No.2(Oct.,1979),pp.249-253。此文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三章。参见(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0-119页。威廉姆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理由就是“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他经济治理分析的代表作,全书的主线是治理,而不是规制。
(14)(15)前引①,许德风文。
(16)即《控制》第128页注2提到的“2003年《纽约市租赁法》”。
(17)(18)(19)前引①,许德风文。
(20)(21)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张卫东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64页。
(22)前引(20),张五常书,第175页。
(23)同上书,第180-183页。
(24)前引(20),张五常书,第271页。额外的小费或称为“贿赂”,而且加上贿赂之后的房租基本接近于均衡房租。参见[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斯蒂格利茨引用记者威廉塔克的调查案例时,也提到了这样的费用。参见[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小品和案例》,王则柯等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25)前引(20),张五常书,第197-198页。
(26)同上书,第194页。
(27)前引①,许德风文。
(28)[英]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上),汪辉敏译,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三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130页。
(29)(30)前引①,许德风文。
(31)Edward L.Glaeser and Erzo F.P.Luttmer,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3,No.4(Sep.,2003),pp.1030-1031.
(32)前引(31),Edward L.Glaeser and Erzo F.P.Luttmer文,p.1044.
(33)前引①,许德风文。
(34)前引(24),曼昆书,第101页。相同的证明和结论,也可参见[美]夏普、雷吉斯特、格里米斯:《社会问题经济学》,郭庆旺、应惟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35)前引①,许德风文。
(36)[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小品和案例》,王则柯等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7)前引(20),张五常书,第187页。
(38)前引①,许德风文。
(39)前引(36),斯蒂格利茨书,第21页。
(40)前引①,许德风文。
(41)前引(31),Edward L.Glaeser and Erzo F.P.Luttmer文,pp.1032-1041.
(42)前引(31),Edward L.Glaeser and Erzo F.P.Luttmer文,p.1038.
(43)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控制》对此文也有引用,见该文第137页注①。
(44)[美]路易斯·卡普洛、斯蒂文·沙维尔:《公平与福利》,冯玉军、涂永前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45)同上书,第59-60页。
(46)前引(31),Edward L.Glaeser and Erzo F.P.Luttmer文,p.1031.
(47)前引(36),斯蒂格利茨书,第20页。
(48)Kaushik Basu and Patrick M.Emerson,The Economics of Tenancy Rent Control,The Economic Journal,Vol.110,(October 2000),p.959.
(49)Jakob Roland Munch and Michael Svarer,Rent Control and Tenancy Duration,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52(2002),p.557.
(50)Michael Svarer,Michael Rosholma and Jakob Roland Munch,Rent Control and Unemployment Dur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2005),p.2179.
(51)(52)前引①,许德风文。
(53)(54)(55)张群:《民国时期房租管制立法考略——从住宅权的角度》,《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
(56)(57)前引(53),张群文。
(58)前引①,许德风文。
(59)前引(53),张群文。
(60)(61)(62)前引①,许德风文。
(63)前引①,许德风文。
(64)(65)(66)前引①,许德风文。
(67)前引(34),曼昆书,第100页。
(68)前引①,许德风文。
(69)[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8页。
(70)同上书,第48页。
(71)同上书,第90-93页。
(72)同上书,第40页。
(73)A.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eds.),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Volume 1.Elsevier B.V.North Holland,2007,pp.75-80.
(74)Sanford Grossman,Oliver 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4,No.4.(1986),p.717;and 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Econometrica,Vol.56,No.4,(Jul.,1988),p.776.简单的模型描述,参见杨瑞龙、聂辉华:《不完全契约理论: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75)[美]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7页。
(76)前引(69),威廉姆森书,第33-35页。
(77)论述思想及方法,参见Robert E.Scott and George G.Triantis,Embedded Options and the Case against Compensation in Contract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104,No.6(Oct.,2004),pp.1456-1476; Avery Wiener Katz,The Option Element in Contracting,Virginia Law Review,Vol.90,No.8(Dec.2004),pp.2205-2226。
(78)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79)前引(77),Robert E.Scott and George G.Triantis 文,pp.1456-1458; Avery Wiener Katz 文,p.2207.
(80)前引①,许德风文。《控制》所引大量调查研究表明,我国房屋租赁合同租期多在1年以下(该文138页注②),这是当事人的选择,其约束条件会有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等各种因素,凭此推断“多数人对租赁合同缺乏稳定预期”似有不妥。
(81)[美]弗里德:《契约即允诺》,郭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82)[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174页。
(83)谢哲胜:《契约自治与管制》,《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4)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85)前引(84),苏永钦书,第1-2页。
(86)同上书,第14页。
(87)[美]弗里德里奇·凯斯勒、格兰特·吉尔摩、安东尼·T·克鲁曼:《合同法:案例与材料》(上),屈广清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88)前引(83),谢哲胜文。
(89)谢哲胜:《房租管制法律比较法之探讨(二)》,载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1618,2010年3月8日。
(90)前引(87),弗里德里奇·凯斯勒等书,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