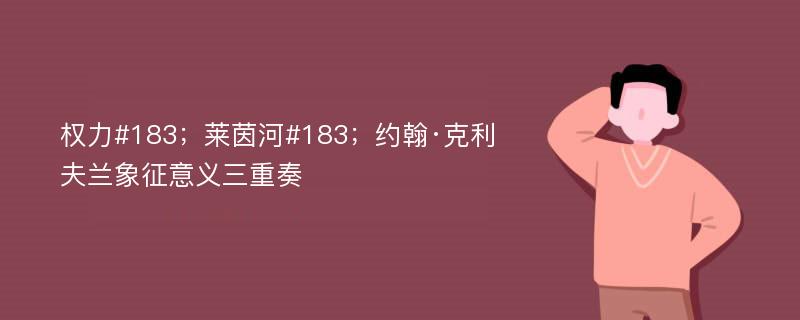
力#183;莱茵河#183;三重奏——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象征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莱茵河论文,约翰论文,意蕴论文,重奏论文,象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作品的思想往往不是直接暴露的,它要借助一个表现形式和手段,而象征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无疑是一部具有丰富思想底蕴与旺盛生命力的艺术巨著;人们对于它的反复而多方面的探讨,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但是,评论家们对它的象征意蕴的忽视不能不说是个明显的缺憾。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对于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的深入把握。为此,本文试从象征的角度,从“思想”与“形式”的契合点上,去领悟作家的思想脉络及其创作意图,以期在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与评价上,能有一个新的开掘与突破。
一、克拉夫脱:生命力的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译本,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本,始终将书名中的“约翰”和“克利斯朵夫”之间的连字符“—”误译成为分字符“·”。这就造成一种误解:复名“约翰—克利斯朵夫”往往被理解为姓克利斯朵夫名约翰。其实,主人公的真实姓氏是“克拉夫脱”。而这一姓氏,恰恰是我们理解小说思想、艺术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作为一个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其姓“克拉夫脱”(kraft)有着明确的德语含义:力。〔1〕显然,罗曼·罗兰以“克拉夫脱”作为主人公的姓氏,是有其深刻用意的。正如他所指出的:“每个生命的方式是自然界一种力的方式。”〔2〕而作为社会中的一股“力”,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又显然不同于芸芸众生,而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贝多芬式的英雄”。难怪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七初版序》中,作者就透露了他了创作伊始对作品主人公的面目的预测:“他必须是有相当高尚的灵魂才能有说话的权利,有相当雄壮的声音才能教人听他的话。我很耐性地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主角。 ”〔3〕“高尚的灵魂”、“雄壮的声音”,才足以吸引人,威摄人,才能率领凡夫俗子前进。这正是“英雄”的品性与价值所在;而“英雄”的根基与来源正在于他拥有了“力”、体现了“力”。
《约翰—克利斯朵夫》对生命力的讴歌乃是这部作品囊括一切的“母题”。它远远超出于“德法友谊”、“抨击世纪初文坛”等项“子题”。正是出于体现“母题”的考虑,作者时时处处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其姓氏所属的古老家族联系起来,并与人类赖以生存、休戚相关的大自然联系起来,从而体现出了某种神秘的色彩、某种浓郁的象征意味。小说多次通过老约翰——米希尔之口,提及“克拉夫脱家族”的某些传统的气质、性格、生活作风等等,似乎“克拉夫脱家族”的人天生有着祖辈相传的强健的生命力。同时,这强健的生命力的来源,则是在于“克拉夫脱家族”世世代代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所以罗兰使书中的主人公生为德国人,使他先天成为一种强者,力的代表”〔4〕。
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一个无拘无束的童年,那时,他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生命宛如一泓刚刚从地下渗出的泉水:清亮、晶莹、唱着欢快的歌,流淌着新鲜活泼的真性,充满了大自然所赋予的一般本能——原动力,具体表现为感受力、思维力、活动力、创造力,等等。在他的感觉里,似乎“一切都是美好”:墙上的糊纸给他讲着动人的故事,天花板上的光线为他欢快地舞蹈,莱茵河淙淙汩汩的水声、圣·马丁寺严肃迟缓的钟声,仿佛奇妙的音乐,宛若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但是,大自然中仿佛还存在着某种原动力的对立面,某种压抑和痛苦,所以他在母亲身边骚动不安,老是断断续续地悲啼,似乎这个小生命“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他怎么也静不下来”。在小约翰—克利斯朵夫内部原动力和压抑原动力的斗争,由此而带来的烦躁与痛苦,正在滋生。这就预示出了他的一生。
克拉夫脱家族所赋予他强劲的原始生命力,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迅速转化为对艺术、爱情和友谊的热烈追求。这是原动力的进一步迸发与激扬。力在他胸中冲撞奔突,扰乱了他整个灵魂:“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降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了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象树叶般发抖。”但是,原动力与其对立面的斗争还没有完全明朗化。
力,只有在征服世界遇到巨大阻力时才会得到最充分的显示。正是在这青春时期,他心中的原动力,迅速受到外来世界(现实世界)的严重挑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最为悲壮的是现在的自我和过去自我的冲突。”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幼年时代的崇拜偶象,正在等待时机,准备新的突破,酝酿有所创新。可是,卑琐庸俗的社会环境将他重重包围起来,时时处处使他感到压抑,感到窒息。然而,也正是在这重重“包围”之中,他心中的那股沸腾不息的原动力使他日夜不得安宁。他感觉到身体充满了摧毁旧世界的力量,血管里流淌着燃烧整个宇宙的烈火。他那颗陶醉的灵魂沸腾起来了,象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颗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挣扎着、活动着。
在经历了种种令人窒息的磨难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终于找到了生命之力的最好出路——创造:创造欢乐,创造精神,创造未来。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看来,“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光明灿烂的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他认为: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他坚信: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能消灭死亡,使生命之力永恒!
在这时,艺术(音乐)成为主人公追求的中心。因为艺术(音乐)是自然的模仿,是人的原动力的具体表现,而以艺术(音乐)为人生的第一醇素,充满着无限生机。年轻的天才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那蓬勃的朝气,饱满的活力,在音乐的殿堂中得到了最为充分、完美的体现与发挥。他的生命之力与音乐的生命之力产生了同频共振,发出了强烈而动人的和弦,奏出了最为美妙辉煌的乐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等到‘力’高歌胜利的时候才有资格得到艺术的桂冠!”
生命力的尽情发挥,也必然要触及与之相对立的丑恶现实。约翰—克利斯朵夫毫不容情地分析和解剖法兰西。谈到当时的巴黎乐坛时,他认为:“只有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又说,“那时的音乐家所缺少的是思想,是力;一切的天赋他们都齐备了——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力。”他同时认为“天才是要用生命力的强度来测量的,艺术这个残缺不全的工具也不过是想吸引生命罢了。”凡是涉及文坛、戏剧界的现状时,罗曼·罗兰所描写的都是一片毫无生机的颓废、腐朽;轻佻的僻习,金钱的臭味,笼罩着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豪华的表面,繁嚣的渲闹底下都能看到死神阴影的游移。然而,在对毫无生气的现实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之后,在苛刻的指摘和尖厉的嘲讽的后面,却潜伏着主人公巨大的创造热情。显而易见,破坏只是创造的准备。他创作了一大批杰出的乐曲,不断冲击着欧洲的艺术界。同时,他集中精力对德意志、法兰西两个民族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比较。在他心中怀藏着一个天真而伟大的方案:以德意志的强劲之力去拯救萎靡的法兰西。
经历了前期的力的搏斗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那股顽强、奔放的生命力扫荡了整个欧洲。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地演奏,整个欧洲为之震惊。但是,到了晚年,约翰—克利斯朵夫却变得平静下来,在他身上一切原始的、粗犷的力变得柔和起来。这是生命之力进入成熟期的标志,只有识透社会,识透人生,人才会变得淡泊宁静,真正归于和谐、融洽与平衡。在作者看来,这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也是人的生命力的归宿。
约翰—克利斯朵夫展现了由童年时代的和谐自由——青年时代的热烈奔放——晚年时期的清静恬适这样一个生命力的回归。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力的回归,而是经过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之后,通过血的战斗洗礼才最终到达平和、欢乐的境界,并取得了对自我、社会仍至宇宙的透彻认识。这是生命力的最高展现,也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展现。可见,罗兰以“克拉夫脱”作为主人公的姓氏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它象征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那股来自内心深处的反抗旧世界、捍卫自我尊严、追求真理与爱的强劲生命力。
二、莱茵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本体象征
这永恒的生命之力的律动犹如莱茵河——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莱茵河是全书的象征。所以在这部罗曼·罗兰看来“不是小说”的小说中,他充满深情地描写了莱茵河。莱茵河的形象,也就内在地与主人公的形象取得了联系。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形象,不仅象征着主人公刚毅、热情奔放、不屈不挠、富有反抗性的性格,而且衬托着主人公坎坷不平、曲折多变的人生历程。关于这一点,罗曼·罗兰在《卷七初版序》中明确表示:“我觉得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象一条河——这条河在某些地段似乎睡着了,只映出周围的田野跟天色。但它照旧在那里流动,变化;有时表面上的静止隐藏着一道湍急的激荡,猛烈的气势要以后遇到阻碍时才会显出来。等到这条河积累了长时期的力量,把两岸的思想吸收了以后,它将继续它的行程——向汪洋大海进发,向我们大家归宿的地方进发。”显然,在作家的心目中,这条河有着深邃的含意——它的绵延不断,它的时缓时急,它的忽明忽暗,它的平静与激扬,它的映照两岸的景色与天光……都与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和命运休戚相关。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古老的莱茵河奔流不息,江声如同伟大的母性之声,它孕育了古老坚强的日尔曼民族,如今它又在孕育着一位日尔曼民族英雄。终于在经历了温柔甜蜜、充满幻想而又颇多艰辛的十月怀胎之后,在阵痛和欣悦的呻吟声中,宣告了一个伟人的降生。莱茵河“水声宏大,它统驭万物,时而抚慰着他们的睡眠,连它自己也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时而狂嗅怒吼,好似一头噬人的疯兽。”然而,随着英雄的诞生,莱茵河也为之欢悦,感到慰藉:“它的咆哮静下来了,那才是无限温柔的细语,银铃的低鸣,清朗的钟声,儿童的欢笑,曼妙的清歌,回旋缭绕的音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是无忧无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莱茵河也仿佛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个不可思议的生物:“从来没有痛苦,只凭着它那股气魄恬然自得……穿过草原,佛着柳枝,在细小晶莹的石子与砂块上面流过,无愁无虑,无挂无碍,自由自在”。
莱茵河,这条伟大的母亲河给了主人公创造的灵感,是他音乐创作的永不衰竭的源泉。当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她时,约翰—克利斯朵夫仿佛也随着波涛一起流淌,美妙的乐曲油然而生:“到处都是花。啊,多美!空气多甜蜜!”“河流又往前去……景色变了……一些垂在水面上的树:齿形的叶子象小手般在水底下打回旋。林间有所村落倒映在河里。”“浩荡的绿波继续奔流,好象一整片的思想,没有波浪,没有皱痕,只闪出绿油油的光彩。”澎湃的水声,使他头晕眼花;汹涌的波涛节奏轻快又热烈,使他头脑中涌现无数美妙的音符,象葡萄藤沿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琴声,有凄凉哀愁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莱茵河,就是主人公的灵魂,就是主人公力量的源泉。
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曾一度徬徨迷惘,消极低沉, 几乎自己糟蹋自己。这时的莱茵河隐灭了,两岸的风景也在他心中隐灭了:“只有一片柔和的,暮霭苍茫的气氛在那里浮动。”恰如莱茵河也有枯水的季节,也有蜿蜒曲折的河床,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也充满了坎坷,充满了苦痛;有过逆境,也有过消沉,但是他心中的原动力没有消亡,美好的素质没有消亡,“理想”之光始终在他眼前“浮动”(尽管“柔和”、渺茫),指引着他、也鼓舞着他走出困境,继续前进。
犹如越过崇山峻岭的大江大河,总有一天会来到宽阔无限的平原地带,由湍急变得平缓,势必越来越宽广。在经历了沧桑巨变、岁月磨难和艰苦奋斗之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心境逐渐趋于平静。也许是经历了长期的跋涉,他需要安静的休息;也许是识透了复杂的人生,他的心胸反倒变得更为宽阔。他以仁爱之心看待世界、拥抱世界。他看清了生命的短暂,体验到了生活的美好和谐。正如他对人生的自我总括那样:“只有一场轻飘的梦,一阕清朗的音乐,在阳光中浮动”。“一个人渐渐的离开人生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明白了,好比离开一幅美丽的画的时候,凡是近处看来是互相冲突的色彩都化成了一片和谐。”在弥留之际,他最后一次看到盈溢溢的莱茵河在田野中泛滥:多么庄严、多么迟缓地流着,简直象是静止不动似的。人生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成就;关键在于执着地追求,向着一个崇高的目标。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书中对于莱茵河奔向大海的描绘是颇为壮观的:“在遥远的天边,象一道钢铁的闪光,有一股银色的巨流在阳光底下粼粼的波动”,那就是大海;河流向着大海狂奔而去!转瞬之间,“潺潺的河水,汹涌的海洋”,融为一个整体!大海是一切河流的母亲,她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她的万千儿女,使它们在这里永不枯竭;同样,归于大海的莱茵河,也使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获得了永恒与新生。作者的描绘是富于深意的:在茫茫无际的海面上,只有音乐的声音在回旋荡漾,舞曲的美妙节奏疯狂般地突现出来;一切都卷入到所向无敌的漩涡中去……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颗自由的灵魂神游太空,“有如为空气所陶醉的飞燕,尖声呼叫着翱翔天际……欢乐啊!欢乐啊!……哦!那才是无穷的幸福!”
伟大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如同莱茵河一般,源于大海,终又归于大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爱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莱茵河把真理与爱这两股“奔腾的流水,合并在一条河床里,爱与真理的合流。”
三、欧洲“三重奏”:人类和谐精神的整体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有三个主要人物,这便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奥里维和葛拉齐亚。而罗兰关于德国的“力”、法国的“理性”和意大利的“美”结合一体的人道主义“三重奏”,就是在他们的交往中,得到深刻而集中的体现的。
众所周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原型是贝多芬。的确,最初两卷(卷一·黎明、卷二·清晨)是按照这位伟大音乐家的传记材料写的,描述了伟大音乐家的幼年和童年生活。然而作品从卷三起,情况就有所变异,且愈加清楚地表明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融进了莫扎特、格鲁克、亨德尔、瓦格纳、沃尔夫等杰出音乐家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贝多芬不过是其中的主旋律。罗曼·罗兰认为生命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生活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同静止作斗争;是创作,是创造,是对旧世界的吸引力、束缚力的永恒反抗。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位天才,而天才是新事物的报信人。所以他的斗争的英勇和伟大,是要取得完美的生命,不断簇新的永恒生命力。
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说,谁阻碍了他的去路,谁就是一种鼓舞、养料和知识。阻力越大,生命力越旺盛,反抗性越强烈,从而经验愈丰富,成就愈突出。约翰—克利斯朵夫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从小就养成仇视专制暴政和市侩习气的意识。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无论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公爵的权威以及小公国市侩的保守主义的铜墙铁壁,也无论是麇集在法国文坛上的腐败文人的强大集团,他都敢于向他们挑战。他的个人奋斗的气质是天赋的,斗争是他生命的源泉。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他都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始终不渝。他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强悍有力和狂放不羁。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来说,阻力与其说是一种痛苦,不如说是一种欢乐。
罗曼·罗兰在小说中还安排一个法国人来同这个德国人相对照,他就是奥里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是相互补充的,他们不由自主地相互吸引着,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都是最高尚的人。奥里维是法国精神文明的代表,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德国强有力的象征。他们两人都是生来就要攀登世界最高峰的理想人物。两人一个严峻,一个温柔,就象长调和短调那样和谐一致,在奇异的变调中体现了艺术和生活的主题。奥里维似乎是为了逃避现实而奔向艺术,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自愿献身艺术。这位德国人是一个朴素的天才,这位法国人却是一位观察家、思想家。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改造整个世界,而奥里维改造的是他自己。奥里维不属于暴力者的队伍,而归于理性者的行列。没有一个失败能够使他恐惧,没有一个胜利能够使他信服。他太理智了,理智得近乎愚钝和麻木。他不愿斗争,逃避斗争,不是因为害怕失败,而是由于对胜利漠然视之。总之,奥里维反映了罗曼·罗兰当时那种反对一切暴力的思想,体现了罗兰书生气的、天真的泛爱主义精神。
约翰—克利斯朵夫很快理解到,奥里维思想上的英雄主义,决不逊色于他实践中的英雄主义,奥里维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也决不逊色于他自发的反抗精神。约翰—克利斯朵夫透过奥里维体态表面的虚弱,看到了一颗坚如铁石的灵魂。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推毁奥里维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搅乱他清醒的头脑。作为纯洁无私的理性代表,奥里维帮助约翰—克利斯朵夫接近平民,完成艺术观的转变。他们之间的友谊表现了人类的精神共鸣和情感价值。“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这熨贴的诗一般的句子,正是罗曼·罗兰给“友谊”写下的最严格的定义。
然而,在小说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主人公,她就是意大利女郎葛拉齐亚。假如这部小说缺少了她,那么《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支雄伟的乐曲便是不完整的、不和谐的。这是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分别代表着两极,中间缺乏借以衔接的桥梁。约翰—克利斯朵夫象征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奥里维则象征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前者带有非理性和自发的盲目性,后者则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第三种形式——葛拉齐亚,才能把这割裂的两极连接起来。因为葛拉齐亚是一种创造性现实。欧洲的“三重奏”从来没有以如此高雅的象征性乐曲演出过。这三种象征就是:
德意志的狂放不羁,强悍有力;
法兰西的自由清新,先进思维;
意大利的和谐柔美,现实精神。
葛拉齐亚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最亲密的女友,她是美的理想的体现。虽然他俩历经人生坎坷,忍受着揪心的磨难,爱而不婚,但“两颗相爱的心灵自有一种神秘的交流: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最优秀的部分,为的是要用自己的爱把这个部分加以培养,再把得之对方的还给对方。”“从葛拉齐亚的心中再去领会自己的音乐,等于和这颗心结合了,把它占有了。这种神秘的交流又产生新的音乐,有如他们交融之后的果实。”尽管后来葛拉齐亚先他而逝,但是他们之间这种心心相印的真挚感情,却一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隐居后的精神支柱。
在这里,罗曼·罗兰蕴含着极为深刻的象征,即想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诚友谊来象征欧洲各民族的团结,用自由、平等、博爱的审美理想去振兴法兰西和欧洲,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愿望。作家和他同时代人的深刻区别,就是在时代已经抛弃这种理想的时候,仍然忠于自己的理想,依然保持欧洲各民族亲如兄弟的信仰。小说中象征性地表达了罗曼·罗兰对欧洲即将爆发战争的担忧。从他儿童时代起,法兰西、德意志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阴影始终没有消除,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罗曼·罗兰在作品结尾时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痛苦地认识到这一代不知战争为何物的人希望战争。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他束手无策,不知如何防范。于是,他天真地想用这种欧洲大团结的精神来消除民族间的仇恨,来抵挡帝国主义分子的枪弹。显然这是行不通的。然而却反映出了罗曼·罗兰追求人类和谐的博爱心胸。
由此可见,在主要人物配置上,罗兰亦赋予它深刻的哲理和美学的象征意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力的象征,而奥里维和葛拉齐亚则分别象征着法国的理想主义和意大利的艺术美,这三者的交融汇聚,便构成为一个充满生气、和谐美好的人道主义理想世界。这是作者所追求的理想,他以鲜明的艺术形式将它体现了出来。
总之,小说运用深刻的象征涵概了整部作品丰富的思想主题,来自家族的传统气质使约翰—克利斯朵夫天生是位强有力的人,是力的代表。而孕育他、哺养他的莱茵河又默默伴随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莱茵河无时不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中潜流。他一生渴望友谊和爱情,而奥里维和葛拉齐亚正使他获得了看似短暂实则永恒的感情,成为他生存的精神支柱、创作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切,象征性地表达了力、理性、美的和谐统一,集中体现了罗曼·罗兰那颗自由、平等、博爱之心,辩证地阐明了理想与现实结合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约翰—克利斯朵夫》才超越时空,震憾世界,并以它特有的激越旋律,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海里掀起了狂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注释:
〔1〕李清安:《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 见《读书》1989年第2期。
〔2〕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七初版序》, 见《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三册, 103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不再一一注明。
〔3〕傅雷:《译者弁言》,见《傅雷译文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八卷,8页。
〔4〕罗曼·罗兰:《内心旅程》, 转引自罗大冈:《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