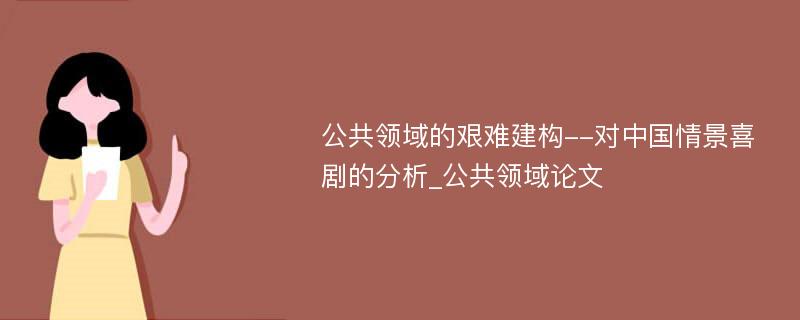
公共领域的艰难构建——中国情景喜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喜剧论文,情景论文,艰难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我爱我家》播出以来,中国情景喜剧已诞生十余年了。在这十余年里,虽然没有实现中国情景喜剧之父——英达预想的目标,但中国情景喜剧无疑已经走出了起初单一的制作圈子、地域范围与表现方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规模和影响。与当年仅《我爱我家》一枝独秀相比,今天一同上演的《东北一家人》、《男人四十跑出租》、《新七十二家房客》等作品显然表露出了几分百家争鸣的气象。如今,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加入了播放情景喜剧的行列,并且还出现了“630剧场”这类专为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节目单元,这便刺激了中国情景喜剧的酝酿与再生产,为优秀剧作的涌现打下了坚实基础。2002年《闲人马大姐》能够登上飞天奖的领奖台就是一个有力佐证。
为什么“情景喜剧”这一完全来自西方的节目类型能够在中国的电视文化语境中扎下根来,并形成相对明确的节目定位,相对成熟的节目风格以及较为稳定的受众群,由此发挥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影响力?本文试图从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这一角度来揭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等深层次的因素。
一、中国情景喜剧构建公共领域的机制
近代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来自汉娜·阿伦特。在她看来,“公共”一词首先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其次则指世界本身。因为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并与我们的私人地盘相区别”。①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共同的世界,将作为私人的个人聚集在一起,自由地讨论并处理与共同利益相关的事务。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领域的相关内涵,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原则……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够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②显然,公共领域是在国家权力之外,公民自由地行使表达权利,进而保障民主意见顺利形成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一个共同空间。
依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领域的形成起码需要具备三方面因素。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其次,公众的讨论应当限制在一般问题上。第三,使文化具有商品形式,进而使之彻底成为一种可供讨论的文化,这样一个相似的过程导致公众根本不会处于封闭状态。③
无疑,中国情景喜剧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典型地反映出了这三方面的特征。
英达在论及情景喜剧与普通喜剧的区别时,格外突出了它的“现场笑声”。的确,情景喜剧令人一望而知的特点就是不时来自观众的笑声。换句话说,这一电视剧种强调观众的现场参与。除了笑声之外,一些情景喜剧,如《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等,还在片头、片尾有意播出制作人员与观众直接交流的现场情景,《我爱我家》的片头甚至还出现了观众进入节目制作现场的镜头,以彰显节目与观众的亲近程度。此类声音与画面并不是导演英达偶尔想出来的讨好观众的招数,而是情景喜剧天生的本质。正是在这样的画面与笑声中,情景喜剧提供了公共领域所需的抹去了社会地位差别的社会交往方式。不管这笑声是出自富人还是穷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文盲,当面对同样的情景时,他们发出了相似的笑声。在开怀大笑的那一刻,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实现了情感上的共鸣,达成了态度上的共识,从而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拖入了这一不知不觉中进行着的交往过程。
当然,情景喜剧建构社会交往方式的主要手段是人物对白,人物对白构成了情景喜剧主要的情节因素。“没有一个非常出彩的剧本和精彩的台词,即便你拍得再精致再用心,都是一部残缺的情景喜剧”。④中国情景喜剧的生产比起它的模仿对象——美国情景喜剧来,似乎更依赖人物的对白,以至于中国情景喜剧给人留下了“耍贫嘴”的印象。这不仅仅因为更多地使用人物对白可以减少制作成本的投入,还在于中国情景喜剧的编剧乃至演员们大多与相声、小品等传统喜剧类型关系密切。在相声、小品这类传统喜剧类型日趋低迷萎缩的今天,它们也需要突破形式的限制,为自身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并且,相声、小品这样的喜剧类型,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期,是人们积极评价各类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季、姜昆的相声,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并成为那一时期民间话语的记录者与表达者。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只是借此指出,当年这类相声小品的风格如今或多或少移入了情景喜剧的创作之中。 同时,情景喜剧中的人物塑造讲究平民化。用英达的话来说,就是“人物应该比观众更低,有时候人物可能比观众高,但所处的环境低,喜剧人物一定要比观众可怜才行……”⑤这些和观众一样的普通人,生活在与观众相似的环境里,使用观众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不停地唠嗑斗嘴,在以家庭为主的电视收视环境中,是很容易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带入人物谈话讨论的情境中去的。在这样的情境中,公共领域的空间得以建立。
就情景喜剧的内容而言,大多数都是紧贴日常现实生活的,这便使剧中人物与观众相互交流的问题能够集中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上。“喜闻乐见”是情景喜剧编剧们严守的一条创作原则。他们不仅要以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为表现对象,而且“为了吸引更广泛的观众,喜剧必须利用大多数人可能认同的社会和文化经历的共同领域”。⑥《闲人马大姐》中的马大姐几乎遭遇了她那个年龄北京小市民有可能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大至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失足青年重返社会,小至市场经济条件下拾金不昧的行为、女儿的就学早恋问题等,都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就其意义而言是普遍的,而且在范围上保证了每一个观众都能进入情节参与讨论的可能性。在筹拍阶段曾备受专业人士期待的《网虫日记》、《中国餐馆》等剧,播出时却不得不接受失败的收视结果,其根本原因仍在于它们的内容超前了,脱离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难以形成一个人们可以自由参与的讨论空间。为了更好地贴近现实生活,中国情景喜剧将新闻时效性注入了自身的创作理念与实践中。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但1994年经过努力争取,北京获得了世界妇女大会的主办权。1994年播出的《我爱我家》第二十集便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纳入了剧情中。宋丹丹扮演的和平从兜里掏出一红袖章,念道上面印的红字:“迎七运,盼奥运……哦,不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了?”翻过来一念:“迎接世界妇女大会。”“时效性”在情景喜剧创作中越来越受重视,英达甚至希望当天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当天就能编入剧情,第二天就能出现在屏幕上与观众分享。虽然这样的愿望在当前的中国电视运作环境下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却表达了中国情景喜剧的本能冲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就一般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交流。
情景喜剧虽然是“舶来品”,今天却已经成了中国电视文化乃至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无论在业界还是在普通观众中,它都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情景喜剧中的一些语言由于深入人心,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尚流行话语:伴随着一些新的情景喜剧的出现与热播,各类大众文化读物也不断追逐着它的身影;网络中出现了专门为情景喜剧而设的论坛,中国情景喜剧迷在其中畅谈、交换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在美国情景喜剧风行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情景喜剧文化也在逐渐形成。就情景喜剧进入中国国门的那一刻起,它就是被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不是电视艺术引进的。在其以后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它从未试图摆脱过自身的这一身份,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播出者,始终瞄准的是情景喜剧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播出时间等诸多能够创造利润的因素。中国情景喜剧发展到今天,正在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产业。⑦在市场赢利动机推动下,情景喜剧的观众自然不会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它们一方面在不同的场合中被召唤、被聚集,主动加入对当下种种问题的讨论之中;另一方面,它们又密切地被制片方、播出机构所关注,成了一件可被公开出卖给广告商的商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情景喜剧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它具备建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潜能。而且,在当下中国社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文化语境下,它的这一潜质尤为珍贵。哈贝马斯曾经论及,公共领域在近代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型”,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众传媒为手段的新型公共话语空间。也就是说,在近代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形是:长久以来,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严肃大众传媒。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件发生时,舆论无法在严肃媒体上获得生存和表达的空间。⑧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今中国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是一种无法遏制的社会性集体诉求,当主流严肃媒体不能担当起这一责任时,代表公众性利益的言论必然寻找替代性的边缘空间,情景喜剧便是这样的边缘空间之一。当1992年英达决定在中国土壤上进行情景喜剧的实验时,这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1989春夏以后,中国媒体的舆论空间退缩到十分艰难的境地,中国社会的整体舆论环境也相当压抑。1992年,当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方向被重新给予肯定之后,舆论空间开始松动,但大多数人的心理仍是小心谨慎,一些重要的言论空间,如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类节目,尚不敢轻易涉足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冲突,因此当《我爱我家》用喜剧性的手法再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突然间掀起了一股收视热潮,由此也成了中国情景喜剧不可逾越的高峰。
直至今天,中国社会仍旧没有可供公众自由表达与讨论的传媒空间;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尤其是传媒机构面临的企业化经营的压力,促使中国传媒的自身功能定位也在默默地发生变化,中国传媒的传播理念也在寻求深刻的变革。除情景喜剧之外,公共空间在更多的边缘性节目中得到拓展,如《实话实说》、《面对面》等谈话类新闻节目。
二、情景喜剧构建公共领域的方式
情景喜剧主要运用两种方式来实现公共领域的构建。一是幽默的叙事风格,一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与消费方式。
英国学者米克·鲍斯提醒人们:“我们必须牢记,情景喜剧应当是滑稽的,幽默是区分情景喜剧和其他喜剧形式,特别是肥皂剧的分界。”⑨可以说,幽默是一切情景喜剧的生命,离开了幽默,情景喜剧不再是它自己。
情景喜剧的幽默效果主要依靠幽默性的人物对话来实现。情景喜剧中的人物对话类似相声演出,讲究在对话中隐藏“包袱”,通过“包袱”的抖落来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譬如《我爱我家》有一集叙述贾家媳妇和平不慎怀孕,她一大早就嚷肚子疼,想吃酸的。贾家的老父亲不明内情,也跟着说肚子疼,要求吃些开胃的饭菜,导致观众席上笑声一片。由于情景喜剧对观众发笑的频率要求相当高,所以包袱的设计铺垫十分重要。当然,情景喜剧的幽默效果还可以借助人物的形体动作来完成。譬如葛优扮演的流浪汉在贾家那副永远也吃不饱的样子,《东北一家人》中潘长江扮演的老舅盛气凌人的姿态与他自身的矮小卑琐形成鲜明对比。这颇类似于哑剧给观众带来的喜剧效果。
然而,幽默与搞笑调侃是有区别的。调侃搞笑纯粹是为笑而笑,人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暂时逃避现实生活的烦恼与压力,获得情绪上的放松。而幽默是有思想与智慧内涵的,它作用于人的理性。许多幽默跟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相关。《我爱我家》播出以后,在北方地区的收视率远高出南方,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表现的是北京市民的生活形态,叙事幽默来源于带有浓郁北京风味的文化传统。而以粤语文化和海派文化为主导的广州、上海地区的观众自然不那么容易分享该剧的幽默。反之,用上海方言创作的《老娘舅》在上海,用广东方言创作的《外地媳妇本地郎》在广州均获得了巨大成功,久演不衰。这也是为什么方言会成为中国情景喜剧的重要因素的原因。方言的排斥性说明了公共领域内部有一个秘密的圈子:我们仅用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符码交流沟通并由此享有共通的意义。在方言文化特有的凝聚力下,作为私人的情景喜剧观众进入公共领域,借助幽默的叙事力量,分享共有文化传统的智慧,取得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感与精神快感,并再生产关于自身文化的话语。公共领域的功能也由此得以显现、延续。
叙事上的幽默还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批判效果。幽默往往是处理局促不安的主要方式,它必然要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无法在主流媒体上得到充分、明确、公开的表达与展现,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恰恰是各阶层利益冲突、新旧价值观念冲突较丰富复杂、尖锐深刻的阶段。当《我爱我家》的小保姆因认真而又执著追求着自己的幸福爱情与平等权利而闹出种种笑话时,欢笑之余,被主流话语极力掩饰遮蔽的中国城乡、等级差别凸现出来,给人以深思。当贾小凡的出国梦想被老傅怒斥为“崇洋媚外”时,当自私胆小的贾志新在媒体面前极力表白自己邱少云、董存瑞般勇敢无畏的英雄气概时(采用了主流话语的叙事方式),反讽的效果不仅在于引出了观众的阵阵笑声,而且在于挑战了我们的主流信仰与价值观念,边缘化的普通公众的信仰与价值观念在笑声中得以倾诉和交流。尽管这样的倾诉与交流是如此曲折与艰难,不得不利用幽默的方式,但它毕竟是公开化了的,规避了国家权力控制的,民主并带有理性的倾诉与交流。在这样的倾诉与交流中,公众舆论找到了发泄渠道,并寻求到了形成共识的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也将迫使由国家权力话语支撑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进行某些调整。具有民主特征的公共领域与国家公共权力相抗衡的态势据此萌生。
当我们仔细分析情景喜剧时,不难发现,大多数情景喜剧与家庭相关。不仅《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开心公寓》离不开家,《闲人马大姐》、《外地媳妇本地郎》这样的情景喜剧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家庭生活展开的。米克·伊顿勾画出了情景喜剧可能发生的三种场景:“第一是在家里,一般围绕家庭情况展开。第二是在办公地点,反映人物在工作环境中的相互关系。第三种场景暴露出既有家庭又有工作范例的结构因素,通常涉及工作地点之外因某种原因牵连在一起的一群各式各样的人物。除了偶尔触及之外,一般不涉及家庭,而只是涉及家。”⑩中国以工作单位为主要人物活动场景的《候车大厅》、《候车室的故事》等情景喜剧,其实从人物之间的关系考察,他们更像是一家人,而不仅仅是同事。 在这些富于人情味的工作场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因素,(11)工作单位在这里成了家的一种延伸,工作单位里的生活也成了家庭生活的补充。
不仅如此,情景喜剧的消费场所也主要是在家中进行的。当我们提及情景喜剧时,其实无一例外指的是“电视情景喜剧”,电视是这一类型戏剧的唯一载体。不像相声、小品或哑剧等其他戏剧形式,虽然它们也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但它们最理想的演出场所并不是在摄影棚里,而是在剧院舞台上。情景喜剧却不需要剧院舞台,它一开始便是顺应广播电视的需要而出现生产的,(12)家庭自然也是它最主要的消费场所。此外,我们不难发现,在今天分众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突出的时代,情景喜剧的受众无论是在人口统计学还是社会关系意义层面,都很难定位。喜欢看情景喜剧的受众究竟是怎样一群人呢?男人,女人?老年人,青年人?白领,小市民,知识分子?我们无法选择并做出准确判断。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情景喜剧是少有的能够一家人一起坐在客厅里观看的电视剧种。有人曾经这样描述情景喜剧:“形式不求新奇,内容不求深刻,这种在25分钟时间内讲完的故事,轻松幽默,老少咸宜,尤其在北方那些夜生活并不丰富的城市里,一家人围在电视机旁,绝不会出现‘少儿不宜’之类的尴尬。”(13)这段话形象而典型地揭示了情景喜剧从内容到观剧形式与家庭生活紧密相连的程度。
家庭生活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家庭生活这个概念是各种关系的混合交织,它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空间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中郊区杂居生活的产物。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家是私人领域的核心。在公共领域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合为一体的。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公私不分的状态走向终结,但家庭生活却保留了下来。(14)“家庭生活,它是一种笼括性的——一种政治——类型。家、家庭、家庭经济都被纳入其中;它也体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联系”。(15)在现代社会中,虽然随着社会关系的私人化,家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边缘化,政治方面的意义逐渐衰减,但通过以电视为中心的传播技术中介,它重新获得了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能力。因此,“家庭生活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公民)消费行为的源头,而且,虽然有点矛盾但也完全有可能的是,它的意义在现代公共领域越来越重要了”。(16)作为私人的我们,表现在公共领域中的身份与价值观是在家庭生活中生产或再生产的。在公共领域中活跃着的公开讨论,主要靠的是一些源自小家庭私人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私人经验,离开了现代家庭生活,这些公开讨论便失去了与自愿、爱的共同体、教育相联系的人性基础,私人主体性也就不能发展为公众。(17)
总之,情景喜剧围绕家庭生活所展开的想象与叙事,以及电视作为家用媒介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当下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情景喜剧构建公共领域的局限性
上文指出了中国情景喜剧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反思社会学所要求的批判性分析反思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情景喜剧在构建公共领域过程中不是没有局限性,而且它的局限性还是那样的鲜明突出,以至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公共领域功能的正常发挥。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构建公共领域自身的要求看,中国情景喜剧不能,也无力承担起这一重要职责。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就公共事务进行最广泛的讨论。过去这类讨论主要在文学公共领域进行,但在哈贝马斯看来,随着公众由主要依靠阅读书籍(文学)变为依靠画报、杂志、电视等现代传媒来实现沟通,文学公共领域消亡了,文化批判的公众逐渐转变成了文化消费韵公众。(18)如果说以电视为主要手段的大众传媒削弱了公共领域的正常讨论功能,电视情景喜剧则更是降低了公共领域的这一功能。因为建立在虚构和幽默叙事基础上的情景喜剧,是在“以消费的充足度代替现实的可信度,从而导致对娱乐的非个人消费,而不是对理性的公共运用”,(19)公共领域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严肃的话题没有用严肃的方式(至少是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进行严肃地探讨,而是在公众的哈哈大笑中一笑了之了。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正常构建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情景喜剧的出现与发展具有补偿性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其次,情景喜剧的环形故事结构大大削弱了公共领域的批判性。由于情景喜剧每一集的主要人物相同,而且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所以其情节线索必然是环状的,而不是线性的。这是情景喜剧与普通电视连续剧的重要区别。环形的故事结构加上半个小时(连带广告)的时限决定了情景喜剧大多都是保守的。它紧贴现实生活,却不能深入现实生活。从起点到起点的故事结局不允许它深入挖掘生活空间。也就是说,它虽然能够大胆面对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诸种矛盾,但它无力揭示矛盾的本质,更无力解决矛盾。于是,依靠环形的故事结构,它回避了因矛盾冲突的激化而带来的悲剧性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批判现实生活,而是在虚幻中美化了现实生活。如《我爱我家》第一集讲的就是老干部不愿退休的问题,《闲人马大姐》中的马大姐也总是陷在下岗、再就业、女儿上学、邻里关系等种种难以摆脱的生活困境中。可是,借助于环形的故事结构,这一切都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孝顺的贾家儿女们热忱地恭请老父主管家庭事务,以慰藉他那不得不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失落心情。马大姐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下岗后在家庭与社会环境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公共领域中的诸种问题没能在公共性的原则基础上被积极对待并处理时,在某种程度上,公共领域便失去了其批判的功能,甚至有可能沦为国家权力的合谋者。
今天,中国公共领域的构建是一个备受知识分子关注的话题。透过情景喜剧这个个案,构建中国公共领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或许能够在一个更切合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实践背景中得到展开与认识。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各类文化实践(情景喜剧也好,通俗报纸也好)与不同的理论话语(西方的或中国的)才拥有了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注释: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81、83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②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126页。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41~4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④蔡明:《只有贴近生活才能赢得观众》,《中国青年报》, 2002年10月4日。
⑤《英达:我是情景喜剧之爹地》,《南方周末》,2002年 12月20日。
⑥米克·鲍斯:《只有当我们开怀大笑时》,见安德鲁·古德温、加里惠内尔编,《电视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6页。
⑦2004年5月在上海专门召开了“2003-2004中国情景喜剧产业研讨会”,全国几十家电视台以及节目制作公司的代表纷纷发言,探讨了中国情景喜剧产业的发展前景。
⑧孙玮博士在她的论文《日常生活的政治——中国大陆通俗报纸的政治作为》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她指出:“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报纸。”本文借鉴她这一观点,并认为不仅仅是缺乏严肃报纸,而是包括电视、广播等在内的严肃媒体都比较欠缺。公共舆论无法在严肃媒体上获得正常的表达空间(《2004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
⑨同⑥。
⑩同⑥,第119页。
(11)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的成功是从家开始的,个人处理家庭关系的手段与能力,同样可以运用于建立自己的社会功业。家与社会,与事业奋斗场所是一致的。
(12)苗棣在《美国电视剧》中对情景喜剧的产生有详细的描述,第7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3)野麦子:《我们有限的欢乐》,《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9日。
(14)Donzelot,Jacques(1979),《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Hutchinson。
(15)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6)同上,第75页。
(1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第153页。
(1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7页。
(1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