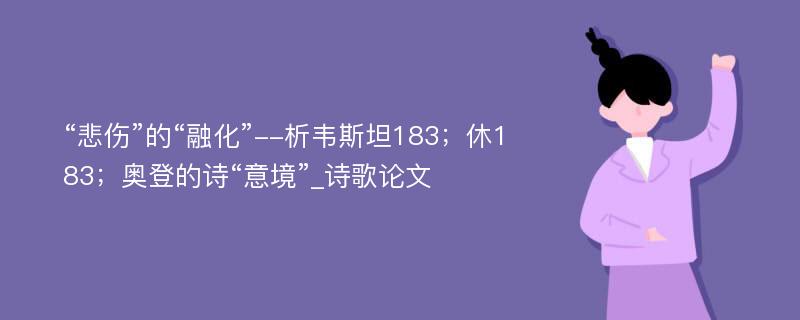
“悲哀”之“消融”——试析威斯坦#183;休#183;奥登的诗歌《寓意之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威斯论文,诗歌论文,悲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9)03-0100-04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奥登一代》的序言中写道:“奥登渴求一种写作。这种写作富于感情、直觉和理性的关照,其中心意图是道德性的而非审美性的,它更依赖这种意图而不是依赖与之相对应的可被观察的世界进行组织。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同时也是某种更艰辛的东西:他在探询另一个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包含着崭新的、意味深长的形态的世界。通过这个世界,文学可以在危机时刻发挥道德作用。”[1]海因斯的这段话,十分形象地概括了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主旨。
一、充满象征的诗歌形式
1930年,年纪轻轻的奥登以《诗集》和《雄辩家》出场,凭借精湛的诗艺和开阔的诗路迅速奠定了自己在英国诗坛的地位。这两部诗集给他的同时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理想,表达了广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感和态度,创造了一个诗歌界的政治取向性运动。可以说,奥登这个时期的诗歌,虽然措词晦涩,但主旨分外明晰,饱含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改变社会现状的积极心态和乐观精神。创作于1933年5月的《寓意之景》(Paysage Moralisé),便是这样一首剖析生活荒原、构建秩序世界的诗歌。
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把诗歌定义为“某种经验的错综复杂而又辩证有序的调和”。优秀的诗歌作品往往能够将内容与形式、感性与理性、内涵与外延等诸多成分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留给读者一个富有张力的意义空间。奥登对英国自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的大部分诗歌形式均有研究,屡有创获。在这首《寓意之景》中,他就成功驾驭了古老的诗体,让诗歌在形式上表现出充满活力的动态状势,烘托了诗歌内容。所以,我们若要完整地理解这首诗歌,就必须对其独特的诗体加以分析。
该诗由六节六行诗和一节三行诗组成,“山谷”、“山峦”、“水”、“海岛”、“城镇”和“悲哀”六个词语以严格的规律分别重复了七次。这样的诗体,在英语里称为“sestina”(六字循序诗)①,由12世纪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人阿赫诺·达尼艾尔(Arnaut Daniel)发明。达尼艾尔是一位诗艺绝伦的诗人,按照他的规定,“六字循序诗”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篇幅上,更重要的特点在于韵脚部位重复出现的六个词语。举例来说,我们以字母“abcdef”指代第一诗节六行诗句韵脚部位依次出现的六个词汇,那么,第二诗节的韵脚部位也只能用这六个词汇,而且它们还非得按照“faebdc”的顺序出现不可。这种顺序,就是一种由外向内轮替的顺序,上一诗节最外面两行诗句的韵脚先出现(下方诗句的韵脚总是在前),接着是由外围数来第二句的两个韵脚,最后才是最里面的两个韵脚。之后的诗节也按照这样的顺序安排依次韵脚。第七诗节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不但有规定的韵脚,还有规定的中间字。整首诗的韵脚结构如下:
第一诗节:abcdef
第二诗节:faebdc
第三诗节:cfdabe
第四诗节:ecbfad
第五诗节:deacfb
第六诗节:bdfeca
第七诗节:eca或者ace(三行诗句中间还要分别出现余下的三个词汇bdf)②
这种复杂、严谨的诗体为达尼艾尔赢得了不朽的诗名,不仅在法国大受欢迎,还得到意大利诗人们的青睐,但丁(Dante Alighieri)就曾在《炼狱》第26篇中高度赞扬了达尼艾尔的诗才,认为他是普罗旺斯地区最出色的诗人。然而,“这样大胆地接受局限、构思这样庞大的结构、并在其中表现持续不变的感情的能力,自锡德尼的时代之后就不复存在了。”[2]50六字循序诗因其高难度的格律而光辉过,也因此逐渐暗淡。身处20世纪的奥登却采用这种古老的诗体抒写现代诗篇,其用意何在?一方面,正如约翰·富勒(John Fuller)所言,他是为了挑战有难度的诗体,提升诗艺。[3]154另一方面,六字循序诗的诗体形式有助于表现他的思想。
首先,六字循序诗不仅有严苛的韵律要求,而且还规定,在一首诗歌里,每一个诗节的诗行长度尽量保持一致。如此地整齐和匀称,是一种对秩序的强调。而“秩序”,就是奥登穷极一生追寻的目标。奥登从幼年时期开始,就对创建秩序的世界非常着迷。在没有写下诗行之前,他曾渴望成为一名建筑师或者一名工程师,经常在脑海里勾勒属于自己的图景。他还给这些图景加了两条限制:图景中的物体必须真实存在;图景中的运作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4]8虽然奥登从15岁开始将兴趣转向了诗歌,但诗人同建筑师、工程师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在现存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作为诗人的奥登,在一定程度上将小时候对“自然规律和道德规范”的强调延伸到生活和创作里,坚信“艺术价值的关键之处在于教导‘自由的人该怎样赞美’”,即如何“重视无序之上的有序,哪怕这种秩序仅仅是艺术的秩序”。[3]289六字循序诗,相对于20世纪流行的自由诗来说,其严谨的格律可以更好地体现奥登“重建城镇”、构建秩序世界的愿望。
其次,正如詹姆斯·卡明斯(James Cummins)在那篇有关六字循序诗的著名论文中所言:“在我看来,六字循序诗体现了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对话。”[5]159在六字循序诗中,相距遥远的韵脚可以在下一诗节中相遇,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给人一种披荆斩棘、达成所愿的想象。这个时期的奥登,正处于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时刻。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荒原”世界,奥登迫切地希望有“神效之方”,“治疗”各种社会疾病,然后“欣然观看”“建筑的新风格,心灵的改变”(语出《请求》,作于1929年)。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他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一些带有梦境色彩的诗篇。1933年前后,他写下了长诗《我青春时期的那一年》,诗歌的主线是但丁式的梦幻之旅,只不过将中世纪的背景换成了20世纪的欧洲。奥登在诗歌中冷嘲热讽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病弊之后,向美好的秩序世界发出了呼唤。紧接其后,他又创作了另外一首描写梦境的诗歌,诗中的主要意象是一艘名为“威斯坦·奥登先生”的船,它带领人们穿越波涛汹涌的汪洋,寻找地上乐园,用原诗的话来说,是一个“流着奶和蜜的海岛”。然后我们来看《寓意之景》,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前面两首诗歌以及《寓意之景》的六节六行诗中,奥登将“崭新的、意味深长的形态的世界”描绘成遥不可及的彼岸,主人公寻寻觅觅、千辛万苦;而到了《寓意之景》的最后三行诗,整个基调发生了变化,诗人豁然开朗,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方案——“我们重建城镇,而非梦想海岛”。现实不再遥望着理想,它可以同理想对话,可以变得美好。
此外,六字循序诗中的数字所承载的文化喻意也很好地呼应了诗歌内容。西方人认为,数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们相信,“六”是物质世界的宇宙数字,象征着“我们置身其中的空间和时间”,“七”是宇宙潜藏的循环周期,象征着“完整、圆满和永恒”。[6]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然后将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这种“6+1=7”的格局被充分地运用到六字循序诗当中,使诗歌形式所隐含的意义得到充分延伸。在《寓意之景》中,我们看到前面六节的六行诗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纵向隐射,而最后一节的三行诗则是对可能达到的秩序世界的一个理想投射,那么,奥登的寓意已经跃然纸上了。
二、意蕴丰富的诗歌内容
《寓意之景》最初发表在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主编的《标准》上,原诗并无标题,直到1945年收录进诗选的时候,奥登才为它加上了这个标题。事实上,“寓意之景”是美学上的一个术语。著名的德裔美国艺术历史学家埃尔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于1937年前后撰写了一篇美学文章,首次使用了该术语。他认为,优秀的作品,往往与它的时代和创作者密切相关,具有深层的意蕴。艺术历史学家除了要了解作品在技术和形式上的特征以外,还要旁涉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史等知识,破解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内容。这个崭新的术语,很快赢得了大家的青睐。对绘画艺术颇有兴趣的奥登,也偏爱上这个术语,并将它作为自己早年诗歌的标题。奥登为旧诗添上新标题,显然并不是源于一时兴起。事实上,这个术语的内涵,与诗歌文本颇为吻合。通观全诗,“山谷”、“山峦”、“水”、“海岛”、“城镇”、“悲哀”这六个词语反复出现,一再叩击我们的心扉。当我们依循诗行的轨迹,像穿越迷宫般在这些词语间绕行的时候,一种场景,或者说一个世界,慢慢地铺展开来,我们逐渐获得了这些词语所指涉的全部含义。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画,画的一边是山谷、山峦和城镇,弥漫着悲哀的气息,另一边是隔水相望的海岛,洋溢着欢乐的氛围;这两幅画截然不同。这种处理方式,跟帕诺夫斯基所形容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寓意之景”(绘画作品)非常相似,即由富有象征意义的对照性的两个部分组成。绘画作品是以线条和色彩勾勒画面,表现主旨,诗歌则是通过语言和声音描绘场景,吟唱主旨。古今中外的学者基本上都强调诗画一致,即使宣扬诗画不同质的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也认为这两种艺术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从这点来讲,奥登运用美学术语“寓意之景”作为这首诗歌的标题,可谓用心良苦。它明白晓畅地向我们宣告:诗歌描绘的场景在说话。
那么,这种对照性的场景是如何铺陈的呢?燕卜荪曾说,六字循序诗通过对关键词语的“重点使用”,“逐渐引起我们对它们的兴趣,从而发挥作用。由于反复,这些词的全部潜在含义都表现了出来,而每一种含义又被用来造成一种简单的奇喻……在人们心中聚合成一种感情节奏。”[2]50奥登就是通过关键的六个词语——山谷、山峦、水、海岛、城镇、悲哀,将我们带入他的诗歌世界。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六个词语,拨开诗歌语言在意义上的面纱,探究诗歌文本的内在逻辑和主旨。
从地貌上而言,山谷和山峦是一组对照性的存在。山谷是山脉或其它高地之间狭窄低凹的区域,是人类起源的地方,也是文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它们就像地球母亲的子宫,孕育着蓬勃生机,滋养着天地生灵。因此,西方人往往将山谷想象成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鲜花遍地,气候宜人,即使有时候它们也会因为过于旺盛的生命力而变得草木丛生,幽暗隐晦。在《寓意之景》中,山谷虽然呈现了它催生生命的美好一面,更多的时候却是以令人沮丧的面目出现。我们看到,山谷中居住着“郁郁”的民众,那儿收成“腐烂”,生活“不幸”。先辈们原本带着梦想、带着希望,费尽千辛万苦抵达山谷,意图缔造可以安居乐业的城镇,然而留给后辈的却是“濒于饥绝”的城镇。更“可怜”的是,山谷相对安全、闭塞的地理特征,使大多数民众变得被动、懒惰,他们“不愿离开”,宁肯死守“悲哀”。
与山谷相对的山峦,无论是绵延起伏的轮廓,还是峥嵘陡峭的地形,都给人一种雄奇壮阔的感觉。人们习惯把平坦安定的山谷看作生活的归宿,把冷峻巍峨的山峦视作征服的对象。在攀登山峦的过程中,高峻的山体、茂密的山树、崎岖的山道不仅带给登山者挑战自我极限的非凡体验,也满足了登山者探视陌生地域的潜在欲望。人类的登山过程,与人类挑战自然、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发展历程非常相似,是一种在探险中寻求收获的过程。然而在《寓意之景》中,山峦的险峻仅仅留下了先辈们的足迹,悲哀的民众早已遗忘了征服的旅程。山峦“荒芜”,乏人问津;金矿银矿“堆积”在那里,无人发现和采掘;仅有的登山者也以失败告终,“垂老”于途中。山峦的高度不再是人类征服意志的体现,相反,它们成为人类无法逾越的“阴影”。
城镇和海岛,一个作为近在咫尺的人居环境,一个作为远在彼岸的原生自然,在诗歌中成为另一组对照性的存在。随着城墙的构建、城镇的兴起,人类与自然日渐分离,“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法则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光荣与卑陋、奢华与贫苦、成功与失落都在这里滋生。先辈们带着希望走向山谷,走向缔造幸福城镇的实践,绝没有料到城镇最终成为囿囚自身的场所。此时,遥远的海岛便成为可以梦想的对象。有些人不顾艰难险阻划向海岛,却“沉溺于水”;有些人在梦寐之中构想海岛,却只是凭空设想;有些人绘声绘色地描绘海岛,却脱离了现实生活。对于居住在城镇的民众来说,海岛那么陌生、那么神秘,是不同于此在的地方,是可希望、可期待的乐园,是摆脱当下处境的一种可能性途径。
然而,悲哀弥漫在山谷,笼罩在城镇,渗透在现实生活里。那么,先辈们呢?他们是否远离悲哀?他们是否过着不同于我们的幸福生活?人们总是对过去怀有一种理想化的幻想,每每抚今追昔,不胜唏嘘。奥登却告诉我们,悲哀无处不在。我们“崇敬”先辈,将过去设想为英雄的时代,这只是源于我们自身意志和能力的匮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悲哀之中想象着他们的幸福生活一样,他们也在悲哀之中渴望缔造的城镇能够带给他们幸福。我们活在对往昔的幻想里,他们活在对未来的幻想里,而我们的悲哀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幻想的破灭。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指出,奥登在这里将视野投向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的悲哀与梦想,映衬着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处的现状和所做的努力:在第二诗节中,先辈们跋山涉水、缔造城镇的过程,象征着古代人类征服自然、发展城市的历史;在第三诗节中,人们“在小床上构想海岛”,黎明到来之后,又不得不面对迫在眉睫的残酷现实,隐射了身处18世纪封建专制统治、呼吁创建资本主义理想国的启蒙思想家们;19世纪浪漫主义者的身影出现在第五诗节中,“朝圣者”渴望逃离自身的城镇、奔向遥远的海岛的心情,与浪漫主义者回归自然的纯朴愿望如出一辙。[4]155他们生活过、梦想过、尝试过,却都没有化解人类生存的莫大悲哀。现代人同他们远古的祖先一样,在悲哀中做着同一个梦,一个有关幸福生活的梦。
既然人类化解悲哀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那么,还有希望吗?拯救的信息是有的,就是水。约翰·富勒认为,这里的水是“一个矛盾性的存在”,它既是“灌溉者”又是“破坏者”,它在孕育生命的同时也淹死了划向海岛的航海者。但是,正是因为它的双重属性,才有可能打破现存的状态,重建和谐的秩序。[3]156这样的水,在奥登看来,过于草率便会“纵身沉溺”,让我们想到艾略特笔下沉沦在情欲汪洋中的腓尼基水手;但是,节制的、有序的水却可以“涌出,奔流,灌绿这些山峦和山谷”,让我们“重建城镇,而非梦想海岛”。
值得注意的是,奥登的这句“涌出,奔流,灌绿这些山峦和山谷”,与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创作的《德意志号沉没记》(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中的第八节形成了互文。霍普金斯是一位虔信宗教的诗人,他笔下的“涌出,奔流”的水是上帝之爱。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推断奥登也将拯救的希望放在宗教信仰上,但至少可以肯定,这里的水也是一种爱。奥登一直坚信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爱。弗兰克·玛吉尔(Frank Magill)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无论在他成为基督徒以前还是以后的诗中,奥登总把爱写成拯救人类的力量。”[7]比如,“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去”(语出《1939年9月1日》,作于1939年),“人必须爱上/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否则就会生病”(语出《短诗》,作于1972-1973年间)。这种爱,既有人对自身的爱,也有两性之间的爱,更是一种广阔无边的大爱,它“凝聚了人类的联合、人类的团结一致和人类的思想的一体化”[8],消融了悲哀,消融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隔膜,在混乱无序之上重建理想家园。
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在这首《寓意之景》中,奥登将自己“探询另一个世界,一个想象的世界,包含着崭新的、意味深长的形态的世界”的愿望淋漓尽致地灌输到诗歌的形式与内容之中,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他那颗剖析生活荒原、构建秩序世界的关怀之心。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曾说,奥登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是“本世纪的批判者”。奥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批判和重建。他就像《寓意之景》中的“水”那样,“几乎穷尽地批判了现有的社会病态”[9]之后,“亮起肯定的光芒”(语出《1939年9月1日》,作于1939年9月)。
[收稿日期]2008-04-28
注释:
①“sestina”一般翻译成“六节诗”、“六行诗”或者“六节六行诗”,但都不能表达这种诗体的本质特征。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翻译为“六字循序诗”。
②《寓意之景》最后三行诗的韵脚和嵌字并没有严格遵守六字循序诗的韵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