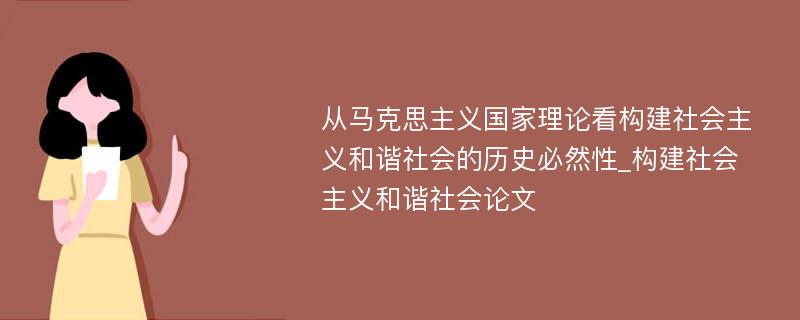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解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国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充分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途径作一阐述。
一、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公共权力回归社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至少以下几个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1、实现社会和谐是任何统治阶级的追求,剥削阶级控制政权的国家也力图社会和谐,这是因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①,这种“秩序”也就是任何统治阶级都梦寐以求的社会和谐。2、国家的存在,又是社会不可能根本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具有双重本质,一是“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一是国家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③。国家的这种双重本质也就决定,在国家存在的状况下,社会不可能是根本和谐的——国家的阶级性必然激起被镇压阶级的反抗,国家的公共权力与人民大众的分离必然激起人民大众的不满,因此,要实现社会根本、长久的和谐,必须使国家具有这双重本质(根本职能),这也就是国家的消亡。3、社会主义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是“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消亡’)的‘过渡’”④的国家,也就是在本质上它是国家与社会结合并向社会过渡的政治形式,即“半国家”。这种政治形式也就决定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需要“构建”的,如果不科学地“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社会和谐就不仅难以实现,甚至退化、异化,如“反右”、“文革”等时期。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述几个基本观点,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根本的、坚固的理论基础,也证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上述基本理论:国家的一重本质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这重本质若不消失,社会不可能获得根本、长久和谐,因而很显然,社会主义要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和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公共权力的回归社会,这种回归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国家机构(官员)的不脱离人民大众。这也就是说,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机构(官员)的不脱离群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实现了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回归社会,就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一方面的根本基础。
现实中,国家机构(官员)脱离社会的倾向也确实很严重。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不仅表现在一些官员贪污受贿、以权寻租,谋取法外利益,而且表现为力图巩固、扩大“法定”(法内)或介于“法定”与法外之间的利益。他们偏离政府部门的公共利益导向,追求部门局部利益,以图实现“权力衙门化”、“衙门权力利益化”,甚至“部门利益最大化”,努力获取有利的职权(如审批、收费、处罚等),冷淡、推脱无利或少利的职权,规避相应义务,如超编(通过扩张政府部门来扩张自己权力)、超支(突破财政预算、拓展预算外收入)等。他们力图借一些法律规章的制订来巩固和扩大“法定”权利。他们争立法权,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与“程序法定”等使部门利益法定化。这些官员在巩固、扩大这种法定权利时,往往假借国家的名义,使部门利益国家化,将部门(往往是部门领导或小团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使部门利益出现国家化倾向。
这些官员力图巩固和扩大法定权利,把这种权利伪托成国家意志,以此谋取个人利益的倾向、做法,充分表明他们已异化为与人民大众脱离的公共权力的掌控者。这种掌控鲸吞着公共资源、社会利益。据国家信息中心一课题组提供,2004年全国公款接待费用 3700亿;有学者调查,全国一年公车耗资3000~4000亿,出国考察费用近3000亿。这些庞大的开支中有合理的部分,但至少有二分之一左右是浪费的,而我国的税收2004年仅2.57万亿。按1999年生活水平,3000亿可解决我国32~35个贫困县5000多万农民和县、乡镇居民进入小康⑤。
基于一些官员对社会公共资源“法定”和法外的严重侵占,以及一些官员由于不负责任的烂决策、利益输出导致国资流失、收受贿赂后抬高物价迫使消费者增加支出、不作为和庞大的官员队伍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负担,官民矛盾,在不少地方实际上十分尖锐。据一些学者调查,评判目前的干群关系,认为“一般”和“对立”的大大高于“很好”和“较好”的。更尖锐的现实是,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将长期积累下的不满情绪,借机发泄,发泄对象则往往是国家和政府的代表、象征——警察、官员。
现实中的这种尖锐矛盾显然表明,这种矛盾如果不予以妥善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纯粹是空想;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只能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寻找根本的理论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深刻地、透彻地揭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权力的脱离社会,消除这种现象的根本、唯一道路则在于推动国家代理的公共权力的回归社会。
二、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执政方式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推进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回归社会,即监督国家机构(官员)的不脱离群众:同时指明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执政方式。
如上所说,国家的本质在于其的阶级性和反社会性,即国家具有双重本质(根本职能),一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也即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⑥;另一是“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这种阶级性与反社会性的双重本质也就决定,国家对其本身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主要是运用暴力和行政方式。
国家的存在既然建立在对被压迫阶级的镇压上,因而它离开暴力就不能巩固政权。正如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⑦;也如列宁所说:“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监狱之类的物质的附属物”⑧。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运动的压力,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赤裸裸的暴力已大为减少,但这种镇压变换着的其他方式则始终存在。这种镇压平时似乎看不清,但一遇到重大事件,就会像闪电一样,把一切照得清清楚楚。
国家的另一本质既然是一种“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那么,这种权力的根本职能除了“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外,它更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⑨,因而国家机构(官员)在依凭暴力强制外,还必须凭藉行政强制,即行政方式。所谓行政方式,就是国家通过自上而下发布的命令,强制国家官员直至普通民众执行它的意志。为此,马克思概括道:“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⑩,国家是“集中化行政权力”(11)。因此可以说,行政管理是旧国家管理方式的根本特点之一。
无产阶级国家,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它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2)了:列宁认为它是“向非国家(‘国家消亡’)的‘过渡’”(13)的国家,它只“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14)。因而无产阶级国家实际上是“半国家”,其本质是国家与社会(自治)的结合并向社会(自治)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也就决定,作为执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对社会与国家的管理既是执政——掌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又是领导——组织、支持和领导社会力量对社会的管理与推动、引导国家向社会(自治)的尽可能转化。这种执政与领导的双重身份,也就使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领导方式与旧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
旧国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因而它不得不建立复杂而庞大的暴力机构,无产阶级国家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相对来说,就不需要保留复杂、庞大的国家机器,从而也就使旧国家阶级镇压和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这双重本质(根本职能)逐渐丧失。伴随着无产阶级国家日益巩固和发展、专政范围日渐缩小趋势的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日益扩大。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国家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15)。
无产阶级国家作为国家与社会(自治)结合并向社会(自治)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不能主要采用行政方式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集中表现在对社会经济建设的管理上。
对经济建设的管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主要任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于经济建设的管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能促使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管理中心和一整套的组织机构,这样的管理中心和组织机构,在相当长时期,只能由无产阶级国家来承担和组织。然而很清楚,这一中心及其机构必须本质上是社会(自治)机构,即它一方面必须尽可能摆脱“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而仅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16);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摆脱行政式的领导方式。这是因为,对经济建设的管理与政府的“各种特殊职能”分属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活动规律和追求目标,后者对前者的渗入,在一般情况下,必然干扰前者对自身规律的遵循和目标的追求;更因为行政方式在本质上是与生产的社会化相对立的,现代化大工业本身是社会化的,它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能按行政区划、行政层次来进行工业布局。列宁曾指出,保留中世纪的行政划分是破坏现代化的条件,大工业需要依照经济合理的原则,根据资源的供给和社会的需要情况来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不能束缚在等级服从的行政结构中,与外界只保留有垂直的行政关系。行政方式一般来说总是不利于经济活动遵循经济和自然规律的。(17)在经济领域,如果主要不是运用经济方式,而是仍然主要袭用行政方式,必然造成经济的混乱和倒退。
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主要不能运用行政方式还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们和无产阶级国家除了有行政的所属关系外,还有其他种种关系,而人们相互之间更有种种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各有不同特点,因此社会主义阶段,行政方式不能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渗透到一切人们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国家不能用行政方式处理所有一切社会关系,还因为社会是一复杂有机体,它内部各领域各有其不同特点和规律。
总之,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及发展规律、人们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社会各领域各有其不同特点和规律,尤其是无产阶级国家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规律等决定,无产阶级国家对国家与社会的管理不能单纯和主要运用行政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方式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适用范围将越来越小。这种管理方式演化的趋势,也就是政府将由社会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变为引导、组织、监督社会组织的调控中心,直至转化为社会机构。
无产阶级国家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不能单纯和主要运用行政方式,既表明无产阶级国家与旧国家的区别,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国家走向消亡的一个体现。无产阶级国家运用适合自己本质特点、适合社会不同领域的不同的管理方法,是实现社会和谐,推进国家消亡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家管理方式的社会主义民主
国家管理的本质方式是阶级性的暴力和行政指令,这两种方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一时都不能完全放弃,因而它还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必须运用的两种方式。然而,这两种方式并非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主要运用的国家管理方式,它运用的主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19)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正因为如此,所以革命导师十分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根本管理形式。为此,他们特别强调要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列宁就指出:“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走向民主。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20);无产阶级国家要能够“有计划地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必须“不是从上面‘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动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去掌握管理国家的艺术,去管理全部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国家是国家与社会(自治)的结合并向社会(自治)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样也就决定,无产阶级国家除了仍具有国家的本质特征外,还具有社会(自治)组织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同时是劳动者自己的社会组织,即它不是脱离社会、站在社会之上、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的机构,而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组织,因而这种组织的管理方式必然不同于国家管理的方式。如上所述,国家管理方式的本质是“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21)——不管是主要使用暴力镇压和强制性指令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旧国家,还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国家——都如此。而这种组织则由于它是建立在对社会共同体利益的认同与认知基础上,因而它的管理方式的原则是自觉、协商、说服、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道德等,也即它主要依靠启发与提高组织成员的道德自觉和通过集中了社会利益的规章以及组织成员内部的协商来进行管理。这种方式的本质即社会管理、群众自治。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用民主、说服的方法解决;“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22)。由于社会(自治)组织的生命力在于人们实现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自觉、自发动力,因此,这一组织内,人们主要不是依据上级的命令,被动地行动,而是根据社会、集体和自身的利益积极地行动,从而其管理方式排斥行政性,更排斥暴力性(不管是少数对多数,还是多数对少数)。在我国实行已久的人民调解制度,正是这种协商方式的成功实践。这种管理也要有领导、协调,这是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的权威,但这种领导、协调不是使用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而主要是运用协商、说服。对于社会(自治)性质的管理和国家性质的管理,列宁曾有明晰和深刻的区分。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届时,国家已消亡,人类社会真正进入整个社会的自治,即社会自组织状态),人们“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总之,很清楚,社会自治,即社会自组织管理的主要方式是协商和道德。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就应认识到,摆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用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并按照准备取消阶级,消灭阶级的方向来进行这一工作。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这种政治形式的管理,不仅要掌握、运用国家管理方式、社会(自治)管理方式,而且要掌握、运用领导、推进国家向社会(自治)过渡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主要内容、手段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引领作用。
意识形态特有的存在方式就是反作用于产生其的物质生活条件,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使命。这种维护,对于先进的、具有生命力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来说就是一方面维系它的稳定,一方面又推动它的前进。意识形态的这种特点也就决定,其本质“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23)
意识形态的这种引领作用具有普适性,即任何追求文明的民族要自立于世界,必须以先进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作引领。正如胡锦涛所指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4)
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我们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管理无产阶级国家的方式。很显然,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直接影响其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执政方式——的正确确定和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才能准确获得。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学说中汲取社会与国家演化规律的思想,汲取必须推进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的回归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把握执政和领导无产阶级国家的方式的思想,我们才能清醒、自觉地管理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事务,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顺利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实践将会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的思想宝库。
注释:
①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160、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⑧(13)(14)(15)(21)《列宁选集》第3卷,第680、90、680、164、192、1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参见《羊城晚报》2006年6月23日、参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24期第50页、《特供参考》2006年第17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⑨(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8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7)(20)《列宁全集》第24卷,第152,153、15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列宁全集》第28卷,111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3)《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3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24)《胡锦涛在第八次文化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06年11月10日。
标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