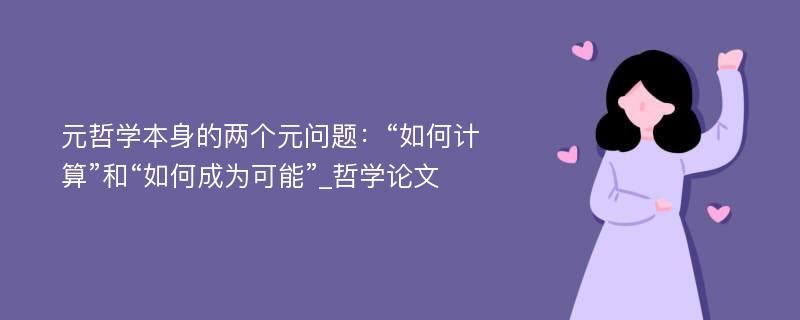
元哲学自身的两个元问题:“怎么才算”与“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才算论文,哲学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2-0037-09
元哲学(metaphilosophy)或哲学元理论(metatheory of philosophy)——也有人把它称作哲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或二阶哲学(second-order philosophy)或哲学观(the outlook on philosophy)——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不仅每一位自觉的哲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哲学元理论,而且许多自己并没有提出哲学的对象理论(the object theory of philosophy)或哲学的实质理论(the substantive theory of philosophy)或一阶哲学理论(first-order theory of philosophy)的人也往往喜欢对元哲学问题发表看法。因此,迄今属于元哲学领域的思想资料可以说非常丰富。然而,从目前已出版的论著看,不仅真正自觉地把哲学元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加以系统研究者不多(哲学家们的哲学元理论通常是在相应的哲学著述的序言或导言中表述的),而且对哲学元问题的讨论往往缺乏元研究(metastudy)的特点,忽略了哲学元理论本身的元理论问题,对某些深层难点问题甚至尚未真正触及。故此,本文拟主要考察元哲学自身的两个重要元问题——元哲学的判定问题与可能性问题。在考察过程中,本文尽量体现哲学自身的论证方式和元研究的特点。
一、元哲学的判定
(一)关于元哲学判定的已有说明及其所包含的问题
据笔者所知,有些人根据汉语中“元”的含义,把元哲学理解成哲学的最纯粹、最根本的部分,即把元哲学理解成相对于“应用哲学或哲学的应用”而言的纯粹哲学或哲学的纯理论、纯原理,但本文所讲的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元哲学。因为把哲学的最基本理论称作元哲学,这是对作为“metaphilosophy”的译文“元哲学”一词的望文生义的误用;就如同不少人对作为“ontology”的译文的“本体论”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和误用一样。笔者下面主要以互联网上规模大、影响广的开放式百科全书“维基百科”(Wikipedia)中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词条为例来考察一下已有的对元哲学的说明。
笔者所看到的出自“维基百科”的“元哲学”词条有三个版本①。这三个版本大体上都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什么是元哲学:一是指出元哲学的特点,二是列举元哲学研究的内容或问题。
关于元哲学的特点,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元哲学本身就是哲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philosophy)。有人曾把“关于哲学的哲学”与“关于别的学问的哲学”作过比较,指出,在通常情况下,“关于某学问的哲学”本身不是某学问,例如,“关于生物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biology)不是生物学,但是,关于哲学的哲学却本身就是哲学。②第二,元哲学是递归的(recursive)、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研究。例如,把自己的方法反过来用于自身(to turn its own methods upon itself)。
关于元哲学研究的内容和问题主要有:哲学所特有的主题;哲学问题的本性、分类以及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哲学所特有的价值与目的;哲学批判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能否像特殊科学那样取得进步。在元哲学所研究的问题中,“什么是哲学”被认为是元哲学的首要问题,而澄清、辨析各种关于哲学的本性的看法就相应地被认为是元哲学的首要任务。一份以“METAPHILOSOPHY”命名的学术期刊所列举的该期刊感兴趣的领域也与上述研究内容类似。③
在笔者看来,以上关于元哲学的看法至少包含两类没有得到澄清的问题:一是关于元哲学与哲学的关系的;二是关于递归与自我指涉的。
1.关于元哲学与哲学的关系
从抽象的可能性来看,元哲学与哲学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关系:首先,元哲学就是哲学本身;其次,元哲学不是哲学,元哲学在哲学之外、之上;最后,元哲学在哲学之中,是哲学之一或哲学的一部分。
如果元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那就要么元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特定分支或部分,而是把哲学的所有分支或部分都包含于自身的哲学整体,要么只有元哲学是哲学,而与元哲学不同的其他的哲学分支或部分都不是哲学。但是,这两种选项应该都不成立,至少与哲学学科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而如果把元哲学看作哲学中决定哲学之为哲学的部分,那么与其叫“元哲学”不如叫“哲学基础理论”。
如果元哲学不是哲学,而是在哲学之外或之上,那就不能把元哲学说成“关于哲学的哲学”。这样一来,上述以“维基百科”的“元哲学”词条为代表的关于元哲学的流行看法也就不能成立。
如果元哲学在哲学之中,如果把“关于哲学的哲学”理解成哲学的诸分支之一,那就又会引出如下一些问题:第一,把元哲学说成“关于哲学的哲学”,意味着把“元研究”等同于或看作哲学研究,或者说,把“元研究”等同于或看作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是这样,那么“元某某学”就等同于“关于某某的哲学”,例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语言学就分别等同于关于数学的哲学、关于逻辑学的哲学、关于语言学的哲学。但是,在通行的学科分类中,元数学、元逻辑学、元语言学之类的元学科至少并不都被看作哲学学科,即“元某某学”至少并不都是哲学。第二,即使把元数学、元逻辑学、元语言学之类的元学科都看作哲学,也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其他学科的元学科或二阶学科”的哲学,“作为哲学的元学科或二阶学科”的哲学,“作为哲学的一阶学科或对象性学科、实质性学科”的哲学,这三种哲学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哲学?或者说,它们能否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称作哲学?如果它们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被称作哲学的,那么这样的称呼就是不合理的,会导致混乱或误解;而如果三种“哲学”的意义相同,那同样的意义又是如何表现为或特殊化为三种哲学的?哲学自身又是如何分出“阶”的?不同阶的哲学又怎么可能都在同样的意义上是哲学?第三,元数学、元逻辑学、元语言学之类的“元学问”作为二阶学问通常都是关于学问的学问,“元研究”作为二阶研究通常都是关于研究的研究。按照这种理解,“元哲学”作为二阶学问也就是关于哲学这门学问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哲学的哲学),是对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本身的研究。如果把这样的学问、这样的研究也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与哲学的其他分支又是什么关系?元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又根据什么都成为了哲学的分支呢?
2.关于递归与自我指涉
如果一门学问所研究的内容也适用于说明和规范这门学问自身,那么这门学问就具有递归性或自我指涉性。而一门学问所研究的内容之所以会适用于说明和规范这门学问自身,又主要是因为这门学问本身就属于该学问所研究的那类对象,或者在该学问所研究的内容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如果一门学问,作为一种理论或认识,本身并不属于它所研究的对象,那就不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例如,在通常的意义上,生物学是一门学问、一种理论,而不是生物学所考察的生物,因此,在通常的意义上,生物学所研究的内容并不适用于说明和规范生物学这门学问自身;换言之,在通常的意义上,生物学不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
虽然元哲学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但是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却不是元哲学所独有的,而且元哲学的递归性、自我指涉性与某些其他学问的递归性、自我指涉性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笼统地从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来确定元哲学的特点。
除了元哲学,至少还有两类学问也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第一类是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在于,哲学基础理论所研究的内容没有例外地适用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因而也必须适用于哲学本身。第二类是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等等关于认识与表达的学问。认识论本身也是一种认识,逻辑学本身也要遵守逻辑,语言学本身也要用语言来表达,因此,这些学问所研究的内容也都适用于它们自身。
元哲学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与上述两类学问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都不同:首先,虽然哲学(严格说来是哲学基础理论)考察所可能知的一切的共有、固有、必有规定或规律,但是“哲学”却只是所可能知的一切之一,因此,对哲学的考察并不是对所可能知的一切的考察。元哲学作为对哲学本身的考察,其内容并不适用于所可能知的一切,从而无法从“适用于所可能知的一切”这一角度确保元哲学所考察的内容适用于元哲学自身。其次,元哲学也不能像认识论等学科那样,因为“自身就从属于所考察的那类对象”而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认识论”作为“关于认识的学问”本身就表明它是一种“认识”,而“元某某学”作为“关于某某学的学问”本身并不表明它就是一种“某某学”。如果“元某某学”本身就是一种“某某学”,那么“元某某学”所研究的内容就应该从属于“某某学”所研究的内容。但实际上,“元某某学”所研究的和“某某学”所研究的不是同一类内容。例如,“生物学”所研究的是生物,而“元生物学”所研究的却是一种认识或一种学问。既然元哲学既不能像哲学基础理论那样(因为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至大无外的适用范围而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也不能像认识论之类的学问那样(因为自己本身从属于所研究的那类对象而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那么,元哲学又如何能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呢?在笔者看来,元哲学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仅仅在于:元哲学作为对哲学的考察,必须包含对元哲学自身的考察。这是因为,无论是把元哲学看作哲学的一部分,还是不看作哲学的一部分,对哲学本身及其领域划分的考察——这是元哲学的内容——都要涉及这种考察与哲学是什么关系。
如果以上所确定的元哲学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能够成立,那么所有的元学科就都会因为同样的道理而具有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这样一来,就又有个元哲学与其他元学科的关系问题:元哲学与其他元学问在什么意义上都是、都叫元学科?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元哲学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还有个与元哲学的二阶性的关系问题:元哲学的递归性与自我指涉性能否是三阶的或更高阶的?或者说,元学科中能否有超越二阶的更高阶的递归与自我指涉?
(二)从“metaphysics”看“元”与“元研究”、“元理论”
为了确定元哲学的本质特征以及元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让我们回到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的解读。
元哲学不是唯一的而且很可能不是最早出现的有明确称呼的元研究(metastudy)、元学科(metadiscipline)。如前所述,除了元哲学外,还有元数学、元逻辑、元语言学等等;而且,后面这几种元学科作为有明确称呼的元学科也许比元哲学出现得更早。不过,最初的具有元学科名称的元学科也许当推“形而上学”(metaphysics),各种其他的元学科追根溯源也许都是参照“metaphysics”与“physics”的关系形成的。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就从“metaphysics”入手来考察“元”与“元研究”。
1.“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上”与“后”
作为“metaphysics”的译文“形而上学”中的“上”(meta)或元理论、元学问中的“元”(meta)是指超越(beyond,transcending,more comprehensive),是指上层、上位;元理论、元学问就是上一层次的理论或学问。这里的“上层”、“上位”主要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逻辑意义上的,是对相应内容的理解意义上的,主要是指前提、预设、根据。因此,元研究、上位的研究就是前提性研究;元问题、上位问题,也就是前提性问题。
“meta”既是“上”(transcending),也是“后”(after);形而上学既是物理学之上的学问,又是物理学之后的学问。但是,“meta”作为“后”,形而上学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学问,应该主要不是指在时间顺序上排在后面,而应该主要是指事后的反思或后思——即德文的“nachdenken”。在这一意义上,元理论、元学问是反思性的或后思性的理论或学问;是相应理论或学说的反身自我认识。
按照以上解释,元研究有两个基本规定:一是前提性研究;二是反思性研究。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元研究就是对相应的下层理论或下层认识本身的“前提或根据”的反思性研究;或者说,元研究、元思考是对元问题的研究、思考,而元问题就是对相应的下层理论或下层认识本身的“前提或根据”的反思性发问。因此,“元某某学”就是关于“某某学”自身的各种前提或根据的反思性学问。
“元某某学”作为“某某学”自身的各种前提预设的反思性学问,类似于人的自我认识。
认识既包括认识到什么(认识的内容),又包括对什么(认识的对象)的认识。只有当认识建立在至少两种活动的基础上,才能把“认识的内容”与“认识的对象”区分开。而最初发生的认识往往只建立在一种活动的基础上,因而往往不能把“认识到什么”与“对什么认识”这两方面区分开。
能区分开认识的内容与认识的对象还不等于能形成自我认识。只有当认识的主体能把自身对象化,该主体才会有自我认识。而只有当认识的主体既能把自身所占据的时空位置区分为不同的时空位置(从而能把处在不同位置上的自身区分为不同的方面),又能通过记忆与联想把不同的时空位置联系起来认作统一的时空位置(从而能把处在不同位置上的自身的不同方面都统一为“完整的我”的方面),才可能把自身对象化,也才能形成自我认识。
这也就是说,只有当认识的主体成熟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自我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一门学问的元理论的发展水平标志着这门学问的成熟水平或成熟程度。
2.两种类型的元理论、元学问
“元某某学”或“某某学的元理论”作为超越“某某学”的上层反思性学问,所反思的前提预设或上层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某某学”所研究的内容的前提预设;二是整个“某某学”本身作为一门学问的前提预设。与这两方面的前提预设相对应,“元某某学”或“某某学的元理论”也就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关于“某某学”所研究的内容的;二是关于“某某学”本身的,或者说是关于“某某学”的学科性的。
(1)第一种类型的元理论、元学问
第一种类型的元理论、元学问作为“对有关的理论或学问所研究的内容的上一层次考察”,主要是对一种理论、一门学问中只使用(或只承认、只预设)而不考察,因而超出了或不仅仅属于“该理论或学问的研究领域”的前提性“概念(或术语)、命题(或语句)、结构”的考察。例如,当用“规范”来说明“道德”与“法律”时,“规范”就是一个只被使用、不被说明的概念或术语;因此,对“一般规范”的说明,相对于运用“规范”来说明“道德”与“法律”,就是一种内容方面的元说明。
通常所说的“元伦理学”就是一门内容方面的元学问,它考察的是“规范伦理学”与“描述伦理学”中只使用不考察的前提性概念(或术语)与命题(或语句)以及相应的结构。“形而上学”作为元学科也是一门内容方面的元学科,它考察的是所有自然科学(“metaphysics”中“physics”是指整个自然科学)都会用到的前提性概念(或术语)与命题(或语句)以及相应的结构。因此,如果可以把元学科看作哲学学科的话,那么严格说来,只有内容方面的元学科才能成为哲学学科。
一种理论、一门学问在内容上有多少种前提预设,就有多少种内容方面的元理论,或者说,它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就会有多少方面。
在对某学科中只使用、不考察的前提性内容加以考察时,可能又会出现或引入另外一些只使用不考察的内容,因此,学科内容方面的元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例如,相对于“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怎么才算‘是什么’”就是一个上一层次的元问题;而“什么是‘怎么才算’”又是更高一层的元问题。又如,相对于用“规范”来说明道德与法律(即道德与法律都可以被看作规范)来说,对“一般规范”的说明是上一层次的元说明;而由于“规范”是一种“规定”,是对人的行为的规定,而且是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无意识的规定,因此,相对于用“规定”来说明“规范”来说,对“一般规定”的说明又是更上一层的元说明。
虽然内容方面的元说明可以不止一个层次,但层次并不是无限多的;也就是说,内容方面的元说明不会陷入无穷追溯。如果层层深入的元说明达到了出现循环的层次,那就意味着达到了最高的层次,即对这一层次的内容的说明不会再引入更高层次的内容,或者说不会再出现更高层次的元说明。
在什么情况下,对某内容的说明一定会出现循环呢?只有当某内容本身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对它的说明才一定会出现循环。这是因为,如果某内容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那就一定既适用于说明它自身,也适用于说明那些用来说明它的内容,即对“它本身以及对它的说明”的说明都会用到它,从而用来说明它的那些内容在层次上并不比它本身高,并没有超越它本身所属的层次。例如,由于“规定”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从而也必定既适用于说明“规定”本身,又适用于说明任何“用来说明‘规定’的那些内容”,因此对规定的说明会出现循环。从问题的角度看,如果某内容适用于发问所可能知的一切,那么对该内容本身的发问就也要用到该内容,这样就不会有比对它的发问更上位的元问题,或者说,用来对它进行发问的内容在层次上并不比它高。例如,“什么是‘怎么才算’”、“怎么才算‘什么是’”都是没有更上位问题的最高层次的元问题。
根据以上说明,如果某学问所研究的内容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那么该学问中“被用来进行说明的内容”在层次上就不会比“被说明的内容”高,该学问中就不会有只被用来说明而本身不能在该学问中被说明的内容。这样一来,该学问就不会有内容方面的元学问。换言之,如果某内容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那么对“该内容”的说明与对“用来进行说明的内容”的说明就都属于同一层次或同一门学问。不仅如此,如果某学问所研究的内容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那么该学问就会“因其内容不可超越”而成为一切学问在内容方面的最高层次的元学问,或者说,成为一切理论在内容方面的最高层次的元理论,并因此也成为“包括元哲学或哲学元理论在内的一切元学问或元理论”在内容方面的最高层次的元学问或元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作为“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形式化思辨考察”就是这样一门学问。也许正因为如此,考察所可能知的一切共有、固有、必有规定或规律的哲学基础理论才能被正当地称作“metaphysics”,即一切自然科学在内容方面的终极元理论。
与元理论相对应的是元语言。与内容方面的最高层次的元理论对应的元语言是在所有的学科中都通用的语言,也就是纯哲学语言;换言之,纯哲学或哲学基础理论所考察的就是在一切学科中都通用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
(2)第二种类型的元理论、元学问
第二种类型的元理论、元学问是从学科性的角度对有关的理论或学问本身的上一层次考察。原则上,有多少普遍的视角(例如逻辑学的视角、认识论的视角、语言学的视角、方法论的视角、价值论的视角)能用来考察、说明、处理一种理论、学说本身,或者说,理论、学说本身有多少种普遍的身份(例如,是一种认识,是一种理论,是一种语言)和规定(例如,有历史,有价值,有对错,有优劣),该理论、学说就有多少学科性前提,该理论、学说的“第二种类型的或学科性的”元理论也就有多少方面。例如,任何一门学问,作为自觉的、具有系统性的认识,都有自己的目标、任务、问题、方法,都有自己的构成要素、体系框架,都包含相应的论证或证明,也都包含相应的是非优劣、利弊得失的评价,并具有相应的功能或功用,还可能分成不同的部门或分支,还会有自己的产生与发展变化;作为与其他学问不同的特定学问,又都有自身的学科特征或判别标准,有与其他学问的区别与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学科性的元理论所要考察研究的。
在一般情况下,第二种类型的或学科性的元理论会有两个层次:一是某一特定学科的学科性元理论。例如,数学的学科性元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性元理论。二是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即对元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学科性问题——例如,元理论的判定问题、类型问题,每一种类型的元理论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元理论与对象理论的关系问题,等等——的研究。
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应该适用于从学科性的角度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元理论(无论是内容方面的,还是学科方面的),从而也适用于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自身。因此,一般的学科性的元理论是最高层次的学科性的元理论,不能从学科性的角度对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再作出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说明。换言之,从学科性的角度对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本身的“进一步”的说明在层次上不会比“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本身”更高,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不会有超出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本身的学科性的内容,从学科性的角度“对一般的元理论本身的说明”与“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属于同一层次或同一门学问。
不能把认识论、逻辑学等等看作是上一层次的学科性的元理论,因为,认识论、逻辑学等学问是学科性元理论在内容方面的上一层次的元理论。
(3)两种类型的交叉
无论是第一种类型的元学问即“内容方面的元理论”,还是第二种类型的元学问即“学科方面的元理论”,两者都包含需要对方来研究的元问题。“内容方面的元理论”自身有学科问题,上面所说的“一般的学科性元理论”对内容方面的元理论也照样适用,也是一切内容方面的元理论本身的学科性元理论;“学科方面的元理论”也有内容方面的前提性问题,从而也有自己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
在通常情况下,某学科性元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方面的前提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该元理论与其对象理论所共有的;二是该元理论所独有的。前者如“包含”、“内容”、“一切”、“因为”、“所以”;后者如“学科”、“学问”、“理论”、“说明”。与内容方面的前提分成两类相对应,学科性元理论本身也有两种“内容方面的元理论”:第一种可以是包括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所有学科所共有的,第二种是学科性元理论所特有的。前面所讲的最高层次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就属于第一种。
这些学问的学科性元理论不必用这些学问本身来研究(除了认识论),这些学问的学科性元理论不是这些学问的应用性分支;而哲学的元理论要用哲学本身来研究,是哲学的应用性分支之一。
因为“学科性元理论”所考察、说明的只是相应的学说、理论,而不是自然物质,所以,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等所研究的内容通常不会构成其“学科性元理论”的内容方面的前提;或者说,这些学问的学科性元理论不会用这些学问本身来研究,这些学问的学科性元理论不是这些学问的应用性分支。但是,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的“学科性元理论”本身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有一部分就是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所考察的内容。例如,认识论的学科性的元理论在说明认识论本身就是一种认识时,会使用认识论中的术语;对这些术语的考察属于认识论的内容。又如,语言学的学科性的元理论在说明语言学本身的表达时,会使用语言学的术语;对这些术语的考察属于语言学的内容。再如,价值论的学科性的元理论在说明价值论作为一种学科的价值时,会使用价值论的术语;对这些术语的考察属于价值论的内容。因此,可以从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的角度考察研究“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的学科性元理论”,或者说,“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的学科性元理论”可以成为认识论、语言学、价值论等等的应用性分支。
也正因为如此,认识论、语言学、逻辑学、价值论等等既是相对于自身的元理论而言的对象理论,也是包括“自身的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许多学科或学问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
(三)元哲学只是第二种类型的元学问
如果一门学问所研究的内容适用于说明所可能知的一切,那么该学问就没有内容方面的上一层次,从而没有内容方面的元理论;而哲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在不加任何定语的情况下,笔者所讲的“哲学”是指“哲学基础理论”)。
哲学作为一种认识、理论、学问,同任何学问一样,也有自身的学科性前提,从而有学科性的元理论。但是,哲学作为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的共有、固有、必有规定或规律的学问,没有自己内容方面的前提,哲学不能把自己内容方面的前提推给别的学问,否则别的学问才是哲学。因此,与其他学问的元理论包括两种类型不同,元哲学或哲学元理论仅仅是“关于哲学这门学问本身”的学科性的元理论,即仅仅是哲学观,而不包括关于哲学内容的上一层次的学问,不包括哲学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这是“元哲学与其他元学问”或“哲学元理论与其他学问的元理论”的主要区别。
虽然哲学没有内容方面的元理论,但是哲学的“学科性的元理论或学科性的元哲学”却有内容方面的元理论。同一切学科性元理论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一样,哲学的学科性元理论或哲学观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也包括两类。哲学基础理论因为考察“包括哲学的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一切学问”在内容方面的共同的终极前提,因而成为“包括哲学的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一切学问”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而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等等则因为考察“包括它们的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一切学问”共同的认识、逻辑、方法等方面的前提性问题,因而成为“包括哲学的学科性元理论在内的一切学科性元理论”的另一类内容方面的元理论。
二、元哲学的困难与可能性
(一)关于“元哲学的困难之所在”的已有看法
“维基百科”中有一个版本的“元哲学”词条专门设了一节讲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How is meta-philosophy possible)④。由于该词条把元哲学本身看作哲学,即关于哲学的哲学,因此主要从循环论证的角度来考虑关乎元哲学能否成立的困难。例如,元哲学作为哲学,当它要考察哲学的方法时,也只能用哲学的方法,即只能用哲学方法来考察哲学方法,否则就不是哲学的考察;因此,除非哲学方法对元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不成问题,元哲学的研究者才可能研究哲学方法;但是,如果哲学方法对元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不成问题,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研究。这也就是说,元哲学要么没有可能,要么没有必要。
国内学者俞吾金教授认为,作为哲学之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元哲学的“困难在于,当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时,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元哲学’。于是,人们又不得不再建立‘元元哲学’对不同类型的‘元哲学’作出研究;而当‘元元哲学’表现为不同的类型时,又得再建立‘元元元哲学’去研究‘元元哲学’。这样一来,人们就陷入了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的窘境中。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如此紧迫的问题现在反而被置于通常所理解的哲学之外,并变形为一种单纯的、无聊的、永远向前奔跑的语言游戏”⑤。与俞吾金教授的上述看法类似,元学问作为前提性学问,如果它本身也有前提,那么相对于“对它本身的前提的研究”来说,它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元学问。这样一来,如果可以一直追问前提,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元学问。
关于元哲学面临的困难的另一种可能的看法是,在哲学没有被完整地建立起来或提供出来之前,无法说清楚哲学是什么。因此,对任何元哲学问题的研究就都必须包含对全部哲学问题的研究。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在哲学之外或之上”专门、独立地研究哲学这门学问本身的元哲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哲学著作的“序言”与众不同时,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⑥
(二)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何以可能
无论是“维基百科”中的“元哲学”词条,还是俞吾金教授,或是黑格尔,都主张把“什么是哲学”之类的问题放在哲学之内而不是之外或之上来处理,并把这看作摆脱元哲学的上述困难的途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会把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本身也摆脱了;或者说,按照这一思路,只有取消了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对元哲学问题的研究才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即使把“什么是哲学”之类的问题放到哲学之中去处理,即使不把这类问题叫做元哲学问题,即使不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叫做元哲学,由于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在内容的层次或类型上不同于哲学的其他部分,因此情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并不会消除原来被认为的困难,或者借用俞吾金教授的说法,这样做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游戏”。例如,如果前面所讲的元哲学在考察哲学的方法时所遇到的困难能够成立,那么即使在哲学之内来考察哲学的方法,这一困难也照样存在。又如,如果因为有可能出现对“什么是哲学”这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使元哲学陷入所谓“‘恶无限’的窘境”,那么即使把这类问题放到哲学之中去考察,由于考察这类问题的哲学本身有可能不同,因此仍然有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不同类型的看法,从而仍然不能避免“‘恶无限’的窘境”。更何况,把对“什么是哲学”之类的问题的“专门明确的回答、处理”分为哲学之中的与哲学之外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待澄清和证明的假设。
实际上,前面所列举的元哲学可能面临的几种困难都并不足以否定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
1.元哲学因不同于哲学而可能
前述“元哲学要么没有可能,要么没有必要”这一困难的提出,事先设定了“元哲学本身直接就是哲学”。但是,元哲学并不直接就是哲学。
元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就是“元学问与对象学问”或“元理论与对象理论”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元学问与对象学问不在同一层次,不属于同一范畴,因此,元学问不同于或不是对象学问。例如,元生物学不是生物学,元经济学不是经济学,“怎么才算生物学”、“怎么才算经济学”这样的元生物学、元经济学问题本身不是生物学问题、经济学问题。同理,对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本身的研究也不同于对哲学这门学问所研究的内容的研究。元哲学或哲学元理论是对哲学这门学问的研究,是关于哲学这门学问的学问;而不是对哲学这门学问所研究的内容的研究,不是关于哲学所研究的内容的学问,“怎么才算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本身不是哲学问题。如果说哲学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的学问,那么元哲学则仅仅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哲学的,而不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的。在这一意义上,元哲学不同于哲学,或者说,元哲学不是哲学,更不是第一哲学。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元哲学仅仅是对哲学这门学问的考察,而不是对所可能知的一切的考察,因而元哲学不同于哲学。但是从研究的方式来看,元哲学对哲学本身的考察可以是描述的、历史的、实证的,也可以是思辨的、哲学的。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哲学同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任何对象一样,可以成为哲学的一种应用性分支,可以成为一种部门哲学。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元哲学是关于哲学的哲学。这也就是说,元哲学可以在哲学的应用性分支的意义上被看作哲学——对一切可能的哲学的思辨考察。
但是,元哲学作为哲学的一种应用性分支,与哲学的所有其他分支——包括哲学基础理论——有一重要的不同。除了元哲学以外的哲学的所有分支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超出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理论的哲学本身”的问题,即哲学的所有其他分支研究的对象都超出了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理论的哲学本身,而元哲学却不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超出哲学的问题,而是研究“哲学的角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
元理论与对象理论(或元学科与对象学科)也可以因为相连续,而被置于同一学科领域。某学科的“内容方面的元理论”因为研究的是某学科内容方面的前提而与某学科连续,而成为某学科领域的一部分;某学科的“学科性元理论”因为“研究与所研究具有对应一致性(即什么样的研究与研究什么对应一致)”而与某学科连续,而成为某学科领域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在这一意义上,把元哲学看作整个哲学领域的一部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元哲学本身直接就是哲学”。
另外,元哲学即使作为哲学的自我反思,也不同于被反思的哲学本身。例如,在哲学研究中被实际运用的方法与被反思出来的方法未必是一样的,水平也可能会不同;这就好像在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中自发地起作用的哲学和他自己或别人自觉反思或总结出来的哲学“并不一定相同”一样。
黑格尔曾经批评康德对认识的先天形式、先天条件或前提的考察(洛克也作过类似的考察)。在黑格尔看来,认识的形式和条件永远无法从认识中完全分离出来,永远超不出认识(这类似于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看法),对认识的形式和条件的考察本身就是认识,在认识之上、之外考察认识的形式和条件无异于游泳而又不下水。⑦黑格尔的这一看法能否成为对“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之不可能”的辩护呢?恐怕也不行。没有人会否认“对认识的考察、说明本身就是认识”,因为这可以说是自明的;但是对哲学的考察、说明却未必是哲学。因此,不能超越认识去考察认识,并不意味着不能超越哲学去考察哲学。更何况,就“对认识本身的考察”与“被考察的认识”在层次和类型上都有区别来说,对认识本身的考察也可以算是对认识的一种超越。
根据以上考察,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之所以可能,主要在于元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在于元哲学的研究内容不同于哲学的研究内容,即元哲学因为与哲学不同而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即使把元哲学看作哲学的一个部门或分支,也不同于最能代表哲学本身的哲学基础理论。
2.元哲学的研究并不必然导致“恶无限”
由“不断地出现不同类型的元哲学”而导致的“恶无限”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如果从可能性的角度看问题,那就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同类型的元哲学不会一直不断地出现,也许到了某一层次就不再继续出现不同类型的元哲学;这样一来,原先设想的困难也就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出现不同类型的元哲学并不必然导致“恶无限”。即使永远不断地一直有不同类型的元哲学出现,那也不能因此就一定得放弃或中止元哲学的研究,或把元哲学的研究认作“无聊的……语言游戏”;恰恰相反,正因为在元哲学所研究的前提问题上有分歧,才需要去研究更高一层的前提,否则就不能有效地交流、对话。
由于作为前提性考察的元哲学本身也可能包含所预设的前提,因此,即使没有出现不同类型的元哲学,也照样可以设想对前提的无穷追溯这种可能性。但是,正如笔者在“第一种类型的元学问”中所论述的,内容方面的元说明不会陷入无穷追溯。退一步说,即使对前提的追溯是无穷尽的,也不能因此认为元哲学不成立。实际上,至少绝大部分学科都不能证明它们的研究是可以穷尽的;大概不会有人因此认为这些学科不能成立,就如同不大会有人因为“不能证明认识可以穷尽”而主张放弃认识一样。
黑格尔式的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元哲学的困难(即在哲学没有被完整地提供出来之前,无法说清楚哲学是什么)类似于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困难。但这一困难并不是元哲学所特有的,而是对所有的理论都存在。任何理论的起点都包含无法由起点本身说清楚的预设。即使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起点——“being”,其中也预设着为什么要从“being”开始的理由。而当要说明为什么要从“being”开始时,就又意味着从“为什么”开始,而非从“being”开始。不仅如此,对“为什么从‘being’开始”的说明也会包含相应的预设。尽管无论讲什么都无法在所讲的内容完成之前完全讲清楚,但又都可以先在一定程度上讲清楚一些。因此,不要因为不能一下子完全讲清楚就认为完全不能讲。
最后再指出一点,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或者论证元哲学不可能”,这种谈论或论证本身就属于元哲学,从而本身就表明了元哲学的存在。
注释:
①参见http://www.ebroadcast.com.au/lookup/encyclopedia/me/Meta-Philosophy.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ta-philosophy; http://www.indopedia.org/Meta-philosophy.html
②Micah Newman,A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http://www.upsaid.com/micahnewman/philosophy.html
③参见http://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aims.asp?ref=0026-1068&site=1
④参见http://www.indopedia.org/Meta-philosophy.html
⑤俞吾金:《第一哲学与哲学的第一问题——兼论哲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态度”》,载《哲学门》第2卷(2001)第1册,http://www.phil.pku.edu.cn/zxm/show.php?id=62
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⑦黑格尔:《小逻辑》,第50、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