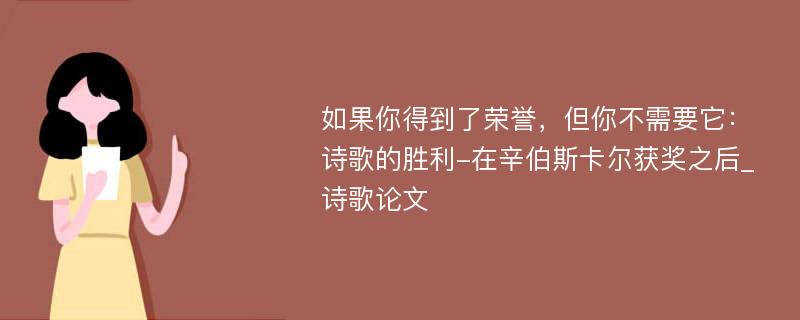
得到了荣誉但无需道如何:诗歌的胜利——席姆博尔斯卡获奖之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卡论文,诗歌论文,得到了论文,博尔论文,荣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有人作过最粗略、最谨慎的预测:鉴于1995年已有爱尔兰诗人希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1996年的获奖者起码该是位小说家。然而,评选结果又一次出人意料。
1996年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席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显克维支(1905)、莱蒙特(1924)、米沃什(1980)之后,第四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作家。波兰又一次为世界瞩目。评委会的先生们评价席姆博尔斯卡的作品是“绝对精确的反讽,融入了个人和历史的经历,使历史学与生物学的氛围表现在人类现实的琐碎片段中”。他们显然感到了语言的苍白和局限,索性借助于音乐词汇来称赞席姆博尔斯卡,誉她为“诗坛莫扎特”,其作品以“流畅的诗句和日常意象展现了质朴之中所蕴含的优雅和深刻”,有时还具有“贝多芬式的剧烈”。
当这一消息由斯德哥尔摩传到英、美等英语国家时,绝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席姆博尔斯卡这个名字。惊讶之余,他们急急忙忙打开电脑寻找有关女诗人的材料,然而能够找到的材料实在寥寥无几:二、三本薄薄的英文版诗集以及二、三篇比较像样的评论性文章。这有点类似于1984年捷克诗人塞弗尔特获奖时的情形。有报道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台原本已安排专人为诺贝尔文学奖编制一个节目,但在听到评选结果后,取消了这一计划。向来自信的美国人感到措手不及,不得不为自己的狼狈寻找借口,电台有关人员在解释此事时说:“获奖者在美国没什么名气。况且是诗歌,又是波兰诗歌,谁也不会在乎的。”
这真像席姆博尔斯卡在诗作《诗朗诵》中所描绘的那样:
十二人在屋里,八个座位空着——
时间已到,该开始这一文化活动了。
一半人进来是因为天下起了雨。
另一半人全是亲戚。哦,缪斯。
幸好,在席姆博尔斯卡的祖国,诗神缪斯尚未受到如此的冷落。女诗人的获奖在波兰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比1980年得知另一位波兰诗人米沃什获奖时,表现出了更大的激动和欢欣。毕竟米沃什长期旅居海外,而席姆博尔斯卡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祖国。几乎所有的报刊、电视、电台都以显著方式传播着这一喜讯。就连持续不断的政治争论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在参议院,当议长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打破程序,宣布这一消息时,正在进行的有关堕胎问题的激烈争论也一下子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全体议员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来不苟言笑的波兰财政部部长也用特殊方式向女诗人表示了敬意:他为席姆博尔斯卡送上了21朵红玫瑰并答应免收女诗人获奖该缴的税。
旅居美国的波兰大诗人米沃什在加州伯克利的寓所接受采访时说,席姆博尔斯卡的获奖标志着,“20世纪波兰诗歌的胜利”,“一个国家有两位诗人获奖,太好了。”
波兰有理由骄傲。
维斯瓦娃·席姆博尔斯卡1923年7月2日出生于波兹南省库尔尼克的布宁村,1931年她随全家移居克拉科夫。德国占领期间,她以秘密方式上完地下中学。以后她在克拉科夫雅盖沃大学攻读波兰语言文学和社会学。1953年至1981年在《文学生活》周刊任诗歌编辑和专栏作家。曾有过两次婚姻:同诗人亚当·沃迪克的婚姻以失败告终。以后又同小说家科尔内尔·菲利波维奇结成忠实的伴侣。
尚在大学期间,席姆博尔斯卡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45年,她在《波兰日报》的青年副刊上发表第一首诗歌《寻找话语》。1948年曾写出一本描写二战经历的诗集,但由于“手法晦涩难懂,主题脱离现实”,未能通过审查。1952年,她出版了诗集《我们为什么活着》。收入的大多是些迎合当时形势的政治诗。出版后,反应一般。有评论称之为“以室内乐手法所作的宣传鼓动”。公允地说,席姆博尔斯卡从创作之始就显露出了一定的才华,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及个人诗歌观念的模糊,她的才华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一些评论家替她辩解:“如果她的开端未显示出多大希望的话,那么,该受责备的是历史,而不是她。”女诗人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初期的创作,在以后的诗选中,她没有收入过一首这一阶段的作品。她解释自己最初的失败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那时试图爱人类而不是人。”
经过几年的沉静之后,她的第二本诗集《询问自己》于1954年与读者见面。与第一本诗集相比,她的诗风有较大的改变,个人风格开始显露。诗集标题“询问自己”就象征性地表明了作者“由外向内”的转向:以前的“回答”变成了现在的“询问”;以前的“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从内容上看,政治标签式题材相对减少,而爱情及其他传统抒情题材得到重视。形式上,作者尝试采用独白、对话、反讽等一些朴实灵活的手法。“询问”是整部诗集的主旋律。正是在“询问”中,席姆博尔斯卡找到了一条通向深刻广博的路子。诗集中的两首抒情诗《钥匙》和《一见钟情》格外受人喜爱。《询问自己》为女诗人赢得了第一个文学奖。
1957年诗集《呼唤雪人》出版。这是女诗人诗歌创作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她开始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爱情等主题在她的作品中出现。作者从一个自信的回答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执著的询问者和呼唤者。在《一次未进行的喜马拉雅山探险》中,诗人的声音在空旷中回荡,清晰而又幽远:
雪人,并非罪恶,
才是这里唯一的可能。
雪人,并非每一句话语
都是死亡判决。
……
雪人,我们拥有莎士比亚。
雪人,我们演奏小提琴。
雪人,黄昏时分
我们点亮灯盏。
呼唤雪人,诗人实际上在呼唤一个更为纯真的世界;呼唤雪人,诗人实际上在寻求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席姆博尔斯卡本人在内的许多波兰文学界人士都把《呼唤雪人》当作她诗歌创作的真正开端。在之后出版的《盐》(1961)、《一百个欣慰》(1967)、《以防万一》(1972)、《巨大的数字》(1976)、《桥上的人》(1986)、《结局与开端》(1993)等六本诗集中,她又进一步拓宽诗歌主题,不断变化表现手法,逐渐使语言趋向于朴实、简明、直接和幽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用米沃什的话说,她的诗集是“一本比一本写得更好”。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们正是为了她1957年之后的创作授予她诺贝尔文学奖。
席姆博尔斯卡常常在诗作中针对生命、时间、死亡、人类境况及艺术同世界的关系等等提出一些“天真朴素的”问题。她在诗作《世纪的没落》中写道:
“我们该如何活着?”有人在信中问我
我本打算向他提出
同样的问题。
一次又一次,
正如上方可以看到,
最最紧迫的问题
是那些天真的问题。
在女诗人看来,没有任何问题像那些“天真朴素的”问题更接近本质,更意味深长。她的诗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她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双重意义:哲学意义和句法意义。而这些问题无论对人类还是个人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面对一张照片,女诗人指出这无论如何不是一张清白的照片,“因为这是人服从时间但又不承认时间”的例证;在描绘人类境况的尴尬时,她又间接地询问:“我们能阻挡时间吗”?(《桥上的人》)她赞美自己的姐姐“从不写诗”,羡慕她“练就一套相当出色的口语散文”时,似乎想告诉读者:在某种情形下,朴实、宁静、轻松的生活比诸艺术更为自然,更为诱人。于是,一个问题也由此产生:艺术能完全反映和代替现实吗?(《赞美我的姐姐》)应该说,能提出一些看似天真实质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需要大智大慧的。正是在一个个这样的问题中,世界的复杂性被诗人以锐利的笔锋呈现出来。
阅读席姆博尔斯卡,我们不难发现她的细腻、机智和“绝妙的幽默感”。同时,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到诗人内心的某种悲哀、怀恋,对西方价值危机和现代文明的恐惧。在《恐怖分子,他在观望》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勾画出一个“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然而,不同于某些西方诗人的是,席姆博尔斯卡始终认为,即便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仍然可以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高贵地活着。从“写作的快乐”中,从“维护的力量”中,从“凡人的复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普通的日常琐事对诗人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一座桥,一幅画,一个商场,一只猫,一部电影,一把钥匙等等都有可能激发起她的灵感。她极善于从这些日常琐事中发掘一些独特的意义。她会从一只猫想到人最后的孤独,从一幅画看到世界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从垃圾发现朴素的可贵,从衣衫寻找真正的永恒。她的许多作品常常以一段日常对话或一个简单的故事为线索,在不知不觉中提出问题,于平淡中给人一点启示:她似乎掌握一种诀窍:用朴素描绘复杂,用平凡表现深刻。
席姆博尔斯卡和她的同代人鲁热维奇及赫贝特一起被波兰文学界誉为波兰国内诗坛三大代表。三位诗人,席姆博尔斯卡的作品最少,名气也最小。有人作过统计,近20年来,她平均每隔半年才抛出两、三首新作。至今为止,总共才发表了二百来首诗。她可能是有意识地少写,因为她一向对诗歌创作要求极高。“寻求魔幻的声音,感觉和思想所构成的和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天才,需要劳动,需要思想的不停运转,需要心灵的贴近和远离,同时也需要某种从容和淡泊。每个作家实际上都有自己特定的节奏。而席姆博尔斯卡的节奏显然确保了她的诗歌的质量。翻开她近20年出版的诗集,有行家惊叹:“每首都是精品。”除去诗歌创作外,席姆博尔斯卡还写过几个短篇小说,但从未发表;她也译过一些法文诗;另外,她还写了130多篇书评,涉及历史、心理学、绘画、音乐、动物学、文学、烹饪等诸多领域。
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结果公布时,席姆博尔斯卡正在波兰南方山城扎科帕恩作家疗养院度假。在记者招待会上她谈到获奖感受时说:“这意味着幸福和责任。从今以后,我将不得不成为一个官方人士,这可是我不喜欢的,这违反我的本性。”追求淡泊宁静的席姆博尔斯卡一直居住在克拉科夫中心一套简朴的两居室里。她喜欢离群索居,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极少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只接受过一两次严格意义上的采访。她不太愿意谈论自己,不得不谈论时,也常常只是三言两语。人们有时可以看见她穿着旧衣衫在四处溜达。但她很乐意和不多的几个朋友相聚,吃着鲱鱼、喝着伏特加,抽着雪茄,谈论一些轻松话题。除了钓鱼外,她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收集旧名信片。对此,她解释说:“废物从不奢望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她之所以没能像她的几位同代作家那样得到外国广泛的注意,同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恐怕有着直接的关联。她的诗作《写份履历》为她的这种举止作了最好的说明:
不管生命长短如何
履历最好保持简短,
事实必须精炼清晰。
风景应由地址取代,
模糊的记忆得让位于可靠的日期。
所有的爱情,只提婚姻;
所有的孩子,只提那些出生。
参加了什么团体,但不必说理由,
得到了什么荣誉,但无需道如何。
“艺术家就是作品,作品就是艺术家。”这是席姆博尔斯卡诗中的主题,也是她的信念。她相信诗歌便是一切。
诺贝尔文学奖给席姆博尔斯卡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诗人的创作和生活。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尚无人知晓。在和米沃什通话时,席姆博尔斯卡说:“我可没有防护机制。我是个平民。最最难办的事就是写演讲词了。我得写上一个月。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但我会讲讲您。”据说,为了躲开各种干扰,席姆博尔斯卡已经搬到一个更为偏僻的地方,谁也无法找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