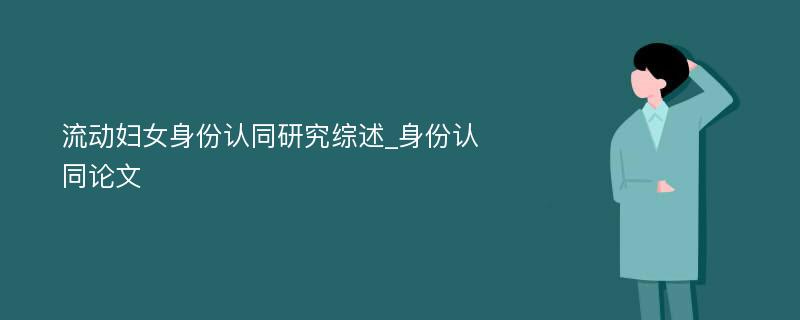
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意义
身份/认同研究是文化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而以往身份/认同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尽管将流动人口/农民工作为一个焦点,但缺少对女性流动者的特别关注,或者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王春光,2001;王毅杰、倪云鸽,2005;潘泽泉,2007;等)。
事实上,女性的流动人数庞大且正在不断增长。诚然,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流动在一些方面意味着共享的经验,比如:在制度层面,城乡二元体制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流动者最多成为半/准公民;在经济层面上,无论男女流动者往往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在文化层面,流动意味着从熟人社会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尤其是这个陌生人社会是一个将他们/她们视作“他者”的社会,使他们/她们面临城里人-农村人的认同困境(王春光,2001,2006;魏晨,2006;王毅杰、高燕,2004;陈映芳,2005;吴玉军、宁克平,2007);流动也意味着传统农业社区内的一些价值观的丧失、无效等。
但是,性别身份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流动中又面临着不同的经验。对流动女性来说,迁移还意味着从传统父权制社会进入到一个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甚至合谋的社会。流动可能使她们面临更多挑战,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对性别关系和女性的主体性带来影响。因此,关注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既可以扩展我们对流动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和扩展身份/认同研究,对于从多方面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流动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文中所指的流动女性特指因就业、婚姻等原因由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而往往未能得到城市市民身份的女性;身份认同的定义很多,这里是指个体对自身社会身份(如阶级、性别等)和自我认同(心理层面)的感知情况。
本文将以已有对流动女性的研究进行文献分析,考察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是以什么样的视角解释流动对于女性的意义的?其不同的学术立场产生了怎样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不足?
二、研究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四种进路
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种进路:一是以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二是以对父权制的分析为主,探讨流动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三是心理层面的分析,探讨流动经验对女性的心理效应和女性的主体性;四是强调多元视角,探讨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交叉性和矛盾性。
(一)资本主义与身份认同
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对流动女性来说,有着与男性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女性被看作是更廉价、顺从的劳动力,受到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和性本身被当作可以运作、买卖的商品。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中,“阶级”一直是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身份”,其他所有社会身份都通过这个范畴加以调和。以上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使得不少劳动问题的学者侧重于考察流动女性的阶级认同和阶层认同。吕鹏对30年来西方社会学相关研究的综述显示,自女性主义介入到社会分层研究中以来,女性的阶级位置与阶级认同,一直是该领域内争论得最为激烈的议题(2007)。
中国流动女性是不是形成了作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身份认同?已有研究持否定态度。潘毅认为,打工妹的阶级身份认同是模糊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打工阶级。她将打工女性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归因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既促使又瓦解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与户籍制度的存在密切相关。
不过,一些研究显示流动女性存在朴素的阶级意识。这正如李静君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class capacity)在市场发展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但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在全国都明显地尖锐化。”潘毅认为“打工妹”代表的是一种“深嵌于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与性别关系之中的次等劳动身份认同”(高景柱,2007);杰华的研究表明,“在另一些情境下,她们(指打工妹)又将自己认同于跟‘老板’对立的工人”(2006:225)。
李春玲(2004)、周玉(2006)等人探讨了社会阶层、性别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不过,她们的研究对象并不特别关涉流动打工者这一范畴。李若建比较了流动女性形成的工人与非流动女工之间的差别,认为女工形成了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2004)。
由于社会性别分工,流动女性往往从事服务业等被看成“适合女性”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价值往往被贬低。一些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则面临文化中被污名的特殊困境,这种认同还容易被她们内化。
(二)父权制与身份认同
在父权制下,流动带给女性的特殊变化包括:一,流动女性从私领域进入了公领域。女性流动者在进入城市之前,活动领域往往被限制在家庭这个私领域,被分配以管理家庭等再生产任务。而男性流动者在流出之前,往往已经具有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经验;二,流动意味着在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要求和女性面临的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发展需求、价值观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时也意味着性别关系的变化;三,流动女性在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之时,同时便进入了当地的婚姻市场,而由于传统男强女弱的婚配观,绝大多数流动男性不会有此境遇。这些变化使流动女性在形成了与男性不同的经验,对女性的性别认同、婚姻/家庭、性别关系等产生了影响。
在这个研究进路下,一些研究者关注在流动女性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性别身份方面,研究者有争议。潘毅认为流动女性的性别认同是非常清晰的,而杰华则不认同这一点。潘毅认为,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有关(高景柱,2007)。杰华持相反意见,认为她访谈的流动女性“从不跟这个城市的其他流动女性认同,并且当她们谈及她们面临的困难时,更多的是作为农民工和外地人的困难,而不是作为女人的困难。……她们很少讨论在薪水和工作条件方面男性民工与女性之间的差异,也不将性别确认为她们经验中的一个要素。……在打工女性有关她们的认同和经验的表述中,以性别为基础的明确认同只起了非常微小的作用。”(2006:224-225)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关注的是婚姻、家庭,或者说,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与其身份认同的关系。流动使婚姻、家庭对两性具有不同的意义,对性别认同和角色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流动男性来说,婚姻“标志着他作为所在社区完全成员的身份获得”,意味着将农村老家作为他的认同以及所依据的持续关系和责任的主要地方。而对女人来说,婚姻意味着与原生家庭的断裂和认同的消失,特别是劳动的性别分工意味着农村女性婚后将以家庭这个私领域为考虑重点,意味着个人的消失(杰华,2006:161-162)。潘毅等的研究则考察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结婚生育、承担性别角色的要求带给单身打工女的困境,“打工妹是城市里的匆匆过客,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得不离开城市而回到农村结婚,转而承担母亲的角色”(高景柱,2007)。在这种要求下,打工女性的职业生涯以及她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所有向往都往往意味着中断。一些女性延迟返乡的时间,则面临大龄单身的污名和失嫁危机。乐观的研究者则认为流动赋予了女性对人生的重新规划,一些流动女性抗拒传统的父权制下的婚姻生活,生成了个人主义倾向(杰华,2006)。但另外的研究则表明,女性在流动地和城市生活中获得的积极性,在返乡后不久即被原先的社会环境所同化(郑真真、解振明,2004)。
有的研究者关注城乡差别对流动女性婚姻的影响。对未婚迁移妇女来说,进入城市或其他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进入了当地的婚姻市场。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女性嫁入流入地往往被看作“上”嫁,且往往只能嫁给当地条件较差的男性。谭琳等人考察了移民媳妇的作为当地社区生活和作为婆家家庭生活的“双重外来者”的身份(谭琳、苏珊·萧特、刘惠,2003:75-83)。户籍制度往往给她们的婚育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使她们感受到歧视(谢丽华,2002)。
传统的父权制家庭文化对流动女性的认同也有深刻的影响。杰华的研究显示女儿身份(孝顺女儿和叛逆女儿)影响了流动女性的打工决定和工作中的认同度、满足感(2006)。李静君则认为“女工的家庭主义,家庭职责界定了她们的身份与利益,而厂方控制策略也得从满足她们的家庭主义入手”。
(三)身份认同的心理效应和流动女性的主体性
作为打工者和女性,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给她们带来了哪些心理感受呢?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做了研究。
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性别认同对女性的影响,认为认同这些身份“反而会给女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或矛盾的心理体验,而不是健康快乐的心理体验。例如自卑、边缘、不自信、厌弃自身的女性性别、无奈、放弃、自足,向往、高估而不是歧视男性特征和性别身份”(孟宪范,2004:158)。周玉认为,传统性别文化对不同性别价值取向和阶层意识的影响仍未消解,男权主义的性别文化及其相应的性别制度依然是导致女性较低自我评价、较弱成就动机和职业发展限制的根源之一(2006)。不少对流动女性的研究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关注歧视对他们的心理伤害(谢丽华,2002;杰华,2006;等)。
制度性要素及主流话语限制了流动女性的积极自我认同,然而,流动女性的认同并非都是负面的。主体性、反抗意识仍然可能在父权制的歧视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中生成出来。一些研究者认为“迁移流动打破了农村妇女单一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使她们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经历。她们积累着对城市生活的正面和负面感受和经验,并融进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建构”(姜秀花,2004)。郑真真等人关于流动女性的研究也显示了这一点(2004)。
潘毅认为:“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们正在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着自身的生活道路。”在与社会的外力塑造相抗衡的过程中,打工妹群体逐渐确立了“自我意识”:“身为女性、身为农民、身为外出打工者,打工妹是生活在变动社会中的一个游离的主体,她们的声音决不会轻易被任何主导话语(无论是知识话语还是政治话语)所湮没。”(2007)杰华也观察到了流动女性对主流话语的拒绝、改编和选择性使用。“她们同时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了改造,接受了其中一些含义和认同,排斥了另外一些。”有的与都市的话语建构联盟,有的则“试图为自己建构一种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06:245)。李静君认为“剥削同时带来反抗赋权的可能”。陈琼认为流动妇女在迁移到陌生人社会后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部分妇女能够在搬迁地通过自己的积极策略寻求自己的存在点,筹划自己的生活,尽管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有时候与政府设置的整套机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但她们能够在既定的框架内寻找并筹划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对正规机构、制度产生影响,从而使社会的权威资源出现有利于她们的重新配置”(2007)。谭琳等人的研究也考察了作为“双重外来者”的媳妇为适应环境所采取的各种策略(2003)。
(四)多元视角下的身份认同
当代多元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身份认同认为,任何有关女性差异或女性身份的声明都会掩盖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人种女性的差异(蒋欣欣,2006)。基于此,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往往将论述的焦点转向差异,突出女性身份/认同的多样化和异质性。
在这一点上,已有研究强调较多的是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关联。在国外研究中,安娜·珀赖特(Anna Pollert)认为1970年代早期工作于布里斯托尔烟草工厂的女工们表现出矛盾的自我印象和矛盾的阶级意识,而这源自她们处于社会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结构中的同一位置,这一位置被隐含在统治阶级霸权意识形态中的父权制假设所强化(戈登·马歇尔,2007)。和她一样,李静君强调性别与阶级之间的交叉性,认为劳资的阶级关系与女工的性别利益和身份认同互相扣连:“性别作为一种权力过程,它可有多样的定义,与阶级之间亦有相互构成的关系。性别不但引致不同的经济收入,也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经验。”潘毅也指出流动女工在阶级认同和性别认同方面的二元结构性,即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共存。
一些研究关注更加多元的变量,如杰华认为,“中国农村打工女性在城市的认同和经验,受到性别、阶级、本地人外地人、城市的/农村的以及认同与划分的区域形式这些复杂因素的交叠影响。”(2006)陈琼也强调了认同的多元化,“移民妇女在搬迁地的身份关系及其背后的规则认同已经多元化,妇女身份认同的显著性程度与经济利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家庭出身等因素相关”(2007)。
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年龄与社会性别认同之间的关联。何明洁对在酒楼打工女性的研究中,用“性别化年龄”(指涉及年龄问题的性别建构)这一概念探讨性别与年龄如何成为女性农民工看待自己工作及处理劳资关系的认知基础和行动源泉。她认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义综合了文化传统的要求,通过“性别化年龄”来界定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角色并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期望和责任,使劳动者对劳动关系、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理解都配合不同年龄的女性角色而产生了分化。“性别化年龄”在劳动者中制造出了有差异的社会类别,并且得到劳动者自己的认可和响应,使得资本对不同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打工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手段(2007)。潘毅认为,“打工妹”的“妹”意味着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况下的性别身份,还意味着年轻的女孩儿,它不仅标示出性别,而且还表明婚姻状况:与“姐”相比,“妹”意味着单身、未婚而且比较年轻(2005)。
本质来说,这些研究实质上是关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结合给女性带来的特殊影响。不过,在避免将任何分类范畴本质化的同时,也不应忽视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的提醒:要突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的重要性,避免在身份疆界中迷失了女权主义者的政治方向(1998)。
三、研究贡献与不足、挑战
关于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的研究,显示了具有不同关注视角、观察不同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如何不同地诠释了流动对女性的特殊意义。由于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同,她们的结论也往往不同。事实上,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两者共同型塑了流动女性对自己迁移、工作和生活的体验。
已有研究的贡献在于:这些研究关注了以往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被忽视的一群人,丰富了流动人口和身份认同研究;这些研究受女权主义关于身份认同、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讨论的影响,与其他有关农民工/流动人员的研究相比,更注意多元探讨和流动人口的主体性。
然而,已有研究仍面临不足和挑战:
一是缺乏性别比较。已有研究往往只是将流动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来研究其身份认同,而缺乏性别比较,这就降低了其贡献。
二是缺乏关于身份认同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研究。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流动的、是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不断变迁的(佟新,2002;魏峰,2006;王毅杰、高燕,2004;汪民安,2007)。而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所做的研究对此缺少关注。
三是已有研究仍有本质论之嫌,而将身份作为策略和位置/立场的视角有所欠缺。已有关于流动女性与身份认同的研究,仍沿袭已有的阶级、性别的分类框架,难免有将社会性别本质化之嫌。
四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对流动女性身份认同的关注缺乏设计严格的尤其是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使我们难以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此外,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已有研究还相当有限,不仅缺乏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统一定义,关于身份认同的动机、心理机制、影响等,也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同时,还缺少与西方前沿理论的对话,如分层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还是个人?“跨阶级家庭”中女性和男性的阶级认同有何差异与联系?这些讨论将扩展我们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