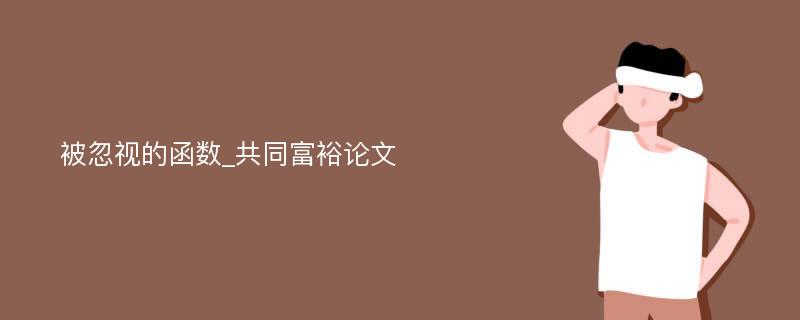
一个被忽视了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忽视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经济特区具有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了的功能,即共同富裕的“带动”功能;由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和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差异,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
关键词 经济特区,非均衡规律,劳动力价值
以往,当人们谈起中国特区的经济功能时,一般总是明确地讲到两点:第一,“改革”中的“排头兵”功能;第二,“开放”中的“窗口”功能。我认为还有第三个功能却被长期忽视了,那就是“走向共同富裕”中的“带动”功能。
但是,当一些人士面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速度,人们的富裕程度差距拉大的趋势和分析到特区高速发展中优惠政策因素时,尤其是当发现某些特殊政策又曾被某种经济犯罪所利用时,便产生了一种相反的结论:似乎正是特区的存在,才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才形成了对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从而违背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藉此,有人甚至建议:在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中应取消对特区的优惠政策,并以“产业倾斜”取代“地区倾斜”。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既否定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又无视了中国国情的根本特征。
本来,“共同富裕”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判断。应该说,这一点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的苦苦追求。无论是人民公社时的供给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破除的种种“资产阶级法权”,都由于实行大一统的平均主义“穷过渡”政策,而最终陷入某种乌托邦幻觉。再加上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终于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本来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舞台上却演出了一场普遍贫穷的悲剧。这段残酷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记取吗?
正是基于中国发生过“二十年停滞”,处在“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状态,邓小平才做出了石破天惊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判断〔1〕;也正是面对着以往这一条根本走不通的路,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才能在深刻地批判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潮的同时,力排众议、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创办中国经济特区的战略性决策。
虽然这一决策有可能首先使特区几百万人口富裕起来,但是邓小平的中心思想却一直是:“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那么,经过15年的发展,特区在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是否发挥了“带动”功能了呢?以深圳为例,请看基本事实:从财政的支付转移上看:(1)1988年后向中央、向省财政累计上交44.5亿元; 国家直接获得海关税、海关代征税以及铁路、 邮电、 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500亿元。(2)“前店后厂”方针使深圳向内地投资高达120亿元,超过了15年内地向深圳投资的总和。(3)外地打工者210万人,每年至少寄回60亿元;从具体支援上看,深圳对老少边穷地区设立“合作发展基金”,已经扶植120个项目,兴建110所希望学校等等。然而,这些耀眼的数字还远远不足以显示出特区“带动”功能中所独有的风采,只有确认特区的最大作用是贡献了一个新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创造了一种新精神——敢闯精神,敢于冲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唯书唯上的束缚,敢于超越自我,向更科学、更民主的方向前进,才算全部挖掘出特区对全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因为这两个根本无法用数字显示出来的巨大精神财富不仅充分验证了邓小平关于特区建设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又在不同程度上充实与发展了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仅就这两点看,它也给全国人民摆脱贫因带来极大的勇气与力量。这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特区人民的辛劳结晶。如果再联系到国际风云变幻的大背景,那么这一切又都向世人展示:倘若您要寻找“对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话,〔3 〕就请走到特区来!这不禁使我想起1963年刘少奇访问朝鲜对金日成说过一句话:只要你们把朝鲜建设好了,也就尽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少奇同志当时批驳那些高唱解放全人类,却只求别人援助,连建设自己家园都毫无兴趣的懒汉行为。〔4〕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特区“带动”功能的发挥是相当充分的。
其实,只要不在绝对平均主义内容上去理解“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就只应表示为社会财富总水平的提高和个人收入越过时代贫困线。它的对立面是在普遍贫穷基础上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而这一愿望的实现,又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仅不是某个一次性的行动,还必然是一种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这是因为不仅个量的贡献与相应的分配总是存在着差异,而且,总量的形成总是具有非均衡性。一句话,“共同富裕”的过程只能通过发展的非均衡性来实现,而且还是唯一的途径,这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结论。我感到,“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就是邓小平对于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所做的通俗表述。在这里,第一,作为过程,邓小平主张“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第二,作为结果,邓小平主张“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作为方法,邓小平主张“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第四,作为时间,邓小平主张“太早这样办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起码本世纪末以前不向你们开刀”;第五,作为方向,邓小平主张“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5〕请同志们看看, 这是一条多么清晰的思想轨迹!
显然,“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这个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和必要的前提。这是因为,在当时全国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内,在本来是全国最为落后地方搞特区、在中央政府又不可能给予更多资金情况下,如果再没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也就根本吸引不来外资,根本无钱搞什么特区的基础设施,特区也就根本无从发展,无论怎样“让”它富也根本富不起来。可见,特区的发展条件就既包括客观的地理、资源环境,也包括主观的特殊政策氛围。正是在这种优惠政策的激励下,中国才出现了深圳、浦东这样一片片神奇的土地。所以说,优惠政策就是特区发展的必要与充分的条件。
这种特殊政策之所以必须,可以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说明。那种含有充分自由市场竞争条件和靠价格信号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理论上“瓦尔拉均衡”,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就更不具备这种逻辑假设了。现实中所出现的却只有一种被政府调整后的非均衡。这既有体制因素(企业改革尚未完成,价格体系难以灵敏),更有自然因素(资源约束尤其是资本约束长期存在)。于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环境差异的国度里,某种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某种垄断就将长期存在,它将诱发某一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就反证了市场调节的某种失灵处和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政府调节的必要性。它要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资源配额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扭曲的匡正、对制度变型的引导,这既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又是对市场调节的必要补充,中国经济特区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谓的优惠政策就是中央政府的一种“逆调节”,它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时也不在一个时空里。正如自由、平等、博爱一样,公平竞争不仅是相对的,而且还是有条件的,这一点早在60年前的凯恩斯时代人们已经关注到了。
中央政府目前对发达地区“逆调节”的必要和将来“正调节”的极限,反映着非均衡经济规律中财富的创造性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不同的两大特征。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社会财富的产权主体,从而区别“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转移”不同性质。如果没有特区对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综合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便没有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总量也就不会被更多地创造出来,经济蛋糕也就不会做大。所以,特区的发达并不是财富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被后者掠夺剥削的结果,特区的发展过程不存在接受内地的输血和寻找政治与经济的租金。倘若取消了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也就自然失去资源配置优化组合的条件。到那时,即使把企业所得税恢复到80%甚至100%, 也会因企业大面积亏损而需要高额补贴,所以国家财政所追求并不应是什么比例关系,而是一个绝对额。在可能出现负税率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特区虽然仅收15%的企业所得税,但仍能获得稳定而真实的财政收入。
其次,我们必须确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从而区别“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实现”不同性质。毫无疑问,即使考虑到相对高的物价水平和对内地亲友的负担两个因素,特区的个人收入水平还是高于内地的,但是这种工资政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应当创造的正常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旧体制下,职工的工资太低,收入向国家倾斜,是利润对工资的侵蚀。所以现行特区的个人收入政策是对职工总体历史欠账的偿还,并不是什么恩赐,而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今天的调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惠”,而是对昨天失误的一种“纠正”,是劳动力价值的逐步实现,因为市场经济并不承认劳动力的“投入”,只承认劳动力的“实现”。正是特区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才能构成劳动力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特区经济的高效运行,才使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步入良性循环。由于产品卖得出去,钱又能收得回来,所以才有了正常收入的现实性。许多内地的职工虽然对产品也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可是或者由于产品没有销路,或者由于虽有销路但钱却无法收回来,所以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就较低,陷入了低收入——低效率的恶性循环怪圈,这也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而所谓“分配不公”,是指个人或凭特权或凭犯罪获得了资本收入、经营收入、劳动收入和合法福利收入以外的收入,特区实际收入的总体构成完全否定了这一点。而且在消费问题上,对于已经分配完毕的社会财富,即使降低一部分人的消费层次,也不会自动提高另一部分人的消费水平,因为市场经济已经不允许再无偿剥夺了。决不存在特区经济愈发展,非特区经济就愈下降的此消彼长的奇怪逻辑。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规律决定着“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过程,而个人劳动差异和与此相适应的收入差异又决定着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如果人为地去扭曲“共同富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那就不仅会大大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一定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进程。
当然,按照邓小平关于特区发展的战略布署,特区将来不仅不能少交税,而且还要多交税,即“到适当的时候,你们要向国家多做贡献”。这就是说,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优惠政策,中央政府将实行由“逆调节”转入“正调节”。但是这个“适当的时候”究竟是何时,邓小平界定为“起码到本世纪末”。我认为,这个时间表来源于两个因素:特区本身发展程度和全国能否达到了小康水平。所谓特区本身的发展程度,是指特区完全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旦取消了全部优惠政策也不至于受到伤筋动骨的损害,而且即使到那时,中央政府也不应取走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全部收入,而只应取走其中的一部分,否则将削弱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与解决地区间经济矛盾相适应,调节个人分配差距,尤其在解决严重分配不公时,一旦实行征收个人所得税制(九级累进)、征收遗产税制(10%—50%),也不至于降低广大居民生活的总水平。一句话,只有当特区从目前的“脆弱的繁荣”走进“坚实的繁荣”时,特殊政策才应取消。而选择这一时机的标准既不是什么美国200年前的公平竞争的宪法, 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上的美好愿望,而只能是邓小平在1992年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利国利民的三条标准。
如果今后我们把深圳定位为“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是“特大保税区”的话,那么它的特区性质就将永远存在下去。如果我们把深圳仅仅定位为一般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话,那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之日,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使命终结之时。今天,我们绝不应当再给这个仅仅出生15年的“城市孩子”赋予更加沉重的负担。虽然这个未成年孩子的生命也同样不可承受之轻,但他既不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也不可能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全能冠军”,更没有能力去充当救世主。也许,正是基于让这颗中国的新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对全国起更大的“带动”作用的考虑,江泽民总书记才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对“特区基本政策不变”的历史性决定。我们确信,在那些不变的“基本政策”中也就一定包括了本文所阐述的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搞平均主义”的这个“大政策”。
本文于1995年9月收到。
注释: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4〕转引自《人民日报》,1963年10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