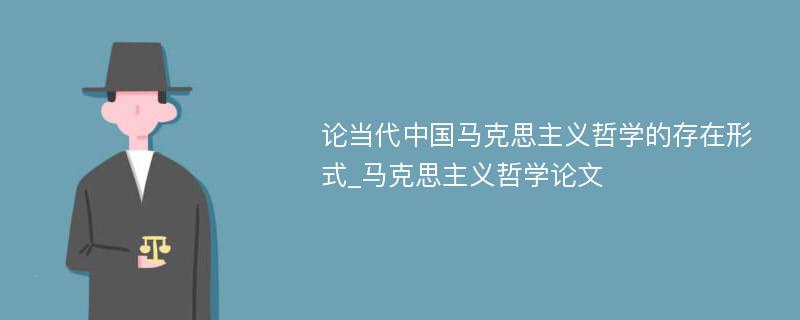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因实践主题、时代特征和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存在形态,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从哲学形态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历史发展的研究还仅仅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及各种存在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建构有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机制和体制,是有好处的。陆剑杰教授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下面简称陆文),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也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这里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陆剑杰教授,并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态
陆文第一部分的开始,谈到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处境,论及学术界对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和看法。他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由如下事实引发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者争来争去,却大多不理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者似乎都把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官方哲学’,而自己不是‘官’,所以‘官方哲学’与自己无关;更有甚者,是把这样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话语、实用理论。”笔者认为这段话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推敲。
首先是陆文的立论根据有问题,因为他所说的“事实”并不是事实。这几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确实进行过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陆文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的提法,恐怕是从那里套过来的。但这样的套用是不合适的,因为学术界并不存在这样的讨论。这几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一直在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但似乎没有听到什么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的观点,更不存在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既无学术性,又无独立性,是称不上‘哲学’”的观点”。
其次是所谓讨论的参与者“大多不理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己“无关”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实际状况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被排斥在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外,有相当多的一批学者在研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最近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的规模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就组织起了几百人的专家学者队伍,计划开展20多个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既积极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并努力使这二者联系和结合起来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是这支研究队伍的主体。所以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并不“缺位”,陆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的一方缺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是所谓有人“把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话语、实用理论,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无学术性,又无独立性,是称不上‘哲学’的”的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不是“哲学”的言论,在中国学术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并不多见。即使有人用一些很隐晦的词句来表达这个意思,但也不是主要潮流。我有时也听到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的言论,这在西方学术界是相当流行的观点,但他们在述说这种观点的时候,往往并不是为了贬低马克思的学术地位。这可能反映的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性和形态变化上的不同理解。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那里,就是作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方法论工具,被实际贯穿和应用于其政治活动和理论研究过程的始终的。在马克思那里,除了早期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和简短的哲学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外,没有一本纯粹讨论哲学的著作。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对哲学不重视,而是表明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研究是为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服务的,是和现实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的。正是这样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存在形态,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的历史发展中,世界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技术上的重大发展,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因此,试图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把它拉回到纯粹“学术”的圈子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的。在当代中国,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的政治现实关注和意识形态色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点,使它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产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第一国际”解散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这种存在形态,在马克思哲学的后继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特定历史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独特的、鲜明的形态特点:其一是鲜明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和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总是作为思想路线和方法论武器被应用和贯彻于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制度措施中,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哲学依据和哲学指导。其二是高度的统一性。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统一全党乃至全体人民的思想,指导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行动,以实现党的目标,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需要,它只能做统一的解释、形成统一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其三是权威性。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以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和文章的形式出现,但最后还是要由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的党章或决议的形式予以正式规定和确认,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通过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则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性还在于它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共产党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在人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也使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具有权威性。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陆文第一部分开头的那段话,实际上是一种主观推测,其中只涉及局部的、个别的事实,然而作者把它们夸大成了带普遍性的东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形态
陆文第二部分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哲学思想)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作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部分。他说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分,是为了解开“马哲讨论中的一个‘结’”。他所说的这个“结”就是指中国哲学学术界负担了或试图负担太重的责任:要面对世界、时代和国情作出判断;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和现实价值找到一条道路;要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他认为中国哲学学术界无法挑起这付重担,结果在讨论中出现了焦虑甚至悲观。他认为通过他的划分,就能够使学者们不必再去承担他们本不该承担的责任,由此而集中精力来专门从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也就不会再出现“焦虑甚至悲观”的情绪了。
首先,陆文的划分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因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外延是很广泛的,包括了在中国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形态,自然也就包括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陆文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反过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和国家吗?既然“在中国”,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并列的、不交叉的。而且,这样的划分在实际进行的时候也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陆文划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按照陆文的标准,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思想就只能被划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合适吗?他们难道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难道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陆文的划分还有一个问题,即在陆文开列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他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当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只能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地说,他的这个说法大体符合历史过程。但他忽略了一个不应该忽略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我们党成立的时候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就是到了今天,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中仍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陆文对这两种哲学形态所规定的分工也是值得讨论的。陆文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人民的智慧为源泉,以取得中国文化形态为努力方向,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的研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世界范围内哲学潮流为背景,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学术为重点的研究”。这种划分的问题是: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不去关注世界范围内哲学潮流这个背景吗?“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不从中国的实践出发,不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陆文还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分工还在于:前者以建立“实践观念”为主题,后者则以建立“理论观念”为主题;前者直接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后者以学术本身的解读、阐释为任务;前者以中国实践提出的总体性问题为对象,后者则以学者自己观察到的问题为对象;前者重在建设,后者重在批判。这样的分工完全割裂了“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政治路线与学术阐述、建设和批判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上是不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但是,陆文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就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存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可质疑性、可修改性、可丰富性、可发展性等特征;而由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所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形态,则具有成果形式的学者论著性、理论观点的研究讨论性、影响方式的非党政性。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仍然摆出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时所具有的那种政治性、统一性、权威性,学者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和讨论了。研究无禁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概念、原理都应该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验,都是可以被质疑、被追问的,都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和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新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修改、补充、丰富和发展。所谓论著性,是说学术研究成果所采取的形式,不像党的指导思想那样采取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讲话、报告、决议和党章党规的形式,而是采取学者或学术群体的论文和著作的形式。所谓讨论性,就是指在理论观点上不过是一家之言,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观点。学术论著上的任何问题、任何观点都是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可以有不同见解的,答案往往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所谓非党政性,是说学术论著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不是通过党政机关组织的、行政的手段和途径,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并以其自身的魅力发生影响,读者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党的指导思想则不同,它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的。对于党员来说,承认并贯彻执行党的指导思想,是带有强制性的组织纪律。由此可见,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像陆文说的那样,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学术,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论,一个是路线一个是学理,一个是现实一个是历史,而是表现在成果形成的社会途径、成果形式的社会性质、成果影响的社会方式上的区别。就政治和学术、理论和实践、路线和学理、现实和历史的相互关系而言,无论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求将它们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正是两者的共同之点。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国家完全可以是一种学术、一种文化,但在中国的存在形态就不可能这样单一,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它的存在形态必然呈现多样性。如何处理好这些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使之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研究的对象。其目的是为了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更好地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各种不同存在形态,虽然说有所分工、各有特点,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政治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理论的社会身份及对社会影响方式上的差别。陆文似乎更多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区分,但我更关注这些不同哲学形态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因为我觉得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强调这些方面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反之,如果人为地隔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让它们各自“画地为牢”、互不往来,是无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的,更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它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期待它为自己提供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多维度的学术视角,这样它才能更准确地指导实践,更好地发挥它对实践的理论指导作用,并在指导实践的基础上获得自身的发展。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没有必要的学术支持,没有扎实的学术理论研究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发现、新见解,就会丧失创新发展的学术根基。
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研究成果必须通过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只有被吸收、被融入到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中去,通过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个不可缺少的中介,才能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否则,它们的社会影响就往往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学者范围之内。可以说,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不能截然分开。陆文在谈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认为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只是“学术本身的解读、阐释,不负担对总体实践的指导责任”,因为它“同总体性实践很难建立反映和指导的双向关系”。他还说到“即使关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解读马克思本本,也应该承认其意义”。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我们不能把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完全限制在“学术本身的解读、阐释”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来研究同样需要观照现实,需要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最突出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把现实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存在和解决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学术指导,即为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提供有效的认识工具和解决方法。如果一种学术研究完全与现实社会无关,那么它的所谓研究“意义”和存在价值从何谈起呢?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证明,任何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事实上是没有绝对分开过的,也是不可能绝对分开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这两种哲学形态的共生共荣、缺一不可。前者没有后者,就丧失了学术根基;后者离开前者,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两者必须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由此而联想到陆文中曾用“在野”来表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地位,那么不言而喻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指导思想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处于“在朝”的地位。这样的比喻同样值得推敲。在我看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那种“在野”和“在朝”的比喻,容易让人想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争斗、相互取代,所以这种比喻并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区别。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形态都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研究者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各有侧重,但不能相互贬低。唯有各种形态之间相互依托、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支持,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合力,才能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出现新格局和新特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形态的多样性。实践证明,一种哲学形态的多样性能够为这种哲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不竭的活力。反之,“独尊”一种哲学形态而排斥其它,只能使这种哲学死路一条。对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种形态的共生共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各种存在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还要探讨有利于这种关系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体制。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