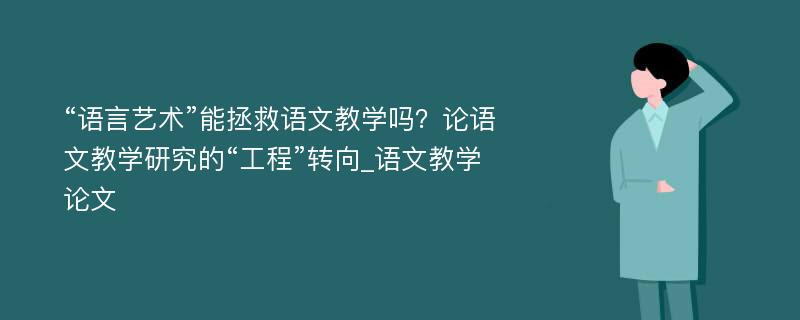
“语言艺术”能否拯救语文教学?——兼谈语文教学研究的“工程学”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研究论文,工程学论文,语文教学论文,语文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症结与药方——语文教学的现实危机在哪里?
20世纪以来,我们对语文教学一直不怎么满意,语文教育工作者好像一直处于忧心忡忡的情绪状态,而语文教学也好像一直处于被质疑、被批判甚至被否定的位置。
1978年,吕叔湘先生大声疾呼:“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20世纪末的语文教育大批判中,有人甚至说它“误尽苍生”。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教学确实有过一段时间让人充满期待;然而,改革8年至今,许多人开始对它表示不满,以致不少人称它是“穿新鞋走老路”。有调查显示,新课程改革以来,超负荷的工作量不仅使中小学教师参与课程研发的热情减退,甚至使部分教师对个人的职业选择产生了疑虑。调查中,高达36.5%的教师表示,如果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他们将“不会再做教师”。新课程改革以来的教育教学(当然包括语文教学)之令人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的语文教学,从欧美化、苏联化,到四不像化;从文道之争、工具性和思想性之争,到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从语言论、文学论、言语论、人文论、文化论,到语言艺术论;从语文教学革命化、政治化,到语文教学科学化、人文化;从语文教学的政治批判、科学批判到思想批判,从教学方法改革、课程改革到新课程改革,我们的语文教学一直处于被革命、被更新的状态。无论是理论的引进与转化,还是模式的借鉴与翻新,在每个时代,语文教学改革几乎都是教学改革领域里最如火如荼、最引人注目的。然而,上述种种努力似乎从未令人满意过,我们对语文教学的忧心忡忡似乎愈演愈烈,甚至总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感觉当然有一种错觉的成分,因为没有经过严密的调查,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有学者就指出,实际上学生的学业成绩未必是落后了,要看前后对比的是什么。
既是教育改革的急先锋、领头羊,又是教育问责的主要对象、教育批判的主要领域——语文教学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艰难地前行着。而广大的一线语文教师,就是在这样的困境里艰难摸索着。语文教学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我们尽管找了很多症结,开了很多药方,似乎都不怎么管用。那么,语文教学的现实危机究竟是什么?语文教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症结,一个找到它、解决它,就能全面解决语文教学危机的症结?
二、性质神话与语文的终结——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本质规定?
相比于其他学科和国外母语教学,20世纪以来,在寻找语文教学症结的各种努力中,各方面用力最多、最有影响的也许就是语文学科的“性质追问”了。在很多人看来,讨论语文教学问题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那就是“语文是什么”,它的性质怎样?它的本质规定及逻辑起点究竟是什么?
这一问题已经困扰语文教育界太久,至今我们都难以走出它的阴影。大家普遍相信,任何一种语文课程与教学行为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理论预设,即都有一个“语文是什么”的个人理解,所以这个近乎“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成了“一个语文教育绕不过去的问题”(李海林语),一个“语文界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潘新和语)。而它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或“语文教学”)的“性质”“目的”“任务”等问题,产生了意见纷呈的本体论课程话语。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虽然大家不断试图破解语文学科所谓“特有的”“性质问题”,找到语文学科“独当其任”的“任”,明确语文学科“是其所是”的“是”,或终结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追问”的努力;但就目前的成果来看,从“纷争”性质到“消解”性质,从“语文”新解(如“言语教学论”)到取消“语文”,我们的这些工作虽已更趋理性,却还远未达成共识。
正如普遍流行的课程话语一“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所揭示的一样,语文、语文学科、语文课程、语文教学所涵盖与指称的世界是如此辽阔和丰富,倘使这一世界没有一个基本的规定性,我们当如何把握它?倘使不能在语文和大语文、泛语文、非语文之间划定界线,在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给“语文”划界,也就是给“语文实践”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规范。而“语文”因此也才获得了某种确切的“身份”。虽然有时我们也不满足于一个给定的身份——比如“工具性”之类,而试图另觅他途,贴上更合适的标签——比如“人文性”“文化性”之类。不过,我们总需要某个标签、某种身份,并借以推销一种主张或践行一种观念。事实上,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们走马灯似的给“语文”贴了各种标签,定了各种身份,设了诸多标准,其反复无常终致人无所适从。
语文学科性质之争折射的是“绝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这个“绝对本质”要么是一种“语文想象”,要么是一种假借“性质界定”而对“课程取向”所做的某种辩护。对此问题,我们以为:1.如果说性质追问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确定性的寻求,而当我们不再以“确定性”为旨归,不再仅从“确定性”那里求得安全感,当我们越来越勇于直面充满差异与分歧的“不确定的世界”时,“是什么”本身也就不再那么引人注意了。确定性之所以不再那么引人注意,还在于人们对确定性、普遍性的追问方式不当,难以达成共识,又僭越了认知(理论)与实践(筹划)的界限,从而影响和改造了语文课程实践,造成种种恶果。2.追寻那个终极性的、不容置疑的、高于实践世界的、所谓一贯正确的语文性质(本质或本体),不过是一种想象和虚构,而且语文课程(话语)的实践历史也表明,某种笼统、抽象的“确定性”从来就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以“本质主义的本体论”的方式把握语文课程存在合法性危机。3.无论是哪一种本体论的探寻方式,我们只能理清局部的道理,无法获得普遍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无论是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课教什么”——当然还有“为什么”和“怎么办”等的设问方式与思考方式——的问题转向,还是抛弃传统的性质追问方法、设计替代性的分析框架,所有这些努力已经向我们显示,基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内的“本体论”正在走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地追问“语文是什么”,注定难以修成正果。4.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是“是什么”,本体之后的语文课程研究,应该尽量谨慎从事纯粹概念思辨式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它所应关注的问题,也许应该转向“为什么”和“怎么办”——为各种课程理解与课程实践提供解释、指导和设计方案。而这也许既能避开本质主义这个魅惑人心的女妖,又可躲过后现代主义这头危险的怪兽。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一切确证性、一切界线、一切规则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不可捕捉的可能性;在那里,实践取代了纯粹的认知,美、善、德性取代了绝对真理和唯一标准。
三、科学品质和设计思想的匮乏——向“运动化”的语文教改说不!
有学者指出,新课程改革操持了“新与旧”“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老路”并不被关心,人们甚至为了突出、美化“新路”,不惜将“老路”简化、片面化甚至妖魔化。比如:如果说“新路”是“三维目标”,那么“老路”一定只是传播知识技能而不培养人的;如果说“新路”是自主、合作、探究的,那么,“老路”必定是死记硬背、机械学习的;如果说“新路”是师生平等的,那么“老路”必定是教师主导的、对学生主体性压制的、教师霸权的……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教改运动化”的表现,其突出特征就是“非此即彼”“片面绝对”“一哄而上”。前述“性质之争”在“语文教改运动化”中其实扮演了“提供理据”的角色。这种“运动化”的语文教学改革对语文教学的正常发展危害极大。可惜,20世纪后半叶以来,语文教学“政治化”“科学化”“人文化”的不断变脸,都未能摆脱“运动化”的推动。
如何摆脱“运动化”的思维方式与操作方式呢?笔者以为,前述“为各种课程理解与课程实践提供解释、指导和设计方案”正是语文课程与教学领域最为紧要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补课:一是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态度与做法,不再简单地将“科学”与“应试”和“标准化”“机械化”相提并论;二是重视“设计思想”,不再以一个虚假的“绝对本质”,一个站不住脚的“逻辑起点”,一场“非此即彼”的语文教改运动来干扰语文教学。
回顾20世纪以来的语文教学之路,我们发现,语文教学运动化的背后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科学化探索”。早在1924年,沈仲久就提出“国文教授科学化”的问题。所谓科学化,在他看来,就是要注重国文教授的“法则”,要持“科学的态度”,应用“科学的方法”,“根据事实以弊除空想,多用分析以救济笼统,多用综合矫正偏见”。在20世纪前期,通过课程、教材、教法的改进来谋求语文教学科学化的不乏其人。比如,吴奔星针对当时“中学毕业生国文程度日趋低下”的事实,提出“教学专精化,学习平均化”的“分工合作制”,以探求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出路。叶兢耕则试图通过对“教材研究”的探讨来“挽救目前语文教学的危机”。心理学家艾伟历时20余年,潜心研究汉字、汉语心理问题,运用教育测量和实验等科学方法、手段,“深入而具体地探讨中小学语文教育实际问题”,为“社会转型期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20世纪后期,吕叔湘、张志公、叶圣陶等著名语文教育家在语文教学科学化上基本达成共识,他们在“什么是语文”“语文教学教什么”“如何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乃至语文知识系统的开发与建构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为语文教学步入科学化的轨道搭建了良好的平台。2006年,余应源有感于“21世纪都过了六年语文教学界还这么乱”的现实情况,“四论语文教学科学化”,他坚持认为:“语文教学与研究要扬弃泛语文化,走科学化之路。”尽管如此,在语文教学与研究实践中,“科学化”还远未成为一种共识,人们对“语文教学科学化”还存在着诸多误解,以致许多人把它等同于“科学主义”“工具理性”而加以排斥。
追问学科性质是一种认知思维、理论思维、本质思维,而具体的课程与教学设计则需要一种工程思维、筹划思维。就语文教学的实际状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课程设计、教学设计、练习和测试的设计都比较粗糙和随意,缺乏科学品质。教材内容编排随意,我们称之为“人文主题组元”;教材知识和能力不成系统,我们解释为语文学习“类似农业,不是工业”(其实就是农业,也有一个原始农业与现代化农业的区分);语文教参单薄,不能为教师提供参考,我们解释为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至于语文练习和测试题目的随意、粗糙、混乱和低级就更是举不胜举了。因此,摆脱“本质主义”“运动化”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加强语文教学的科学研究,重视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科学设计”,应该是语文教学改进的当务之急。
四、基于语言艺术的工程学转向——我们究竟拿什么拯救语文?
有研究者提出“语文课程研究的范式转型”,即语文课程研究要实现由“学科性质”到“课程理解”再到“课程理解后的课程开发”的范式转型。其实,我们需要的倒不是这种转型,而是一个研究重点的转向、研究重心的转移:由追问学科性质和运动化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转向科学严谨的课程设计、教学设计和评估设计。我们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重点的转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工程学转向”。
当然,这里所谓转向或转移,并不是要取消对“学科性质”和“课程理解”的研究,而是强调:1.对“学科性质”与“课程理解”要以“合乎问题类型”的方法加以研究。在笔者看来,“学科性质”是教育哲学领域的问题,“课程理解”是解释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搞清楚它们的问题界域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它们,以避免非理性的、非此即彼式的无休止论争。2.学科性质、课程理解、课程与教学设计之间也不是简单的“转型”和“取代”的关系,而只是研究重心的转移、转向的问题,强调“设计”并不妨碍对设计外的问题感兴趣。
那么,这个“工程学转向”的基点和具体方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以为,它应该是“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简而言之,陶本一先生的“语言艺术”,或笔者强调的“语言的理性实践”庶几可以用来指称它。
“语言艺术”的语文观来自美国语文的启示。所谓“语言艺术”,“是与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等并列的艺术形式,主要是指人类按照理性和审美的规律运用语词进行交流的能力和技巧,它是以语言为媒介和材质并指向‘语言艺术化’(即把语言从一般的交际工具升华为艺术形态的过程)的,既包含了对‘艺术化的语言’的感知、审美活动,也包含了‘语言艺术化’的技能”。“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其他学科主要侧重于‘表现什么’,关注点在于‘说了什么’,以言语内容、言语作品的方式呈现;语文学科则不仅关注‘表现了什么’,更看重‘怎么表现’,关注点在于‘怎么说的’,主要探究言语内容、言语作品的组合、构建方式。”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指向“语言素质的多维建构”,它具体包括:语言态度、语言体验、语言经验、语言单位、语言规则、语言策略、语言交流、语言思维。
如果我们摆脱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甚至摆脱语文学科性质这类纠缠不清的问题,从“基于语言艺术”和“为了语言艺术”的角度,从“语言理解”(即“语言输入”,包括视、听、读)和“语言表达”(即“语言输出”,包括说、写)的角度来考虑语文课程、教学和评估的具体设计,科学严谨、扎扎实实地研究、论证,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诸般乱象也许能逐渐得以扫除,其科学品质也许会大大增进。当然,“工程学转向”与“课程、教学和评估的具体设计”要不要非得借助“语言艺术”的语文观,或者说,要实现这种转向,我们是否仍然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名”,是否仍然需要一个对语文学科的“相对本质的规定”,这也还值得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