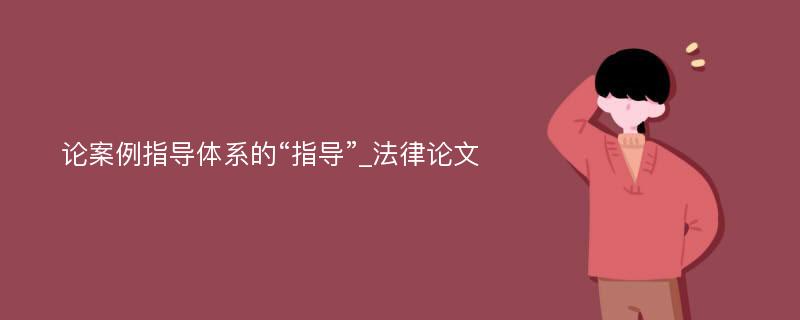
案例指导制度之“指导”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案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案例指导制度的目标就是发布指导性案例,其最为核心的词汇即为“案例”和“指导”,而选择何种案例作为指导则与指导的目的相关,即“为何指导”;指导性案例要发挥作用也与“如何指导”以及“指导的效力”相关,因此,我们大可以“指导”这个关键词为核心来研究案例指导制度。
一、为何指导:司法统一和法律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设置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表述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如果细究起来,主要可以表述为两层目的:第一层目的是实现“同案同判”、“统一司法”;第二层目的是在司法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统一司法”和“同案同判”是法律适用的普遍性和法律安定性的需求,不仅是在中国,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或普通法系国家也同样重要。①但是,“同案同判”既指后案与前案的统一,又指不同法院判决的统一。有学者指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提出,更多着重于横向上不同法院判决的“司法统一”②。是否真是如此?除此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6条要求指导性案例首先必须是具有既判力的案例,其次必须符合五类情形:(1)社会广泛关注的;(2)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3)具有典型性的;(4)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5)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第五类情形的规定是个兜底条款,暂且不论,我们可以逐一分析前面的四类情形。
(1)何为“社会广泛关注”?这个表述中有三个没有被清晰界定的词语:“社会”、“广泛”、“关注”,何为“社会”?一般来说,社会是自然形成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具有其自有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我们可以在社会之前增加不同的修饰词,例如“和谐社会”、“移民社会”等等。在“社会广泛关注”这类表述中,这里所要强调的社会是一种不设定社会成员特征的社会,也即最广泛的社会,例如“中国社会”。何为“关注”?关注就是指关心重视,广泛关注就是广泛的关心重视。从我们当下日常用语中,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广泛关注的体现形式可能有三种:媒体的相关报道、网络平台上的讨论、群体性的信访事件。那么这类案件是否一定具有法律上的疑难?很可能这类案件并没有法律上的争议,但是完全可能成为具有争议性的案件,人们往往从案件的结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法感情、妥当感、价值标准去判断这个案件是否具有争议性、是否引发人们的关注。例如媒体关注的案件往往并不是具有法律争议的案件,却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往往这类案件具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并且是能够用一般的妥当感去判断裁判正当与否的案件。这类案件可能肇因于某种制度缺失或违背一般人的道德体认,而并非一个具体的法律疑难所致,“社会广泛关注”仅仅只能从最宽泛的层面上说是一个法律现象,而将“社会广泛关注”作为指导性案例选择的首要情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社会广泛关注”案例的裁判具有重要的社会调控意义。在我国,人民法院有着重要的政治使命,人民法院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和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在这类案例上,“同案同判”并不表现为时间轴上的后案遵照前案判决,而是体现为同一时间点不同地域之间的“同案同判”,或者说是法律的普遍性。为了实现这样的司法统一,似乎只有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为适合。
(2)第二类情形表述为“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所谓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可能体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法律规定表现为法律原则的形式,二是法律规则中所选择的法律概念比较宽泛和抽象,未作明确界定,这些问题会造成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类情形却与第四类情形存在交叉和重叠的可能。
第四类情形规定了两种情况:疑难复杂、新类型。所谓的疑难案件往往是指法律规定上存在瑕疵而造成裁判者在适用法律上的困难。③法律规定为何存在瑕疵,这有可能是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存在冲突或漏洞所致。如果法律规定缺乏明确性,那么自然会导致法律适用中的疑难。指导性案例之为指导性案例,与人民法院法律适用过程密切相关,而并非是主动对原则性表述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和具体化——主动进行解释和具体化属于立法机关立法解释的范畴。所以就逻辑而言,是因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导致了法律适用中的困难,因此才需指导性案例进行指导,“法律规定比较原则”这类情形完全可以并入第四类情形中之“疑难复杂”。
第四类情形中之“新类型”,亦属疑难案件,其可能是因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或漏洞所致,如果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我们已经有一套基本的理论和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法律漏洞,一般而言是指法律应作规定而未作规定的情形,可分为公开的漏洞和隐藏的漏洞。前者是指关于某个法律问题,法律依其目的及规范计划,应积极地加以规定,却未设规定;后者则是隐藏的漏洞,即关于某个法律问题,法律虽已有规定,但依法律之目的及规范计划,应对该规定设有例外,却未设例外。除此之外,尚存在第三类法律漏洞,即超越法律计划的漏洞。④所以,如果从一般法律用语和法律实践来看,第二类情形与第四类情形无疑是不必要的累赘和重复,我们均可以将其视为“疑难案件”。
(3)至于第三类情形“具有典型性的”,何为“典型”?第一,所谓的典型案例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例,这与前述第一类情形近似,均可视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第二,典型案例之“典型”往往意味着这个案例中存在的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与某一类法律规范的理解有相当高程度的契合。如果典型案件是契合相应法律规范最为完整的案例,那么,这类案件是近乎起说明作用的教学案例。很有可能,某个个案和相应的指导性案例行为类似,但是性质不类似;行为类似,但是争议不类似。因此,这类典型案例很难实现指导性案例对裁判质量的控制以及对下级法院审判的监督功能。第三,最有可能的是,典型案例可以视为在一个法律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转折作用的案例(leading case),它代表了法律本身和法律方法的发展。之所以它有这样的地位,一是可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诉讼主张,超越了原有的法律规范或者是先例;二是可能一种新型的价值主张影响了法官对于规范的解释或衡量从而影响了裁判结果。但是这样的典型作用并非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事后对法律发展的影响所做的评价,这些案例原本的样貌就是疑难案件。
从上述的分析可知,案例指导制度所设定的五类指导性案例所符合的条件,不外乎出于两类需要:“司法统一”式的“同案同判”;“疑难案件”的“法律发展”。那么,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否真正能实现其所预设的目的?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也就是对于之后作出的类似案件的裁判是否真的具有权威;二是指导性案例如何指导、如何对类似案件的裁判发挥作用。
二、何种指导:“硬指导”和“软效力”
指导性案例是否真的具有权威?其效力如何?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等同志曾在《法学研究》发表《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一文中提出:“如果指导性案例是经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地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案例解释,其效力和作用也相当于司法解释,其对全国法院的指导就是一种硬指导,法官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作为法律适用的一种依据引用;如果指导性案例没有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发布,而是通过其他程序发布的,则其效力和指导作用就是一种软指导,法官事实上应当遵循指导性案例的要求,在裁判文书中不得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引用,但可以作为说理的依据引用。”⑤
必须区分“硬指导”和“软指导”,这与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依据相关。按照《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指导性案例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而且从该《规定》的效力来源来看,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进行解释的权能。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这种授权的列举式的规定,我们只能认为是一种专属的排他性权力。在《立法法》中,也仅仅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的行使。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已经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但是在1982年《宪法》中并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如果说,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该条规定能够被认为是合宪的,那么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决议》明确授权最高法院对于法律适用中的问题进行法律解释。有学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授权属于模糊授权,其立法原意应该是限定于诉讼程序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最高法院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来指导全国各级法院审判工作。⑥但就1981年的《决议》原文来看,并不能得出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就实体权利进行司法解释,而且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也经常这样去发展法律,立法机关也经常予以默认。对于如何具体引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采用“解释”的形式,这个解释往往可能改变法律已经确定的实体权利安排,这种具有实体权利安排的司法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⑦具有准立法的效力,可以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因此,既然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依据是来自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同样具有“准立法”性质的效力,那么,指导性案例自然只能是“硬指导”。
那么,这个“硬指导”究竟有多“硬”?
《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7条这样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何为“应当参照”?在此规定出台以后,胡云腾接受《法制日报》的采访中曾言及如何理解“应当参照”。在他看来,“应当就是必须,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而未参照的,必须有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既不参照指导性案例又不说明理由,导致裁判与指导性案例大相径庭,显失司法公正的,就可能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当事人有权利提出上诉、申诉”⑧。
波兰法学家佩兹尼克(Aleksander Peczenik)曾基于对各个国家先例制度的实证研究,按照先例约束力的强度,区分了四个层级,如果对照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应属于第一个层级的规定,也就是形式上的约束力(formal bindingness):一个判决如果不尊重先例的约束力则为不合法,因此也可以在上诉时被推翻。其又可区分为:(1)严格的约束力:必须在每个案例中被使用;可辩驳的约束力:除非在特定的案例中,先例必须被严格遵守。(2)无论有没有例外,形式上的约束力不能被否定或修改。⑨这样预设的强拘束力几乎可以和判例制国家相媲美。
受限于法律渊源理论,同为成文法国家,如法国,先例并不意味着一个有约束力的决定,先例仅仅意味着高等法院作出的裁判,这些裁判对于低等法院来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低等法院会依照这些先例来进行裁判,但也是出于实践理性上的考虑;⑩又如在德国,虽然说很难发现在高等法院的判决中不提及或参照先例,而且如果先例与现在争讼的案件相关,律师们也会在法庭上引用先例,但是在理论上,德国法院的先例并不具有形式上的拘束力。(11)
或许会有人说:因为依前所述,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司法解释近乎于立法,所以有这样强的拘束力理所应当。但是指导性案例毕竟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更不是立法。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案例指导制度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行使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又明确说明司法解释一共有4种形式,其并不包含指导性案例。摆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弱的拘束力的现状,以及摆脱作为司法解释中批复这一形式带来的有关妨碍审判独立及审级制度的恶评,也是案例指导制度产生的部分原因。
甚至,“指导性案例”这个名称的提出就有最高人民法院澄清立场的意义在内。曾有学者对于“指导性案例”这个名称提出匡正意见,主要理由是“案例”这个名称失之过宽,主要存在表述形式累赘、功能定位偏差、学术交流不畅的后果。(12)其实,之所以用“指导性案例”这个名称,主要在于法院试图避免被指为“法官造法”,而僭越我国宪政建制中的立法权,亦试图表明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制度之距离,是一种司法机关不去触碰立法权的自我表白。
但是,“硬指导”是否真的能够实现?
从本身来说,形式性的约束力应该被视为一个没有层级的概念,要么有约束力要么没有约束力,但是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形式性的约束力并不是那样简单两分,而是在运用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层级,例如:有约束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等等。因为,之所谓有形式上的约束力,只是出现在当后案法官违反先例,并因此判决被推翻的情形中;而不能事先就预设哪个先例具有形式上的约束力,而哪个先例则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13)“如果案例的裁判结论及其论证理由不能被社会以及法官所认同”,即便规定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性约束力,“法官们也同样会运用区别技术、调解等各种途径予以规避”。(14)
不仅如此,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自己颁布指导性案例作为其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方式而予以实施,但这种依赖于指导性案例的监督方式并不能违反审判独立和审级制度,因此,受限于审级制度,即便是硬指导也很有可能只具有“软效力”。
基于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原则,我国几乎大多数案件都集中于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按照我国的审级制度,绝大多数案件在中级人民法院就已经终审,虽然有提审和再审程序,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法官并不会因此面临裁判被撤销、改判的风险。而且就我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可以视为一种行政发包制,这是造成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为了减少中央监督和决策的成本,中国传统的行政逐级发包制塑造了一个全能型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把所有事务连同各种执政权力统一“打包”给地方各级政府,其中包括司法审判权。司法连同行政权力具有严格的属地化特征。在西方国家,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是分开的,司法不受行政权力的影响,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形成重要的制约。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下,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地方政府一级是结合在一起,统一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民地方法院实施“双重管理、地方党委为主”的人事管理制度,实际上法院要想地方党委负责,地方政府也把法院看做是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15)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可以视为改变司法地方主义的一种努力,但是在目前的审级制度下实现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硬指导”的“硬效力”实现很困难。
相对来说,“软指导”却有着“硬效力”。所谓“软指导”即为事实上的拘束力,而所谓事实上的拘束力,正如胡云腾等同志在《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一文中所指是“本级和下级法院‘必须’充分注意并顾及,如明显背离并造成裁判不公,将面临司法管理和案件质量评查方面负面评价的危险,案件也将依照法定程序被撤销、改判或者被再审改判等”(16)。当初该文中区分两种指导性案例的硬指导和软指导的效力,就是因该文写作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公布之前,考虑到可能会有其他级别的法院成为指导性案例的公布主体,所以提出了这个“软指导”。这个“软指导”实际上是建立在审级制度中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之上。假设一个中级法院并不遵守高级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那么这个案件有可能被上诉至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可以作出撤销、改判的法律决定,而且正如此文所言,中级法院也将面临司法管理和案件质量评查方面负面评价的危险。在目前的法院系统的考核体制中,这对于每一个主审法官的裁判行为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软指导”却有着“硬效力”。
要想实现地域上同案同判,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摆脱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通过审级制度对裁判的控制,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么案例指导制度只能是一种尴尬的存在。如果有发挥效力的审级制度,那么根本不需要强调什么案例指导制度的“硬指导”,上级法院的上诉审足以对下级法院进行裁判监督,并能一定程度上实现同案同判。作为软指导的案例指导制度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现在基于司法解释提出的案例指导制度反而是一种不那么自然的存在物。
三、如何指导:裁判规范与案例比较
如果设定指导性案例具有形式上的拘束力,那么势必会考虑指导性案例中哪些部分具有形式上的拘束力?
这是必要的,因为所谓的拘束力自然是一种规范性的效力,我们不能说事实陈述也具有规范性的效力。因此,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区分案例中哪些部分具有约束力?而且一般在成文法国家,判例的主要作用就是抽取出一定的裁判规范或是一般性的裁判理由。即便在判例法国家中,主要是将判例和后案通过类比的方式来做出裁判,裁判规范或一般性的裁判理由一说也并非没有市场。(17)凯尔森认为如果仅仅是适用实证法,而并没有创造新的裁判规范,则不能认为具有判例的特征。一个判例最重要的要素是法律创制功能。(18)基于这样的观点,指导性案例若具有规范性的效力,其具有拘束力的部分只可能存在于从裁判中归纳出来的裁判规范上。不仅如此,从理论上来说,成文法国家中先例之所以具有约束力,是因为其具有内在的正确性,这种内在的正确性就是对成文法规范的正确解释,因此,先例的运用其实就是运用通过先例形成的对成文法规范最好的解释。(19)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裁判规范究竟是制定先例的法院总结表述还是由后案的审理法院总结归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与裁判文本的形式也密切相关。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了4个指导性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首先分别总结了4个指导性案例旨在解决何种法律问题以及体现了何种社会价值。指导性案例包含6个部分:关键词,这是便于搜索的需要;裁判要点;相关法条;基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理由。在现有的指导性案例的样式中,事实的陈述或者事实命题并不具有规范性效力,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归纳、裁判结果和理由是法官思维过程和论理的具体化,而能比较明确表现规范性效力的内容可能出现在两个地方: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
因此,裁判规范有4种可能呈现方式:(1)先例法官在裁判要点中表述出来;(2)先例法官在裁判理由中表述出来;(3)后案法官在裁判要点中提取出来;(4)后案法官在裁判理由中提取出来。
就案例指导制度的设计目的来看,若是主张(3)、(4),则会陷入一个非常巨大的困境。裁判理由与案件本身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于极少表述为一般性的裁判规范。如果由后案法官从指导性案例中总结出一般性的裁判规范,不同的法官有非常大的可能会总结出不同的裁判规范,那么势必就违背了案例指导制度“为何指导”所设置的目的:“司法统一”;也违背了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依据:作为司法解释的变种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指导性案例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公布,相应地,裁判规范也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来予以总结。
而且,如果说最高人民法院仅仅想公布一个较好的案例,以作为其他法官判决时的参考,或者说,使指导性案例仅仅对裁判理由提供支持作用,那么,原先的公报案例就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目的。而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提升到硬指导的层次,甚至于在公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同时,也特别强调提出“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以期强调指导性案例的独特地位,其原因就是为了实现司法统一,而为了实现司法统一,则最好是通过对规范具体化,形成一定的裁判规范,各级法院以涵摄的方式依据裁判规范进行判决。如果不是运用裁判规范,那么指导性案例就仅仅只能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而不再是“应当”参照了。
那么,就仅存在(1)与(2)的可能性。
就写作方式来说,裁判要点和之前公报案例中的裁判摘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有学者曾归纳了裁判摘要的类型:对法律的具体条文进行解释;对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文进行再解释;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解释;确认习惯的法律效力。(20)总体而言,这些都是一些抽取出来的一般性的规范。在第一批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点形式上并没有摆脱原先公报案例的裁判摘要的样式,例如3号指导性案例中的裁判要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实际上就是对受贿行为进行了具体化。“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样的表述更明显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释。就裁判的事实和理由部分而言,也并没有脱离现有的裁判文书的写作框架。
1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确认了两个内容:第一是确认了“跳单”格式条款有效,第二是确认“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Ci)……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其中隐藏了本案适用的规范N1:在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C1),如果买方违反“有效的”跳单格式条款(C2),则应承担违约责任(O)。N1来自于合同法的基本规范:违反有效的合同约定,则应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在于,1号指导性案例的目的并非是确立一个规范,而在于确认一个事实,也就是Ci不属于C2。对于事实的判断自然不能说具有规范性的效力。那么,1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就不能被认为是确立了一种裁判规范,甚至于还不能说确立了一个是否满足构成要件的判断标准,因为它仅仅否定了Ci不属于C2。
相比而言,其他3个指导性案例确立了一定的裁判规范,例如3号指导性案例将受贿罪中的受贿行为进行了具体化,通过对受贿行为进行解释,而形成具体的裁判规范。其中裁判要点第1条可以表述为一个规范:“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应以受贿罪论处。”
而4号指导性案例则是突破了原先的规则,创造了一个新的裁判规范。结合《通知》中所申明的案例的指导精神,4号指导性案例裁判规范可以表述为:因恋爱、婚姻矛盾导致(C1)手段残忍的故意杀人(C2),但是被告人具有从轻处罚情节(C3),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C4),并且犯罪发生在2011年4月30日之前的(C5),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Pi)。根据修正后《刑法》第50条第2款、第78条第2款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问题在于是否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以前犯罪的判决,其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但无疑是一种具体化。胡云腾等同志在有关文章中指出:“经研究,2011年4月30日以前犯罪,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包括三种情形:(1)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依照修正前刑法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依照修正后刑法可不立即执行,但需要限制其减刑的;(2)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但依照修正前刑法原本即应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3)除前两种情形以外的其他死缓犯,即不具有累犯情节,所犯罪行也不属于上述八种暴力性犯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上述第(2)、(3)种情形下,应适用修正前刑法第50条、第78条的规定,即不能限制减刑,对此各方面认识完全一致。”(21)
从4号指导性案例中关于裁决结果的表述来看,一、二审判决均判决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核准死刑,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认为被告人应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其行为为故意杀人,如果没有刑法的修改,那么被告人可能的结果就是死刑但缓期二年执行,或者甚至是无期徒刑。换句话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但是依照修正前刑法原本应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或无期徒刑等,这种情形并不能增加适用限制减刑,因为对于本来应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来说,适用限制减刑实际上是加重了刑罚。因此,这个指导性案例几乎创造了新的裁判规范,甚至于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C1和C4对于增加限制减刑的判决具有重要的意义。
依前所述,我们可以将4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范表述为:
C1∧C2∧C3∧C4∧C5→Pi.
那么,假如被告人并非因恋爱、婚姻矛盾而故意杀人,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故意杀人,是否可以依照这个裁判规范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或者假如被告人因恋爱、婚姻矛盾而故意杀人,但是被害人亲属没有要求依法惩处,或者是不存在被害人亲属,那么是否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限制减刑?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一旦将裁判规范和案例紧密地结合起来,指导性案例依然不可能摆脱判例法中的区别技术和相应的分析技巧。其实,运用1号指导性案例同样也是如此,其势必只能采用指导性案例与后案事实之间的比较,来分析新案件中买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的情形,是否属于“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的情形。
分析到这里,看起来已经很明了,案例指导制度最初的设计目的就是司法统一和发展法律;而案例指导制度的合法性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职能和作为发展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因此具有了硬指导的效力;而正是因为硬指导和司法统一,指导性案例中具有规范性约束力的部分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抽取出来,无论是从裁判要点中抽取还是从裁判理由中抽取,裁判规范都必须要结合案例——假如不结合案例的话,指导性案例存在的意义就付之阙如,其又与司法解释何异?既然要结合案例,那么一旦运用到后案之中,势必会有后案与前案的比较,则无论如何还是摆脱不了判例法传统发展而来的案例比较技术。
虽然指导性案例从命名最初,就想摆脱与判例法的关联,希望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但是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并非无根之木,即便指导性案例一再强调与判例法的区分,也无法让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讨论摆脱判例法的学术背景和相应的学术概念去思考指导性案例如何指导这个问题。案例指导制度的出台必须首先有其相应的制度资源和学理资源,离开了相应的制度资源——司法解释,无法论证其合法性;离开了相应的学理资源——判例,无法进行有效的指导,缺乏相应学术概念支撑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否能再创一套行之有效的概念体系或语言体系?有学者认为“只要承认一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具有拘束力,或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或构成指导性案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判例法方法。既然如此,普通法系成熟的判例法方法和娴熟的司法技艺在此过程中就应最大限度地得到尊重和贯彻”。(22)
其实,无论是“判例”、“先例”、还是“指导性案例”,都出自于对法律安定性和普遍性的追求。而且,无论哪种先例制度,本质上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制度,多样性和争议是不可避免的。若干年前,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和美国法学家萨默斯(Robert Summers)就组织各国学者对各国的先例制度进行实证研究,汇集成册,在他们看来,各个国家先例的运用基于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如法院体系、风格和法院判决的公布等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对其先例的运用都有其可被理解的合理性基础,这些合理性基础也反过来影响了先例运用的结果和方式。在不同的体系内也会有对先例的批评,或许是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或许也因为其他的因素。(23)这样看来,虽然案例指导制度有些尴尬,许多新词也代表着为了制度和社会变化未来的形式和方向所做的努力,但无论案例指导制度还存在多少问题,其至少可以推进案例的运用和研究,也促进了法律的安定性和普遍性。
当然,颁布指导性案例是一个方面,指导性案例的运用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行文至此,反思前文,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是指导性案例发布者或批判者的视角,其实,不同的视角对于先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发布者来说,所谓的先例是后案法官不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或分析就可以在相关案例中直接运用;对于后案法官来说,先例是具有重要性的一些裁判决定;对于研究者来说,先例则可能是在特定的案例中被提出的那些例子或阐释出来的那些裁判规范。(24)如果从后案法官的视角来看,先例不外乎是一个用以论证的理由。既然有所先例,法律推理和后案法官运用先例予以论证说理就不可避免。现在已公布了4个指导性案例,其运用也就更值得期待。只有在案例的比较和运用之中,指导性案例的生命才能生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先例制度之所以在不同国家都有所存在,是因为:在合法性基础上,我们更期待着通过理由/理性的裁判,让法律人践行正义、发展法律。这才是法律真正的智慧和魅力。
注释:
①参见Zenon Bankowski,Neil MacCormick,Lech Morawski and Alfonso Ruiz Miguel,"Rationales for Precedent",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488.
②参见秦宗文:《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色、难题与前景》,《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
③参见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81-130.
④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6-300页。
⑤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⑥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⑦参见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⑧《“两高”研究室主任详谈“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法制日报》2011年1月5日。
⑨参见Aleksander Peczenik,“The 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463.
⑩参见Michel Troper and Christophe Grzegorczyk,"Precedent in France",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111.
(11)参见Robert Alexy and Ralf Dreier,"Precedent in tIl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 (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p.23-24.
(12)参见刘风景:《“指导性案例”名称之辩正》,《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4期。
(13)参见Aleksander Peczenik,"The Binding Force of Precedent",p.478.
(14)参见李友根:《指导性案例为何没有约束力——以无名氏因交通肇事致死案件中的原告资格为研究对象》,《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4期。
(15)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页。
(16)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
(17)参见Geoffrey Marshall,"What is Binding in a Precedent?" 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p.508-511.
(18)参见Hans Kelsen,"Will the Judgment in the Nuremberg Trial Constitute a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1(2),1947:153-154.
(19)参见Zenon Bankowski,Neil MacCormick,Lech Morawski and Alfonso Ruiz Miguel,"Rationales for Precedent",pp.483-484.
(20)参见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比较优势》。
(21)胡云腾、周加海、刘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1年第13期。
(22)宋晓:《裁判摘要的性质追问》,《法学》2010年第2期。
(23)参见"Appendix:Final Version of the Common Questions,Comparative Legal Precedent Study,September 1994",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Precedent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Ashgate,1997,pp.551-552.
(24)参见Geoffrey Marshall,"What is Binding in a Precedent?" pp.503-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