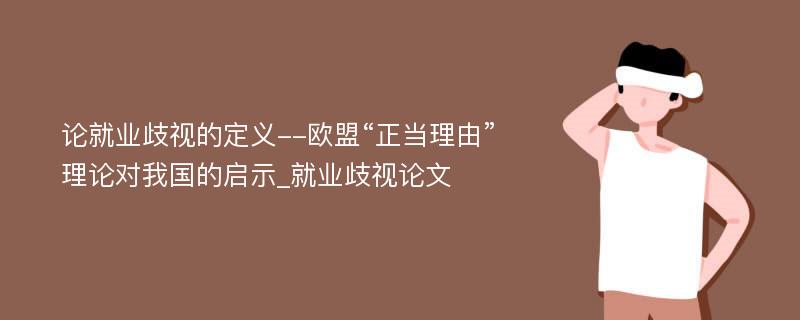
论就业歧视的界定——欧盟“正当理由”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正当论文,启示论文,理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2年4月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身高行政诉讼案以来, 与就业歧视相关的报道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不管是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的蒋韬案,还是被称为“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的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的行政诉讼案,都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法学理论界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两案对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推进意义上,而对就业歧视的讨论远没有宪法诉讼来得热烈。分析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发现,诉讼当事人或者“倡诉者”试图通过宪法的平等原则来对抗就业过程中的歧视对待,在操作上实属无奈之举。正因为我国劳动法在反就业歧视上的缺陷,社会各界对于制定相关立法的呼声高涨。① 然而,究竟怎样的行为是就业歧视,是否所有区别对待都构成歧视,如何界定就业歧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更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拟对此做一探讨。
一、正义原则与就业歧视
从正义这一概念的分配含义来看,它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则把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相等地东西给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东西给予不相等的人。② 然而,人类的属性在于: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各不相同。谁与谁相等或同类?换言之,应该依何种标准来划分人类群体,从而在法律上给予“同类”的人以相同的对待?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法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具体领域中确定此等本质性范畴,形成一些合法与不法的基准。
就业意味着职业作为一种资源或财富的分配,即利益的分配。平等就业也就是对利益的平等分配,这种分配应符合正义标准——相同者予以相同处理,不同者予以区别对待。法律制度本身在设置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对类属进行划分。一种合理的归类,应正好包括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处境相同的人,换言之,应对法律上“相同”的归类做合目的性考量。所以,要探求含义模糊的“相同”与“不同”在具体情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在归类的背后寻找法律的目的。笔者认为,在反就业歧视中,上述归类应着重于消除个人先赋起点的差异,保障就业机会的平等;同时,对那些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群体给予特殊保护。
罗尔斯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因此,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为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③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和调节机制,不应该基于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给劳动者设置不平等;反之,应消除这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的现实上的不平等。据此,这类人力难以支配的先赋因素不应成为对劳动者进行归类的标准。虽然,不同劳动者在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外貌等先赋条件上存在差异,但在法律上,他们仍应享有相同的待遇。所以,基于先赋因素决定个人就业机会的不同是不正当的,从而构成歧视。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由于人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得每个人不可能具有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主观努力程度,故经过自由竞争后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如果法律无视这些差异,反而是不正当的。因而,在一定的方面和程度上,允许正当的区别对待。一般认为,以能力、经验、知识等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的自获条件为标准的区别对待,是通过个体之间的竞争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因而是正当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构成歧视,歧视的本质是一种违背正义原则的、不正当的区别对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区别对待现象异常复杂。并非所有基于先赋因素的区别对待都是不正当的,也并非所有基于自获因素的区别对待都是正当的,在这两大类区别对待中都存在着例外情形。如何衡量就业过程中区别对待的正当性是各国立法者和司法者们一直力图解决的问题。
二、比较视野下的反就业歧视——欧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自1957年《罗马条约》以来,追求两性平等一直是欧共体关注的目标。而欧盟的反歧视立法主要是依靠欧洲法院在两性工作平等领域的司法实践而发展起来的,这种司法实践为欧盟反歧视法律中普遍原则的出现和“关键概念”的具体化奠定了基础。《阿姆斯特丹条约》的签署,使欧盟反歧视法律不但在两性工作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获得了解决种族、民族、宗教、肤色、性取向、年龄和残疾等领域歧视的权力。④ 为了保障《阿姆斯特丹条约》的实施,欧盟颁布了两项重要指令——第2000/43号“实施反种族和民族歧视的平等待遇原则”指令和第2000/78号“在就业和职业领域设立平等待遇一般框架”指令。这两项指令对工作领域的歧视做了最新的具体规定。
在欧盟法中,歧视按其表现形式被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两大类。根据第2000/78号指令,直接歧视指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残疾、年龄和性取向等原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给予另一主体较差的待遇。歧视的动机或意图不是直接歧视的必要条件,只要该措施的结果具有歧视性就足够了。⑤ 间接歧视则被用来针对那些有歧视效果的措施:某一表面中立的条款、标准或行为,若使特定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残疾、年龄或性取向的群体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时,就构成了间接歧视,除非该表面中立的条款、标准或行为可以被一个客观、合法的目的证明是正当的,且达到该目的的手段合宜且必要。这种从结果出发进行的考量,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因为只要雇主的行为使受保障群体的多数成员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就推定这种损害结果源于雇主对受保护群体的歧视,除非雇主能提出正当理由推翻这种因果关系。对于间接歧视的构成是否以具有歧视意图为要件的问题,欧洲法院的态度从起初的肯定回答逐步转向否定,因为将间接歧视只限定为有意图的行为会明显地限制它的有效性。⑥
举证责任问题是歧视案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原告即受害人通常难以获得雇主的歧视证据,因此欧盟通过了第97/80号“性别歧视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指令。 该指令规定了性别歧视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原告只需证明存在着可推定为性别歧视的事实,即雇主的某一行为导致特定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被告则需要证明其区别对待具有正当理由,因而并未违反平等待遇原则。这一指令不但适用于性别歧视情形,之后也适用于立法所涉及的其他领域的歧视。
不管在直接歧视还是在间接歧视的案件中,都存在着例外情形使区别对待行为得以正当化,但论证这两种区别对待合法的理由并不相同。
(一)直接歧视案件中的正当理由
根据法律传统,没有人会为直接歧视辩护,除非有明文规定的特殊例外。⑦ 按照欧盟法,这类例外是指“真正的、决定性的职业要求”,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以及国家为实现实质平等而采取的“肯定性歧视”(比如规定企业雇佣残疾人的比例)。
第2000/43号指令第4条规定:“成员国可以规定,根据与种族或民族身份有关的性质产生的区别对待不构成歧视,如果是因为特殊职业活动或其从事工作的性质,而这种性质构成了真正的、决定性的职业要求,假使其目标合法,要求恰当。”第2000/78号指令第4条也以相似的条款起草,规定了种族和民族领域直接歧视的“职业要求”例外。该指令第2条还规定了平等待遇原则在性别领域的三种例外:首先,劳动者的性别构成决定性的因素(第2款);第二,妇女需要保护, 尤其是怀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第3款);第三,国家已实施“积极性的行动”方案(第4款)。
为明确平等待遇的例外情形,法律在某些具体领域做了进一步阐释。例如,第2000/78号指令第5条规定了关于年龄方面的正当的区别对待:
(a)禁止获得就业和提供特殊工作的规定以保护年轻人和老年劳动者;
(b)设立最低年龄标准作为退休和残疾津贴合法性的条件;
(c)根据职业对身体或精神方面的要求,设立不同种类或群体的雇员可获得退休或残疾福利的不同年龄;
(d)根据工作岗位的培训要求或在退休前合理期限的就业需要, 设立被录取人员的最高年龄标准;
(e)设立关于职业经验时间长短的要求;
(f)为实现合法的劳动市场目标而设立恰当的必要的年龄限制。
由于“真正的、决定性的职业要求”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在具体情况中,判断特定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年龄、外貌等先赋因素是否为某一职业所必需仍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欧洲法院对此做了严格的解释以推进平等目标的实现。⑧
(二)间接歧视案件中的正当理由
自工作领域的反歧视法制建立以来,在欧盟发生的歧视案件多为间接歧视。
与直接歧视案件中的区别对待行为一般不能被正当化不同,根据间接歧视概念中的除外条款,区别对待行为所造成的歧视效果可以因被告提出的正当理由而合法化,因此法院在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构成间接歧视时,“正当理由”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1986年的Bilka案中, 欧洲法院首次明确阐述了供成员国评判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否正当的测试方法。⑨ Bilka案⑩ 涉及同工同酬问题,在该案中,Bilka公司的全职人员在退休后享有一笔奖金,而兼职人员则无权享有,除非该兼职人员的合计雇佣时间达到15年。欧洲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奖金制度构成对女性的间接歧视,因为多数女性劳动者由于其家庭责任而无法承担全职工作,也就没有资格享有奖金。法院进一步指出,成员国法院有职责评判雇主提出的理由能否证明其区别对待的正当性。如果内国法院认为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客观的,并且符合以下几点要求,那么影响女性数量远大于男性的事实并不足以得出雇主行为违法的结论:(a)是为了满足企业的真实需要;(b)对达到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而言是适当的;(c)对达到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而言是必要的。Bilka 案中形成的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在之后的歧视案件中为欧洲法院所沿用和发展,构成了欧盟关于区别对待正当理由的判例法的基础。
然而,欧洲法院在理解正当理由判断标准的含义时,其态度在不同的歧视案件中有所不同。
譬如在“企业真实需要”标准上,欧洲法院未给出应在何种严格程度上适用该标准的指示。在Rinner案(11) 中,法院允许宽泛模糊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正当理由;而在Danfoss案⑤中, 法院则认为“真实需要”应考虑所涉雇员的特定职责,而不能以雇主从雇佣具有某一特征(该案中指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中获得某些模糊的好处为由而将之视为“真实需要”。这种将“真实需要”与“职业相关性”等同的测试方法无疑更为严苛。
之所以出现欧洲法院对正当理由标准的游移态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价值判断的固有特点,法律语言的内在缺陷以及歧视领域社会状况的多变性和复杂性共同决定了欧洲法院对正当理由标准的理解的变化和发展。正因为对正当理由的审查是基于“客观性”、“合宜性”、“必要性”等价值色彩浓厚的概念的评判,故对歧视的认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从法律原则出发进行的自由裁量。
三、欧盟反就业歧视法律中的“正当理由”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就业的权利和义务。 ”宪法的这一规定不仅确立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而且为公民实现平等就业权提供了保障。作为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我国《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的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13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禁止就业歧视在我国劳动法中被正式确立。但是,《劳动法》只是以列举的方式将四种歧视规定为就业歧视,我国目前十分常见的户籍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健康歧视、外貌歧视等是否应为法律所禁止?我们无法从《劳动法》中找到依据。立法上的缺陷要求我们借鉴法律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适合我国社会现状的就业歧视规则。
根据欧盟法对工作领域歧视的分类,直接歧视是基于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残疾、年龄、性取向等因素的区别对待,比如在招聘启事中声明“只限男性”、“35岁以下”等条件。而在间接歧视中,法官审核的是雇佣实践的结果,看是否不成比例地取消了受保护群体的就业机会并且有无正当理由。但由于与欧盟法制进程所处的阶段不同,我国目前的就业歧视中最突出和首要解决的是直接歧视问题,因此欧盟的划分标准对我国的就业歧视而言不具有针对性。此外,间接歧视的概念尚不为我国所熟悉且认定规则复杂,在欧盟也是通过一系列判决逐渐成形的,我国法院在掌握这些规则时容易发生困难和偏差。所以,我国尚不急于对歧视做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的划分。
与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的分类相比,以先赋因素和自获因素为标准对就业歧视进行分类更为明晰和直观。笔者认为,基于先赋差异的区别对待原则上构成歧视,而证明其合法的正当理由应主要由法律规定,以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保障就业平等的实现。基于自获因素的区别对待原则上不构成歧视。但根据欧盟反歧视的实践经验,可以预见到仅仅禁止先赋因素歧视将导致“托词式”歧视的出现,即雇主虽实际基于先赋因素对某一群体成员给予区别对待,但表面宣称这种对待并非基于先赋因素,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的存在。此时,我国立法可以借鉴欧盟间接歧视的相关规则,防止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具体认定规则如下:
(一)基于先赋因素的歧视的认定
先赋因素是指人力难以选择和控制的因素。对于影响就业的先赋因素,法律应明确加以规定。我国劳动法只列举了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因素,而且是穷举式规定,这显然不够周延。根据我国常见的歧视情形,应把户籍、年龄、外貌、健康状况等诸项劳动者的先赋因素增补为列举内容,并加“等”字兜底,以备必要时进行扩张解释之用。用人单位若基于上述因素实施区别对待,拒绝录用某一群体的劳动者或设置不同的录用标准,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就业歧视。
同时,法律还应规定基于先赋因素的区别对待的正当理由。在立法规定这种正当理由时,可参考两项标准——保护弱势群体原则和职业内在需要标准。根据前一原则,法律为弱势群体设置了特殊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比如欧盟2000/78号指令第5条(a)项“禁止获得就业和提供特殊工作的规定以保护年轻人和老年劳动者”,我国劳动法第七章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职业内在需要标准是指当某一先赋因素在特定职业活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基于该先赋因素的区别对待才是正当的。美国将这种职业的内在需要称为真实职业资格(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简称BFOQ),也就是雇主给予歧视待遇完全是职业本身正常运作之缘故。(13) 某些职业对先赋因素有明显的限制,例如演唱、舞蹈、模特、体育等职业对容貌或身高的要求,食品卫生行业对于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这些都属于职业内在需要,应由法律明确规定。
然而,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能否以某一先赋因素确为职业活动所必需来认定区别对待的合法性呢?笔者倾向于肯定回答。因为目前我国规定歧视例外情形的法律十分欠缺,法官不能等待法律完善后才来处理层出不穷的歧视案件;即使法律完善了,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作为职业内在需要的先赋因素。在欧盟的反歧视司法实践中,直接歧视案件中的区别对待不能被正当化的做法产生了一些难题,法院在某些案件中也已突破了这种限制——虽然这种情形很少。(14)
当然,法院在审查先赋因素的区别对待时,应严格把握“职业内在需要”的含义,考察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和特定职业中的专家意见。这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尤其体现在健康歧视中。医学知识的缺乏和主观偏见导致多数人对艾滋病、乙肝等病毒携带者的恐惧心态,但从医学常识上讲,这类病毒携带者仍可正常生活工作,并不会通过正常的社交活动传播,不会对周围的人群构成直接危害。此外,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对携带某种可能致病的非正常基因者的歧视问题也已经引起关注。(15) 在这些情况中,法官判断区别对待合法与否的根据应当是专业人员的科学鉴定,而非社会成员的主观认识,否则无疑是对无知与偏见的纵容和强化。此外,顾客或同僚的一般偏好,如多数顾客偏好女性接线员或男性驾驶员等,并不足以构成“职业内在需要”的抗辩,因为在就业平等与一般偏好的冲突中,前者的价值更应受到保护。而在诸如医院限制男性获得助产士职位的情形中,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两性敏感性等问题,法官则不得不考虑到社会普通成员的主观心态,而不是以纯粹科技上的观点来否定产妇本能的心理需求。
(二)基于自获因素的歧视的认定
自获因素指能够通过主观努力逐步养成的,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劳动者的学历、专业、经验、是否通过某种资格考试等的要求。以这些自获因素的差异为标准进行区别对待的行为,原则上是合法的。
有学者认为,用人单位对社会因素的限制必须是合理和必要的,否则构成歧视。(16) 这种规制主要是为了抑制当前人才高消费的不良现象,但笔者认为,要求法院审查用人单位基于自获因素的区别对待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操作的。首先,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虽然某些用人单位管理理念中的误区也是其成因,但它主要是目前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形势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才高消费难以避免,也无法通过法律的强制规定加以改变。其次,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用人单位有用人自主权,用人单位最清楚自己需要怎样的人才,它对劳动者自获因素的限制应属于其用人自主权的范围。让法官代替用人单位判断对一项自获因素的要求是否与应聘职位合比例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也会给法院带来过重的负担。所以用人单位对自获因素的要求是否合比例的问题可以交由市场自身解决,法律对此无须做行规定。
但为了防止在仅禁止先赋因素歧视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托词式”歧视,法律应规定基于自获因素的区别对待构成歧视的条件:①用人单位实施了区别对待行为;②具有某种先赋特征之群体成员处于不利地位;③这种不利地位与区别对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要具备上述要件,就可以推定区别对待的原因是基于先赋因素的差异,或者说构成歧视的初步证据,除非被告能够提出正当理由。在此,可以借鉴欧洲法院评判“正当理由”的规则,用人单位的理由必须符合下述条件才是正当的:
(1)为了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
“用人单位的需要”与“职业的内在需要”含义有所不同。前者指与职业运作有密切关系的一切因素;后者则强调劳动者为使某一职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技能或条件。从外延上讲,“用人单位的需要”不仅包括不可或缺的、具有决定性的职业需要,而且包括与企业需要和目标有关的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保护第三者安全的需要等。对职业内在需要的认定一般基于某一职业对劳动者要求的社会共识,法官必须从严把握;而对用人单位真实需要的认定则与涉讼之雇佣本身有一重要关系即可。但同时,为了防止法官对用人单位真实需要的认定过于宽泛以至于妨碍立法目的的实现,正当理由还必须符合下文中的比例原则。
(2)符合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原本是公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通过考察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来防止超限度地破坏利益与价值的均衡。在就业歧视领域,比例原则指用人单位的区别对待行为适当且必要,并且相对于其追求的目的而言是合比例的。具体而言,“适当”意味着用人单位区别对待的方式和措施正确,并且能够实现用人单位的真正需要或至少有助于其需要的实现。“必要”意味着在数种能够实现目的的措施中,必须选择那些对劳动者造成损害最小的措施。最后,必要的行为方式和措施对劳动者所造成的损害与用人单位和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应成比例、保持均衡。
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对个体区别对待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考察,已经要求法官从简单判断其他可行措施的存在转向要求雇主寻找可替代的方法。只有在雇主穷尽了所有防止或限制不利情形的必要步骤后,区别对待才能够被正当化。与此相似的是加拿大法律规定的雇主的“合理适应”(reasonable accommodation)义务。雇主必须证明其已努力与间接受其职业要求损害的雇员之间达成协商,这种协商考虑到了双方的利益和需要。雇主的这一义务直到其承担的限制超过合理界限时为止。(17)
不正当的区别对待构成歧视,正当的区别对待则否,故就业歧视的界定规则也就是判断区别对待正当与否的规则。就业歧视的界定是反就业歧视立法的核心问题。然而,对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而言,仅仅确立一种界定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设置有力的执行机构、拓宽被歧视者的救济途径,乃至提高社会公众的反歧视意识。因此,本文仅是解决我国反就业歧视问题的一个开始,望能引发对此问题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
注释:
① 譬如,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洪宇于2004年3月和2005年3月两次在第十居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
② 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
③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④ 《阿姆斯特丹条约》第13条:“在不影响本条约的其他条款以及在它赋予欧共体的权限内,理事会在咨询欧盟议会后对委员会的议案通过全体一致投票采取适当行动来反对根据性别、种族或民族、宗教或信仰、残疾、年龄或性取向而产生的歧视。”
⑤ Case 69/80 Worringhan v.Lloyd's Bank(1981) ECR 767.
⑥ [英] 凯瑟琳·巴纳德:《欧盟劳动法》,付欣译,郭捷校,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⑦ [英]凯瑟琳·巴纳德:《欧盟劳动法》,付欣译,郭捷校,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另须注意:此处的“歧视”是广义的, 其含义等同于“区别对待”,因为狭义的歧视本身就是违法,无法被正当化。
⑧ See Marie-Ange Moreau,‘Justification of Discrimination’Lectureat the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Ⅲ.
⑨ T.K.Hervey,Justification for Indirect Sex Discrimination inEmployment:European Community and United Kingdom Law Compared (1991) 40 Internationa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10.
⑩ Case C—170/84 Bilka—Kaufhaus v.Weber von Hartz (1986) ECR 1607.
(11) Case 171/88 Rinner—Kühm v.FWW Special—Gebaudereinignung (1989) ECR 2743.
(12) Case 109/88 (1989) ECR I—3199.
(13) 曾恂:《美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启示》,《南方经济》2003年第5期。(14) See Case C—132/92 (1993) ECR I—5579.
(15) 参见“基因歧视”法律问题专题研究系列,《科技与法律》2003第3期、第4期,2004年第1期、第2期、第3期。
(16) 许建宇、王怀章:《就业歧视立法规制初探》,《中国劳动》2004年第2期。
(17) D.Proulx,op.cit.p.73 etseq.Refer to Marie-Ange Moreau,‘Justification of Discrimination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