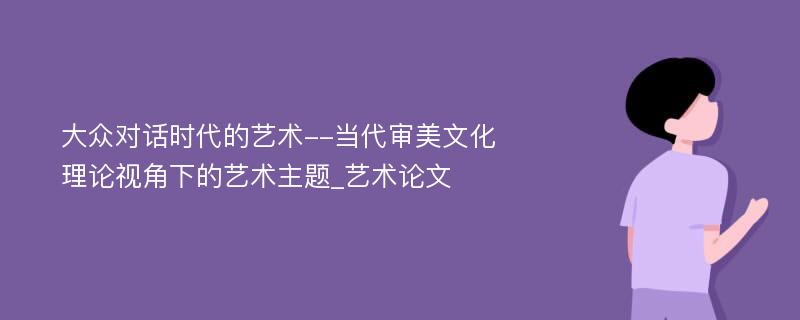
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艺术——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视野中的艺术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大众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众化:当代艺术新方向
1.一个艺术时代出现与存在的“合法的”必然性,建筑在其文化隐喻的必然性。艺术时代的变迁,就是人类文化变革过程及其结果的历史本质的一种“书写”形式,也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之开始确立。今天艺术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过程及其结果,本质上仍与当代历史/文化、生活/世界的丰富变化相一致。没有人会怀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艺术所经历和正在进行的一切,正是对一个崭新文化时代的全面凸现。也没有人能够怀疑,当代人类文化进程及其本质,其实正是今天艺术的最深刻核心和原动力。也许,人类还从来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一个普遍大众的艺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艺术史上还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普遍适应人类文化利益的、大众自觉的时代,那么,今天的世界文化进程及其未来,已为产生这样的艺术时代提供了充满竞争力的机会。在这个时代,人们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文化多元选择性,拥有空前广泛的自由追求的欲望。然而,这一事实是否为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的到来以及它的发展确立了至深的基础?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实践过程及其正在进行的工作,能否使我们肯定,当代艺术必然而且有能力在审美文化建构层面完成同这个文化时代的对应,清晰而有力地铭刻当代文化的精神/价值转换?
2.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艺术时代的变迁,其行为过程的具体化又意味着什么?
把这个“艺术行为的具体化”放到艺术时代的变迁中看,它最主要就体现在艺术结构形态方面,即:一是在整个文化时代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并与文化活动相适合的艺术审美风格形态的变异;二是通过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工作,艺术自身创造形态的变异。这里,艺术审美风格形态侧重其可感的形式;直接产生审美效果的,就是这种表现为艺术独立价值、诉诸人的审美知觉的感性形式特征。从这种可感形式上,艺术所表现以及人们感同身受的,是深深浸润在一种审美风格形态之中的特定文化时代的强烈动态过程和因素。而一个艺术时代的产生,其审美风格形态的显著变异,就是其文化时代的特殊宣言、具体感性的告白。如果我们放弃考察一种艺术审美风格形态变异的深刻文化过程,我们除了能从艺术现象上获得一些技术性证据外,便将无以回答艺术时代变迁的根本文化性质问题。从这一点来讲,可以认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必定有它自己相应的艺术认同、确证形式;艺术时代的变迁,在其审美风格形态变异方面,决不可能超越特定文化时代的根本利益、表现和追求。
与此相似,当我们主要从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过程来探讨艺术创造形态的变异时,同样可以发现,无论就艺术创造心理的文化制约因素、艺术家活动的现实范围,还是就艺术家创作中的直接文化认知而言,在艺术时代变迁意义上,艺术创造形态的变异都与一定文化时代氛围及其所提供的可能性相联系。也就是说,在艺术创造形态的实践机制中,同样体现了艺术时代与一定文化时代的内在关系。由此生发开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单纯技术性层面,一定文化时代同样直接铺设了艺术创造形态变异的现实具体化过程——以文化时代本身的特定技术进步,直接导致艺术家创作实践过程中操作方式、材料等的选择和应用;从而使艺术时代的变迁在艺术创造形态变异这一具体化行为方面,充分感性地体认一定文化时代的巨大特征。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能够诞生光效应艺术,计算机艺术、新现实主义艺术等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从上述立场来考察当代审美文化领域的艺术走向,当代艺术的自身行为具体化过程,其最大特征就是审美风格形态日趋简洁易明、直接普遍而可以重复。在这个方向上,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开始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大众进行“对话”:对话的主体是互为的,既不是艺术或艺术家告诉作为接受群体的大众以某些特殊的东西,亦非大众绝对地规定了艺术和艺术家,而是双方在共同的文化/生存环境中,以相互间的文化性沟通为内容进行交流。相应地,当代审美文化领域的艺术创造形态,一方面为满足当今文化时代的艺术审美风格形态变异而不断趋向多样化、丰富化、生动化和日常化;另一方面,艺术创造形态的丰富化、多样化、生动化和日常化,又积极地生成和促进着当代艺术与大众对话的普遍前景,生成并促进着艺术大众化努力的全面展开。其如现代抽象艺术的最大意义,莫过于从艺术审美的“自明”维度,反叛了那种经典自然主义“自作自然”的艰涩,从而显示出艺术创造形态变异在观念和技术操作上是可能的,并且具有潜在而巨大的变通性。
从这种变通性上延伸,沿着现代艺术道路发展下来的今日艺术及其创造活动,在更广大范围内,同时在更加热情地与当代人类文化/生存环境相契合的过程中,通过观念和技术的力量,把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大众对话的多样丰富性大大地推进了。即以绘画来看,画家们一方面继续艰难地探讨着当代文化实践进程中的大众观念及日常生活、文化精神/价值构造的现状及其具体问题,同时这种探讨往往又更多集中在与大众现实文化行为直接关联的领域,并且试图以那种具体、直观的视觉感受符号/形象来刺激大众的普遍情感心理和文化认同。(注:参见拙文《视像与快感》,长春:《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可以说,在当代审美文化的艺术实践层面上,当代绘画运动已经走入了以千奇百态、变换无穷的符号/形象制作及其表演性、展示性来直接隐喻生活/世界的文化性结构和活动的天地,从而使当代大众不断从自身生活中直接产生出某种同艺术的更为广泛、直观的联系。当代各种具象艺术形态的纷呈叠现,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一个新的、当代审美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向我们摆出了一种明确的姿态:当代艺术及其创造活动的大众化努力,标榜并正在不断实现着艺术与当代大众的广泛对话过程。这一对话的基本核心,就是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当代大众日常生活状态之间的相互趋近和认同,而不是彼此的间隔或分离。通过这一大众对话时代的诸种可能性及其现实活动,当代艺术愈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在人的生活和文化创造中的位置,愈益明确地显示了自己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及其过程的现实力量。当代大众的所有日常活动则因这种对话/交流,在艺术的具体、直观形式里益发变得可以与自身生活、自身的文化性存在事实相一致,进而在社会中掌握着广泛传达自己的欲求、深入表现自身的可能性,同时也不断获取自身当下生活享受的“审美化”能力。
在这个大众对话时代,艺术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普遍的文化延伸。在这一延伸中,当代文化的纷纭表象、人的活动和思考,经由艺术过程得到鲜明呈示,在对话/交流中提供给人们以生活里未曾全部知觉的文化意味。而当代艺术作为这种延伸的实现,一方面使艺术家有可能集中关注当代生活/世界和当代人类文化的价值变动,集中沉思当代文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则使得艺术活动及其作品形式在大众接受中成为鲜明可感的直接呈现,而不再是隔着一层似有若无的纱帘来做猜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确信地“把一件艺术品看作艺术家及其群众所处社会的图画”。(注: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512页,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1988。)
可以认为,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由艺术现实所确立的,是一种艺术、艺术活动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对话——艺术与大众之间实现了一种人与艺术形象、日常生活与艺术活动的双向动态交流,而大众则从中直观自己的现实文化处境。这样,艺术、艺术家和大众共同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共同体验和表达对当代生活/世界的情感,共同体验和表达一种对当代生活/世界的文化价值态度。这种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在与大众对话的进程中将成功架设艺术本身与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通道,日渐改变艺术的传统职责。这也是艺术在当代人类审美文化实践中所发生的根本扭变。
二 大众对话的生成背景
1.当代社会是一个交织着多种复杂性和可能性的社会。各种现实生存困厄、思想冲突、意识形态危机、人类心灵的曲折隐痛、经济结构的多元分化、政治权势的连纵对抗等,统统掩藏在当代文化活动动态的相互关系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人的文化/生存环境便产生了新的行动可能性,人们得以有意识地从事各种自我表现的“审美”的文化实践,并且在其中形成持续的联系。而艺术活动恰巧是产生这一持续联系的便捷形式,是人们对付已知的现在和未知的将来的有效文化形式。在这里,艺术家充当了必要的中介,当代艺术则被确认为一种重要的沟通和沟通活动。也因为这样,当代艺术必定趋向于同大众文化要求和思想相一致:或表达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差异因素,或表达大众对现实环境的认同,或体现大众日常生活在特定意识层面的自由想象,或体现大众文化活动的内在反叛。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大众对话过程所体现的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借助这一进程得到加强,并在整个审美文化领域连续深入地展开。
当代社会中,人们对自身文化活动及其结果的共同要求,同样使得今天的艺术和艺术活动不再是一种仅仅由艺术家个人承担责任的行为,而成为整个当代文化/生存环境中的人类普遍沟通的过程。整个社会文化所要求和规定于艺术、艺术活动的,是在一种特定“审美形象”的构造中重新显现现实文化精神/价值的具体存在形态,以使大众从独特的建构行为和结果上直观自己的处境;现实文化进程及其利益所要求于艺术家的,则是充分观照和具体表达当代大众日常生活的文化立场。由此,可以认为,当一个艺术时代的诞生伴生在人们普遍生活的文化形式中,这个艺术时代的基本面貌便必定受到这种共同生活要求的过程和性质影响。艺术不惟可以传达当代人类文化精神/价值状况,而且可以在与大众相沟通的对话过程中,确定自身的基本文化形式。艺术与大众对话过程作为当代艺术大众化的努力,稳定地建立在艺术活动、艺术家对当代文化实践过程的认同之上,并使自己显示出了人的现实文化实践的力量。
2.当代科学技术环境,是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及其创造手段不可能不纳入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以及人们在科技进步中所发展起来的技术能力、观念。作为越来越具体、直接地参与艺术活动的力量,当代科学技术一方面在观念层面逐步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理解方式,另一方面,它在艺术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艺术创造的语汇,既积极地提供给艺术家以更多的技术手段,又主动而广泛地把大众日常生活引入到艺术活动范围中。这一情形,曾经在波普艺术(Pop Art)中得到过证实:当代工业技术的典型手段被艺术家们引入到艺术构成元素里,再一次典型地表现了人们在技术时代中或焦虑或满足的问题——晶亮豪华的汽车图像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繁荣的象征,撞毁的汽车残骸隐喻了生活中的悲惨性和紧张不安;彼得·布莱克的《玩具店》,则用橱窗里如实摆放的工业社会廉价产品来交流人们内心的那份怀旧感。波普艺术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化条件下艺术与大众对话这一大众化努力的成功例子——其所依赖的发达科学技术背景,就是这种成功的基本力量。
也许,当代科学技术之于艺术的巨大渗透可以从不同方面来看待。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代艺术发展无法回避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其相互遭遇的结果则是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更多地面向整个社会文化构成中的大众利益,而不是孤单地存放在艺术家个体作坊中。其如当代大众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迅速发展、大众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已日复一日地改变了当代大众的文化表达和感受经验及其审美方式、审美趣味能力;广播、电视、卫星传播等的发达,甚至改变或创造了艺术活动的形式。当代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转向技术,以之为艺术活动的更加直接的手段和方式;当代艺术活动注定在这样一种变化了的文化/生存环境中,依赖科学技术力量来扩大自身的内在张力。就像电影的拍摄材料和技术进步所表明的: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电脑制作渗透进视频技术而使摄录设备的功能更加齐全、性能更趋完善,从而打破了以往认为的录像片色调与清晰度不如电影的看法,并进而扩大了电影本身的表现能力。当年的《星球大战》、《超人》,近年里的《哈里·波特》、《终极者Ⅲ》、《指环王》等影片在世界各地观众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就足以证明电影依赖技术来扩大自身张力的可能性。正由于这种艺术的内在张力极大地内化了科学技术的力量,因此,对于我们来讲,肯定科学技术在当代审美文化领域的客观性,肯定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之于艺术和艺术活动的广泛改变,是深刻理解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的必要前提。
当然,艺术大众化过程所要求的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大众的广泛对话,其所根据的一切文化背景最终通过艺术观念来发生现实作用。即便对当代科学技术力量的肯定与内化,同样首先通过艺术观念内部的普遍确认,才成为一种审美文化的现实。
三 艺术大众化的文化性质
1.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实现了一种“跨越”:现实生活方式向艺术活动、日常生活经验向艺术经验的跨越。其结果是“只要能够体会自身的审美经验,人们就可能使生活成为无止境的玫瑰花与欢乐”。(注:欧文·埃德曼:《艺术与人》,9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不过,这一“跨越”并非直接达到了艺术超越本身。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能真正看到的,是艺术和艺术活动在当代审美文化领域的某种现实“跨越”形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超越。这正是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的真实而深刻的文化本质。如果说,当代艺术与大众对话的过程,在人类文化活动的审美形式上有可能深刻指向生命超越的本体价值,那么,此时此刻,它却只能借助这种现实的“跨越”形式而显现自身:生命的终极意义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的现实形式中,而是作为一种生命本体,在现实生活方式向艺术活动、日常生活经验向艺术经验的“跨越”中被艺术本身及其大众接受过程逐渐自觉。
从文化性质方面分析,当代艺术在大众对话时代所实现的“跨越”表明:
第一,今天的艺术已直接进入大众日常生活领域,对当代人的文化/生存环境和文化实践进行直接审视,从而强化了大众与艺术间的相互亲近感。“大地艺术”之不满足于传统的在画廊、美术馆及私人房间里展出作品这一形式,就是很好的说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所展开的大众对话时代,实际已从当代审美文化实践方面把人的自我文化理解的可能性更加突显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不是高高在上、与大众日常生活相分离的神圣对象,它才可以切实履行自身的现时代文化责任。
第二,当代艺术与大众接受过程之间已由传统的那种作品对于接受者的单向展示方式,积极地转向了人与艺术、生活实际与艺术活动的双向动态交流,大众在艺术中所直面的就是自己的文化/生存状态;阻隔艺术与日常生活、艺术家与普通大众、艺术过程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壁垒已被推倒,“为艺术而艺术”不再能够成为当代审美文化领域中艺术的唯一准确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和全体大众一样,都在生活中努力表达着一种文化态度、人类全体的情感状态,只不过艺术家先行了一步,或者说更熟练掌握并在自己的独特行为中先行实现了这种表达,以此与社会大众共同分享表达的过程和结果。
第三,当代艺术和当代文化一样,拒绝把理想主义提前到现实生存环境之中。当代艺术功能已经以对日常生活的直接切入,代替了那种对现实之外的理想的尽情赞美。它对当代文化/生存现实的直接审视,一方面出自当代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直接要求、人对现实状况的满足或不满,另一方面则同时是当代文化的直接隐喻——隐喻了文化变迁中人的自我审度过程。也因此,当代艺术能够在今日世界里充分多样地运用新的艺术语汇,直接与大众在日常活动层面进行对话。
作为一种文化“跨越”形式,大众对话时代的艺术过程“只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只是克服生活辛劳这件事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连艺术的生产也是得首先理解为文化的生产的”。(注:巴琮·布洛克:《作为中介的美学》,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2.从当代审美文化本身来看,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在艺术活动、艺术家、艺术作品与大众对话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这样两个问题:其一,艺术大众化努力、当代艺术与大众对话的广泛性,是否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合法性?或者说,当代艺术怎样确定地成为一种当代的文化活动?其二,不断走向大众对话时代的当代艺术显然潜在着“庸俗化”的威胁,我们对此应当怎样加以理解?
这里,不仅“艺术合法性”是一个必须追究的理论对象,而且,由于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本身仍在遭受许多人的指责,因而客观分析、阐释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及其过程,便向作为文化批评的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提出了一种挑战、一种要求。这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化/生存环境和艺术现实面前,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不仅要说明当代艺术发展的本质,还应能够解释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的内在文化意味。我们所说的“艺术合法性”和艺术对“庸俗化”威胁的自身理解,其实已不是一般美学或艺术学所能予以彻底阐明的,它必须依赖当代审美文化理论的批评力量加以深入探究。
在一定意义上,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已改变了艺术的传统色彩。由于当代艺术已从艺术家个人内心独白变成为社会大众的文化沟通/交流过程,艺术活动成为人们所从事的直观自身文化/生存环境的一种独特精神方式,因而对于当代艺术大众化努力中的“艺术合法性”及其作为人的文化活动的理解,总是涉及对整个艺术传统和许多固定的艺术观念的重新阐释,涉及当代人类文化活动本质与艺术观念之间关系的全面把握。换句话说,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之于当代艺术阐释的必要性,最基本的、也是前提性的,在于对艺术观念的重新审视,包括对“艺术是什么”问题的理论辩证。
艺术对于人的生活及其文化现实的表现,其根本归途是通过艺术活动刺激、强化人内心的文化意识,在艺术享受中体验自我生命的困厄或喜悦;人的永恒生命精神冲动始终是艺术表现的对象和艺术自身价值之所在。但艺术对于人的文化意识的强化,并不是单一向性的过程,其中同样包含着人对于艺术的选择。所以,艺术只有在各种方式的表达过程中才能全面满足人的要求,实现强化的效应。尽管当代艺术的大众化努力可能在审美文化领域产生“庸俗化”的问题,然而,“庸俗化”并不是艺术大众化的等同物。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一种与传统观念不同的背景下,从整个当代文化层面来把握自身的追求——这里,我们仍将涉及“艺术是什么”问题的重新阐释。
更何况,在一个业已进入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发达商品时代,艺术想要完全拒斥商品社会的“庸俗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当代社会经济及商品观念的发展,作为人的文化现实/生存环境,是否可能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是一种当代生活方式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促进更多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和艺术家产生出来,从而使“庸俗化”威胁被消解在人的普遍的艺术活动及其自我享受当中?甚至,如果我们能够从积极的方面,而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面对艺术的“庸俗化”问题,那么,我们就可能像斯金纳(B·F·Skinner)那样大胆地看到,“也许一种勇敢的庸俗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可能使我们培育起一片土壤,更多的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将从这里产生”。(注:B·F·斯金纳:《造就创造型的艺术家》。见《艺术的未来》,75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想象,当代艺术的发展及其现实,必定要求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一方面能够对艺术的当代性质和追求进行有效阐释,另一方面又必须能够在当代文化的丰富现实中,调整自己对艺术的审视方式和理解观念,真实地把握当今文化时代中人的现实生命实现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