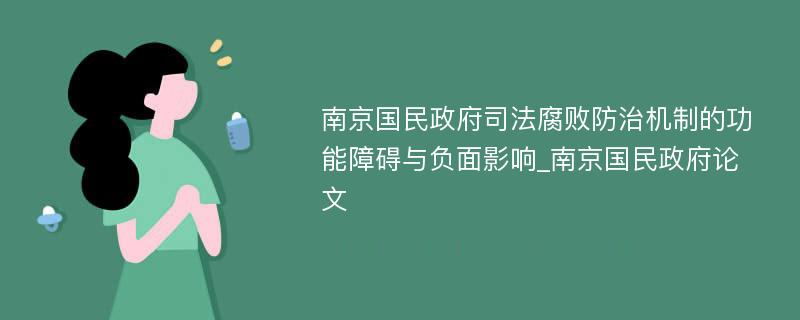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功能障碍及负面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负面论文,腐败论文,功能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问题是古今中外良性政治的“天敌”;司法腐败又使这一“天敌”失去了应有的 克制方法。几乎所有王朝或政府,为巩固其政权,都曾想方设法构建司法腐败防治机制 ,欲创造清正廉洁的政治氛围。由于各自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不一,司法腐败防治 机制的功能效应大不一样:功能强化,则正面效应大;功能弱化,则负面效应大。南京 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功能效应大体属于后者。
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设置及运行
南京国民政府权力机关组织,主要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设置的。在 防治司法腐败方面,一方面通过五权分立体制,保证司法独立;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 和完善相应机制,克服司法弊端,遏止司法腐败。
扩大审判权,缩小检察权。我国的刑罚制度一向根据报复主义精神,在诉讼上沿袭纠 问主义,没有国家主义的意识。直到清末设立了独立审判机关后,才采用检察制度,实 行审判权与检察权的对等体制,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独立,互相制衡。1927年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审检配置制度。同年8月16日,国民政府以糜费过多、手续过 繁、同级两长易生意见为由,撤销了各级检察厅,并从11月1日起,将检察官配置于各 级法院之内,只设“首席检察官”,而无独立检察机关。检察官职权仍旧,不过经费、 预算不独立,由法院统一办理。监狱、看守所的监督指挥和各县管狱员的任免也归法院 院长,而不属于首席检察官,其行政权限较前大为缩小。
加强司法行政监督。国民政府对司法腐败的行政防治机制主要体现在司法行政部的作 用上。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关系几经变更,或隶属行政院,或隶属司法院,多数时间隶属 行政院。它直接管理司法行政,拥有任免全国司法人员、设立或废止法院和监所、审核 全国司法经费等职权。其对全国司法部门司法腐败人员有直接管辖权和处分权,是防治 司法腐败的关键性机构。
设置惩戒机关。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3条中规定 :司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及行政审判之 职权。1931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惩戒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惩戒机关分为两部分: 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和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均隶属于司法院。1932年4月以后正 式成立中央惩戒委员会,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同年,国民政府又设政务官惩戒委员 会,由国民政府委员组成,职掌政务官的惩戒。1946年制宪议会时决定,公务员惩戒委 员会为司法机关,隶属于司法院。1948年以后,撤销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和中央公务员惩 戒委员会,所有公务员惩戒事宜一律归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掌管。7月1日,修正公布《公 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除总统、副总统按照宪法规定,由监察院向国民大会提出弹 劾外,无论政务官、事务官、文职与武职,均在惩戒委员会权限之内。
发挥监察功能。监察权在国民政府“五权”中独为一权。监察权主要由监察院及其监 察使施行,监察司法腐败行为,是其重要职权之一。监察使按区分派,直属监察院,凡 他们认为司法人员有违法渎职行为,严重的可以向检察机关告发。经检察官员向法院提 起公诉,他们访查所得证据往往就是检察官起诉的理由。稍轻的如“废弛职务”一类, 直接向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提请惩戒,由该会根据监察使的弹劾及司法行政机关的进一步 调查,决议对该司法人员的惩戒或免于惩戒。被惩戒人如提出申辩,则由中央公务员惩 戒委员会上报司法院裁定。监察使也可将案情呈报监察院,由监察院函请司法行政部查 核处理,并将核查结果通报监察院。
制定专门法规。国民政府为了防止官吏贪污,在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之外,专门颁布 了一系列特别法规,加以禁绝。1930年4月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执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的《限制官吏兼职案》,对官员兼职作了种种限制,如事务官除在本机关外不得兼职。 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惩治吏治条例》,计14条,对于腐败贪污行为处罚尤为 严厉。(注:《民国法规集成》第39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104页。)明清以来,除 朱元璋钦定的《明大诰》外,似乎还没有比这更严厉的法典。它具有适应战时需要的特 点,是抗战时期的特别法。孰料抗战结束,贪风不减反炽,政府认为,加重贪污处罚的 这一特别法,仍有继续施行的必要。1948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044号,又补登 有“惩治贪污条例施行期间,着自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延长一年”的命令。(注:参见黄 昭旸《论惩治贪污条例施行期间之延长》,《法律评论》16卷11期,总773、 774双周合刊,1948年5月26日印行。)足见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何等严重。
奖励举报。除颁布和沿用惩治贪污法规外,政府还通过行政渠道,奖励举告贪污。蒋 介石就曾于1947年7月2日,手令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陈诚及中央、地方各军事、行政 机关,对于贪污情事应奖励举报。如果其主管长官贪污,确有其事,也可以准由部属向 上级机关举发,并不视为背叛或越级之不法行为。至于公务员贪污,可以奖励人民告发 ,政府对于告密人员应奖励、保护,并保守其秘密。9月13日,行政院召开会议,讨论 决定并公布了奖励告密的6项办法。(注:《中央日报》1947年9月14日,第2版。)
国民政府建立起司法腐败的防治机制后,试图通过实际运行,获得预期效应。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随着审检配置的实行,检察官的职权仍然保留,只是范围不如审检分立时 代。以前刑事案件的起诉,须由检察机关进行,部分民事案件中,检察官也有起诉监督 的义务。1928年起,凡亲告罪及初级法院管辖直接侵害个人法益的罪行,均许被害人直 接向法院起诉。1935年又将自诉的范围进行了扩充,凡一切犯罪的被害人,均可以提起 自诉。检察官对于第三审案件不得添具意见书。司法警察署移送的特种刑事案件,法院 可以直接审判,审判期日,检察官可以不出庭。婚姻亲子等民事案件,在民事法规中早 已不设有关于检察官的规定。检察官的职权在日益缩小,国家、社会对于检察官的重视 程度日渐降低。(注:参见翁敬棠《论加强检察制度》,《中华法学杂志》第7卷,第2 、3合刊,1948年印行。)但还是有一定的司法监督作用,如通过对受理的案件进行预审 ,可以将大量案件作为不起诉处理,既保护了当事人利益,也减轻了法院审理负担;( 注:参见杨兆龙《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杨兆龙法 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通过“抗告”书方式,可以对同 级法院的判决提请上级法院重新审理,为纠正不当判决提供证据。1935年至1949年间, 新疆地区检察机关就曾通过该形式,纠正法院的错误或不当判决1620起。(注:参见王 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司法行政部对办案疏忽、有明显过错的司法人员的处分,首先是根据司法机关的申请 处分请求,其次是根据各界人士的举报。举报案件到部后,依据所举报的事实情况,决 定予以受理或不受理。对于各级司法机关对所属人员违法渎职主动提请的处分,无论轻 重,司法行政部都会尊重司法机关的意见,只要当事人没有申辩,很少驳回申请。这样 既能把腐败问题在司法界内部解决,通过司法机关的“自查自纠”,纯洁司法队伍,还 可避免惊动其他监督机构,避免“家丑”外扬。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行政主管机关移送的惩戒案件,可决议不受惩戒,或应受撤职、 休职(停职)、降级、记过、申诫、减俸等处分。司法行政部移付惩戒的案子,公务员惩 戒委员会一般都尊重并依照该部的意见,拟订议决书,依法惩戒。偶尔也有司法行政部 移送的惩戒人,而被议决不予惩戒的,大多因为惩戒理由不够充分。
监察院认为公务员有违法失职情事者,即将弹劾案连同证据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 议。监察院直接告发的案子,虽然可以直接向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提议惩戒,但也有 多重手续。监察使获得民众的举报,只要认为证据确凿,被检举人又没有重要的社会关 系,监察使都一般乐意弹劾。监察院只要监察使有弹劾意见报来,就会函请相关部门核 查。违法渎职的司法人员即使离开原职原地,仍有被弹劾和追加处罚的。如云南高等法 院的检察官姚鹏飞,1941年任广西柳州高三分院检察官时,在处理当地袁、宋两商民因 赎屋涉讼一案中,有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行为,1944年,姚鹏飞已升任云南高院检察官, 结果还是被监察使弹劾,提请惩戒,经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决议,给予降二级改叙的 处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案卷号160。)不过从有关当档案资 料看,被弹劾的司法人员以中下级司法官居多。
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功能障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置的司法腐败防治机制,从制度模式上看比较完备,实际运作 中,对司法腐败的惩治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由于制度结构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加 上该机制的操作主体出于自身或客观原因,未能完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因此司法腐败 防治机制的功能受到多方制约,难以承载起反腐使命。
检察体制设置缺陷,不利于检察权的发挥。曾有第一线的检察官以及一些学者明确指 出当时检察制度的弊端,如:检察权不独立;组织机构不独立;配置的人员太少;经费 不独立;上级机关行文不专属;警备力太弱;待遇歧视;检察官于侦查方面,往往不够 主动等。(注:参见翁敬棠《论加强检察制度》,《中华法学杂志》第7卷,第2、3合刊 ,1948年印行;《司法院法规委员会关于检察制度报告书·附贵州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韩景斗呈现行检察制度的商榷》(1946年),见《中华法学杂志》第6卷第3期,1947年印 行。)这一切,都妨碍检察官作用的发挥,难以很好地行使检察职权。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官基本都是被动侦查,主动侦查的很少。特别是有关国家的根本制度及官吏风纪的 大案,没有人出面告发,也没有人能出面告诉,检察官也漠不关心,给人以在其位难谋 其政之感。加之诉讼手续过于烦琐,各级检察官事务繁简过于悬殊,挫伤了基层检察官 的积极性,不注重效率、故意拖延时间的现象屡见不鲜。对司法警察的指挥权也徒有虚 名。
司法行政部处分的违法渎职人员,主要局限在中下级司法人员,涉及较高层次的,处 理起来就比较隐讳。虽然所检举司法人员违法事实详尽,只要发现检举人并未向其他有 关部门分寄出同样的呈控信,就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大批违法渎职司法人员因 此而免受惩戒。抗战期间,政府簸迁,人事不定,惩戒难以正常开展;战后,政治窳败 ,朝野贪蠹,惩不胜惩。1949年前后,行政机器运转不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防治司 法腐败方面的作用愈发削弱。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行政部在司法行政监督上,有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 则,不愿多揽事务。如1941年8月,韦文顺等向司法行政部呈控广西上林县县长侯匡时 违法渎职,擅自释放烟犯,请予以撤职。司法行政部签呈的意见是,上林已设立了县司 法处,县长并不兼理司法,其行政上的监督权归广西省政府;烟毒案件属特别刑法,不 是司法监督范围。因此决定将呈函转送广西省政府依法办理。最后结果只批示为“存查 ”(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案卷号197。),既不指令核查,也不转 函广西省政府查办。如此办案态度,纯系推卸责任。
监察机构举劾监督的成效取决于监督的对象身份,高层势力之间排挤倾轧、法官与监 察机构的微妙关系等,都可能影响监察效能的发挥。1946年,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弹劾“ 国大代表”、珠江航政局局长周演明“贪污违法”、“贿赂公行”,就遭受到巨大阻力 ,最后还是因后台坚硬和各部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才使被弹劾者受到薄惩。(注:参见 莫擎天《刘侯武弹劾周演明案始末》,《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大案纪实》 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7页;黄韶声:《解放前广东司法黑幕》, 《广东文史资料》第5辑,1962年版。)
监察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五权宪法正面效应的体现;监察功能过于突出,尤其是在司 法行政方面,则又反衬出司法功能的弱化。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 法渠道,依靠司法机关或司法行政机关获得救济。如果该渠道壅塞,只能求助于其他途 径,监察机关则是他们首选对象之一。而受监察院弹劾、最终移交有关部门惩处且依罪 科刑的,多为位卑职轻之辈,真正的“大鱼”即使被监委们网住,最终也有办法破网而 出。因此,有人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院几乎成了民主政治的装饰品。没有它,则 不能体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有了它,并不一定有案必办。监察院承袭了过去御 使的某些职责,但是它几乎没有实效。(注: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8页。)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严刑峻法,试图遏止贪污腐败之风。然而,政府中利用特权公然或 私下贪污的并未因此减少,权商合一,权钱交易,成为吏治腐败的重要土壤源。如孔祥 熙曾担任国民党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达10年之久,政绩不著,腐败有余。部分正直 的司法人员如最高法院院长郑烈,想收集证据,将孔法办,蒋介石出面打圆场,虽迫于 舆论压力,不得不免去孔的行政职务,但没有追究其任何法律责任。(注:参见张昌华 《毁誉参半傅斯年》,《人物》2001年第6期。)南京国民政府自抗战开始,到战后接收 ,官吏贪污之风愈演愈烈,已是不争的事实,《惩治贪污条例》难以得到施行。自该条 例施行以来,依照该条例逮捕法办的,多为下级吏员,或为“污吏”,真正的“贪官” 却很少被绳之以法,(注:参见郭卫《法治庸言·如何防止贪污》,《法令周刊》10卷4 0期,统号第476期,1947年10月1日印行。)《惩治贪污条例》似乎专门为下级“污吏” 而定。中级以上巨贪也有个别被抓法办的,那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资本不够,靠山不稳, 或上面的“关节”出了问题。政治资本既不牢靠,上峰关系又未理顺,司法机关才拿他 们开刀。
司法腐败防治机制功能弱化的负面效应
国民政府制定六法,改革司法体制,当然是以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为目的,另一 个直接目的则是为了撤销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 和会上北京政府代表团力争取消领事裁判权,未能如愿。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 ,北京政府重申前议,经议决,由参加会议12国代表组织中国司法调查团实际观察,提 出建议,再作决定。1926年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书,对当时中国司法的缺点做出4点结论 :军人干预审判;法律之适用不统一,各省自行制定单行章程与刑法抵触;司法经费不 足及法官之薪俸过少;警察厅及陆军审判机关皆操普通审判权。国际调查团当年指出的 中国司法状况不如人意的诸多方面弊端,直到南京政府时期都仍然存在,而且1935年就 有人指出,近10年来的司法状况与以前相比,不进反退,表现有:审判权不统一;法令 适用不统一;诉讼延迟;判决不能执行;初审草率;下级法官受人指责;司法经费不足 ;法官薪俸过少。这些问题与当年国际调查团报告中反映的情况相比不但没有改观,甚 至有所加剧。(注:吴昆吾:《中国今日司法不良之最大原因》,《东方杂志》,第32 卷,第10号,1935年5月19日印行。)1943年领事裁判权基本废除之后,司法界每况愈下 ,“抗战以来,最使人痛心者,莫过于司法界声誉之跌落”。(注:徐道邻:《假如政 府肯全面革新》,《申报》1949年2月6日,第1、2张。)
1948年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宪政”,但司法腐败之风未见得有所刹止。有法不依、违 法不究、司法权不独立等现象愈演愈烈,司法腐败防治机制的功能益发弱化。如1948年 政府发行金圆券、实行币改后,孔祥熙的公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照样囤积居奇。此 案发生后,监察院公开发表了由熊在渭、金越光等监委的纠举书。监委们认为涉及司法 部分,并即移送法院办理。监委还认为,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经济 警察大队长程义宝、上海直接税局局长黄祖培、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委霍宝树、江海关 税务司张勇年等,均有玩忽职务之处,被一并纠举。(注:参见《字林西报关于金圆券 发行的评论》1948年9月13日,《国民政府新闻局档案》,《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 册,第493页;天津《大公报》,1948年12月22日。)按照《惩治贪污条例》第2条第六 款的规定,根据孔令侃的犯罪情节,理应判处死刑。依第8条规定,市长吴国桢等当以 共犯论处。因有宋美龄撑腰,不但直接当事人孔令侃等安然无恙,市长吴国桢还被政府 另加重用。朝野也曾出现过“清算豪门”的呼声,1948年11月初,立法院数十位立法委 一致呼吁,监察院委员讨论,慷慨陈词,拟就议案,咨送行政院,力主“清铲豪门,严 惩亲贵”,并决定不得结果,全体监委将总辞职以谢国人。(注:《观察》特约记者: 《物价·豪门·大局》,《观察》5卷24期,1948年11月13日印行。)可直至南京国民政 府终际之日,立法院也没有拿出“清算豪门”的议案,也未听说监察院委员集体辞职, 《惩治贪污条例》一类的法律法规仍在做“澄清吏治”的牌坊,司法机构也在耐心地等 着个别触了霉头的小“贪污犯”上门受审。
南京国民政府构筑的一套司法腐败的防治机制运作效果不佳,影响了司法腐败的防治 。司法腐败防治机制功能的弱化,随着其政权后期不可逆转的政治、军事危机,而引发 了司法信誉危机、社会诚信危机,使得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发生崩溃。民众合法权 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自然普遍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由于司法机制也是整个国家政 治机制的一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日益严重,并不完全是司法机关的不是, 司法机关只能等案办案,如果相应机关不加配合,司法机关即便有心惩贪,也无力传讯 案犯。抗战以后,贪赃枉法的案件如果都被移送到法院,依《惩治贪污条例》一一法办 ,整个法院系统也无力承办。其实,也正是这帮贪官污吏蛀空了其政权的根基,司法腐 败得以滋生蔓延,直至政权一败涂地,覆水难收。
司法机制的良性运转,是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良好的政治机制,则是司法机制良性 运转的根本保证。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腐败,既是政治危机的结果,又是政治危机的加 速器。缺乏良好的政治环境,再好的防腐机制也毫无效用。这一点,国民政府的教训是 深刻的。
标签: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检察官论文; 司法行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律论文; 监察对象论文; 行政监察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