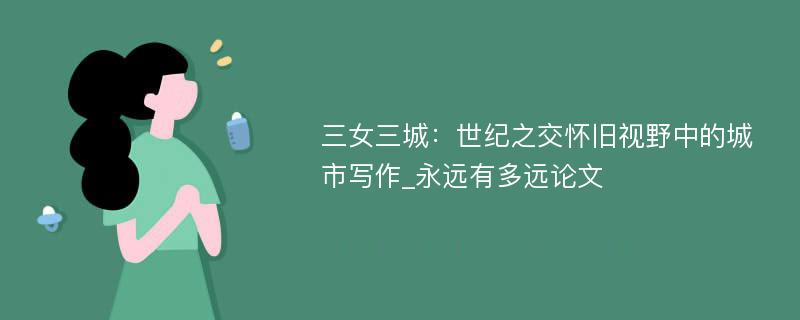
三个女人与三座城市——世纪之交“怀旧”视野中的城市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三个女人论文,三座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出现的三部中长篇小说:铁凝的《永远有多远》(1999年)、王安忆的《妹头》(2000年)、池莉的《生活秀》(2001年),是颇值得关注的分析对象。这三部小说均由当代重要女作家创作,发表于相近时间,并引起了超越文学文本的广泛关注:《妹头》入围第二届(2001年)鲁迅文学奖;《永远有多远》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生活秀》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连续剧和话剧,并带动北京城大街小巷名号不一的“鸭脖子店”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这三部小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城市/女性的同构书写,表现出颇为典型的文本特征。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作为一个重要书写对象,越来越醒目地凸显于中国大陆文坛。城市不仅构成文学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景,而且构成文学表现的独特的审美对象。由“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建筑群,由胡同、弄堂和老街构成的城市空间,生活其间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方式等,这些现代都市场景,开始被文学呈现为有着内在精神构成的寓言化或人格化主体。这种书写主体的形成,显然联系着90年代后大陆新一轮的城市扩建高潮,联系着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空间的扩张和重新组合,同时也联系着文化消费市场对于城市身份命名和认知的内在需求。似乎是,在推土机和塔吊的轰鸣声中渐次消失的“老城市”以及拔地而起的新摩天大楼,和在“拉动内需”的刺激下形成的节假日漫卷全国的旅游观光人群,共同创造了一种兼容了“怀旧”和“命名”需要的文化动力,使城市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会处呈现出形态各异且栩栩如生的面貌。颇有意味的是,当城市被作为独立表现和命名的对象时,文学再现中的城市大多长着一张女性的面孔,城市与女性的同构书写,成了一种关于城市再现方式的模型。因而,本文尝试以《永远有多远》等三部小说作为分析个案,从较为宽泛的纬度挖掘城市书写和女性表象的意识形态内涵。
三个女人与三座城市:城市/女性的文本同构
《永远有多远》、《妹头》和《生活秀》,均以一个女性作为书写的核心对象,并明确地将其视为一座城市的精神象征。
《永远有多远》一开篇便用一个比喻,即“树叶”/“叶脉”/“汁液”,建立起北京—胡同—女性之间的同构关联,并直截了当地点明小说的书写意图。在这里,胡同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真正经脉和坐标。比起那些作为现代消费空间而崛起的摩天大楼,它们是更能标识北京并显现北京城市性格的所在。因此,不是“‘世都’、‘天伦王朝’、‘新东安市场’、‘老福爷’、‘雷蒙’”,也不是“世都咖啡厅”和“凯伦饭店”,而是那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的几乎难以辩识的旧胡同口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和“老旧的灰瓦屋檐”,让叙述人“认出了北京,站稳了北京,并深知我此刻的方位”。这位现代都市的消费者,坐在世都“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窗使你仿佛漂浮在空中”,品着名为“西班牙大碗”的咖啡,眺望着“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的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而她怀念的却是20多年前胡同口小酒馆的冰镇杨梅汽水。国际化的消费空间和消费者,与已然消逝的胡同和对往昔消费品的赞叹,使得小说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浓郁的怀旧情调。而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则是叙述人此刻正在等待的表妹白大省,她也正是被称为北京的“城市汁液”的胡同女孩子。在倒叙结构中,叙述人向我们展示这个女性的“仁义”品性,以及她“永远空怀着一腔过时的热情,迷恋她所喜欢的男性,却总是失恋”的故事。白大省与四个男性的情感经历,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她的痴情和善良,不能为她赢得男性的爱,而只有漠视、索取、背叛或同情。小说结束的时候,叙述人和丈夫漫步在即将拆迁的驸马胡同,感慨着白大省的“不可救药”;而正是这份不可救药,使她永远恨着和爱着白大省和北京。《永远有多远》以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女性的情感故事,来呈现北京精神的全部内涵,这一叙述结构及其象征性表达是相当清晰的。白大省的故事并非仅仅是一个女性的故事,而同时是北京的故事。她的“仁义”,她的“傻里傻气的纯洁和正派”,她的实在和“小心眼不多”,她的“笨拙而又强烈之至”的感情,也正是北京胡同的品性。颇有意味的是,小说将这种品质呈现于白大省与异性的婚恋关系当中,以她的“忘我的、为他人付出的、让人有点心酸的低标准”,来显示一种被漠视和遭鄙弃的北京城市的文化品格。
与《永远有多远》相似,《妹头》同样讲述一段婚恋故事,但占据小说核心场景的,不是人物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类人类学式的关于上海弄堂及其生活方式的呈现。在完成《长恨歌》(1995年)及《我爱比尔》(1997年)之后,王安忆在《妹头》中着力呈现的是处于上海中心的淮海路弄堂里的女孩子。同样是在一种怀旧式的倒叙结构中,《妹头》以小白和妹头这一对生长于淮海路弄堂里的小夫妻从相恋、结婚到离婚的经历为线索,娓娓讲述妹头成长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小说不厌其烦地细致描述弄堂的格局、器物、日常场景、人际关系,乃至城市的气味、日常心理和人物形状。小说的叙述视点发自小白,在他记忆和书写妹头的时刻,上海正在完成着新一轮的改建高潮,他从弄堂迁往的开发区,“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正是在远离淮海路弄堂的新居,在眺望“万家灯火”的时刻,妹头作为上海的象征终于浮现出来。面对着时尚而雷同的繁华街道上的女孩子,小白回想起往昔“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的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妹头已经消失和远离,她“飞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说《永远有多远》将胡同作为北京的核心空间场景,那么《妹头》则无疑将弄堂视为上海的真正依托;而完美地体现了“弄堂里的中等人家,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等方面的经验和规矩”的妹头,则在弄堂生活已经被高楼大厦和街头时尚遗忘和抹平的“现在”,越来越清晰地作为上海的象征,浮现于小白同时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心头。
池莉的《生活秀》书写的是另一座城市即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与前两篇小说相似,其核心场景聚焦于“蛰伏在繁华闹市皱褶里的小街”——吉庆街。小说所写是吉庆街上一个卖鸭颈的女性来双扬。围绕着吉庆街老房子的产权归属,小说节奏紧密地展示来双扬如何周旋于家族关系、个人情感之间,成功地成为老房子的合法继承人。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展示她的精明、干练、泼辣和情感牵系。小说采取了池莉小说所惯用的为“小市民”“神圣的烦恼人生”立言的叙述语调,几乎毫不迟疑地赞美且认同吉庆街女人“强健的生命力”。吉庆街对于汉口这座城市而言,“是一个鬼魅,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漂泊码头;是一个大自由,是一个大解放,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大混乱,是一个可以睁着眼睛做梦的长夜,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如张旭东在分析张爱玲的《封锁》时写道的,所谓城市的“内心”,出现于“处在不设防的、停业的、心不在焉的、梦幻的状态”,“不正常的状态比正常的状态更能有效地流露出内心活动来”(注: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上海寓言》,收入《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吉庆街的夜晚,也可以说是汉口这座城市的“内心活动”的真实流露。当人们“过着日子,总不免有那么一刻两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口里就苦涩起来,心里就惶然起来,没着没落的”时,吉庆街就成为一个情绪释放的场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场白日梦,一个欲望和潜意识汇聚的空间。它甚至比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更“真实”地显露人们的内在欲求。而来双扬,她“是吉庆街最原始的启蒙。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定心丸。来双扬是吉庆街的吉祥物。来双扬是吉庆街的成功偶像”。换句话说,来双扬就是吉庆街同时也是汉口这座城市精神内核中的欲望化主体。更有意味的是,小说相当有意识地使来双扬融会了欲望客体和主体的双重身份。小说一方面将来双扬描述为汉口这座城市的欲望投射物,一个审美凝视的对象,使她始终置于被观看的位置;同时她又并非一个单纯的欲望客体,而是深谙欲望观看机制的主体,在被看的位置上“表演”(秀,SHOW)着人们的欲望诉求——“她还是那么有模有样地坐着,守着她的小摊,卖鸭颈;脸上的神态,似微笑,又似落寞;似安静,又似骚动;香烟还是慢慢地吸着,闪亮的手指,缓缓地舞出性感的动作”。
白大省—胡同—北京,妹头—弄堂—上海,来双扬—吉庆街—汉口,这三者和三个层次的同构关系,清晰地显现于文本表达的层面。三篇小说以一个城市一种都市生存空间中的女性形象,抽象出这座城市的内在精神性格,或宽厚或精明或泼辣, 从而完成对城市的寓言化书写或人格化描绘。
时间与空间的置换:“怀旧”的文化动力
这三部小说在书写城市时,不约而同地回避了(或将其视为反面的参照对象)当代中国都市最醒目的空间标志:摩天大楼、新建住宅小区、商厦和大型超市、咖啡厅和酒吧等现代消费空间。事实上,类似的都市空间也正是《上海宝贝》等畅销小说竭力凸显的城市时尚性空间场景。与之相反,《永远有多远》等三部小说所选定的城市标志性空间,是胡同、弄堂、老街。这些空间联系着城市的或许并不悠久的现代历史,但它们确实是记录或负载着城市记忆的所在。而另一个更醒目的特征是,这些空间在趋向国际化而日益膨胀的大都市现代建筑群中,将日渐消隐或萎缩。它们是“过去”或“历史”,而非“现在”。因而颇具症候性的是,正是这些城市空间在现实中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时刻,在文学书写中,却被提升为城市的象征。
《永远有多远》的开场,类似于一种“凭吊”场景,它凭吊的是被“世都百货公司”、“新东安市场”等现代摩天大楼所摧毁、覆盖或取代的旧北京胡同。在“新北京”,胡同所存留的只是两级“边缘破损的青石台阶”和“老旧的灰瓦屋檐”,一种“隐匿”地存在的废墟性标志物。驸马胡同即将拆迁,它将被新的摩天大楼所取代,所能剩下的大约也就是青石台阶、灰瓦屋檐和青砖砌死的门,“就像一个人冲你背过了脸”,同时也是一段城市的记忆隐没于时间的背面。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关于胡同的记忆却分外活跃,在这记忆中浮现出了作为“城市的汁液”的白大省。小说的倒叙结构充分地显露出“怀旧”的时间纬度,这是在朝向“过去”的回眸中完成的关于白大省、关于胡同、也是关于北京的重写。如果说,在现实中,胡同被摧残为废墟;那么,在“怀旧”的书写中,胡同却被命名、被精神化和抽象化为北京的象征。在“新”/“旧”北京之间,不难读出,这事实上也就是“伪”/“真”北京之间的价值指认的颠倒。
《妹头》的倒叙结构与《永远有多远》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永远有多远》中作为胡同精神象征的白大省最终从“记忆”走到现实中,并一如既往地“不可救药”,她因而也象征性地承载着胡同精神由历史向现实的延伸;而《妹头》中弄堂精灵妹头则渐行渐远,不仅远离了淮海路的弄堂,甚至去往了国际都市“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几乎是弄堂长大的人们无从想象的遥远、陌生而无名的“他乡”。因此,不同于《永远有多远》由叙述人呈现的那份由爱生恨的追认、恋旧和叹惋,《妹头》表现出更为浓郁的感伤。那是一种永远不可失而复得的、永远消失的惋惜,或许可以说,那是“永远”的“尽头”。如果说,《永远有多远》的怀旧和感伤确实表现为一种“没有结果的询问”(注:铁凝:《永远有多远》“后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但“永远”一词本身却展示了一种无限绵长地朝向未来的时间纬度;那么《妹头》却终结了这一时间纬度,“过去”的消失使得“此刻”、“现在”成为无限的空洞。小说结尾出现了“飞翔”的意象:妹头“飞翔起来,很多脸都落到了她的身后。她飞翔,飞翔,一直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与这部小说前面部分关于弄堂里的生存空间、家庭教养、人际关系和情感经历等的滞重乃至沉闷的工笔描绘相比,小说最后部分的叙述显露出一种被抽空的轻盈,“飞翔”意象的出现由此并非闲笔。“飞翔”是一种漂浮的、没有质量、没有重感,因而没有历史/现实、过去/现在的感觉,它是一种时间“空无”的状态。而小说文本呈现的是,这种时间终止的时刻,恰恰出现于小白——被叙对象同时也是潜在的叙述者——终于意识到自己远离了淮海路弄堂的时刻。小说开头类似于“楔子”的小段落和结尾处的“尾声”,把小说主部关于弄堂、关于妹头、关于他们在淮海路弄堂的成长经历和婚姻生活的描写,包裹于“回忆”的叙述结构之中。小白是在新开发区的林立高楼之中和“万家灯火”的时刻,开始了回忆和书写:“远处有几部塔吊在工作,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一明一灭,更显出夜的辽阔空旷。他的思想便在这空廓中活跃着。”——同样并非偶然的是,这里所使用的“空廓”一词。如果说在小说文本结构上,弄堂部分和搬出弄堂之后的部分,形成了滞重的繁复和简洁的空灵两种叙述风格;那么人物的“飞翔”和“空廓”的心理体验中,却是“历史的时间”和“历史时间”“终结之后”的对比。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弄堂的上海”和“没有弄堂的上海”之间的对比。在此,时间和空间同样构成一种价值上的颠倒:在空间(弄堂)消失之后,时间(城市的记忆、历史)开始全方位地回缩到“过去”。这里,“历史”甚至不再借助一个抽象的人格化形象(妹头)而延伸到“现在”,“历史”完全终止在“过去”,终止在弄堂或妹头的弄堂。因此,不是“新”/“旧”上海对应“伪”/“真”上海,而是对应于上海的“非存在”/“存在”。那事实上也就是说,“现在”不再有“真正的上海”,它仅仅存在于弄堂或过去。
相对而言,《生活秀》的怀旧意味要淡泊许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活秀》刻意将吉庆街描述为一种不可取消、生生不息的存在。吉庆街不仅是有“来历”和有历史的,而且将依靠它强健的生命力一直延续下去。小说特别提到吉庆街一次又一次被政府下令取缔,但它“取缔多少次就再生多少次”。颇有意味的是,小说在描述这种威胁吉庆街存在的破坏性力量时,将其指认为“政府”和“媒体”,在这样的意义上,来双扬的妹妹来双媛构成其对立面。两姐妹生活态度的差别被书写为池莉小说所惯常建构的“市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小说中始终质疑、否定来双扬生活方式的正是来双媛。作为知识分子、当着“电视台社会热点的特约编辑”的来双媛,同时是住在“市郊新型的生活小区”“拥有自己的书房”的来双媛,一次次地质疑来双扬的生活,并最终动用媒体和政府的力量再次要取缔吉庆街。但如果小说文本所表现的,来双媛对来双扬生活方式的质疑,不过是不懂“人情世故”和“现实生活中的道理”的“生瓜生蛋”的表现,“做人都没有做像,还做什么文化人”。真正懂得生活的是来双扬。尽管来双媛已经离开吉庆街,且被人捧为是“女鲁迅”,但她生活的真正依靠还是需要姐姐来替她解决。有趣的并不在于池莉小说为什么要建构这种“知识分子”/“市民”、“夸夸其谈者”/“真正的生活者”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建构这种对立的内在逻辑。小说中有一段写到吉庆街通行的且为人们认可的行为逻辑:
说是真的,到底也还是演戏,逗你乐乐,挣钱的!挣钱就挣钱,没有谁遮掩,都比着拿出本事来,谁有本事谁就挣钱多,这又是真的!用钱作为标准,原始是原始了一点,却也公平,却也简单,总比现在拿钱买到假冒伪劣好多了。……别的不用多说,开心是能够开心的。人活着,能够开心就好!什么公侯将相,荣华富贵呢!
如果说吉庆街确实是汉口这个大城市的一场释放欲望的白日梦,一个表演的舞台,但这个梦和舞台却有着分外现实的游戏规则,那就是金钱逻辑。看起来,池莉似乎刻意将吉庆街这个小市场描述为一个公平的也自由的所在,因为金钱所衡量的是人们诚实劳动的成果,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体味一种“平等”和“放肆”的快乐,就如同“只要五元钱,阶级关系就可以调整”,就如同卓雄洲这个“体面的成功男士”,终于可以在这里逃避豪华写字楼里“正襟危坐”的拘谨生活,“仅仅花五十元钱,就让一个军乐队为他演奏了十次打靶歌”。——这种实际也实惠的生活方式,显然比起来双媛那种“奢谈”“精神家园”,奢谈“高雅”生活和“改天换地”的“知识分子”,要来得实在得多。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吉庆街才成为“大自由”和“大解放”的不败象征。来双扬也才如此笃定,坐在吉庆街正中央的小摊旁充当吉庆街的“定心丸”,也成为“天南海北的外地人”争相来到武汉所欣赏的“生活秀”的象征。
但如果将吉庆街的“挣钱”逻辑推向更普泛的层面,或者说,将吉庆街放置于当代中国城市扩建高潮的现实处境之下,它的命运显然并非如此单纯。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影《生活秀》(导演:霍建起,主演:陶红、陶泽如,2001年)显露了更为残酷的现实面向。电影相对于小说的最大改动,不在于将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汉口搬到了重庆,而是对于来双扬“生活秀”的忠实观看者同时也是来双扬的欲望对象——卓雄洲,这一人物的改动。在小说中,卓雄洲仅仅是一个“体面的成功男士”,被来双扬及其“秀”着的生活所吸引,最终在欲望真正实现的时刻因无法满足来双扬的性要求而败北离去。在象征的层面上,这一情节也可以解释为这个生活在“豪华的高层写字楼”中的都市男人,事实上并没有能力承受吉庆街女人强健的生命力。这也在另一层面上再度证实来双扬作为城市象征的力量。而在电影中,卓雄洲成为了一个拥有雄厚资产的房地产商,他不仅被来双扬所诱惑同时也诱惑着来双扬,最关键的是他买下了吉庆街的地产,并要将其改建为另一处高楼大厦。也就是说,是这个比吉庆街的人们有“钱”得多的大款,而不是小说中的政府和媒体,最终将彻底地取缔吉庆街的存在。也正因此,在电影中,吉庆街始终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视觉呈现中:影片开始,夜晚吉庆街的全景,摄影机的镜头从高楼大厦处缓缓摇落,落在灯光灿烂但被周围的高楼所包围所挤压的吉庆街。与那些灰白色的庞大建筑相比,吉庆街的灯火显得那样孱弱。只有当镜头忽略周围高楼的存在,停留于“久久酒家”和来双扬鸭颈摊前转动的灯箱时,吉庆街才真正灯火辉煌。另一反复出现的场景,是来双扬前往戒毒所看望弟弟时,乘坐的缆车在高空穿越城市,此时在俯拍的大全景镜头中,那座城市真正成为林立的钢筋水泥铸就的现代奇观。只有偶尔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残破的黑色屋顶,显示着类似吉庆街的空间的存在。——或许正因为此,电影《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没有了小说中来双扬的那份张扬和强悍;而整部影片,也始终显露出丝丝缕缕的感伤和迷惘。影片结束的时刻,来双扬仍旧手执香烟,很“秀”地坐在自己的鸭颈摊前,但她突然抑制不住地开始流泪,为那场被出卖的情感,也为即将被推土机铲平的吉庆街。
如果说电影和小说的《生活秀》因为对吉庆街的命运有着不同的再现方式,而显露出“感伤”和“张扬”这两种不同的叙述风格,那么事实上这也正是构成《永远有多远》和《妹头》浓郁的“怀旧”情调的现实来源。朝向传统城市空间的怀旧的目光,正因为那个空间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这其中蕴涵的内在意识形态,正是关于“现代化”想象的转变。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中,高楼大厦曾经是“现代”、“文明”、“高雅”的象征,那么此时它们却成为了侵犯性的、不可战胜的、无名而陌生的庞然大物;相反,是那些曾经被批判地作为“封建”、“愚昧”、“落后”象征的旧有城市空间,如胡同、弄堂、老街(可对比于叶之蓁的《我们的建国巷》、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铁凝的《玫瑰门》等的描写),则开始成为人们深情注目且无限缅怀的对象。这种变化显然因为8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在90年代的现代化(同时也是都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一种震惊性和创伤性体验,如同戴锦华在《想象的怀旧》中所分析的:“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现代化’还如同金灿灿的彼岸,如同洞开阿里巴巴宝窟的秘语,那么,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不无创痛与迷惘地发现,被‘芝麻、芝麻,开门’的秘语所洞开的,不仅是‘潘多拉的盒子’,而且是一个被钢筋水泥、不锈钢、玻璃幕墙所建构的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注:戴锦华:《想象的怀旧》,《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11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正是这种新的都市空间本身的物化特性粉碎了“现代化”的理想化想象,使得人们把目光从它们掉转开去。
但是,彼岸/此岸、未来/过去、时间/空间的颠倒性书写,并不仅仅透露出关于“现代化”意识形态想象的碎裂。《永远有多远》等三部小说在将想象的乌托邦由“未来”掉转向“过去”的同时,把“怀旧”的对象建构为一种空间性存在,即将欲望的满足落实于一种类似于精神家园的乡村式老城市空间,并全盘地接受同时也是重新建构了这一空间本身所携带的意识形态。三部小说所选定的城市空间——胡同、弄堂、老街,正是传统市民群体会聚的场所;而小说书写的重心,是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精神特征。重写这一曾被“国民性”话语视为“藏污纳垢”之所的城市空间中人们的生活伦理和精神面向,实则在重构一种市民伦理。三部小说均颇具症侯性地写到一个关于城市“老房子”的故事。祖传的、象征家族延续的老房子,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对象,而成为市民伦理的象征性对应物或一个具体而微的空间。更有意味的是,小说正是通过将女性书写为“老房子”的真正继承人或最后的守护者,建立起城市与女性之间的血脉联系。于是,这种都市书写似乎是对一种现代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质询,但它同时也是另一种或许并非反主流或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重申。那些被填充于已经或即将消逝的城市空间中的人物和故事,尤其当这种人物和故事的书写如此倚重于一种女性市民的修辞表象时,它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不仅构成对城市符号/记忆的一种消费方式,同时更是对并非老旧的市民意识形态和市民伦理的示范和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