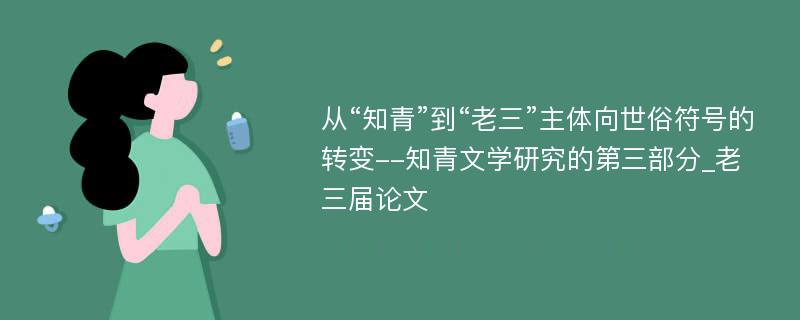
从“知青”到“老三届”——主体向世俗符号的蜕变——知青文学研究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之三论文,世俗论文,三届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2-0107-08
在《离散的历程:知青文学分类考》[1]中,我已分析过1987-1988年前后,以文学为主要表现领域的知青主体已全面裂散,曾作为“新时期”文化(学)重要主体类型的知青,似乎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将飘零为意识形态的尘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约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股“老三届文化热现象”。它一方面既重新引起了社会对知青话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似乎又想以所谓的“老三届”(注:这里给“老三届”一词加引号,主要不是因为它的专名性,而是权对这一名称的怀疑,就象对“知青”这一名称的怀疑一样。不过,为了避免繁琐,以下除必要之处将略去引号,但引号的含义依然保留。)代际主体取代知青这一过时了的主体。由于这一文化现象同知青话语的直接联系,也由于它是九十年代初中期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所以有必要对其作认真的考察。除此而外,本文还将从狭义的文学范围讨论一些前期主流知青话语的延伸性文本。
一
“老三届文化现象”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并引起了研究者广泛的重视。如文化界颇富盛名的《东方》杂志,1995年2期就刊载了《“老三届文化热”透视》一文。《中国青年研究》也从1995年始开辟专栏,呼吁各界人士对老三届文化现象进行讨论。由此而言,本文将要进行的工作或可看成是已有研究的延续,但两者又具有较大的差异。我承认老三届文化现象与所谓的“老三届人”的活动有关,但它却不是一代人的文化特性的自然社会呈现。另外,现有的老三届文化现象研究表面上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实质上则往往又构成了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我所见到的唯一例外,是戴锦华的《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载《钟山》1995年第2期。此文以其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敏锐,绽裂了“老三届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拼合性。)这正是我要避免的。我要考察的是真正的老三届文化现象而不是这一现象所关涉的所谓老三届一代人的话题。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我不准备描述老三届文化热的表面现象,(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以下文献:戴锦华《救赎与消费——九十年代文化描述之二》;陈小雅《老三届“文化热”透视》,载《东方》1995年第2期;1995年以来的《中国青年研究》杂志;刘晓航《青春无悔的深情呼唤——近期知青文学热扫描》,载《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姚新勇、葛红兵等《“老三届”文化现象批判》,载《青年探索》1996年第6期。)而想直接对该现象进行深层分析;并且我想把老三届文化现象同知青文学进行比较。因为很明显,知青文学与老三届文化现象有着直接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前提,而且,知青文学所达到的历史水平,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已往的历史对象化了,可以作为一种尺度来衡量老三届文学现象。另外,这种比较还可以使我们更切近地认识知青主体蜕变为老三届主体类型后的性质。
首先,我想对老三届热和八十年代初的知青文学创作高潮的全社会多方参与性,做些分析。老三届文化现象是一种泛文化现象,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这与成形期[2]的知青文学、知青主体的全社会共促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尤其表现在从《伤痕》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一阶段的知青题材写作上。但两者共同参与的各基本社会力量的构成、它们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状况,却具有本质差异。
知青主体的成型[2]是由民间力量、政治文化领导权力量、知识分子力量这三者的共同作用完成的。这三者中虽然政治文化领导权力量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其它两者也发挥了直接和实际作用。而且这三种力量被共同结构于反“文革”文化革命的情境(或意识形态场域)中,具有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革命性。这就决定了不管成型期知青文学具有什么样的缺陷,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文化—文学行动,毕竟在“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和文学的贫瘠状态中,结出了新的文学成果。虽然老三届文化现象的形成也与这样三种力量的作用有相当关系,但它出现的意识形态场域,是"89"风波的急停和大众商业文化迅速席卷全国的情况;支配和推动这场文化热的力量,是商业大众文化势力与一定高压性国家意识形态的威慑,而民间和知识分子因素则受摆布于上述两种力量之中,根本没有形成什么创造性的集团势力。
这种说法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老三届文化热”透视》一文就因参与创作人数之众和绵长恒久的劲力这两点,认为老三届文化热具有“创作热”的特点。然而实际上这里存在的是一种经达变形的带有几分“自产自销”的商业文化现象。这些众多的撰文者(这里主要指那些参与回忆录写作的人)的写作,基本上并不具有当初知青文学写作的创作性。大量的回忆录文章都是片断的轶事回忆,与叙事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距离。这些文章的思想观点尽管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都是被纳入文集的“青春无悔”和“苦难与风流”这个框架下的,真正具有深度的思想探索性无从谈起。他们集大众文化产品的制作参与者和消费者两种身份于一体,商业出版者不过是利用了他们怀旧的讲述和重顾的冲动,把他们集结起来进行一种群体炮制而已。这同商业性报刊所进行的有奖征谜活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另外,这些众多的写作参与者和消费阅读者,尽管也具有某种知青或老三届身份的认同,但他们并不能结成民间的集团性力量,这不过是一种更具虚幻本质的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除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外,还被作用于商业文化消费的“大数法则”。
当然,我并不否认“老三届”文化热中也有与体制主流文化相异的民间性色彩,其主要是一种民间史学性因素。大批知青运动史料集或不少史料集性质的史学专著的出现,带有程度不同的民间自发性,与体制史学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也的确间接地反映出了某种对体制冷禁知青运动史研究政策的不满。(注:知青运动属于“文革”历史的一部分,而“文革”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研究的禁区。这种状况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历届政治核心力量都是一样的,其差异不过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己。更具体地说就是,历届当局只希望人们按照它们所定的基调去理解“文革”,而不希望对其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仅就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学来看,(注:在体制许可的当代史学研究空间之外,很难说没有真正异质性的民间因素,只是它们处于一种隐在状态而已。这可从《二十一世纪》(香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得到证明。两刊已陆续登载大陆人士对“文革”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和意向显然与体制正统史学有很大距离。不过似乎也不能对此估计过高。因为在重新复刊的《今天》上的有关文章,似乎与大陆的老三届言说没有质的区分。参见《未完成的篇章——为纪念〈今天〉创刊十五周年而作》,《诗的往事》,分载《今天》1994年第1期和第2期。)这种民间意识并没有多少真正富于革命性的创造力,更多地带有窥秘的猎奇心态,而这一点正是大众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携手共舞的隐性契机所在。它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间力量,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至于那些积极参与老三届热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总体上也局限于老三届话语的限制:个别表现出批判力度的言说,也被大众的窥秘性消费热潮和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所淹没与扼杀。至于这些文化人中有不少带有商业性动机,具有某种“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的心态,就更不用提了。[3]所以我们可以说成型期知青文学属全社会性泛政治文化批判建设活动,而老三届热则是商业性泛文化活动。
二
上面主要是从宏观意识形态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下面我想更进一步具体比较知青话语与老三届话语。
首先,让我们来看老三届概念与知青话语的关系。我不清楚“老三届”这个概念究竟起于何时,它很可能早在“文革”期间就产生了。但是任何概念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一个由书写符号组合而成的具有固定含义的名称,由于时代的不同,它所具有的含义肯定会有极大的差异。现在人们对老三届这个概念的使用大致具有这样几个基本含义:一是指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二是指那些曾经积极参加了“文革”初期的造反与大串连活动的红卫兵;三是知青运动中首批上山下乡的人;四是备受磨难、人生阅历丰富的具有理想主义的一代人;五是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应该说,这诸种含义的老三届概念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在知青文学中或者说被知青作家提出了。最著名的如张抗抗的《塔》与肖复兴的《啊,我的老三届》。《塔》是有想把“老三届”从泛义的知青中区分出来的意味(至少客观上给人这种印象),但它更着重的是对所谓老三届一代人的自我反思;“老三届”这个概念更主要是作为一种集合概念,而非一面骄傲的旗帜。作品人物更引人注意的是知青身份,而不是老三届。相较而言,《啊,我的老三届》则是更直接、更纯粹地来写老三届人,而且对他们的记写也更着重于目前现实生活的报告,更富旗帜性张扬的意韵;也有评论指出它为“老三届一代人”而写的意义。但是主要由于社会接受的原因,当时它也只能是一种零散的声音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塔》的反思,还是《啊,我的老三届》的不无赞美性的报告,都与老三届话语的激烈、冲动、自豪甚至还带有怨愤的“青春无悔”、“苦难与风流”的旗帜或焦点有相当距离。这种激情的喧哗还需同主流知青话语进行更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不是仅仅与一两篇作品或某一概念的联系就可以阐述清楚的。
“青春无悔”作为一面“鲜艳的”旗帜是进入到九十年代后才被高高扬起、呼啦啦作响的,它招至广泛的喝彩与不少的讥评。但这面旗帜当然不是老三届人自我缝制的。就知青文学总体发展来看,无悔的激情、自我肯定的冲动,从伤痕文学中的知青作品起就逐渐成为主流知青话语的基本要素之一;(注:如果再联系到《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更早了。)主流派知青小说所充满的“两级抗衡的张力:压抑与反抗,理想与现实,崇拜与反叛,爱与恨,拒绝与依恋,掘弃与回顾”,都与这种所谓的不悔的知青情结密切相关。[4~5]尽管在我已发表的知青文学研究论文中,我曾对这些内容做了相当严厉的评析,[1~2]但是八十年代末期之前的知青文学,毕竟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做出了贡献。因为那时所谓“知青情结”的对立性矛盾和困惑的激情,并不是赤裸裸的、声嘶力竭的自吹自擂。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场域和文化生态,使这种对立还富于创造性、批判性张力,而且那时他们的确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拥有更多、更为真实的青春激情;这一切共同促成了主流知青文学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艺术魅力。可是当这些曾经是强烈的思想情感的矛盾,直接归结为“青春无悔”的喧嚣之时,当那些不无怨愤式的指控与自我肯定,更多地染上自诩式的“苦难风流”的吟唱之际,当涸渴而疲惫的已频近暮年的心态,被自己和主流意识形态牵强地延迟扮演时代青年的时候,创造性、批判性的张力就基本丧失殆尽,变成了一种自欺的矫情和做作的“青春”激情。所以梁晓声在1995年举行的老三届晚会上,以类长辈的口吻告诫青年人,要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父母时,就与那延迟了的青春形成了讽刺性的对照。无怪乎一个也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发出这样的感慨:“反复吟唱‘青春无悔’之类究竟还能在这个时代激起多少涟漪……难道我们的生活哲学都贫困到如此地步了吗?连语言也显得那么苍白空泛,没有生气。”[6]
三
上面的分析比较笼统,多结论式的评语少具体的分析,这对总体的老三届热现状与那些回忆录合集还较合适,而对那些个人的长篇来说就显得有些武断,所以有必要具体分析几部当时比较走红的作品。
首先来分析梁晓声的《年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此部作品长达907页,可谓是大部头之作。不过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上不仅没有超越梁以前的知青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地蜕化,矫情苍白而无力。全书基本的情节结构线索是按主人公们的几个生活年代(1961年饥饿时期、文革时期、兵团时期、返城初期、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唱主角的时代)自然延续而成。这倒是切合《年轮》二字,却也突出了构思的平淡无奇。再细看具体的章节内容安排,就不令是平淡无奇,而更接近于旧作拼凑和支离破碎了,这点相当明显。如关于主人公们知青岁月生活的第三章就可以发现不少梁晓声以前知青作品的痕迹,像《为了收获》(《青年文学》1984年第10期)、《兴凯湖船歌》(《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等。还有起承转作用的第八章第一小节,也不过是《今夜有暴风雪》的并不高明的改写。(注: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进行比较:一、整体的情绪描写;二、溃散而归的返城之兵;三、徐克奋不顾身保卫自己的一车炭,与《今夜有暴风雪》中知青保卫国家财产。)第二节则直接套用了《雪城》下部一开始的情节、语言和情境。
不仅如此,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显得陈旧乏味和煽情。与知青情结理性的告别和情感依恋的冲突早在《雪城》中就已淋漓尽致地渲染表现过了。苦难的磨炼对所谓这一代人品格的黄金般的意义,是不乏鼓励人们自强不息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渲染却替代了对1961年全国性饥饿的当下诸多政策性、经济性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也许这种批判的要求有些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太强人所难,但是作品关于苦难是黄金的描写,与非智化倾向的联系则是不能不点到的。同梁晓声以前大量的代表性作品不同,《年轮》只用了一章不过88页的篇幅来描写漫长的十年知青生活,而且只稍微详写了知青刚到北大荒时的不乏悲壮性的头几个月的拓荒故事,以后的知青经历都被扫略点染而过。作者刻意强调的是主人翁童年时期的生活,细致反复地描写了童年的苦难和含辛茹苦的母亲们对这些主人翁们一生永远的烙印。这样长达114页的第一章就奠定了全书的基调。我不否认早期童年生活对人的可能性基本影响,但是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尤其是对梁晓声这样的“首席”知青作家来说,过分渲染少年经历,而忽略“文革”影响(注:这是第二章的内容,只有52页。基本强调的是红卫兵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而这人情味又是被少年生活经历奠定基础的。)和知青经历,若不是表现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无能,也至少让人怀疑那曾经推动过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不悔情结,已蜕化为幼稚而近蛮浑的反智性倾向。如果说作品的这种情节、情感逻辑的安排与反智性情感的联系还比较隐诲的话,那么书中许多直抒胸意的议论,则是赤裸裸的表白了。且看《年轮》的封底题辞:“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的荣耀”。照此而言独特的希特勒也可以荣登历史的明星榜了。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反智倾向是整个老三届话语的基本倾向之一。晓剑的《中国知青秘闻录》整本书就是把知青浓缩为一个类人猿的存在,将传说、实史,编造拼凑在一起,歌颂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致的所向披靡的不悔人生。翻翻众多知青回忆录合集,几乎每本的前言或后记,对如何评价知青运动或知青一代都有一种不甘而又无可奈何的放弃心态。就连颇具批判和反思性的《中国知青梦》的结尾也这样写道:“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时代的同龄人对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还原一个历史过程……”。[7]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曾经红极一时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如果列入“新移民文学”之列可能更为合适,与《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这类作品共同填塞着千百万憧憬西方世界、梦想发财致富的欲望,并使这些欲望得到想象性的暂时满足。不过由于它有意识地强调主人公过去的知青苦难经历与其异国闯荡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把它纳入此节讨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讲述了一个东方丑小鸭变成西方美天使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一文不名被人鄙视瞧不起的中国女人成功地征服美国成为商业成功者的故事。然而可惜的是,这种自豪的成功(发财)史的叙述隐形逻辑就是萨特分析过的自欺(Bad-faith)。主人公未加反思地先在性地把美国式的存在定为欲超越的对象,视为是其所不是,这与她作为一个贫穷的中国女人的是其所是的存在形成了一种镜象式的她—我关系;在那对象化的镜子中,她看出傲慢的美国和屈辱的中国,从而刺激了她超越对象,征服对象,确证自我的欲望;而当她最后自以为终于征服了对象,可以自豪地扬起她那颗中国女人的头颅时,也正是她丧失了自我,被对象性的美国存在方式所吞没的时候。用抽象的哲学表述就是,作为成功者的她,是以其所欲征服的其所不是来证明不再是其所是的过去的其所是;若以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就是;她是以变成美国中产阶级上流社会富婆的成功,来宣布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女人的骄傲。所以这种骄傲与其说是面对傲慢的美国所昂起的中国头颅,毋宁说是显示给已不再是她的中国同胞的炫耀面孔。
当然自欺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存在性陷阱,而且这里所分析的对西方既崇拜又欲征服的自欺心态是相当普遍的,似乎不必对《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大加讨伐。但是普遍性的存在弱点,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都不能作为它逃避批判的遁词。因为它不仅显得相当浅薄,而且还以苦难的知青经历和所谓的老三届的不屈奋斗精神,冒充着时代的楷模和理想主义的英雄,可谓是右手拎着时代的钱袋,左手举着理想的旗帜。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偶然的作品,还表征了老三届文化现象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注:与其大同小异的老三届(知青)叙述很容易发现,读者不妨去翻翻《劫后辉煌》、《我还是我,周励》、《苦难与风流》、《中国知青在世界各地》、《青年流放者》……)
当然过去知青苦难的经历,并非都被当作点铁成金的魔杖,也并非都被缝制为今日辉煌之袍的衬里,像《孽债》、《中国知青梦》就各具不同程度的沉重感。叶辛将《孽债》解释为“难以还清的感情债”。一些评论同名电视剧的文章也认为该作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历史感,它形象而生动地说明,过去的历史不会轻易与一代人告别,历史以新的方式,对两代人发生着影响。不过尽管这样的评论并不算溢美,尽管这部作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平心静气而论,此作并没有达到八十年代知青长篇作品的水准。按说《孽债》利用血亲关系这一纽带将过去的历史与当今的现实,将偏远的景颇山寨同上海大都市联系起来,客观上具备了形成时空交叉、纵横交错的宏篇巨制的可能性。然而作者把矛盾的焦点过分直接地定位于普通的亲情关系和世俗人伦关系上,使得这种可能性流产,读起来给人的感觉相当接近于《渴望》这类室内侃剧——或曰一种中国式的肥皂剧。
四
纵观整个老三届文化热中的知青题材写作,唯有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既旗帜鲜明地质疑和批判了“青春无悔”这面老三届旗号(或曰知青情结),同时又将它所含有的情感冲动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地创造性批判,从而将青春无悔的激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的悖论是很明显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开这一悖论,对此部作品作出更接近历史实际的分析。《中国知青梦》发表后不久就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好评。(注:《中国知青梦》发表后不久就在京召开了座谈会,王蒙、雷达等文艺界知名人物出席。参见《当代》1993年第1期。)除赞誉外,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取得成功。大致观点是:这与作品所写内容有一定的关系但却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关于知青大返城事件已不是什么秘密,它已断续地在各报刊上散见了,而且在它之前郭晓东的《中国知青部落》已相当直接地描写了此一事件。它的成功关键在于作品对历史结构关系的宏观把握与具体微观分析的成功配置。说白了就是,《中国知青梦》不是靠题材的新奇与爆炸吸引受众,而是靠历史的穿透性征服读者。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说服力,但却有些过于在大众接受层面的成功和文化历史批判深度上的成功两者之间划分界线了。实际这两者对《中国知青梦》的大受欢迎可能是互相渗透的。我想这涉及到应该把《中国知青梦》放在什么样的文化结构场域关系中把握的问题。
我以为《中国知青梦》的成功,是因为它以其自身的能量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历时和共时的纵横交充叉点。早期“伤痕型”知青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血色黄昏》——《苍凉青春》——《中国知青部落》——《中国知青梦》是历时性横轴;漫溢九十年代前半期的老三届文化热是共时性纵轴。历时性横轴实际是“伤痕型”知青文学的点状弹进,(注:我这里之所以用“点状弹进”而未用“发展”,主要是强调由于政治禁忌所造成的此类作品产生的非连续性。)也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知青运动史自觉不自觉的书写过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以及连带事件一直是历史研究和理性分析的禁区,是社会公开言说的禁忌。然而不论是众人们的天生的窥视欲望来说,还是以文革对当代历史的重大而持续的影响来看,彻底禁说既不可能,也不明智,于是文学或准文学(这里指那些各类报刊上的所谓的记实性文学作品)的言说被体制所默许。自然这种文学的言说也不可能不服从于体制舆论导向和其意识形态指向的控制,带有特有的扭曲性。
早期“伤痕型”知青写作的一些作品是暴露了知青运动的某些负面效果,然而它们不是从史的角度(文革史与知青史相互结合的史学角度)展开创作思维的,而是过于直接地受限于当时政治主导话语的局限。另一方面它们往往把知青的苦难作为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往事,又实际上遮盖了1978-1979年之交正展开的知青返城风暴。不过比起《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来看,它们毕竟更多几分事实的真实性,而不象后两者那样更近似对知青运动史的美学化变形。大约同一个时期出版的《血色黄昏》、《苍凉青春》、《中国知青部落》比起前期作品来,带有更刻骨的真实性,而且也以其各自不同的角度多了几分知青运动史学的穿透性和沉重感。(注:《血色黄昏》成书于七十年代末,但其既不脱开“文革”背景,又欲把知青经历作为一种历史运动来把握的意图(尽管老鬼还不很清楚地意识到此点)却是超前的。《苍凉青春》写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已变成了农民的知青故事。它所采取的素朴而非娇情的平实报导手法,具有特殊的心理震动性。)不错这三部作品都是记实性报告文学,结合1988年左右所谓的“报告文学”大潮,我们不难体会它们与当时不无焦躁的普遍社会心态的关系。陈思和把这变形了的八十年代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辉煌,看成是“有点象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走向晚清谴责小说一样,实在表明了一种英雄气短。”[8]不过这种比附可能多少忽略了七十年代末以来文革讨论和史学禁忌造成的文学越俎代疱的现状,忽略了这种禁忌所造成的大众窥密欲求、民众不满情绪、社会直接批判性冲动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我们再结合1989年“六·四”之前的新闻界的各种动态的话,我们是否更该强调一种归位性要求(即将文学、史学、社会文化理论批判、当下经济学、政治学分析的学科各自分立)的难以继续控制和某种契机的到来?(注:这种由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所造成的情况,实在与讽刺小说“演变为谴责小说”不同。那时文学过分的政治化不主要是由强制性的政治控制造成的,而是与“政治小说”倡导者对文学政治功能的夸大关系更切。)虽然那场风波的戏剧性突变在社会表层上打断了文学与社会科学可能性正常的发展,但前述的那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搅和并没有消失。正是它提供了《中国知青梦》大获成功的重要契机之一。
现在我们再来看老三届文化热的共时性这一极。它对《中国知青梦》的影响是多重的:那种“青春无悔”的自美情结至少构成了作者创作的直接性动机之一,同时它也与作品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和火热的批判激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也由此造成作者被缠绕于青春无悔的情结中而难以自拔。(注:这无需多论,不仅作品本身就很清楚,而且当时的许多评论也是围绕此展开的。相当有趣的典型就是梁晓声的《关于知青文学的断想——兼评〈中国知青梦〉》,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这是就作品自身而言。从它的存在合法性与社会接受方面来说,情况就更要复杂了。作者拘于“青春无悔”的老三届话语范围这一选择给他提供了双重合法性:第一是公开在《当代》这样重要杂志上发表的政治宽限度的合法性。作品的第一段题记就隐含地说明了这一点。是呀,不论作品所暴露所批判的历史情况多么黑暗,也不管它实际批判的触角已超越了文革十年,但它毕竟“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和那个时代的书”。[6]第二是老三届热文化氛围的适时性,既可能满足知青情结迷醉者的口味,又投合了对那种过分自恋不满的社会情绪,对那些无所谓迷醉也无所谓反感的但也受到了老三届现象、知青现象影响的人来说,它又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书。历时和共时交叉点位置对《中国知青梦》的意义还在于,历时链为共时性青春无悔的激情提供了形成张力展开的载体,避免了这种激情流于浮躁、苍白喧哗的命运。也就是说带有现实主义的历史批判性意向与强烈的情感得到了一定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知青梦》特有的魅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老三届”文化热总体并没有结出真正的文化果实,根本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倡导者们的过分激情,甚至与青春无悔的执迷也无必然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激情的掀起、青春无悔旗帜的张扬,有着复杂的现实——历史原因,而被卷入这一文化现象中的绝大多数人们,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复杂的原因,将青春不悔的激情,虚幻地归属为老三届一代人,而且又使这种带有不妥协反抗精神的激情,远离现实——历史的批判。这样,就必然造成为激情而激情,为旗帜而旗帜的表征:激情就流于纯粹的矫情,旗帜蜕变为空洞的符号。所以在其热闹过后显得那样干瘪空洞,毫无光彩和生命,就像是红外膨胀之后坍塌的白矮星一般死寂。
[收稿日期] 2000-12-11
标签:老三届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今夜有暴风雪论文;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论文;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论文; 年轮论文; 血色黄昏论文; 青春无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