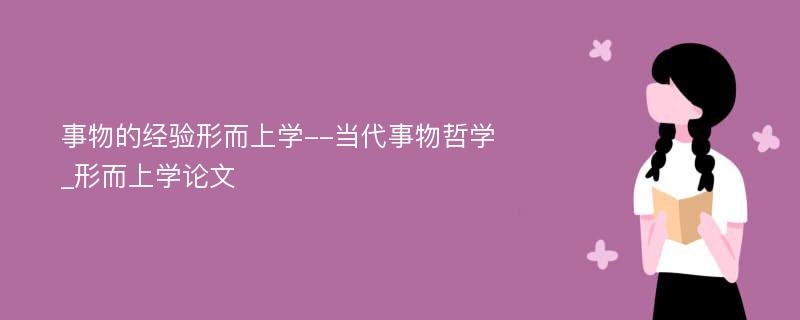
物的经验形而上学——当代Samp;TS中的物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经验论文,T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传统科学哲学和早期S&TS的认识论抱负不同,当代S&TS(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开始将学术视野扩展到本体论,发展了一项形而上学的事业;同时,由于它大多采用人类学或经验哲学的方法,规避纯粹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进路,因而这项事业又是经验性的。在此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经验形而上学、“实践形而上学”①或“应用形而上学”②。如果形而上学成为经验性的,现实世界中的“物”③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注点。当代S&TS采取了诸多进路对物进行经验哲学反思④,这种新的物哲学,一方面为人们重审传统科学哲学的许多难题提供了新的洞见,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在当前的技术化时代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哲学审视。 一、从主客二元论到物的实践一元论 在传统科学哲学的语境中,物呈现为客体、实在等概念的形式,因此它要么被作为形而上学的因素而排除,要么被视为科学的本体论根基而封存起来,不管在何种情形下,物都是脱离历史和实践视野的抽象存在,规避了实践分析的可能性。在S&TS领域,对布鲁尔式的社会建构主义而言,由于其经验进路的不彻底性,因此仍未跨越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界线,物也就脱离了其哲学视野,就如他在与道金斯的争论中所强调的,其哲学关注仅仅是“关于自然的表征”,而非飞机本身;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开始关注物的本体论地位,但由于其思想中存在着巴什拉应用理性主义与布鲁尔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他对布鲁尔宏观因果模型的微观化改造,实际上仍然将物归属于社会,也就缺失了对物本身的真正关注。上世纪80年代S&TS的一场学科危机,促使了一种新的物哲学的产生。当然,这并非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联,而只是说前者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学术契机。 1.本体论的对称性 80年代初,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如SSK)为代表的S&TS的不断发展,传统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这场运动在认识论上的破坏性,并对之展开批判。如劳丹为代表的认识论与合理性的批判、科尔为代表的对因果模型的发生机制的批判等。尽管这些批判并未削弱S&TS的学术影响力,但也引发了S&TS内部的诸多反思。一方面,伍尔迦、塞蒂纳等人开始质疑社会的本体论地位,认为社会无法为科学提供根基,因为它本身仍需要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拉图尔、卡隆直指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二分,认为不能在内容(科学)和语境(社会)之间设置对立,而后在两者之间做选择,而应深入科学实践,切实考察实践中行动者的网络建构机制。这样,自然就开始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卡隆和拉图尔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 对称性是理解S&TS的恰当切入点。在布鲁尔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如拉卡托斯)是不对称的,因为它在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划界,从而将前者交给哲学家,于是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科学提供定义,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而将后者交给社会学家,进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么考察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要么找出科学出错的社会原因从而为科学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经验(劳丹所谓的不合理性假定)。鉴于此,布鲁尔提出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前者要求对真理与谬误保持公正态度,后者要求用同一类原因解释科学的成功和失败。不过,这种对称并不彻底,因为它仍停留在认识论层面,在本体论上依旧极端不对称。因此,卡隆和拉图尔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要求将自然和社会同等看待,以消解传统进路关于自然和社会在认识论解释权上的对立与互斥。 回归自然,并不等于回到传统实在论。因为这里的自然是指内在于科学实践的物质性因素,并不具有超越性。自然与社会的超越性都是人们的虚构,就如同波义耳和霍布斯的争论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然(真空)和新的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巴斯德的科学研究也为自然和社会增加了新的内容(作为自在之物的细菌和巴斯德化的法国社会)一样。客观的自然与超越的社会,与其说是科学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科学的结果。这样,一方面规避了拉卡托斯式的目的论和布鲁尔式的因果论,另一方面本体论也就从对超验实在的哲学思辨转变为了对可见实践的经验考察。因此,自然的回归的真正含义是将哲学视野贯彻到实践层面,进而赋予实践以本体论地位。只有这样,一种物的哲学才成为可能。 2.二元论从未存在过 消解二元论、打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本体分割,是当代S&TS的共同目标。基于对科学实践的考察,皮克林用冲撞的辩证法否定科学实践过程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分裂,从而提出实用主义实在论和后人类主义的哲学立场。哈拉维立足于女性主义,以赛博为切入点,消解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理世界与非物理世界之间的界线,导致“身份的破碎”,“我们自身都成为了赛博、杂合体”,因此“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本体论的分割”⑤。在此基础上,哈拉维质疑一切二元论,呼吁一种新的赛博本体论。海尔斯则进一步将人与机器的联合体称为后人类(posthuman)⑥。 基于对科学实验室的人种学考察,拉图尔指出,自然和社会的超越性仅仅是科学研究结束之后所带来的假象,它们实际上都是内在于科学实践的,是实践的理论建构物。而现代哲学却忽视物在现实中的多样性和杂合性,从纯粹的自然极和社会极出发,进而从物身上纯化(purification)出主体与客体,以此消解转译(translation)的工作。既然纯化是虚假的,那么,作为纯化结果的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也就是虚假的。进而,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现代性或现代哲学也就是虚假的。基于经验哲学立场,拉图尔呼吁一场“反哥白尼革命”,即不应再让世界围绕客体旋转(客观主义)或主体旋转(康德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而应该从主与客的中间地带、从物出发来反思主客两极。在此意义上,以主客二元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性根本未曾实现过,与前现代人一样,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非现代的世界之中,现代性在西方人身上所塑造的时间分割以及在西方人与非西方人身上所划定的空间分割都不存在,现实与历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网络的规模,这种差别是量的差别,而非本质差别。 3.从孤立的客体到“集体”中的物 在消解主客二元论的基础上,物的界定方式发生了两个层面的改变,一是从实指性界定到述行性界定,二是从实体性界定到关系性界定。 物的实指性界定方式,首先在语词与世界之间划定分界,而后考察语词与外在指称物之间的关系,并主张前者从后者获得内涵。皮克林和拉图尔主张用述行性(performative)取代实指性界定。述行,在皮克林的体系中,是作为表征科学观的替代物出现的,它具体指代科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与物质世界发生的关联,进而,科学的根基就不再是某种实体性存在,而是实验室内的操作过程。拉图尔将述行这一符号学术语,扩展到了对物质世界的分析中,从而将符号学的内在指称模型改造为了流动指称模型。在后者看来,科学家的实验操作实际上是人与物质世界的互构过程,科学及其结果(事实或物)都在这种互构中获得界定。例如,当科学家们要确定雨林和草原之间的界线变化时,其操作包括:按照一定规则在雨林和草原上划定标记、在标记处打孔、从孔洞的一定深度取土壤样本、将样本放入土壤比较仪、在土壤比较仪上标记颜色、将土壤样本转变为数据并最终将之塑造为科学论文的一部分。在传统指称理论看来,问题在于论文的结论是否指称了真实的世界,而拉图尔则认为,科学所指称的并不是外在的雨林和草原,而是从雨林和草原到最终论文的转译链条,这一链条的完整性保证了科学的合理性。同样,TRF也并非指代自然界的某种结构,它对应于某种生物鉴定程序;细菌和钋也非凭其内在性获得界定,而是对应于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实验过程中的一系列操作,只不过当实验结束、黑箱被关闭时,“行动之名”成为了“物之名”⑦,于是,物开始获得自存性和超越性的假象。 实体性或实质性的界定方式认为,物是实体性存在,拥有固定的本质,由此,物通常会获得实在的称谓,甚至如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成为了一个难以接近的概念,而属性则与实质相对,成为物的附属物。当代S&TS消解了这种本质主义界定方式。有学者认为技术物具有物理和功能双重本质,而且这两种本质都无法在各自单独的概念框架内得到解释,因此必须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融合物的物理属性和功能属性⑧。在对某些历史案例的物质符号学解读中⑨,劳视物为关系效应,但拉图尔并不倾向于劳的关系主义定位,他担心这一术语的共时性特征会消解其时间性和历史性内涵。与劳的社会学和历史分析相比,拉图尔的讨论更哲学化,这种讨论最初在其形而上学体系中展现出来,后来又体现在对物的经验哲学考察中,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具体化。 拉图尔形而上学体系的首要原则是非还原性(irréduction),“万物,就其本身而言,既非可还原又非不可还原到他物”。显然,这一原则所要否定的就是对物的实质性界定方式。在他的框架中,物被界定为“力量的考验”,“行动者是一个本质还是一段关系?如果没有考验,我们就无法言说”。“考验”并不是一个专指名词,它所指代的是不同行动者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也可以用其他的词如“凝结”、“折叠”、“遮掩”等来替代。既然万物是非还原的,那么“万物,只在一个地方,仅仅发生一次”⑩。由此,可以将非还原性分解为两个层面,一者是内在的,一者是外在的。前者是指物并不拥有内在本质,物的改变也是不可逆的,存在着时间的不对称性;后者是指物的本质不能由外在关系永恒决定,因为关系仍处于时间之中。在拉图尔将这一形而上学体系具体化为行动者网络理论之后,这种界定就更加明显。“界定行动者的关键是它在实验室的考验之下的所作所为——它的述行”(11),这就与拉图尔对物的述行性界定联系起来;同时,行动者不是“占位符”(placeholder),它“必须能够带来差异”(12),这样,行动者不仅没有了本质,因为某一行动者是从其他行动者那里获得界定的,而且也超越了物和人的界线,甚至超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线,因为虚构之物如神话人物、电影角色,只要能“带来差异”,就可以被视为行动者。因此,他提出用符号学的actant来代替actor,以表达行动者的这种非本质性特征。如此,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人与物交杂的世界,拉图尔将之称为“集体”或“物的议会”(13)。 因此,物不再是二元论框架下独立存在的抽象客体或实在,它成为了实践中处于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杂合体。哈拉维和劳的“物质符号学”、劳的“异质工程学”、林奇的“本体图式”、皮克林的“冲撞式实践”、拉图尔的“行动者—块茎本体论”等,都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 二、通过对“实在”的改造重回唯物主义 既然物在本体层面是杂合的,那这种杂合性又是如何获得的呢?这就涉及到对物的建构性的讨论。 1.物:因为被建构,所以实在 传统二元论无法赋予物的杂合性以真正的本体论地位,因为它将物等同于基础的、本质的、隐蔽的实在。后者的纯粹性与超越性,一方面无法与物的杂合性相容,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求物只能在0(不存在)与1(存在)之间做二值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具有时间性,即是说,一物存在则永恒存在,如果不存在也就永远不存在,不会有在某一时空中开始存在或变得存在的东西。这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实在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争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当代S&TS破除了这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使物摆脱了超历史的普遍性框架的束缚,进入到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物不再是抽象的类概念,成为了实践中的、具体的、此时此地的物。这种彻底的经验立场,使物同时获得了杂合性和时间性。 从词源上看,fact最初与doing、making联系在一起,意指某种被制造的东西,17世纪以后,它慢慢获得了“非人造”的含义,甚至指代被给予(given)的东西(14)。在此意义上,科学哲学自休谟和康德以来一直纠缠于下述矛盾中,“一方面,事实是在实验中被制造出来的,从未逃脱其人造背景,另一方面,就本质而言,事实又不是人造的,[实验中]出现了某种非人造的东西”(15)。而拜物(fetish)一词则与事实相反,它本身空无一物,就如一张白纸,等待着人类情感、希望、意志等的投射,在此情形下,人们反而遗忘了它的物质属性。为了表明两者同时具有人造性和非人造性的特征,拉图尔巧妙地将这两个词融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新词“factish”。factish的含义与拉图尔对reality一词的改造(带有巴什拉哲学的印记)联系在一起。在拉图尔看来,实在的原初含义是关系,“如果实在具有什么含义的话,那么,它所指的就是‘阻抗’……一力之重压的东西……那些无法被随意改变的东西就是被视为实在的东西”(16),进而,“任何经历阻抗考验的事物都是实在的”(17)。拉图尔甚至提出了“阻抗梯度”的概念,以表示实在的真值并非只有0和1,还包括了从0到1之间的众多状态,对阿哈米斯(ARAMIS)的“恋爱史”的考察,就清晰展现了这种本体论地位的可变性。由此,实在被改造为了实存(existence),甚至“相对实存”。而物的实存则靠网络与关系(替代与联结是其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式)的建构来维持,于是,事实的客观性和拜物的虚假性,被factish的实存性所取代。进而,问题不再是“它是实在的还是建构的?”,而是“它是否被建构得足够好,从而能够成为一个自治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拉图尔的观点是“越建构,越实在”(18)。 当代S&TS学者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工作践行了这一立场。有学者通过对化学史的考察指出,许多物质都是“化学制剂或人工制造物”,就如水一样,H2O与自然状态的水不仅在“化学意义上”相差甚远,甚至“拥有不同的所指”(19)。拉图尔本人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在学者们发现某些对象‘之前’,这些对象存在于哪里?”。其回答是,“在科赫之前,杆菌并不具有真正的实存”,因此,“在1976年……拉美西斯二世死于结核病”(20)。这一观点尽管颇受争议,但如果站在一种经过经验化改造的物概念的基础上,也就不难理解。达斯顿因循巴什拉的认识论障碍的概念,在日常对象与科学对象之间进行区分,并将对科学对象的上述立场称为“应用形而上学”。她指出,纯粹形而上学站在“上帝之眼”的立场上分析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永恒存在和普遍存在,而应用形而上学“研究的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从实践科学家的视野中出现和消失”,进而可以说“科学对象开始存在”,实在具有了“程度性”特征(21)。与达斯顿的应用形而上学将视界停留在科学对象的领域不同,拉图尔的实践形而上学认为万物皆是如此,他对门、宾馆钥匙等日常物的分析,同样贯彻了这一立场。 2.重返唯物主义 拉图尔早期对唯物主义的理解相当素朴,唯物主义在其著作中仅有的几次讨论,也都处在被批判的位置。拉图尔后期反而呼吁“回到唯物主义”,这表明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 唯物主义的传统界定总是“诉诸某一类型的力量、某些实体和力,以使分析者能够说明、祛除或认清其他类型的力量”,“[它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物质基础来解释概念性的上层建筑”。因此,它可以帮助我们拆穿“那些试图隐藏在诸如道德、文化、宗教、政治或艺术背后的最真实的利益”。但这种唯物主义在两个层面上都是唯心的。一方面,它坚持“认知方式的几何化”与“被认知之物的几何化”之间的“符合”,因为人们将几何性质视为被认知对象的第一性质,从而将其第二性质消除殆尽。但事实上,对任何一部机器而言,作为一副设计图纸、作为“内在于长久以来的几何史所发明的同位空间的一部分”而存在,与“作为一种能够抵御侵蚀和腐烂的实体而存在”,完全不是一码事。因此,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坚持“物自身的本体论性质”与“图纸和几何空间……的本体论性质”的等同性,但这在本体论上至多是一种抽象信念,在认识论上已被抛弃。另一方面,旧唯物主义无视在机械装置生产过程中的“生产”、“确认”、“追踪”、“聚集”、“维持”和“校准”等的艰辛劳作,而仅仅认为,似乎一张图纸就决定了机器的产生,脱离了真实的实践(22)。 立足于对实在、客体与物、实存的区分,拉图尔赞同海德格尔的观点,将物界定为一种“集合”、“聚集”、“物化”(thinging)的过程,物不再具有内在的固有本质,它所指代的是各种因素(行动者)在聚集过程中聚合为物的过程。因此,旧唯物主义对物和技术的界定,忽视了它们的“物性”(thingness),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拉图尔则主张从物的角度来思考世界,从而践行一种真正唯物的唯物主义。这样,唯物主义就与其建构主义实在论的立场协调起来。 与拉图尔的物哲学一样,皮克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尽管并不彻底)强调实践操作的情境性、林奇立足于常人方法论突出科学实践的“索引性”、劳对异质性的强调以及他与哈拉维对科学实践的物质符号学立场,都主张将传统唯物主义的纯粹形而上学立场经验化,以使科学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 三、通过物消解传统哲学的三重对立 物从纯粹形而上学的实在、物自体,变为了经验形而上学的实存,这就要求对传统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进行彻底改造。这种改造消解了事实与价值、客体性与主体性、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对立,并开辟了传统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1.物的政治本体论:消解事实与价值的对立 当代S&TS首先打破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二分,下述两个例子表明了这种打破工作的两种时间进路。一方面,基于对波义耳和霍布斯争论的历史考察,夏平和沙弗揭示了科学和政治、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仅仅是波义耳的科学家继承者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家继承者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假象,在真实的历史中,波义耳和霍布斯关于“真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代表了实验哲学和理性主义两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格兰,知识的生产方式又与权威的来源联系在一起,最终,实验哲学的集体知识生产形式,成为当时混乱不堪的英国政局的最佳选择,知识秩序问题也就成为了社会秩序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考察,“实验室研究”的工作表明,实验室内的微观政治通过修辞、磋商等途径与知识的生产过程和事实的制造过程纠缠在一起。由此,对科学之政治维度的考察主要有两种逻辑进路,一是从政治维度解读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跨空间传播,二是对物之政治性的考察。前者并不必然要求一种新的物哲学,因此,在此主要考察后一进路,尽管这两种进路时常共同出现。 传统观点主张事实与价值二分,物作为事实,本身是中立的,就如出现在杀人现场的匕首,它本身是客观、中立的,不用对杀人事件负责,需要负责的是它的使用者。通过对物的建构性的考察,当代S&TS学者主张物本身并非中立,它是一种“内在的”政治存在。 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从未存在过的人造物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这些“怪物”(monsters)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类社会结构的改变。例如,温纳从技术政治理论的视角指出,技术(如纽约长岛低矮的立交桥、巴黎四通八达的道路等)通过对人类行为的选择,可以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拉图尔考察了巴斯德和细菌对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位的结构改造,因此,整个法国开始变得“巴斯德化”。在此意义上,技术物“不仅仅是某种社会秩序的象征”,以使某些人获益而某些人受损,“它根本就是这种秩序的化身”(23)。另一方面,某些技术物本身具有内在的政治性。温纳指出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必然要求对它进行集权式的控制;女性主义者也考察了某些技术物(如早期的飞机驾驶舱)内在所具有的性别偏见。 政治性是通过建构性进人物之中的。首先,在物的建构过程中,设计者的意图(拉图尔称之为行动纲领)会被内折(fold into)到物之中,如红绿灯、减速带、路边的警察或警车形象的竖牌、校园里的铃声等等。但人们一般视之为中立的存在物,这是因为,在技术物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和被设计对象是共同在场的,而当建构完成后,这种共同在场就消失了,“点化”为了具体的时空存在物,物由此获得了价值中立的属性。其次,物以规约(prescription)的方式发挥作用,规约是指先前被设计到物之中的政治性,它以允许和禁止的方式对使用者的行为进行控制,这在各类技术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上得到充分体现。第三,物的规约作用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物不能从建构性中获得本质界定,它会随着其所处的物质—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如锤子的设计者并没有把杀人凶器这一属性内折到锤子之中,但锤子仍然可以被当作杀人凶器一样,这也表明物的政治性并不必然是设计者有意而为。 借用斯唐热的概念,拉图尔将这种把物纳入其内的政治称为“万物政治”,赋予物以政治和伦理属性。进而,对物的政治和伦理分析,就不再是为物及其未来使用设定普遍原则,而是根据具体时空中物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其政治和伦理维度进行经验考察。这就要求在实践中贯彻一种“负责任的”科学观,科学研究不仅求真,因为这种真尽管是有条件的,但它是有效性的基础,而且求善,这里的善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理念,而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而生发出来的具体的善。在此意义上,林奇主张用“伦理图式”取代伦理学。 2.“集体”中的人与物:消解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对立 传统二元论哲学将客体性赋予物与对象的世界,将主体性赋予人,这两者不仅分割,而且为客体和主体所独享。但在经验形而上学看来,无历史的物和有历史的人都在实践层面得到了统一,因此这两种属性不仅不再割裂,而且相互依存。 物会分有人的存在,更准确地说,分有“集体”的存在,这种分有通过“实践”(皮克林)或“行动”(拉图尔)中的述行而获得,就如身份证既是物的存在,又在一定程度上分有了人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替代主体的存在。同时,人在实践中也会分有物的存在。一方面,人的身体会在与物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新的属性,在此意义上,人没有永恒的本质,他在每时每刻都是一个崭新的人。就如拉图尔在辨香器(malettes à odeurs)的例子中所展现的,非常迟钝的鼻子最终会变得非常灵敏,这是因为它们通过“交流”重新分配了彼此的属性,鼻子开始分有了辨香器的存在,进而“辨香器与身体同在”(24)。另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人要借助物来实现主体地位,就如身份证的例子一样,法语中的“sans papier”指代的就是失去身份证件而无法获得有效主体身份的人。 因此,“通过一系列关键的转译、表述、委派、上位和下位”等活动,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彼此内折到对方之中(25)。这样,客体性和主体性就不再分离,它们都成为了流通于人与物的“集体”和“议会”中的属性,成为了一种在人与物的“异质工程”中,与特定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部分性地获得或丧失的东西(26)。进而,如拉图尔所言,“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这不是因为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不存在内在的心灵”(27)。 3.建构主义实在论:消解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对立 新的物哲学的“反哥白尼革命”,开辟了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传统进路首先预设主客之间的二分,而后考察科学能否承担起架构两者的桥梁作用,差别在于前者将科学奠基于外在的抽象本体从而承认桥梁的存在,后者则否认科学的桥梁作用,从而将科学等同于语言游戏。而对物的经验形而上学的考察,在实践基础上重塑了一种本体论化的认识论。 从认识论层面看,知识无法脱离实践而存在,其有效性总是奠基于它产生于其中的某个网络,它所指称的也仅仅是从物质世界到最终论文之间的复杂转译链——流动指称。因此,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立体结构被扁平化(flattening),“升降梯式的语词”(28)被“日常语词”(29)所替代。拉图尔在此意义上呼吁认识论问题的去认识论化和再本体论化,认为只有两者合一才能为科学奠定新的基础;迪尔也主张用“认识图式”代替认识论,以强调认识论的实践特征。 认识论问题的本体论处理方式,在实践层面上将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这对矛盾体统一起来。知识的有效性必须立足于建构它的地方性实践,因此,知识的扩展,就必然伴随着其条件性的扩展,就如火车可以借助铁轨行驶到全球任何角落一样。巴斯德的疫苗拒绝穿越法意边境,但却在德国效果显著,原因就在于意大利人仅仅带走了巴斯德的疫苗而忽视了其条件性,德国人不仅带走了疫苗,还学会了消毒、分类、清理等程序,从而将农场改造为了一个简易的实验室,这就保证了疫苗的效果。哈金在对实验室科学的研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30)。这样,科学的地方性与普遍性就在建构性和情境性的基础上得到统一,只不过这里的普遍性是有条件的普遍性。进而,知识就同时获得了建构性和实在性,实在论的优势(可说明科学的有效性,但无法说明其历史性)和社会建构主义的优势(可说明科学的历史性和建构性,但无法说明其有效性)在建构主义实在论的框架内协调起来。 综上可知,当代S&TS的物哲学的本质是,消解实在的超越性和实质性内涵,通过将问题“实在是什么”转变为“物何以为物”、将视角从超越于时空的普遍性维度转变为立足于某一具体时空的地方性维度,从而将实在改造为经验层面的物,进而,立足于对其建构性的讨论,使得物的述行性和关系性界定成为可能。在物通过建构而获得述行和关系界定的过程中,一方面,内在的主体性和外在的客体性开始在实践层面纠缠,最终成为一种内在于实践的集体属性,另一方面,政治、伦理开始渗透其内,但由于物的述行和关系仍非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得以确定的本质,它对未来永远保持开放(“开放性驻足点”[open-endness]),因此,物的政治属性和伦理属性同样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物的关系变动中,它不断地得以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这种物哲学将“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和美学融合起来”(31),不仅在实践层面上深化了对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的理解,也为人类在技术化时代更好地反思自身存在提供了新的途径。 注释: ①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0. ②Lorraine Daston,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tific Objects,in Daston(ed.),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 ③学者们对物的概念使用并不完全一致,thing、matter、material甚至经过改造的object概念都被用以指代物,但他们在根本的哲学取向上是一致的。 ④“当代S&TS”也仅仅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诸多进路的综合,就如塞蒂纳和马尔凯在分析80年代初S&TS领域的状况时一样。K.D.Knorr-Cetina & Michael Mulkay,Science Observed,London & Beverly Hills:SAGE,1983,p.1. ⑤Donna 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New York:Routledge,1991,pp.149-181. ⑥N.Katherine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 ⑦这里的物,对应于客体、实在,而非拉图尔在其它文本中讨论的物。 ⑧Peter Kroes and Anthonie Meijers,The Dual Nature of Technical Artifacts,Techné 6:2 Winter 2002,p.5. ⑨John Law,On the Methods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Vessels,Navigation,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in Law(ed.),Power,action and Belief,London,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pp.234-263. ⑩Bruno Latour,Les Microbes:Guerre et Paix,suivi de Irréductions,Paris:A.M.Métailé,1984,pp.177-181. (11)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303. (12)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54. (13)[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14)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27.Lorraine Daston,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tific Objects,in Daston(ed.),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 (15)(18)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25,p.274. (16)Bruno Latour &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60. (17)Bruno Latour,Les Microbes:Guerre et Paix,suivi de Irréductions,Paris:A.M.Métailé,1984,pp.177. (19)Ursula Klein & Wolfgang Lefèvre,Materials in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7,p.70. (20)Bruno Latour,Ramsés II est-il mort de la tuberculose?,La Recherche,1998,N°307(March),pp.84-85. (21)Lorraine Daston,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Scientific Objects,in Daston(ed.),Biographies of Scientific Objects,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1. (22)引文参见Bruno Latour,Can We Get Our Materialism Back,Please?,Isis,2007,98,pp.138-142。 (23)Langton Winner,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27. (24)Bruno Latour,How to Talk About the Body?,Body & Society,Vol.10(2-3),2004,pp.205-207. (25)(27)Bruno Latour,Pandora's Hop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93,p.296. (26)Bruno Latour,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8. (28)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29)(31)Michael Lynch,Ontography:Investigating the Production of Things,Deflating Ont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13,43(3),p.452,p.451. (30)[加]伊恩·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7页。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本体论论文; 科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建构主义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拉图尔论文; 实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