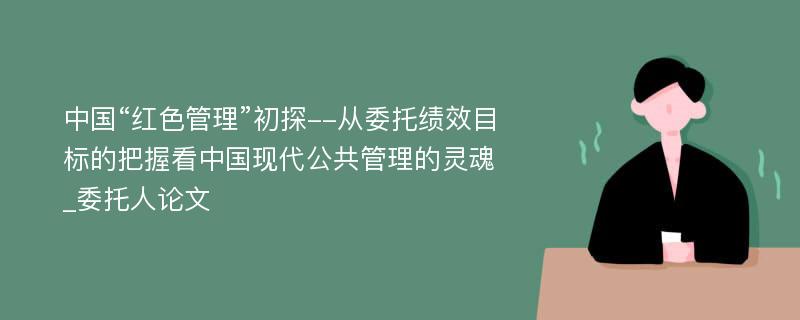
中国本土“红色管理学”初探——从委托绩效目标的把握看现代中国公共管理之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绩效论文,之魂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如“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由官民关系、政民关系不融洽所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且有逐渐蔓延之势。由于这种关系的紧张,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中上访、越级上访几乎成了政府管理的常态。从统计数据来看,2005年之前我国地方政府中信访率连续12年高速增长,2005年之后仍然维持了增长的势头。这些上访行为是当前政府管理不善的集中体现。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曾公开承认,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所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应予以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入,转型期的部分政府、领导干部逐渐丢失了革命本色,丢失了以前的管理传统,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从张朝丽(2011)的调查来看,仅有28.9%的干部认为干部与民众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而65%的干部认为干部与民众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王国红(2008)甚至认为,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我国赖以安身立命,在过往年代保障我们取得各种斗争胜利的政民“鱼水关系”逐渐蜕变为了“蛙水关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为了使得过去的管理经验在当代重放光辉,近年来我国管理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红色管理学”的研究。用“红色管理”来摆脱当前的困境,逐渐为世人所重视。对“红色管理”的发掘本质上是对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管理理论”的深挖,力图使得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管理学”在当前国情下绽放出灿烂的光辉,为解决当代各种社会管理问题提供借鉴。 一、我国对“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懈追求 自公共管理学引入中国,一些对学科抱有崇高使命感的学者就一直引用公共管理学大师罗伯特·达尔的名言“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中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来警告我们需要探索“中国式公共管理”,开发“中国式公共管理学”(张康之,2004;陈振明、薛澜,2007)。在探索中国式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薛澜、陈玲(2010)提出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过程学说;马骏(2015)提出了中国公共管理学应该具有合理的“想象力”;张康之(2009)提出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组织科学理论的中国式非任务组织管理理论;蓝志勇、魏明(2014)以解读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在追溯中西方行政实践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旨趣的公共管理命题;包国宪、王学军(2012)则从绩效的视角入手,提出了一种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希图以之解决西方公共管理理论难以兼容于中国的问题。还有一批在国外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学者也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朱旭峰(2011)对中国式智库、中国式政策过程的探究;敬乂嘉(2009)对中国式公共服务中渗透的管理哲学的厘清;何艳玲(2009)对体制改革中如何凸显中国理论“在场”的梳理;杨立华(2010)对我国治沙防沙政策过程的解析,都属于对建构“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有较大贡献的研究。 虽然有一批学者在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但还较少有人真正回头去看那些历史上由中国人开创的一系列公共管理实践,回头去总结这些实践中所蕴含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在这些实践中,最令世界震撼、最令人民满意的恐怕要是革命战争年代各个革命根据地中的公共管理实践了。这类公共管理实践被一批从事管理培训的讲师称之为“红色管理学”(冯成略,2006),它是既具有现代属性,又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公共管理学”。本来,提出“红色管理学”是对我国公共管理原创理论的巨大贡献,但较为遗憾的是,这些命题更多还是管理培训师、企业培训师所提出的一些看似动听,实则很不严谨的“说法”,而非系统的、严谨的管理学学术研究。从CNKI数据库来看,没有一篇探究“红色管理”、“红色管理学”的文献是刊登在规范的学术期刊上的。鉴于此,本文力图从公共管理学的视野,对何谓“红色管理”、何谓“红色管理学”进行初步的厘清。 总体而言,本文是一篇历史史料基础上的规范研究,它以对历史史料的解读为基础,以个人学科知识的积累为工具,对已有材料背后的逻辑进行“显影”,更多以主观的方式来界定“红色管理”与“红色管理学”,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研究方法。就方法论而言,本研究较为远离科学,与人文学科更为靠近。虽然这种方法存在着主观性过强、科学性不足的问题,但它有助于发现那些未纳入当前科学研究范畴的议题(Fry,1985)。在这种具有批判性方法的基础上,本文以公共管理应该实现绩效目标为切入点,先探讨到底什么是“红色公共管理”与“红色管理学”,接着探索“红色公共管理的元规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希图搞清楚“红色管理”如何确定绩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绩效目标。 二、中国做派的“红色管理(学)” 就当前文献来看,管理培训师、企业培训讲师认为“红色管理”或者“红色管理学”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实践、管理行为、管理理论、管理哲学等(冯成略,2006)。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细究起来却有些不符合逻辑,因为“红色”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时期,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就已经将自己的使命确定为“解放”全国,“解放”之后的历史时期便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它一般不会再被称之为“红色”时期。如果以“红色”泛指改革前,不仅不符合近代史的断代方法,而且也不符合党中央的政策口径。鉴于此,笔者认为,所谓“红色管理”一定是与“白色管理”、“黑色管理”、“黄色管理”等概念相对应的一种研究范畴,具体到我国来说,应该指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它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终止。尽管中国共产党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且在1921年之前还产生过多个共产主义小组,但在这些时段中,无论是共产主义小组还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都未曾践行真正的管理实践,并未将自己所坚持的管理哲学、管理技术、管理方法在公共部门、企业组织、NPO、NGO组织中予以践行,至少它们都未上升到各类组织的主流治理地位。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中国共产党作为辖区内(红区)的执政党,将具有共产主义红色精神的管理哲学、管理技术、管理方法在本区的各类组织中都做了很好的贯彻。既然称之为“红色管理”,它本身代表了一种暂时性、非制度性的存在,本身内涵了与当时旧军阀纵容“四旧”的“黄色管理”、与地方独裁割据势力高压统治的“白色管理”、与国统区人民缺乏权利的“黑色管理”的对比性,体现了与“五光十色”的管理一样具有的暂时性、非正规性、非制度性。由是,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后的管理,不应该被称之为“红色管理”,而应该叫做“社会主义计划模式的管理”,当前的管理应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的管理”,两者都是对“红色管理”的继承与发展,但并不代表这两者已经继承、发展了红色管理的所有合理内核、所有优秀的精神,这也是当前重新挖掘红色管理的根本原因——去搜寻红色管理中那些被遗忘的珍珠。笔者认为,“红色管理学”应该是指那些廓清了“红色管理”期间我国红色管理实践规律,抓住了“红色管理”本质的学问与知识体系,不能简单地将涉及“红色管理”的论调都叫做“红色管理学”。 三、“红色管理”的元规则 与对红色管理学的理解一样,当前管理咨询讲师、企业培训师对“红色管理”的真谛理解并不严谨,也不系统:有的人认为“红色管理”的要领是政策与策略关系处理得当;有的人认为它的核心在于亲民爱民;有的人认为它体现了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刘倩,2005;洪延艺,2011;冯成略,2006)。这些说法无疑都有一定的正确性,也都有很多借以立论的证据,但笔者认为这还未抓住红色管理的“真理”,还未把握住一条根本性的规律,借用哲学术语而言,就是没抓住“元规则”。 一般而言,无论在何种组织,管理的存在都是以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Fama,1988;冯根福,2004)。在没有委托代理的世界里,所有工作都依赖于每个人的亲力亲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践者即为管理者,他只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可。但在现实世界中,随着各类组织的扩大,随着各类事务专业性的增强,除非万能的上帝在世,否则没有人能从事如此之多、如此之专、如此之繁的工作,这便使得委托代理既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须,也成了组织发展进步的常态。可以说,管理者只有把握了委托者的真正目标,取得了委托者想要的绩效,才算是实现管理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有效、准确地把握委托者的绩效目标,就是管理者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与此相对应,如何把握委托者的绩效目标,便是“红色管理”的首要规则,它是其他规则赖以展开的基础性规则,因此我们称其为“元规则”。 从一系列历史事实来看,“红色管理”的元规则在于弄明白谁是委托者、谁是管理者、何为委托标的(绩效目标)。毛泽东(1967)很早就提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党的干部不能有“当官做老爷”的念头,要让每一个党员干部明白,党员干部就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一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要处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防止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领导者变为“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剥削压迫老百姓。毛泽东屡次引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指明共产党人、共产党员干部、党的政府组织、党领导的企事业单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其主人就是人民。党没有自己的事业,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这廓清了作为管理者,无论是党员还是党组织,都只是受托人、是管理者(manager),而真正的主人是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基层的人民,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从根本上廓清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对“红色管理”中委托代理关系的界定,具体表述为:“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在他看来,作为管理者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只不过是实现“主人”目标的具体实践者,他们不可能是委托者,只能是代理人、管理者。 在廓清了委托人和管理人的基础上,“红色管理”特别注意对“主人”所托之物的把握与厘清。早在井冈山早期,根据地政府就特别注意有效把握民情、民意,注意把握人民最迫切的需求,并将它们作为政府管理中亟待达成的绩效目标。从史料来看,甚至连每个乡有多少光棍需要解决婚姻问题、有多少无地或无居贫民需要栖身和生存、哪些山上还可以垦荒都列入了政府年终报告中,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绩效目标。它们不是由管理者想当然地推出的管理目标,而是通过走访、与人民谈心、调查等方式获得的委托人(民众)迫切需要实现的切切实实的目标。当前在我国管理中,尤其是公共管理中,政府频繁推出各种管理目标,比如“民俗一条街建设”、“PX项目集中地建设”、“百佳家庭评选”、“群众心理调适计划”、“经济开发区建设”等,这些管理目标看着都很新颖,似乎都是地方发展所需要的,但殊不知这些未必是作为委托人的人民所需要的(尚虎平,2008)。为什么当前人民对统一规划性质的强拆意见颇多,为什么人民往往抵触PX项目,为什么人民对部分政府干部颇为不满,为什么国有企业中基层员工对管理层颇有微词,因为这些费心费力的项目都不是人民所委托的目标,在这些项目上取得的成就并非人民所需要的绩效目标。用一句北方谚语来评价就是,“爹给我的那块糖压根不是甜的”,在委托人所委托的绩效目标外行事,多而无益,往往是此类目标越多,委托人越不满意。从委托人角度而言,非委托目标的实现,是管理层利益僭越委托方利益的表现。 四、“红色管理”有效把握绩效目标的主要方法 任何科学理论最终都要化为改造世界、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提出的依据,但科学理论最终能够落地生根、促进社会发展,需要依赖于一套方法体系。人民是管理的主人,党的各类组织是受托实现管理目标的管理者,人民的需要就是管理者的绩效目标,这就是“红色管理”的元规则。但这个规则的实现,也是需要一套方法做支撑的。概略来看,“红色管理”主要采用了召开委托人大会、“定点解剖麻雀”、“诸葛亮会”等来把握绩效目标。 (一)召开委托人大会 毛泽东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可以说,开人大会既是一种将政治科学中的民主技术有效运用到管理领域的科学尝试,也是我国“红色管理学”在管理工具上卓有成效的创造。本来,召开委托人大会属于政治民主范畴,但“红色管理”将其扩展到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其他类组织管理中,使得人大会成为了最有效把握民情民意的管理工具。人大会发挥作用的最根本一点在于确认每个委托人的平等性,凡是人民(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均有权利、资格参加,在参加的过程中也均具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且意见享有被借鉴、参照权,这也是这种民主技术转变为管理工具的基本条件。正是通过各种人大会,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才能有效把握委托人的各项需求,才能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才能实现淮海战役中数百万民众支援前线的局面,从而实现了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二)“定点解剖麻雀” 曾有人将红色管理的“解剖麻雀”看做一种案例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够到位,也没有真正理解“解剖麻雀”的本意。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由此可知,“解剖麻雀”是一种与委托人大会相互补充的技术,它也源于政治科学的方法,其立足点类似于福利经济学中的“弱势群体受益”原理,认为真正的委托目标存在于占数量绝大多数的基层人民群众,如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这是一种平等权利技术。另外,由于我国自古就有的中央集权下的单一制模式,一个地方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大多数地方存在的问题,这种“定点解剖麻雀”的方法往往还具有全局意义,它不仅可以与人大会方法互补使用,在经费、时间的约束下,它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方法来把握委托者的绩效目标。 (三)“诸葛亮会” 这是一种集头脑风暴法、代议民主、精英决策思想的融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方法于一体的管理新技术。在经典管理学、心理学教程中,往往比较重视头脑风暴法、专家法;在传统政治科学中,往往比较重视代议民主或者精英决策方法。头脑风暴法比较重视小群体中的畅所欲言;代议民主法常常重视按照一定比例选择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候选人代表;精英决策法一般持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智者手里”的理念,这些方法单独使用往往只能顾及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的重要因素。“诸葛亮会”法既注重“三个臭皮匠”的畅所欲言,也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有能力判断自身需求的代理人,这使得这种方法较好地结合了管理科学、心理科学与政治科学的优势,能够有效地收集、判断人民(委托人)的各种需求,从而形成管理所需要实现的绩效目标。从历史资料来看,我国各根据地的部队、政府、企事业单位广泛推行“诸葛亮会”制度,使得它成为了一项日常性的民意收集技术、绩效目标决策技术。 五、“红色管理”落实绩效目标的方法 总体来看,“红色管理”实现绩效目标最关键、与其他类管理区别最大的一点,恐怕就在于对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视了。各种根据地、各个红区、各个解放区与其他类政权、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管理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能够很好地发起集体行动来落实绩效目标,这种集体行动不仅仅是管理者的行动,就连大量的委托者(人民)都深度卷入了其中,形成了“主人”与“服务员”共同向委托目标迈进的壮观局面。概略而言,这些集体行动主要通过爆发式集体运动、突击、义务劳动、组织专业队等方式来实现。 (一)爆发式集体行动 爆发式集体行动是指管理者在面临严峻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资金等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尽最大可能使得管理幅度内的各类人员,包括部分委托者、既非委托者又非管理者(如国际友好人士白求恩)参与到绩效目标的落实活动中。在落实目标的过程中,往往将爆发式集体行动按照目标分解为不同的实施小组,比如妇女战斗队、儿童团、尖兵队等。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实践界与学术界往往混淆了“爆发式集体行动”与“运动”的区别。实际上,“运动”是一种临时性、突发性的,以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实现某种目标的社会性活动;而“爆发式集体行动”一般都有确定的目标、确定的程序,它一般不会破坏既定的管理秩序、法律秩序。“运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它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而“爆发式集体行动”属于管理实施的范畴,它具有很强的建设性,类似于现代管理学所讲的“任务型组织”的集体行动(张康之,2009;Rosenbloom,2001)。 (二)突击 突击是一种承包式加班制度。它通过将绩效目标分解为众多的次级绩效目标并规定严格的完成时限,这种时限往往低于社会平均完成同类工作所需要的最低周期,需要承担管理任务的组织、人群投入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在实践中,“红色管理”一般都采用夜间加班、用餐时间加班等方式,将“一分钟当两分钟使”。突击的核心思想是,人、资源、机器都不能闲着,这样时间自然就争取出来了。这是通过最大化利用人力和设备节省时间的工作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式管理方式,是与时间老人赛跑的方式。毛泽东的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是对突击法的形象写照。 (三)义务劳动 突击往往是为了强制性地完成某个绩效目标,而义务劳动则是非强制性地、用精神感召的方式,使得组织内的每个人把实现绩效目标当成自觉的行动,当成一种精神追求。这既是柔性管理的最高境界,也是当前所追求的塑造“组织文化”的最高追求。通过对共同愿景的塑造,红色管理使得组织内的各类人群认识到实现组织目标就是实现自身追求的过程,它既是造福当代,更是利在千秋的事情。通过这种塑造,大家都把实现组织的绩效目标当成了一种信仰,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地开展工作。从历史资料来看,义务劳动主要分为日常性义务劳动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前者是每天工作之余抽出部分时间心甘情愿地免费工作,后者是在周末休息日参加非任务型、非报酬性工作。从管理会计角度而言,义务劳动不投入成本,却能形成产出,是一种无本万利的行为,是任何组织都奢望出现的局面,但这需要管理者强大的共同使命、共同愿景的塑造能力。 (四)组织专业队 对于一些专业性绩效目标,往往不一定“人多力量大”,这个时候就需要发挥“专家”的作用。对于这些目标而言,“人多力量大”表现在组织的专业人员越多,则力量越大。在根据地、解放区的实践中,往往采用成立各类专业人才队伍,如爆破队、纺织能手队、武工队、手枪连、通讯班来专才专用、专才集体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在专业人才极度短缺的时代很好地解决了机械生产、水利攻关、农业增产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才资源产业集群”的思路,与当前世界各地推行实业生产产业集群的思路是一致的,但这种思路的形成要明显早于迈克尔·波特等人的产业集群理论。这种人力资源集群思维是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极度短缺环境下的管理学创造,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六、对“红色管理”的扬弃 近年来,部分学界与实践界的人士大力倡导向“红色管理”寻求济世良方,甚至有人呼吁回到过去,笔者认为这种论调有些过头,脱离了科学、理性的轨道。“红色管理”的产生,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源极度短缺的管理情境下形成的。这种短缺甚至远远超越了经济学上所说的“短缺”的含义,它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绝对短缺。就是说,再短缺一点,可能无论是委托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可能连基本的生命体都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萌生、发展、壮大的管理学是一种极端状态下的管理学,就如同人与狮子同笼,人可能会迸发出无限潜能将狮子打死,但这种情况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作为当代的人们,作为当代的组织,我们应该吸收“红色管理”的“合理内核”,摒弃那些不符合常态生活、不符合法治精神、科学管理原理的内容。 就继承、发扬光大而言,我们应该学习“红色管理”明确委托人、确定受托的绩效目标、落实绩效目标的做法。当前,除了民营组织之外,我国各类管理中都存在着委托人不明确的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尽管我国被称之为“人民共和国”,但目前我们却很难把握作为委托人的“人民”的追求,以及人民所期望的绩效目标。在GDP导向下,公共管理领域产生了太多的问题,出现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作为委托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没有掌握人民所希望获得的绩效目标(尚虎平,2015)。我们可以借鉴“红色管理”中辨识委托人的做法,在最基层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中选择人民代表,而非在各界名流中把握民意。目前,我们辨识委托人代表的方法出现了系统性偏差,这是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企业管理领域,我国也存在着与公共管理领域类似的问题。我国众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委托人都极不明晰,“国家”、“集体”都无法真正地监督企业使其为了委托人的绩效目标努力。有统计数据表明,大量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根本不给股民分红,除了税收之外的收益,都是组织内自行支配。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委托人的利益,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情,但每年的“股东大会”都会顺利通过这种资金分配方案的审核,这说明这些委托人代表(股东)的选择是有问题的,没有把那些真正的委托人选出来。这也可以借鉴“红色管理”的做法,将股权、股东代表权赋予普通工人、民众,使得监督刚性化,使得股东大会能够收集真正的委托方绩效目标,而不是被管理人目标置换。在选择好了委托人之后,未来可以借鉴“红色管理”的大会法、“定点解剖麻雀法”、“诸葛亮会法”来收集绩效目标。 “红色管理”落实绩效目标的做法,都有浓厚的社会动员痕迹,它们都属于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学流派的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目前后工业社会的管理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比如爆发式集体行动和突击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时限约束下如何最大化发挥人力资源、设备的功能,这些方法未来可以使用到我国的各类组织中。义务劳动方法可以说是管理学中所追求的“手中无剑,心中有刃”的管理最高境界,达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效果,它依赖于宗教式的奉献与虔诚,依赖于员工对组织使命、价值观发自内心的认同,依赖于员工将绩效目标变成自身的内心追求,将来各类组织都应该朝这方面努力,尽量使得员工“爱政府如家、爱企业如家”。为了实现绩效目标,员工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地奉献,而组织成本却不增加。 “红色管理”中不合时宜之处主要在于缺乏对技术规律、管理规律的客观把握,缺乏对人作为生物体、生命体最低承受力的保障,缺乏对人、设备、人与设备交互等可持续性的保护,未来管理中对这些方面应该予以戒除,这是需要批判的方面。 总之,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红色地区的管理创造出了远胜于国统区的比较优势,取得了压倒性的竞争优势,最终将国统区的同类组织击垮,取得了竞争的胜利。红区的管理是一笔厚重的财富,它通过对政治科学方法、社会动员方法的引入,大大丰富了管理科学的方法库和知识库。 当然,本文的探索只是抛砖引玉,“红色管理”的精髓还需要我们通过大量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来揭示。也许,只有将红色管理细分为“红色公共管理”、“红色企业管理”、“红色社会管理”、“红色决策学”、“红色绩效评价”、“红色运营管理”、“红色公共关系学”等进行研究,才能够洞察它各方面的精髓,也更有利于红色管理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