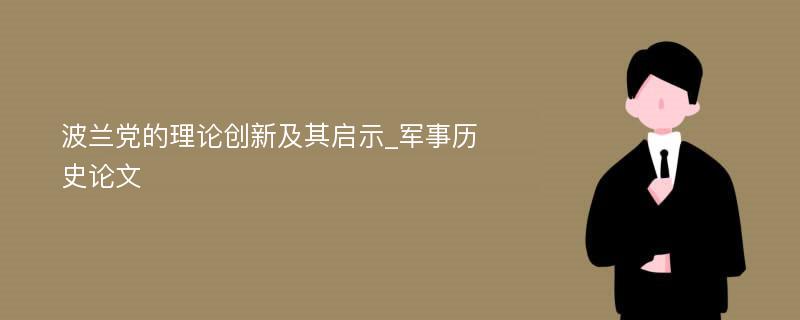
波兰党的理论创新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教训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执政的45年里,为寻求符合波兰国情的发展道路曾进行过许多理论探索和创新。但是,其中有的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已夭折,有的实施了几年之后被放弃,最终在“放开手脚”进行理论创新时丢掉了政权,教训十分惨痛。曾经担任过波兰统 一
工人党第一书记的拉科夫斯基说过:“失败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一种制度及其理论
。”[1](p4)由此可见,理论创新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一、在苏联的高压下进行理论探索,无功而终
20世纪40年代,波兰提出了走“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道路和“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38年,共产国际以奸细混入党内为由解散了波兰共产党(注:波兰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第二年被宣布为非法,从1921年起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曾是议会党之一,1938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局解散,1956年恢复名誉。),二战中波兰没有共产党,直到1942年才又在苏联帮助下成立了波兰工人党。唯一未被处决的波共政治局委员阿尔弗雷德·兰普曾在1943年设想,战后波兰应走“既非西方也非东方的发展道路”。他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波兰应当“采用经济政治的渐进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苏联合作的政府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从红军手中接管政权,那么“波兰社会主义事业将被推迟3—4代人的时间”[2]。兰普的这些理论主张同后来哥穆尔卡提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如出一辙。
二战结束后,波兰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与几个民主党派一起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领地位,决定了波兰党的理论创新必需听从苏联的安排,党和国家没有独立主权可言。即使如此,哥穆尔卡还是根据波兰国情在1946年11月30日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他说,这条“道路”有三个不同于苏联的明显特点:1)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在我国则是和平实现的;2)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我国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3)苏联的政权是由苏维埃来行使的,它把立法和行政职能结合在一起……我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制基础上[3](p97)。哥穆尔卡进一步解释说:“工人阶级专政,尤其是一党专政,在波兰既无必要,也不可取……我们认为,我国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民主政党来行使。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共产党,在我国则有几个民主党在公开活动……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他还指出“毫无必要追随苏联的农业经济”,“要完全摒弃农业经济的集体化”,在波兰条件下,集体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有害的”[3](p98)。
哥穆尔卡大胆进行的理论创新,由于同苏联模式大相径庭,自然为苏共和波兰党内的“紧跟派”所不容。因此,他的理论创新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在苏联高压下夭折了,他本人则被指责犯了“右倾民族主义”错误,不但被解除了党的领导职务和开除党籍,而且
被关进监狱,险些被处死。
50年代中期哥穆尔卡复出后重提“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从1948年底开始,波兰党在贝鲁特领导下进入了“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这一模式与波兰国情格格不入,因此每过若干年就爆发一次政治危机,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秘密报告”。这一文件向波兰全体党员进行了公开传达,它打破了许多原来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舌头”,成了“波兹南事件”的催化剂。而这次事件是波兰人民公开反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大爆发。紧接着,波兰党在反对赫鲁晓夫粗暴干涉的“波兰十月”事件(注:“波兰十月”:1956年10月,波兰党召开了八中全会,准备推举哥穆尔卡重新出任党的第一书记,并改组政治局。就在会议开幕之后不久,赫鲁晓夫突然来到波兰,向波兰党施加压力。波兰党与之进行了说理斗争,赫鲁晓夫最终屈服,波兰党赢得了决定本党事务的“部分权利”,哥穆尔卡最终复出。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支持哥穆尔卡的游行示威,欢呼波兰党的胜利。后来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这被统称为“波兰十月”。参见本人编著的《波兰独立之路》第十二章“波兰十月的转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中赢得了胜利,哥穆尔卡重返政坛,他再度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57年5月,哥穆尔卡在党的九中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波兰道路”的内容:第一,建立工人委员会;第二,扩大人民会议的权力;第三,发展各种不同的农民自治经济形式[3](p197)。他说:“这条道路意味着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不同于苏联的方法……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苏联在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对其他民族来说,既不是完全必要的,也不是完全适宜的。我们强调波兰道路,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不同点和民族特殊性,不能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出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则。在实践中否认这一点就会直接导致取消社会主义。对一般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过的规律估计不足或加以否定,这是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应当与之进行斗争;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特点和特殊性估计不足或加以否定,这是虚无主义的教条主义,同样应当加以批判……”[4](pp185—187)。他在全会上还引用列宁的话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pp64—65)。
从1956年“波兰十月”到60年代中期,波兰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实行了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政策。例如,大力提倡建立工人自治机构,参加企业管理,把工人委员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一种工人民主形式”;充分发挥议会的作用,使合法存在的民主党派拥有越来越多的参政权;强调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在文艺领域,一扫以往沉闷的气氛,作家、艺术家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创作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批判照搬苏联模式错误的基础上,波兰以“经营不善”为由在三个月内解散了85%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以后解散了几乎全部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在东欧各国,除了提倡“自治”的南斯拉夫之外,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1967年5月以色列入侵阿拉伯国家,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的胜利使一部分波兰犹太人兴高采烈,但苏联同以色列的关系却出现了紧张。在1968年波兰“三月事件”之后,哥穆尔卡意识到必须坚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理论探索必须考虑苏联容许的程度,遂逐渐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这样,一个曾经受到千百万群众热烈拥护的领导人却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这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失去了同自己阶级的共同语言。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6](p35)。1970年12月发生的“沿海事件”流血冲突导致哥穆尔卡下台,他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也宣告彻底破产。
70年代盖莱克时期提出“党领导、政府管理”的观点。“沿海事件”之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他批判了哥穆尔卡闭关锁国的政策,大力提倡向西方开放,不顾本国的偿还能力大举借债和引进先进技术。波兰著名反对派人士莫楚尔斯基说:“在历届党的领导人中间,盖莱克是最不屈服于苏联霸权主义的党中央第一书记”[7]。尽管如此,波兰还是追随苏联,根据苏共关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再强调波兰“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是“党领导、政府管理”这一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还写进了党的七大文件。这一理论主张咋看起来确实不错,但在70年代的体制下,面对苏联的高压,不可能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所以没有在体制上认真加以贯彻落实,结果依然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拉科夫斯基在批评当时的政策时曾经举例说,当时就连远离华沙600多公里的西北部城市什切青新盖的一幢楼房应该刷成什么颜色,也必须由党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结果是“党不党、政不政”,党依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至于理论创新流于形式,变成空头支票。
80年代上半期以“协商对话”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是波兰党提出的新理论,目的是寻求适合波兰国情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种理论探讨却是导致波兰制度剧变的催化剂之一。
1980年团结工会兴起后,波兰党内一片混乱,各种“横向结构”和“论坛”纷纷出笼。但是以第一书记卡尼亚为代表的温和派赢得了主导地位,顶住了苏联和党内强硬派的压力,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场席卷全国的工人运动,没有按照苏联的调子把它定性为“反革命”,而将其看成“工人阶级反对工人政党”的运动。1981年7月14日,卡尼亚在党的九大上指出:工人抗议“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原则;不是反对人民政权,而是反对恶劣的掌权方式;不是反党,而是反对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8](p930)。党的九大确定了以“协商对话”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在党的纲领中第一次规定教徒可以入党。但是,党和政府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最后,在团结工会准备夺权、苏联准备出兵干预的危急关头,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对波兰全境实行军官,取缔团结工会,停止一切社会团体的活动。尽管如此,党依然坚持“革新”路线。1982年的中央全会上又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大大扩大职工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党将灵活地选择符合波兰国情的方法,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这一时期理论探索的目标是建立“波兰式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波兰应成为完全的工人自治共和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本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建立合作社,展开相互竞争。这一理论比“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走得更远,所以同样遭到了苏共和党内强硬派的批判。
1982年3月1日,波兰党的领导人向苏共汇报国内情况时,勃列日涅夫当场指责波兰党搞的是“波拿巴主义”,试图贬低党的领导作用。他对波兰党扩大职工的管理权提出批评:“这又是你们波兰搞的什么新花样,自治!一个新的铁托!难道苏联社会不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实行自治的吗?如此良好的运转机制,有什么好改革的!”[9](p20)应当承认,波兰党已经看到了改变党自身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取得明显成效。这正是波兰党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脱离群众”窠臼的原因之一。
为了压制波兰党的理论创新,1984年5月波苏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华沙召开了理论研讨会,提出波兰“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在主观和客观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与当时学术界广为流传的波兰搞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均未成熟的论点针锋相对[10]。同时也与波兰党强调的波兰“依然处在过渡时期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放弃“党的领导作用”。雅鲁泽尔斯基曾一再强调,“党的纲领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信赖,是党发挥领导作用必不可少的基础”,不论情况如何特殊,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必须注意:1)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进步,加速社会经济发展;2)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国家职能;3)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巩固自己的决定性地位;4)在国际舞台上同发号施令做斗争,要创造性地对待各国的特殊条件。
二、放开手脚搞理论创新,丢失政权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心想卸掉东欧这个沉重的包袱,使本国经济从中解放出来[11]。在东欧各国党领导人汇集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时,他批评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并告诉大家,从此以后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处理自己的问题。不久,他担任苏共最高领导,并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等理论。波兰党感到,戈尔巴乔夫为已为各党“松绑”,“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独立自主地安排自己家园了”,于是理论探索的重点开始转向寻求放弃社会主义模式。
1986年波兰党的十大进一步强调“革新”路线,并在纲领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波兰“仍然处在过渡时期”的论点,这比70年代“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明显倒退。根据这一提法,波兰党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例如“一般规律必须同各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普遍的东西同特殊的、特有的、民族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规律”,“特殊的东西不能夸大到用此来反对普遍的东西”等[12]。在执政党问题上,提出“党还是这个党,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党要发挥三大职能——“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服务职能;对社会的引导职能;对国家的领导职能”;提出了同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理论。然而,理论不一定能贯彻于实践。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后来也认识到,“在社会群众的心目中,党并不是一种引导力量,而往往是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尽管我们费尽心机,人们还是认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把我们说成是行使独裁政权的人,反民主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政权。”[1](p149)
如果说波兰党的理论创新在8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戈尔巴乔夫升到苏联权力顶峰后,波兰党逐渐脱离了这一轨道,理论创新简直就是大踏步地向放弃政权的方向发展。
雅鲁泽尔斯基在80年代后期提出了大量与过去的提法具有实质区别的理论观点,其中最典型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的理论。他说:“这种多元化同所谓‘各种政治力量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概念毫无共同之处,它不会造成对抗。它的实质是,在维护和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从根本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13](p569)。他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时提倡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本来并无意识形态的特点,只有其使用目的显露之后才具有阶级特性。社会主义对已成为人类文明财富组成部分的一切东西不能不加以利用。”[13](p565)
实际上,这时党的任何理论创新均不可能有积极成果,除了交出政权外别无他途。改革必然意味着“改向”。应当承认,为了维持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波兰党吃尽了苦头,80年代整整10年一方面受到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全国人民的反对,另一方面受到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搞得筋疲力尽,日子十分难过。因此,这个制度的垮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沙夫教授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垮台,人们不必为此感到沮丧落泪;相反,应当为此感到欣慰,因为它为建设一个真正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拓清了道路”[14](p139)
三、若干教训
理论创新必须有宽松的政治环境。波兰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都是在苏联制肘的夹缝中进行的,党和国家没有主权可言,根本谈不上宽松的政治环境。总结苏联党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教训,可以看出,它自己没有理论创新,也绝不让别人有任何理论创新。40、50年代批判南斯拉夫是如此,50、60年代批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原来,在苏联霸权主义体制内搞理论创新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在必须看苏共脸色行事的处境中,波兰党不可能有什么成功的理论创新。与此同时,由于波兰党承受不了苏共的压力,因此理论再好也无法贯彻实施。
波兰党是在苏共高压下进行理论创新的,这决定了它必然无功而终。这也与波兰和俄罗斯的历史宿怨有关。由于历史上俄国是瓜分波兰的元凶,波兰人对俄国人的民族仇恨已融入波兰民族传统之中,仇俄、恐俄思想深深扎根于波兰人的感情深处,反俄情绪比东欧其他民族都严重。在波兰人眼里,俄国是“千年宿敌”,而苏联人就是俄国人。苏联对波兰政策指手划脚,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列宁在1917年5月召开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压迫过波兰人,俄国人充当了沙皇扼杀波兰自由的刽子手;没有人像波兰人那样憎恨俄国人……”[15](p264)波苏关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波兰人民的心头,党的理论创新不可能有任何宽松的环境。
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大方向。戈尔巴乔夫给中东欧各党松绑后,波兰党的理论探索迷失了方向,与反对派殊途同归。尽管口头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党内“改革派”同社会上的反对派里应外合,共同“拆除”了社会主义。因此,波兰社会主义的垮台是当权派和反对派“从隧道两端同时开挖”的结果。
1987年,雅鲁泽尔斯基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的理论,这直接导致了放弃“党的领导作用”。“多元化”同“党的领导”两者无法兼容,实际上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信心,党正在迅速退却。拉科夫斯基作为党的第一书记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反问道:“当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拯救苏联时,还能指望革新社会主义吗?”[1](p336)他还指出:“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后,我们才完全明白,若不抛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体制民主化的进程就会遇到无法排除的障碍”[1](p61)。他明白无误地宣告: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设想和行使政权的方法已经到了尽头,那种认为只要进行小小的修修补补就能使波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并使党保持领导地位的观点,是错误的[1](p228、pp235—236)。当波兰党在1989年的议会大选中失败后他又说,我们执政40多年了,也该让他们(指反对派)来执政了,“我们永远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1](p321)。
同样,雅鲁尔斯基也致力于“拆除”原来的制度。他说:“我深深理解,按照苏联体制的政权结构,波兰这列火车再行驶下去就要翻车,发生大灾难……要重新制定新的列车时刻表是需要时间的,要等到条件成熟……,所以直到1989年才召开‘圆桌会议’……我深深感到我们原来犯了许多错误……但历史是复杂的,既要考虑内部条件,也要考虑外部条件”[16];“在一年半时间里,我也致力于拆除原来的制度,我曾十分关心其进程”[17]。1999年5月在纪念“圆桌会议”十周年之际,一些反对派人士曾建议有关方面给雅鲁泽尔斯基颁发奖章,予以表彰。
理论创新不能对反对派企图夺权丧失警惕。80年代,波兰党在“民族和解”的总方针下,不但放松了对反对派企图夺权的警惕,并且给反对派夺权制造了理论基础,把反对派区分为“建设性的”和“破坏性的”两类,但实际上把所有反对派一股脑儿都当作建设性反对派来对待。例如,在“协商对话”框架内,把一些反共老手吸收进由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磋商会议”,与之平起平坐,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人民的呼声,并决定同他们“分权”,企图让他们对国家“共同承担责任”。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向反对派投降。须知,反对派提出的“社会主义不可救药”的思想已被人们广泛接受,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人们相信只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波兰才会逐步好起来。党的任何理论和政策,即使符合波兰国情,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在反对派亮出夺权底牌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时,波兰党领导既丧失警惕,又丧失原则,所以丧失政权完全是咎由自取。
理论创新首先要有观念的更新。波兰党固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缺乏任何理论创新,这是因为原来的社会主义原则缺乏任何观念更新,它把市场和计划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可是始终未被执政党所重视和采纳。70年代,盖莱克尽管在实践上试图引进市场机制,但在所有制问题上依然墨守成规,鹦鹉学舌般模仿苏联,高唱“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把公有制成分的多寡看成是社会主义是否成熟的标志。
总之,为了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波兰党进行的理论创新经历了一条创新——受压——再探索——再受压,直至放弃政权的悲惨道路。假如哥穆尔卡提倡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能够得到实施,那么波兰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后来事态发展的道路,80年代末的制度剧变也许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