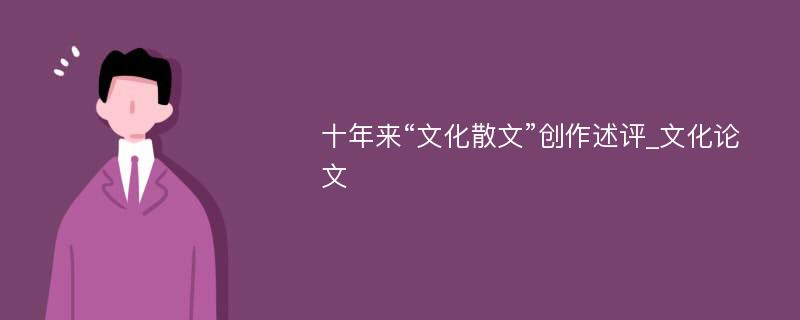
近十年“文化散文”创作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十年论文,散文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散文在6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抒情散文的高峰,到了80年代,又因报告文学这种广义的散文文体的崛起而使这期间其他类型的散文创作相形见绌。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创作虽然出现了一个观念多元、手法多样、文体杂陈、风格迥异的繁盛局面,但相对而言,其中也有发展得比较成熟的散文品种,足以代表这期间散文创作的特色和成就。被人们习惯称作“大散文”、“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卓尔不群,一枝独秀,就是这期间散文创作新的特色和成就的标志。
一般说来,“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是指那种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往往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这种散文的作者多为一些学者或具有较深文化修养的学者型作家。因为上述原因,这类散文往往视野开阔、气魄宏大,且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追溯这类散文创作的艺术源头,其远因自然是出自中国散文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散文,既有精巧的山水游记、轻松的性灵小品、质朴的书札笔记,也有以《庄子》为代表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以丰富的想像和深邃的理性著称的哲学散文,以《左传》、《史记》等为代表的时空廓大、气势恢宏,以历史的沧桑感和记人的生动传神、叙事的纵横捭阖为特征的史传散文,以及以孟(《孟子》)、荀(《荀子》)、韩(《韩非子》)、贾(贾谊)为代表的富于雄辩的论辩散文,以汉赋为代表的铺张扬厉的诗体散文等。这后一方面的传统,就孕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散文”、(“大散文”、“学者散文”)的艺术精神。其近因,则是直接肇自近20年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学变迁。中国古代散文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转变之后,虽然“又来了一个展开”,其“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但那主要是指一种随笔“小品”(包括杂文)式的散文品种,后来虽然有所发展和变化,但除新兴的报告文学这种广义的散文文体以外,其规模体制的艺术格局,从总体上看,依旧比较狭窄。近20年来,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的推动,散文作家如同其他文体的作家一样,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但文化视野在逐步扩大,而且艺术表现的形式、方法与技巧,也在日趋多样化。在这样的情势下,近20年来的散文创作,一方面致力于恢复和重建中国散文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同时也注重吸收外国尤其是台、港地区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近20年来的文学发展,从80年代初的历史反思转向80年代中期前后的文化寻根,是触发“文化散文”创作的主要艺术契机。
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由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传统的回归的影响,一些作家的散文创作就比较注重发掘其表现对象中的文化内涵,或有意识地开掘一些有较深历史文化积淀的创作题材,如王英琦的“文化遗址散文”系列作品《我的先民,你在哪里?》、《“木乃伊”旁的奇思异想》、《烽火台抒怀》、《古城墙断想》、《南疆界碑》、《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青山有幸埋诗骨》、《不该遗忘的废墟》、《塔克拉玛干之谜》等,通过凭吊从半坡到圆明园、从古长城到永乐宫、从南疆界碑到青山古冢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址和作者自己深入蛮荒的冒险经历,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们的身旁有一片不该遗忘的废墟”。这既是针对“文革”及其前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极左的政治思潮轻漫、蔑视以至于全盘否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现象,有感而发,也是为人们思考现实问题、挣脱现实困境、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英琦的这些看似发思古之幽情的散文创作,实则集中地反映了这期间的散文创作拨乱反正、反思历史、重建传统的一种精神取向。这种精神取向因为与这期间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向同步,因而也是这期间正在蓬勃发展的“伤痕—反思”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王英琦的散文因为取材的特别,思虑的深入,且具有极强的反省意识、忧患意识和浓郁的文化色彩,而有别于当时颇为盛行的伤悼散文和忆旧散文,一扫这类散文的感伤气息和落寞情怀,而具有一种浑厚凝重的气魄和雄强豪放的风格。因为上述特征,王英琦的散文创作事实上已经奠定了“文化散文”的一些基本的艺术雏形。与此同时,这期间,受中国现代乡土地域文学传统,及台港地区的乡土散文和地域散文的影响,一些作家也把这种注重文化内涵的发掘的创作旨趣,具体到对一些乡土和地域题材的开掘之中,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一些带有乡土和地域特色的散文创作,如汪曾祺的写老北京、贾平凹的写商州等。这些散文虽然也具有“文化散文”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因为格局较小,或与同一作家创作的笔记小说相类,因而又缺乏“文化散文”作为一种“大散文”所应有的艺术气魄和文体特征。但这类散文的出现,对“文化散文”的形成和发展,无疑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当它作为早期“寻根文学”的一些代表作,更对嗣后受“寻根文学”思潮影响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艺术影响。
80年代中期前后,由于“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文学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体认,同时也由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和文学解禁,扩大了艺术表现的领域(包括地域),这期间通过开拓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发掘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已经受到了各体文学创作的普遍重视。尤其是以“西部诗歌”为先导的“西部文学”的崛起,和某些新潮诗人从倡导民族史诗向重构民族文化方向的创作深化,更进一步加剧了文学创作中的这种文化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对后来的“文化散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标志着“文化散文”创作在早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是一些从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的“西部诗人”,其中又以周涛和马丽华的创作转变最具代表性。作为“西部诗人”,周涛和马丽华的诗歌创作都以表现西部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情习俗和历史文化著称,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但向人们展示了长期以来为文学所忽视的丰富多彩的西部题材,而且也为文学注入了一种以雄强豪放著称的西部风格和以开拓创业为特征的西部精神。他们在80年代中期前后先后转向散文创作,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西部题材、西部风格和西部精神为特征的。与王英琦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她在祖国各地游历的经验不同,周涛和马丽华的创作之源主要是出自他们长期在新疆、西藏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当然也包括在整个西部地区的游历乃至冒险的经历。他们的创作也因此而较王英琦多一些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少一些旁观者客观、冷峻地审视的色彩。这同时也是“文化散文”创作由寄寓于历史反思到转向注重自身的文化体验的结果。周涛和马丽华的散文创作因而也是“文化散文”由早期的略具规模到逐渐壮大成形和不断走向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就这两位作家从80年代中期迄今的散文创作而言,虽然他们都是来自内地,但由于进入西部有时间的先后长短和进入的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人生经历、创作经历乃至文学和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因而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分野。如果说马丽华的散文创作注重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西部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的话,那么,周涛的散文创作就似乎更偏向于由西部的自然风光、民情习俗、人文景观和历史文化所引发的想像和思考。他的散文创作因而依旧保留了他作为一个“西部诗人”所特有的诗性和神性的特征。这位作家的散文代表作品主要有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和《周涛散文》(三卷本)等。在这些散文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记录具有西部特征的景物人事,但他的笔触却不流连于这些景物人事本身,更不去精细地刻画这些景物人事最能体现西部特征的那些精确的细节,而是转向抒写对这些景物人事的独特感悟,和由这些景物人事所引发的独特思考。而且这种感悟和思考又不停留在这些景物人事本身所显示的具体确定的社会意义和人生价值的层面,而是指向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或终极性的生命和存在的哲学问题。通过对西部的景物人事的这些独特的感悟和思考,周涛的散文不但在西部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漫游,而且作者也把这种借助散文创作精神的漫游,作为自己融入西部,与西部的历史文化、自然人文融为一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周涛的散文创作因而在进入90年代以后,又以其独具的诗性特征和理想主义格外引人注目,成为这期间的文学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一个独特的标帜。在艺术上,周涛视散文创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描摹生活的画笔”,(注:周涛:《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周涛散文》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因而他在创作中也就格外喜好议论和抒情,而疏于叙述和描写。而且他所主张的这种“表达思想”的散文,又必须是绝对自由的,不受章法和规范的约束,要能“让思想和感情自由奔放地表达”。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就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带有极强的自我表现的性质。这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式的精神漫游,即使得周涛的散文创作较之那种拘泥于叙事和细节描写的散文,显得格外生气贯注、自由灵动,另一方面也因为疏于对文化事相的完整记叙而难免要削弱作品的文化含量。
相对于周涛从50年代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就随父辈进入新疆,以后又长期生活、学习和工作在新疆的经历而言,在70年代中期结束大学生活后进入西藏的马丽华,此后虽然也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但毕竟只是一个羁留于西部的人生之旅的过客和外来的文化闯入者。因此她的散文创作也就不可能像周涛那样,与西部的山川风物和历史文化天然地融为一体,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感受、体验和认识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带有一种传奇色彩的充满了游侠式的浪漫冒险经历的女作家,在进藏后的20余年的时间内,足迹差不多踏遍了西藏大地,尤其是最能体现藏文化特色的藏北地区,创作和出版了大量散文作品,其中长篇纪实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和它们的合集《走过西藏》,更是她的西藏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作为一位诗人,马丽华最初的散文创作如同周涛一样,对西藏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也充满了一种诗化的想像,但与周涛不同的是,这种诗化的想像,不是源于作者对西藏文化深刻的内心体验中所生发出来的诗意,而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闯入者,在对西藏的自然人文的审美静观中所获得的感性经验。她的这些创作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对西藏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景观的深情礼赞,在这种深情礼赞中,同时也寄寓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和对于人生理想的诗意追寻。随着作者对西藏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和感受与体验的进一步加深,对西藏的这种由诗化想像而生发出来的深情的礼赞,就开始转化为一种建立在对西藏文化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深度的文化体认。这种文化体认不仅表现在作者在无尽的游历中,用自己的身心去追寻藏文化的足迹,去体验藏文化的悠久神秘和博大渊深,从而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到这种文化的历史中去,实现文化的融合、灵魂的净化和个体的精神升华。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在设身处地地企图通过自己的想像,重新经验藏文化在西部这块高寒缺氧的山地上孕育发生和成长成熟的奥秘,通过这种想像性的经验,重建藏文化的历史阐释,在这种新的历史阐释中,使这种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和生机。这是作者对西藏的经验和感受、理解和认识的凝聚,也是她的散文创作的诗意的提升。在马丽华的散文创作中,天然地贯穿着汉藏两种文化的比较和碰撞,这种比较和碰撞的结果,是通过作者对藏文化的融入实现两种文化的亲和。与此同时,作者在对藏文化的理性审视中,也引入了一个现代的维度,即从现代历史和现代生活进程中,审视西藏这一古老文化的发展演变和存在状态,为这一古老文化在历尽沧桑后走向现代,提供一种理性的参照,马丽华的散文又因此而对藏文化多了一层从现代文明的高度进行批判性审视的色彩。与周涛视散文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不同,马丽华的散文虽然也不乏对藏文化深刻独到的感受和思考,但她一般不脱离具体的描写对象去作天马行空式的冥思玄想,而是把她的思想感情融注到具体的物象之中,从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的考古式的发掘与探险式的游历中,去深入地感受、体验、领悟和思索藏文化的精神奥秘。她的散文因而既展示了藏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绚丽多姿的山川风物、诡奇幻异的民情习俗,同时又无处不浸透着浓郁的诗意和深沉的哲理。她的散文也因此既是历史的、游记的,又是诗的、哲学的,兼有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双重意义。
80年代中期,当周涛和马丽华以一个“西部诗人”的身份,先后转向这种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的“西部散文”创作的时候,在小说界掀起的“文学寻根”的热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注重文化的散文创作追求。这期间的散文创作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由伤悼逝者、反思历史向追求文化的创作转换,“文化散文”已然露出了一种新的创作转换,“文化散文”已然露出一种新的创作苗头。如前所述,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格局初开、商品大潮涌起之际,散文如同其他类的创作一样,也出现了一种盲目追随市场潮流,日益沉迷于一种“消闲”和“消费”性的“小散文”的商品化创作倾向。为挽救散文创作的这股颓风,创刊于90年代初的《美文》杂志,开始倡导一种“大散文”的写作:“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注:《美文》杂志创刊于1992年9月,由作家贾平凹主编,引文见该杂志创刊号由贾平凹撰写的《发刊词》。)按照倡导者的理解,这种“大散文”,要实现如下几个方面的创作目标:“1、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2、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辨。3、发动和扩大写作队伍,视散文是一切文章,以不包专写散文的人和不从事写作的人来写,以野莽生动力,来冲击散文的篱笆,影响其日渐靡弱之风。”(注:贾平凹:《走向大散文》,《贾平凹文集》第1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提倡虽然在散文创作和理论界也引起了一些关于“大散文”问题的讨论,被人目为此后的“文化散文”写作的始作俑者,但究其实,它的真正意义却在于,推动了在80年代中后期已日渐露出苗头的“文化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文化散文”创作的规模和声势,使“文化散文”的创作由前此阶段的分散、自发的状态,发展到一种较为集中、自觉的艺术追求。“文化散文”因此在90年代呼应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提倡,在反拨市场化、商品化的潮流中,逐渐发展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新的散文艺术品种。
进入90年代以后,从事“文化散文”创作的作家,就其广义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其一是上述周涛、马丽华等作家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创作的自然延续。这类创作因其前缘而带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和较浓的乡土气息。是“文化散文”中的一支“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散文的创作劲旅。其二是以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的勃兴。这类散文或回忆故人往事,或述说人生经历,或漫论旧学新知,或记叙,或描述,或抒情,或议论,形同古代笔记,又如现代随笔,既有深厚的学养,又见娴熟的文笔,是一种学、艺双佳,文质彬彬的新古典主义的散文文体。其三是以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为代表的跨文体或兼文体作家散文创作的繁盛。如果说从80年代中期前后,相继有作家从一种文体如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尔后成为专司散文写作的散文作家的槐,那么,到了90年代,这种创作转换就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跨文体或兼文体的写作,即在专擅一种文体(主要是小说)写作的同时,又兼司散文创作。尤其是在文学倡导人文精神、高扬人文理想的过程中,一些作家在把这种创作题旨贯注入自己专擅的小说或诗歌文体的形象描写的同时,也借助散文这种更直接的表达形式,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的思考。这类散文创作虽然也如“学者散文”一样讲究思想和学问,但由于作者的擅长形象描写而兼有形象的实感,更具感性特征。除此而外,这期间的一些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生活小品和哲学随笔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文化散文诗”的一些艺术特征。追求散文中的文化意味,已然成了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气。
作为90年代“文化散文”创作产量最丰、影响最大因而也最为引人注目的散文作家,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无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位学者型的散文作家在专事散文创作之前,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从事戏剧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和文化史论论著。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个学者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方式,他也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拷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因为这种反省和拷问,所以他才“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在古老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遍布华夏的文明遗址上,同时也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山山水水间,开始了无尽的精神漫游和文化追寻。从80年代中后期起,他在《收获》杂志为他开辟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个专栏上,发表了他走出书斋后创作的大量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作品分别结集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此后又有选本《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和散文新作《霜冷长河》等作品出版,在“文化散文”创作中一时蔚为大观,成为广大读者争相传阅的对象。进入新世纪以后,余秋雨又借香港凤凰卫视组织的“千禧之旅”和“欧洲之旅”,将自己的精神漫游和文化探寻的足迹,拓展到中东、南亚和欧洲各地,陆续出版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等新的散文作品集,在探索了中华文明之后,又相继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进行了深入的文化探寻,表现了这位作家在“文化散文”创作方面的最新成就和持久不衰的旺盛的创作生命力。
在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余秋雨说:“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睛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涌而出。”中国古代山水,正是因为有无数“有悟性”的文人,先先后后在同一个地方站立过,所以才把他们的经历、学问、思想、情感乃至整个人生和命运,都留在了这平平常常的山水间,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层层累积的历史和文化的沉淀,所以才引发了作者的兴趣。作者“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是一种“人文山水”而不完全是“自然山水”,(注:以上引文均见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无疑正是要从这些历史文化蕴含极为丰富的山山水水间,追寻古代文人的足迹,发掘古代文化的沉淀,通过这种追寻和发掘,既寄托自己的文化关怀,又给读者以文化启迪。他的散文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散文之中。在谈到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召唤自己的“文化指令”,和自己的散文创作观照这些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精神标准”时,余秋雨说:“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注:余秋雨:《文明的碎片·题叙》,《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围绕这样的主题,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主要从如下几个精神向度,展开了他的文化寻觅。其一是追索一种文化生成的奥秘。文化是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积淀,大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小到一个地域的文化或一个行业的文化,都与该民族、该地域和该行业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的一定历史和现实环境有关,是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体现为一种文化事象,往往不是已经消逝了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活动本身,而是这些活动所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留物。这些历史的遗留物虽然不能系统地呈现一种文化形成的历史和完整的形态,但却保留了该种文化的深厚的精神积淀。余秋雨的这类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历史的遗留物,去追寻一种文化孕育、萌芽、生长和发展、演变的奥秘的。如《莫高窟》写敦煌佛教文化、《抱愧山西》写山西晋商文化等。前者通过审视敦煌洞窟开凿兴建的历史和洞窟壁画形成的历史,深入地揭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历代众多信徒虔诚的心灵所孕育创造的辉煌的佛教艺术文化,是一个民族心底的“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的产物。后者则通过考察山西境内现存的一些商号的遗址和它们的兴衰的历史,深入地揭示了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民情风习和历史变迁,对独特的晋商文化所起的孕育和催生的作用,如此等等。这类作品更多地表达的是作者对一种文化的赞叹和神往,同时也带有一种文化寻根的意味。其二是感叹一种文化的历史兴衰。文化作为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历史沉淀,在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本身就会经历许多兴衰际遇,就要经历历史风雨的冲刷淘洗。今人所面对的,只能是在这种历史的兴衰际遇中,经过历史风雨的冲刷淘洗所留下的文化的残存物。这种文化的残存物,在今人眼里既是一种文化的特殊标志,同时也记录了该种文化在历史的兴衰际遇中所留下的冲刷淘洗的擦痕。深入这种文化残存物的内里,细致地辨认这种文化残存物所存留的历史风雨的擦痕,不但可以捕捉到该种文化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同时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该种文化的命运变迁所昭示的历史宿命。如《道士塔》写敦煌佛教艺术宝库的盗卖和流失,《风雨天一阁》写一个藏书家族的兴盛和衰落等。前者通过一个道士的无知,揭露的是一种腐朽的制度和一段屈辱的历史导致敦煌艺术的毁弃。后者通过一个藏书楼的历史,揭示的是一种历史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导致一种藏书文化的兴衰。前者所写的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后者所写的则是“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二者都隐含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沧桑际遇的一种深切的历史感叹。在表达这种感叹的同时,这类作品也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和对一种文化历史的理性审视的态度。其三是对一种文化的缔造者的由衷的礼赞。文化既然是一种群体的历史创造的产物,因而文化总是与一定的人群和一定的历史相联系。但是,在文化的创造中,那些起着举足轻重或决定性作用的始作俑者或核心人物,如某些明君贤相、圣哲先贤、仁人志士、骚人墨客等等,他们的历史活动和文化活动所留下的行迹,又往往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历史表征。这种文化的历史表征不但忠实地记录了该种文化艰难缔造的历程,同时也生动地显示了该种文化的缔造者的思想性格和精神品质。穿越这种历史的表征,我们不但得以窥见该种文化的缔造者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而且还得以领受这些文化的缔造者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如《一个王朝的背影》通过承德山庄写康熙皇帝,《都江堰》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写蜀郡太守李冰等。前者写的是奠定了一个王朝基业的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后者写的是开创了“天府之国”富饶历史的李冰泽被后世的无量德政。这类作品在表达作者对这些文化缔造者的由衷礼赞的同时,也重塑了这些文化缔造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形象。其四是对一种文化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人因其是文化的缔造者、守护者和传承者而成为在社会人群中身份地位都比较特殊的一群,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与一个时代的文化兴衰枯荣、发展变异紧密相联。通过这些文化人的命运,往往可以捕捉一个时代精神发展的脉络,折射一个时代风俗时尚的变化。尤其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有诸多文化人因为坚守一种文化立场和道德操守,或与统治者意见不合,或遭受奸佞之徒的陷害,或因派别斗争而罹祸,或因直言诤谏而见疏,如此等等,这些文化人的命运自然是脱不了贬谪流放,甚至因此而妻离子散,客死他乡。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文化人遭受贬谪流放的足迹,也构或了一种独特的流徙文化,他们遭受贬谪流放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也构成了一部独特的文化历史。追寻这些流放者的足迹,不但可以通过他们的坎坷命运和尴尬人生,深入探究一代文化人苦难的精神历程,而且也可以借此触摸这些文化人历尽磨难却依旧不乏高贵的心灵,如《流放者的土地》写清代流放宁古塔的官吏文人,《苏东坡突围》写苏东坡流放黄州的经历等等。前者写流放者的坎坷命运和在流放地艰难竭蹶的生存状态,后者写苏东坡因流放而有幸获得个体精神的“突围”,都寄托了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和命运的无穷感慨。在感慨这些文化人的人生和命运的同时,也对造成他们这些不公正的人生和命运遭际的社会文化乃至心理性格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思考。其五是发掘一城一地的文化蕴含。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保存于书本之中的文人的文化,也有存留于生活之中的民间的文化。尤其是有众多人群聚居的村墟乡镇和现代都市,更是一种文化最易呈现自己独特形态的处所。发掘这种人群聚居地的文化蕴含,无异于开掘一种蕴藏丰富的历史地层,从那些存留于历史遗址中的世俗生活场景、保存于历史化石中的民俗风情,乃至历史在今人的思想性格中的一种文化投影,都易于把握该种文化的一种历史发展和现实形态。如《白发苏州》写苏州的历史,《贵池傩》写贵池的民俗,《上海人》写上海人的性格,《江南小镇》写江南的民居园林,《西湖梦》写西湖的文化和传说等。这些作品或通过一段历史写一座城市的古老,或通过一种民俗写一地人民的性情,或借助一种市民性格写现代都市文化的复杂,或借助一类建筑写旧式乡镇生活的恬静,抑或用亦真亦幻的传说来勾画一片湖水的文化梦境,如此等等,都意在通过这种考古式的发掘,为现代生活提供一种精神文化资源,除上述几个主要方面外,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还涉及到回忆故人往事、月旦历史人物、评说文坛掌故、赏玩自然山水,乃至独抒一己性灵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创作无一不贯穿着余秋雨对他的描写对象独特的文化发现和文化阐释。
作为一位有代表性的“文化散文”作家,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重文化的感悟而不重过程和细节的描叙。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涉及到的描写对象,相对而言,主要有游历性的和观赏性的两个类型。前者多见于一种游历的过程,后者则见于一种观赏的细节。但无论是突出过程的游历对象,还是凸显细节的观赏对象,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一般都不把他的笔力主要放在对这些游历过程和观赏细节的描叙上面,而是特别注重在游历过程和观赏细节的同时所得到的文化启示和文化感悟。他的作品为表达这种文化启示和文化感悟而生发的议论和抒情,因而要远远大于叙述和描写性的因素。夹叙夹议、夹抒夹议因而也成了他的“文化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艺术特色。第二个方面是重文化的联想而不重事实的考据。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涉及到的许多对象,都是过去年代的历史,有些还是争议颇多或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历史事实作大量的考订工作。余秋雨的散文创作虽然在事实的考订方面为人所诟病,也确有一些知识性的失误,但在保证一些基本事实和主要细节相对准确的前提下,他在创作中注重的是由这些事实和细节所引起的文化联想和文化想像,而不是这些事实和细节本身。这样,他的散文创作反而因注重文化想像而显得自由灵动,因注重文化联想而显得摇曳多姿,与某些头巾气重的胶柱鼓瑟的所谓“学者散文”判然有别,这是他的“文化散文”的又一个主要的艺术特色。第三个方面是重理性的阐发而不重资料的引证。与上一个方面相联系的是,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既不重事实考据,也就无意于论证某种文化事象的确凿无误,评判某种文化历史和文化人物的正谬曲直、是非功过,而是追求对对象的文化蕴含的深入挖掘和独到阐发。而且这种理性阐发也不是依靠逻辑的推演和实证的分析,而是依靠丰富的文化想像和文化联想完成的。这就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创作避免了过繁过甚的“掉书袋”式的资料引证,而具有一种因此而带来的独特的理趣。这是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第三个主要的艺术特色。与上述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色相关联的是,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因重想像和联想,而融合了虚拟性很强的戏剧和小说一些艺术表现手法,他的某些散文作品因而具有很强的情节性,甚至出现带有一定冲突性的戏剧场面。同样是因为上述在丰富的文化想像和文化联想中完成对表现对象的理性阐发的创作特色,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也融合了庄子的哲学散文天马行空、汪洋姿肆的思维理路和两汉赋体散文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他的散文因而又呈现出浸润了一种理性精神和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因为是处于一种游动和行走状态之中,是一种所谓“行者散文”,因而就难免要留下许多行色急急匆匆、行程断断续续的痕迹。这种痕迹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某些散文作品思虑不深、了无新意,往往流于一些即兴的观感和泛泛的议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另有某些散文作品缺乏必要的剪裁构思,行文随意,篇章散漫,都影响了他的散文创作的整体的艺术质量。
标签:文化论文; 散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周涛论文; 马丽华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