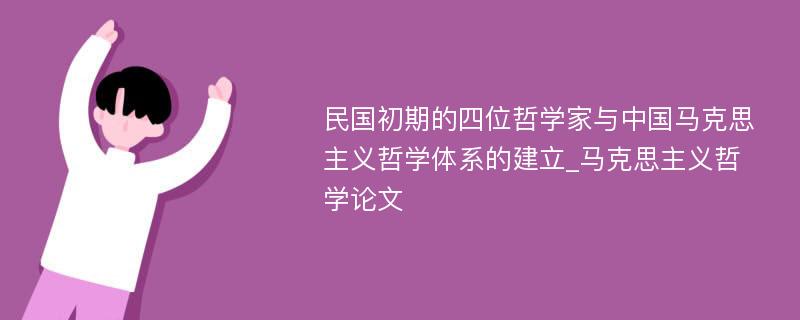
共和国前期四大哲学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国论文,哲学家论文,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哲学的定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胜利的哲学实绩,最终体现为20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和国的全面胜利的演进过程中,最有可能在哲学体系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是两个人,这就是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李达和艾思奇,最有可能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是两个人,这就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最高领导杨献珍。这四个大家的哲学思想走向,基本上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设想一下,如果四人能通力合作,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创造上,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精神的现代哲学大概应能产生出来。然而,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未能让这四人具有通力合作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政治型哲学,而且是强调斗争性的政治型哲学,这决定了四人的哲学思考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进程的,而当四人由所在的政治位置和政治境遇而产生出不同的哲学思想方向和哲学运思的时候,笼罩他们哲学倾向的共和国前期的总体精神,决定了其哲学在生成过程中,不是在学术争论中反省自身也反省别人,而是在政治的批判中让自己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这样,共和国前期的政治现实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定型,最后凝结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
且看这最有可能创造中国现代哲学辉煌的四人的哲学活动。
一、李达与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贡献
李达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社会学大纲》),倘若他能入主北京的哲学中心,一心哲学思考,也许能有机缘更上一层楼。当时毛泽东是希望他留在北京的,而且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繁忙中,与李达聊天半夜,又让刚治胃穿孔出院的李达当夜睡在自己的床上。这让李达当时兴奋不已,从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出来,便向他的小老乡唐棣华讲东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白天饮酒晚上同榻且“加脚帝腹”的典故。①当时中央已经对李达有一系列的任命,包括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这明显地是让他主持新中国哲学界。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早年与陈独秀合作不愉快而最后脱党的经历或决定这一经历的李达的性格,让他不愿留在政治中心的北京而去了南方(先长沙后武汉)搞教育,虽然后来李达在武汉大学创建了哲学系,但其哲学写作却主要是写时尚的哲学解说(解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和时政解说(宣传新宪法等),以及参与时尚的哲学批判(批判胡适哲学和梁漱溟思想),直到晚年才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只主编了上卷《辩证唯物论大纲》就去世了。在以其《社会学大纲》为基础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他想大改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因此李达在共和国哲学中的创新是合乎本人愿望地完成了。而在这一上卷中,他心中考量的是苏联科学院1953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1959)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因此,总体而言,其《辩证唯物论大纲》仍在苏联哲学模式中打转而未能超越出来。整体观之,李达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一言以蔽之:民国时代一人写成的《社会学大纲》的完整体系和共和国前期一人主持、团队完成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的半个体系。
艾思奇在民国时期以半部哲学体系《大众哲学》赢得大名,自从其进入革命中心延安,又进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一直处于哲学中心。他是延安新哲学会(1938)发起人和哲学核心;在延安张闻天主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1941),他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在毛泽东组织的六人(毛泽东、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杨超、和培元)哲学小组中(1939),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哲学核心;在张闻天部长兼组长的中宣部哲学学习小组中,他是学习指导员,当时的延安机关和部队人员,多慕艾思奇之名来参加学习,包括朱德总司令,每次都来得很早,自带一个马扎,认真阅读小组发的学习提纲。在北京,艾思奇是哲学重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后兼副校长),建国初曾兼任清华和北大哲学教授,在北大首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主导了新哲学对旧哲学的改造和规训,通过讲课和广播,主导了全国的哲学思想演进,主导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说和对旧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一统始终战斗在哲学的前沿。自《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上赢得大名之后,艾思奇一直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化运作,在延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研究提纲》(1939),在北京中央党校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人民出版社,1957)。在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学术化表述的同时,艾思奇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半的研究工作,这就是三写和三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秀实绩。正是在这多年的开拓和进取的基础上,在1960年共和国决定编自己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机缘中,艾思奇理所当然地成了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编,②该书于1961年出版,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定型。艾思奇主编国家级教材的时候,心中所考量的是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当时中国各高校的同类教材(人大本、北大本、上海本、吉林本、湖北本、广东本以及中央党校本③)。因此,总体而言,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在苏联哲学模式中打转而未能超越出来。整体观之,艾思奇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上,即民国的半部体系和共和国的整个体系。在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创建上,艾思奇的历程与李达的历程,正好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
二、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思考
与艾思奇和李达相比,杨献珍(1896-1992)的哲学训练主要不是来自米丁型的苏联体系型哲学,而是来自马列原典。1931年春,杨献珍被捕,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狱中党支部买通狱卒买进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杨献珍等四人(杨与廖鲁言译英文,殷鉴和孔祥祯译俄文)翻译出来大家学习,监狱变成“红色党校”。杨献珍这位“囚徒翻译家”的职位是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在当年一道坐牢的作家王玉堂(又名冈夫)的记忆中,这些著作里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与民族问题》,以及当时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陶里亚蒂、皮克等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许多文章。在红色党校里,杨献珍内在的哲学素质和教员素质得到了提升,出狱后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党的教育战线,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1937)到北方局党校(1940)到延安中央党校(1945)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1946)到马列学院(1948),其时,刘少奇是校长,他是教育长,马列学院迁入北京改为中央高级党校(1955),杨献珍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而在北方局,杨献珍与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时任北方局妇救会领导)是好友,当时在杨献珍鼓励下赵树理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不能出版,杨献珍与浦安修商议,说动彭德怀支持,方得以面世并引起文坛轰动,这成为一段佳话。这里节外生枝,提到这一点,是要从杨献珍革命经历和人际交往上(狱中的薄一波等、北方局时的彭德怀等、马列学院时的刘少奇等)来体会当他提出一种特异的哲学观点时,将会让那强调斗争时代的人们,作出怎样的无穷的联想和曲折的寻味。言归正传,杨献珍的哲学训练是靠马恩列斯原著及西欧共党领袖的著作完成的,1936年出狱后,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期间,杨献珍翻译了一本意大利人阿多拉茨基撰写的英文版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建国后,他写过《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1958)、《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1963),这与米丁型的哲学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也许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杨献珍一直是艾思奇的领导(马列学院,杨是教育长,艾是室主任,中央党校,杨是校长,艾先是室主任后是副校长),但杨与艾的思维路数又总是不同的原因。在建国初的一系列主流性哲学运动里,杨也不断著述,比如,在大学“社会发展史”中,他写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6月6日),在大学毛泽东“两论”的运动中,他写过《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但其远不能与艾思奇的风头相比。不过,也许正因为杨献珍没有被米丁型的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一方面在于他的哲学训练里更强调唯物主义,从而与特别强调辩证法、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所区别,更容易正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哲学与特别强调绝对的对立和对立面斗争的斗争哲学也有所区别。他在第一次哲学争论中提出的“综合基础论”应该是与他对唯物主义的个人理解相关的,在第二次哲学争论中,他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认定为唯心主义也应该是与此相关的;也许正因为坚持着唯物主义,加上一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又更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资源,第三次哲学争论中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这正是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启发而产生的灵感,同时又与他的思想本有的、与斗争哲学不同的一面相关联。在党校,杨献珍与艾思奇都是领导,同时又都亲自授课,二人的分工是杨主讲唯物主义,艾主讲辩证法;在原著讲解上,杨讲解《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艾讲解《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杨虽然不主讲辩证法,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思考辩证法,特别是当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之后,哲学的突破从这一根本规律上突破,应该是一个可一鸣惊人的创新。最有意思的是,杨献珍想进行的思想创新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来,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一条发展进路来,而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来。杨自云,1956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他读其中的《谈谈辩证法》一文,文章开头即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④斐洛的这段话是:“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们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伟大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看到这里,杨献珍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古希腊人那里有反映,在具有无数伟大哲学家的中国也应该有体现。自此之后,他一直在寻求和思考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的表达法。1962年1月,杨献珍与部分党校教师在西安参观,阅览《蓝田县志》,⑤读到晁公武《读书志》讲蓝田吕大临著《老子注》如此阐述老子思想:“盖老聃之学,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什么叫“合有无谓之元”呢?又引《老子》第11章:“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杨献珍心中一亮,意识到这是一个由先秦(老子)到宋(吕大临)到明(晁公武)一直流传着的思想。思维敏捷的杨献珍又马上把这一中国思想与列宁思想作了对接,认为“合无有之谓元”正是列宁所讲的“任何事物都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而中国古人的“有”就是“存在”,“无”就是“非存在”。所谓“合无有之谓元”,正是指的“有”与“无”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矛盾统一,也类似于黑格尔讲的“存在和无的统一,提供转化生成”的思想。熟悉中西哲学史的人知道,杨献珍虽然没有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哲学“有与无”的真正内蕴,但他确实看到中西哲学上最根本的东西(西方的存在与非存在和中国的有与无)之间的相似的一面。这一西安之行中的灵感促进了杨献珍进一步从中国思想史上去思考对立统一规律。1963年杨献珍读到明代方以智的《东西均》,立即顿悟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把物称为东西,东与西方向相反,相互矛盾,这就是一分为二,但同时相反的东与西又合为一个东西,这就是合二为一。且看《东西均》如下之论:
东起而西收,东生而西杀。东西之分,相合而交至,东西一气,尾含而无首。以东西之轮,直南北之交,中五四破,观象会心,则显仁藏密而知大始矣。(《东西均·开章》)
东西轮尊之宗一也,一即具二。主宗者用一化二,而二即真一,谓之不二。“吾道一以贯之”与“一阴一阳之谓道”,三“一”者,一一也。(《东西均·开章》)
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东西均·三征》)
何为几?交也者,合二为一也;轮也者,首尾相含也。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征矣。(《东西均·三征》)
圣人因一在二中,阴阳清浊,而立善恶之榜;因人生有好恶,而使知最初之公好公恶;因有名字,因有是非,此有昊之公符也。(《东西均·公符》)
在对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有了新进展的今天,学人已知《东西均》不仅有“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更有中国型的“一分为三”的思想(世纪之交,庞朴特别提中国思想的一分为三,并注释《东西均》以彰显其一分为三的思想⑥),更有区别于西方哲学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中表达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思想,而呈显的是事物中包含两种对立面的统一,一是两个实体性的对立面的统一,二是一虚一实的对立面的统一。杨献珍是从提升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视角去看《东西均》以及其他中国思想的,因此,他只看到了中国哲学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有关的两个方面,一是“一分为二”,二是“合二为一”。杨献珍由《东西均》再想到中国的其他思想,比如,张载的“不有两,则无一”,想到作为中国思想核心表述的太极图,体悟到“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可以说它是一分为二,说它是合二为一也可以。”⑦杨献珍关于被毛泽东所认为的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律的思考,到读方以智《东西均》时,形成了合而为一的思想。杨献珍主张,对立统一规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分为二,二是合二为一,只有两方面都讲到了,对立统一规律才全面。正如杨献珍《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1964年4月)一文中所说:
对立物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不是铁板一块。“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二本于一”。中国语言中把物叫做“东西”,说明物本身就包含着正(东)反(西)。物叫“东西”,实即表达了“对立统一”的意思,或“合有无谓之元”的意思。⑧
以前毛泽东、艾思奇只讲一分为二,杨献珍“发现了”合二为一,因此合二为一成为杨献珍的贡献,从而也成了杨献珍的标签。特别是别人不同意他的“发现”或他的补充,一定要坚持只有一分为二,没有合二为一,坚持说一分为二是对的,合二为一是错的,这样,双方的对立理论又成了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对立。有了双方的尖锐对立,杨献珍的理论又只成了合二为一。以后,一提到杨献珍的理论,我们就说,他提出了“合二为一”思想。这里,历史和现实的诡谲,很是耐人寻味。
历史和现实更耐人寻味的是,杨献珍以为他完善了对立统一规律,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这是不错的。而实际上,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思想,不仅是一种纯哲学理论,更是一种政治型哲学,其中包含了整个中国革命历程的内容,对立统一的规定在毛泽东那里,是与革命的斗争性紧密相关的,是毛泽东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哲学武器,更是毛泽东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哲学武器。当杨献珍想用合二为一去补充和完善一分为二的时候,真的是修正(至少是减弱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斗争性。因此,革命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马上认识到,这是用“调和论”来反对“斗争论”,这是“反对我”!这一认识上的差异是政治家与学者之间的差异。虽然杨献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他提出的合二为一确实显出了两种思想的差别:中国型思想与西方型思想的差别,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想、特别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的差别。虽然杨献珍在提出合二为一的时候,已经将中国古代思想大大地西方化和现代化了,但中国古代思想的味道还是在其中。而杨献珍是带着一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去找寻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哲学表达方式的。⑨自建国后,寻找和发现中国资源,就是杨献珍的一种运思方式。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争论中,他对中国的主观唯心论作了梳理,发现《大藏经》、《华严经》以及宋明哲学话语中充满这样的思想:
事物皆为真心全体所现,虚妄不实,所谓空也。
心外无境。
一切唯心所造。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万法即万事万物。识即意识)。
陆象山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王守仁说:“意之所在便是物。”“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李贽说:吾之身色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⑩
对这些中国古代哲言,虽然杨献珍只从唯物唯心这一角度去读,但读着这些哲言,还是能够感到其内蕴的智慧。杨献珍思想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对中国思想的梳理本身和对中国思想的寻找本身中显透了出来。
现在回头看,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演进,一直面对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与世界先进的关系,二是现代中国与传统的关系。在第一个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中国思想跟上世界先进的前进步伐,它又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如何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第二,如何把世界先进思想运用于中国的实际,以改变中国的实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就不仅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学到手,而更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第二个方面,如何让中国传统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即把传统和现代结合起来,推进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前一方面做得相当好,那么,在后一个方面则几乎可以说是空白,虽然,毛泽东、艾思奇、李达的著作中,都引中国的事例,但其功能则只是作为例证,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普遍性,而在艾思奇和李达的体系性哲学著作中,一是中国思想史不是世界思想史主流的一部分,人类的哲学史只是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中国人的份儿,二是中国思想始终是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从中国现代历史的初段,特别是在革命阶段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不完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感受到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上,当与莫斯科派斗争的时候,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在文艺上,当急需用文艺唤起工农的时候,他提出了文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然而,对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以达到民族思想文化复兴上,却基本是空白。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但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而且已经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内蕴。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杨献珍的哲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以服务于中国哲学的伟大复兴。当然连杨献珍自己也并未看清自己所做之事的这一意义。试想,如果有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有一种自由探索的空气,杨献珍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做下去,这一方向恐怕会逐渐地呈现出来的。而当这一方向被呈现出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应会得到一个大的提升。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于是,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或可想见杨献珍在风景如画的中央党校的52号楼的临时监房里,面对突如其来的监禁,心情该如何复杂与不知所措。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到贡献
毛泽东与前面三位大哲学家不同,不但是一个大哲学家,更是一位大革命家,只有从大革命家角度去理解其哲学思想,其哲学的重要意义才能较好地呈现出来,特别是毛泽东哲学如是呈现的形式,在中国化方面达到了远远超越其他三位哲学家的高度和深度。但他又不能像艾思奇哲学和李达哲学那样作出体系化的表述。这一点,对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如是定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是大革命家,他投身浸心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即为中国崛起的奋斗)中,在最复杂最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对中国革命(即中国崛起)进行了理论总结,这一总结从本质上说,是中国型的和中国现代型的。所谓中国型,是指以一种中国的实践理性(实事求是)进行着革命实践,所谓中国现代型,是指把自己的革命实践与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最后认定在共产主义思想上)联系起来。理解这两点,是体悟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一个基本点。对中国文化实践理性的固着坚持,让毛泽东在关注世界先进的思想的同时,始终关注中国的具体现实,并使他在领会先进思想的精神的同时,将之化为对中国现实的洞见。正是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让他逐渐地深入领悟了中国社会自现代性以来的演化历程的“实质”,逐渐地领悟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的“真相”。对世界的先进思想的追求,让毛泽东把这一中国现代性演进的“实质”和“真相”,用一套世界的先进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出来,获得了一种“世界的普遍性”。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从话语表层来说,是完全世界型的,从话语的深层来说,是完全中国型的。从前一个方面说,可以看到毛泽东话语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发展传统,从后一个方面说,可以看到毛泽东话语不时地特别是在根本问题上与苏联—第三国际指示偏离,不断与中共党内主掌着领导权并代表苏联—第三国际的莫斯科留学生派作着斗争,直到让自己的“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取得主导地位。
正因为毛泽东在亲身的实践和不竭的理论思索中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他把中国革命定位在武装斗争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中国革命的主体确定在农民上(“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通过阶级分析和发动群众,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成了具有铁的纪律的军队,通过群众运动而提高了穷人的威风,树立起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战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极端复杂的情况,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思想和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在历尽曲折的中国革命史上,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每一次创新,都或在根本上或在具体上对苏联模式和第三国际具体指示有“背离”,有意思的是,而每一次“背离”又都导致了中国革命的一次新胜利,从而最大地符合了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利益。只有深入中国的实际,才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只有把中国的实际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话语表述出来,由中国实际产生的思想才能获得普遍性的意义。思想的核心是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直接来自苏联,表现在李达和艾思奇的哲学体系中,当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经验按照苏联哲学的话语方式进行提炼时,创造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这两篇著作建立在苏联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又对这一体系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点(认识论和方法论)按中国方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精致化,在哲学深度上取得了最大的突破。毛泽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基本突破,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来说,已经够了,《实践论》确立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合法性(中国革命的理论只能来自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矛盾论》不但给了怎样看待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一个根本的方法论,同时也给了怎样看待世界革命问题的一个方法论(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一个事物,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诸多矛盾聚合在一起,要抓住主要矛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统一战线)是由这一方法推导出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基本方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统一战线,也是由这一方法推导出来的。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对苏联型哲学体系内两个基本点上的创新,已经达到了这个体系所能容许的极点,这极点对苏联型哲学体系的暗中“偏离”,或者说“内在”的中国化,如果不完全脱离苏联型哲学体系,就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如果完全脱离苏联型哲学体系,又难以达到世界的普遍性。当毛泽东在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在苏联否定斯大林而“变修”之后,一方面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中国革命的实践,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话语上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面对一系列理论难题,他开始公开地要反对从恩格斯到苏联哲学的三大规律和五对范畴体系的讲述方式;要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根本规律,也就是把矛盾斗争作为宇宙生态的根本规律,把《矛盾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这样做,就是要把由革命时期得到的哲学,认做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认为同样适合于建设时期。因此,毛泽东首先在共和国时期推出自己的两论,继而批评从恩格斯到斯大林的哲学总框架不对,要从以矛盾为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上来建立一套哲学体系,这呈现在毛泽东共和国前期的一系列讲话中: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的发展,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毛泽东1964年8月同康生和陈伯达的一次谈话)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11)[1965年,毛泽东在阅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内部讨论稿上册,唯物辩证法)一书时所作的批注]
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思是,辩证法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毛泽东1965年12月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50年代的一段话,通过否定斯大林的权威来强调对立统一是根本规律,60年代的三段话,第一段鲜明地要把对立统一作为根本规律,并让其统帅其他两条规律,第二和第三段则明确地是要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统帅其他两条规律和五对范畴乃至所有问题。在讲话中,毛泽东把恩格斯到斯大林的套套框框明指为“旧哲学”,意味着把在列宁那儿已有基础而自己明确提出的新观点看为“新哲学”,在这一新哲学中,毛泽东要求把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斗争精神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切方面中去。
毛泽东能够突破苏联型哲学体系,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了来自中国自身的经验,包括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以后的新变,或者说,毛泽东内蕴着中国精神而投身于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在中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结合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以对立统一矛盾斗争为核心的哲学思想。简言之,这一哲学思想的得出,建立在三个中国经验的基础之上:
第一,中国复兴的雄心:有着五千年辉煌的中国文化一定要在世界的现代化演进中崛起,这是由中国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也是从曾国藩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心中一以贯之的思想。毛泽东在1921年讨论新民学会方针时,就将之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1923年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用革命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在其晚年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的崛起是要建立在宇宙规律和历史规律之上,这样,从表层上看,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斗争规律代表了毛泽东对宇宙规律和历史规律的掌握,从深层上看,对这规律的掌握是为了让中国文化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复兴,让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崛起。
第二,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国要在世界的现代化演进中崛起,只有实行武装斗争。这是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现代性斗争历程和斗争实践一脉相承的。中国现代性发生以来,从鸦片战争由军事带来失败和屈辱开始,中国就以强化军事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性历程,历史的每一进步或在进步中的每一退步,都与血与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中国的现代工业、现代教育、现代服饰的出现,都与军事上的奋起紧密相关。在这一弥漫着血与火的历史中,中国现代领袖要成功必须军人化成为一个定式,从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到毛泽东均如此。从另一方面看,未能把自己军人化的领袖,则是与失败相联的,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武汉国民政府时的汪精卫,和共产党延安时的王明……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士人转变为军人,是一个大的演进方向,由军人成功而成为行政领导,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演进规律,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湘军系统,李鸿章的淮军系统,成为晚清转变中的行政主流。袁世凯的保定军系和张之洞的新军,成为变晚清为民国的关键。而袁世凯的保定军系,成了北京政府的行政主流。蒋介石的黄埔军系,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主流。而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解放军的主体骨干,则正为共和国的行政主流。理解中国现代性在战争中演进,中国的革命家成批地被训练为军人或由革命家转为军人,中国的现代政治精英从战争和军人中崛起,是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关键。当然,更宏观地看,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是由两批人决定的,一是军校生,一是留学生。在前一方面,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共产党军校(从井冈山军校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性三个不同时代(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共和国政府)的政治主流;在后一方面,从留美留欧学生,到大规模的留日学生,到留苏学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知识主体,而西方、日本、苏联留学生,在激烈、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性历程中,除了形成一个知识主体之外,大批地投身到军事斗争之中。这样留学生群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形成一种知识群体,固守在学院里,一是进入政治领域,成为行政精英,三是进入军事斗争,成为军人,而在这三个群体中,军人占了主流地位和主导地位,北洋政治的军阀时代是如此,国民政府的党国时代是如此,共和国时代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亦是如此。而且在共产党的体系里,留学生所代表的知识体系,也被定义为一种工具和武器,当毛泽东说,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2)之时,是对文艺这一知识形态的一种军事式定位,当毛泽东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时,(13)是对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军事式定位。这一定义是要让文艺和哲学具有军事性质,同时也是要让文人和哲人具有军人性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哲学里,内蕴着对中国现代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向军事性方面转化并不断发展的经验的总结,正如先秦《老子》一书具有兵书的性质,内蕴着对远古以来中国历史通过一系列残酷战争而向前演化的经验的总结。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哲学体现了对中国文化进入现代进程中的军人思想的哲学总结,代表了中国现代进程中的军事化思维的哲学总结,并把这一军事性思维上升为一种宇宙的根本规律。
第三,群众运动的方式。康梁变法失败,绝望于体制上层,而诉诸下层的民众,并希望把维护旧制度的臣民,改变为支持现代性宪政的“新民”。孙中山上书被拒,绝望于体制上层,而走向革命,诉诸于各种体制外的力量。如何唤醒和唤起内蕴在中国土地上的巨大的能量?这一巨大的力量究竟存在于何处?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各种思想求索、思想实践、思想竞争中,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中国共产党知道了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力量在什么地方,而毛泽东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把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断地调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最初认为,革命的最大动力在商人,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以这一分析为基础,毛泽东说: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负担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负担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14)
在此之后,毛泽东看准了革命的最大动力在农民,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有未来,农民是注定要分化和消失的,但中国革命的主力确实在于占人口总数最大部分的农民,如何把毛泽东看准了的这一中国革命的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结合起来呢?在话语的运作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等同于无产阶级,又等同受压迫受剥削阶级,又等同于穷人,在后两个词汇中,无地和少地的雇农、贫农、下中农全包括进来了。这样,西欧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在中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成为穷人闹革命。进一步,以作为穷人的工人农民为基础,扩大为一切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谁代表了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谁就会成功,谁唤起了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谁就会胜利。进一步,革命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们/敌人,在本质上,我们一定占据多数(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敌人一定是极少数;在现象上,永远是:我们/中间者/敌人,革命的过程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唤起在本质上属于我们的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中间者,打倒极少数的敌人。这一根本的道理,毛泽东在开始革命时很快就掌握了,并且不断地重复着。在1923年的《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一文中,他把中国革命的势力分为三种: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在建国初,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闭幕词里(1950),他把人分为三种:革命派(包括彻底革命派和口头革命派)、不革命派、反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而这一根本性的道理,正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相符合。当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行这样的理论抽象和哲学抽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在生产关系进而在阶级关系上的体现,就成为根本性的东西,而经济发展本身,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其他与人的社会性同样有关的一系列东西,如科技革命等等,被忽略了,经济自身的规律和科技自身的规律被忽略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斗争,当被看成与经济规律和科技规律相对立的时候,很容易地被指向了在低级经济条件下的“天下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不知不觉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宁要红,不要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之所以会不自觉地出现这一偏离,又是因为整个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是与将对立统一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相一致的。
由中国革命经验总结而来的毛泽东斗争哲学,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的惯性。我们看到,这一惯性是如何地在经济上让中国的建设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的大跃进;我们看到,这一惯性是如何在一系列事件(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东欧出现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等等)的综合冲击之下,在政治上让中国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这一理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正如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并反复修改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概括为六点,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15)按照这个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另一方面,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中,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独立性,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消灭了之后,还继续存在。因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更加激烈也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一小撮混进党内来的和腐化变质的人,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革命,向走资派开战,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尽管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造就出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但作为这一运动的哲学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却未能展开为一个哲学体系。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型
共和国成立以来,艾思奇通过一系列努力,创就了自己的理论,这就是1961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基本停留在苏联哲学模式上的学院化的理论,从上面所举的毛泽东在艾思奇著作已经出版后的一系列讲话看,他并不满意这一理论,于是有196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庐山上鼓励李达重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一幕出现。然而,当毛泽东1965年读到李达《辩证唯物论大纲》时,感到还是与民国时期的《社会学大纲》一样,抄苏联教科书。这里,透露出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政治型哲学,但艾思奇和李达是用一种学院式方式去做,并将之看成学问来做,遵循的是一种学术逻辑,而毛泽东则完全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型哲学,将之紧密地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思考哲学,让哲学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学术上看,艾思奇和李达未能获得一种学术上的深厚资源来改变和推进苏联型的哲学体系,因此,呈现出来的只能是一个苏联型的哲学体系,毛泽东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在一些基点上,超越了苏联型哲学体系,也因为没有学术资源而不能展开为一套体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哲学的立足点和框架本身,使之既打不碎既有的体系,又无法展开为自己的体系。因此,中国现代哲学或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完成只是以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定型的标本了。
虽然,从本质上讲,共和国时期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民国时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从《社会学大纲》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语汇却在不断地走向标准化和统一化,特别经过共和国初期以来的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已经成了唯一的哲学话语形式。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共和国的哲学话语的标准形式。这样,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代表了天下一统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对中国思维的演进和中国哲学的演进,都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得天下一统地位,也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内容完全纳入其中,形成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宇宙的根本规律、整体上以苏联型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形态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哲学已经从传统型的和谐哲学完全转到现代型的斗争哲学。这一转变,从全球互动的角度看,是对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回应,在这一回应中既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武力扩张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巨大影响,又可以看到西方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思想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这一双重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在革命阶段显示了成功的一面,在建设阶段却暴露了其失败的一面。然而不管怎样,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性定型。这一定型不仅是思维方式的定型,更是哲学词汇的定型。
民国时期,哲学话语在不同的哲学家中是多样的,就是日常话语在不同的管理区也是不同的,冯友兰讲自己在北平刚解放时的经历,从中可以见出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日常语汇不同,以及因这一语汇不同而产生的误解:
……徐(特立)老说,话说明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合作了。这个我们一方面是我,一方面是党,并不是徐老个人。这个“合作”的意思是很广泛的,并不是只指徐老当时领导的那个单位的工作。徐老的意思,总的说起来,就是说过去的事只要说清楚了,共产党还是要你的。可是我当时没有了解这种意思。……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之后,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还有上边所说的清华刚解放,校务会议让愿留者签名登记。那个时候吴晗还在解放区,他回来以后,向会计科领工资,会计科一查登记表没有他的名字,就不发他的工资。吴晗在一个会上说,清华规定,凡是从解放区回来的都得登记。我不了解“登记”这个名词的新含义,大概新的含义是对于有问题的人才称为“登记”。这样一传开,就说是清华认为到解放区的人有问题,引起了文管会的查问。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校发不出工资,在教授会上有许多人质问,并要我向上面去催,我当时心里很生气,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吴征镒说,这是个思想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在1949年4月29日,清华举行校庆的时候,周总理派人找我,问我有什么意见。照我当时的了解,周总理所要问的“意见”,是对于国家大事有所“拾遗补阙”的那种意见,那时候的国家大事我看不出有什么“遗”“阙”,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该“拾”该“补”的地方,只好说没意见。后来才知道,所谓“意见”比我所了解的要广泛得多,大至对国家大事有什么看法,小至对个人工作、生活有什么希望和要求,都可以作为“意见”提。如果我当时有这样的了解,我就会向总理提出,请他把我调离清华,因为我觉得,我在清华处境很困难。我举这些例,是要说明,在当时我同共产党接触的时候,虽然说的都是一样的字眼,可是各有各的了解,往往答非所问。在解放之初,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情况,不过我当时在清华处于领导地位,表现得更加明显,更为突出。(16)
日常语言尚且如此,哲学术语上就更是这样了。民国时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是一套话语。但经过建国后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用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去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并且对于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去将之对号入座,特别是在批梁漱溟和胡适之后,所有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话语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有了一种对换,得到一种定位,并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去指认,这一哲学家是什么(比如是封建阶级的思想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一种观点是什么(比如是先验论的还是反映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这一命题是什么(比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一段话是什么(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是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一个一个的思想运动之后,一个一个的批判运动之后,整个哲学界都知道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都会运用这一话语方式去言说一切哲学问题,在冯友兰那里,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语汇消失了,在金岳霖那里,民国时期的西方哲学语汇消失了,在叙述中国哲人和西方哲人的思想而不得不呈现其原来的语汇时,这些语汇都与马克思主义语汇形成对应的指认关系,都变成了应该批判的语汇。正是这样的话语实践中,中国现代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汇上得到了统一。
注释:
①王炯华等著:《李达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②参加教材编写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肖前、李秀林,北京大学的高宝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贲思,中央党校的韩树英、王哲民、耿立、艾力农、马清健、李公天、方文、卢国英,胡绳和关锋参加了审稿工作。
③1959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两本书,从编写决定中说的苏联教科书未能包括中国经验,可知此书宗旨。书记处把任务让中央文教小组理论小组落实,按理论小组布置,哲学这一本第一阶段由北大、人大、党校、湖北、上海、吉林有关部门用三个月时间各新编一本。各单位于1960年2月编成。参见韩树英:《艾思奇与第一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理论视野》2008年第2期。
④《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⑤一说是1962年夏,杨献珍因病在西安住院时借阅了几部县志,其中有《蓝田县志》。
⑥参见庞朴注释方以智著:《东西均》,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⑦龚士其主编:《杨献珍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315页。
⑧杨献珍著:《合二为一》,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⑨杨献珍说:“我在这里,由于一种民族自尊心的支配,认为我们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反映了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老子的‘合有无之谓元’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法,也是一种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见《杨献珍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⑩《杨献珍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11)《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4)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5日。
(15)两报一刊编辑部:《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1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杨献珍论文; 艾思奇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对立统一规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矛盾论论文; 实践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哲学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