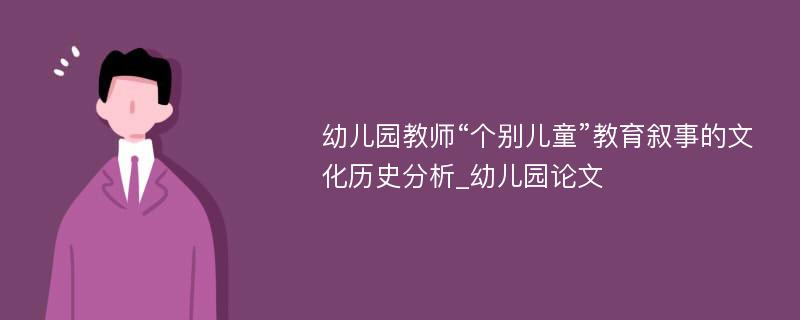
幼儿园教师关于“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的文化—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幼儿园教师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幼儿园教师讲述的故事或者写就的随笔中,总有个别儿童因为倔强、任性、执拗、顽劣,与集体或同伴冲突不断,而显得与整个班级和集体格格不入。其实,相较集体或同伴中的大多数,他(她)们本无特异处,不过是因为个性无拘束地表现出来,冒犯集体或者所谓师道尊严,不能见容于集体或者难以管教,而成为不能被轻易归入集体当中的个体。“个别儿童”是这类标签各异的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叙事中约定俗成的统称。实际上,他(她)们在不同历史—文化脉络当中有着各不相同的面相,是中国幼教工作者笔下的“刺头”“闹将”、苏联上个世纪30年代儿童学学者和50年代“实践家”眼中的“难教育”儿童,也是美国上个世纪40年代进步学校收容的“反叛者”。但不变的是,与“个别儿童”狭路相逢或者干脆被他(们)逼到墙角,纠结或挑战着许多教师的职业生涯,成为不同文化—历史语脉中的教师不因时代变迁而稍改的教育叙事主题。 “个别儿童”无疑是少数,与集体中的大多数相比处于发展或高或低的端点,是因为很长时间里习惯性地抓两头、带中间的教育方式,而从边缘跃升为教师关注的焦点。但在历史上,有关“个别儿童”的叙事,却是借助广播讲座、书刊出版物、经验交流推广现场会等样式,以时代强音形式记录和发布,因为强大的经验筛选、传播和留存功能,而使此类个案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围绕“个别儿童”的教育叙事由此不再是简单的个案,而折射着一个时代教师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涂抹着极其鲜明的文化—历史底色,使之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或历史碎片,而是文化交融和历史变革的分析单元。 本研究试图以文化—历史视角,从时代转折期的典型文本入手,分析幼儿园教育形式化、成人化的特殊年代和东西方文化与教育交汇的新时代,有关“个别儿童”的教育叙事相对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脉络和社会环境表现出的深层稳定结构,以及在应对异质文化挑战中传统难以断裂成文化异型的过程,从而把握“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类型、结构及其变化的内在机制,探寻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有关“个别儿童”的适中叙事类型 (一)适中叙事类型的集体意识 有关幼儿园“个别儿童”的教育叙事文本,较早可追溯至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因为遭受“左倾”思想影响,形势极度混乱,幼儿园教育实践处于跃进之中,批判《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试行)》之风波及全国,幼儿园教育几乎失去自身特点,出现了口号化、成人化和形式化的现象。[1]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0年为适应事业迅速发展需要,北京市幼儿教育研究室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学前教育通讯》在改成《教养员之友小报》之后,旋即改成以幼儿教育广播讲座的形式服务广大城乡。是年5月至6月间,北京幼儿教育广播讲座曾专门讲到怎样对待任性和执拗的“个别儿童”:[2] “我们小班有个叫韩敏的小朋友,家里就他这么一个孩子,父母娇惯,奶奶溺爱,事事说一不二,都得让他。孩子任性、执拗,在园里不能碰,也不能惹。有一次吃过午饭该睡了,我看见韩敏仍站在盥洗室,噘着嘴一动不动,于是我走过去说:‘韩敏,该睡了,快漱口。’说着拉起他的手走向放碗处,这可招来了不是,只见他膀子一拧,手脱离了我,回答:‘就不!就不!’我接着问他:‘怎么了韩敏?告诉老师。’不提醒还好,一提醒反而大哭起来,为了不打扰别人,我没硬要求他去睡,后来我把别的小朋友都安置好了,才走到他身旁很亲切地说:‘韩敏,来,你都哭累了,老师抱你睡去。’听说去睡,他哭得更厉害,索性坐在地下,两脚乱蹬着,嘴里一个劲地嚷着:‘就不!就不!’为了不让孩子执拗下去,我完全不提睡觉的事了,只是边给他擦着眼泪边说:‘那好,跟老师出来看看吧。’这样他才没有拒绝,跟我走到另一个屋子里,我抱起他,也不和他说话,只是轻轻地哼着歌曲,慢慢地他睡着了,我才把他放到寝室我的床上。到起床时,我去叫醒了韩敏,帮他穿鞋、叠被,又帮他梳好头发,才又问他:‘韩敏,刚才为什么不睡?还哭呀?’他又不高兴地告诉我:‘奶奶没给我洗好被,那条是妈妈的被,我不盖。’我说:‘噢!原来为这!妈妈昨天在家吗?’‘没。’于是我说:‘你看妈妈昨天没休息,奶奶又得给你做饭,太累了,才没给你洗,她们有时间一定会给你洗的,你看奶奶多疼你,怕你没被盖,才想了个好主意,给你先盖妈妈的大被!快别生气了!’接着我又给他提出了要求:‘以后有事告诉老师,不要生气了就发脾气和哭,这样把眼哭肿了,多不好受。现在去玩吧,今天放学时老师给妈妈写个条,请她有时间一定把你的被洗好。’他点了点头,跑出去了。” 显然,上述故事发生在一个极端特殊的年代。思想的动脉为时代束缚,但血液还是顽强地通过毛细血管四处渗透,留下了自己的痕迹。[3]故事里的教师在艰难时势下叙述的面对执拗和任性儿童时的实践智慧,不仅反映了当时幼教成人化背景下应对“个别儿童”问题的紧迫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上世纪50、60年代起陆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优秀教师在教育“个别儿童”时共同具备的一种集体意识。如当时的优秀教师琚贻桐在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会每每提及小刚。[4]这也是个所谓的“个别儿童”,任性、执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一到了户外,就很难把他叫回班,稍不如意就大发脾气,甚至打老师、咬老师,对小朋友就更甭提了。但他的特点是活动量很大,跑得很快,好像过剩的精力总没地方用,最爱玩“马缰绳”的游戏,套上“缰绳”当小马在前面奔跑。只是跟谁也玩不长,因为他跑得太快,又不顾别人,经常把后面的“赶车人”拖倒。琚老师看到没人和他一起玩,就走过去亲切地说:“小刚,你当我的小马好吗?”小刚最初愣住了,琚老师又说了一遍他才看着琚老师点点头。于是,琚老师当赶车人跟在他后面跑,一会儿怕他跑累了,吆喝一声“吁”,告诉他:“小马跑累了,快吃点草吧!”一会儿又“得儿驾”一声,让他撒着欢儿跑起来。为了培养他按要求控制自己的行为,琚老师还在游戏中编入了一些情节:“小马,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该干活了。这回马车要运热水瓶,想想要注意什么呀?”“热水瓶怕摔,得轻轻的。”小刚说完后,果然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装完车,琚老师又轻声喊:“得儿驾!”小刚则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动作,轻轻地慢跑着。差不多同一时期,特级教师康德瑛对于“闹将”——倔强任性、经常和小朋友发生冲突、爱咬人的孩子,同样也不会马上批评,而是通过仔细观察,发掘他精力充沛、热情、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的优点,慢慢引导他把精力用在健康的兴趣和爱好上。[5]特级教师王月媛老师班里的山山,在小朋友眼中是个“很坏”的孩子,经常把班里搞得“天翻地覆”,而王老师的看法是,“他的确淘气、好动,有破坏行为,需要调教,但有时他也蛮可爱的,他聪明,回答问题积极踊跃,且很准确,难道他就不需要尊重,不需要理解吗?”[6]淘气、爱惹事、经常发脾气、很少有小朋友主动和他游戏的孩子,特级教师李玉英老师也教过。李老师的做法是,一方面把教育工作做在问题发生之前,不给他重复不良行为的机会,一方面帮他建立长大了的意识,留心他的优点与进步,帮他树立威信,建立克服不良习惯的信心。[7]特级教师卢珊珊老师对待不合群、社交能力差的小朋友,同样也是注意寻找他身上的闪光点,提高他在小朋友中的威信。[8] (二)适中叙事类型的基本结构 在1960年5月至6月间北京市教育局幼儿教研室主持的北京幼儿教育广播讲座“怎样对待任性执拗的孩子”中,叙事者在分析孩子身体差或大人粗暴、溺爱、迁就、放纵等原因的基础上,归纳出对待任性执拗“个别儿童”应采取的教育步骤:[9]“当孩子执拗起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先不要注意他,也不要去劝他,尤其不能急躁地以强迫手段来压服他,而应等一会儿,当孩子发现没人理会他的时候,会很快安静下来,再对他讲道理,就容易被说服而接受教育了”,或者“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使之精神不再紧张,脑子比较平静,就容易接受教育了”;“有些孩子则不愿意服从直接对他提出的要求,而容易服从以一般形式对大家提出的要求”;“对固执的孩子可以有一个等待的时间,不一定要他马上执行”;“在教育固执的孩子时,必须善于对次要问题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采取让步的态度,但是在重要问题上如遵守集体规则、爱护年龄小的同伴等,一定要求他很好地完成,不能过于迁就原谅孩子。” 叙事者归纳的步骤,与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谈到过的一位中学教师改正“顽皮”学生的经验颇多相似处。据其爱人回忆,这位教师的经验同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0]调动积极性,“她真心喜爱每一个孩子,主动接近她们,鼓励他们的任何倾向;帮助解决具体困难,“进一步亲近,做到思想见面”;摸清每个孩子的思路,“找出思想障碍的所在及其产生的原因,分别加以处理”;在这个基础上,如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帮助他们解决,如由于思想不正确造成,则帮助他们分析、解剖、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在同学面前,只能个别谈话),纠正其错误;如有改正,随即当众表扬;如有条件,分配他们做一点班级工作,通过工作加以鼓励、锻炼、考验;由于这类儿童个性强,大都有能力,一旦扭转过来,会成为很好的学生。 从以上叙事与总结的教育步骤可以看出,那一时期我国的儿童教育工作者们共同自觉践行的其实是“外部条件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的教育原则,其叙事类型有着如下相对稳定的形式或结构: 首先是不对立。在冲突与对立面前,切忌以暴易暴,而应“冷处理”,转移孩子的注意力,等待他安静之后,再行教育。对上海优秀幼儿园教师先进经验的已有研究也发现,“优秀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时,教师自己的角色是经常变换的,有时是和幼儿平等的,有时是幼儿的指导者,有时又显得比幼儿小,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幼儿站在同一立场上是相当重要的,即教师不将自己与幼儿对立起来”。[11]当然不对立,并不意味着一味退让和妥协,如琚老师也曾明确对孩子表达自己的不喜欢;上海黄浦区南京东路幼儿园法勇青老师的经验也是“对于违反规则不改正的幼儿,该生气时还是要表示出来的”。[12] 其次是发现优点。譬如,琚老师从“内因”上着眼,找到了小刚的问题之所在——他太快,其他孩子们都配合不了,所以主动当小刚的玩伴,很好地调动起了他的积极性。而法勇青老师之所以能成功地转变能力较差的幼儿,同样也是因为她通过潜心研究,发现了孩子身上存在的“火花”。 再次是发挥集体的作用。有时候,孩子可能不愿意服从对其个人直接提出的要求,而愿意服从对大家提出的要求,因此在对幼儿进行常规培养时,教师不应把自己放在幼儿的对立面,成为一个常规的监督者、批评者,而应该设法使班上的每个孩子都成为常规的捍卫者。此外,有了进步,当众表扬,或者分配他做一点班级工作,也是充分发挥集体作用,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的好办法。 这样一类坚持外部条件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的立场,主张不对立,从发现优点、发挥集体作用入手解决问题的文本,构成了有关“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 二、“个别儿童”教育适中叙事类型的变型 有关“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及其形式或结构,在同质的文化—历史脉络中既会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又会在遭遇异质文化的挑战之后,以结构性断裂或改变作出回应,由此会出现有关“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的变型。 (一)不足叙事类型 有关幼儿园“个别儿童”的适中叙事类型并非空穴来风。叙事者在更详细的文本中谈到了个人认识的转变过程,“我们按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导,改变了过去教育行为问题较突出儿童的错误途径——只着眼于帮助孩子克服缺点”。[13]这一有关观念转变历程的叙述,提示了考察适中叙事类型来源的重要历史脉络,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叙事者面对“个别儿童”自觉采取“发现优点”立场之前,存在着一段“帮助孩子克服缺点”的观念前史。事实上,“帮助孩子克服缺点”的“个别儿童”回应立场实实在在地渗透在我们的教育传统之中。 如“特殊儿童”索安是叙事者在以往10年教育经历中很少遇到的极有个性的“个别儿童”:[14]一天下午,小朋友在看动画片。索安用双手向身边的小朋友做扑的动作,一下碰到一个小朋友的眼睛。那个小朋友哭着走向老师,还未开口,索安一下子冲到老师身边,大哭大叫起来:“我不对,我错了,我弄自己还不行?”说着,他夸张地用手打自己的眼睛。被碰的小朋友这才来得及告诉老师:“他碰我眼睛了。”话音刚落,索安顺手拿起一把夹子:“我扎瞎自己还不行吗?”索安的脾气上来是什么也不顾的,面对他准备伤害自己该怎么办呢?老师急中生智也拿起一把剪刀,握紧剪刀尖递给索安:“夹子没用,用剪刀吧。”他扔了夹子来拿剪子把,这时老师把夹子紧紧握在手里,当然剪刀也不会让他拿到了。危险解除了,索安哭了起来。等他哭了一会儿,老师才和他谈心:“你和小朋友开玩笑,不小心碰到别人,用不着这么大发脾气。你承认错误也不用这样伤害自己。”“我怕您说我。”“你发脾气我就不说你了?谁都会做错事,做错了要想办法弥补,而不是大嚷大叫。你这样的道歉别人会不会接受?你哭得比受害者还凶,就证明你没错了吗?”索安低头不吱声。“你想想,什么样的道歉会让人家原谅你。”索安看看我,走到那个小朋友身边说:“对不起,我以后会小心的。”“没关系。”小朋友又看电视去了,索安也平静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如果我没有用剪刀换他的夹子,而是去硬抢,说不准他还真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来。我没有被他的威胁吓倒,就是让他知道威胁不能解决问题,好好道歉倒是能得到他人的谅解。 从叙事的时间线索来看,上述有关“个别儿童”的教育叙事发生在陈老师、琚老师的适中叙事类型之后。但某种意义上,它们生动再现的却是她们的观念前史,揭示了“适中”叙事类型由来的文化原型。如杜威所言,师生之间的对立是割裂预期的未来和现在的可能,因为“没有激发和指导的力量,必须另外搭上一些东西,才能发挥作用”。[15]而所谓“没有激发和指导的力量”,其实针对的就是与适中叙事类型结构中的“发现优点”相对立的“帮助孩子克服缺点”;而所谓“必须另外搭上一些东西”,就是“以奖赏为诺言,以痛苦作威胁”,简单说,就是威逼利诱。如此一来,冲突与对抗在所难免。 避免冲突与对抗的关键,当然是适中叙事类型所揭示的“不对立”,让孩子清楚地感觉到教师和他是站在同一立场的,正如特级教师沈心燕所说,把孩子当孩子对待,而不是把孩子当作成人来对待。[16]而威逼利诱其实是把孩子当成人看,自己是成人,孩子也是成人,于是乎成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消失不见。这种视角绝不像字面上显示的那样,是高估了孩子;恰恰相反,它因为过高估计和看待成人自己的教育作用,而压低和轻视了孩子身上蕴育着的诸般能动性、发展性。把孩子当孩子看,并不单单是强调成人肩负着必要的养育或呵护职能,更是强调充分导引和发挥孩子身上可贵的能动性,让孩子真正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正是因为过高估计和看待成人自己的教育作用,压低和轻视孩子身上蕴育着的诸般能动性、发展性,由此构成了上述与适中叙事类型相对的不足叙事类型。 (二)过度叙事类型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前教育工作者们在面对“个别儿童”时除了自觉继承前辈从“发现优点”的基本立场出发的教育传统外,往前走得更远,出现了另一种源自个人主义观念的文化异型——过度叙事类型,其强调的立场和态度是“不理孩子”、教育需要等待,试看以下案例: 我们每年都会面临幼儿第一次入园这一问题,孩子哭闹的时候,作为教师,总有一种“我要为孩子做点什么的想法”,认为越热情越好。可菲菲非但不领情,反而只要我们接近,情绪就会变得很激烈。通过与家长交谈了解到,孩子从小由保姆带大,平时与他人接触很少,对陌生人比较排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讲,要尊重幼儿在发展水平、能力、生活经验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菲菲正是因为入园前生活经验与他人的不同,即非常缺乏和陌生人交往的经验,使她对于老师的“热情”行为的感受是不同于其他幼儿的。通过分析,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我们老师的过分关心、过度重视和保护造成了她的心理负担。《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应随时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敏感地观察孩子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据此,我们改变了方法。游戏时,我们不再去拉她共同游戏,当大家去玩大型玩具时,我们不再自以为是地借此时间主动出击,与之交流,而是采用“冷处理、远距离接触”的方法,给予她充分的理解与尊重,让菲菲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自己认识和了解周围的事、物、人,让她自己去慢慢消化和接受这些新的信息。(节选自2004年12月14日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试点园现场会发言) 借助以上叙事,教师还同时叙述了自己学习《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心路历程:“说实话,以往我们是不敢这么做的,尤其当有专家、园长来时,热情往往要加个‘更’字,‘不理孩子’那怎么行?现在有《纲要》做依据,以及园领导对实践工作的支持,大家没有了心理上的负担,更加愿意去挑战自我,对自己以往的教育行为进行反思。”从这段叙述中提到的“以往”,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面对菲菲这样的孩子,以往是从发现优点入手的;接下来的一句“不敢这么做”,更在漫不经心间道出了这种教育传统以及与此关联的个人习惯的强大影响作用。由此可见,“不理孩子”的确非同小可。对此,叙事者本人也有着清楚的认识:如果不是《纲要》撑腰、园长支持,“不理孩子”根本就难以想像。由此不难理解,叙事者为何经常脱离语境,反复对照《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注解。 导向性文件、政府规程等“集体叙述”,一向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据。有学者在考察影响中美两国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的因素时发现,中国教师优先选择的是政府规程(“因为这是导向性文件,我们必须遵守”)、儿童特征(“因为这是我们所有的教学计划的基点”)、教育与专业训练,而美国教师的选择依次为儿童特征、教育与专业训练、个人经验。[17]其实,作为导向性文件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是教师成功经验的集中体现,它是在汇集实践智慧积聚而成的良好传统基础上,指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只不过,我们的叙事者更习惯以集体叙述代替个人叙述,[18]而在根本上,它也是从“儿童需要”出发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和西方相隔着价值观念的铁幕,[19]同样是“儿童需要”,东西方解读大相径庭。 与以往传统和习惯中的“热情往往要加个‘更’字”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叙事者所谓“远距离、冷处理”“不理孩子”,已经是一种与前述“适中”叙事类型迥然不同的异型,其根源更贴近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传统。这种所谓个人主义一向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典型要素,其核心原则是个体是分离的,在本质上是非社会的,人们很自然地将自我假定为客体,认为它应该被整合为一体,反映他人的关注但并不以此为中心,因此儿童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逐渐认识到他(她)与他人是分离的,并且他(她)能自主、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同样是从“发现优点”的基本立场出发,这样一种叙事的异型构成了与适中类型相对的过度类型。 三、“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与其变型的对比 新时期叙事者所谓“这是导向性文件,我们必须遵守”,集中反映了个人经验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凸显了个体在改革中蜕变、取得专业成长的艰难。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调整自己、追随教育改革的步伐,通常带来的不是返求诸己,而是不得不舍弃自己的教育传统和个人习惯,走向未知的断裂与疏离。所以,对于叙事者而言,是舍弃教育传统和个人习惯,在犹豫不决中走向断裂与疏离,还是表面采用理论的话语体系、政策提示的行动方式,实际却呈现个人的兴趣与选择,始终是个两难的问题。[20]叙事者的心路一方面提示了文化本身有着稳定性与传承性,珍视个体归属手集体的传统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开放西方儿童中心主义思想和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带来的冲击,使教师从追求整齐划一到承认和尊重个体差异,这或许正是上述有关幼儿园“个别儿童”教育的不同叙事类型之间存在异同的根源之所在。 (一)借助集体和情境克服不一致 仔细考察有关“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的适中类型和不足类型,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共同的落脚点,那就是克服不一致。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幼儿教育广播讲座的讲述者,还是新时期教育叙事的写作者,在她们眼里,是家庭环境原因引发了孩子的性格缺陷,导致了所谓“个别儿童”。由此基本点出发,她们采取的教育措施虽然也注意与家长沟通,但总体上还是侧重教育之补正作用,以克服“个别儿童”的“难教育”“反叛”现象,将他们拉回到正常轨道。对叙事者来说,教育固然可以暂时等待,但最终还是要迎头赶上,其真正目的无一例外,是面向未来的。一旦个体对抗,她们的实践智慧是借助集体、情境的力量巧妙迂回,务求将“不一致”拉回正轨。 这种对克服“不一致”的执着追求,其实生动叙说的是叙事者服膺的自我依赖他人和周围社会情境的文化—历史传统。在中国、日本、韩国、南亚以及南美大部分和非洲文化传统中,自我不会也不能与他人和周围的社会情境分离,而是相互依赖的。[21]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西方个人主义极权传统国家是“把人从社会性纽带上割裂下来还原为‘个’,再基于‘个’的本质去重建社会”,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人”以有限的土地为生产手段,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且生产力有限,因此只能是农村社会中共同分享生存的“人群”。[22]因此,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人施行的“仁”或者所谓仁者爱人,一向潜隐着实用的目的—“大部分中国人的慈善行为的一个明显动机便是寻求一种利益、恩惠,那些沉湎于自己的善心冲动、慷慨施舍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自己可以从来世获得回报”。[23]这充分说明,我们习惯在人与人的联系、网络中考虑问题,包括“个别儿童”的教育问题。 (二)调适教育环境以适应儿童个体需要 对有关“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的过度类型来说,其基本出发点与适中类型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发挥集体作用”,不过与适中类型强调“发挥集体作用克服不一致”相对,这种叙事类型强调调适教育环境,以适应儿童个体需要,引导儿童个体发展,其文化根源可追溯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传统。在这种教育传统看来,“不一致”未必就要克服。 在教育“个别儿童”问题上,杜威认为没有普遍原则,只能个别对待,为此教师“要尽其所能地找出造成这些顽抗态度的原因”,[24]并“尽可能把发生的每一个冲突—冲突是必定要发生的—从以威力和暴力作为解决的手段的气氛和环境中取出来,放到讨论和智慧的气氛中去,就是把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的人,看作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人,并且达到把他们看作朋友的程度”。[25]正因为杜威把“个别儿童”“进步学校的反叛者”归因于教师的教育而非家庭,把儿童之间的不同、冲突视作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所以同样是“发挥集体作用”,杜威强调的是预先调适教育环境,以适应儿童个体的特殊需要,同时引导其发展。由此可见,杜威的教育主张实际是在接纳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谋求集体的整体改善,而非以集体之名克服个体的“不一致”。 有关“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类型的考察,对我们从文化—历史的视角客观审视和评价教师面对幼儿园“个别儿童”时的教育行为,寻求教师专业发展途径,具有重要启示。 (一)提升叙事的文化—历史意识 有关幼儿园“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及其变型的文化—历史分析表明,教师的教育叙事都是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文化的合金。在中苏、中美文化挑战与回应的文化—历史框架中,伴随改革与开放而来的文化交流或思潮碰撞,对于传统叙事形式及结构的冲击是强劲而直接的。在它面前,叙事者个人的认识和观念不得不以一次次深层次的断裂艰难回应,从“不足”朝向“适中”,从“适中”走向“过度”。然而,断裂式回应并不意味着传统和惯习的轻易消失,这既表现为“不足”和“适中”共同抱持着“克服不一致”的落脚点,也表现为“适中”和“过度”共同分享着“发现优点”和“发挥集体作用”的前提与结构。由此,以文化—历史视角审视,有关“个别儿童”教育的适中叙事类型与“不足”或“过度”类型相比,彼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而是共同围绕“个别儿童”教育这一有着鲜明儿童教育特点的叙事主题,构成我们讨论和审视我们自身的教育观和儿童观的完整框架,既看到文化传统的力量,又看到时代变迁带来的改变,从而帮助我们获得一份知己知彼、鉴往知来的专业自觉,而不至于偏执一端、一意孤行。 (二)承认个体样式的千差万别 帮助孩子克服缺点还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始终是关乎每位叙事者儿童观和教育观的重要抉择,也是避免师生发生尖锐对立和冲突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文化和传统有着强大的惯性,在不同历史情境中以柔韧姿态展现出自己的文化特性。尤其是近年来,有关幼儿园教师教育行为的已有研究显示,虽然“教师日益注重自身行为的教育价值与意义,减少了无意义的行为和活动”,但同时也暴露出“倾听幼儿少”“个别解决问题少”“情感表达少”“具体评价少”等问题。[26]这提醒我们,幼儿园小组活动、区域活动在展示孩子不同个性、满足其多元需求的同时,也有可能正以教育之名挤压和侵占了儿童个人发展空间。凡此种种伴随教师主体教育意识觉醒而暴露出的、教育教学实践本身对孩子自由、选择与差异的不适当倾轧现象都警醒我们,传统和习惯中的“不足”叙事类型不会因为历史—文化情境的变迁而轻易改变,叙事者和“个别儿童”的冲突在所难免。新时期叙事者的“不理孩子”与其前辈有着不小的差异,是从“发现优点”和“发挥集体作用”的“适中”历史传统出发,遭遇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冲击的结果,决定了它不可能不受传统与惯习的牵引,也就不可能完全倒向西方个人主义的怀抱,并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方向性的文化—历史课题:如何从中国的传统与历史出发,引进西方个人主义观念,使人人不仅成为自立的主体,而又不致于对既有的个体统合于集体的框架进行根本性改造。这必然要求我们承认并尊重儿童个体样式的千差万别。 (三)建构平衡的教育环境 到底应该以集体之名克服不一致,还是应该调适教育环境以适应不一致?上述有关“个别儿童”教育叙事类型的文化—历史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可能冲破非此即彼格局的思考框架,那就是从“发挥集体作用”、着眼于教育和情境出发,在“适中”和“过度”之间谋求新的平衡。其实,无论是“适中”叙事类型,还是“不足”与“过度”叙事类型,都始终未曾脱离集体,只是对集体抱持着根本不同的期许。这突出表现在,集体是通过关系和网络连接的相濡以沫的共同体呢,还是由彼此松散的个体组成的相忘江湖的联合体? 杜威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出发,强调不一致未必就要克服,并提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教育者义不容辞地要制定一种更明智的,因而也是更困难的计划。他必须精细地考虑他要对付的一些个人的特殊能力和需要,同时,必须安排为了取得经验而提供教材或内容的情境,以便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他们的各种能力。这种计划必须具有相当的可变性,容许经验的个性能够自由地得到表现,而且这种计划又必须具有相当的坚定性,使能力的继续发展得到明确的方向。”[27]这一路径其实已经兼顾到适中叙事类型中“发挥集体作用”的基本立场,是在肯定“真正的教育是在受学生(学习者)控制的因素与学生(学习者)无法控制(影响)的因素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环境”。[28]这也就是说,集体中既应该有孩子无法控制和掌握的方面,也应该有孩子能够控制和掌握的方面。由此,“理想的学习来自学习者能够识别出他在学习情境中必须适应的因素,以及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加以控制的其他因素”。[29]在面对无法掌握和支配的教育环境时,孩子的想入非非和自由散漫便顺理成章,所谓服从和反抗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教育立场在强调让儿童能够控制和掌握环境的方面更接近传统意义上西方个人主义的“过度”叙事类型,但其对集体中儿童无法控制和掌握方面的强调又更接近“适中”叙事类型,是一种试图协调不同叙事类型,以达到新的动态平衡的积极尝试。这一平衡立场游走在东西之间,也许可以为我们指示一条别开生面的叙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