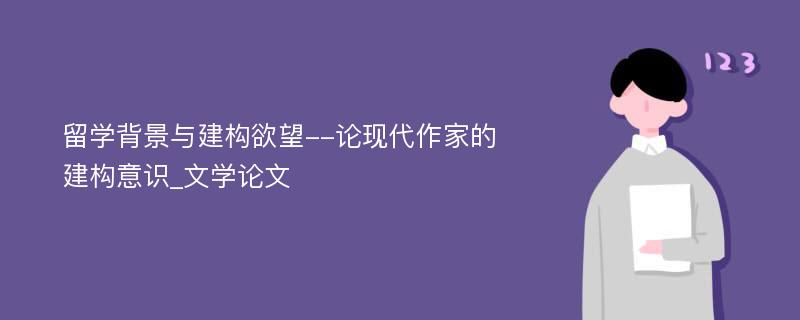
留学背景与建设渴望——试论现代作家的建设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意识论文,作家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111-05
1917年,在留学美国7年博士毕业,即将离开纽约返回祖国之前,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笔:
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1](P350)
这段话不仅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胡适归国前的心声,而且对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群体而言颇具象征性。它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告诉人们,作为一名就要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最大心愿或者说最强烈的渴望在于祖国的建设事业,然而通过种种渠道他们又往往预感到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其二,这段话清晰地使用了建设和破坏两个中心词汇,可谓提纲挈领,极有意味。纵观现代文学史,这两个普通的汉语词汇几乎维系和概括了胡适及其一代人的人生和事业,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所关注的大多是他们破坏、摧毁和激烈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我们以为,后者也许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因为从本质上说,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无疑是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建设的一代。
一、激烈的背后
提起“五四”前后具有留学背景的一代知识分子,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对腐朽、黑暗以及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封建文化传统毫不留情的摧枯拉朽般的强力破坏形象,“文学革命”初期形形色色反对派的攻击也首先集中在这一点上。抛开那些谩骂式语言的情绪化成分不论,这些反对者对新文学和新文学缔造者的总体感觉,应该说还是极为敏感和准确的。从鸦片战争以后每况愈下的国运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过去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秩序中,存在着极为严重地压抑生机和活力的有害成份。而不同程度的留学经历和国外生活,又使他们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和体味中深深认识到这种固有秩序的欠缺、荒谬和不合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动摇、改变、颠覆乃至彻底摧毁这“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秩序。从严复三番五次关于“牛体安能为马用乎”的种种疑问,中间经过辛亥革命曲折翻覆的惨痛教训,陈独秀得出明确的结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2](社会思想卷P38)他们决然地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面目出现的“调和迁就”,这一切标志着时代的思潮已经越过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中体西用”的坚固壁垒,而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开始了一个“西学批判中学”的“五四”时代。这是一个信心重建、价值重估的时代,是一个向一切“天经地义”的清规戒律挑战的时代,鲁迅在著名的《狂人日记》中借用狂人之口喊出了一句极具代表性的话,叫做:“从来如此,便对吗?”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化精英们从一开始就对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们以对传统的激烈批评,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意识。诚然,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甚或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并非不对传统特别是蕴涵于传统之中的积极因素有若干肯定,但是总体上说,他们处在“中/西”、“古/今”、“新/旧”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基本上是把传统视为一个应予否定的整体。用鲁迅的话说:“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3](P333)新文学的设计和创立,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和使命,它成为一代先驱者反抗全部旧秩序种种手段的实验地和突破口,深刻的怀疑,严峻的思考,悲愤的抗争,决然的破坏,综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内在的血脉和鲜明的特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同时,也应该看到蕴涵于这一特点之中的更为复杂的因素,看到“激烈”背后的复杂存在。其一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以为,应当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先驱者特殊的处境,考虑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口号,考虑到在中国改变传统的艰难。正如鲁迅等人多次强调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人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是不肯行的。我们以为,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之所以如此强调批判,强调破坏,与他们迫不及待地摆脱旧物,寻找出路,渴望迅速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开辟是目的,破坏只是手段,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要服从目的。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甚至不惜把话说绝,比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再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破坏与建设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要善于体察蕴涵于破坏之中的建设因素。为了更为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胡适曾将《新青年》同仁的文化言论概括为一句话,叫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概括无疑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彻底地颠覆和批判,其二则应是努力地吸收和建设,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促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而获得长足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五四”一代先驱者共同的追求和方向,对他们而言,破坏和建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辩证统一的两个部分:破坏和反传统“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建设则是引进、吸收和新生;建设需要对旧的基础进行彻底地清理,而破坏则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建设。哲学家贺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着意指出,这一运动表面上是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清除了儒家思想中僵化腐朽的东西,为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学术思想的有机结合开辟了道路。鲁迅曾尖锐地批判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他说这类破坏的“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他真诚地呼唤尼采式的先觉的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3](P192-194)我们以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自身就是这样一批在理想光辉照耀下的破坏者,在他们激烈的文化批判背后分明洋溢着强烈的建设意识。
二、旗帜和实践
这种建设意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口号和旗帜上。翻检历史,我们常常感叹于海外归来的一代学子对建设的钟情和执著。当他们陆续返回祖国,开始诸项文化事业的开创和谋划时,不仅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当时身为北大学生的傅斯年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他曾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指出:“今后但当从建设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以往,已成定论,不待烦言矣。”话中的意思与胡适的日记一脉相承。我们认为,在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胡、傅等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建设倾向、流变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值得高度重视。而且细读这些先驱者的言论,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主张都非常注意平衡破坏和建设的关系。作为“青春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文学先驱者们往往是真诚、直率,甚至是无所顾忌的,“要”什么“不要”什么,“打倒”什么“建立”什么,“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往往旗帜鲜明,清楚明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当中提出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在现实中无疑都是有所指的,但什么是与之相对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陈独秀却语焉不详,大概此时他自己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把它们当做理想中的文学模式提出来,作者的用意却是很明显的,他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止是要推倒旧的文学,也就是说不止是要破坏,推倒旧文学目的在于建设新文学。1919年,当人们对《新青年》的办刊倾向提出种种质疑和猛烈抨击时,陈独秀又特意撰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这是一篇解释的说理的文字,其耐心和恳切在陈独秀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著称的文章中是少见的。他用反复的言词告诉人们,之所以破坏,之所以激烈,是因为要拥护民主与科学,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将中国从黑暗中救出。之所以要大力破坏黑暗腐朽的旧社会,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新社会。为了突出自己的“建设意识”,陈独秀还一再强调“创造的精神”,他们相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完全可以在传统的废墟上创造出一种健康向上、充满希望的新型文明。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以往的历史尽管时间漫长,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以下两种时代的交替: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我们“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3](P213)
谈到这种建设意识,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胡适,在新文学阵营中,他与陈独秀等人在许多观点上有所不同,相比而言,他更注重理性的创造,注重一点一滴的积累,注重不断渐进的过程。因此,在破坏与建设之间,他对后者似乎更是情有独钟。他自己说过,当初写作《文学改良刍议》时,他特意把自己早已明确当作口号提出的“文学革命”改成“改良”,而且颇为谨慎地添上了更加温和的“刍议”两字,把题目取得“很谦虚”,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激烈和刺激,“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P53)而当陈独秀把口号中的“改良”二字又改为“革命”,并以慷慨激昂的《文学革命论》大文与之呼应时,他又连忙作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文学革命”前面特意加上“建设”两字,足见其意之所在和用心良苦。一些研究者曾从不同的侧面论证过,胡适一生中极为浓郁的形式感、秩序感和建设意识,与他留学时的母校康乃尔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所学校独具特色的校园环境、办学理念以及对学院知识分子责任的要求和定位无疑深深地影响着胡适,他首倡白话文运动便是要为中国文学造一新形式,建一新秩序。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大声呼吁:“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并且明确指出:“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部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他将新思潮的意义定位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句话。胡适在他的言论中多次把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并一再强调“复兴”二字,直到晚年依然念念不忘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念念不忘新的文明的产生。这种浓郁的建设意识贯穿着胡适的一生,在许多时刻许多方面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甚至成为他生命和生活的基调,成为其文化与精神变革的心理基础。与他同时代的朱自清先生较早地也较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胡适论文>指导大概》中曾着意指出胡适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明确肯定“这是建设的工作”。
这种建设意识其次表现在艰苦细致的建设实践上。以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青年》为例。《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2年7月休刊,共出版了9卷54号。它比较充分地展现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等一代具有特殊知识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曾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中产生极大的震动,被誉为“青年界之明星”。一位青年曾这样致信杂志:“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并说:“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悟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5](P6)由此可见这份杂志当时的影响力。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求益书社重印这本杂志时,胡适曾为之题词,高度赞扬“《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提起这本著名的杂志,人们的印象中往往就是“摧枯拉朽”以及“彻底批判”、“无情否定”等等,近来我们读到一些新意盎然的评论文章依然这样为之定位。经过仔细的文本阅读和认真思考,我们认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定论是值得商榷的,最起码是不全面的。翻开这部尘封已久的著名杂志,除了强有力的思想冲击力外,我们常常为它的“广、博、杂、细”所感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规划大全”或“建设丛书”。反复阅读那些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的重要文章,有两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它涉及的领域之广阔,举凡中西文化、中西哲学、政治、科学、宗教、鬼神、社会、时事、青年、妇女、劳工、教育、时尚、人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童话、文学改良、语言文字等,都包含在《新青年》的讨论范围之中。而且凡是那个时代能够想到的问题,这本杂志几乎都要轻重不同地有所体现;凡是人们提出的疑问,《新青年》诸君则要竭尽全力给出答案。其二,是这本杂志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强烈的建设意识。事无巨细,荜路蓝缕,披荆斩棘,从一点一滴做起。单就语言文字领域而言,先看看这些文章的题目吧:《西文译音私议》(陈独秀)、《论注音字母》(钱玄同)、《汉字索引字说明》(林玉堂)、《关于华文横式及古典小说的讨论》(钱玄同 独秀)、《句读符号》(钱玄同)、《注音字母》(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 独秀)、《国语文法的研究法》(胡适)、《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钱玄同),还有许多许多。从标点符号到注音字母,从西文译音到汉字索引,从海外归来的这些人从方方面面为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进行着扎扎实实的奠基工作,其认真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关于华文横式及古典小说的讨论》的通信中,钱玄同这样对陈独秀说:“我以前所说的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随后他的一席话则令人感慨:“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使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这又是宜于横式的。况且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2](语言文学卷P430)读着这些深思熟虑和细致入微的文字,我们仿佛触摸到一颗对民族文化、对祖国建设赤诚和滚烫的心。钱玄同古道热肠,好为高论,他的同学鲁迅曾批评过他:“十分话最多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6](P66)陈独秀也曾为其“废除汉文”的主张解释,说他是“愤极了才发出这样激切的议论”。但无论如何钱玄同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应当高度评价的,他“一方面在研究上精益求精,一方面总求适用于教育,不遗弃普及工作;一方面嘉惠士林,一方面唤起民众”,[6](P58)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他于建设事业的独特思考和探索,而上面给陈独秀信中的这番话,则较为集中和典型地反映出具有留学背景的一代作家极为浓郁的建设意识、建设渴望、建设视野和建设的信心。
三、更深层次上
分析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的建设意识及其建设成就,在更深层次上,还应特别注意这些作家在知识结构上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对严格的现代科学基础训练和相对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
研究现代作家的留学经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受当时“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具有留学背景的一代作家在学校里学的大多是理、工、农、医等属于“实学”的专业,真正学习文学、戏剧、艺术的并不多。像鲁迅、郭沫若、陶晶孙学的都是医学,丁西林学的是物理与数学,成仿吾学的是兵器制造,胡适最初学的是农科,夏衍学的是电机科,夏丐尊、朱湘学的是工科,张资平学的是地质,洪深学的是陶瓷工程,汪敬熙、郑伯奇、白薇学的心理学,再加上一部分人学的是边缘性、综合性学科(像徐志摩、陈西滢、郁达夫等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其中也有相当多的理工知识。因此,总的来说,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接触理工农医乃至天文等知识的就相当多。这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优长,当后来他们纷纷转向文学研究和创作时,他们知识结构中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较为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比较稳固的科学世界观,便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接受理性启蒙精神、严格技术训练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现代性与宽广性,不仅使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建设意识,而且使他们的建设实践形成某种极为可贵的科学化、规范化的追求和趋向,形成某种对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认同。这一点胡适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博士论文的“导言”中就指出:“哲学是受方法论制约的……哲学的发展取决于逻辑方法的发展”,对科学方法的重视贯穿胡适的一生,进而影响了周围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顾颉刚在一个胡适思想批判的座谈会上发言:“我和胡适都生长在累代书香的人家,阶级成分是相同的。我和他都是从小读旧书,喜欢搞考据,学问兴趣又是相同的。他从外国带了新方法回来,我却没有,所以一时间钦佩的五体投地。”[7](P114)尽管在那种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气氛下,顾颉刚依然如此强调胡适对他的震动,由此可见胡适引进的新方法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文学创作和研究是人类社会一种特定的知识创造活动,它的健康成长和蓬勃发展,有赖于不断地创新,不断地科学规范,更深层次上,也有赖于创造群体科学修养、科学精神和科学情怀的不断提升和壮大。而在这个创新、规范和提升的过程中,具有留学背景,特别是具有自然科学基础的现代作家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科学熏陶,使他们拥有较强的探索精神和发展期待,使他们往往对现存的事物不满足,对改革、创新、批判和超越具有强烈的渴望和追求;而较为严格的科学训练,则赋予他们较多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理念,使他们严谨务实,注重实效,对浮躁、轻率、盲从迷信等等,具有相当的警惕和抵制。许寿裳在探讨鲁迅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时,特别强调“科学修养”这一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其影响颇大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鲁迅》中他一再指出:“鲁迅当初学矿,后来学医,对于说明科学,如地质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细菌学,自然是根底很厚。不但此也,他对于规范科学也研究极深,他在医学校里不是伦理学的成绩得了最优等吗?这一点,我觉得大可注意的。”他认为:“惟其如此,他对于一切事物,客观方面既能说明事实之所以然,主观方面又能判断其价值之所在,以之运用于创作,每有双管齐下之妙。”并说:“鲁迅有了这种修养,所以无论在谈话上或写作上,他都不肯形容过火,也不肯捏造新奇,处处以事实做根据,而又加以价值的判断,并不仅仅以文艺技巧见长而已。”[8](P60-61)作为鲁迅一生的好友,许寿裳这番话不仅道出了造就鲁迅的诸多因素中“大可注意”的一面,更为重要的,它阐明了科学修养对于作家而言的价值、意义和潜在的功用。这一点在众多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身上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郭沫若甚至把科学当作锻炼自我意志力和训练理性思维能力的独特方式:“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9](P226)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的价值在郭沫若的心目中已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深化和升华,它不仅依然发挥着事实判断之作用,而且也兼具了价值判断的正向意义。此外,这种知识背景还直接影响到这些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并渗透到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理性化特点。
综上所述,浓郁的建设意识和建设渴望,是具有留学背景现代作家的一致的追求,共同的特点,也是他们取得卓越成就的力量源泉。有意识并不意味着一定有行动,但行动却一定需要意识的先导,强烈的建设意识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独具特色的作家群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和构建,无论在基础性建设、规范性建设还是在引进性建设等方面,他们都奋发积极地走在了前面,并且最终成为各种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而这些建设加在一起则铸就了现代文学30年令人瞩目的辉煌。
收稿日期:2002-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