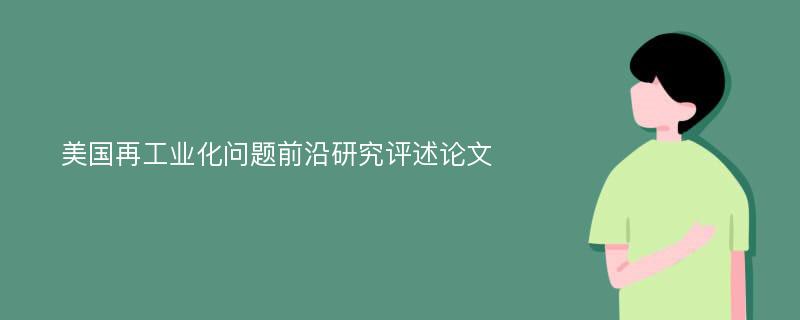
·经济学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美国再工业化问题前沿研究评述
王 展 祥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摘 要: 较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再工业化大讨论,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更大规模且更为持久的再工业化浪潮,再工业化政策从奥巴马政府的呼吁号召、政策制定与经济层面逐步向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形式体现的强化过激与政治层面升级。普遍把美国再工业化归为主要由贸易和生产率等因素导致的多年去工业化及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非正常锐减,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美国再工业化的理论依据、潜在优势、产业回归顺序及地区分布,以及再工业化对其国内及中国的长短期经济影响上。中国决策层和理论界需要认识到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风险,加快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突破,早日跻身技术与创新型发达国家行列。
关键词: 再工业化;去工业化;制造业;经济结构;美国
再工业化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吸引了美国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注意力,一方面,理论界不断强调美国再工业化的重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美国两届政府先后提出《制造业促进法案》以及《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与此同时,以“苹果”等为代表的美国公司在减税政策激励下,纷纷将海外收入带回美国并宣布增加在美投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福耀玻璃”“富士康”等也纷纷到美国投资设厂。美国这波再工业化浪潮来势汹涌,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再工业化呼声日盛,这对正处在产业升级上升通道、由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机会与挑战兼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一、美国两次再工业化浪潮及其背景
再工业化不是一个新问题,美国历史上有两次关于再工业化问题的大讨论。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重建后的欧洲以及日本工业的相继崛起而导致对美国出口的增加,美国许多制造业部门如钢铁、彩电、汽车等的世界主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决策部门和理论界呼吁美国进行再工业化以恢复制造业、繁荣美国经济基础(Bluestone和Harrison,1982)[1]。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多年持续去工业化并没有影响美国整体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少部分制造业受到影响(Kutscher和Personic,1986)[2]。美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和弹性对此做出反应,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又主导了一批世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如微处理器、航天航空、计算机网络设备、制药、软件等,重建了更强的竞争力和生产力,美国制造业投资、产出和就业也迅速增加。去工业化的阴霾以及再工业化的呼声悄然消失。
殆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历经两届政府,美国从总统到学者乃至民众再次掀起一股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讨论热潮。舆论普遍认为,多年持续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成千上万企业倒闭,甚至引起关于制造业危机的频繁预警。以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美国制造业产出份额与1947年相当(Lawrence和Edwards,2013) 。Snyder(2010)更是图文并茂罗列出具有一定震撼效果的美国去工业化的19个事实,如美国自2001年以来有4.24万个工厂关闭,其中75%是雇佣500人以上规模的工厂,2000年10月以来美国制造业总共损失了550万个就业岗位;平均而言,中国每购买1美元美国产品,美国对应购买3.9美元中国产品;美国有43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51年来贫困人数最多的记录等。Snyder甚至还指出美国去工业化是一场国家危机。
与上一次再工业化大讨论相比,此次再工业化浪潮的最大特点是美国决策部门迅速对此作出应对,如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提出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此后美国许多世界500强公司如福特等开始响应政府号召,纷纷把海外制造工厂或办公室回迁到美国以增加就业。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主要是停留在呼吁号召、政策制定与实施等经济层面,侧重美国再工业化以增加制造业就业机会,有其经济上的合理解释。后来随着美国再工业化呼声的日益高涨,美国理论界开始把再工业化问题讨论向纵深推进,把美国再工业化问题研究从必要性向合理性和可行性方向进行延伸;特朗普政府甚至把美国的再工业化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政治层面,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这实际上是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从呼吁号召与经济层面逐步向强化过激与政治层面升级。
美国理论界与媒介一方面强调美国2000年以来的巨大损失(Snyder,2010),另一方面又在强调中国加入WTO后的巨大收益(BCG,2011)[3],如2001—2009年,中国出口近乎增长了5倍,占全球出口份额从3.9%提高到9.7%,在鲜明对比中把美国持续多年去工业化而导致的经济问题不断上升到国家危机乃至政治层面,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从过去的必要性不断向合理与可行层面推进,把制造业就业机会从开始的吸引回迁至美国向制造业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向转变。这是此次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的背景及其根本目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当其它变量不变时,产品零售价格敏感系数k增大,产品销售量下降,由此带来总利润的下滑;同时,产品销量的下降导致物流服务规模下降,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为保证一定的总利润,只能降低物流服务成本,从而使得物流服务水平降低;除此之外,当产品零售价格敏感系数k增大时,为保证一定的产品零售量,产品零售价格会随之降低。
二、美国再工业化的贸易与生产率之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此次再工业化大讨论的直接导火线。再工业化讨论的核心也主要围绕金融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问题展开,进而追溯到美国去工业化问题。有关美国制造业讨论的焦点在于其制造业的大量工作岗位损失是否是因为贸易或自动化,对去工业化基本原因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美国此次再工业化的缘起与本质。
贸易导致以失业和衰退体现的去工业化。Atkinson等(2012)认为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的因素67%要归于贸易。Scott和Kimball(2014)认为中美商品贸易赤字增加导致美国在2001—2013年失去了320万就业机会,其中240万(3/4)为制造业岗位;计算机和电子产业岗位损失最多,约为125万,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岗位损失最少,约为3.5万;而制造业工作损失遍布美国每一个州。Scott(2017)在后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认为,2001—2015年美国制造业工作损失了340万,其中大约有3/4(260万)归因于美国与中国同期贸易赤字的增加。Autor等(2013)以8个高收入国家对中国进口的变化为工具变量,分析认为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解释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90—2000年下降原因的33%,2000—2007年的解释比例为55%,1990—2007年的解释比例为44%;美国用于购买中国产品的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从1991年的0.6%提高到2007年的4.6%[4]。Autor等进一步分析指出,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降低了美国非制造业部门工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导致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最后增加了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转移支付。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中美贸易对美国的分配效应及效率损失,可能也是导致美国公众对全球化以及与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赤字感到矛盾纠结的原因。Cooke等(2015)研究发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贸易进口对美国低学历工人影响更大,1992—2007年间美国具有大学教育的制造业工人基本没有受到来自中国出口的冲击影响。
可见,对美国以制造业就业份额持续下降体现的去工业化的原因的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时间上,从单独分析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的急剧下降到对比分析中国加入WTO前十年与加入WTO后十年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再到分析1960—2010年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变化;原因分析上,从国际贸易与自动化及相伴随的制造业生产率因素等不断向消费模式升级与产品需求及消费支出比重、投资、教育、创新等因素转变,不断从单因素归纳走向多因素综合,由侧重宏观的解释逐步向偏重微观分析过渡;工作岗位损失上,从制造业总就业损失向分产业、分地区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进行扩展研究;从短期剧烈波动因素向长期趋势变化因素分析转变。对美国去工业化原因的不同理解是对美国再工业化认识的基础。
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对美国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短期来看,再工业化政策有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和强劲发展,并增加就业。美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2016)报告高度肯定了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政策,该报告分析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几乎是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是50年来制造业超过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最长的时期,美国制造业比过去具有更强大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直接激励了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将海外收入带回美国,贡献税收并创造就业岗位。Wakabayashi等(2018)分析认为,苹果、通用电气等海外收入留存较多的公司将在新税法施行后纷纷回流到美国,潜在回流规模高达1.1万亿美元,其中苹果公司已经宣布将海外收入带回美国直接贡献380亿美元税收,并将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基金提高到50亿美元,在未来五年新增2万个就业岗位,遍布50个州超过9000多名美国供应商将直接受益。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1)估计,到2020年,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额的10%~30%将很可能转回国内生产,其每年能给美国带来的GDP在20亿美元到550亿美元。普遍认为再工业化短期有利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增加与经济增长。
自动化能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在产出不变乃至增加的情况下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这也与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就业下降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相一致。1960—2015年,美国制造业实际产出增加了5倍,而制造业工人反而减少了300万,无疑生产率提高是就业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Rose,2018)。沿着生产率思路,Baily和Bosworth(2014)分析认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尤其是对于计算机产业来说[8]。Kehoe等 (2018)认为,1992—2012年美国只有15.1%的制造业就业下降可归因于贸易赤字,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才是制造业部门就业下降最主要的驱动因素。Tregenna(2011)把制造业就业水平值分为部门增加值变化以及部门劳动密集度变化两个部分,分别考察制造业就业份额变化的劳动密集度效应、部门份额效应以及总劳动生产率效应,发现制造业劳动密集的减少是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同价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自动化;越是在高收入国家,以实际值增加表示的制造业增长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紧密联系在一起[9]。这个观察强调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促进制造业增长的重要性,更为制造业在吸收劳动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一个挑战。Hermes(2013)也认为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改进对制造业工作减少的影响,超过了因经济萧条导致制造业产出下降进而对制造业工作减少影响的3倍,因此伴随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去工业化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是痛苦的,但对经济长期增长则是必须的。Nager(2017)则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工作减少而生产率更高这一传统观点的不足,原因在于美国官方有关制造业的统计数据被异常值扭曲了。如制造业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在2000—2010年实现了350%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考虑这一因素,其他18个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期只增长了46%;而且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巨大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摩尔定律导致的质量调整的结果,是一个错觉,至少它不能反映美国能生产更多的计算机;把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排除在外,其他18个产业在2000—2015年就业下降了27.3%,实际增加值只增长了6.4%(同期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增长230%)[10]。总而言之,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以制造业就业减少所度量的去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此外,Atkinson等(2012)把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归因于制造业产出下降,并分析认为,2010年制造业19个部门中有13个部门(占制造业工人的55%)的实际产出低于其2000年水平;更进一步,Atkinson等把产出下降归因于美国全球市场竞争能力的显著下降,而这又源于国外过度的重商主义保护政策以及降低企业税等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当然本质上还是把美国去工业化归因于贸易,但其产出视角颇为新颖。
由表1可以看出不同浓度吲哚丁酸(IBA)对金叶风箱果扦插生根影响效果较明显。在同等栽培管理条件下,不同浓度的IBA对金叶风箱果插条的生根率、生根数效果明显不同,均优于对照组,处理A2生根率为最高,达到92%;平均发根数上,依次为处理A2,处理A3,处理A4,处理A1和对照为最少。处理A4在根系长度上影响最大。
Campbell(2016)研究发现,美国实际汇率变化使得其相对单位劳动成本在升值,在更加开放经济条件下,这导致其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产出、投资和生产力不成比例地下降,大致可以解释21世纪早期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2/3[12]。Atkinson(2016)报告强调了美国过去三十年来公共投资(包括科学研发、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与私人投资(包括资本设备、劳动力培训和研发)的持续下降与不足是导致美国生产率进而去工业化的主要因素。Bonvillian(2016)提出教育及创新能力系统的弱化在美国去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毕业率开始停滞乃至呈下降趋势,而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技术与技能在持续增加,进而导致教育曲线落后于技术曲线;同时美国长期建立在研发、设计与生产基础上的创新能力随生产过程的转移而被割裂开,削弱了其在创新领域的比较优势。
除贸易以及与自动化相伴随的生产率因素外,还有综合考虑贸易、生产率以及产品需求、汇率等因素来分析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原因。Lawrence和Edwards(2013)研究认为,就像快速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农产品有限需求相结合导致农业就业份额下降一样,美国1960—2010年制造业就业份额持续而稳定下降主要源于制造业相对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制造产品价格的下降以及对收入增长和低价格制造产品需求的缺乏弹性;减少贸易赤字能促进制造业一次性就业增加,但不能改变制造业就业份额长期下降趋势。Christopherson等(2014)则把以美国为代表的OECD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去工业化原因概括为更低生产成本竞争者的出现,导致大量的进口渗透;跨国公司离岸外包以及制造业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向更低生产成本地区的重新配置;技术进步减少了单位产出的劳动力需求;投资和创新的不足;消费者偏好服务等[11]。Hicks和Devarai(2015)提到了美国国内对其制造业产品消费需求不足也是其制造业工作减少的原因之一。
与贸易导致就业减少与衰退观点相反,Krugman和Lawrence(2008)则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部门规模几乎没有净的影响[5]。Hicks和Devarai(2015)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主要是源于自动化,而不是国际竞争与贸易;在2010年生产率与2000年持平的假设条件下,期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损失只有13%可归因于贸易(进口或进口替代),大致为75万工作机会,87%的制造业工作减少源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Acemoglu等(2016)运用四位数代码的制造业数据以及投入产出表分析指出,1999—2011年来自中国进口的直接效应占到同期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10%,约为56万;考虑到投入产出关联等其他渠道导致的间接效应,制造业工作减少98.5万[6]。这两篇文献基本认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与衰退发挥作用,但不是主要因素。世界银行前总裁、美国贸易代表及副国务卿Zoellick(2016)则更多从产值而非就业角度提出美国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而不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输家。他认为,美国进口产品有超过60%是用于在美国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在过去五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在制造业上实现了23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2003—2013年的出口增加了130%,美国种植作物的1/3用于出口;进口产品的低关税帮助美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节约了1万美元。在Zoellick看来,如果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是不健康的,则美国制造业从来就不健康,不能责怪贸易,贸易本身没有损害美国制造业。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6)更是认为贸易鼓励美国经济资源更加有效的配置,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而促进工人实际收入的增加;贸易降低了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提高了产品多样性选择,让美国消费者和公司受益[7]。Rose(2018)则把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分为总效应和净效应,前者指进口导致的就业替代,后者指贸易对总就业的影响;在分行业研究的基础上,Rose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净效应只占到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中的很小一部分,不同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与其对应各部门的贸易赤字之间呈弱相关关系,贸易不是美国去工业化的原因。
STEM教育同中国传统学科教育的区别 中国传统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强调以教师为主体,以课堂为中心,课堂由教师绝对主导,单方面的知识灌输成为课堂的主流,课堂交互性较低;在教学内容上,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灌输,忽略学生能力的培养,造成大学教育同基础教育的断层,同时课堂内容强度大,记忆知识点成为多数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在评价方式上,考核方式单一,近年来国内部分发达地区虽然将综合素质列入考核因素之中,但规模较小,改革仍停留在表面。学生在此种教育模式下缺乏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条件,主体性以及创造性的培养被忽视,无法快速适应社会生活,缺乏独立思考问题的思维,欠缺合作沟通的能力。
三、美国再工业化的潜在优势与产业回归优先顺序
针对美国再工业化以恢复其制造业是否具有理论依据和现实可操作性等问题,有许多研究对此展开分析,集中在再工业化的潜在优势与可能劣势以及再工业化回流到美国的产业顺序及地区分布等。
从实践角度看,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和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从理论角度看,不同学者对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着力点及主要方向或目标有不同认识;从国际角度看,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对美国经济及他国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是理论界的关注焦点。前者主要是美国政府相应出台的再工业化政策,这里主要对后两者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析。
如果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时,仅仅将国学经典生硬地引入进来,就很难让学生做到充分的理解,同时也会让课堂变得非常枯燥,所以,教师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开展课堂教学。从心理学上讲,小学生因为年龄较小,他们往往对声音、色彩、形象有非常高的兴趣,特别是那些动态的事物,很容易让学生的注意力得到集中。
从现实角度看,美国发展制造业进行再工业化的现实可能与优势何在?对此,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由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1)[3]提出。BCG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将导致许多针对北美消费者的制造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从而支持美国的再工业化:(1)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与美国低劳动力成本的州相比,其成本差距在急剧缩小;(2)对许多制造业产品而言,当考虑交通、关税、供应链风险、土地价格等综合成本,与美国低成本州相比,在中国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将日趋最小化;(3)中国的自动化以及其他旨在提高生产率的措施并不能保持其成本优势,外包到中国的吸引力正在减小;(4)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在中国投放产能以适应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也把部分制造业生产配置到美国以适应北美市场;(5)一些制造业产品将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生产,但这些国家也存在很多风险,如基础设施、熟练工人、市场规模、国内供应链网络的缺乏和不足,以及政治风险、知识产权风险、低劳动生产率、腐败、个人安全风险等,并不能完全吸纳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产能。Shih(2013)认为,美国再工业化是由许多要素组合导致的必然的经济结果,包括基于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贸易的再平衡、中国和美国之间劳动力成本差距不断缩小 、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的更低能源成本、消费者需求的返回、有利的美国政策干预等;不利之处在于离岸供给价值链的组合或美国制造业供给价值链的不完备部分限制了回迁到美国的制造业数量;并预测中国仍然将是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伙伴,中国仍将尤其是对欧洲来说具有吸引力,但中国将明显不会成为美国离岸生产的首选地。Hermes(2013)把美国再工业化的优势概括为三点:(1)与中国迅速递增的劳动力成本相比,尤其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尤其是南方各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日益体现;(2)页岩气革命将导致的低能源成本以及税收激励;(3)企业对海外供应链的过度扩张导致的脆弱性或完全依靠国外供应链的危险性的认识在不断增强,这将使得美国制造更有吸引力。其中,不断下降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再工业化的主要决定因素。Zhao等(2014)认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建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基础上,具有四个无法比拟的优势,即分销网络广泛而合理、信息渠道畅通、贸易方便以及友好的市场环境。[15]德勤与竞争力理事会(Deloitte and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2016)则把美国再工业化的优势概括为其全球制造业竞争力上,并认为尽管2016美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第二,位于中国之后,但是到2020年美国将取代中国居于第一位。[16]这无疑鼓舞了美国制造业的回流与振兴。
措施二:对基坑周边进行限载,限制基坑两侧重型运输车辆通行;加强现场施工组织管理,合理组织施工节拍,形成流水作业,在具备基坑封底条件下,及时完成底板施作,负二层侧墙、中板、负一层侧墙、顶板施工紧密衔接。
美国再工业化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回流到美国的制造业工作有多少,哪些行业将会优先回流到美国或者美国再工业化的重点产业及其优先顺序是什么?从广义角度看,有研究指出美国再工业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而是建立在广泛服务经济基础上的再工业化(Zhou,2013);再工业化的方向是振兴制造业,尤其是能创造更高报酬工作的制造业,并要警惕低工资、低技术工作的回流以降低美国生产率,导致美国产业转向低附加值产业(McNamara,2013;Zoellick,2016)。Nager(2017)认为,配之以适当的政策,如对可交易部门产业的企业制定更低更有效率的税率、对工业或竞争前研发以及合作研发的支持等,至少能有一到两百万制造业工作回流到美国。从具体产业角度看,Shih(2013)提出,美国制造业复兴将是有选择性的,主要集中在如技术密集型产品或那些企业仍具有很强私人生产能力的产业;或者能源及化石原料是成本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如塑料制品及石油化工产品;发电机设备及燃气轮机设备或者那些仍具相当国内市场规模的产业;很难看到大规模电子产品制造业在供应链组成部分不在美国的情况下会回迁到美国。Hermes(2013)认为美国再工业化需要有选择性支持的产业包括农业、建筑/采矿、机械(包括油气领域机械、发动机、涡轮机及动力转换设备)、医疗设备、石油及半导体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还包括在北美具有巨大市场优势的汽车零部件产业。Hermes从19个部门的分析中预测,能积极回迁到美国的制造业部门具体可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计算机及电子产品、机械、家具及其他制造业产品四个部门,代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56% ;第二梯队包括金属制品、电子设备与器械、塑料和橡胶、非金属矿产品四个部门,回迁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值每年在2820亿美元,且回迁的地区可能主要集中在南方各州,如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北卡罗莱纳、新墨西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2011)也强调未来几年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总成本略高10%~15%的美国部分州,如南卡罗莱纳、阿拉巴马和田纳西州,将会吸引制造业回迁,率先进行产业承接,尤其是许多针对北美地区市场的制造业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就产业而言,劳动力占总成本份额较小的产业如汽车零部件、建筑设备以及家用电器会率先回流,劳动所占成本相对较高且生产数量较大的制造业产品似乎仍会在中国生产,劳动密集型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如服装、鞋子将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更低成本的国家[3]。
也有部分研究指出美国再工业化的潜在可能劣势。如Bonvillian(2016)认为,以大学毕业率度量的教育曲线在一百多年以来一直领先于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技术曲线,这是美国在“二战”后稳居世界创新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基础;但过去几十年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生产过程被大量转移到国外,相应美国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及其创新能力、进而美国创新系统被削弱了,生产创新与研发、设计等创新之间形成了重大差距,这是美国再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之一。Nager和Atkinson(2015)以及Nager(2017)提出五点可能的不利因素:(1)船运成本较低。2008年衰退导致国际船运需求的减少以及繁荣期新造船只的交付导致船运成本在不断下降,2015年世界船运成本更是创新低,这导致产品出口到美国的相对成本更低。(2)强势美元,或者说石油增产导致美元升值的影响比更低能源价格导致的边际储蓄效应更大。(3)页岩气革命导致的能源成本节约又因世界范围内更低能源成本的出现而被抵消。(4)中国正在迈向更高附加值产业,如半导体等,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5)中国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与美国南方各州工资差距在缩小,但中国地区之间工资差距很大,平均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仍只相当于美国的12%,中国传统产业可以在内部跨省转移,也可以向越南、印度、柬埔寨等进行转移,不一定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缩小就回流到美国。其中第四点为很多学者认同(Navarro,2018;Taplin,2018)[17]。
四、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目标与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的理论依据与潜在优势。广为引用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麻省理工学院(MIT,2013)所提出[13]。该报告在调查255家大公司(其中包括美国178家、中国36家公司)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仅保持高附加值如设计环节在美国,不断将低价值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低工资国家如中国,不断把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环节分离开,这将导致美国连提高效率和设计的机会都失去了,并可能使那些一直把生产外包到海外的高科技公司停止前进;在此基础上,MIT研究人员认为制造业应该被视为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发展的产业群,它是新思想、新技能和新产品的源泉,不能被视为衰落的产业,更不能把它与知识经济和服务业对立起来;其结论是要努力维持和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此外,Pisano和Shih(2012)从研发、设计和生产相互依存角度,强调生产活动对于制造业进而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14]。McNamara(2013)研究发现,在2008年至2009年8月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但其中绝大部分岗位来自低工资行业(主要是低端服务业);对消费支出约占GDP2/3的美国而言,缺乏良好薪酬的工作显然不利于经济持续强劲复苏,其根本的解决之道从历史的角度看还在于制造业。此外,Hermes(2013)直接提出制造业是美国的心脏,是美国再工业化的基石,是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关键部门。Bonvillian(2016)则从沙漏和价值链角度来理解制造业,把制造业承载的生产过程视为美国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也具有更高乘数效应,去工业化进程中随制造业的转移美国在创新能力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明显被削弱,因此美国有必要把创新系统和生产系统再度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个制造业生态系统。与Bonvillian视角类似,Meckstroth(2016)从上下游价值链角度研究认为,美国制造业产品价值链与作为其他工业部门供给链的制造业一起占到美国GDP和就业的1/3;生产最终需求产品的制造业领域一个同等工作(afull-time equivalent job),能在非制造业部门创造3.4个全职同等工作;创造100万美元增加值,制造业需要5.8个全职同等工作,而交通运输和服务业则需要7.7个、零售业需要16.9个全职同等工作,其结论是制造业价值链远大于想象。这些研究都强调了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支持重振美国制造业,鼓励创造高技能和高收入制造业工作,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再工业化政策的根本目的主要集中在改变贸易平衡、创造制造业工作机会、提振美国创新能力等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学界和媒介多集中在复兴美国制造业以创造工作机会(Snyder,2010;BCG,2011;Lawrence和Edwards,2013),乃至调整既有产业设施和发展新产业(Wu,2012),《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就设定2012—2016年新增制造业就业目标为100万(实际完成1/3)。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贸易平衡问题引起更多关注。如Shih(2013)认为无论如何,美国制造业不可能恢复到外包热潮之前的行业构成中,美国要进行再工业化更大的目标或效应在于改变贸易平衡,再工业化背景下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是一个劳动力更富弹性、生产率增长、要素成本改进、需求选择性返回的综合性蓝图。Bonvillian(2016)则强调了美国再工业化以加强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性。Bonvillian认为美国制造业能力与创新系统能力直接关联在一起,在创新与生产的关系上美国先后呈现美国生产/美国创新、美国创新/他国生产、他国生产/他国创新的演进趋势,去工业化可能导致美国创新能力也转移到海外,因此再工业化过程中生产环节的回归对于恢复和巩固美国创新系统和创新能力势在必行。
Q 之前纠结于适马的35mm和50mm两支定焦镜头,而最近适马又推出了40mm镜头,请问老师这支新镜头有什么优势吗?
中长期看,美国不仅仅是将再工业化政策项目集中在与制造业有关的广泛工业部门上,更重要的是美国更多创新导向的全国和地区政策(包括联邦、州和地方各个层面)都在鼓励R&D和自主创新能力,这将把美国再工业化引向基于创新和技术进步道路上,必定对美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制造业生产带来重要积极影响(Wu,2012)。McNamara(2013)也提出,适当的再工业化政策以及政府、行业和大学的共同努力将为美国提供具有更高报酬的制造业工作,在长期看可以恢复美国制造业。Lawrence和Edwards(2013)认为,尽管再工业化在短期能减少制造业贸易赤字,促进制造业就业短暂繁荣,但它不会永久性改变美国制造业长期就业份额下降的趋势。因此为技能不足的美国工人增加就业机会的关键是基础广泛的经济复苏,而非专注于制造业的再工业化政策。Kurtzman(2014)把美国制造业与能源油气、创新与包容风险的美国文化以及大量现存可投资资本并列作为美国经济继续再主导世界100年的四大动力之一,无疑是较为乐观的,其着重强调的是制造业对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Nager(2017)[10]认为,鼓励制造业工作回流促进美国再工业化,在短期来看可能会导致更高的价格,长期看或将带来更低的相对价格,因为美元收入将随最终实现贸易顺差而增加;从消费者福利角度,因回流而导致的更高工资将至少会部分抵消价格的上涨。如果美国能制定更加有效反制国外不当政策(出口补贴或汇率操纵的重商主义),同时快速提高其生产率增长以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美国制造业产出每年能增加6300亿美元,贸易赤字也会拉平,在全美能创造130万个工作岗位,因为美国还没有发展到英国去工业化的程度,依然具有强大的制造业生产力量。
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产业升级及经济潜在影响包括正面、负面与中性三种观点。 中性观点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2011)[3]为代表。BCG认为,与取代中国相反,美国的再工业化不会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广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基础设施,以及促进系列制造业部门持续进步的熟练技术工人队伍,大多数跨国公司还要配置更多生产能力以服务于收入不断增加的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将持续成为西欧主要的低成本出口商,2010年长三角地区经过工资成本调整后的生产率仅相当于西欧的25%,2015年也仅相当于西欧的38%,远不到拐点。但中国和美国之间成本结构的转变将提供更多制造业及外包选择,如主要针对亚洲市场的具有高劳动力含量的产品,在中国生产仍然具有意义。当考虑新建制造业生产能力以满足中国以外的市场时,则需要作出更多战略性决定,尤其是针对北美市场的产品。
负面观点普遍认为,现阶段中国整体创新能力还不足,如中国制造业技术中的核心技术超过50%来自于进口或转移,在此背景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转向创新基础上的先进制造业可能对中国及其他制造业竞争者产生冲击,尤其是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中高质量制造业产品,中国工业生产面临更高技术产品供不应求以及国际上高质量低价格产品对国内市场挤压的多重挑战等(Wu,2012;Zhao,2014)。Hermes(2013)认为美国制造业能力回迁将对目前在中国生产而目标市场为美国的中国制造业部门产生负面影响。Taplin(2018)则隐约指出伴随美国再工业化及其对敏感技术的趋严控制,中国新技术的获得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和廉价,中国的创新与研发成本将会更高[17]。
从以上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实验班成绩的方差虽然有缩小趋势,但是仍然高于对照班成绩的方差。这说明实验班的数学成绩较为分散,低分段学生人数较多,教师应当给予他们高度关注。教师要关注低分段学生的学习,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引导他们确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让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教师要善于发现低分段学生数学学习的闪光点,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为他们主导课堂创造更多的机会,帮助他们逐渐树立学习的信心,养成浓厚的数学学习兴趣。
正面观点多侧重于美国再工业化系列政策及美国制造与日益增加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可能倒逼中国加快先进制造业和关键产业的自主创新与突破式发展,尤其是中兴公司事件之后。如Jin(2018)认为特朗普政策将促使中国加速推进国内改革,长期来看中国将会是赢家。
五、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再工业化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吸引了美国从总统到理论媒介乃至一般大众普遍持续的关注,表面上看,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持续多年的去工业化,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中国从传统低端制造业向现代先进中高端制造业转型发展及中美比较优势的转变。多数学者的分析客观而理性,从贸易、生产率、产品需求、汇率、研发投资、教育等多方面,分短期与长期、不同制造业产业、不同地区对美国再工业化背后去工业化的缘由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再工业化的理论依据、现实与潜在优势及不足、再工业化基本目标、产业回归顺序,以及美国再工业化对国内经济及他国经济的影响进行正面与负面、短期与中长期的分析。值得指出的是,学界对美国再工业化相关议题的研究普遍比较细致而具体,比如产业回归顺序及规模测算、旨在服务再工业化战略的贸易战对美国各具体产业在就业数量与产值等方面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前景及政策等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预评估。
透过美国再工业化问题研究,理论界需要认识到美国再工业化不完全是定位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的再工业化,因此,有必要研究美国再工业化各具体有关政策对中国相关制造业产业、地区的就业与产值的影响,分析在部分制造业回迁到美国、部分制造业外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国家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兴制造业的协调发展问题。决策层需要充分意识到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经济的风险,灵活运用当前美国与欧盟、日本等国错综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关系,为中国赢取最大的国际贸易空间。舆论上对中国与美国客观存在的现实差距要正确加以引导,避免过激言论。企业界尤其是研发创新部门,要加强基础技术研究与最新前沿应用技术开发,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到来、因物理极限导致发达国家技术“堵车”之机,加快中国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以早日跻身技术与创新型发达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 Bluestone B.,B. Harrison,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2.
[2] Kutscher R.E., V. A. Personic,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hift to Services”, Monthly Labor Review , Vol.109,No.6,1982,pp.3-13.
[3]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 “Made in America, 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S.”, The BCG Report , August, 2011.
[4] Autor D.H. et al,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103,No.6,2013,pp.2121-2168.
[5] Krugman P.R., R. Z. Lawrence, “Trade, Jobs and Wages”, Scientific American , October 13, 2008.
[6] Acemoglu D. et al.,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 Vol.34,No.S1,2016,pp.S141-S198.
[7]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How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September, 2016.
[8] BailyM. N., B. P. Bosworth, “US Manufacturing: Understanding its Past and its Potential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 Vol.28,No.1,2014,pp.3-26.
[9] Tregenna 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UNU -WIDER ,Working Paper No. 2011/57.
[10] Nager A.B., “Trade vs. Productivity: What Caused U.S. Manufacturing’s Decline and how to Revive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oundation Report , February,2017.
[11] Christopherson S. et al., “Reindustrialising Regions: Rebuilding the Manufacturing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 Vol.7,No.3,2014,pp.351-358.
[12] Campbell D.L., “Relative prices, Hysteresis,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CEFIR /NES Working Paper series , No 212,2016.
[13] MIT Taskforce on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A Preview of the MI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ve Economy Report”, Production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 (PIE )Commission , February 22, 2013.
[14] Pisano G. P., W.C. Shih, “Does America Really need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the March Issue, 2012.
[15] Zhou Mi,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S re-industrial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476, 2013.
[16] Deloitte and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2016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Index”, Deloitte and the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 May,2016.
[17] Taplin N., “Chinese Innovation Won’t Come Easily without U.S. tec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18-05-15(B12).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11-0097-09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互联网+’背景下江西制造业质量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19JL01)
作者简介: 王展祥,1979年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美国阿卡迪亚大学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房宏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