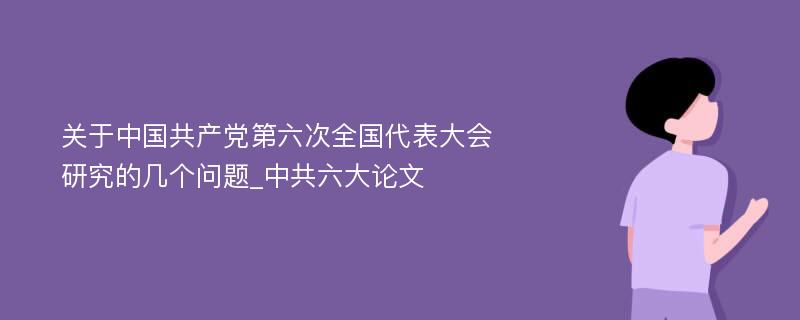
关于中共六大研究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4-0037-08
192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大,至今已经80周年了。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学术界都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论述中共六大的著作、文章,其中也不乏佳作。《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对中共六大的部分档案文献资料亦曾有所披露。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六大的档案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没有公布,对六大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之际,笔者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在现有条件之下,对六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一点探讨,并希望通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使对六大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一、中共六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召开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中共六大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呢?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六大召开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全国的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比以前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时的情况都严重。全国人民“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①。当时有人写文章称:“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② 鲁迅先生更揭露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③。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党的一切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仅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2.1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2.6万名共产党员。如果在国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
第二,在国内没有找到能够保证安全开会的会址。召开中共六大,是由党的八七会议提议、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但这两次会议,均未决定开会的地点。在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说:“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④。此后于1928年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做了报告,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但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开会讨论后,首次提议并决定:报告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批准中共六大能够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并希望斯大林或布哈林等领导人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市郊的五一村(即中共六大召开地址)的工厂旧日志中,也有记载说: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不可能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帮助他们在苏联召开代表大会”⑤。在同年的2月10日至15日间,瞿秋白、向忠发也分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或写信,反映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严重”情况。这使共产国际执委会认识到及时召开中共六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遂于3月份专门讨论与决定了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并复电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事宜。还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前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第三,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六大之前,共产国际是用派共产国际代表的形式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这些被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既执行了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执行了其错误的思想;而且,他们对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贯彻得好。也就是说,这些共产国际代表虽然在中国做了一些工作,但都犯了错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派往中国工作的代表也并不十分满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充分发挥指导与顾问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共力量聚集起来,使之在莫斯科稍得休整,恢复一下元气。中国共产党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直接指导。
事实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确实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及时的、直接的指导。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是中共六大主席团的成员,他们始终关注着大会的进行。周恩来曾回忆说:“‘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⑥ 布哈林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他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予以直接指导。时任共产国际远东部副部长的米夫,也是在大会上做实际工作的,并参与了大会的全过程。
第四,有利于会后直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几个会议。在筹备中共六大的过程中,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将要在当年的春天和夏天于莫斯科分别举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农民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在会后直接派代表团就近参加上述国际会议。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正如此。六大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7月20日在布哈林别墅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定苏兆征、项英、周恩来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之主席团的成员;邓中夏、余茂怀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驻农民国际代表,等等。当时他们都分别参加了各自相应的国际代表大会。
第五,可增加同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代表之间接触和交流经验的机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中共领导人、全体与会代表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之间提供了相互接触、增加了解和直接交流经验的机会。斯大林在大会之前,会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六大路线的确定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程。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召开的前夕,还召集了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布哈林亲临中共六大予以指导,并做大会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以及中国少共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等先后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许多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应邀莅临大会。例如:苏联、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捷克斯拉夫(即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波斯(即伊朗)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或代表,都在中共六大上致词或发言,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赞扬和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并通报了各国的斗争情况,交流了经验。这是此前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盛况,它使与会代表能够同各国兄弟党的代表直接接触和交往。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一种学习和交流,更是一种鼓舞和促进。
第六,可以利用留苏学生做会务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会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正在苏联学习的一部分留学生,被指定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组成了强有力的秘书处班子,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大会秘书处的秘书长,黄平、罗章龙任副秘书长。秘书处直接负责大会的会务工作。为了全面做好会务工作,在秘书处之下专门设立了四个科,即文书科、记录科、翻译科、庶务科。其负责人分别是:龚饮冰、瞿景白、陈绍禹(王明)、胡秉琼。这些负责人及各科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来自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等校工作或学习的学生(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中共六大能够在莫斯科召开,这也是当时一个有利的条件。这些参加中共六大会务工作的人,诸如:陈绍禹、龚饮冰、瞿景白、沈泽民、孟庆树、胡秉琼、蔡树藩、胡锡奎、李培芝、曾钟圣、涂作潮、王培五等等,既是留学生(其中有的是已毕业而留校工作),又是被“指定及旁听”的大会代表(均有大会的编号),而且也有发言权。大会上的许多报告和讨论发言,都是由他们做记录。共产国际代表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各国兄弟党的致词,都是由他们做翻译。大会的许多文件资料,也都是由他们整理和抄写。现在翻开中央档案,就可以充分说明以上情况。他们为这次大会的会务工作,付出了辛劳,作出了贡献。
二、关于中共六大召开的具体地点
大家都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但对其具体的开会地点并不很清楚。在过去的一些史书、文章中,对此也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最流行的说法,认为六大是在“莫斯科市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的。这个说法,来源于盛岳的半回忆半研究性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⑦。盛岳,原名盛忠亮,中国革命的叛徒,并进入国民党“中统”当了特务,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该书是他在六大召开40年后在海外写的。实际上,他单凭回忆而写的中共六大具体会址的名称,是记忆有误、不准确的。
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郊外纳罗法明斯克城五一村”召开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的注释注明: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该书中还收有“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在该记录中,特别标明:于“1928年6月27日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⑧ 对于中共六大会址,这是在档案里首次明确记载。这种档案记载,应当是准确可靠的。
这里所说的五一村,距离莫斯科市区大约有40公里。五一村属于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南部。六大代表在这里开会,距离莫斯科繁华市区较远,代表们在会议期间不随便外出、不去游览市容。同时,代表们也不用真实姓名,都用代号。因此,在这里开会,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是绝对有保障的。
在五一村与中共六大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共有三处:第一处,六大主会场,原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庄园的主楼,即五一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旧庄园主楼。它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非常美丽,被称为“银色别墅”。这是一座三层的楼房,共有七八十个房间(包括会议厅、办公室、居住室、活动室、厨房等),六大代表们在这里开会、吃住和活动。第二处,在该主楼北边的后面、近在咫尺(只隔一条不很宽的马路)的二层小楼,这也是一座小型别墅。在六大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刘伯承等领导人,就住在这里。斯大林、布哈林等有时也来这里,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会面。这里曾是苏联内务部克格勃保密区的一个办公地点,其保密性和安全性都很好。六大时领导人有些小型会议,也在这里举行。第三处,在距主会场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原来很豪华的二层楼房——布哈林别墅。1928年7月20日,第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其他常委会委员也在这里进行了分工。到目前为止,在这三座旧址建筑中,布哈林别墅毁坏得最为严重。
关于中共六大会址,苏共中央宣传部曾有对其开发利用的动议。在苏联解体前夕,他们的一位副部长,曾被派来中国与中联部联系关于苏、中联合整修、开发“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的事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联部有关人员共同商议了此事,认为做这件事很有意义,但还需要再进一步了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中方到底有哪些要求,他们考虑的具体计划或意见是什么等,决定待苏方意见返回后,再继续商谈。但是,苏方尚未来得及回复,即事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苏联就解体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代表团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时,笔者参观、考察了上述中共六大开会和活动的所有旧址。这三处特殊珍贵的建筑,损坏极为严重,已经摇摇欲坠、破败不堪,楼房周围杂草丛生,完全没有了昔日恢宏、豪华的风采,亟待拯救性的护理和整修。这种严重的状况,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三、关于中共六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
从1927年到1930年间,由于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有很大变化。在这期间全国党员人数,根据中央档案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共五大时为57967人,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减少到1万多人,六大时的统计为130194人,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时为69300多人,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时为122300余人。以上的党员人数,除了六大的统计数字以外,都是比较准确的。
关于六大时全国的党员人数到底有多少,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史书、教材、文章中,对六大时的党员人数有多种说法,诸如:“四万说”、“三万说”、“二万说”和“十三万说”。“四万说”,是指认为六大时全党人数有40000余人。但这种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传统说法,始终没有文献根据,是一些专家所作的一种估计。“三万说”,是一种推算出来的说法。因为六大时党员的成分,76%是农民,10%是工人。当时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7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大后向共产国际的报告说:全党工人成分最高数量不过4000人。据此认为:在中共六大时,工人党员与农民出身党员的比例,大体为1∶7。按照工人党员最多为4000人的话,则农民出身的党员应为4000×7即28000万人。两者相加,为32000万人。“二万说”,来源于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该书中写道:“到1928年夏天六大时,党员人数大幅度下降到二万或顶多二万五千人了。”⑨ 显然,以上这些说法,都不是当时直接的统计数字,而是一种估计、推算或回忆出来的数字。至于“十三万说”,具体来说就是:六大时全国党员为130194人。这是根据当时档案资料的一种说法。这个党员数字见于以下三个文献资料:(1)1928年6月3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2)同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3)六大档案资料:1928年6月《全国党员数量统计》。根据这份统计资料,到六大开会时,全国共有17个省委(包括临委),40个特委,391个县委,38个市委,56个区委,165个特支;把各省分别统计的党员人数加起来,总计为130194人。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130194这一数字,在当时条件下的统计是不够准确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这时全国党员“总数有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农民居多数,但海陆丰、醴陵一定要有很大损失。所以,总数是不能正确的”,而是个“很夸大的数量”。在六大《组织问题报告大纲》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夸大的数量”。后来,周恩来进一步说明:“中国党乡村支部的统计非常困难,所以数目很难正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员数字产生了有增、有减的迅速变化,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一方面是各地在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中,党的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党员的人数也就有增加;另一方面,当时毕竟处于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像广东海陆丰、湖南醴陵等地方的斗争遭到失败与挫折那样,致使党员的数量也会有许多减少。第二,在统计党员人数时,有的地方存在“宁多毋少”的思想。有的代表在六大上讨论组织问题的发言时,批评了这种现象,指出:“恩来同志报告现有全国党员共十三万人,表示可疑样子,当然这个统计不大精确。一般普遍心理,党员少无面子的样子。以前说,数量增加,可以改善质量。现在这句话是不正确的了。我们计算党员,以支部为标准,在支部的同志,才是确切的党员数量。”第三,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群组织混淆不清现象有直接的关系。有的地方甚至把凡是积极参加暴动的赤卫队员、农会会员等非党群众,也统计为“党员人数”了。中共中央批评了这种现象。因此,在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要求各地党组织要坚持党员标准,不要把党群混淆,“党不要企图把所有的倾向于革命的农民都加入了党”。但这种现象直到六届二中全会时,仍然存在。周恩来在六届二中会上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批评说:“在农村中党与群众组织混合在一起了。”他举例说:“平江原来(有党员)七万人,现在巡视员回来的报告只有一万人,原来的数目包括群众组织”。由此可见,这种把党群组织混淆不清的情况,影响了党员人数统计数字的正确性。
总起来看,“四万说”和“三万说”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都是估计或推断出来的,不是直接的统计数字,而且也没有直接的文字根据。“十三万说”,它的来源则是唯一有档案资料根据的。但这个数字最大的问题,如前所述,主要是把党群混淆,统计不精确。因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既没有直接引用“十三万说”,也没有采用上述的“四万说”或“三万说”。该书在写到中共六大全党人数的时候,采用写实的办法,只在小注中注明:“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⑩。但是,“十三万说”毕竟是当时全国各省逐个、直接统计起来的总和数字,总比没有文字根据而全凭估计或推论出来的数字更有参考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另外发现新的文字根据之前,在讲到六大党员人数时应当写上这个数字,同时又要指出它是不够精确的。到底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还应当继续进行探讨。
四、中共六大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认识
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他们怀疑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至1930年期间,包括斯大林、布哈林等在内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问题,不但不重视而且有非常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1928年中共六大时,斯大林并没有“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11)。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比斯大林更悲观。他在中共六大上做政治报告的结论时说:“我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总(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一个同志说,在乡里做工生活好些,因为乡中有鸡吃。那么,他们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农民在开始的时候,自然对待他们是很好的,看他们这样奋斗,杀了好多土豪劣绅,但是他们今天将我的最后的一个老母鸡吃了。第二天则这样喊的人要多些了,第三天则这样喊的人更多些了。最后便会有人说:‘见了鬼!什么红军!还要我的米、我的鸡给他吃。’或者说:‘红军是好的,但是难得维持他,他也不与城市发生关系,他又没有银行,又没有商品。’你们想想,到这时候便该知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以为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虽然红军在开始是因为农民而反对了劣绅土豪的。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开始表现过了。因此我们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三部分,四部分,看当地的条件怎样。分聚到各地方,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区域中,还是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当着他住在这一区域的时候,他可以变成农民的自卫军,来保护农民,来尽一个人民自卫军的作用,以后再继续前进,去进攻另一地方的地主、土豪、劣绅,于是在那里又可以吃一吃鸡而到别处去。这样也可以变成组织的连系,时去时来,都带着一定的任务。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12) 在这里,笔者不惜篇幅,引述布哈林这段冗长而生涩的话,是为了如实地具体地说明他当时的最基本的思想观点。这可以说是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悲观思想的真实写照。
六大虽然也一般性地总结了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并提出了任务,但对于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地位,缺乏必要的应有的正确认识。显然,这是受到了共产国际负面影响的结果。直到1930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特殊的重要性的认识才逐步有所转变。
五、中共六大为什么选举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由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普遍存在着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错误倾向,致使当过工人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拔重用。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思想,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中共六大的“主席团名单”中,特别注明:向忠发的出身是“工人”,其资格是“湖北代表、中央委员”(13)。向忠发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够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这里简要介绍向忠发“出身”和“资格”的一些基本情况。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早在1894年他就开始进入湖北汉阳兵工厂,做了两年的学徒工。接着,他先后在造币厂当工人,在江汉轮船上当马头工和水手,在汉冶萍公司的轮船上做差事。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湖北总工会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等职。由于向忠发当过工人,参加和领导过工人运动,并在武汉地区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八七会议,但却经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提名,而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中旬,向忠发同李振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并担任该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他到莫斯科后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1928年2月,他和李振瀛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他与李振瀛还参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会后在赤色职工国际还工作了一段时间。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向忠发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主要领导人同共产国际与联共(布)领导人的“会见”和“政治谈话会”。这实际上都是为召开六大做预备的。中共六大是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向忠发参加了大会,并被大会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是大会的主要主持人之一。在大会期间,向忠发是职工运动委员会、湖北问题委员会的召集人和政治、军事、组织、妇女、苏维埃运动、财政审查、湖南问题、广州暴动等各委员会的成员。他还向大会做了职工运动和讨论结论的报告。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14) 由于向忠发的上述经历和和当时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他在7月10日的大会上,继五大之后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7月19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从此,向忠发就成了党中央的主席,但人们仍习惯地把他称为“总书记”(这是陈独秀时代的称谓)。直到1931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和被枪杀之前,他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他只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的“领导干部工人化”的一个最高标本。周恩来曾指出:中共六大时“太强调工人成分”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15)。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始终参与大会并贯彻国际的意见。米夫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并利用他放炮,攻击别人。同时,向忠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讲话口才比较好,而且有时也比较幽默。例如,他在六大上讨论发言时首先就说:“现在‘大工贼’要讲话了”,博得大家哄堂大笑。向忠发在这里自己戏谑的“大工贼”,实际上是早在武汉时期别人送给他的一个“绰号”。上个世纪70年代,陈独秀的秘书黄玠然先生在接受笔者访问谈陈独秀的情况时,也提到了向忠发。黄先生回忆说:“在武汉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工人同志,都知道有个向忠发,其表现很活跃,是工人组织中的一个头头,有人送他个外号叫‘大工贼’。”向忠发的一些表现,确实也曾迷惑了不少人。当时,在党内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他们都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了惨痛失败或严重挫折,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由工人干部领导才行。
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国际提出的和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这种“唯成分论”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向忠发的上台。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描述:“向忠发之所以爬上宝座,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出身。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把一艘正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船,交给一个未出过海而只是划过长江小船的人去掌舵,实在是极大的风险。正是这一决定,使得李立三能够从向忠发的领导无能中掌握实权,从而推行他那灾难深重的立三路线。”(16) 在这里也形象地说明了向忠发上台的原因及其负面影响。
六、对中共六大历史地位的评价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对六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共六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作了概括与结论,它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历史决议对六大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呢?这是因为:第一,六大正确地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前途。第二,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按照大会的规定,党在当前的总路线,不是马上组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第三,六大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第四,六大对党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作了重要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阶级基础,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第五,六大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反对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由此可见,六大提出和解决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大会确定的党的路线的基本方面都是对的。
召开党的六大,是非常必要的。六大解决上述问题,具有特殊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党所面临的全局性的,也是党迫切需要及时解决的大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朱毛红军上井冈山,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大方向。但是,如果只有八七会议和井冈山的斗争,没有六大的召开,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是很难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六大可谓居功至伟。它的历史功绩,正如李立三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说:“六次大会开(始)了新的阶段,给予我们以新的生命,是党历史上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整个问题都有正确的回答。”(17) 毛泽东在后来亦指出,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得“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18)。
中共六大的历史功绩巨大,但其不足也明显。对于六大的缺点,党的历史决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著作中,都有深刻论述。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六大对于中国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中间阶级的政策,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缺乏清醒的分析和明确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对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等,都缺乏必要的正确认识,依然是强调了“城市中心论”;它虽然开展了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但总结经验教训不够;大会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在选举中片面强调了“唯成分论”等。因此,周恩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19)。
对于中共六大存在的不足、缺点或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正如周恩来所说:六大“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20)。这就是说,六大的缺点、错误,虽然对后来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即被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片面发展和极度扩大了,但这不是六大本身的直接责任。所以,这不能掩盖六大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更不能否定六大功大于过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78页。
② 罗漪园:《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载《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3期,第69页。
③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88页。
⑤ 李颖:《寻访中共六大会址》,《百年潮》2006年第11期。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⑦ 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98~199页。
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
⑨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90页。
⑩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31页。
(11)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9页。
(1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13) 《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页。
(14) 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15)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184、181页。
(16)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01页。
(17)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76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19)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187页。
(20)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