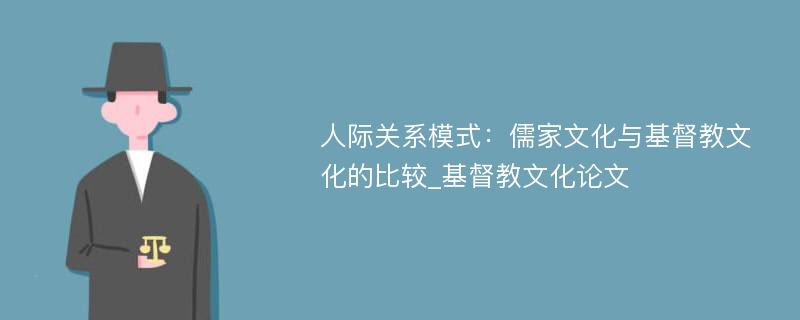
人际关系模式——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教论文,基督教论文,人际关系论文,文化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个体和人际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文化传统。而人际层次的文化传统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并更具稳定性和分异性,更能体现不同文化体系的长期特点。西方人偏重于个体层次上的文化传统,忽视人际层次上的文化传统。而对于重伦理的东方社会来说,更注重人际层次的文化传统研究。
关键词 人际关系;模式;儒教;基督教
我们可以区分个体和人际两个不同层次上的文化传统。前者虽然也必然地是在群体中形成,并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保存下去,但却是分别地由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人实行的价值取向,如勤劳、节俭、理性、创新等美德,以及懒惰、奢侈、非理性、保守等恶习;后者则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如诚实、守信、合作精神、对他人的责任感等美德,以及以其相反的恶习。相比而言,已往有关文化的研究更为偏重于前者,本文则偏重于后者。与个体层次上的文化传统相比,人际层次的文化传统更具稳定性和分异性,更能体现不同文化体系的长期特点,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而且,偏重个体层次上的文化传统,忽视人际层次上的文化传统是西方个人本位的分析取向和模式,而对于具有重伦理的东方社会来说,人际层次的文化传统研究也是最具东方特点的下手处。
一、两种人际关系模式
在任何社会中,无论何种交往,都会受到各种人际关系或大或小的影响。而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对一种特定的交往影响的大小则决定于交往者的取向,即交往者是否重视或是否更为重视人际关系。按照这种影响的大小,帕森斯和希尔斯区分出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不同的取向、行为准则或人际关系模式。所谓特殊主义是指:根据行为者与对象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高低。普遍主义则是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按彼德·布劳的解释,区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标准是:支配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特殊的区分标准是,支配人们之间的取向和交往的价值标准是独立于还是不独立于他们的地位属性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帕森斯和希尔斯的划分与其他很多分类方法一样,是一种理念上的划分,在现实中,“特殊关系”总会有某种影响。因此,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划分本身是相对的,也即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有些成员的取向更具特殊主义色彩,有些成员更具普遍主义色彩。就不同社会或群体而言,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中,总是即存在特殊主义也存在普遍主义,其差别也只体现为“色彩”的浓淡。
按照布劳的说法,特殊主义取向是“整合和团结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即它只在已经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起“整合和团结”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建立关系的能力似乎是有限的,厚此必然薄彼,“亲亲”必然“疏疏”。就此,舒马赫曾写道:“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与数量很有限的人同时接触……”特殊主义取向在不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会起到分隔的作用。或者说:“特殊主义的价值在副结构中创造社会团结的整合纽带,但同时也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副结构之间创造隔离性的界限”。所谓“副结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圈子”,特殊主义在一个社会中划分出了许多“圈子”。一般说,“圈内”的是“自己人”,“圈外”的则是外人。“自己人”相互信任,易于合作,交往频繁;对“外人”则充满疑虑,不易合作,交往较少。但这并不是说,“圈内”的关系都是和谐美满的,事实上,由于“圈内”的交往频繁较大,与之相伴的冲突也较多,而且越是关系密切的“圈子”其内部冲突也越多。但这种内部冲突通常不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而且,人们总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
由于各种特殊的关系作用范围不同,“关系”是分为远近亲疏,三六九等的。从而,“副结构”或“圈子”有大有小,相互套结,这便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在范围不同、属于不同层次的“圈子”之间也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作为一种理想,柏克希望:“对局部之偏爱不会影响对整体的爱”。但在特殊主义文化环境中,人们总是首先忠于内部关系更为密切的小群体,而这种“对局部的偏爱”必然会“影响对整体的爱”。不仅是当小群体的利益与包括这一特定小群体在内的大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小群体的利益,从而可能有损于大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且小群体间的冲突也会产生所谓“内耗”。更重要的是,一般说,在构成群体的情况下,小群体内部个人之间存在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的机制。因此,与小群体内个人的冲突相比,大群体内小群体间的冲突更难消解,冲突也更为剧烈、持久,由此产生的“内耗”也更为严重,从而特殊主义取向本身就具有限制大群体形成和运行的作用,也就是说,特殊主义取向是对群体规模的一种限制性因素。
具有普遍主义取向的人们不大重视已经存在的各种关系,在交往中,更多地依据“理性的计算”作出抉择。用布劳的话说,普遍主义取向是“交换和分化的媒介”,“普遍主义的标准引起了社会地位的分化,因为普遍受到重视的属性或成绩把声誉和权力给予了具有这些属性或成绩的那些人”。同时,“它们把交换交易和地位结构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互动的界限之外”。在普遍主义色彩较浓的社会中,特殊关系的作用较小,一个人不大与某些人特别亲密,也较少与另一些人过份疏远。这便产生了与特殊主义社会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即较少存在明显的“圈子”,既使存在“圈子”,其界限也较为模糊,较具开放性和流动性,“圈内”与“圈外”人际关系亲疏差别也较小。总的说,普遍主义色彩较浓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单一而淡薄,但却可以更多地在较大范围内发展一定的关系,其关系的规模较大。
二、儒教与基督教典籍文化的比较
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仅讨论其在人际关系模式方面的差异。而且,人际关系模式即体现在观念、价值取向的层面上,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层面上。本文主要讨论观念层面上的差异,有关结构层面的差异当另文分析。无疑,在观念层面上,中国及其东南周边国家文化传统的核心是狭义的儒教或儒家思想体系,而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则是基督教,并且两种文化体系的很多差异都与此有关。如梁漱溟曾说:“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以儒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来指谓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关系。如前所述,无论何种文化传统,都同时包含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不同的成份,而且一般说,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都更具有特殊主义色彩。但是,既使在现代化的传统社会中,儒教与基督教两个文化体系在人际关系模式的观念和取向上就已存在重大的差别。相比之下,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普遍主义色彩较浓,而由孔孟开创的儒教文化传统更具特殊主义色彩。这种差别在这两个文化体系的形成期就已经有所显示,而在随后的发展中,这种差别又有所扩大。
帕森斯指出,基督教神学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来文化,二是希腊文明。它从希伯来文化得到了一个信仰的上帝,从而继承了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传统;又从希腊文明得到了一种理性逻辑的求知工具,从而继承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尤其是前者,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在基督教的经典中,存在着强烈的普遍主义取向,甚至存在着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信奉唯一的上帝面反对与任何人过分亲近的倾向。如耶稣说:“如果有人来我这儿而不厌恶他的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那他不可能成为我的门徒”。“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韦伯说:“爱一个人,超出了理智所能允许的限度就是一种荒谬的行动,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不合适的……这经常迷惑人们的心灵,这样便妨碍了对上帝的爱”。贝拉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从摩西启示时代起,社会关系的每一种特殊模式原则上就没有绝对的意义”。
在儒教经典中,则存在着浓重的特殊主义色彩。儒教的“圣人”们虽然也主张仁爱,但他们的仁爱是有差等的。他们明确地表示,人们应该根据对方与自己的关系而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在《论语》中,有多处表露了孔子“亲亲”“尊尊”,“尊卑有等,亲疏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更能够生动地表现孔子特殊主义取向的是孔子与叶公的一段话:“叶公语孔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同样也主张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取向,他不仅有“事,孰为大?事亲为大”等对特殊主义取向的正面论述,而且对主张“爱无差等”的墨子大加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儒教典籍中的这种特殊主义取向与耶稣在人际关系上的取向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应该承认、孔、孟并不排斥非亲非友的陌生人,“仁者爱人”也包括了对非亲非故者的爱,但这种爱是有差等的,更重要的是,“亲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疏疏”,对小群体的爱常常会损害对一般同类的爱。
当然,基督教文化传统与儒教文化传统都包含了不同的来源,具有不同的成份。例如,基督教文化的另一重要来源——希腊文化是多神论的,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伦理特殊主义的成份。而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具有某些普遍主义的成份。如佛教经典中的“一切皆空”、“即心即佛”是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墨子的“兼爱”及“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以义相亲”的思想更具有强烈的普遍主义色彩。张载的“民胞”之说,明确地将路人看成兄弟。甚至在某些公认的儒家经典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主义思想。如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礼记·礼运》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普遍主义色彩。但是,无论是基督教文化中的特殊主义成份,还是儒教文化中的普遍主义成份,在其各自的典籍文化体系中,都只是支流而非主流。
三、从宗教典籍到宗教生活
典籍文化与人们的现实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以基督教而论,由典籍文化到现实生活的过程,首先是从宗教典籍走向宗教生活,而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地具有特殊主义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东正教传统中,这种倾向尤为强烈。在天主教中,存在着严密的教会组织,并分划为不同的教区;每一个人只能通过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宗教典籍是由神职人员来解释的,而不同的神职人员会对同一典籍作出不同的解释,这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教派。教区的划分和教派的分歧意味着教区或教派内部联系紧密,对外则相对排斥,对同属一个教区或教派者和不属于同一教区或教派的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这显然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表现形式。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取消了这种中介,人人得与上帝直接沟通。这一方面削弱了超越性的权威,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解释去信仰上帝,从而增加了特殊主义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却消除了教派之间敌对性纷争的组织基础,也模糊了教区的划分。而且,新教徒及随后的启蒙主义者“予设认为不管何处人性基本上是一样的,目标也是一样的”,这便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普遍主义的取向。韦伯发现,当时工商业中的成功者大多是新教徒。其原因恐怕不仅在于新教使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合理化,为追求利润提供了“正当理由”,而且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束缚,为人们在追求利润的活动中忽略特殊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正当理由”,也就是说,新教比天主教更具有普遍主义色彩,使人们更能在交往中采取理性的态度。
很多学者指出,严格地说,所谓“儒教”并非一种宗教。例如,韦伯认为:没有基督教那样强大的宗教信仰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文化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庄泽宣、陈学恂写道:“儒教的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的教”。整个儒教文化体系虽然不乏来世观念,却是模糊乏力的。知识分子通常对来世抱着一种不可知也不必知的态度。孔子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来世采取谨慎“不语”的态度。庄子主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老子则说:“道可道,非常道”,“大道不称”。民间虽然有轮回观、报应说,但也都是非常模糊的。既然来世是模糊的,不可知的(相比之下,对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来世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可知的”),则其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作用必然就大大地减弱了。因而中国人都抱着“三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态度,将眼光集中于现世,现世的生活并非人们修得来世福祉的手段,而是本身就具有终极价值的意义。在民间信仰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神,但这种多神论恰恰将仅有的一点信念分散到了许多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神身上,以致“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这种弥散、多元、分裂的宗教情感自然进一步减弱了人们的信仰,形成了一种对所有的神都不得罪,对所有的神也都不虔诚信仰的态度。“吃教的多,信教的少”,“对各路神仙毫无真情实感,朝秦暮楚地对待宗教”。因此,森三树三郎说儒教是“接近无神论的泛神论”。
实际上,儒教文化传统中的神“在世界之中”,而非“在世界之上”。人们按现实生活设立神灵的倾向极为明显。众多的神有不同等级,分管不同区域,各有不同的职能。这无疑地是特殊主义取向在宗教生活中的表现。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中国,例如,日本传统的行业各自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再如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以及欧洲各业的守护神或圣者。不过,就世俗宗教生活而言,儒教文化传统的特殊主义倾向也强于基督教文化传统。
四、世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两者相互作用。不过,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这两个方向的相对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人神关系对人人关系的作用较大,人与人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信仰一方面疏离了亲近者之间的人人关系,另一方面也拉近了非亲非故者之间的人人关系,产生了一种使人际关系弥散化的效果。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人神关系对人人关系的这种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人的自然情感以及现实生活有其源于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宗教信仰所能够完全抵消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并非没有区别,只是相对而言,亲疏的差别较小。而且,不仅与宗教典籍文化相比,与世俗宗教生活相比,在非宗教生活中的人人关系中,特殊主义的色彩也存在着进一步强化的倾向,也即与世俗宗教生活相比,世俗的非宗教生活更具特殊主义色彩。
在儒教文化传统中,人人关系对人神关系的作用较大,人神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人人关系的被动反映,人人关系更多地直接源于人的自然情感和现实生活。不过,儒教的特殊主义取向同样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首先是来源于人们的自然情感和现世生活。如袁阳所说:儒家思想在人民大众中的感召力可以说一开始即“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的召唤在人心激起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并且,这种取向得到了其典籍文化的认可和支持,通过将人们注意力集中于人际关系而得到了强化,使关系本身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因此,在非宗教的现实生活中,儒教文化传统更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色彩,在人际关系上更为亲亲、尊尊,人们在交往中,“相比之下不太讲抽象的原则”。在儒教文化中,“一切普遍的标准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东方人常常感到西方人办事缺乏灵活性,太过教条;而西方人则常常认为东方人缺乏原则性,太过灵活。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面是:西方人受普适性原则约束较多,受人际关系的羁绊却较少;而东方人受普适性原则的约束较松,受人际关系的约束却较紧。东方人只在陌生人之间是“机会主义者”,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而在与熟人之间的交往中却受人际关系的约束,迥旋余地则很小。易劳逸在认为中国人是“机会主义者”的同时写道:“大多数中国人在其行为中就发现自己无可摆脱地陷入了一张人际关系网中,自立自依的无法实现,清醒认识到自身包含在较大的社会集团中并对其负有责任,以及对人情要求和压力的痛苦感受,使得他们——如果有冲突的话——牺牲抽象的原则而屈就人际关系”。就“灵活性”而言,诚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之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提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罪的文化”和“耻的文化”。她强调的是“内在”制约“外在”制约的区分:“罪的文化以内在的道德意识为基础,耻的文化从强烈意识到的他人的议论所造成的强制力中产生”。实际上,这里的“内外”是依观察角度、分析层次的不同而变化的。“耻”外于个人而内于“圈子”,所谓“面子”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只存在于与之认识人所构成的“圈子”之内,在一群陌生人中是无所谓“面子”的,也不会有“耻”感。“罪”虽然内在于个人而外于“圈子”,却又源于外在于整个世界的、具有绝对权威的上帝。“耻”体现的是人际关系,是特殊主义的;“罪”体现的是人神关系,是普遍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使得移民于普遍主义文化环境中的特殊主义群众,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群体,具有某种优势。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既可享受普遍主义的好处,又可在需要的时候得到特殊主义关系网的支持。与之相反,特殊主义文化环境中的普遍主义者,如日本的美国企业却可能处于劣势,他们在这种社会中得不到特殊主义的支持,也享受不到普遍主义的对待。
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取向上的差别还会作用于人与事的关系。在西方普遍主义人际关系的文化环境下,人们更多地是以事由建立人际关系。而在东方特殊主义人际关系的文化环境下,有特殊关系则一切可以通融,一切都“好办”;而对没有这种关系的人则极端冷漠,缺乏信任感,这就自觉不自觉地为对方设置了障碍。因此,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在东方特殊主义文化环境下,人们常常不是通过事由建立人际关系,相反,是用人际关系统领事由。“当他们组织起来从事一项事业时,他们通常会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构架”。而在事情必须办又没有现成的关系可资利用时,就需要“找关系”。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论述是以“东方”和“西方”为分析单位的,实际上,在东方各国之间,以及在西方各国之间也存在差异,只是这些差别不如东西方之间的差别那样显著。例如,中国人与日本人比较,日本人在认知特殊主义上弱于中国,而在伦理特殊主义上甚至强于中国,表现在与外国的关系上,中国人虽不易接受外国文化却能够接受外国人,日本人能够接受外国文化却不易接受外国人,特别不能接受外国人的权威。中国人能够接受外国人这一事实,使其能够在外资企业中接受外国经理的管理;而在日本的外资企业中,外国经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在日本,合资企业中外国经理人员很少,这不仅仅是由于上级和同级管理人员的排斥,还由于下级人员不愿接受外来者的权威。
本文于1997年7月8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