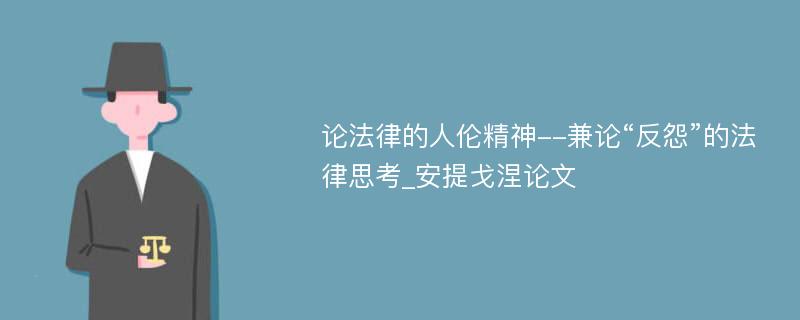
论法的人伦精神——关于“安提戈涅之怨”的法理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伦论文,法理论文,精神论文,安提戈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提戈涅之怨”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塑造的一个女英雄的文学形象。在《安提 戈涅》这一文学作品中,普雷尼克(安提戈涅的兄弟)因犯叛国罪,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被禁止埋葬。安提戈涅基于血缘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城邦的法令 ,按当时的仪式埋葬了她的兄弟,她的理由就是:她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 (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 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但结果她 还是受到了克瑞翁的严惩。但安提戈涅的形象却成了一种符号,代表公民基于人伦精神 和天理良心来对抗国家的实证法,她对城邦法的控诉在西方法学中被称为“安提戈涅之 怨”。诚然,用我们今天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来看,对安提戈涅的严惩似乎是 必要的。任何公民违反了法律,理应受到处罚,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法律权威和司法权 的有效行使。但是,如果加以仔细考量:我们的法在确立其自身权威的同时,是否还应 当包容公民基于人性而生的人伦情感呢?法是否应对公民普遍的道德情感予以尊重呢?
法的人伦精神:历史由来及表征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在这种小农家庭里,以长幼尊卑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形的等级结构,维持这一等级 结构稳定的准则便是伦理的制度及观念,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架构,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种家族结构的摹拟和放大。统治阶级基于其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需要,自然地 选择这种伦理化的制度和观念作为其最好的精神武器,并大力予以提倡和实践,使之纳 入立法和司法之中。台湾学者李钟曾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 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注:李钟声:《中华法系》(上),台湾 中华书局1985年。)这就直接指出了中华法系法律制度的伦理化性质。而要探究中国古 代法的人伦精神,可直接追溯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法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 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恕之道”等都是这一 原则的具体体现;孔子提倡“礼治”,一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 级制度,而且他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思想,主张“以德去刑” 和“无讼”,创设了一套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礼”的秩序的伦理法体系;至两汉,董 仲舒集儒学之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创造 了一套加强封建专制的法律理论,他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进入理想化的人的生存境 界的程序设计,密切地联系着儒学一贯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昭告着对一种保有和谐的 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注:陈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 》,第94页。)统治者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 久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 观念和礼教所支配。”(注:瞿同祖:《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 ,第326页。)法律伦理性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的 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容隐原则可作为其鲜明的佐证。
容隐原则是法的人伦精神在中国古代诉讼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它在历朝历代的法律中 都有所规定。系统提出这一原则的第一人是孔子,他曾就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之事表示不 同于告父者的意见,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注:《论语·子路 》。)至汉代,这一思想被确立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汉宣帝曾专门下一诏令,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 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 上请,廷尉以闻”,(注:《汉书·宣帝纪》。)这一诏令从人类亲情的本性出发解释容 隐制度,正面肯定妻、子、孙为夫、父、祖隐在法律上的正当性(如同我们通常所讲的 “赋予合法权利”),认为基于血缘、亲情、人伦,容隐之行是出于天性,不可违之且 不为罪。在《唐律》中关于容隐的规定,形成了一个较完备的规范系统。《唐律》中对 容隐制作了直接的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 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为使之得以落实,《唐 律》中还作了相关规定,由此,不仅容隐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谋匿犯罪的亲属,即使 是漏泄其事或通报消息给罪犯,使之逃匿也是无罪的”。法律在此体现了对人伦的较大 程度的宽容。至清末民国时期,变法之后,亲属容隐制度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从《大 清新刑律》到民国刑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不罚,放纵或便 利亲属逃脱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千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不罚 ,为亲属销赃匿赃得免罚,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出自诉等规定。” (注: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这些规定,从人所固有的恻隐、是非等天性出发,以人为本,注重人之伦常,是人 伦精神在法律制度中的直接体现。
另外,历代统治者中省刑罚、薄赋敛、以民为本、体恤民困的统治思想亦不在少数, 那些为政以德、安人养民、恤刑慎杀的较为宽平的立法倾向不可否认是为其维护权位、 巩固统治服务的,但也表明他们已能较充分地认识到民众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及其人 格尊严的权利,透发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素和人伦精神。
以上文所及为佐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由于其形成的特定 的经济、政治及历史文化条件,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伦理化倾向,对人伦关系的法律保 护成为其基本的法价值理念。
法的人伦精神:现代命运及缘由
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终于摆脱了古代的樊篱而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与此同时,中 国传统的法律文化逐渐式微,走上了现代化的历程。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我国绝 大多数学者认为“体系过时,品性尚存;整体腐朽,局部可取”。而法律制度最终必以 人为目的,强调以人本位,也就意味着法律本身应当体现并实践着对人的本性的尊重和 理解,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肯定和维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基于人性而生的伦理关系 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应予以保护,而法律制度之于人伦精神的关注无 疑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可取的品性和局部”之一。比如,那和谐的以父慈子 孝、夫刚妻柔为特征的社会人生模式,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人性需要的健康流露,即便在 现代文明条件下,也依然葆有自己的特殊魅力。
然而事实上,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特别是地方制定的法律法规都往往漠 视了法的人伦精神。仅就容隐原则来说,我国新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 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表明无论什么人实施窝藏 、包庇行为,皆应受到处罚,而不管他与犯罪嫌疑人是何种关系,即便是直系血亲也应 一视同仁。从人之伦常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苛刻。与之恰成比照的是,对 法的人伦精神的关注这一中国特有的价值理念却在当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制度中 有所体现。仍以容隐原则为例,德国、法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的现行法律中都有有关直 系血亲或配偶犯窝藏、包庇罪不予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例如:《法国刑法典》在第 434—1条第一款规定了窝藏罪,紧接着第二款又规定了例外情形,即下列人员不属于前 款之列:1.重罪之正犯或共犯的直系亲属、兄弟姐妹以及这些人的配偶;2.重罪之正犯 或共犯的配偶或众所周知与其一起姘居的人。同样,在第434—6条规定包庇罪之后,也 附加了排除处罚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法国,近亲属间、夫妻之间实施窝藏、包庇行为 ,不受刑法处罚。英美法中虽无类似之规定,但英美证据法也有“夫妻互隐”和“神父 为告者隐”等关涉伦理的特殊规定。法对亲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包容几乎成了当今世 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而在其渊源地的中国却已销声匿迹,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依笔者看,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之人伦精神的匮乏和荒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法治理念渐入人心的今天,再去固执地强调人之伦理、世之伦常极易被视为封建 主义的东西,在现代化的旗帜下,“要把这些封建残余扫除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它们自然也就难免遭受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噩运。二是立法者观念的偏差。长期 以来,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服从,以社会本位湮灭个体独立,要求 个人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而往往忽略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要求。在这种 法律文化结构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观念对于立法的影响恐怕不是一两日就可以 消除的。第三,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中的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了历史,造成传统的断 裂。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常纲纪的社会,这一传统至今仍然生生不息 ,并不会因为我们今天倡行法治而悄然断裂和消失,立法者往往忽略法律赖以生存的社 会基础,过高地估计公民的道德水准,甚至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抛 开自己的个人私欲和利益(包括亲情),这不仅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而且违背了公民的 道德情感要求,漠视了公民对人伦关系的认同与拥护,由此制定出来的法自然难以体现 人伦精神。
“安提戈涅之怨”的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讲,安提戈涅是国家实证法的牺牲品,而这个实证法又是背离人伦、漠 视人性的恶法。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现时的法与古时的法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众多学者孜孜以求的,那就是任何“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 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注:洛克:《政府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636页。)法治也不应当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还应当包容 人在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从这一点上讲,法 律具有温和性)。谢晖曾精辟地指出:“每个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现 象,这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天理’是强加给人们的世界各民族 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的、导引我 们民族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民族史留下深刻创痛的‘奇理斯玛权威’。”(注:谢 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第238页。)现代社会、政府等一切计划、安排、行为 都应围绕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进步、人的发展、人的生活而展开,法律应当最大 限度地给个人留置自由的空间,至少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如亲权这种纯朴的原 始的权利)的空间。因为“无论一个个体随其天性之律作些什么,他有最大之权这样做 ,因为他是依天然的规定而为,没有法子不这样做”。(注: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转引自石泰峰编:《称量正义的天平——法律卷》,第46页。)“法律不强人所难 ”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旨在维系普遍和谐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法治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制度体系,当然要 强调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法的至上性和人性、人伦甚或人的尊严对 立起来,这也正是当前构建法治的过程中较为令人担忧的一种倾向。不少地方把法治单 纯看成是治人,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村等的大旗下,无视群众的 道德情感,背离基本的人伦观念,盲目地膨胀地立法,恣意地专断地执法,结果往往是 法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却缺乏丰富底蕴的支撑,法律实施的结果也往往违反法治 的初衷,真正的法治思想从未能在百姓心中扎下根。“操纵人们迫使他们在不可能的情 况下为求你——社会改革者的目标,这是对他们的人性的否定,是把他们作为没有自身 意志的物体来对待,因而必然会使人们退化。”(注:彼得·斯坦等著:《西方社会的 法律价值》。)事实上,人并非法的对立面,人的至尊与法的至上完全可以实现有机的 统一,而人伦精神所指向的正是人基于其天性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它体现和追求的是作 为个体的人的本性和尊严,自然应当成为实现两者统一的一个路径(但并非唯一的路径) 。所以人伦精神应该自始至终地融汇于法律之中,成为其道德的支撑力。这样我们建构 出来的法治最终才能体现出对人类自身的关怀,而不至于异化为压制人、扼杀人的工具 。
我们今天呼唤法的人伦精神,应当超越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法文化的精神,注入现代 社会的价值理念。首先,这要求我们的立法者纠正长期以来的指导观念的偏差,深入挖 掘法律生成的社会土壤,正确估量公民的普遍道德水平,关注群众的情感和呼声。法律 所设的行为标准必须以正常的普通的理性人的行为可能性为限,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 有可能得到公众的拥护,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其次,法律规则 的确立仅仅是构建法治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规则的实施即司法,即便是法律 规则体现了公民的人伦价值追求,也难以保证其在司法过程中被忽视甚至被否定。所以 司法作为纠纷解决的实现机制,应充分注重对人的主体地位、自主意志、人格尊严的承 认和尊重,追求司法过程的人道化,防止法官的恣意专断,确保人伦精神在司法中得到 真正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