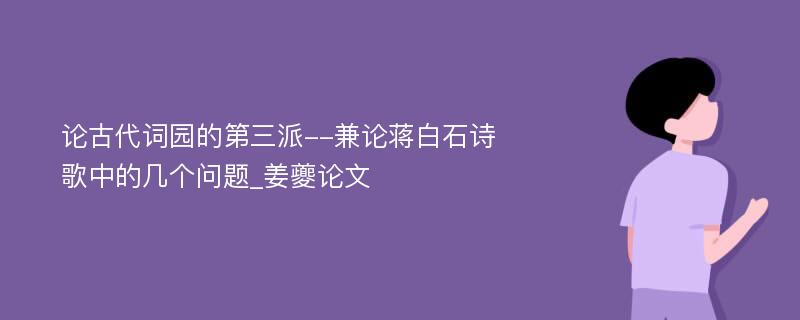
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兼谈姜白石诗词评论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词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试论论文,白石论文,诗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姜词当属于清雅派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词划分为豪放、婉约两派,有些论者还把姜词划入婉约派。这种“两分法”对于南宋以前的词派也许是适用的,对于南宋及其以后的词派就很难适用了。其原因就在于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姜夔,又出现了一批姜氏词风的后继者。他们的词分明是在豪放、婉约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自成另一新的词派。
早在南宋末期,柴望在《凉州鼓吹》(即《秋堂诗余》)的自序中,就把词分为三类、三等,认为“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尚,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认为白石词的风格是“隽永委婉”,是对美成、伯可的词风“一洗而更之”,其《暗香》、《疏影》是“别”一“家数”。尽管他划分的三类、三等并不妥善,尽管他用“隽永委婉”来概括姜词风格并不贴切,但他用“三分法”的眼光观词、指出姜词自成一派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到了清代,从浙西词派的创始人朱彝尊开始,词论家们普遍地认为姜词是自成一派,有些人并且自觉地运用“三分法”辨析以往的词派。例如蔡宗茂在《拜石山房词钞序》中说:“词盛于宋代,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并且用“姜、张清隽,苏、辛豪宕,秦、柳妍丽”的评语来区分三派的不同风格。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语》中说:“宗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认为姜夔是醇雅派的代表。他还引用了王鸣盛的论述:“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认为这是“持平之论也”。这些论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毫不含糊地把宋词区分为三派。至于许赓飏在《双白词序》中所说的:“建炎而还,作者尤盛,……然好为纤稼者不出乎秦、柳、力矫靡曼者自比于苏、辛,求其并有中原、后先特立,尧章、叔夏实为正宗。”虽未明确地区分词派,实际上也是把宋词划分为三派,并以姜、张为正宗。
既曰“词派”,当然需有一个风格相近的作家群。那么,组成姜、张词派的作家群有哪些人呢?清初汪森《词综序》、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均列举有一个追随姜夔的作家群名单,其中包括史达祖、王沂孙、周密等十多个著名词人。清末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序》,也讲到这个作家群:
高、孝以来,词流盖夥翳,惟白石实长齐盟。于是,史邦卿、吴君特羽翼于前,王圣与、张叔夏标映于后。此五君者,譬诸渥洼美驷,荆野明瑶,词学一日不湮,斯人亦一日不没。……其他卢申之、高宾王、蒋胜欲、周公谨之属,亦能各引一端,同声相应,洵长城外之偏师,廊庑中之高弟矣。
由此看出,姜、张词派阵营可观,声势不小。而在这个新词派中,“白石实长齐盟”——实为高、孝以后的南宋词坛盟主。入清以后,由于朱彝尊等人大力标举姜、张,词人们更是普遍地以姜、张为圭臬,其影响之大甚至达到“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地步。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的概念,必须要由大规模地积累的实践经验来完成。”(《资本论》第1卷第404页)既然姜、张词派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积累了大规模的实践经验,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无视这个存在,仍然固守那个“两分法”呢?为什么不应该根据这种新的实践经验,来“完成”关于词派的新的理论概念呢?显而易见,对于南宋中叶以后的词派,不应采取“两分法”,而应采取“三分法”;不应分为两派,而应分为三派。
那么,姜词究竟属于何种词派?或者说姜夔所开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派?对于这个问题,看法颇有歧异,清代的词论家曾称之为“清空派”或“醇雅派”,夏承焘先生则称之为“清刚派”,①另有些论者又称之为“格律派”、② “风雅派”。③在仔细审视姜词的总体风格和前人的评论之后,就觉得上述称谓不太恰切,不如称之为“清雅派”较为妥帖。
最早把姜词推到一个崇高地位的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张炎。他在《词源》中说:“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张氏这些评语,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几乎被目为定评。后人在评价姜词的艺术风格时,大都离不开“清”、“雅”二字。请看以下评语:
白石道人洞音律,大乐建议,勰诸太常,故其为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虚,且又骚雅。
——陶方琦《曰石道人歌曲序》
南渡以后,尧章崛起,清劲逋峭,于美成外别树一帜。张叔夏拟之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可谓善于名状。
——蒋兆兰《词说》
这些评语中所说的“清虚”、“清劲”、“清空”、“骚雅”以及“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都非常明显地受有张炎的影响。除此之外,运用“清”、“清逸”、“清超”、“清妙”、“清新”、“清俊”、“清绮”、“清芬”、“清真”、“清炼”、“清峭”、“清隽”、“清挺”、“清拔”、“清刚”以及“雅”、“淡雅”、“醇雅”、“浑雅”、“雅洁”、“雅正”之类评语评定姜词风格者也比比皆是。用语虽不尽相同,但目为“清”、“雅”则大体一致。这些评语,包括“清空”、“清刚”、“骚雅”以内,均能标示姜词风格的或一特征。唯独“风雅”二字,含意过于汗漫,很难特指姜词的风格特征,也很难特指某一词派。因此,如果说把姜词称之为“清空派”、“清刚派”、“醇雅派”尚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把姜词称之为“风雅派”就很难说有多少道理了。至于“格律”二字,固然也能标示姜词的或一特征,但用以分派却有失严谨,很容易把不同风格的作家装进同一个大木桶里。
用“清”、“雅”二字来评定姜词风格,大体上是贴切的。白石的绝大多数词作,确实是以清雅之辞,抒清雅之情,写清雅之意,吐清雅之气,或咏清雅之物。像《暗香》的开端:“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所写的“玉人”月下“攀摘”梅花的情景,以及下面“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千树压、西湖寒碧”所写的梅花香气浸入瑶席的情景,“千树”梅花盛开时映照在“西湖”水面上的情景,均显得十分清新幽雅。又如《疏影》的开端:“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即使我们不知道它用的是赵师秀在罗浮山梅林中遇见仙女的故事,读的时候也会感到一缕清灵之气扑面而来。又如《念奴娇》的上片:“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所描写的荷花世界的优景色,在微风细雨中那种水波荡漾、翠叶轻摇、荷花飘香的绮旎风光,也显得非常清雅俏丽,醉人心魄。我们知道,白石爱梅,在他现存的一○八首词中涉及梅花的词多达十七首。白石又喜爱荷花,他在吴兴时曾屡屡徜徉于荷花构成的“水晶宫”中。梅、荷本是清雅高洁之物,一经白石以清雅的词笔出之,自然也就呈现出一种清雅的格调和风貌。白石咏物词的内容颇多,除梅、荷外,还有咏芍药的,咏牡丹的,咏茉莉的,咏柳的,咏黄香木的,以及咏蟋蟀的等等。这些物本身虽不一定清雅,但一经白石以清雅的词意予以描摹,也大都含有清雅的韵味。白石寄情山水,向往隐逸生活,其《湘月》、《清波引》、《庆宫春》、《点绛唇》、《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等词,均表现了他陶醉自然山水之情,有的还流露了追随陆龟蒙归隐江湖之意。这样的情意也历来被视为高雅清逸,一经白石以清雅的笔调予以抒写,自然也呈现出一种清雅的格调和岁风貌。在白石词中,还有表现怀才不遇的,乡关之思的,个人恋情的,以及黍离之悲的,也大都写得或清虚骚雅,或清冷幽雅,或清逸淡雅,或清真典雅,或清新雅正。一句话,两个字,就是“清”、“雅”。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盖为近之。”又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可谓道出了姜词清雅高洁的基本特征。
郭麐在《灵芬馆词话》中说:“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磬幽响,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也可谓道出了姜、张词派的清绮雅洁的重要特征。
根据对姜词的总体审视并参照前人的评论,我们认为,南宋中叶以后的词 应该划分为豪放、婉约、清雅三派,不应该仅仅区分为豪放、婉约两派。把姜词视为“婉约派”、“风雅派”显然欠妥,把它视为“清空派”、“醇雅派”、“清刚派”、“格律派”也不够完善。姜词当属于“清雅派”,姜夔正是“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
二、历代评姜者的一些问题
历代评议姜夔的文字多如麻竹,但却存在有一个共同的疏漏,就是忽视他的一首爱国词——《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一首忧民诗——《箜篌引》。
在对姜词的评论方面,大多数人只是从艺术性着眼,只有少数人论及思想内容。在论及思想内容时,有些评论家还具体指出姜氏某些词作含有“故国之思”、“黍离之悲”。但其所列举的词作往往仅限于《扬州慢》、《齐天乐》、《凄凉犯》、《点绛唇》、《惜红衣》以及《暗香》、《疏影》等篇什,而并未涉及《永遇乐》。而这几首词即使全有寄托,所表现的也尽是对南宋因遭金人侵略而造成的悲惨时局的一片哀伤、感叹之情,毫无积极进取、奋发图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之意。真正显示出慷慨激昂、积极进取精神的倒是这首《永遇乐》:
云鬲迷楼,苔封很石,人向何处?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使君心在,苍崖绿嶂,苦被北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
白石晚年受辛弃疾影响,一度精神振奋,胸襟开朗,词风也有转变。辛弃疾在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在这年秋天曾写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抒发其“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壮志。白石此词,即是“步稼轩北固楼词韵”而作。全词洋溢着对抗金英雄辛弃疾的热情歌颂和殷切期待。“大旗尽绣熊虎”一语,写出了辛弃疾在镇江府大刀阔斧地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语,道出了沦陷区人民渴望大军北伐的迫切心情。这首词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和广大人民的心声,诚为难得的佳作。
可是,这样的佳作却长期受到封建文人的漠视。这首《永遇乐》在白石词中诚然属于“别格”,属于豪放派,不属于清雅派,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倒是提到这首《永遇乐》,可惜又旋即以“并非他(指姜夔)的本色,是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的”为由,而不加评说,就一笔带过了。于是,就仅以《扬州慢》为依据,说词中“缺少振奋人心鼓舞正气的热情,而具有感伤的消极情绪。”给人的印象,仿佛姜词中抒发的爱国情思全是一片消极感伤似的。还有的先生在谈到白石“虽长于表现个人感受和抒情状物,却短于写重大的题材”时,未提《永遇乐》,仅以“白石晚年与辛弃疾唱和之作又当别论”为由就又一笔带过了。④这种一笔带过的作法似也欠妥。
白石以词驰名于世,实际上他在诗歌、音乐、书法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且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就其诗而言,在南宋诗坛上也是别树一帜,受到当时以及后世不少评论家的击节赞赏。清代大诗人王士祯认为:“白石,词家大宗,其于诗亦深造自得。”《四库全书》编者认为:白石作诗“以精思独造为宗。”并说:“今观其诗,运思精密,而风格高秀,诚有拔于宋人之外者。”⑤黄培芳说:“宋人七绝,每少风韵,唯姜白石能以韵胜。”⑥又说:“宋人绝句,若东坡、石湖、白石三家,风调清远,多逼唐人。”⑦他们这些评语是符合姜诗的实际的,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尽管评论者颇多,对姜诗评价很高,可是并不全面。如同对姜词的鉴赏一样,他们对姜诗的鉴赏也多是从艺术性着眼,而忽视其思想性强的诗篇。特别不应该的,是对白石诗集中一首极为难得的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视而不见,那就是《箜篌引》:
箜篌且勿弹,老夫不可听。河边风浪起,亦作箜篌声。古人抱恨死,今人抱恨生。南邻卖妻者,秋夜难为情。长安买歌舞,半是良家妇。主人虽爱怜,贱妾那久住。缘贫来卖身,不缘触夫怒。日日登高楼,怅望宫南树。
诗中不止是揭示了“缘贫”而“卖妻”、“卖身”者本人的痛苦,而且把笔锋拓展开去,用“长安买歌舞,半是良家妇”二语,显示出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尤其“今人抱恨生”一语,简直是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读这首饱含人民性的诗,不由令人联想到白居易的《新乐府》,也令人感到历来忽视这首诗是何等的不公正!有了上面这两首爱国忧民的诗词,才使我们能完整地了解姜夔其人及其作品的全貌,也够使我们对姜夔的性格“另眼相看”了。至少在评论白石诗词时,对其思想性的看法要有所矫正。至少在评论姜词的爱国情思时也可更全面一些,不至于笼而统之地讲它只是消极感伤的“黍离之悲”吧。
自从张炎给白石词以高度的推崇后,姜词在元、明两代已颇受好评。入清以后,词论家们更是普遍地尊奉清雅派为词坛正宗。对于姜词可说是一片赞扬。纵观历代对姜词和清雅派的评论,也颇有一些褒贬失当之处。
自从朱彝尊在《黑蝶斋诗余序》中提出“词莫善于姜夔”这一极高的评价之后,词论家们越说越“绝”。有些评论家甚至把姜夔比为词中老杜,誉为词中之圣,并且把白石词视为词之顶峰:有的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戈载《宋七家词选》)有的说:“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叶申芗《本事词》)。还有人认为:“南渡如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诸家。”“词之有姜张,犹诗之有李杜也。”⑧对白石其人其词的推崇真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众所周知,杜甫之所以被视为“诗圣”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因为他在众多的优秀诗篇中深刻而又广阔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社会生活,抒发了十分深切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并且在艺术上奄有众家之长。而白石词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狭窄,具有“故国之思”的词作数量甚少,感情也不及杜诗深挚,艺术上也并未“奄有诸家”,远不及杜诗丰富多彩,怎么能与杜甫相提并论?作为清雅派的代表人物,充其量也顶多只能与豪放派、婉约派的代表人物鼎足而立,各有千秋,怎么能视为词之极致、词之止境或词之顶峰呢?“词圣”、“绝顶”云云,显然是不着边际地“拔高”了。
与这样的“拔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个别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识地贬斥姜词以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例如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又明确地标举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而贬抑姜、张,认为“碧山恬退是真,姜、张皆伪。”认为姜词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支处”、“复处”,并且举了例证。在经过一番贬抑和挑剔之后,他自己也承认其“纠弹姜、张”是“皆足骇俗”。
白石词当然不是完美无缺,早在南宋末年,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就指出它有“生硬处”。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姜词的缺点是完全可以的、必要的。问题在于周济所指责的“俗滥处”、“寒酸处”等等,多半是故意挑剔,并不符合实际。比如《扬州慢》开头的“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是被指责为“俗滥”的例证。其实这是点明所咏的地理位置,何“俗滥”之有?白石怀才不遇,产生“恬退”归隐的念头原是很自然的事,又何“伪”之有?至于说“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也属立论无据。姜词清雅绝俗,开宗立派,奉为古今词坛盟主固然不妥,奉为南宋中、后期词坛盟主或清雅派盟主是完全可以的,怎么能说他在南宋“亦非巨擘”呢?周氏这种偏激的论断,即使在常州词派内部也难以得到认同。比如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张惠言,就把姜夔与苏轼、周邦彦、张炎等人一起列入“正声”,认为姜词也是“渊渊乎文有其质焉。⑨该派的重要理论家冯煦认为“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⑩该派另一理论家陈廷焯认为“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11)并认为“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为冠。”(12)两宋作者,断以清真、白石为宗。”(13)所谓姜夔在南宋“亦非巨擘”之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附带说一下,清代词人由于推崇白石词,遂把清雅派抬高到豪放、婉约两派之上,奉为词坛正宗,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无论是豪放派、婉约派还是清雅派,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硬要把清雅派与其他两派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清雅派的高处达不到豪放派那种疆域辽阔、慷慨激昂的高度,其低处也降不到婉约派那种绮罗香泽、纤靡淫艳的低度。否则就失去了“清雅”的特色,不成其为清雅派了。像白石那首《永遇乐》就逸出了清雅派的樊篱,跑到豪放派的营垒去了。陈洵有句话说得好:“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14)清雅派的疆域的确也是比较狭窄的。所以,把婉约派奉为正宗固然不妥,把清雅派奉为正宗同样不妥。从提倡风格多样化和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要而言,应该吸取三派之长,做到三派并重才是。从提倡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而言,对豪放派应该格外看重才是。把清雅派奉为词坛正宗,应该说也是一种褒贬失当。
注释:
①《论姜白石的词风》,见《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③邓乔彬:《论南宋风雅词在词的美学进程中的意义》,见《词学论稿》,华东师大出版社。
④邓乔彬:《论姜夔词的清空》,见《词学论稿》,华东师大出版社。
⑤《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⑥《香石诗话》,上海书店版。
⑦《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版。
⑧《词源跋》,见《词源》,词活丛编本。
⑨《词选序》,见《茗柯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⑩《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
(11)(12)《白雨斋词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13)《词则·云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14)《海绡说词》,词话丛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