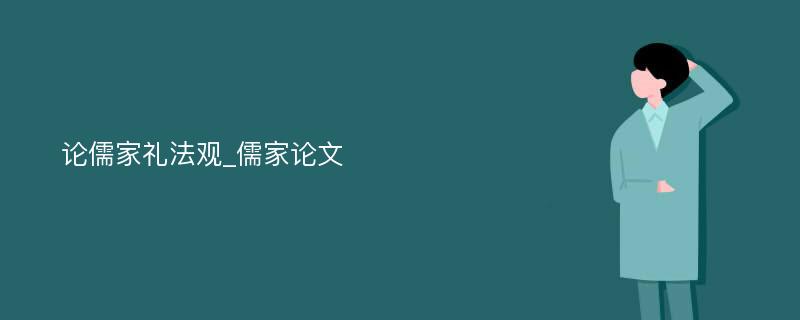
论儒家的礼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礼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文化异常发达。正所谓“统承先王,修其礼物”(《尚书·微子之命》),“无礼不相见也”(《仪礼·士相见礼》),“不以贽,不敢见”(《礼记·表记》),礼物交换在小至走亲访友,大到婚丧嫁娶、朝聘会盟等场合都是不可或缺的。儒家文化传统素重“礼尚往来”,“三礼”等经籍文本对礼物的本质、形式、种类与馈赠原则等问题有着不厌其烦的详细规定。清儒姚际恒说:“古者相见,先之以介绍,将之以辞命,附之以礼物。”(姚际恒,第77页)过去人们如此,现在人们亦同样乐此不疲地交换礼物。正是礼物在人际之间循环不竭地流动,造就了浓郁多样、深具特色的中国礼物文化,并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以礼物生产与交换为内容的礼物经济。也许是由于礼物这种东西过于司空见惯,以至于人们几乎忘记了对于礼物之本质的追问。尤其是在现代处处奉行非人格化的、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环境中,人们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礼物的价值,甚至干脆直接用礼金来代替礼物,礼物商品化与货币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反之,有些纯粹的商品与利益却换以礼物的美名大行其道,市场正在改变、侵蚀其所能够调控的物品和非市场逻辑的社会惯例之性质。(桑德尔,第132页)我们不禁要问:礼物究竟是一种人格化的、纯粹无功利性的神圣之物,还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完全功利性的普通商品?礼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此,已有许多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礼物社会学与礼物经济学论述。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从哲学的层面来重新审视儒家礼物观的情感主义与道德主义特质,从而为礼物正名,为儒家礼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提出建议。
一、儒家的“礼物之灵”:“有礼之物”与“无礼之物”
在“仪礼三百,曲礼三千”的儒家礼学传统之中,礼物作为表达人类情感和道德寓意的物质载体,其本质在于“礼”而不在于“物”。孔子有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的物质形式是次要的,精神内涵才是主要的。北宋学者李觏对此说道:“但以器服物色、升降辞语为玩,以为圣人作礼之方,止于穷奢极富,炫人听览而已矣。……苟礼之所之,止于器服物色、升降辞语,而无仁、义、智、信之大则,是琐琐有司之职耳,何圣人拳拳之若是乎?”(《李觏集》,第15页)言下之意,儒家注重器物服色等礼物程仪不是为了穷奢极欲、攀比炫富,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有形形式来体现、渲染和强调礼之精神内涵。可以说只有理解了礼物所承载的心理、道德和社会寓意等精神内涵,才能理解儒家对礼物的本质界定。在儒家看来,礼物之所以与一般的物品或商品不同,关键就在于“礼”与“物”的区分与联结:礼物是“有礼之物”而非“无礼之物”。换言之,“无礼之物就只是物品而不是礼物”。(阎云翔,第43页)相对于一般商品所必须具备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来说,礼物之“礼”——情感关爱、道德寓意和社会象征才是礼物的本质特征。
首先,礼物是具有“情感性”的物品。礼物作为人际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其所交换的不仅仅是实物,更是一种情感。在某些特定场合,赠人礼物是表达同情、感谢、好感、祝愿与尊重等情感的特别方式。对于满足人类的情感需要来说,一种没有什么实际利用价值却包含了丰富情感的东西,可能要远比有诸多实用性的物品来得更有意义。在儒家看来,“礼因人情而为之”,“礼义也者……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也”(《礼记·礼运》),“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通过礼物交换不仅可以加深人际间的亲密关系,甚至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当一个馈赠者出于某种情感动机送出礼物之后,馈赠者有特定对象的情感表现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因为接受者保留了礼物这一情感的物化形式得以长期留存。一件物品可以通过非人格化的公平交易手段而无数次地转手,可是一旦当它被作为礼物无偿赠送给某个人的时候,这件物品就因其所附着的特定主体的情感内涵而具有了人格化特征,而具有了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虽然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礼物被赠出之后,礼物即归受礼者所有,物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皆发生了完全转移。可是,礼物中所包含的情感却依旧是属于赠礼者的,它不仅无法让渡,而且受礼者似乎还必须为赠礼者所付出的这份感情尽到保管的责任,不能随便抛弃或转手他人。这样一来,礼物就不可能像商品那样完全地让渡:它虽然归受礼者所有,可是在某种程度上仍归赠礼者所有。正所谓“商品概念以互报独立性和可异化性为前提,是礼物概念的镜像,礼物概念是以互报依赖性和不可异化性为前提的”(格利戈里,第15页),礼物所具有的这种人格化特质乃至神秘的精神力量,也就是马塞尔·莫斯所说的“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参见莫斯,第18-22页)。礼物中所包含的情感与灵魂给受礼者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准确地说就是“感情债务”,只有通过类似的回赠行为,才得以平衡,于是精神伴随着礼物的流动而得以在人际之间传递不止。这对于促进人们的情感认同与精神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礼物是具有“道德性”的物品。“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礼记·礼器》)从个人角度而言,纯粹无私地赠礼物给他人,即真正的施恩不图报的行为,无疑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慷慨无私的美德;而接受他人的礼物之后,受礼者力所能及地回馈赠礼者或者他人,无疑也体现了一种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的心理。从社会层面而言,礼物交换行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馈赠与报恩的道德情感与人情法则,它不仅可以促进社会道德氛围的进步,还可能为社会平衡人际关系冲突提供一种自发、持久而稳定的伦理道德机制。这也正是刘向所说的:“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见向宗鲁,第116页)推扩仁爱之心,普及道德风教,形成一种礼治秩序,是儒家之所以一贯强调礼尚往来和忠恕之道的真正动机。
在儒家看来,“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见钱玄,第497页)一言以蔽之,即“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这里的“义”,就是礼物程仪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道德规范。仅就礼物而言,儒家异常注重这种道义上的价值,而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反而显得无关紧要。当然,礼物交换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礼物的物质内涵之交换,但是用来交换的礼物在种类、数量、交换方式和精神实质上皆需要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某种社会道德寓意。例如,在中国古代的诸侯或国家交往过程中“出疆必载质(贽)”(《孟子·滕文公下》),“交贽往来”(《左传·成公十二年》),礼物成为和平交往的重要手段。国礼中通常会包括圭、璋等贵重且数量庞大的物品,赠礼与回礼的程仪也非常讲究。《礼记·聘义》曰:“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之所以用圭、璋作为聘礼,是因为其贵重,比较适合于国家会盟等重大场合;而“已聘而还圭璋”则表示礼物本身的物质内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礼物所要表达的和平寓意。《礼记·中庸》有云:“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即为了和睦国家关系,有时回礼需要比赠礼的数量更多、价值更高。这表明礼物只是联结、促进关系亲密度的手段,此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耳。当礼物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时,礼物的实际价值有时远不如通过“夸富性”的赠予所表现出来的“怀广远,明盛德,远国莫不至也”(王贞珉,第335页)的政治道德与象征价值重要。
与严肃庄重的国礼交换及其体现的政治道德寓意相比,个人之间的礼物交换行为则随意得多,但同样表现出其社会道德性。《左传·庄公二十四年》有记载:“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粟枣脩,以告虔也。”这是说,男子相见的礼物的大小与多少,固然表示了一个人的身份和等级,但是与女子相见所用的小食品一样都表达了一种诚敬之德。到了汉代,《白虎通义·瑞贽》已经尝试着对日常礼物交换进行彻底道德化的解释:“私相见亦有贽何?所以相尊敬,长和睦也。朋友之际,五常之处,通财之义,赈穷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饮食之,故财币者,所以副至意焉。”(见陈立,第358页)显然,人们在择定礼物时必须考虑到礼物所可能包含的种种道德意义,即使是直接馈赠财币的行为也最终是在赈穷救急而非务求回报的道德动机激励之下的结果。作为不需要偿还的礼物,它充分体现了赠礼者乐于奉献甚至牺牲的崇高道德品质。当然,如若赠予他人一种无礼之物,它不仅是对受礼者人格与尊严的侮辱,也会反映出赠礼者的恶劣道德品质。从这个意义讲,礼物就是道德寓意良善、吉祥的物品。
再次,礼物是具有“仪式性”和“象征性”的物品。人类学家李亦园曾将人类的行为分为实用行为、沟通行为与宗教巫术行为三个层次,其中“宗教巫术行为与沟通行为都属于无实用目的之象征行为,所以一般都可以合称为仪式行为”。(李亦园,第307页)在宗教与沟通行为中,很多礼物是纯粹仪式化和形式性的,象征意味强烈,几乎没有实用性,仅用以表达某种愿望。仪式性礼物无疑是纯粹的精神消费之对象。古代礼仪活动中所陈列的大部分礼器皆属于象征性礼物之列,现代中国人在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仪式活动时互赠的一些小玩意也应归属此类。
我们说礼物具有仪式性和象征性,当然并不是说礼物的物质内涵可有可无,而只是说即便是最为注重价值的实用性的礼物交换行为,也必须要有一定的仪式性和象征性。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馈赠现金时,通常会用“红包”、“利是”等形式包装起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华人学者杨美惠在分析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所伴生的“礼仪经济”现象时指出,礼金、礼品等非常实用的人情支出其实是一种从纯粹逐利性中摆脱出来的“非生产性活动”,通常只是“为了获得它的社会和精神意义及其效果”——“自主存在的时刻”。(杨美惠,2009年a,第30页)与此类似,郭于华在对骥村的个案研究中也证明了礼物交换的世俗性与超越性兼备的双重特征:“这种不断重复的满足而又超越了实用性的礼物交换关系,形成了骥村农家在公共生活中的处世哲学,也构成约束其行为的规范与准则,从而建立起和谐互补、共存共荣的社区生活。”(郭于华,第350页)总体看来,儒家的礼物往往是世俗性与超越性、实用性与象征性的统一体。
礼物的象征性还特别体现在它是一种社会等级、权力、权威和地位的表达符号。布迪厄在研究社会资本的时候曾指出,礼物作为一种形式性、象征性的资本“没有了具体的和物质的作用,简单说,它们是无偿的,亦即非功利的,也是无用的”资本,但是当这种象征资本“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可能与宗教资本一起组成唯一可能的积累形式”。(布迪厄,第186页)在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儒家就经常用礼物来表示人的身份等级与地位。例如韦昭注《国语·周语上》“为贽币瑞节以镇之”条中记载道:“贽,六贽也。谓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显而易见,不同的社会等级对应着不同的礼物种类,礼物在稀缺性、象征性等方面差别很大。在这个意义上说,“礼物交换者所指望的是通过礼物交换所产生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东西本身。”(格利戈里,第20页)礼物交换遂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儒家认为礼物虽然是“礼”与“物”的混合物,但是其本质内涵在于“礼”而不在于“物”。要言之,礼物应具有以下几个本质特征:情感性、道德性、仪式性和象征性。这些其实是儒家的“礼物之灵”——礼物之“礼”的形上意蕴之所在。正是礼物中的形上意蕴,使其最终与仅仅注重实用价值的一般商品区别开来。
二、儒家礼物交换的两个基本原则:“礼尚往来”与“亲亲尊尊”
鉴于不同的交换动机,礼物交换的方式和原则是不尽一致的,有时差别异常明显:有些是完全不求回报的、纯粹表达性的馈赠,有些是有来有往的均衡互惠,有些则是有来无往的、纯粹工具性的馈赠。儒家礼物交换一般依据的是以下两个原则——“礼尚往来”和“亲亲尊尊”,它们既具有人类的共通性也具有儒家的特殊性。大致上,“礼尚往来”通常是“表达性”和“均衡性”的礼物交换行为,而“亲亲尊尊”则可以对应于“工具性”和“非均衡性”的礼物交换行为。然而,中国社会的礼物循环过程中通常是混合性的礼物居多。礼物是表达性的还是工具性的,遵从的是均衡原则还是非均衡的优位原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一方面,在儒家看来,无论是表达性礼物还是工具性礼物,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性礼物,在礼物的形式、内容和数量上都应遵守“礼尚往来”这一均衡互惠原则。《礼记·曲礼》有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杨联升就此认为,“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当然,实际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杨联升,第349页)中国人通过礼物不断地赠送——接受——回报的循环,维系和巩固了平等、互惠、互助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可以说礼物循环中的馈赠与回报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另一方面,儒家传统不仅要求礼尚往来的互惠、对等原则,其差序格局有时还要求遵循亲亲与尊尊这两个非均衡性原则。在家族内部,按照血缘关系呈现出远近亲疏的差序特征,而在家族外部则依从社会权力与地位之不同表现出尊卑贵贱的等级特征。杨联升在指出“交互报偿”的原则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基础”的同时,还指出中国礼物交换行为的另外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家族主义,二是现世的理性主义,三是道德的分殊主义。(同上,第349-373页)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偏爱实用性、工具性的实用理性(有人干脆称之为实践理性),对不同的人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由于受儒家亲情伦理与实用理性影响,在国人的礼物交换活动中,平等主义的交互报偿原则并不是普遍有效的,随着血缘亲疏和地位尊卑的不同,礼物交换往往体现出单向性和不对等的分殊主义。在权力、地位和声望等社会资本积累水平明显不同的人之间,礼物交换行为通常会突破“礼尚往来”的对等互惠原则,改为依据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高低而单纯向上流动的优位原则。例如君上可以接受臣下的献挚而不必回礼,士向大夫献挚时大夫则三次谦让之后仍旧“终辞其挚”,这是为了避免在上者屈尊回访、还挚。虽然正如彭林所指出的那样,“不同身份的人见面,地位高的一方如何处理对方的‘献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彭林,第132页),不过地位高的人在礼物循环活动中拥有最终决定权恐怕是比较普遍的。这种不同社会地位与等级之间的非均衡性礼物交换行为,由于声望归于收礼者而非赠礼者所有,因此其实质是对社会权力、声望、地位与等级进行不断确认、累积的再生产行为。布迪厄指出,人们凭借节日、仪式、赠品交换、拜访和回访、礼节性来往尤其是婚姻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活动,“是集团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再生产”。(布迪厄,第177页)儒家的礼物在很多时候担当了社会“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礼记·曲礼上》)的工具,对于认可和强化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和等级地位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里,礼物交换行为中的“礼尚往来”原则依然受到肯定,而“亲亲尊尊”原则则受到了严厉批评。在西方学者当中,马克斯·韦伯应是第一个明确指出儒家伦理深具特殊主义与人格主义特征的人。在他看来,“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和制约”,而这种基于血缘共同体而建立起来的儒家伦理有悖于强调非人格化的、公平交易的资本主义精神。(参见韦伯,第266-271页)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也同样认为,“为儒家伦理所接受和维护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批评这种关系主义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不健康的因素。(cf.Parsons,p.551)类似的批评还有很多。在他们看来,要想转变浸淫着深厚的“亲亲尊尊”色彩的儒家礼物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伦理来取代中国的家族主义伦理,以平等主义伦理与社会制度来替代中国的等级主义伦理与社会制度。(黄光国、胡先缙等,第25页)
上述批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如果礼物循环同样遵从了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法则,那么礼物就彻底变成了商品。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之所以不同,就在于礼物交换的“不可异化性”,亦即礼物与交换双方有着不可分离的人格化属性。毕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血缘关系和权力等级相交织的社会场境之中,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可能等距和同质,因此礼物交换既然是人格化的行为,那么就无法完全避免特殊主义伦理的约束。虽然现代文明催生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化规范、契约化关系、非人格化的交易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与礼物交换行为的人格化交换模式不应是现代与前现代、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应是一种互补关系。用人类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所有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几乎都是人类学的”,亦即“所有的交换,都同社会交往的某些方面,在考虑交换物质层面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的社会层面”。(萨林斯,第213页)这里的“社会层面”,其实就是指价值理性所关照的情感、道德、审美、宗教等无法用货币数量来衡量的因素。
时至今日,儒家礼物经济行为中所奉行的特殊主义伦理,更遭受到现代商品经济所奉行的一种完全自愿、平等和公开交换的普遍主义经济伦理的强烈挑战。然而在笔者看来,不仅原子式个人之间完全平等的礼物交往是不存在的,而且由于礼物本身具有因人而异的人格化特征,因此浸淫着分殊主义伦理的儒家礼物观在现代社会仍旧会有顽强的生命力。况且私人之间的礼尚往来行为体现了儒家的“忠恕之道”,遵循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增强了人们的道德义务感,对于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制度、工具理性来说应该是一个必要的补充。用金耀基的话来讲,礼物交换行为中所包含的“人情”,“不止规范了社会性的人际关系,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系统出现强韧的凝结力”。(金耀基,第94页)杨美惠等人则认为,礼物交换经济中所体现的“关系艺术”,作为“一个次生社会的动力因素”,尤其是在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格局中民间社会需要冲破种种体制约束的大环境之下,应视作是中国市民社会建设的积极因素。(杨美惠,2009年b,第257页)
三、儒家视野下礼物交换的公-私边界
事实上,即使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等价交换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里,非商品性、不对等的礼物交换行为也不仅没有被商品交换所抵消或替代,反而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品交换与礼物交换这两种大不相同的社会交换行为同时存在的事实,并不表示二者没有冲突,而是表示在冲突的二者之间也许能够实现一种平衡:既能够避免工具理性横行天下而形成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又能够防范价值理性泛滥而陷入对工具理性的压制。要想实现这种平衡,需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个是人们对于上升到道德境界的非工具性交换生活的利他追求;另一个是为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兼容设计出一整套法律与制度规范,对双方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划出适当的边界。当然,为纯粹的礼物交换与实质的利益输送两者之间划出一个边界,指明何时、何地、何种形式的礼物交换行为应该遵从工具理性或遵从价值理性,遵从平等伦理或遵从差序伦理,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礼记·丧服四制》曾试图笼统地给出礼物交换行为的边界之所在:“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在家庭内部,父母长辈的恩惠是无限的,子女晚辈的报偿也是无限的。双方的恩惠与报偿固然会构成一个礼物代际之间流动的链条,但是双方在赠礼的时候大多是不求回报的,纯粹是出于对家庭成员的道德义务,而非追求一种价值上的公平对等。在家庭外部则恰好相反,礼尚往来——体现为经济互惠的道义公平则是人际交往的主导原则。这显示儒家在坚持家庭主义和等级主义的同时,其实也存在一种普遍平等的道义诉求。然而从总体上看,儒家礼物观的上述划界是不甚清晰的,难以避免对礼物的广泛误用。
家庭本位的巨大伸缩性使得中国社会俨然是一个公私不分的大家庭,社会性的工具性交换行为也必须采取家庭内部的表达性交换行为的形式。在儒家泛道德主义或者严格道德主义传统的氛围中,多数有偿行为被包装成不求回报的无偿馈赠而盛行于世。尤其是与公权力有关的“礼物”交换行为,明明是出于牟取私利或者利益输送,却偏偏以“礼物”馈赠等面目大行其道。礼物由此沦为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之手段,彻底颠覆了礼物本身存在的合法性。正是由于公私不分,使得中国至今的礼物交换行为依旧弥漫着等级主义、自私主义和腐败主义的气息,这是我们在反思儒家礼物观时必须予以充分正视和有力批判的。
除了道德的自律之外,对于诸种涉及公共权益的礼物交换行为,必须施以明确的法律规范。礼之用,和为贵——礼物是增进感情、促进交流的最佳润滑剂之一,因此适当的做法并不是一律禁止涉及公共身份或公务活动的礼物交换行为,而是对礼品的数量、金额及对象等作出具体而严格的限制。目前国人礼物交换之乱象,既与公私之间伸缩性极大的儒家礼物观传统有关,亦与相关法律规定的欠缺以及人们法律观念的不强有关。
四、回归礼物的本性:“礼物永远多于应得之物”
现在,人们对掺杂于礼物交换活动中的阿谀奉承、贪污贿赂、敲诈勒索甚至于羞辱蔑视等种种不良现象可谓深恶痛绝,对于礼物已然不成其为礼物痛心不已。但无论如何,礼物具有实用价值和人文价值,这一点自古至今似乎从未改变。那么,礼物的真谛究竟在哪里呢?有没有一种真正而纯粹的礼物呢?在回顾与反思儒家的礼物观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应该回归礼物的非商品之本性。礼物不同于商品,不能简单地用现代流行的商品交换观念来解释礼物及其交换行为:礼物主要是情感交流与精神消费的物品,而不只是商品。平等交换而来的商品只有被消费的命运,并且双方互不亏欠,礼物则除了可被消费的实际使用价值之外,还能够不断传递友爱、善良和精神的愉悦,形成一股爱的潜流。正如斯特拉森所说的那样,“如果他所回馈的与其最初接受的相等,那只能说偿还了债务”,因此“礼物永远多于应得之物”。(Strathern,p.216)然而,精于算计的工具理性在礼物交换活动中的误用,使得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日益同质化,这对传承已久的礼物交换行为存在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好在“人成为机器,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充满了情谊、道义和精神寄托的礼物交换行为的经久不衰,恰恰可以表明我们人类“还没有到一切都用买卖来考量的地步”。(参见莫斯,第186-201页)
其次,应该回归礼物的人格化之本性。由于平等主义观念深入人心,儒家礼物观中“亲亲尊尊”这一分殊主义与等级主义色彩浓厚的交换原则遭到了猛烈批评与拒斥。然而,“礼尚往来”并不等于说礼物交换必须是对等的,它往往是因人而异的。一则,礼物交换不可能像商品交换那样完全非人格化,因为礼物包含了赠礼者的情感、道德——“礼物之灵”,它们是不可让渡的。二则,礼物交换不仅不可能完全均衡,有时它甚至表达了牺牲与奉献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礼物是无价的,其价值是无法度量的。一个对等的礼物交换行为如同还债,形同拒绝,因此礼物的流行呈现出不对等、不可逆的开放过程。三则,礼物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均衡流动,形成了一种非制度化的、隐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显性的制度理性是一个有益补充。
再次,应该接近礼物的纯粹性。当莫斯为人类没有完全陷入工具理性之泥潭而感到庆幸之时,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回归礼物本性的道路:只有“打开循环经济,尽可能地远离那些义务和礼仪的限制,才是对礼物‘纯粹性’的接近”。(Lucy,pp.43-45)也许只有在礼物不被当作利益交换、求得报偿的功利手段的时候,只是纯粹地为了表达人类的同情、感恩、祝愿等各种美好情感的时候,只是纯粹地出于自己的道德义务感而牺牲奉献的时候,才会是真正的礼物。泰戈尔曾说:“当我们内心充满爱时,只要有一点象征性的纪念品就对我们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它不是为了任何特殊的用途,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为了我们全部的生命,因此它永远不会使我们厌倦。……在爱中,得失是均衡的。……爱将舍弃与接受两种运动带到一起,并且将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泰戈尔,第68-73页)如果说礼物的灵魂是爱,那么儒家礼物观之神髓就是让爱的天然情感在人际之间永恒不息地传递与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