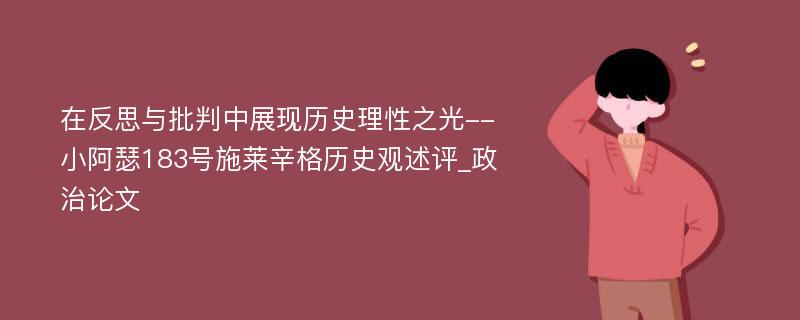
在反思与批判中彰显史学理性之光——小阿瑟#183;施莱辛格史学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莱辛论文,述评论文,之光论文,阿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6-0064-008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Jr.,1917-2007)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多部论著或颠覆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或是相关领域的开拓之作,都曾在史学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①他的学术论著主题贴近时代,叙事生动流畅,在学术界之外也拥有众多读者;他所主编的大量历史、政治论著和普及读物在美国社会亦影响广泛。②在学术园地勤耕不辍、佳作迭出的同时,施莱辛格的从政经历亦十分丰富。他于战后初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③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在多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中担当过重要角色,并于1961-1963年任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特别助理。他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的理论家、民主党的喉舌,他的《核心:自由的政治观》(The Vital Center:the Politics of Freedom,New York,1949)一书被称为“战后自由主义宣言”,他的笔被誉为“美国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武器”,④经常在《哈泼氏》、《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样具全国乃至世界性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时评,还曾被《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可以说,施莱辛格在美国学术界和社会中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施莱辛格长期活跃于美国政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党派倾向,同时他对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有着长期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立场便自然为不少学者质疑。在这些学者看来,《杰克逊年代》的每一页都在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投票,施莱辛格被任命为白宫特别助理以及他后来为肯尼迪家族撰写的两部著作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宫廷史学家”,他用于解释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美国政治周期论”⑤则是为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理论武器。总之,施莱辛格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对他的学术研究倾向有极大的影响,导致其历史研究缺乏客观性,至少是使丰富的历史变得政治化、简单化,⑥有的学者则明指施莱辛格出于政治目的而篡改了历史事实。⑦但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指责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丧失了客观性的同时,他们本人恰恰也落入了客观性的陷阱。难道仅仅由于施莱辛格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公众面前经常以政治评论家的面目出现,甚至由于他学术论著的主题多与政治相关,就能得出此结论吗?这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我们在对一个学者作出评价之前全面和深入地解读其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或许能得出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
一、学术取向的形成
施莱辛格以美国政治为中心的学术取向之形成同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生于1917年,在初具政治意识的中学时代聆听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次就职演说,随“新政”的实施而成长,新政对这一代美国人而言是具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他热切地关注新政及其涉及的重大问题,即经济权力与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反对保守主义对新政的攻击。对现实的种种关切和思考促使他对美国历史中的相关部分怀有特殊的兴趣,对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历史中思想与制度根源的追寻成为引导他早年学术研究的航标。在《杰克逊年代》中,施莱辛格表明,罗斯福新政并非如保守派所指责的那样是同美国历史的根本分裂,抛弃了传统的经济自由与民主而走向独裁或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新政的思想渊源深植于美国精神和传统之中,杰克逊反对尼古拉斯·比德尔和第二国家银行的斗争即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经济保皇主义者”的先例,而杰斐逊主义中已经暗含有“强势政府”的思想,这就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它是随美国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的[1]。《核心:自由的政治观》一书则是《杰克逊年代》中政治争论的延续。在这部著作中,施莱辛格针对美国保守派30年代对“新政”及二战后对“公平施政”、“福利国家”等民主党政府施政纲领的批评,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点,指出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不仅是要保证个人自由,而且要保证人民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权利,该原则在美国的立国文本《独立宣言》和《宪法》中已充分体现[2]。《罗斯福年代》则着重追溯了新政思想如何在吸取老罗斯福“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新自由”两者合理之处的基础上形成,又如何以实用主义的哲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从而贯彻了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精髓并拯救了危机中的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生活方式”的[3]。正如施莱辛格本人在《杰克逊年代》前言中所说,他是在美国历史中寻找民主的含义,探寻在历史中“它展现出多少种可能性?以何种方法建立合法性?其价值观及源流是什么?”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导引下,施莱辛格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理路。
同时,如果仅凭浏览一遍施莱辛格的学术论著目录,就得出结论认为他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都回到了传统的政治史和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从而使丰富的历史政治化、简单化,这无疑也是对“新史学”的一种误解。首先,政治史本乃“新史学”的题中之意,新史学强调扩大历史学的范围,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其目的并非排斥政治史,而是令史学适应当时强大的进步主义潮流而更为民主化,国家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民主化进程自然是其关注重点。其次,施莱辛格笔下的政治史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政治史。他所关注的是传统政治史忽视的人物和群体;虽然他也强调伟人的历史作用,但正如新史学家所言:“‘伟人’仅仅是‘伟大的多数’借以发言的机制。”伟人的作用是领导民众向民主的方向前进,杰克逊、罗斯福和肯尼迪在施莱辛格看来都是劳动阶级的支持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多数”的代理人[4]。最后,施莱辛格的研究方法也不同于传统政治史,他将思想史同政治史相结合,从思想发展、冲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上的政治时代、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新颖的研究理路;他的政治史中还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容,在他研究美国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史的两部杰出著作《杰克逊年代》和《罗斯福年代》中,均有大量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专门撰写的章节,获得了学界的好评。由此可见,施莱辛格的政治倾向固然对其学术旨趣有着重大影响,但因此便一概而论地加以指责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施莱辛格频繁地在政界活动,亲自为多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助选,甚至步入白宫决策圈,更为一些学者指责他在学术研究中缺乏客观性,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提供了口实。但笔者认为,“参与政治实践”与“以历史为政治服务”这两者在施莱辛格身上并没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发生必然的因果联系。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作为一名史学家,同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施莱辛格对自己的双重角色以及自己在履行双重职责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历来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不断对相关问题进行着反思,包括史学家的社会角色、史学家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能否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与公正、如何保持这种客观与公正的态度,以及历史学家能否为政治提供现实的教训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如历史的功能、历史有无客观性、历史有无规律性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施莱辛格虽未对历史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上述问题都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判定施莱辛格的学术立场有否受其政治倾向影响之前,显然必须了解其相关论述。
二、历史的双重功能
历史究竟有何功用,这是史学家常被问及的问题,也是每个具有责任感的史学家都必须加以回答,并在学术研究中时时将其置于脑海中的问题。对它的看法决定着史学家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从多数学者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大多十分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并进一步在其内部区分出数种不同的功能,如知识作用、教化作用、向导作用等等。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施莱辛格还特别指出并强调了历史学作为学术本身的功能。他认为,历史学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即知识功能和社会功能[5]。它首先是一种学术训练,有自己独特的标准、目的和价值观,以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作为自己的理想。同时历史又不仅是学术的训练,它还在国家的未来当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便是历史的社会功能。施莱辛格认为,历史编纂和历史教育是界定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和塑造社会目标的手段,同时也是塑造历史自身的手段,历史撰写已经从学者的沉思变成了一种武器,正所谓“掌握过去的人将掌握未来,掌握现在的人掌握着过去。”[6]施莱辛格指出,历史的两种功能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有时两者会互相强化,现实需要很可能引起史学家对过去进行新的思考,将其注意力引向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和被压制的问题。有时两者则会发生冲突,史学家出于回应现实的需要,很可能被引诱利用过去达到自己的非历史目的。当民族主义牵涉其中时,历史的知识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张力就可能变得格外明显,这是历史的两种功能发生冲突的鲜明例证[5]。
施莱辛格指出,由于只有历史才能建立起国民对国家特性的认同和国家传统的持续性,因此历史本身就成为获得国家认同的武器,利用这种武器是民族主义自身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民族主义对历史撰写的影响程度则多取决于史学家的个性和行为。有的史学家出于民族主义的现实目的去研究历史,却在历史中发现了其本身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民族主义还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和焦点、新颖和有益的视角。但它同时也会产生危险的诱惑,一些利用历史为某种动机服务的人很快被这种动机完全支配,从而变成了贩卖神话的商人而不再是历史的分析者。这两种情况在史学界都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施莱辛格认为,即使是同样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而撰写的历史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学术”的,另一种是“虔敬”的;两者都渴望证明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但前者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颂扬在学术允许的范围之内,而后者则混合了历史和神话;当历史真实和现实动机发生冲突时,前者主张历史真实,后者则弃历史的真实于不顾[5]。
其中“虔敬”的民族主义历史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历史常被用以证明统治阶级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胜利者的历史”,用以证明现有权力安排的优越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由于它为现状辩护,为现存政权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手段辩护,因而又可称为“辩解的历史”(exculpatory history)。另一种历史通常被用以证明当前权力的受害者的存在,这是“受害者的历史”,它为拒绝承认现状的人辩护,通过发明或夸大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荣耀和重要性来证明自己,借以弥补在现实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因而又可称为“补偿的历史”(compensatory history)。此两种历史的共同之处是都会出于塑造未来的目的而利用过去[[6—p48~51]。前者在前苏联、日本和德国都出现过,而后者在美国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中心论”则是其极端形式。
施莱辛格充分认识到,当历史的社会功能与学术功能发生冲突时,不当的处理将会带来何种后果。因此他格外强调要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要认识到历史除了作为建立国家认同的武器,或令人们从中获得教训之外,还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历史的崇高目的不是对自我的表现,也不是对自身的辩护,而是对复杂性的承认以及对知识的探索。”当人们仅仅将它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时,便贬低了历史本身,这是对历史的滥用,同时历史也将由于失去了真实性而不成其为历史[6—p55、72]。
三、客观主义的理想与现实
当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张力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历史的真实让位于为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中寻找合法性的社会动机,那么不论撰述的主体是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抑或是在社会中被忽视、受压抑的群体,产生的都将是非学术的历史,这显然与历史学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相去甚远,是对历史的贬低和滥用。然而,即使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之中的史学家恪守学术道德,写出了“学术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知识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是互相强化的情况下,历史撰述是否就能达到其完全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呢?施莱辛格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他认为,历史学家永远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之中,他们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自己职业的标准,却又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事实最终是无法接近、也无法恢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史学家与每个普通人一样,都是时代的创造物,是“自身经历的囚徒”,因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应该十分明了自己的事业并不是完全中立或客观的,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即便他尽其所能研究过去,却无法逃避自己的现在,就像人类无法逃避原罪一样。每一代历史学家对现实都有不同的忧虑,并因此对过去有自己独特的需要[7—p373],在史学家研究过去的过程中,“我们用来照亮过去黑暗的聚光灯由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所引导。当新的关注出现在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中时,聚光灯的方向就会改变,照亮始终存在着、但被早先的史学家排除出集体记忆的事物。”[6—p46]在施莱辛格看来,历史事实处于过去的黑暗之中,无论史学家是否去关注它们、研究它们以及如何去研究它们,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但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是远离现实而无法触摸到的,必须通过史学家这个研究主体才能被人们所认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就像照亮历史的黑暗的聚光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出于不同的关注在历史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像聚光灯的方向不断地变化。聚光灯永远无法在同一时刻照亮所有的黑暗之处,它所指向的地方成为时代关注的热点,也似乎成为人们眼中历史的全部真相,而其他事实就被排除出集体的记忆而隐藏于历史的黑暗中,无法被人们所了解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史学家总是在按照自己所处的社会的倾向和需要去从历史中获取事实或反映历史。就此意义而言,现在重新创造着过去[6—p46]。
不过,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获得的,但他却不像“现在主义”派宣扬的历史相对主义那样认为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撰述工作是一种先验的活动,是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实现,是历史学家主观上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构造出来的。施莱辛格眼中的历史学家在历史撰述中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是史学家保持客观理想的努力在客观上受到时代的限制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施莱辛格虽然认为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是难以获得的,但他坚持指出,历史学家即使永远不可能完全成功,仍然必须努力超越现实,这是他们的职业职责[7—p373]。虽然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客观理想,史学家仍然是特定价值观、特定标准和特定传统的保护者,必须致力于实现批判性的分析、准确和客观的理想,而不像小说、儿童读物、政治演说或道德小册子的作者那样可以在没有历史论据的情况下创造英雄形象和反面人物。面对为满足社会动机而放弃历史真实的“糟糕的历史”,真正的史学家所应该做的不是从另一个角度撰写更多糟糕的历史,而是撰写更好的历史,更彻底、更有判断力、更精确的历史。施莱辛格承认,在某种意义上,非客观性的观点在历史和社会中是很难避免的,但史学家必须在洞察力和资源都极有限的情况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获取历史的真实。如果历史学抛弃了这一追求,抛弃了真实地重建过去的理想,即便是以道德为借口,或者以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为借口,那么不仅将距历史学的理想越来越远,而且还将摧毁社会中能够防止非理性蔓延的防线,而人类自身发展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有效地利用人最独特的能力——理性。虽然永无可能逃脱自我中心的困境,永无可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和环境的限制,但在对真理的理性探询中经历的批判性过程将使人类有机会向更健康、人道的社会前进[5]。
在历史上,曾有不少史学家乐观地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可以将主体完全消灭,史学家只需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便能获得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也有很多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认为所谓的历史事实只是史学家的创造。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关于历史认识的正确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也不可能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而施莱辛格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观点既肯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又对历史学的相对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既强调历史事实的真实叙述,又不否认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撰述中所起的作用;既肯定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又认识到这种主观性受时代和个人经历等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勇敢地承认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必然带有偏见,这种关于历史认识的科学态度对史学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立足于这种科学的态度,认识到自己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可能带有的偏向性,才有可能尽量避免这种偏向。
四、历史能预测未来吗?
历史研究能否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学家能否在公共领域起到作用,历史教训能否给政治家以教益从而令他们在决策中更为明智,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对某些史学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但认为历史研究能够且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且主张现实需要在历史撰述中应占据特殊地位,甚至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直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但施莱辛格作为一名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史学家,对此给出的却是否定的回答。这初看似乎并不合理,但如果我们了解施莱辛格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如历史作为一种预测手段成功与否,历史是否应该为人们预测未来,历史的发展过程有无规律可循等等,就不难理解这一立场。
关于历史是否一种成功的预测手段,施莱辛格认为,史学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史学界内部,职业史学家就整体而言对历史的预测功能并无幻想,他们研究历史并非出于预测未来或是其他功利的目的,他们比局外人更明白历史的训练不会确保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自动获得智慧。施莱辛格指出,无论是基佐、班克罗夫特、马考莱、梯也尔还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史学研究的训练都不曾对其政治生涯产生多少影响。但在史学界之外,一些面对同行会十分坦率地承认历史研究并不具有预测功能的史学家却常会以堂皇的理由证明自己的有用之处,教导人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掌握历史知识能对未来提供正确的指导[8—p524~525]。对此施莱辛格是表示怀疑的:“在什么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为何历史应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这就牵涉到进一步的问题,即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循,有无可能对其进行归纳性分析。施莱辛格指出,某些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历史知识能够对未来提供指导,是因为他们假定历史现象是多次重复的,因此人们有可能对其进行归纳;而在积累了足够多的历史归纳并将其互相联系,便可以产生洞察未来的能力。针对这种观点施莱辛格指出,迄今为止多数职业史学家都否认归纳是历史研究的目标,而是致力于研究个别事物,致力于具体地重建过去而非抽象的归纳,致力于研究“生活”而非“规律”,事实上这正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区别[8—p525]。
不过他指出,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绝对独特的理论同样也是荒谬的,即便那些否认历史规律存在的史学家也承认历史中会有一致和重复之处;历史归纳虽存在缺陷,但仍然可行并确实可能加强政治家处置未来的能力[8—p525]。只是在进行历史归纳时须注意,历史通常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榜样,它教导人们的不是必须做某些事,而是不能做某些事,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人们往往会在现实中进行某种历史“类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治领导人从慕尼黑会议及协定得到的历史教训是: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大陆均势体系中对一个高度武装的极权主义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很有可能打破权力均势,并使进一步的侵略行为难以避免,这便是一种历史“类推”。但就此便认为所有通过谈判来避免战争的企图都必然成为“慕尼黑”,显然是错误的。这便是机械地进行历史“类推”的危险之处。事实上,世人以避免“慕尼黑错误”为名而犯下的错误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次错误本身,比如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便常常使用不合理的、被曲解的历史归纳,根据成见来制定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桑塔亚那的那句格言应该反过来说:常常正是那些能够记得过去的人必然会重复它[8—p528-530]。
历史类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有效的,施莱辛格赞同历史比较大师汤因比的看法,史学家“永远不可能保证我们正在进行比较的实体就调查目标而言在严格意义上是可以比较的。……无论我们进行比较时在两方面成功地发现多少组同一的样本,我们也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忽视一些不同的因素,并且这一不同因素不是解释不同案例中出现不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案例在我们看来本是情况相同,但实际却并非如此。”[8—p531~532]施莱辛格认为,大多数有用的历史归纳都是关于长时期内大规模的社会和思想运动发展规律的叙述。人们可能对社会发展作出大范围的、长期的预测,但不能提供小范围的、短期的预测。因为短期的预测必然是细节的预测,会由于事件的复杂和难以预料的不同事件之间的交叉、碰撞以及人的自由意志而存在过多的变数,导致无法进行准确的短期预测,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未曾被人们预见到的原因所在。施莱辛格认为,历史绝没有给人们提供获得敏锐洞察力的捷径,而是令人们认识到未来充满了惊奇,“历史研究产生的不是科学的精确,也不是道德的定论,它产生的是讽刺。”[8—p532]正因为如此,历史只适于回答长期趋势问题而不适于进行短期预测。但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者却很少对“长期”感兴趣,而通常关心政策的短期后果,因此政治家对史学家提出的通常是历史最不适于作出回答的问题。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施莱辛格认为历史是无法像某些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在公共决策中起到直接作用的,相反还常会起负面作用。面对政治家所谓的“咨询”,历史学家常常会成为替政治家寻找证明其决策正当性的理由的工具,这与历史学家参与公共领域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拒绝了解历史的理由,而只是提醒人们,对历史仅有肤浅的了解却妄想从中获得智慧是绝无可能的。在施莱辛格看来,历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历史的可能性比人类智力所能想到的要远为丰富和多变,简单的历史类比决不足以洞察这样一种过程。只有更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产生对事物的诊断能力而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产生对事物的洞察力而非透视问题的捷径[8—p534~536]。因此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有效影响在于通过努力思考根本的问题来提供根本的答案,而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尽其所能写出最好的历史,并相信倍数效应。”思想者只有在思想时才是最强大的[9]。
美国虽然是一个极为注重历史研究的现实效用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在有人提倡使过去从属于现在,从现实出发来研究历史,甚至不断有史学家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乃至进入最高政府决策机构的同时,也不断有学者质疑历史学的现实功用和学者参与政治实践的行为。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提出,政治积极分子和学者这两种角色并不互相排斥,其中多数人认为,学者在一个时间段内应该只承担一种角色,而不应该将两种角色混同起来。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学者能否将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截然分开呢?学者对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是否必然影响到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客观公正呢?
对此施莱辛格并未仅仅回答是或否,而是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的功能、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及历史是否具有规律性等问题作了解答。而在剖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这个主题始终萦绕在他脑中。他不想躲在象牙塔中与现实隔绝,同时充分认识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可能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就某种意义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思考和梳理,为自己的双重角色建立合理的前提,也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建立一个合理的前提。他承认自己和普通人一样是现实的囚徒,因而在学术研究中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客观,但即便如此,史学家仍然要尽一切努力超越现实,追求客观地重建过去的理想。为此,施莱辛格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首先必须履行历史的学术功能。他充分反思了历史研究的特性并不时提醒自己,历史并不具备进行短期和小范围预测的能力,并且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如此之复杂,其丰富和多变性远非人类智慧所足以预料,因此虽然历史可能使人更明智,却绝不适合政治家的现实需要。当然,重视历史的学术功能,强调史学家应该在学术研究中追求客观主义的理想,并不意味着要在现实中放弃对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而只是让学者们意识到作为史学家和作为政治积极分子的区别,并促使他们决心将这两个角色加以分离。在施莱辛格看来,史学家具有现实关怀是一回事,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也是许多学者的共识。
何兆武先生曾经慨叹:历史永远有,而人们对历史的警觉并不常有。⑨历史学这一古老的职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却未必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即便是在当代,也并非每个史学家都能自觉地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当一个史学家充分认识到介入政治可能带来学术偏见,认识到史学家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客观主义理想的时候,不仅不会有意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且会自觉地提醒自己在研究中保持客观的立场,在收集、辨析、使用史料和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会更为审慎,在历史事实和社会动机发生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无法证实施莱辛格在历史撰述中能否完全保持客观立场,更何况就某种意义而言,完全的客观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同那些对自己没有自觉自律的学者相比,他必然能更好地处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写出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
注释:
①其首部代表作《杰克逊年代》(The Age of Jackson,Boston,1945)大胆反驳了当时美国史学界如日中天的边疆学派对“杰克逊民主”的解释,提出杰克逊民主的真正动力源于日益城市化、工业化的东部,而不是蛮荒的西部边疆,且更多表现为阶级之间而非区域间的冲突,在学界引起激烈争论,使年仅28岁的作者声誉鹊起。该著作于次年获普利策历史著作奖。1956-1960年间出版的《罗斯福年代》以宏大的时代背景、时代思想的全面展示和论述的充分有力在同时代众多有关“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著作中独领风骚,影响了一代公众和学术界的见解,并成为后来许多史学论争的基础。其中《旧秩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Boston,1956)一卷同时获弗朗西斯·帕克曼奖和班克罗夫特奖。他为纪念肯尼迪兄弟而撰写的《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1965)和《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Boston,1978)均获国家图书奖,前者还获普利策传记奖。他在“水门事件”后出版的《帝王般的总统》(The Imperial Presidency,Boston,1973)一书以其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到的视角广受学界赞誉,在研究总统制的众多论著中独树一帜。
②施莱辛格主编或参与主编的著作主要有: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New York:Chelsea House,1971; The Coming to Power:Critical El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Chelsea House in association with McGraw-Hill,1972; History of U.S.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in association with R.R.Bowker Co.,1973;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73,New York:Chelsea House & McGrawHill,1973; Congress Investigates,1792-1974,New York,Chelsea House,1975; The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3;The American President Serie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2-1994; Running for President:The Candidates and Their Imag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4.
③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简称ADA,是美国的一个独立自由主义政治组织,成立于1947年,创始人包括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1953-1954年,施莱辛格曾任该组织主席。
④Allen J.Matusow,"John F.Kennedy and the Intellectuals",Wilson Quarterly 7(Autumn 1983),142; Thomas Axworthy,"Politics on the Seesaw",Macleans,April 6,1987,p.50.转引自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i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4,pp.x,5.施莱辛格在阿德莱·斯蒂文森、约翰·F.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乔治·麦戈文的竞选班子中都是重要的成员。
⑤“美国政治周期论”是施莱辛格继承前人学说,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充实、发展起来的理解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宏观理论框架。该理论假定,美国历史周期性地受“公共目标”(public purpose)和个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情绪的左右,当公共目标占主导地位时期,自由主义思潮上升,政府推行积极干预政策,民众被号召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而在受个人利益支配的时期,保守主义思潮上升,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民众对空洞的政治口号感到厌倦,开始追求自我实现。所谓的“政治周期”即国家在“公共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持续不断运动的过程。在整个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内在矛盾产生,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某个历史事件便会成为导火索,引发美国社会中相反情绪的爆发,从而推动美国社会进入政治周期的下一个阶段。这种周期是自生、自动的,具有一种独立性,其阶段性变化不受外部事件干扰;它不是在两个固定点之间的运动,而是螺旋形状态的运动,每一次循环都在更高的层面进行,并且每一次循环都将使美国社会更为接近“公共目标”的一端。另外,在循环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各种新的因素。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p.27-29,31.
⑥Sean Wilentz,"The Vital Centrist",The New Republic(December 25,2000),23-28.参见Arthur Herman,“High Priest of Liberalism”,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8,2000),45-48; James Nuechterlein,"The Last Liberal",American Prospect,Jan.29,2001.Stephen P.Depoe,Arthur M.Schlesinger,Jr.,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4,Preface.William E.Leuchtenburg,"Review of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1919-1933",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3,No.3(Sep.,1958),460-463.
⑦在众多学者中,诺姆·乔姆斯基对小施莱辛格的批判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他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曾同施莱辛格发生过一系列激烈的论战,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Violence:America in the Sixties,New York,1968;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Ideas,Power and Violence in America,Boston,1969,以及施莱辛格与乔姆斯基在Commentary(December,1969; June,1970)上的评论与回应。在《反思肯尼迪王朝——肯尼迪、越南战争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Noam Chomsky,Rethinking Camelot-JFK,the Vietnam War,and US Political Culture,Cambridge:South End Press,1993.)中,乔姆斯基认为施莱辛格等“肯尼迪圈子的主要知识分子”为替肯尼迪辩护而“修改了历史记录”,并详尽地列举了他认为被“修改”之处。
⑧详细论述可参见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in John Patrick Diggins ed.,The Liberal Persuasion:Arthur Schlesinger,jr.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Pa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9—42.
⑨参见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三联书店,2003年,代译序。
标签: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施莱辛格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客观性论文; 新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