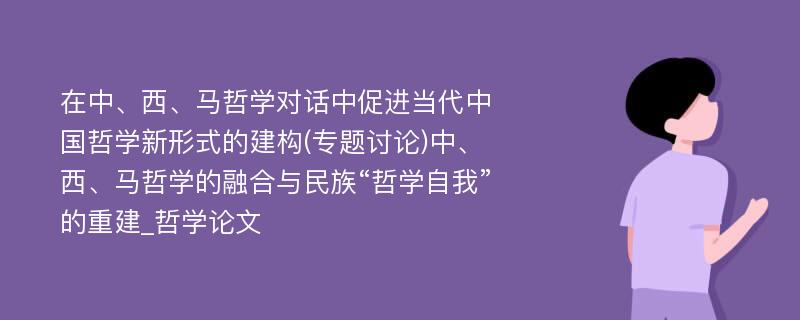
在中、西、马哲学对话中推进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专题讨论)——2.中、西、马哲学的融合与民族“哲学自我”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在中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要创造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基本共识。但如果把问题引向深入,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思考:中、西、马哲学对话与融合的内在根据和基本目的是什么?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实质和内涵究竟是什么?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度思考,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就有可能流于外在化与形式化,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也有可能沦为一种标签化和流俗化的“意见”。
要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切实的回答,我们必须从一个更高的思想视野出发。在我看来,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在深层是与我们民族哲学特殊的历史遭遇与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构成这种历史遭遇与命运核心的便是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危机以及对“哲学自我”重构的迫切要求。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危机,是中、西、马哲学对话与融合的内在背景与根据,而“哲学自我”的重构,则构成了中、西、马哲学对话与融合的根本追求与目标。
这里所谓“哲学自我”,指的是中华民族以一种哲学反思的方式所表达的对于自身命运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生命境遇与生存意义的自觉理解,这其中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梦想,凝聚着其对于生命意欲与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信念。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把哲学视为一个民族的“思想之镜”或“思想自我”。由于哲学所具有的这一本性和功能,不同民族的哲学总是呈现出不同的思想个性,英国哲学与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俄罗斯哲学与意大利哲学等等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具有不同的民族个性。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我们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生命历程与发展前景,对此进行深入的反思,形成系统的自我理解与自觉意识,这就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哲学自我”。
在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哲学一直是中华民族占据主导地位的哲学形态,它立足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表达着我们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凝聚着我们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与人生态度的悟觉,是我们理解世界、把握社会历史、领会人生意义的内在根据。这种哲学形态是与我们的生存样式与生活世界基本相适应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为这种哲学样式提供着深厚的生活土壤,哲学则为这社会结构与生存状态提供着思想上的支持,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就此而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是“自足”的,它表达着民族的自我认同,承担着人们生活意义的支撑与根据,因而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哲学自我”。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生存样式的危机相伴随,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地位和功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随着中国现代性程度的日益深入,这种挑战日益严峻和难以回应,并因此使传统哲学作为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地位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
这种危机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难以对迅速变动的中国现实生活作出充分的理解和阐释。社会结构的分化、民间社会的被改造、生活世界内容的变异、生存方式的复杂化等等,这些中国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需要哲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并提供合理的阐释。传统哲学虽然曾经与传统社会水乳交融,但在这种变局面前,它已经失去了社会制度与生活基础的根据,因而显得力不从心。其次,它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已难以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充足的思想资源与引导。在传统社会中,传统哲学作为“唯一必然之神”充当社会生活的合法性根据,引导着人们对生存意义和生命目标的诠释。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之区别于传统社会,在于它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世界的“祛魅”意味着“唯一必然之神”的消失并使得“价值的多神化”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在此情境下,中国传统哲学已不可能享有它以往曾有的“独尊”地位,扮演以往曾承担的“立法者”角色。
因此,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危机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产生的。克服这一危机,重塑“哲学自我”,也必须置身于这一历史方位之中。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现实道路、重建我们的“哲学自我”,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课题”。
之所以把它称为“现代性课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面临的特殊的思想境遇。与中国传统哲学失去其主导地位相伴随的,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空间中同时“在场”,形成了当代中国哲学领域特有的“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形态,那么,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哲学思想产生了异质化与分化,出现了三种来自不同思想传统、代表着不同价值信念的哲学形态。这就造成了我们所面临的一种悖论性的思想境遇:一方面,是现代性进程中“哲学自我”的危机与“哲学自我”重构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是异质性的哲学传统的同时“在场”。在这种复杂的思想局势下,重构“哲学自我”的现实道路如何可能?
我认为,正是这一思想任务,为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内在的依据。面对这一思想课题,中、西、马哲学中任何一方如果试图脱离其他二者,把自身孤立化与实体化,以之作为唯一的基础和根据来重建民族的“哲学自我”,都是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所处的特殊思想语境相违背的。除了通过三者的良性互动,在三者的对话与融合中,寻求重构民族“哲学自我”的现实道路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具体而言,这一论断包含两层基本含义。
首先,它所要强调的是,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的对话,是与克服“哲学自我”的危机,重构我们民族的“哲学自我”这一根本任务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构成了其根本目的和终极旨趣。就此而言,通过中、西、马哲学的对话,来探索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不是某种形式性的要求与主张,更不是以“新”作为时尚和标榜,而是内在地包含着一核心性的指向与鹄的,那就是要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重新确立与我们民族地位相称的哲学个性,生成我们的思想自我。这一点,构成了把三者相互联结起来的共同纽带或基础,离开这一点,三者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化的“拼凑”与“相加”。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论断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在“哲学自我”的重构中,中、西、马哲学三者各自承担着特殊的职责,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互补”的关系,因此,三者的对话与融合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换言之,在当代中国特殊的思想语境中,中、西、马三种哲学形态在“哲学自我”重构这一使命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三者的对话与融合,是实现“哲学自我”的创造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由于哲学起源于人对于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活意义的反省,它代表着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社会生活的永不停止的反思批判活动;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理论。因此,一个民族的“哲学自我”实质上就是它对自身独特的生命特质和生活经验的自我反省与系统觉解。当我们说“哲学自我”危机的时候,也就是说这种自我理解与自觉意识出了问题。与此相应,当我们说要重构“哲学自我”的时候,实质也就是要重新建立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与生命存在的自觉理解。正像福柯所说的:“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①以哲学的方式来对“我们是谁”作出个性化的回答,实现对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深度透视,也就是重构“哲学自我”的核心含义。
在我看来,面对理解“我们是谁”、重构“哲学自我”这一课题,中、西、马哲学各自代表着一个不可相互替代但同时又都“有限”的“扇面”,在对话中实现三个不同扇面的“视界融合”,是切中这一课题的根本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哲学自我”,但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它失去了这种功能并使我们的“哲学自我”处于危机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于今天我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失去了价值。我们从历史中走来,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面,蕴涵着当代中国人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传”与“文化基因”,因此,它始终是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世界的面貌,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理解和阐释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样式,又是“不够”或“不足”的。这种不足内在地要求它向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敞开。西方哲学,尤其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是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培植和生长同步而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映照和哲学表达。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推进以及世界交往的日益深化,西方哲学所映照和表现的生活基础,已日益成为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融,将为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自我理解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西方,但传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来,它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占据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除纯粹学术理论之外,它还在生活实践中承担着推动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创新、促进社会进步等重大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要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源泉。可见,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状态的自我理解与反思中,都发挥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的作用,三者中任何一方的缺席,都意味着我们在自我理解与自我反思上一个重要维度与视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因而将直接导致“哲学自我”重构的失败。也就是说,在克服“哲学自我”的危机与重建“哲学自我”这一重大问题上,中、西、马哲学三者在价值上拥有平等的地位,它们从不同的扇面出发,服务于“哲学自我”的重构这一共同目标。这一点是三者进行良性对话与融合的前提与基础。
回顾历史,在中、西、马哲学的关系上,所存在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对上述三者在价值上所拥有的平等地位缺乏自觉的认识,使得三者难以实现彼此的相互承认,并使它们之间真实的对话与融合变得困难重重,重构“哲学自我”这一当代中国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也因此而被再三耽搁。这或者表现为把中国传统哲学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位置,认为它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本位”,在价值理性上拥有比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高的优越性;或者表现为把西方哲学置于价值等级的最高位置,认为它代表着哲学的“正统形态”,规定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概念框架与思维方式,因而,在寻求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重构我们的“哲学自我”这一问题上,它占有着根本的、优先的地位;或者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与绝对化,而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只有资格充当“哲学史”,为哲学的发展提供“资料”与“文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上占据着无可置疑的制高点,因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拥有最后的裁判权。很显然,当三者这样把自身实体化与中心化的时候,必然不可能承认“他者”独立的“主体”地位,三者之间必然是一种相互排斥与对立的关系。在此情势下,中、西、马哲学三者是不可能真正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向他者敞开,并因此形成一种创造性的对话与融合关系的。
如果同意前述讨论,我们就会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自我”的创造,是中、西、马哲学三者面临的共同课题。在这一共同课题面前,中、西、马哲学三者中的每一方既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视野和资源,同时又不足以提供唯一的终极答案,它内在地要求三者各自超越自身的视界,在“他者”的面孔中敞开自身,通过三者无止境的对话与融合,催化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发育和生成。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中、西、马哲学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历史障碍将涣然冰释,三者之间也将真正形成一种“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创造性的对话与融合关系。
注释:
①转引自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