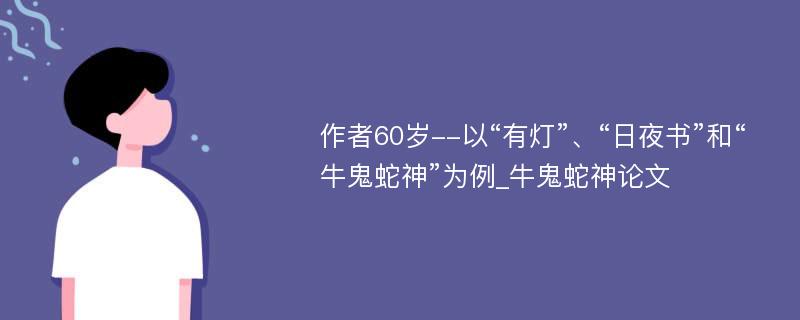
作家六十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牛鬼蛇神论文,为例论文,日夜论文,六十岁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到2020年,50后作家们都将先后步入六十岁,中国俗称“花甲”之年。《论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而耳顺。”郑康成注:“耳顺”,闻其言,而知微旨也。皇《疏》:“但闻其言,即解微旨,是所闻不逆于耳,故曰耳顺也。”由此可知,“耳顺”就是耳的功能已经通顺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故能闻他人之言,即知他人的心意。此是耳闻无碍之境。一方面是古人的耳顺之年,意味着再没有听不懂或者逆耳的话。另一方面,六十岁可以退休了,接近颐养天年的年龄了。对早熟的中国人来说,还有“人生三十不学艺,人生四十午过天”的说法。这种心理暗示,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
2012年、2013年,贾平凹、韩少功、马原先后步入六十岁。贾平凹在《带灯》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他焚香默念,向母亲祝祷自己的六十岁,并祈愿新书《带灯》圆满完成;韩少功则半带调侃地对记者说:到了这个年纪,快完蛋了,快退场了,因此更应珍惜时间,善用自己的体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他把这部《日夜书》当作献给自己这代人的纪念,“中国的知青和老三届都要60岁了,很多人都陆续退休了。所以我通过这部小说来做一个回顾,而且也正是合适的时候”。马原更是因为诊断出罹患绝症,声称在六十岁来临之际,对生命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并以此为契机,重回小说界,有了这部《牛鬼蛇神》……
那么,这三位最早步入六十岁的作家,在献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三部长篇里,是否带有一定普遍性规律性地折射出中国作家六十岁所呈现的写作状态。当然,这三位作家无疑位列当代文学最活跃、最具革命性及最有各自特征的成员之中。他们分别从三个面向,向读者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及对当代小说的贡献:贾平凹的语言才能、韩少功的思想功力、马原的形式实验,(众所周知,莫言、余华、苏童等一批作家都自有贡献,此文专论贾、韩、马三人)对当代文学体貌的塑形进程产生了影响。当然,在这里专提贾平凹的语言、韩少功的思想、马原的形式,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他方面不强势。比如,贾平凹自《废都》起,就以社会观察家的敏锐和深刻为其小说的思想底蕴作支撑。他的每一部长篇,都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关键词或照相式总结。韩少功对语言之关切及理性觉悟,也许是当代作家中之最,他自2004年起就撰文《用语言挑战语言》《现代汉语再认识》《韩少功:语言的表情与命运》来讨论语言的问题,《马桥词典》《暗示》更不用说是对语言本身的思考与想象;除此之外,韩少功还是一个文体实验高手,他自《爸爸爸》起就开始借鉴现代派表现手法,到《马桥词典》的革命性文体尝试、以及《暗示》到底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形式也总是力争超前。马原的形式实验,实际上同时依赖于他小语言材料的组合技巧及他的语言轻易就能达到的中国作家一般难以达到的轻灵状态。而《牛鬼蛇神》中对于生命VS科学的思考思辨,也将马原式思想的资源及妙趣展露无遗……
但是,贾平凹的思想较之于他对语言的使用与追求,语言显然是他的第一性;韩少功尽管三十年来都在跟现代汉语较劲,且具有超强的形式感,但比较于他对思想的执着和狂热,思想才是他的生命线;马原的叙事圈套,故事达人的形象,则依赖于他对小说结构形式的天赋与精研,形式才是他的小说本质。
那么,在他们三十年的时间里充分展示各自小说魅力,到今天迈过六十岁,三部近作是否正体现出一种艺术上的保守甚至一成不变?当年创下品牌的各自优势正在渐渐失去曾经的新鲜和独特?艺术增值的空间随着生命激情和灵感冲动的减弱而付之阙如?是整体想象的失却导致世界和生活的支离破碎,使写作几乎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人们不再需要阅读文学或故事,作家也对世界失去象征建构的雄心(这已经带有堂吉诃德的乌托邦色彩了)?……本文试图从长篇小说《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来解析讨论以上问题。
一、贾平凹:靠语言拉动的小说群
对贾平凹的评价,业内早有公认。他也早已凭借其三十多年的高产写作,牢牢地奠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学的地位。已经耳顺之年的贾平凹也许也想听听来自他方的、不同的意见或建议。当然,前提是善意的。一部《废都》,西部鬼才震撼出世。那样一种敏锐、深刻,力图把握一个时代一座古都的宏大野心;那样一种古色古香、秦陇沧桑的语言,震惊得世人纷纷侧目。贾平凹是从明清世情小说最得益,也研究得最深透的,若干方块让无缘看《金瓶梅》的看客趋之若鹜,销售量逼迫正统的评论界承认这部小说的价值。此后,贾平凹推出了《浮躁》《高兴》《秦腔》《古炉》到《带灯》,这许多长篇,每一部出来必引发极大关注,得奖也得的不耐烦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历经伤痕、寻根、意识流、拉美魔幻、先锋派、新写实主义、现代派、荒诞派、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流行方法,似乎都难以跟贾平凹扯上更多的关系。如果说他也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或内容,毋宁说更像是中国古代神怪志的表现(《秦腔》《古炉》里均有此类内容)。该作家的艺术个性及其稳定性,在当代作家中堪称独步。如果说贾平凹有什么创作神器,他的语言才能及其独特风格应该当之无愧。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凭借着超乎寻常的语言才能及独特风格,贾平凹创造了自己的叙事奇观,并使其语言本身成为奇观现象。语言的超强张力及惯性使贾平凹保持着高产,并“不落伍”的文学地位,语言拉动起他的长篇小说群。
《带灯》以细腻的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笔法,更加靠近传统小说:讲一个主导叙事动机的故事,有中心人物带灯,并力图使她鲜活生动、性格鲜明。故事以悲剧收场,令人感动感慨。《带灯》所表现出来的乱象,涵盖了当前农村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基层社会究竟应该怎样管理和服务、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基本权益谁来保障,贫困群体以及农村养老……还有与此相关联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和社会公正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消费、娱乐的文本海洋中,有作家原原本本地还原当下农村的真实生活,本身变得有价值。但一部作品不能因为它内容上的道德优势而免于艺术上的被弹劾。读者要问的是贾平凹此次艺术上的突破在哪里?也许再没有比作家本人更明了自己的局限,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他要从明清品位向两汉品格努力转身。遗憾的是,转身这个动作,到《带灯》的最后一个句号,还只是在意识里。
贾平凹这一次似乎解决了他小说过于散文化,人物脸谱化(与《秦腔》比较)的不足,却解决不了曾经带给他一夜暴红的语言问题:他写什么都以明清世情小说的叙事调子,与当下大转型快节奏大破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他的语言神功再也不能助他弥合这分裂的生活和精神。
贾平凹写什么都以明清世情小说的路数来写,这种路径依赖是否已经正在失去它的土壤?时间过去了百年了呵。这“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的细碎泼烦,农民式思维控制下的句法结构(句子经常很突兀地没有主语,随意跳散),以及整个长篇其实以陕南方言的话语结构铺成,更兼作者一贯的古典情调和一派的精致逸韵,致使其在难读程度及阅读感觉上跟《金瓶梅》这样的明代小说有得一拼。当然,小说家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大众保持他认为的艺术之为艺术必须要有的距离和难度是明智之举。伟大小说从来不是让你一次毫无障碍地读完的,伟大小说甚至是不可以读完的。《芬尼根的守灵夜》是治失眠的神器,中国也应多产生一些这样的治失眠神器。但遗憾的是,《带灯》的语言,在着力营造一种古中国情调上,与《秦腔》等一脉相承,成为贾平凹标志性语言风格,但此风格耽留在一个段位上的时间太久了。贾平凹既然可以在保留古中国韵味上做得很好,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并可以去大胆地尝试一下艺术上的冒险?明清世情小说那一路的叙事调子能不能从当下、从外国的叙事成就中找到可为己用的部分,化出一种更新鲜、强健、理智、丰沛的表达?
乡野生活俗归俗,也有文人式的雅化文字来描绘,字里行间都透着乡野士大夫清高自许的品位,比如:经常游离出叙事的闲笔,此等闲情逸志就是兼攻书画的贾平凹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一个无名作者写成这样个性卓然,大概是不会有出书机会的。每个画了黑框的片断,当然使阅读单位分割小了变得容易且醒目,既符合我们这个一切都零散化的后现代美学要求,但更实际的作用是不是相当于电影的分镜头?
人们常批评说贾平凹的小说节奏太慢,他粘着于细碎日常情节没完没了当然显得故事推进无力,节奏太慢。他就是要粘着于日常生活细碎地往前移动,只有这样,作家才能找到他写作的自信和基础。但现在情形是,《带灯》的句子,动词一个追一个,话赶话快捷无比,从细部看,他一点也不慢,动词的推进力度使人以为要发生大事情了,但结果没有。小说的结构方式就是不搭架子地混沌一块地往前推,整个地看起来就像一个千足虫在行动:无数个小细腿代表那些了不起的动词和动作,它们多且眼花缭乱地在动着,而整个沉重的肉身却并不得益于这些细小的腿。这是贾平凹的文字炫技了,只有那些写到一定程度,把文字玩到精熟的作家才有这个本事,但这一本事也许就是熟能生巧的惯性,且此惯性却是于文本并无更大创新或贡献的悲哀?
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清时的中国是小农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比现在缓慢悠闲,文人的内心节奏在依时气而歌而画时,也是悠闲从容的,文人和艺术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和谐。而现代生活的时间感是破碎零散的,节奏是加速的,人们早已被物化、异化,意识观念也早已不是明清时的意识观念,语境早已不是明清时的语境,而作者还在用明清时的调子讲述现在的故事,工具会不会老化不适用?这是为什么《带灯》的语言风格表面上古色古香,而作者的内心节奏早已被现代生活控制——一个追一个的动词和动作被写出来,而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却在内部破坏作者一意要酝酿的古典情调,那种宁静和谐、松弛悠闲的韵味。由此,一种分裂症或不适应症就这样表现出来。古调难以调和新韵,文字和内心难以达到同一的境地:心里已难再有古风,而文字还在一味地仿古?
二、韩少功:被思想绑架的辩证癖
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是《韩少功研究资料》单正平作序的第一句,并且一句话自然成段,充分传达出这句话的分量。他接着写道:“他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3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每一重要阶段,韩少功作品均为其中不可或缺之重要组元:《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之于‘伤痕文学’,《爸爸爸》之于‘寻根文学’,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于反思现代主义的‘媚俗’风尚,《马桥词典》之于小说叙事艺术,直到近年新作《暗示》《山南水北》之于新世纪小说路向与散文创作,无不具标志性甚至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或可说:读韩少功,30年中国文学,知过半矣。”
这段概括性评价不算过分。韩少功当之无愧已成为有定评的经典作家。尽管这段评价略除了对《暗示》,甚至韩少功最了不起的作品《马桥词典》的一些批评和争议。如果事事求全,左右衡量,这序也没法写了。诚如他所述,韩少功分别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跃居中国当代文学最前沿,或引领潮流,或别开生面,千禧年的十年里也以散文《山南水北》的结集,宣告着这位“思想型作家”始终没有停止对当代社会、文学、文化尤其是思想的思考。这也是他得到业内格外看重的重要因素:韩少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比较少有的以思想见长的作家。“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创作,都与当时的思想主潮紧紧相扣,是中国知识分子30年来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一个代表,从‘反思文学’到‘先锋派’,从《百年孤独》的传入到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分化,在他那里都有反映。”(清秋子语)“韩少功的小说诗学,将韩少功的小说中蕴含的东西抽象为一种完整的辩证法,有着独特的思维模式。”(石晓岩语)“韩少功是一位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家,一位主要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当代思想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韩少功的世界中,文学与思想相互滋养,文学因而深刻,思想为此而丰润,文学的边界被拓宽,思想的形式被超越。”(何吉贤语)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等于“难度”,或令评论家们失语,或令批评家们发怵:韩少功自己的精深透彻、雄辩之风,让试图诠释批评他的人显得多余和赶不上趟。厚厚一本《韩少功研究资料》里,很多的分析评论并未超过韩少功本人的阐述,而很多评论者实际上是在亦步亦趋地对韩的自我说法的跟踪。
说《马桥词典》抄袭模仿,现在看来纯属无聊的非文学低智口舌。个人收藏《马桥词典》的最早版本,并以为该书是韩少功最了不起的文学创作,也是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90年代最有价值的文本之一。但一个作家是有限度的,韩少功自《爸爸爸》一飞冲天,到《马桥词典》,个人在小说艺术上的高音华彩呈示完毕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少功的思想出现了徘徊,也许是对有些问题没想清楚,因而未能再产生像《马桥词典》那样深刻的作品。对此,相信不少人都抱着热切的期待。”这句在韩少功海南作品研讨会上的评价,婉转地道出人们对《暗示》的失望。《暗示》,不过是《马桥词典》的遗绪。作为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哲学类思想随笔或者随想录,《暗示》尽管更加的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文体实验的革命性冲动、卖弄思想,尤其是辩证法思想的雄辩滔滔,都令这部长篇很难归于小说范畴,也尽失《爸爸爸》《马桥词典》所表现出来的诗意、象征、形象、情感以及内在整体性等文学性属性。
到了六十岁而作的《日夜书》,距离《暗示》又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里,长篇笔记《山南水北》的写作,让韩少功写出了笔记惯性。《日夜书》虽被作者强调:是小说。但看起来仍然恍若一个大拼盘、一堆思想的碎片。韩少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语言的思考,我觉得在前两部长篇中已经告一段落。那么在这本书里,我更注重叙事和内心,愿意让人物本身走向前台。除了有三个章节就人的“身体”展开思辨,这本书里的议论非常节制,作者的主观介入最小化。
世上的事都是知易行难。韩少功完全明了《日夜书》可能招致的诟病,或者说它的短处。他先发制人,说出这一套千真万确的说辞。但读者的阅读观感却可以对此提出质疑,让我们来看看《日夜书》是如何叙事的:“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段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
这小说第一节叙事的人物大甲,就这样被他的主观论述代替了客观描述。他所谓的“叙事和内心”,也不过是他自己的叙述和内心。他用自己的判断帮忙读者做出判断,给他的人物没有留下自己成长的空间,韩少功急不可耐地圆满论述分析了他们。小说开头第一段“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就是一个主题句,接下来他要论证大甲的性格。他通过回忆知青生活、大甲后来的混迹艺术圈、出国等等的“叙事”,来证明说明“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由此,一个完整的论证完成了。
他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他用这些看似顺畅迅捷的判断句给判断了。人物没法自己活起来,他们都只能是韩少功嘴里跑出来的印象式论述。“让人物本身走向前台”“议论非常节制,作者的主观介入最小化”的夫子自道,恰恰就是他根本没有完成的许诺,并成为一个在小说中思想成癖、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典型案例。“当然,与前两部长篇相似,这本书里也有散文的元素。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欧洲传统小说脱胎于戏剧,中国传统小说脱胎于散文。我对散文的体裁遗产一直饶有兴趣,因此有些作品像散文,但散文里面有小说,如《马桥词典》。有些作品更像小说,但小说里也有散文,比如这本《日夜书》。在散文和小说这两极之间,我会有各种配比不同的尝试。”韩少功何许人,马上接着用散文来当护心救驾的法宝,他在小说完成之后,还宛若上帝一样自信,全能,以为小说完全可以按照他的设计和配比来实现艺术效果?
小安子这个人物,就是他在09节的补记里帮读者论述出来的,小安子何以会成为这样的女人呢:“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世界里大凡读过一些洋书的女子,谁没几个关于爱情的梦,关于艺术的梦,关于英雄的梦,关于欧美化都市或田园的梦……”此段延续下去,直到09节要完的最后一小段,他总结道:显然,当一个人连洋娃娃都不敢面对,如果不投入一种更为迷幻的梦游,又怎能把日子过下去。又由此,小安子的论证过程完成了。
这是小说的写法吗?
读者看完只能无语:被他圆满合理的论述弄得心服口服,完全没有参与进去的欲望了。话都是你说的,你全都说尽了,还要别人说什么。最严重的是,他自己的主题思想先行之后的“叙事”,因为被格式化在一些零散、“闪回”和“跳接”,大跨度的转换和大反差的拼贴中,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细节、情节都难以给读者留下印象。整部长篇看完,好像告别一大堆海一样的议论文,小说应该保有的体温、活气、眼神、表情几乎丧失殆尽。小说是讽刺的艺术,真正的小说家总懂得将它的真理隐藏起来,不说出来,而且不可以说出来。它通过揭示世界的暧昧性而使我们失去确信。而《日夜书》几乎没有什么暧昧性,它太清楚了。而那些想通过风格的做作,故意使小说变得难懂是无用的。小说的神奇还在于,既能融合诗歌,也能融合哲学,还能毫不丧失自身。而我们看到,《日夜书》被韩少功式的思想绑架并失去了自身。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没有了。
三、马原:用形式开启的实验技
马原,中国当代作家中的一位奇才。他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被称为先锋小说的开山之作。何立伟曾说,80年代中后期,马原小说的巨翅的投影不但覆盖了几乎整个文坛,而且成了后来包括甚至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在内的一大批青年作家的叙事蓝本。“马原是当代作家中最具有文体革命意义的作家”,吴亮说,马原为1986年和1987年以后的先锋文学开辟了道路。“中国小说文体之父”、“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作家中的作家”。马原曾经带给文坛的震惊和失措,至今还是80年代的传奇。
惜乎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之后,也就是1991年之后,马原就不再写小说了,还发表过“小说已死”的言论。二十年之后,马原以《牛鬼蛇神》重返小说。《牛鬼蛇神》以怪异的目录昭示出不同凡响的结构;以神神鬼鬼的内容比拼现代科学的宏大叙事;以归零部分的思辨议论挑战中国读者的阅读癖好;以一生的“神迹”再次彰显马原式神秘色彩、哲学意味;用中国作家少能达到的轻灵状态,以巅峰的游戏风采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马原式叙述魅力不减当年,语言材料的组合技巧一向是马原的优长,由此造成句式间的推进力度强悍无比。
“形式之王”不会让读者对他的形式失望。全篇分四卷,从卷0开始,卷0的第一章不叫第一章,叫第三章,依次第二章、第一章、第零章,接着是卷2,第三章、第二章、第一章、第零章……所以从卷0开始,是承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谓万有生于无。既从0有了开始,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他“卷”的来历。至于到“章”的时候,又为什么倒着从第三章开始呢,每一章又倒着从3开始至0,这就是“归零”的说法了——自此,马原“有生于无,一归于零”的结构出来了。从目录来看,透着怪异,甚至有故弄玄虚之嫌,但却是马原道家思想底蕴的承续,且于形式上造成陌生化效果。此乃马原式形式实验的故伎——一切都要弄得神神秘秘、虚实难辨。最讲究的小说家,最知道结构对于小说的意义,艺术的形式从来不仅仅是形式这么简单,马原显然深谙此理。
北京卷也是卷0,即无,正是从这个无,生出了有,才有了后来的故事,有了两个少年“牛鬼”和“蛇神”一生的缘分。《牛鬼蛇神》的大结构似乎有着既包容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又不失去结构上的清晰性的野心。四卷的内容囊括了两个少年的一生,动用了复调的形式,卷1海南岛李德胜的故事与大元的故事,在同一时间里各自运行。正是马原对海南的诗性情感,这一卷写来得心应手神奇美丽,是四卷中唯一毫无瑕疵的一卷;动用了什克洛夫斯基的“嵌套”——在小说套盒中再套入短篇小说,如卷2拉萨中色季拉雪顶的故事;当然还有一定会受到诟病的,马原将过去小说直接贴进《牛鬼蛇神》的做法。马原的拼贴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至少可以在一个文本中看到不同时期马原的作品,比较它们的风格,而显然早年的马原至少在语言上比现在更激进,更具冲击力。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家的力度是与年龄成反比的。马原的纯粹拼贴,造成了断裂、炫目的新奇感,是他操弄形式实验的又一重演。
但显然问题也是明显的,卷3的海南,不但从卷名上重复了,至少从此卷第2章的2:当真恶鬼上身了直至最后,都是多余的。小说家突然卸下戏装,穿着家常衣裳上阵了——他开始背叛自己的虚构,打破小说与读者间的古老契约。尤其是卷3第一章,别一样的日子,第零章,琼州海峡日志,不知作者出于什么心理,完全忘掉了小说先贤早就说过的话:不要让自己出现在小说的前面,当小说家被关注超过小说本身的时候,是小说的悲哀。“福楼拜说,艺术家应该让后世以为他没有生活过。莫泊桑说,一个人的私生活与他的脸不属于公众。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说,我厌恶说自己。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征:不喜欢谈自己。福克纳希望“成为被历史取消、删除的人,在历史上不留任何痕迹,除了印出的书”。而马原到了这一卷,看上去似乎是罢演了。但其实他写下的文字反而都是最真实的,他将自己得了绝症的经过、结婚、生子,甚至单位领导对他的关心,以及他如何通过骑单车、晒太阳等自我疗病都事无巨细地写下来,而为什么这些对他来说“真”的内容,反而看上去“假”得令人不能忍受?毫无小说的美感,跟前卷内容简直难以统一起来。如果说前卷里呈现的是马原小说叙事的神奇、美丽,那么到了此卷,他的不虚构,所谓的形式实验之一种,就有些破产的迹象了。马原是到底要写一部自己的传记,还是一部小说的矛盾爆发了。读者显然不能接受他将自己似乎是悲惨的晚年生活直接端出来当作小说材料的做法——形式之王这回早已顾不得自己的形式追求?
北京卷显然兼顾了作者想要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少,早想写一部成长小说,之前也有《上下都很平坦》垫底,这一次的回忆,虽则将重点在成长之外,放在了显现神迹的主题上。但由于写得太细,有些地方仍然津津于自己青春年少时的华丽回忆,使人几乎忘了马原的主题乃是神鬼的世界。因为主题的凸显上有欠缺,这一卷欠简约、浓缩。米兰·昆德拉说,把握现代世界中存在的复杂性意味着一种简约、浓缩的技巧。要直入事物的心脏。这一卷完全可以去掉那些小说技巧带来的固有的长篇啰嗦、废话,变得更浓缩、有力起来,才更能凸显“万有生于无”。而卷2拉萨的问题比卷1更多一些。神迹的炫耀成了纯粹的炫耀。好些内容几乎完全与全篇无甚关系,比如圣诞夜狂欢,不知作者兴致勃勃地写来何意,还是像卷0北京一样,对回忆青春有着不可遏制的冲动和嗜好?杀人老太婆的故事像在搞悬疑剧,是否为突出西藏本为神的世界?一些西藏名胜的运用,像是导游图。总而言之,这一卷故弄玄虚的游戏色彩过头了。
马原在这部归来之作中,还是延续了当年创下品牌的诸般形式实验技巧,如对故事结构的极端重视;作家、叙述者、小说人物三位一体,不同叙述视角轮流转换;早年对博尔赫斯“元小说”“迷宫”技巧模仿横移的故伎重演,但程度已弱化;崇尚自然、东方式玄思冥想、禅机及周易命相说、庄子无为思想的思想资源等。无奈,年满六十岁、又身患绝症的他,更大动机也许只是回顾自己的一生。由此,小说与传记之间产生了难以平衡之感,在向写实靠拢的时代叙事美学的逼迫下,一方面读者早已没有了当年看你玩弄纯形式的耐心,另一方面作者本身六十岁的心理暗示也早已钝化了当年的艺术雄心和敏锐。曾经虚实难辨、华丽谜团的形式实验技巧,终于只能以弱化的面目恍惚出现。
由此,《牛鬼蛇神》的形式实验技,显出了力不从心的分裂感——马原已不能再创辉煌。
标签:牛鬼蛇神论文; 韩少功论文; 带灯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秦腔论文; 爸爸爸论文; 山南水北论文; 贾平凹论文; 马桥词典论文; 散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