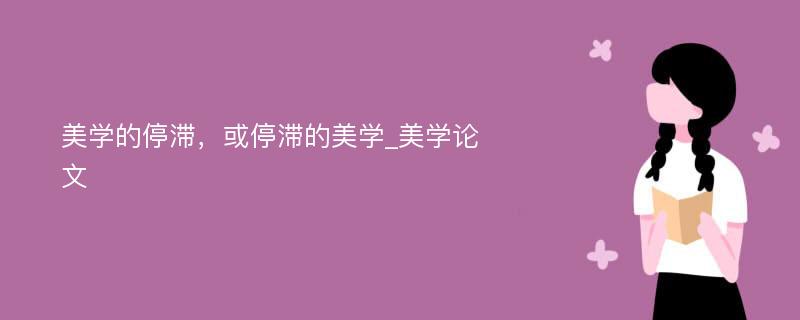
美学的凝滞,或凝滞性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字面意义来看,“凝滞”并非一个新词,在古代汉语中其实是一个常用词,如《楚辞·渔父》中“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论赞》中也有:“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其意主要包含拘泥、粘滞、停止流动、遭遇困阻、面临聚结等。我用“凝滞”来描述新世纪以来的文艺状况,主要想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意指21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创造性的总体性匮乏,可以用“美学的凝滞”来概括。在此,“凝滞”并非指新世纪以来没有出现一些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并非否认21世纪以来文艺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如以新媒介技术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文艺创作格局的总体性调整、伴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兴起而重振雄风的影视艺术和动漫游戏、在“理论之后”的语境下文艺理论批评领域所展开的一系列努力(审美性救赎、文化性越界、政治性复活、经济性强化),等等。我想用来描述以下与美学的凝滞有关的文艺现象:
表现之一,“纯文学”、“雅艺术”的“自闭”或“坚守”。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的那样,“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的作品这个理解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1]一样,“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艺术”(Fine Art)虽然古老,但在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照相术、录像技术的发展,整个艺术观念遭遇到“现代主义”的彻底改造,不仅诞生了以基于工业革命的视觉技术的艺术化(即本雅明所说的“摄影作为艺术”和“作为艺术的电影”),更重要的是逼迫“艺术”(Fine Art)作出适应性调整。而基于古希腊以来形成并在德国古典美学那里定型的“美学”,则只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和理论思考的资源而存在。中国当代的“纯文学”、“雅艺术”观念的变迁则更为复杂,先后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延安文艺”的改造,并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赋予其“严肃文学(艺术)”崇高使命;1980年代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运动,作家艺术家又肩负起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所有这些观念体系,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严肃文艺”(即纯文学、雅艺术)被迫作出“后撤性调整”。如王安忆在应对80后作家咄咄逼人的物欲化写作时,也不得不以“你们别想改变我,我也不会去改变你们”,来寻求一种“唯我独清”、“独善其身”式的自保。在面对《小时代》时,王安忆有意隐藏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将权力移交给了历史:“过于物质化,从来都是艺术的天敌。而当下,像《小时代》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这种以物判人的观念,变成了如此被高度关注、吸引人高度热情的对象。我想,这个确实有点奇怪。而这个奇怪现象,可能会被将来的文学史注意到。”[2]此外,大学文学教育所传递的文学理想与大众文学阅读的欣赏尺度之间的距离问题等也体现出“纯文学”、“雅艺术”在现时代所面临的窘境。
表现之二,理论批评对“网络文学”之类新媒体文学的解释性乏力。所谓“新媒体文学”就是指基于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而诞生的新的文学品种和文学活动(写作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新媒体文学”对重新定义文学提出了挑战。在由印刷时代而形成的文学观念中,“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是文学区别于美术、音乐、舞蹈、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标准,但是新媒体本身并没有直接取代“语言是文学的媒介”的位置,所改变的只是语言存在方式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对新媒体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分析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其一,新媒体本身并没有改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本属性,因此,新媒体是口头的、书面的语言之后出现的新的语言载体;其二,新媒体文学自身并不具有文学类型的独立性,它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文学活动上,这些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但是在我看来,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语言的存在方式,丰富了语言的表达力和想象力,新媒体自身所具有的技术特点对语言的运用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因素虽然没有完全改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属性,但是已使之形成了有别于基于口传时代、印刷时代而形成的文学类型和文学观念。由新媒体而催生出来的已经逐渐成熟的网络文学和刚刚兴起尚未定型的手机文学等,远远不是所谓“新瓶装旧酒”的问题,而是赋予了文学新的内涵。此外,文学活动方式的变化会带来文学场域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会对文学生产机制产生重大变化。但是,当前对新媒体文学的相关讨论,除了南京大学的赵宪章和中南大学欧阳友权的团队对这些问题集中展开过研究之外,尚没有引起更多文艺学美学研究者的关注。前者侧重于“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展开文学艺术史的历史性考查;后者则更多借鉴文化(创意)产业角度,展开现状描述、数据统计、态势分析等,学术界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直接将之引入文学研究学术领域中的恰当方法。
表现之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艺术终结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观念的滞后。“艺术终结之后”形成了“当代艺术”的观念,但中国的文艺总体上没有实现“当代艺术”的转型,还停留在“艺术终结”之前的现代主义艺术观念时期,甚至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仍具有极强的支配性。“当代艺术”已是一种全新的艺术类型,最典型的代表是以装置化、互动沉浸式、“非物质性”的数字技术、超越感官的“神经交感技术”等作为手段的新媒体艺术,与已成传统的文学、美术、电影、电视等截然不同。新媒体艺术有诸多“历史性形态”(或历史新媒体艺术),如录像艺术、数码艺术,等等,它们或多或少与传统艺术类型保持着某种关联,但在艺术观念上已有根本差异。这种狭义的“当代艺术”及其所承载的全新的艺术观念,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当代中国艺术家所接受。即使是当代中国一批自称是“新媒体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都还只是部分地、细节性的引入新媒体技术。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家“当代艺术”观念的滞后以及新媒体技术的落后,加之对技术更多只是从工具论意义上的应用,还缺乏对新媒体技术之于艺术表现的本体性思考,更没有真正去思考新媒体作为全新的“技术”所能够带给“艺术”的从“观念”到“手法”的所有可能性。因此,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影视艺术也一直试图搭上当代艺术的班车,如前些年的数字技术,目前比较热闹的3D电影,以及4D技术的奇观性展示等。但是如果认真辨析,我们不难发现,这里变化的不是艺术,而只是呈现艺术的方式。艺术(观念)本身凝固了,停滞了。
另一方面,“凝滞”更是对这一段时期美学主导风格的概括,这可能是更为切题的一种思考,姑且可以用“凝滞性美学”来命名。“凝滞”是相对于“进步”、“变化”、“流动”而言的,如果说,后者曾一度是文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的话,那么,“凝滞”则是对21世纪以来出现的艺术现代性(包括后现代性)精神耗散趋向的一种概括。我想借此表达的是,现代性曾经是100多年来文学艺术创造的不懈的冲动,而今可能正在消逝。150年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由科学技术所引导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视“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审美现代性反思,[3]以及由达尔文、马克思为代表的以“进化论”、“发展论”为代表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现代性思潮,共同推进了现代性美学(包括后现代性美学)100多年的世界性扩散。虽然这种以变化、改变、变动为基本特征,并被赋予进化、进步、发展的价值取向的现代性美学至今仍然是21世纪文艺创作的主体部分,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溢出现代性美学框架,甚至与现代性美学趣味形成尖锐对立的美学观念和审美风格开始形成,并获得很大的发展。本文所谓“凝滞性美学”即是指新世纪文艺中出现了溢出现代性美学的某些因素,或者说有可能,这些因素正在走向了现代性美学的反面。
表现之一,时间的停滞带来了叙事性艺术的新变。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进步”,所谓“永恒与瞬间”都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作用的;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则是“时间性的终结”,即詹明信所言的“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4]。但新世纪以来,以“穿越架空文学”为代表的网络文学试图重新确立一种看似“错乱”的时间观念:不再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截然区分;三者可以自由穿越。这里的时间既非线性的,亦非循环的;既非现代主义式的断裂,也非后现代主义式的只有现时。所有的时间相对于其所穿越的时间而言,都进入巴赫金在“时空体”理论中所提出的“超时间空白”:无论这段时间具体有多长(或一瞬间,或三五百年),时间对人物的“成长”、性格的“转变”、情节的“进展”并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在穿越架空小说中,时间看似在“流动”,甚至像“漩涡”,但其“时间性”几乎为零,不具有任何意义。同时,网络小说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容量——一部标准的网络小说因其采取网络连载的形式,为适应读者每天阅读的时间和赚取相应的稿酬,往往以动辄两三百万字的规模呈现,大大超出以纸质小说为阅读方式的“纯文学”的容忍度。这里包含着一系列时间性关系的倒转:创作时间(码字)无限逼近阅读时间(浏览)极大地破坏了艺术所应有的必要的节制;艺术时间无限制地“拉长”削弱了艺术整体性的地位,现时的、即时的审美(创作和阅读)行为无法构成从日常生活情境中“抽身”、“区隔”或“解放”出来的力量,相反,整个审美活动被肢解、分化甚至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表现之二,空间的凝缩与移置。詹明信在《奇异性美学》中将后现代性命名为“空间对时间的压制”、哈维在《后现代性状况》中使用的“时空压缩”、曼纽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以及索亚的“第三空间”,都试图描绘一种传统空间关系的解构。但所有这些不能很好地解释或套用到新世纪中国的文艺创作中:“历史性”仍是重要的主题,但同时被归为一种“地方性经验”(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天香》)。在这里,一方面是历史被高度地方化了,完全成为一种“地方志”,从而消解了历史的整体性(世界史、全球史);另一方面则是地方被高度地历史化了,地方性经验被时间定格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凝固成标本,被体验为风格。《长恨歌》第一章所采用的“综合性叙述”方法,用一种叙述讲述多次发生的事情,《天香》中随处可见对民间风俗、日常生活细节的知识化堆砌,所带来的正是这种“叙述的凝滞”。“乌托邦”仍是21世纪头十年文艺创作的动力,但同时具有的多种时空的向度(如阎连科的《受活》中向后看的“天堂日子”和向前看的“社会主义”同时成为其乌托邦叙述的指向,并相互拆解)。在艺术创作中,“在地性”(Site-specific)也成为艺术家抵抗全球化、多元化的一种手段。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就引用霍米·巴巴对于“在地性”的批判(“在地性”就是“价值的区域性、美感的独特性、观众或原住民的自发性、激情的原发的力量”等),认为中国艺术家对“在地性”的认识与后殖民主义的“在地性”不太一样,“作为‘在地者’的文化立场,我们强调本土的文化重建。‘本土重建’既不是狭隘的地域观念,也不是权宜的时间观念,它的文化立场源于本土的生存经验,思考的是在急骤变迁时代中的文化个性的营造和坚守”。因此,中国艺术家确立的使命应该不是“漂泊者、浪子”,而是“在地者”、“守夜人”[5]。
表现之三,风格的固化。风格曾是一个作家、一个流派或者一批作品艺术独创性的标志;形成具有可识别性的风格,也是一个艺术家所追求的目标。不过,进入文化工业时代,风格化成为标准化、统一化的同义语,意味着艺术家个性的丧失。所有这些,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并成为“为市场的艺术”(通俗文化、文艺商品)与“为艺术的艺术”(严肃文学或纯文学、雅艺术)的分水岭。作为一种抵抗性的姿态,“非风格化”、“反风格化”、“无风格化”一度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主义艺术寻求艺术观念和表达方式突破的方式。但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先锋姿态很快陷入严峻的创新悖论:一方面是前无古人的豪迈,另一方面却是后无来者的寂寥。现代主义艺术诸流派因拒绝重复、反对模仿而迅速成为“历史先锋派”:不仅因其创新而与传统断裂,而且因其拒绝复制而无法形成新的传统。正是对这一创新悖论的克服,后现代主义艺术才将“戏仿”作为克服“影响的焦虑”的法宝。但是,新世纪的文艺创作所出现的风格的固化与之还有明显的差别:其一是文化工业的逻辑在新世纪得到飞速发展,原因就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从学界的呼唤到政府的推动,并最终成为国务院第十一个产业振兴计划,曾经一度为生计发愁的文化产业部门开始“不差钱”了,风格化、类型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生产的基本特色;其二是艺术观念不再成为推动艺术创新的动力,科技作为艺术的媒介和呈现方式,成为艺术变迁的根源。技术进步的逻辑对艺术创新逻辑的简单替代成为现时代文艺评价的一种标准。但进步的是技术,而非艺术。
也许,上述许多文艺现象有的还只是个案,或只体现在某个具体的艺术部门之中,还不能说已具有了某种普遍性:“美学的凝滞”还受到“时代和技术的发展”的遮蔽;“凝滞性美学”还被裹挟在看似变幻莫测、变动不拘、弥漫流动的现代性美学中若隐若现。但这些现象和问题才是最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因为新世纪中国文艺的未来,就在这些细节中萌动、生长。
标签: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新媒体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新媒体论文; 文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