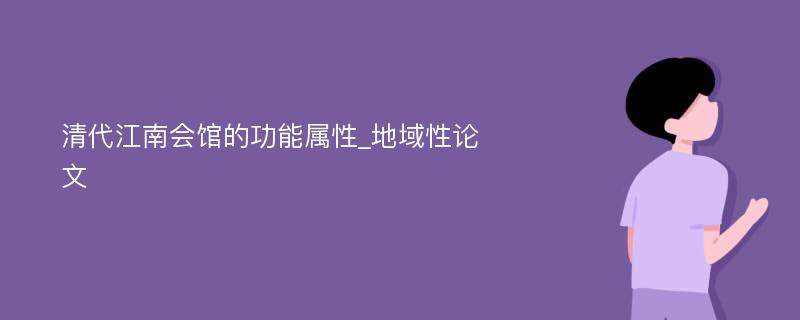
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会馆论文,清代论文,公所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恐怕莫过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成果也较多。但以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各抒己见,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似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这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同,自不可一概而论;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其经济功能自不能轻描淡写。
一、会馆公所异同论
为了探讨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有必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会馆公所是行会性组织,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较为一致的看法。但80年代初吕作燮认为会馆并不是工商业行会,会馆与公所这种行会组织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后者是同业的组织;前者有仕商、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参加,而后者的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本地人不设会馆,而本地工商业者都参与一定的行会组织(注:吕作燮:《明清时期的公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新近的研究既有仍持原来看法主张会馆也是行会者, 也有同意会馆并非行会但与公所没有根本区别也无截然界限者。试举数例。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主张会馆是同乡的公益团体,不具有行会的职能,只有公所才是行会组织的看法,是拘泥于会馆公所的称谓,而忽视了对其实质的考察。就当时上海的情形而言,会馆、公所的称谓,在一部分同业同行团体中是通称的,说明会馆公所的名称既不是划分同乡、同业团体的标志,也不是区别是否行会组织的依据(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0 ~511页。)。
王日根认为,会馆与公所在很多场合往往不易区分,倘若真要说出二者的区别,其主要点当在于,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公所则更多地注重实效。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于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据地。而中小商人则既可栖身公所,又可寄居会馆(注:《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5页。)。
邱澎生认为,会馆、公所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自愿参与结社,并不是由政府或其他外力强迫结社,都具备一定规模的共同财产,并且制订有一套征收经常性公积金的筹款办法,都经过向官府立案申请的手续,获得官府明令保护其公同财产而成立,所以都是一种“自发性”、“常设性”和“合理性”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因此以会馆代表同乡团体、而公所代表同业工商团体的说法,其实是不精确的二分法,失之粗疏。就语义上来说,会馆和公所都是商人借来称呼自己建筑物名称的现成名词(注:《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硕士、博士论文)。)。
以上各种看法都强调了会馆公所有着根本的共同点,所举例证也大多说得通,因而具有合理的地方,有一定的说服力。
会馆公所有着一定的共同点,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当时人特别是会馆公所的建立者就认为在公共场所这一意义上会馆与公所并无截然界限。如道光中期陶澍就说,“会馆设在市廛,为众商公所”(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八《查核上海会馆并无囤贮私盐暨舟山地方产盐应归浙江经理折子》。)。苏州的广东嘉应会馆的创立者说,当地人“将房卖与广东嘉应府众仕商王仰莲等为公所”(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52页。 以下简称《江苏碑刻》。)。安徽宣州会馆的主人也说,“向来贸易苏省者……设立公所宣州会馆”(注:《江苏碑刻》第383页。)。 上海的福建泉漳会馆的创建者说,“会馆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以下简称《上海碑刻》。)。上海的浙绍公所参与者说,“绍郡绅商,在沪贸迁,设公所以相晤语”(注:《上海碑刻》第260页。)。在这些人看来, 公所即公共场所,会馆就是乡人的公共场所,因此同乡的会馆与同乡的公所是一个概念,二是会馆与公所在名称上往往是相通的。如苏州的浙绍公所又称绍兴会馆,元宁公所又称元宁会馆,兰溪公所即兰溪会馆,上海的四明公所即四明会馆,锡金公所即锡金会馆,台州公所又称台州会馆,钱庄业有南市钱业公所和北市钱业会馆,乍浦的咸宁公所又称炭会馆,常州的洪都公所即洪都会馆,湖州四安镇的新安公所即新安会馆,南汇县新场镇的金陵公所即金陵会馆。同一会馆或公所在名称上前后也会变化。如上海的潮惠会馆,道光十九年创建时称公所,同治五年易地重建时称会馆。木商会馆咸丰八年初创时称,光绪二十四年易地改建后称会馆。茶业于咸丰五年与丝业合组称丝茶会馆,同治九年公所移办事处时称茶业会馆。诸如此类,较为常见。正因为会馆公所有这些互通处,所以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三《建置下》主张,“至或称会馆,或称公所,名虽异而义则不甚相悬,故不强为区分”。清代中后期的同业组织大多以公所命名,大概也是出于公共场所之本意和基于会馆公所不相悬殊的事实。清末民初乃至直到50年代欧美人、日本人都将会馆视为行会,大概也是基于会馆公所的共同点。
那么,会馆公所是否就没有区别可以等同视之,会馆公所的研究是否就可以到此为止不必再加深究呢?回答恐怕是否定的。
笔者以为,吕作燮以地域和行业为标准,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异,过于绝对,故为人诟病,而新近的研究则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同,过于笼统,故仍有缺憾,个别论者更以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来区分会馆与公所,更属牵强。我们认为,考察其内部实质,应从地域或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即地域性会馆公所和行业性会馆公所,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这样,或许会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或许更有利于问题的探讨。
考察江南的会馆公所,苏州、上海、湖州等地的会馆既有地域性的,又有行业性的;苏州、上海、湖州、杭州、嘉兴等地的公所同样既有行业性的,又有地域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会馆公所相同论者的看法是说得通的。然而会馆即使表现为地域性的同时也表现为行业性,但地域性占绝对比例,在整个江南的227所会馆中,地域性会馆为215所,占95%,行业性会馆仅为12所,仅占5%;相反, 公所即使表现为行业性的同时也表现为地域性,但行业性占绝对比例,在整个江南的352 所公所中,行业性公所为312所,占89%,而地域性公所仅为40所,占11 %。我们不能因为会馆公所字面意义并无大区别而忽视了他们的数量差别,并且应该由这种数量的差别注意到它们的内在区别。这就是从总体而言,会馆主要是地域性的社会团体,公所主要是行业性的社会团体。苏州的吴兴会馆碑记称:“苏城吴兴会馆,系乾隆五十四年浙湖闵峙庭中丞抚苏时建造。虽为绉绸两业集事之所,而湖人之官于苏者,亦就会馆团拜宴集,以叙乡情。故不曰公所而曰会馆也。”(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以下简称《苏州碑刻》。)可见当时人在会馆和公所的称呼上并不是全无区别的,在地与业上毕竟有所侧重。一些公所可能是地域性组织,因其“虽不以会馆名实已举会馆之事”(注:《洞庭东山会馆记》,《上海洞庭东山会馆落成报告》。),但会馆为行业性组织者究属偶然,不足以影响我们作总体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吕作燮的看法是有见地的。看来,将会馆公所的区别绝对化不尽妥当,但将会馆公所视为一体,也未能究其底蕴。
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就总体而言,江南的会馆自明后期产生后,康熙年间逐渐增多,乾隆时期大量增多,嘉、道时期臻于极盛。假如以太平天国为限,已知确切或大致时代的126所会馆,在前有87所,占69%; 在后则仅有39所,占31%。江南的公所真正开始产生是在康熙十年的苏州,即印书业崇德公所,终康熙之世仅此1所,雍正年代仍只有零星的13所, 乾隆时期稍有增加,但其高峰是在同治以后。若也以太平天国为限,已知确切或大致时代的189所公所,在前仅55所,占29%,在后则多达134所,占71%。实际上不知年代的会馆大多产生于嘉、道以前,相反,知年代的公所则绝大部分形成于太平天国以后,上海的公所甚至大多是清末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会馆形成于太平天国以前,甚至是鸦片战争前,而绝大多数公所形成于太平天国以后。
就各地区而言,会馆公所的产生也有一定的时间差。大体而言,苏州最早,到乾隆时大多数会馆已经产生,到道光时公所也已形成不少;南京、杭州、湖州、常州、嘉兴等地会馆的兴盛期在嘉、道时期,所谓“嘉道间,海内无事,商贾懋迁……皆一时各建会馆”(注: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七《建置》。);上海会馆较晚,大量产生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各地会馆公所特别是会馆形成时间上的差异,说明不但会馆与公所的兴衰有前后的区别,而且各地之间也前后相继,或者说各地的经济兴盛期有先后,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区位优势,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最为兴盛期已是江南其它城市的衰落期,会馆公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可见,不但会馆与公所不能混为一谈,无视其间时间上的差异,而且各地的会馆公所也不能笼统而言,看不到它们在地域上的差异。
二、地域性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会馆公所的创建者和撰文纪事者留下了大量有关内容的文字。蔡世远说苏州漳州会馆之建,“以事神而洽人,联情笃谊,所系綦重”(注:蔡世远:《漳州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一○六《艺文》。)。余正健说苏州的三山会馆“宫之建,不特为答神贶而资游览,且以敦乡谊,讲礼让”(注: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乾隆《吴县志》卷一○六《艺文》。)。兰溪人戴曦则是这样表达在苏州创立金华会馆的目的的:“虽苏之与婺,同处大江以南,而地分吴越,未免异乡风土之思,故久羁者,每喜乡人戾止,聿来者,惟望同里为归,亦情所不能已也”,“为想春风秋月,同乡偕来于斯馆也,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蔼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脱近市之习,敦本里之淳,本来面目,他乡无间,何乐如之”(注:《江苏碑刻》第366~367页。)。史茂在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中表达了完全同样的意思:“余惟会馆之设,所以联乡情,敦信义也。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河渭之间,材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注:《江苏碑刻》第375~376页。)。上海的豫章会馆碑载,设立会馆,“凡事遇公私,集议其中,藉可时常亲近,未始非联属乡情之善举”,“俾春秋佳日,宴集谈心,不时聚首,虽处异乡,情同故里,一举之善,其快何如”(注:《上海碑刻》第336页。)。其他如苏州的兴安会馆、汀州会馆、潮州会馆、江西会馆、浙宁会馆、上海的泉漳会馆、乍浦的咸宁公所(俗称炭会馆)等碑文,都表述了同样的内容。
可以说江南各地几乎所有的地域性会馆公所的创建者或修葺者都反复强调会馆公所的建立,旨在联乡谊,祀神祇。这可以说是地域性会馆公所最为常见的活动内容,最易理解的创设动机。客籍人士要在异乡托足,建立在地域乡邦基础上的扩大了的宗族姻亲势力是最可凭藉和依赖的力量。而集结、联合、扩大这种力量,唯有通过叙乡谊、祀神祇的形式,以同宗同亲,同乡同风,共同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来维系和感召。会馆公所这一建筑物本身就是乡情亲情的表征。岁时令节,同乡之人,无论关系亲疏,熟识与否,营业异同,语同音,食同风,拜乡土神,演地方戏,亲不亲,故乡情,雍雍熙熙乐陶陶的气氛是会感染每一个人的,思亲之情,乡愁之苦,于此也可得到慰藉。平时的互通信息,互相照应,互相周恤,互相支持,更会使异乡孤客随时随地感受到乡党的可亲可爱。会馆成为联络广大客籍人士强有力的纽带,同籍人士在客居地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
联乡谊是与祀神祇联系在一起的。各地商帮都崇奉固定的神祇。福建、广东这些航海商帮以及其他沿海商帮都崇奉蹈海救难、屡著灵验、保佑航海的化身天妃(天后)。在江南,天妃宫往往就是这些商帮的会馆所在地,留存至今的材料不少就是天妃宫记。徽商、宁国商人、山陕商人、江浙商人、山东东齐商人等崇奉忠义侠胆、正义伟力的象征关公。山东济宁商、江淮商崇奉宋末殉节、能庇佑河运的诸生谢绪为金龙四大王,江南的大王庙往往为这些商帮所建。江西商帮崇拜旌阳令主许逊为许真君。这些神化了的忠心正义、力量的化身,经历代渲染,都成了护佑一定地域或某些行业的功德神,已经超出了乡土神的范围。奉祀这些神祇,既祈求保佑平安吉利,又借以树立各地域商帮特有的形象。正像各地民间普遍供奉诸多神一样,“许多会馆也并非以仅供一神为满足”(注:《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第282页。)。祀奉主神的同时,也配祀、 配享一个或数个乡土神或乡先贤。徽州、宁国商人在盛泽镇的徽宁会馆,正殿中供关羽,东供忠烈王,西供东平王,殿东行宫供奉朱文公朱熹。苏州的潮州会馆,始建仅有天后阁,后增建观音阁,观音阁中还建有昌黎祠(祀韩愈)。光绪八年落成的苏州的两广会馆,中间三间堂屋,“祀乡先生之官斯土者”,明代为应天巡抚广东人海瑞,清代为江苏巡抚广西人陈宏谋。苏州的钱江会馆,外供关帝,内奉文昌。苏州的嘉应会馆供奉关帝以外,旁祀四尊,内楼供奉南华六祖。苏州的江西会馆主奉许真君外,后殿供奉天后。上海的建汀会馆,中奉天妃,“旁有数楹,或祀土神,或奉先董”(注:《上海碑刻》第278页。),最为特别。上海的祝其公所,既奉关圣, 又奉天后。上海的潮惠会馆前堂祀天妃,后堂祀关帝,左右祀财星、双忠。上海的商船会馆创设时仅奉天后,后增祀福山太尉诸大神于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膝大神于南厅。徽商在乌程县眺谷铺还有祀朱熹的朱文正祠,又称新安乡祠。宁绍商人在归安县济川铺则有宁绍三贤祠,又称宁绍乡祠,由此可见,明清会馆神灵崇拜经历了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关圣天妃,财神土神,乡贤名宦,释祖先达,都可作为崇祀对象,反映了各地域商帮的企求是多方面的,相当宽泛和复杂的。
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要使异地异业的众多同籍之人对会馆公所长久保持向心力,光凭联乡谊与祀神祇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大多公开声明将力行善举也即社会救济放在重要地位。加入会馆公所的仕商,共同集资为会馆积累资金。有些会馆如江西会馆还规定按经营所得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会馆公所通常置有房屋田产以收取租息。在这方面,徽州商人、潮州商人、宁绍商人等是较为突出的。所有这些公积金及公产所得租息,大多用于救济本地域的贫病无依、失业及死亡者。公馆公所对同籍人士的生养死葬予以资助,失业者救济,年老不能经营者资助返乡路费,或者因病延医供应汤药。有的公馆还为同籍或同业诵经超度,祭祀设忏。在这方面,尤以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最为突出。四明公所内,木业有长兴会,肉业有诚仁堂,竹业有同新会,内河小轮业有永安会,马车漆业有同议胜会,钢铁机器业有永生会。会馆公所大多设有殡(丙)舍、义冢,停放棺柩,埋葬棺椁无力返乡者。据笔者初步统计,各地域商帮在江南的这类寄柩所、义冢等身后慈善设施多达70余所,几乎遍布江南各地,特别集中在商人活动最为活跃的苏州、上海等地,创设者有安徽的徽州、宁国商人,浙江的绍兴、宁波、金华、湖州商人,福建的兴安、汀州、泉漳、晋惠、三山、福宁、建宁商人;江苏的洞庭、句容商人,以及山东、江西等地商人。其中以徽商的义冢等设施为最多,达24所。怪不得泾县人朱珔慨叹,“皖江多好善,所在辄置义冢”(注:《小万卷斋文稿》卷一八《徽郡新立吴中诚善局碑记》。)。这些慈善设施,不少置于会馆建立后,但有不少早在会馆创立之前就购置了,甚至未设会馆的不少地方也有这类设施。有的会馆还没有义学,让本地域的贫寒子弟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各地域商帮举办这些善举,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对内的向心力和对外的竞争力。在江南的各支商帮的实力似乎正是与会馆建筑、善后设施相一致的。因此,就其实施社会救济而言,会馆公所又是力行善举的社会组织。
联乡谊、祀神祇和办善举表面上看起来构成了地域性会馆公所的全部活动内容,也是创办者公开宣称反复标榜的,但实际上这些活动既是社会意义的,也是经济意义的,而且最终恐怕还是为了更加讲究经营之道,维持和发展各支商帮自身的实力,以便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吴大徵在上海的潮惠会馆迁建记中全面地表述了会馆的功能:“会馆之建,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与乐其乐也,亦以懋迁货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耆旧,曷由排解?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瘠。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井邑,宜援陷阱,凡此皆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临以神明,盟之息壤,俾消衅隙,用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拯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不容缓也。”(注:《上海碑刻》第331页。 )说得很清楚,会馆不但联谊祀神拯乏,而且还要排解经营纠纷,对付各种苛索骚扰势力,捍卫和维护地域商人的利益。马登云也说,苏州的潮州会馆设立后,“凡吾郡士商往来吴下,懋迁交易者,群萃而游燕憩息其中”(注:《江苏碑刻》第344页。)。苏州的金华商人也曾声称, 会馆建成后,“于是吾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注:《江苏碑刻》第367页。)。乾隆四十一年, 当苏州的钱江会馆屡屡被仕宦借居引起该地商人不满诉之公堂后,吴县令裁决,“查会馆为商贾贸易之所……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注:《苏州碑刻》第22页。)。会馆是商议经营事务之所,是堆贮商货、居停商客之所,也是从事贸易之所。客籍商人千里跋涉云集到商品贸易极为发达的江南,自然不是为了叙乡情、联乡谊,而是为了牟利致富。会馆公所这种公共建筑正是利用集体的力量,切磋经营之道,商讨经营方针,互通贸易信息,采取联合行动的大好场所。《东齐会馆碑记》载,商人纷投于金玉财宝之乡,“然而钱贝喧阗,市廛之经营,不无参差。而好究侵渔之术,或乘间而抵隙,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运转于物我两忘之情,相勖以道,相尚以谊,不可也。会馆之设,义亦大矣哉”(注:《江苏碑刻》第369页。)。 说到底,会馆是权量物候,商议商务的组织。联谊祀神也好,力行善举也好,对商人来说,多半都是为商业活动打基础,为恢扩经营服务的,而且这些活动本身便可视为商人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商业发展着眼,会馆公所又是客籍人士广为联络,加强团结,自我保护,自谋发展,增强实力,开拓商务的乡邦团体。明中期起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商帮,就是在会馆公所的旗帜下不断发展壮大的。
会馆既是地域商人在客籍地联络了大小商人自我管理、谋求发展的社会组织,也就成为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管理、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的重要辅助力量,道光年间,有人明确提出在江南利用会馆管理都市人口的构想:“省垣五方杂处,易成朋党,易起衅端。此中查访难周,最难安放。窃意各省有各省会馆,各行有各行会馆,各归各帮,尤易弹压。宜于会馆中,择贤董数人,专司劝导,每逢月朔日,各会馆宣讲馆约……三次不到,即屏斥,或资遣回籍。如此……虽五方杂处,亦不足患也”(注:《宣讲乡约新定规条》,载余治编《得一录》卷一四。)。这种构想具体实行起来恐有难度,是否实行也不得而知,但会馆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有力工具当可肯定。乾隆四十九年,苏州潮州会馆的碑记中有姚姓“客长”的署名,此“客长”大约就是专司管束客籍商人的。
综上所述,地域性会馆公所是祀神祇的公共建筑,联乡谊的聚会场所,办善举的社会组织,谋商务的地域团体,甚至还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辅助力量。这种地域性会馆公所,不是行业的组织,没有东伙之别,而是“人各异乡,居各异地”,包括了一特定地域的各行各业全部客籍人士的地域组织,它对内并不互相限制、互相排斥,而在乡邦精神的号召下,“相勖以道,相尚以谊”,提倡和力行互持互助,互相保护,对同乡的经营活动不加任何限制,以人数众多、实力不断发展为自豪;对外不搞垄断,而是鼓励发展,提倡竞争,讲究经营之道,展开与其他地域商帮的竞争。这样的地域性会馆公所是工商业、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促进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事实表明,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工商业会馆公所最多,商品经济与工商会馆公所的发展是同步的。把这样的地域性会馆公所不加区分,一概说成是对内限制发展、对外排斥竞争的封建行会组织,确实从理论上和史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个别论者所谓商人会馆“举凡行会精神的主要方面,如垄断市场、统一售价、统一度量衡器、统一商品规格,乃至控制和排斥非本行会的商人,色色俱全”的看法(注:汪士信:《明清商人会馆》,《平准学刊》第3辑。),实际上主要依据个别行业性公所而来, 很难用来证实所要讨论的商人会馆的性质。
三、行业性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行业性会馆公所是工商同业组织,大多有行规,对入行条件、商品价格、使用的度量衡、招收学徒、同业救助等有着相应的规定,称之为行会,未尝不可。但这样的行会,也有着中国固有的特色,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在内涵上和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不能拿西方的行会来随意框套。这是因为:
第一,江南的手工行业,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并非如人所说都以行会为必要形式,都是行会手工业。有人强调,“在中国封建社会条件下,行会既是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又是城市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形式”(注:彭泽益:《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也有人说,“行会普遍存在于各行业”,“所以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前,苏州的手工业仍然是行会手工业”(注: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157页。)。还有人说,“手工业行会在明中叶至清前期已达到它的鼎盛时期”,“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行会已显现出逐步瓦解的迹象”(注: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4页。 )。这些各行各业都存在行会的说法,与历史实际的出入是很大的。已知的江南行业公所康熙时才出现,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也未“普遍存在于各行业”,其绝大部分是鸦片战争后甚至是同、光年间才陆续产生的,而那些行业无疑是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存在了。把尚未以公所为普遍形式的所有手工业都论断为行会手工业是缺乏说服力的,而即使是将公所理解为行会,称其方兴未艾日趋兴盛之势为“逐步瓦解”,更是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
第二,江南相当部分的行业性公所与中世纪西方的行会在产生目的、成立时的社会背景等方面都不一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世纪西方社会城乡之间不断战争,农村领主贵族与流亡到城市的工商业者严重对立,商业很不发达,城市之间联系很不密切,城市居民稀少需求有限,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为了在政治上组织力量反对封建贵族,在经济上为了维护同业利益限制同业竞争而结成了行会组织。由于市场的狭窄,在行会内部,各个劳动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熟悉全部工序,凭借专业和熟练的技巧,像生产艺术品一样生产有限的商品,每一个手工业者世袭地继承生产技术、行会特权,甚至顾客和销售市场(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一章;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第 1019 ~1021页。)。在中国,在工商业公所日益增多的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中国向来城乡一体,城市统治乡村,城市工商业主与乡村地主也无截然界限。明清时期,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极为发达,商业贸易相当繁盛,城市之间联系紧密日益不可分,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市场需求相当广阔,鸦片战争前后更面临着与西方商业势力的竞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行业性组织公所的成立,就有着远为复杂多样的动机和目的。
台湾邱澎生在《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体》一书中认为,那些会馆公所成立的动机至少有如下四种:特许商联合禁止非法业者进入市场营业,批发商联合对中介商人进行集体谈判,包买商或大作坊主联合对劳工进行集体抗衡,部分行业的工商业者联合建立寡占市场。他进而指出,在这四种经济动机中,只有第一与第四种可与“限制自由竞争”扯上关系,第二与第三种则根本不适用。而其中的第一种动机不是因为工商业团体本身的经济特权,而是来自政府法律对于中介商人的管理法令,工商团体不过是重申政府法律限制“自由竞争”的禁令而已,所以单举“限制自由竞争”为结社动机,有立论过于含混的弊病。这些看法是作者对鸦片战争前苏州的会馆公所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类考察后得出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笔者以为,如果全面分析江南行业性会馆公所、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大量兴起的公所,探讨其产生原因,除了上述邱澎生所说的四种,至少还有如下几种。
不少行业设立公所是为了谋求官方保护。在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府毕竟是维持秩序、稳定社会的力量。工商行业要想维持和获得发展,就必须获得官府的保护,以官衙的权威来对付各种不法势力的骚扰劫夺。大量行业公所成立时向官府备案就是出于这种动机。苏州豆米杂粮业就明确声称,“白拉名目,不论何业,均有此名称。既无公所,亦莫由官厅给示保护,布告禁止”,如果营业受损,“不但国税攸关,而同业亦受其害”(注:《苏州碑刻》第238页。)。 苏州成衣业公所也是为了应付无业游民、地匪游勇在其公产内酗酒赌博、任意作践而成立的(注:《苏州碑刻》第225页。)。 同西方行会与封建势力互相对立正好相反,中国的封建政府与工商业团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不少行业创立或恢复公所是为了维护行业信誉和产品质量。如苏州酒行,因被无帖私牙领卖短减,担心份量价值短长不一,乃于道光二十四年设立醴源公所,置立公砠,各行仿设量卖,使无欺短之私(注:《苏州碑刻》第258~259页。)。苏州酱业,未曾注册的酱店往往“代牌营私,偷造酱货”,以致质量低下,销售不畅,同业就于同治十二年创建酱业公所加以整顿(注:《苏州碑刻》第260~261页。)。苏州煤炭业,“因无公定规则,售价不一。甚有巧计营生,或跌价放秤,兜揽生意;或次货混冲,欺谎买客,种种技巧,奸伪百出……致买客疑窦丛生,外负重利之虚名,内受亏蚀之实害”。在这种情形下,同业创建了坤震公所以维持商务,筹办善举(注:《苏州碑刻》第278~279页。)。上海珠玉业新汇市公所成立后,“珠宝玉器各商入市贸易者,莫不以信实为之。故定章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注:《上海碑刻》第369页。)。确保产品质量, 反对假冒伪劣,提倡诚实经营,制订交易规则,完善市场设施,严禁不正当竞争,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这是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的必要措施或手段,所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我国传统商业的合理内容,应该予以肯定。不少行业创立或恢复公所是为了因应日益繁多的同业事务。工商行业生产经营者少,规模不大,事务稀少,没有成立同业组织的必要;同业发展,头绪纷繁,事务剧增,为了谋求发展,才需群策群力,聚会商议。鸦片战争后,江南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工商各业联合起来共商事务尤为必要。不少公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或恢复的。如上海靛业,太平天国后,“各处靛市,有聚有散,而上海之盛,十倍于昔。靛之产自中土以及来自外国者不一,其名来者既多,去者亦远,非明定条约,何以昭信义,而广招徕乎”,于是光绪三年才有靛业公所(注:《上海碑刻》第371页。)。他如上海油麻业、鲜果业、 冰鲜业,苏州寿衣业、洋货业等,原因大多如此。这些公所的创立,不是行业垄断的产物,而是行业发展的需要,不是经营者为了维护小生产局面的结果,而是同行业迎接新形势、因应日益繁多事务的结果,很可能不是为了垄断市场,而恰恰是为了扩大市场。上海等城市随着工商百业的兴盛,新行业增多,老行业扩大,公所迅速增加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更有不少行业创立公所是为了对付西方经济势力并与之展开竞争。如上述上海油麻业成立公所也在于当时出口既多,销场益盛,同业认识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为营业的关键,“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者,惟其对于内则精益求精,对于外则同德同心故也”。公所成立后,“凡所以筹进行之方,图生利之策,协力经商,同心御侮者,胥在于斯”(注:《上海碑刻》第353页。)。上海钱业也指出,“顾商战之要, 业欲其分,志欲其合。盖分则竞争生,而商智愈开,合则交谊深,而商情自固。公所之设,所以浚商智联商情也”(注:《上海碑刻》第398 页。),于是光绪三十二年设立了沪南钱业公所。上海的水木工业公所认为,“且夫人必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强,而后其国强,其种强”,公所之设,“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与“杜联合心智,而切劘其智识才能”(注:《上海碑刻》第322页。)。光绪三十二年,苏州银楼业修复安怀公所, 旨在“联群情,结团体,互启新知,勿私小利,使吾业于商战界上,占进步而操胜算也”(注:《苏州碑刻》第175页。)。这样的公所, 是为了团结同业,以浚商智,联商情,应商战,与保守、封闭的西方中世纪行会毫无共同或相似之处,而是体现了中国工商界反对西方列强掠夺诈取的强大的团体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绝大部分公所所起的作用与西方行会迥然不同。亨利·皮朗对中世纪欧洲行会的作用是这样论述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工匠既免受外来的竞争,也免受同行之间的竞争。它把城市的市场完全保留给同业行会的工匠。它排斥外来的产品,同时又监视不使同行的会员因损害别人而致富。正是由于这个原故,逐渐形成了许多详细的规定。”“例如规定工作时间,规定价格和工资,禁止任何种类的广告,决定每一个作坊中的工具数量和工人数目,指派监督人进行最细致、最严格的监督。总而言之力求保证对每一名会员的保护,并且尽可能做到完全平等。这样,它的结果就用全体一致的严格的服从来保证每个人的独立,同业行会的特权与垄断所造成的反结果,就是一切创造性的毁灭。任何人不得用较别人生产得更多与更廉价的方法来损害别人。 ”(注:Henri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London,1936,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165—166页。)江南的公所由于其创立宗旨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与西方行会不同,也就决定了它起不到西方行会的那种作用。
江南的工商各业,不但多数成立公所时间很晚,如苏州的纱缎业、纸业、棉布加工业,南京的缎业、染业等,而且这些居有重要地位的主要行业,即使成立了公所也未必就有行规。如苏州印书业崇德公所,成立于康熙十年,但直到道光二十五年,该所还宣称,“缘刷印书籍,向无行规”(注:《苏州碑刻》第95页。)。苏州等地的丝织业,力主行会说的学者认为,那是自十一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即形成的“一种很古老的行会手工业”,但却不得不承认,“有关明代苏州丝织业行会组织活动和行规的具体资料,还没有可能见到”,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关苏州丝织业的行规”(注: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关系的形式与性质》。)。没有发现行规自然不等于一定没有行规,但对这些没有行规或还未发现行规的手工行业,我们怎么就能断定它们必是行会手工业,并从而认定它们实行垄断、限制竞争、防止内部分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呢?实际上,在江南的丝织业中,其生产方式由明后期在“以机杼致富者尤众”的基础上的简单协作,发展到嘉、道年间取得普遍形式的帐房领织制,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行会在起作用(注:拙著《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九章。)。如果是有限制竞争行规的行会手工业,为何对那些领有四五百张织机的李扁担、陈草苞、李东阳、焦洪兴等帐房主不加任何限制?棉纺织加工业是苏松地区的重要行业,在棉布收购、踹染、发售过程中竞争相当激烈,我们同样看不到行会干预的踪迹。清初,徽州氏在苏州开张棉布益美字号,为扩大销售量,“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年销布百万匹,每匹赢利100文,获利20万两。十年后即“富甲诸商, 而布更遍行天下”,其后,“二百年问,汉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注: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这种类似于今日利用优质品牌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的竞争手段,前后持续了200年, 居然没有遭到同业干预。其它如苏州的纸业、钱业、典当业,上海的运输业、水木作业、成衣业、洋货业,杭州的丝绸业,南京的丝业、丝织业等,经营规模前后变化较大,似乎都看不到行会势力的干预。无视这些事实,把没有行规或尚未发现行规的这些行业一概说成是限制竞争的行会手工业,自然难以服人,也不利于行会史研究的深入。
在我们所知的江南各业的行规中,主要是关于救助同业、捐资办法、工价给付、工匠管理、产品质量、禁止假冒、抵制不法牙行、对付地棍势力等内容,也有一些关于产品价格、开业条件、交入会钱、招收学徒年限等内容,而有关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内容则很难见到,以致于力主行会说的学者也承认“根本不涉及买卖交易成规”(注:彭泽益:《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断定公所一定限制了内部竞争,垄断了外部市场,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呢?
至于那些为了控制生产规模、防止内部分化、保有经营特权的规定,似乎多存在在一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或技术要求特殊的行业中,如锡箔业、蜡笺纸业、玉器业、冶业等业中,而那些有关国计民生如米粮、木材、丝绸、棉布、纸张等生产和贸易行业就无相应的规定。即使是那些限制性行规,其实行也是颇成问题的,苏州蜡笺纸业行规规定六年准收一徒,捐足12千钱,而有戴传芝者,六年中收了6个徒弟, 而且“非惟自名下抗不付捐……反敢捏饰诬蒙请示”(注:《苏州碑刻》第103—104页。)。看起来,这样的行规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人们喜欢引用的苏州金箔作因违规收徒被同业咬死的事例,只因事主不但不听同业劝告,反而赴县禀控,称同业把持,得到县令“私立规条,本非国例,所当管办”的裁示后,更加有恃无恐,同业忍无可忍,才在“人少而利厚”的情形下作出了此极端之举,而且为首者仍抵了命(注:《申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参见黄钧宰《金壶七墨》逸墨卷二《金箔作》。)。同业把持是地方政府严禁的,所谓“把持行市,律有专条。若欲强分疆界,垄断居奇,万难准行”(注:《苏州碑刻》第139页。 )。也就是说行规必须在不违反“把持行市”律条下才算合法。因此,这样的事例没有多少普遍典型意义,不能一见行规就以为实际生活中就必然如此。
纵观江南的公所,它们是得到地方政府保护的同业组织,其创立或复设,或因应付复杂的环境,或因谋划日益急增的同业事务,或因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同业信誉,也有的为了与西方列强经济势力抗争。它们在救助同业、社会救济等慈善事业方面,在镇压工匠反抗、配合封建政府的基层统治方面,在保证产品质量、维护营业信誉、讲究经营道德方面,在整顿经营环境、抵制不法势力方面,在谋求工商发展、提倡公开竞争方面,在与列强抗争、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等发挥了各种作用。江南行业性会馆公所的不断增多,实力的不断壮大,正是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标志,它们是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促进和有利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个别行业公所在招收学徒、生产规模、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束缚了同业的手脚,不利于行业的生产和发展,但这样的公所不占主流,发挥的作用更属有限,不能以这样的公所来理解和评价江南所有的公所。江南的公所是千姿百态的,其形成时的社会背景与西方行会迥然有别,产生时间前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产生原因复杂多样,不能用举例子的方式来以偏概全,也不能不作具体分析,一见公所甚至会馆公所即认定为欧洲式的行会,更不能凭概念、凭直感,以中世纪欧洲行会的模式来准齐江南的公所。我们不能在用欧洲行会的特点框套江南的公所不符合时就说这是中国行会的特色,而在论述中国行会的作用时却又以欧洲行会来生搬硬套。从行业的角度理解,称江南的公所为行会未尝不可,问题在其性质、作用和对经济的影响,与欧洲行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极而言之,即使把江南的行业公所全部视作行会,正如有的学者论述的那样,江南的行会与西欧中世纪行会在功能与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160页。),根本起不到西欧行会那种严重阻碍生产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