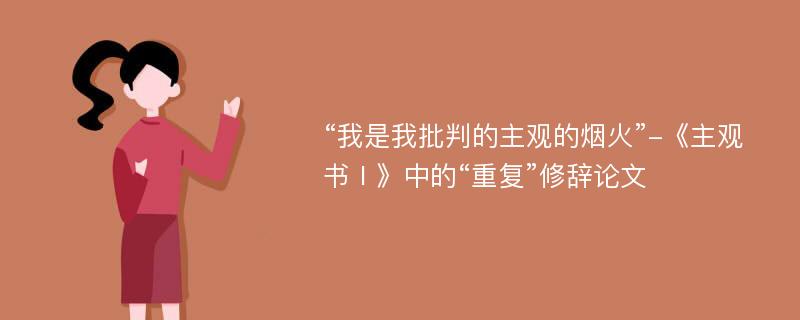
“我是我批判的主观的烟火”
——《主观书Ⅰ》中的“重复”修辞
文 〇 刘阶耳
闫文盛《主观书Ⅰ》“中卷”自《寡人只祭国与酒》以下计14篇,均从“寡人”云云,文白夹杂,话语辨识度极高;其中《关于梦境的记忆和修辞》一篇,与“上卷”中的《格调的修辞》相对读,饶有意味,很有必要。面对闫文盛“主观书”这样的巨型文本,任何异于寻常的话语症候其实都宜严肃对待,否则其话语“系谱学”属性很难确凿掌控了。
譬如说,闫文盛对尼采、佩索阿、卡夫卡推崇备至,自不待言;至于与之相颉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见之《主观书Ⅰ》似乎只有一处,从反讽的语气而讲了一句:“李白、曹雪芹、鲁迅也都是过时的”(《耻于谈论的》),可若就李白、曹雪芹、鲁迅风华标劲的文化抱负、与物神游的话语藻思、绝诣超迈的文体极境等方面来看,闫文盛所曾受益的着实一言难尽;像迄今只能在影视、戏剧中得闻其详的“寡人”云云这样的“敬辞”,竟然令闫文盛化腐朽为神奇,其实不失其一则旁证。为是我不禁联想到闫文盛为“晦涩”正名的一篇文章;且不说闫文盛出生的岁月(1978)适值“今天”诗派横空出世,因诗意的“晦涩”、“朦胧”而举国关注的“新诗潮”艰难崛起,至少对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再往前追溯,倡导“美文”的周作人有鉴于“文学革命”的成就容易滑向玲珑剔透、“玻璃球般”的明净,继而对“含蓄”或“朦胧”之类的“晦涩”情有独钟,甚至为当时因“晦涩”而遭诟詈的废名不遗余力地辩诬、揄扬,且以“文章之美”来概括其弟子不俗的文体建树,佳话一时,思之神往。熟悉这类文坛掌故,对理解闫文盛之所以也为“晦涩”正名可提供更深层次的“视野融合”的际遇或机会;至少他在文体上的恣意妄为,意欲“创造一种陌生的可能性的文体”,绝对是不忘初心,应对裕如的,毕竟“它有无数曲面,总是形义难辨。”——详见其《可能的文体(一)》。
既然在为“晦涩”正名,假如其表达失于流畅、平时,岂不贻人口实?闫文盛的这篇文章题为《晦涩:一种语言力学》尤为清俊;收在《主观书Ⅰ》的“下卷”。有感于其“语言力学”的提法,我意欲对读的前述两篇文本,其实不过是一次个案似的考察。除了“寡人”云云的14篇文本外,见于《主观书Ⅰ》的“上卷”、“中卷”,诉诸“高频词”往复循环之类的行文格式、建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胜不胜数。诚如乔治·巴塔耶所云:
行动引入了已知(制造了已知),而后与已知相联系的知性把未知的、非制造的因素带回到已知。然而欲望、诗歌、笑,不停地让生命滑入相反的方向,从已知到未知。存在最终揭开了知性的盲点,并立即消失于其中。除非在某一点上能停息下来,就不会有别的可能。不过这也没什么要紧:唯一留存的是循环往复的骚动——在迷狂中永不衰竭,又从迷狂中重新开始。(《内在经验》)
式中:x是d维设计变量,y(x)是目标函数,gi(x)是约束函数。当问题(1)的目标和约束函数值只能通过昂贵仿真得到时,通常借助代理模型以降低优化过程的仿真试验成本。
通过向杭州中院、杭州律协(调解中心)调取统计数据和向律师抽样调查(向全市13个区县的律师发放调查问卷330份,回收263份),有关情况如下:
谓余不信,不妨参照《记忆的修辞》。“我们不只不可轻信他人,也不可轻信自己(的讲述),所以,追溯往事大体是一种修辞,我们必须拼接我们空荡荡的本能去寻找一条道路,若非如此,我们又怎么理解直接无穷尽的饥饿呢?”其“本能”云云,纵使是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而运用的,那也无从掩盖闫文盛意欲命名的现代性当下交互主体性社会构建的和谐愿景。舍此无他,否则各个不同的相似所致使的“集体噤声”(《烟酒店的客人们的集体噤声》)如何克服避免?从传统的主、客二元论方面讲,人的社会化构建要么沦为目的/手段的对接,“他人即地狱”萨特式的虚无化的悲观论调即会甚嚣尘上,要么借变或不变的偶然性所滋长的投机心理则将长盛不衰;何去何从,好似无从选择,羁绊现代性伦理的沉疴的确亟需警惕呀!
相形之下,纯然白话打造的《格调的修辞》率先见到的同类“重复”极其清澈,“你一定要记得我”,且只出现了4次。从语气上看,呼吁的、“祈使”的心愿很炽烈。每次呼吁,都似穷本溯源,摆明理由,“因为你生来就记得我”,“因为你睡眠中都记得我”,“因为我们一直邂逅,反复地重复,因为你一直都没有离开我”,“因为我生来便被记得,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如是絮絮叨叨,总似“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张九龄《望月怀远》),而其诉说的终局,归结到所以“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已然记得你,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从你/我而“我们”,意犹未尽,所谓的“生活”才是最终所要揭晓的目的意向:“这不可忘怀的生活,它为何成了我们的生活?不孤寂,不完美的生活。”——很显然,“生活”云云,三次强调,意指间不胜唏嘘,是认可又质疑,反诘下无奈去认同。不过,回过头来看,先次两度“你一定要记得我”的呼吁中,“我是你”伦理角色分明大颠倒而施予的换喻之效,毋宁又都集结在过去(“一百年”)及“未来”虚度的“光阴”一面,——结尾引出的“它”,迅速跌向“生活”的命名用意就着实不致显得飘渺了。“生活”与“光阴”原本意近“形”远的意指联系诉诸这般(重复)话语的轰炸,愈陌异则愈感亲切。
想要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达到小学语文教育的理想境界,就需要教师改革教学理念,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加强课堂教学中的有效互动,同时还应积极创新传统教学模式,采取多样化教学方式,正确地引导学生,培养学生自主预习的习惯,激发学生对小学语文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创造力,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整体质量与效果,达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目标。
“寡人被噩梦惊醒”乃首句,此后展开的叙述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显著的特点:①一开始就引出的事涉“纠缠不休”的陈述句计34次高频出现,②首位贯穿的表感叹的“啊”字句,亦出现了11次,③文本收束际由关于“超越”的判断句亦出现8次,“重复”用法极其强悍,其中的“啊”字句略显特殊。从感叹的对象方面讲,首出的“压抑悲愤的梦境啊”乃孤例,但所感叹的对象由加修饰的“摹状词”给予指示。接下来行文泰半,姗姗来迟的“寡人啊”引出的感叹,与首出的那句相比,改换了感叹的方向(对象),句式也清癯了几许,类似的句式,计出现了3次;而同一对象接连8次被感叹的,很显然是由相应的“摹状词”而孔武、鹰扬的。然而类似的区分,不可或缺。
请看快结尾时这样的陈述:“寡人,是对自我之我的超越”。它(陈述)不但遥接开首的那句:“寡人被梦境惊醒”,且与文末最后一句:“寡人能够感受到陷身在被温情地化解的梦想里的超越”,有其意指“互文性”的交涉。至少从未加修饰成分的“句式”相对明净的意指属性上看,所谓的“寡人”遭命名的功能属性,俨然有其逐层深化的戏剧性功效。毕竟首尾两句,“被……惊醒”/“能够感受”经历了由“受事”而“施事”之被动/使动的转变。所以专就此而言,“寡人啊”之类的感叹,其先两次及其后一次各个所指意向还是有所区别。“被噩梦惊醒”时意识初始状态,牵连着“纠缠不休”所意指的“噩梦”袭扰之状,为惊恐,是庆幸!而“超越”相关的自我指涉一旦被明确后,重兴感叹,慨怀的莫非近乎欣悦之类的情绪体验了。
合而观之,文白夹杂的前一篇所表达的“戏剧化”处境较为隐晦;多样“重复”的修辞再节外生枝,也无从掩盖“惊醒”时“寡人”出入梦境及“当下”所觉知的心理历程。而该篇(《格调的修辞》)直接呼告之,觉知状态先期明确,“重复”被指引的强调之意,无非肇自呼告及被呼告的双方因为“不孤寂,不完美”所致的“合而不和”般极具差异性的戏剧性关联之中。诚如“记得”一词所示的本然涵义,每次相关的呼吁及祈使,无非表明相应的痛彻的体验其实存在着遗忘的可能性,也就是讲肯定性的陈述毋宁裹挟着否定性的意向,那么有关“生活”即“它”的再度反复慨叹,概莫能外,又分明警省着“存在遭遗忘”这般显而易见的事实。所谓的“格调”,难道不是和遗忘相反的“记忆”形成转喻的腾空联想吗?也就是讲,为了“忘却”的记忆,作者乃有斯作。
排练厅的低台是用红色地毯铺了面的,并不大,但因着王爷瘦,又是坐着,所以那低台仿佛在他身后空而寂寥地延伸了一大片过去。
总之把《格调的修辞》中的“人称”代词当作“物主”代词来看待,进而再将其代词“专名化”(生活),不失接近其表达蕴涵的正解。这个思路若是反向运作于另一篇“修辞”之作,同样奏效。因为作为专名的“寡人”,在文言的语境中乃“寡人好色”意味上的皇权特指,其口吻乃若第一人称,假如“先期”予以还原,恢复其“寡德之人”之本义,该“寡人”觉知的“戏剧化”处境分明又被注入了适切的深邃义涵,“自我之我”以及“超越”云云,在当下已被披上了厚重逻辑铠甲的哲学化的所指范围,不消说可以借助“寡人”相应暧昧的“皇权”专属涵义,于“传统”与“现代”交集间形成“间离”分化之效,自然会非唯所执地呼召出交互主体的鲜明现代性的意涵;所以假如从“朕即天下”之“我”的方面看,闫文盛的文白夹杂的该“修辞”之作岂非属于纯然的第一人称的宣喻?可正由于这样的“寡德之人”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现代性的怅惘则将不复是洗心革面的道德自省,割发代首,惺惺相惜了。——相对于《格调的修辞》中“你”/“我”间的人称转换,“寡人”更进一步地触及了交互主体性的命题,自不待言。
闫文盛所谓的“语言力学”何尝不是接近类似的境界?有鉴于其惯于从“高频词”中平抑其“从已知到未知”的迷狂,更何况他又对行文的话语“修辞”格外器重,——除了以下将对读的两篇“修辞”入题的文本,见于《主观书Ⅰ》的同类文本还有《记忆的修辞》 《修辞》,即为明证,那么,他“在迷狂中永不衰竭,又从迷狂中重新开始”之具体神会的想象性劳作,姑且以“重复”的修辞性名义加以裁定,也不失为接近他的“语言力学”的一条便捷通道。何况他在《诗与散文》谈及他对相应的文体的要求时还曾讲到:“而散文需要更为尖锐与突出的深度,甚至更高的旋律。”对于他“甚至”云云而言,“重复”修辞至少在满足“旋律”的形式化需要上尤其便当,毋庸讳言!“深度”云云,能否满足?下文略作发挥。
先看“寡人”云云那篇——《关于梦境的记忆和修辞》。
闫文盛的“语言力学”莫非正奠基于斯。寻常的“自我”指谓,不但“寡人”云云般“专名化”承袭的文化尘灰亟待拂拭,就连你、我、它等“代词”在断言与蕴涵上也加剧了其指称性的危机;交互主体性的社会构建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和谐与公正的基本诉求又缘何得以确切保证呢?闫文盛对“观察性写作”不屑一顾或许正是有鉴于此;他的《主观书》每每揶揄复数人称的“我们”,什么“我们都在与永恒的对抗中挽救自己。”(《我母亲意识到的永恒》),什么“我们是自己的复数,但也是最后的孤立自己的人。”(《我的反对》),什么“在简洁壮观与随俗腻烦之间,充满了我们的自我寻求和自我成就。”(《可能的文体(一)》),什么“我们需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对自身及运命的体现”(《诗与散文》)……,貌似极端、武断,其实机敏得很;毕竟他先期施予日常语言的“诊疗”功夫,使之无畏于一切“框架式生活”的约定,他的《主观书》所以也无疑于是对一切被规训的激情的拒斥。
“我因为某种激励我的鬼魄被埋葬而开始了我的无尽的长叹”(《烟酒店的客人们的集体噤声》),闫文盛如是夫子自道,洵非妄言!
汉制的真实内核,即暴力与伦理相抗衡的结果,不是暴力的伦理化,而是伦理的暴力化。汉以后的儒学不同于先秦儒学追求平等与责善,而是将等级内化于伦理之中: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下册,P499),而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4](P1158)。暴力与伦理的最终一致,是北魏孝文帝将游牧部落的绝对奴仆制规定于华夏,并在唐律中得到定型与确认。
闫文盛经年来适其所愿地打造他“主观书”这般巨型文本,莫非正是为了可“辨识的一种灵魂状态”,从而“将已知引向未知,将已知撕碎”,“去修复被滥用的语言”(《乔治·巴塔耶:《内在经验》)的。收入《主观书Ⅰ》125篇文本,语言历险,丰富而壮阔;类似的“重复”修辞为数巨多,苦心孤诣,丝毫不勉强,很显然,并非出乎偶然!
“总之,我不知道在修辞的内部会发生什么,但我以我的主观心怀向我的忧愁和达观涌了过来。我是我批判的主观的烟火。它们身上都没有诞下一个真正的沧桑者我。”(《修辞》),诚哉斯言!
